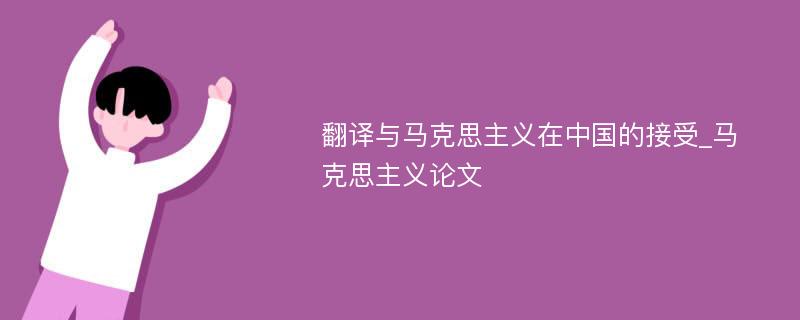
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探讨中,普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再后来,还有“植入型的现代化”这个提法。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讨论中,有一个语汇用得很多,就是translated modernity,翻译过来就是“翻译的现代性”、“被译介的现代性”。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几员大将都是由海外留学归来);二是中国人最早的现代性体验是与翻译西方的生活词汇、科技术语、文学话语等活动交融在一起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翻译的现代性”势必要讨论“翻译的马克思主义”。
人们通常以原语和作者为中心,以译作是否忠实原语来评价译作的优劣。所谓忠实,简单说来,就是不增添什么,不减少什么,不改变什么。这种以原语为中心的翻译观为原文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经典/权威地位,并预设了原文有一个统一确定的客观意义,认为只要有“理想”译者的存在,就可以产出一个与原语完全“对等”的译本来。为产出一个“对等”的译本,译者最好是文化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各学科的专家,精通双语,精通双语文化,精通转换技巧等等,总之译者必须是全才,能人,是神。[1]其实,李伯元的《文明小史》(1905)早就颠覆了这个神话。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译者和编辑辛修甫。据说他有一本秘笈,收集了从外国书籍中学到的词汇名称,无论多么晦涩难解的原著或翻译,辛先生“取出他那本秘本来”,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李伯元通过这个人物提出疑问:难道世上真有一本秘笈,能够轻易地把所有的语汇、观念、知识转换成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吗?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劳航芥,曾在日本和美国接受法律训练,并在香港工作过。安徽总督需要一名传译员,劳先生欣然受命。一个法国副领事到安徽访问,劳先生硬着头皮不懂装懂,把领事说的话瞎猜了一通。总督很是不满和不解:这西方在地理上、语言上不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吗?他根本不了解,西方的众多语言参差不齐。或许,这正暗示出西方的科学、风格和价值系统多元驳杂,单一的“现代性”并不存在。[2](P253~263)
“忠实对等”这个翻译标准具体到语汇上,就是寻找对等词。人们相信:它是可以找到的;它是原本就存在的。至于为什么原本就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共同人性,同一个宇宙,等等。坚持等效翻译的学者当然了解,说到具体的词,如果是脱离上下文的具体的词,两种语言之间却又很少对等的关系,我们头脑里的很多“A=甲”的等式,和外语学习初期的“记单词”方法很有关系。[3](P87)坚持等效翻译的学者也很熟悉,文化与词汇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在不同社会中生活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同的分类标准,这是不同语育的特征之一。这就造成,在翻译的过程中,有直译和意译之别,有词量的增减、词类的调整、意群的调整、译词的多样化、非动词化等等。尽管如此,坚持等效翻译的学者还是努力探讨词汇对应的若干类型,试图通过灵活用词来确立和实现对等关系。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文论界和译界开始认识到,孜孜以求地探索对等词固然重要,不过,更需要追问的是,当一个外文词在汉语固有的词汇中找到对等词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出于翻译的需要,新造一个汉语词汇以示对等时,又发生了什么?“忠实对等论”最大的问题,是在把话语透明化的同时,抹去了翻译的政治性和历史性。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的就不再是“首先考虑词语的对等,而是要研究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是对等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考虑,使译者这样译或那样译;译者那样译试图达到什么目的;又是否达到了目的;为什么说达到了,又为什么说没有达到”。[4](P166)这些才是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
当代的翻译研究表明,译者既是读者、作者、改写者、研究者,同时也是调节者、征服者、代言者、权力的运作者。[5](P59~87)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工作,它与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围绕应该“译什么”以及“为什么译”等,曾经展开过争论。[6]当代英国的描述翻译学认为,翻译远不止符号间的过渡,每本译作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任何对翻译实践的描述和切实可行的解释都离不开其固有的语境,即“谁在何种情况下为谁翻译什么内容、何时翻译、怎样翻译、为什么要翻译以及有何后果。”[7](P307~308)
马克思主义并不源出于中国和东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翻译而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五四以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之所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因为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无论是革命文学或是革命理论著作,在那个时候主要是靠翻译。翻译工作者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达到翻译和理解的准确,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毛泽东曾经讲过,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功不在禹下。①尽管以往围绕翻译也曾有各种各样的讨论,②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误译”的苛责,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在严厉的批评者看来,诸多“误译”数十年间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的混乱之大,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之巨,是很难形容的。③翻译的是非曲直当然值得理论,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争论产生的背景、时机和情景。在我们看来,所有的争论和探讨本身,都是时代规划的有机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首先应当关注的,是译介的历史契机和具体环节。
1.节译和摘译。《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是以节译或摘译的方式,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如果说节译或摘译可能使中国读者无法领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貌,在理解上有断章取义的可能,那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的先后次序,不同于其本身写作的次序,这也可能会构成一个新的理论脉络和空间形象。
2.转译。古今中外,转译并不鲜见,如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大多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从各种西域语言(胡语)翻译过来的。晚清时期,中国留日的学生居多,懂得日语的也最多,所以当时许多西方小说都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大抵也是如此。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原文,他们最初所接触的,大多是经过日文转译而来的文本。1930年代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经由俄文系统转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如果我们承认语言负载着文化意义和历史经验,那么,就应该关注,在转译的过程中,日本和苏俄的文化意义和历史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锲入了汉语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
3.复译。在中外翻译史上,复译是很常见的一种译作类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复译也是很多的。复译当然是出于精益求精的考虑,除了这个一般的、通常的因素之外,就文学作品而言,不同时期翻译方法的差异,现代汉语的不断发展,是复译不断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说,复译本的不断出现,更多的是出于理论理解的深化,这尤其体现在对等词的选择上。
4.对等词。让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进入汉语世界,需要为其找到恰当的汉语对等词。[8] 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不是一开始就被译为“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和“共产主义”作为Kommunismus的对等词也是经历了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现在的译法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对“Ein Gespenst”曾有过多种翻译方案:“鬼”,“鬼怪”,“妖怪”,“幽灵”,“怪影”,“幻影”等等。“umgehen”的译法也不少:“游荡”,“徘徊”,“出没”,“闹鬼”,“转游”等等。早在延安时期就和徐冰合译《共产党宣言》的成仿吾,垂暮之年独自重译,把“幽灵”改为“魔怪”。[9]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可谓是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境界的升华,尤其表明了确立对等词是何等的艰难,需要怎样的小心翼翼。
翻译作为阅读和阐释,是一个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语汇和思想会“归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会“规训”既有的思想和习惯。翻译的场域充满争议和协商。在极端的情况下,翻译就是一种改写,即由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影响,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符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便于其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一些学者业已认识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后者中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同或相近的先天素质;而马克思主义一旦在中国落户,也必然要被迫改变自己的形式,从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0]如革命作为Revolution的对等词,一方面,它从传统中获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世界革命”意识的引进和融合,它变得错综复杂,富有包容性,因而能在急剧变动的时代适应政治、经济和心理的变革的需求。[11]
通过我们有限的考察,至少有三点体会:
第一,就主旨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是晚清以来浩大译事的有机延续。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在汉语中的“安家落户”,也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相关对等词的选择和确立过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在20世纪中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简言之,它促成了时代的规划和主体的召唤。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封建”概念。中国本原意义上的“封建”指称的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只是一种“政治事件”,至多不过是一种“政治制度”。直到19世纪中叶,它和西欧的“Feudalism”还毫无瓜葛。后来,先是日本人,继之是严复,将“封建”一词用作形容词,并将其作为“feudal”的对等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封建=前近代=落后”,此后,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大革命后“现实中国半封建说”逐步确立,频频出现于瞿秋白等中共理论家的著述中,尤以1928年中共六大文件表述得最为完整。30年代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获得知识界的广泛认可,泛化的封建观普遍流行开来。[12]在翻译的过程中,一系列“主词”在汉语世界中应运而生:人民、农民、无产阶级,共产党,等等。这些“主词”召唤了主体的诞生,进而强有力地引导和造就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
第三,依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P534)我们充分认可这一观点的权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是指它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这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补充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化”的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的概念和原理在中国得以具体化,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实践则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和价值。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何以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和感召力。
注释:
①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翻译一度被视作教条主义滋生的根源。设在马列学院的马列著作编译部被撤销,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被指斥为“教条主义典型”。后来毛泽东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参见李魁庆:《历经沧桑淡泊名利——缅怀潮籍外交家、翻译家柯柏年》,载《汕头日报》2005-06-05。柯柏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理论思考,可参见柯柏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问题》,载《翻译通讯》1951年12月第3卷第5期。
②例如,罗书肆:《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译本》,载《翻译通讯》1950年第4期;谢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译文中的一些问题》,载《翻译通讯》1951年第1期;赵少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载《翻译通讯》1950年第4期;赵俪生:《略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译本——兼及“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张译本》,载《翻译通讯》1950年第4期。
③诸如“公有制”还是“社会所有制”,“所有权”还是“所有制”,“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出版自由”还是“新闻出版自由”,“党的文学”还是“党的出版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