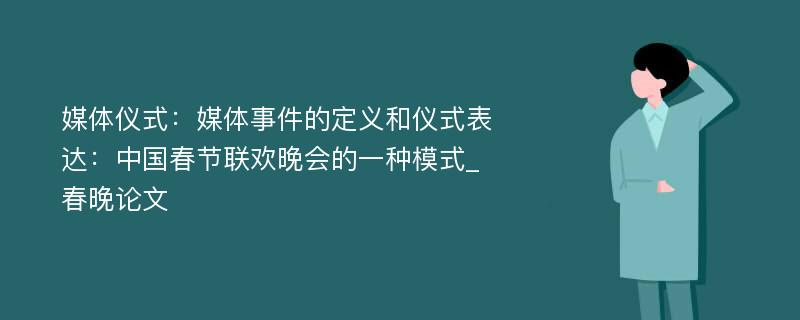
媒介仪式:媒介事件的界定与仪式化表述——以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为范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仪式论文,范本论文,春节联欢晚会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2009)04-0006-04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媒介事件”作为一种新颖的电视样式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全球有近2亿人在1969年同时目睹了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壮举;1981年英国皇室为查尔斯与戴安娜举办的婚礼则在79个国家现场直播,观看的人数超过5亿……而在1999年岁末,全球几十家电视台联合现场转播的24个时区中,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继跨入2000千禧之年的盛况,更是吸引了几十亿人的目光。这些经由电视媒介传播的历史性事件,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众多观众进入“空中”的“历史的现场直播”,经历了“一种不在现场的‘现场体验’”。[1](中泽本序2)媒介事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种“虚拟的真实感”,它还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参与式的仪式感”,可以这么说,媒介事件被策划、传播以及收看的过程就是一场“媒介仪式”的举行过程。
一、媒介事件的界定
一般说来,“媒介事件”这个概念包含着以下几种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媒介事件就是那些经由媒介传播的“假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所著《形象》一书中提出“假事件”概念,他将假事件界定为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并指出了假事件具有人为策划、适合传媒报道等特征。他把诸如记者招待会、大厦剪彩、游行示威乃至候选人电视辩论等事件都归入“假事件”之列。[2]韦尔伯·施拉姆对这一现象使用过“媒介事件”的概念来表述。他认为媒介事件“主要是制造出来供传媒作报道的事件”,并且重点讨论了为各种竞选服务的媒介事件。[3]施拉姆所说的媒介事件,实质上就是布尔斯廷提出的假事件,是由政治利益集团制造的假事件。[4]
对于“媒介事件”概念的第二种理解出自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媒介事件》一书,在该书的开篇作者就提出了“媒介事件”的含义:“本书讲的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1](1)这一理解从文化的角度讨论宏大事件的电视直播,专指电视媒介中的重大事件。
对于媒介事件的理解与阐释,我国大陆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5]:有的主张将其限定在戴扬和卡茨所界定的“特殊电视直播事件”的范畴内,反对将媒介事件过度泛化;有的主张比较宽泛的理解,把媒介事件不仅仅限于伪事件,而是将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事件通称为媒介事件,不管它是人为制造的伪事件,还是自然发生的真事件。
在本文中,笔者还是比较倾向于对媒介事件的具体的微观理解,认为媒介事件就是那些“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但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电视中的媒介事件的进展过程中,并不排除其他媒介对该事件的传播。比如,一场由电视直播展现的政治竞选,仍然可以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拓展其传播渠道,以获取更多的受众,但这并不影响这场竞选的“媒介事件”性质。
二、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
媒介事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电视上一幕幕的宏大画面和解说词里一句句的煽情演绎,它为观众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感觉和体验,是一种感情上的融入和心理上的寄托。媒介事件运用一个集体性的体验,带人们进入了神圣的仪式过程,社会整合和文化认同由此实现。在分析媒介事件如何向媒介仪式转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仪式的具体含义。
(一)仪式与媒介社会
1.“仪式”概述
“仪式”的定义灵活而广泛,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对仪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比如,在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和意义范畴内,仪式首先被限定在“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这一基本表述上。广义上说,仪式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从“你好”等日常问候的礼节到天主教弥撒的隆重仪式。[6](12)从语义学来说,仪式是“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动”。[7]早期的戏剧性分析的倡导者使用“仪式”一词时,依据的是公开确立的仪式活动的原有意义。他们主要将仪式视为沟通和维持群体传统活动的途径。[8]
此外,不同的学者对“仪式”的描述和侧重也有所不同。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利奇是广义使用“仪式”的代表人物,他将仪式本身看作一种“信息”,而信息的不断重复和传递形成“仪式”,在他那里,言语(祷词、咒语、圣歌)如同手势动作和物器使用一样都具有仪式的特征和价值。特纳则相对缩小了仪式的范围,认为仪式只属于概述类行为,专指那些随着社会变迁、具有典礼的形式,并发生于确定特殊的社会分层之中。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主要偏向于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和结构,“神圣/世俗”的关系和行为被看作二元对立的基本社会分类和结构要素。[6](12)而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人类和象征是紧密相连的,人类依赖象征和象征体系,以至于这种依赖决定着他的生存能力。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成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9]
2.现代社会中的“媒介仪式”
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的代表”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一种仪式性的传播模式。他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一种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0]这一模式突破了当时主流的传播的“传递观”,强调传播在共同信念的表征和社会的维系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此,有关媒介仪式的议题逐渐进入到了众多传播学者的视野,许多有关媒介仪式的解释也不断涌现。
所谓的媒介仪式,就是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活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9]还有一种对媒介仪式的普遍理解,就是将如今普及率最高的媒介——电视,作为引发媒介仪式的主要场所和媒介,将受众观看电视中的直播事件作为参与媒介仪式的主要手段,由此将媒介仪式定义为: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被邀请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最终呈现的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11]不难看出,以上两个有关媒介仪式定义中的“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和“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即是指“媒介事件”。
(二)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的关系
1.媒介事件是媒介仪式的发生主体
媒介仪式是“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被邀请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即媒介事件),最终呈现的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由此可见,媒介事件是媒介仪式形成的前提和主体,没有媒介事件的预先组织和播出,就不会有观众的关注与参与,也就更不可能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
媒介事件强调的是事件本身,即它的呈现和播出形式;而媒介仪式则强调的是观众的参与行为和实践过程。前者是静态的陈述,而后者则是动态的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了更为真切地了解媒介仪式的运作过程及其对观众的影响,对媒介事件的先期观察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2.媒介仪式是媒介事件的“仪式化表述”
媒介事件经过策划、播出和收看之后,为何能够成为神圣而庄重的媒介仪式?这主要是由于媒介事件的呈现过程中具有许多“仪式化”的特征,换句话说,媒介仪式其实就是媒介事件的“仪式化表述”。正是这种“仪式化”的呈现方式,才使得以媒介事件作为主体的媒介仪式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仪式化”是一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格鲁克曼早在20世纪中期就使用这一概念,以指示在仪式中个体化角色之于社会活动中的神圣关系和社会地位。[6](6)而本文中所涉及到的“仪式化特征”则同这一仪式化解释有所联系,主要是指媒介仪式中的个体或群体角色和行为在“媒介事件”转化为“媒介仪式”的过程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和起到的重要作用。
当然,各种媒介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仪式化特征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媒介事件,在不同的策划、播出和收看阶段也具有许多独特的“仪式个性”,为此,需要真正了解媒介事件是如何转变为威力无穷的媒介仪式,一个典型案例的选取必不可少。
三、“春晚事件”中的仪式化特征分析
显而易见,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的电视直播事件,它不仅具备媒介事件的“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1](11),还具有媒介仪式的“盛大性、神圣性、庆典性和融合性”。为此,每年的春晚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一件典型的媒介事件“仪式化”后产生的重大的媒介仪式。从春晚的组织、播出和收看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媒介事件是如何进行必要的仪式化表述的,又是如何运用种种仪式化的特征吸引和影响观众的。
春晚中具体的“仪式化表述”并不显现于这场文化表演的表面,而是隐藏于春晚筹备、进行和结束后的各个环节之中,体现于融入春晚的各类群体的具体行动之中;这些不同群体在春晚中所表现出来的仪式化特征是春晚备受关注的深层动因,也是推动春晚不断前行、不断延续的巨大动力。
(一)“春晚事件”的筹备——“国家符号”的植入阶段
在传统的民间社会里,仪式中的“国家符号”并不十分明显,随着现代国家的影响力日益浸透、深入、扩大到民间社会,仪式中的“国家符号”也就越来越多。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始于1983年,最早是以“电视观众大联欢”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为此,由它产生出的媒介仪式既不属于传统的民间仪式,也不属于对民间仪式的“改造”,而是为了适应社会现状而产生的一种“新编”仪式类型。既然是一种“新编”的仪式,春晚必定有其特定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我们知道,我国的春晚往往被冠名为“央视春晚”,它是一个由我国的中央电视台策划和举办的一台迎春综艺晚会。表面上看来,春晚的组织者是中央电视台,而策划者是其总导演。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春晚的前期流程就可以看出,在央视和导演身后,广电总局、各级领导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所代表的就是那个伫立在春晚背后的看不见的巨人——国家。
每年春晚总导演的选拔被戏称为“三进宫”,首先导演们首先开始筹备标书,然后在编委会上抽签排序,逐个阐述自己的投标方案。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编委会针对每个导演的投标书,报送国家广电总局,最后总局下达文件,公布“花落谁家”。
央视春晚的节目内容每年要经历的几乎都是“六审六彩”,六次审查和六次彩排,当然,这也并非绝对的,审查也未必有确定的次数,可能是六次,也可能五次、七次。每次负责审查节目的名单中,总导演都要排在十几名,前面全是各方面的领导,审查节目时毫不留情。虽然每次审查都会带观众,“但节目的去留并不是以他们的满意度和笑声来决定,观众的反应在审查时丝毫不影响结果。”[12]
从春晚总导演的选择,到春晚节目的审查和彩排无不充斥着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和国家权力,而节目的策划也紧紧扣印着那一年的国家大事和主旋律。春节民俗,或者说晚会的狂欢性质被消解了,它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象征色彩,民俗符号、身份象征、历史召唤共同组成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家/国辉映的结构,同时传达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共同的心声”。[13]由此可见,春晚这一媒介事件自其组织和策划伊始就有其“国家在场”的“仪式化”特征,它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现代政治生活和权力的运作与基于大众传媒的媒介仪式息息相关,这在仪式的组织与策划阶段就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晚事件”中的国家在场,为其提供了一个统一而神圣的仪式主题,那就是牢固的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和民族自豪感。尤其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以“儒家大一统”为基础和历史的东方大国来说,与生俱来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情感模式,也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前行的重要精神动力。为此,在春晚这一特殊的媒介事件中注入“国家”元素,既显得贴切自然,也为观看春晚的受众找到了共同的感情基础,有利于民族情感的激发和爱国热情的传延。
(二)“春晚事件”的表达——文化表演与角色展现阶段
我国历年春晚都是以综艺性文艺晚会的方式同观众见面,以一种系列性的“文化表演”的形式进行主题的展现和表达。在当代的文化研究中,辛格首先使用了“文化表演”的概念,用它来概括人类社会文化在演变过程中的诸多历史形态和传统,并由此引出了“文化中介”的相关内容。“文化中介”是一种交流方式——不仅包括人类的语言交流,而且包括非语言性的交流,如歌舞、行为、书法及造型艺术等,或融合了多种艺术要素的交流性民族、族群文化,如印第安文化等。[14]由此可见,春晚是一个系统的“文化表演”体系,它运用多种“文化中介”,包括语言性的(如小品、相声等)、非语言性的(如歌舞、魔术、杂技等)方式表达和表现一定的主题和历史传统。
当代最负盛名的仪式研究者,表演人类学家特纳使用了“社会剧”(social drama),以强调仪式的表演性。春晚“社会剧”具有以下特征:无论是歌曲、舞蹈,还是相声、小品,春晚的各类节目最初都是来源于大众生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总结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这些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文化表演”性质的仪式内容拉近了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距离,观众能够通过自身理解与表演者建立交流和对话意义;春晚中的各种表演又不是单纯的娱乐性表演,每一个节目都负载了一定的主题和思想内容,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各种国家大事、社会矛盾、人生百态等现象都被融入至春晚的叙事内容之中,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简洁、直观但涵义丰富的媒介仪式的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总之,春晚的具体内容,即“文化表演”也是其“仪式化”特征的一种表现,这种常见的表演内容为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媒介仪式的表达方式。
在“春晚事件”的表达方式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那就是春晚演绎主体的“仪式化”特征。具体说来,在春晚这一重大的媒介仪式场合中,主持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承担一般晚会上所没有的角色,他们要同老百姓一起过年关,因此,主持的语境、语言、词语都具有特殊性。在古老的宗教仪式中,主持仪式者大都属于世俗社会的领袖和头人,同时他们又是“通神”、“通灵”之媒,具有“人-神”的身份。当传统仪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各类非传统的“新编”仪式重新定义了主持者的地位和身份,但无论怎样变化,仪式主持者都起着充当仪式中介、控制仪式进程的作用,他们的角色和能力都具有“公共性质”,是被“集体”赋予的特殊行为。[6](90)春晚的主持人们构成了那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当权者”和“执事”,是整个仪式现场的中心和核心,能够起到节目串联和锦上添花的作用,他们的行为和表现充满了“仪式化”的特征。
此外,那些被选为春晚表演者的人员,也属于仪式演绎的主体,策划者将其表演进行特殊的改编和排序,以更好地表达其表演主题或表现某种特别的情感。无论是对于“春晚事件”中的主持者,还是表演者而言,由电视媒介传播的这场媒介事件都是一场人生中的“通过仪式”。根普纳的“通过仪式”树立了仪式内部进程分析的里程碑,将“仪式中的社会”作为研究重点,它使人们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暂时脱离出来,进入并经历一系列的仪式活动,然后重新聚合到社会结构中。经历这一仪式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将获得“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稳定的或反复性的文化认同。[15]部分群体或个人(春晚的主持者和表演者们)获得了参与媒介仪式的机会,即在现实世界与媒介世界之间穿梭转换的机会,他们在重返日常生活秩序之时,社会身份和地位往往有所提升,既有的文化认同也得以巩固。[16]春晚这一媒介事件对于参与其中的主体人员来说,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国家仪式、民族仪式的内涵,而成为了人生中重要的“通过仪式”或“就职仪式”,成为了许多演员们追寻一生的梦想。当然,与此同时,他们在仪式中也会受到其他社会成员或仪式观看者的严格的价值考量,仪式主持或表演中的一个小错误都会遭受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由此可见,将春晚置于演绎主体自身成长和生活的轨迹中理解,也脱离不了其显著的“仪式化”特征,演绎主体的选择也成为了“春晚事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春晚由此增添了不少吸引力。
(三)“春晚事件”的观看——社会化控制的显现阶段
有文化学者为春晚辩护说:“观众的心态需要调整,你就应该把春晚当成一个伴随的伙伴,而不能觉得这个年就靠它过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会很失落。”[17]无论是将春晚当作“一个伙伴”或是“纯粹的寄托”,我们都能隐约感觉到作为媒介仪式的“春晚事件”之于其观众的“强制性”。媒介仪式中的“强制性”并非现代社会中带有国家权力性质和机构的“强制性”。相反,观看和参与春晚是个体“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任何社会总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秩序,而维持社会秩序就必须借助相应的社会价值和实践形式,仪式便是二者的结合体。每个人都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社会里,在所谓“面对面的社群”中,个体生命和生活的存续有赖于一个社会秩序的维系,个体的意愿必须满足社会整体秩序的存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仪式也就具有“强制性”。[6](72-73)也就是说,即使你不参与或不观看春晚,但是你不能背离春晚的所传达的“主流文化意志”,也不能阻止他人谈论和评价春晚,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样的秩序和原则,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媒介仪式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
与将仪式视为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文化展演,强调仪式的符号与文化内涵的现今研究取向不同,早期的宗教现象学者以及宗教历史学者主张仪式是表达宗教信念的媒介,他们强调仪式的整合力量与控制力量,同时将仪式视为调节社会生活的工具。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参与春晚的观众也就成为了被“整合”、“控制”和“调节”的对象。春晚在表面上为我们带来的是一场以庆祝和娱乐为主的文化表演和媒介事件,但既然我们在其组织和策划中看见了“国家在场”的痕迹,那么大多观众对具体表演的理解也都会采取“主导”的方式进行解码,即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将理解置于“主流文化意志”的框架中,同时受制于“媒介仪式”的宏大主题。
此外,观众不仅在观看春晚之时,被其中的主流文化意志和政治意志、国家意志所控制,就连春晚结束后,也会被媒体铺天盖地的主流赞扬式评论所影响,而且几乎不受负面评价的影响。观众完全被融入和沉浸在春晚这一媒介仪式所带来的整合和控制的力量当中,个别的“对抗型”评论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春晚以其巨大的魔力使观众深陷其中,并成功地将全体观众“仪式化”,崇拜、敬仰、热忱的仪式参与心理随处可见,媒介仪式的社会控制力量展露无疑。
四、结语
媒介仪式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媒介事件,而媒介事件的种种仪式化特征又是其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来源。春节联欢晚会是我国典型的媒介事件,对其进行性质的界定和仪式化分析是找到其巨大影响力的根源。本文即是以此为例,展现和分析具体媒介事件与相应媒介仪式间的紧密联系,以期引起学界对此类问题的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