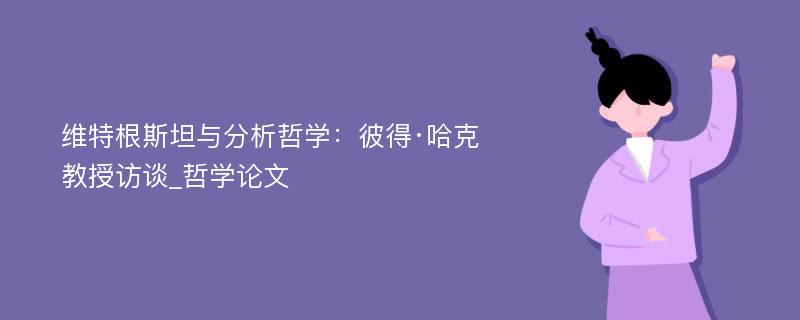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访彼得#183;哈克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彼得论文,哈克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4)02-0021-05
问:在《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注:Peter Hacker,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Blackwell Publishers,September 1996.)这本书中,您认为,维特根斯坦对20世纪分析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这既包括其前期哲学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也包括其后期哲学对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您认为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的发展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答:我一直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维也纳学派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他对剑桥的分析学派影响极大。1929年重返剑桥之后,通过他的教学及其培养的许多著名学生,使他成为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物。随着1953年出版的遗作《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开始在此后20或25年分析哲学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我认为,是他首先发起了分析哲学中的所谓的“语言转向”,《逻辑哲学论》朝着这个转向最先迈出了大胆的步伐。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认为,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才能探讨事物的本质和特性。接着,他要求放弃所有有关哲学的“崇高性”的观念,即哲学是探讨独立于语言和心灵的世界本质的哲学概念。其后期的哲学方法就是澄清语法的方法,这是他后期哲学的主题,即为了消除哲学问题而对我们语言的逻辑—语言结构进行描述。因此,或许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哲学方法完成了他所发起的语言转向。维特根斯坦曾一度转变了主流分析哲学中的一般哲学概念和哲学方法,尤其是英国的分析哲学,当然也不仅仅限于英国哲学。他也改造了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影响衰弱了。他在语言哲学中所倡导的思想和方法被一种努力寻求关于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取代了。维特根斯坦认为,普通的哲学观念是一种有助于人类理解,而不是为了增加人类知识的阐明性活动,这种哲学观念也为那些信奉与自然科学结盟的认知哲学观念的哲学家们抛弃了。
问:在您的著作以及收录在克洛克(H.J.Clock)编的《维特根斯坦评论文集》中的《哲学》一文中,您谈到了对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误解。这样看来,似乎有两种维特根斯坦的形象,一种是您眼中的维特根斯坦,另一种是其他研究者眼中的维特根斯坦,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同时也希望,我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能够与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如冯·赖特、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肯尼(Anthony Kenny)的研究取得普遍的一致,能够与一些较年轻的哲学家如克洛克和舒尔特(Joachim Schulte)等人的研究达成一致。我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一些微小的细节,我认为基本的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对维特根斯坦研究中的实质性分歧,是我和当前美国的维特根斯坦学派之间的争论,他们自称为“新维特根斯坦派”。他们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是由已故的波士顿大学的伯顿·德雷本(Burton Dreben)(注:伯顿·德雷本(Burton Dreben)(1928~1999),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弗吉尼亚大学的科拉·戴蒙特(Cora Diamond)(注:科拉·戴蒙特(Cora Diamond),弗吉尼亚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研究维特根斯坦、弗雷格、语言哲学、道德和政治哲学、哲学与文学,代表作有《实在论精神: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心灵》(The Realistic Spirit:Wittgenstein,Philosophy,and the Mind)、《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讲稿》(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等。)提出的。而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注: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1958~),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美学等;对维特根斯坦、康德、尼采、克尔凯郭尔、詹姆斯、弗雷格、卡尔纳普、普特南、罗蒂等人颇有研究。此人乃新维特根斯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新维特根斯坦派的年富力强、孜孜以求的后继者,他发表了大量作品来维护由德雷本和戴蒙特提出的对维特根斯坦的诠释。其他一些美国学者也加入了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而且,在英国也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个学派。新维特根斯坦派往往对《逻辑哲学论》感兴趣。他们强调,这本书的结束语表明,整本书的内容都应当被宣告为是完全无意义的。他们认为《逻辑哲学论》的目的完全是治疗性的,从而在《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间存在更多的连续性,这远比所谓“标准解释”所愿意承认的连续性要多;而我往往被看做是这种标准解释的主要代表。他们声称,《逻辑哲学论》的目的在于治疗书中前半部分所描述的那种致力于形而上学反思的倾向。而这种反思是无意义的,看和显示之间的区分也是无意义的。因此,在他们看来,《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并不是说此书所力图说的东西本不可说,而只能被经验命题的形式显示出来,相反,这种思想也是没有意义的,是要被抛弃的。
问:您不同意新维特根斯坦派的这种观点吗?
答:我的确不同意这种看法。针对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解释我写过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对《逻辑哲学论》的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注:“Was He Trying to Whistle It?”in A.Crary and R.Read eds,The New Wittgenstein Routledge,London,2000,repr.with Modifications in P.Hacker,Wittgenstein:Connections and Controversies,Clarendon Press,Oxford,2001,pp.98~140.)我给出了两个方面的批评,第一方面的批评涉及这种解释与《逻辑哲学论》本身是否一致。我试图表明,《逻辑哲学论》结尾的评论之所以认为书中命题是无意义的,其原因在于:这些命题本身正是《逻辑哲学论》整个论证框架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如果这些命题本身是无意义的而加以放弃,那么就没有理由来指责整本书是完全无意义的。但是,如果这些命题具有说服力,那么随之而来的其他论证也是可以接受的了。另外,在新维特根斯坦派的解释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在矛盾。
我的第二个批评(注:“Wittgenstein,Carnap and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ians”,Philosophical Quarterly,53,2003,pp.1~23.)涉及到维特根斯坦自己对《逻辑哲学论》的评论,包括1914年之前、构思此书的那段时间、一战之后1919年到1921年间,以及后来的评论这四个时期。他在后期著作中对《逻辑哲学论》做了许多批评,一再指出他在写作那本书时这样那样的思想是错误的,而且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新维特根斯坦派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维特根斯坦从来就没有犯过这些错误。因此,维特根斯坦必定要匪夷所思地忘却1919年之后的所有思想以及这本书的写作目的,而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的第二篇文章针对的是柯南特的观点。他区分了“严格的”无意义概念和“实质性的”无意义概念。实质性的无意义概念认为一个无意义的语句是由有意义的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的意义并不“连贯”(cohere),因此,这样的语句被认为具有一种作为无意义(nonsense)的意义(sense),或者说表达了一种无意义的思想。柯南特指责卡尔纳普持有的这种无意义的概念,而且进一步认定我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无意义概念是这样的:无意义的语句的惟一错误在于,我们没有赋予这些语句中的某些语词以意义。最重要的是,柯南特还认为,所谓无意义的语句违背了逻辑句法或语法的规则,这种思想与维特根斯坦风马牛不相及,恰恰源自卡尔纳普和我自己的误解。但我在文章中表明,卡尔纳普根本没有接受所谓的实质性的无意义概念,他明确批判任何这种思想。卡尔纳普不认为无意义的语句是由没有意义的语词构成的,这话没错;但他确实认为在这样的语句中语词被误用了,这些语词以违背其使用规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些语词的结合方式即语句是没有意义的。卡尔纳普向来认为无意义的语句只不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语词的一种形式,这样的语句应被排除在语言之外。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接受“实质性的”无意义概念,甚至自30年前出版第一部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以来,我一直反对这种被误导的思想。维特根斯坦当然认为无意义的语句违背了逻辑句法或语法的规则。
问:您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最大遗产是他的新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我理解这是一种从追求真理到追求意义或理解的转变,这种新的方法能够提供清晰的表达。您认为这是维特根斯坦所开创的新哲学的核心吗?
答:我打算清楚地阐明1929年维特根斯坦的新哲学形成之后其方法的核心。哲学总是以问题为特征的,这些问题不是经验的、科学的问题,不能通过实验来解答,也不需要新的发现,这些问题通常是关于事物的本质或特性的问题。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的典型特征在于寻求意义,它们产生于某些概念的不清晰;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澄清概念来解决,或者通常被消解。那么,这是如何产生效果的呢?
这主要是(但不是惟一的)通过认真地描述语词的使用来澄清概念,解决哲学问题。当然,描述语词的使用是语言学家的工作,但哲学决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那么这两个学科的区别何在呢?它们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不同,所关注的语词使用的角度也完全不同。传统语法(语言学)注意到及物动词后面要跟宾格表达式;但哲学的关注更类似于如下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可以将“……的西南”这样的语词用作“北极”这个指示词的前缀(否则就是在胡说)。因为哲学关注意义的界限,从而澄清由于界限而产生的问题,或者因为越界而出现的问题。当我们能够说明所问的问题中存在的误解,许多(但不是全部)哲学问题就不是被解答(answered)而是被消解了(dissolved)。例如,我们习惯于问“心身关系是什么?”或“心脑关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心”(mind)这个语词的使用时,我们会发现心并不是能够存在于心身或心脑的任何关系中的实体。同样,哲学家总是想知道逻辑命题描述了什么,或者数学命题描述了什么。弗雷格就认为逻辑命题描述的是思想之间最普遍的关系,它与所讨论的思想的内容无关;他还认为算术命题描述了数与数(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但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认真研究逻辑和数学命题的使用可能会使我们认识到这类命题并没有描述任何东西,它们具有十分不同的作用。
哲学方法是描述性的,其目标在于消解概念困扰和概念混乱,并且阐明概念的类型。哲学的成就通常是认识到某个概念更类似于属于这个类型的概念,而不是属于其他类型的概念。例如,理解(understanding)更类似于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说,某个概念并不属于其表面上归属的那个范畴类型,例如,意谓某物(mean something)并不是一种行为或活动,看到一种心理意象不是一种知觉形式,相信也不是一种精神状态。
但是,在此需要注意,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来源于我们语言的那些令人误导的特征,也有许多其他的引发概念混乱的原因。我们总是为科学和科学方法所迷惑,因此,总是试图在哲学研究中模仿科学的程序。例如,当我们使用所谓的推理来解决“他心存在”的问题时,就已经把他人存在这个命题当做了一个假设。我们在强大的科学信念的驱使下进行归纳,而归纳是科学中最重要的理智特征,在科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将各种各样的现象归于一个法则或解释理论之下;但在哲学中,这种归纳的特征可能就是引发大量混乱的来源,从而使我们歪曲了概念现象,在只适合于特殊性之处寻求普遍性。
问: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描述语言的使用来消除哲学问题,因此,他试图将语词的形而上学使用转变为日常用法。但在日常语言的用法中似乎也存在着大量误解,那么,如何能够通过描述语言的日常用法来消解哲学问题呢?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种误解。我们应当区分日常的、标准的语词使用与不标准的、隐喻的、比喻的语词使用以及对语词的误用;而且我们应当区分日常的语词和非日常的专门术语,当维特根斯坦讨论有关名称和意义的问题,或者有关思维和想像问题时,他关注的是日常的非专门术语。但是,当他在《哲学语法》的数学哲学中讨论超穷基数、有限和无限集合之间的关系以及狄德金分割(Dedekind cuts)时,他所考察的就不是日常的普通语词,而是高等数学中的专门术语。但他所关注的这两种情况都表明,无论是日常语词还是专门术语,当所讨论的语词被误用时,我们就陷入了混乱。
认为在语词的日常使用中也有许多误解,这容易引起误会。语言中日常表达式的日常使用所说出的东西可能包含许多误解和错误,但是,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词的日常使用的兴趣并不是日常用法所说出的东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只关心什么使语词有意义,什么使其无意义。他关注的是语词的使用规则以及确定意义的规则,而不关心人们在街头巷尾使用日常语词所说出的话是真理还是谬误。维特根斯坦并不像摩尔那样是所谓常识的辩护者。的确,他并没有维护任何这样那样的经验信念,而是试图描述意义的界限,从而阐明由于违背这些界限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和困惑。
问:您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新哲学方法是哲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吗?
答:我想可以这么说。康德认为其批判哲学的特征在于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维特根斯坦对必然命题的本性的阐释掀起了又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维特根斯坦认为,先天命题看上去是描述了实际上事物之必然所是,但实非如此。逻辑上的必然的真是空洞的同语反复(重言式),在同语反复中不可能说任何东西。但是,每一个不同的同语反复都内在地与一种推理规则相联系。除此之外,其他的必然的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法命题”(grammatical propositions),它们似乎属于先天综合范畴——但在那里它们是必然的但不是分析的——例如,“红色和绿色不能同时全都出现在同一个对象上”,或者“红色更接近于橙色而不是黄色”。它们实际上是表达的范型,即伪装成描述的形式使用其构成语词的规则。我们总认为语法命题是对世界中的客观必然性的描述,它们也的确貌似如此,但之所以貌似如此只是因为这些本来体现了表达规则或习惯的语法命题像阴影一样遮蔽了世界,而我们却将这种阴影误认为实在本身。我认为,在澄清必然性的本质方面维特根斯坦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做了更多的工作。
问:在《分析哲学:现状、历史和未来》(注:《哲学译丛》1996年第3期。)这篇文章中,您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衰落了,您可以给我们谈谈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的发展概况吗?
答:我们还不能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近30年分析哲学的发展盖棺定论,因为我们距离那个时期还太近。如果25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
我自己的看法是,当前的许多哲学流派已经失去了与其分析哲学根源的联系,已经抛弃了20世纪20~70年代分析哲学家共有的基本原则。赖特曾经谈到,分析哲学的主要遗产可能就是哲学史的编纂将会体现一种我们在20世纪所习得的分析技巧。他说的没错。当代的哲学史编纂远远超越了100年前编纂的哲学史,这种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分析方法的应用。
显然,在过去的30年中,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们正在日益远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远离他的哲学方法以及整个哲学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蒯因的影响,以及他对分析与综合的区分的批判;同时也因为更普遍的文化影响,分析哲学家们日渐地抛弃了这种非认知的、阐明性的哲学概念,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的特征,也是20世纪20~70年代分析哲学的特征。与此相反,哲学家们模糊了哲学和科学的界限,将哲学看做是一种可以建构、证实或驳斥与世界有关的理论的学科,能够对科学理论进行补充。从我自己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我认为这些改变是错误的。它们很可能会培养一种理智的幻觉,甚至促进了遍布在这个世界中的胡说的蔓延。
问:您谈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哲学中心从牛津转向了哈佛、普林斯顿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大学,这是否也意味着新实用主义的影响正在日趋增强?
答:是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牛津失去了其哲学的统治地位。但我认为美国的哪一个哲学中心都不会像20世纪40~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牛津那样能够主导分析哲学的发展。美国的一些大学里有著名的哲学系,如哈佛和普林斯顿。但同样,在美国没有哪一个哲学家或者哪一个派别的哲学家们能够像早期蒯因和后期戴维森那样统领美国哲学的发展。我很遗憾地说,牛津只是处在其曾经拥有的辉煌的余晖之中。当然,现在牛津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哲学系,也有一些优秀的哲学家,但无人能够与赖尔或奥斯汀、哈特或柏林、葛赖斯或斯特劳森相提并论。
实用主义从来没有对英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就我所知,当前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