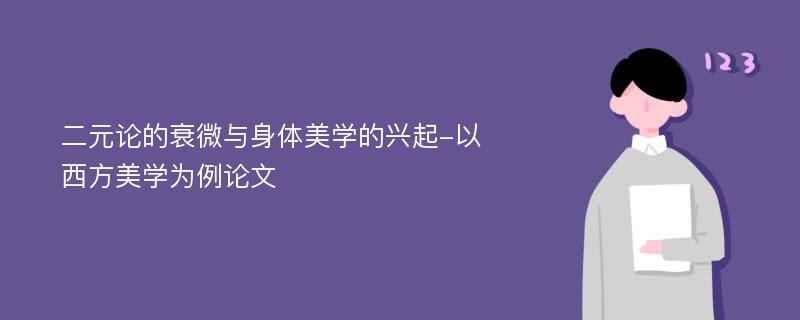
二元论的衰微与身体美学的兴起
——以西方美学为例
王晓华
摘 要: 在西方美学史上,二元论(dualism)曾经长期占据上风。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建立起等级制的人学图式: 心被想象为一种主体性角色,身则被当作需要驱动、充实、引导的被动之物。从逻辑上讲,这种图式蕴含着一个悖论: 倘若身心根本不同,它们就无法相互作用,当然也不可能联合为人;要是它们本性相同,将它们划分为两元同样悖理。在破解这个悖论的过程中,身体的意义获得了吊诡性的揭示。尤其是到了近代以后,自然科学持续揭示了精神活动对身体的归属关系,提供了解构二元论的证据。随着二元论的衰微,现当代理论中的身体开始展示其主体形貌,美学建构出现了层层递进的身体复兴: 在18世纪中叶,作为“身体的话语”的感性学诞生了;到了19世纪末,尼采标画出身体美学的原初形貌;进入20世纪以后,在现象学、实用主义、认知科学的合力推动下,身体美学最终升格为一个学科。可以预见,这个进程还将持续下去,属于身体美学的时代还刚刚开始。
关键词: 二元论; 悖论; 身体; 主体性角色; 感性学; 身体美学
在西方美学史上,二元论(dualism)曾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建立了不偏不倚的人学图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其诞生之日起,相关言说就具有等级制的结构: 心被想象为一种主体性角色,身则被当作需要驱动、充实、引导的被动之物。于是,相反的可能性被长期遮蔽了: 活的身体(the living body)是生活的承担者,所谓的心不过是其内在构成。正因为如此,二元论的流行意味着身体的被压抑状态。当且仅当它被质疑、松动、解构,身体才能获得出场的机缘。回顾西方美学的发展踪迹,我们会发现二元论的衰微对应着身体美学的兴起: 1.有关二元论的假设总是导致各种悖论,破解它们的过程吊诡地敞开了身体的意义;2.到了近代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持续揭示精神活动与身体的关系,提供了解构二元论的证据;3.随着这个进程的深入,现当代理论中的身体开始展示其主体形貌,身体美学应运而生。
网络中心度用来刻画特定城市与网络中其他城市直接关系的线的数量,在既定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主办城市网络规模里,网络中心度越高,其获得的知识共享、资源互补的机会就越大[8],说明该城市的竞争优势就越大;网络中介度代表一个城市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中介性高的行动者往往掌握并控制着信息流以及商业机会,因此可以从中获得中介利益;网络联系度表示任意两个城市由于举办相同项目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而产生的关系总和,某一城市的网络联系度越高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关系越密切,举办的赛事数量和级别就越高,其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节点优势就越大。
一、 二元论的前现代形态与身体的遮蔽-敞开
在重构二元论之前,有必要反思曾经普遍流行的说法: 人类曾经历过完全和谐的时代,原初文化没有任何裂痕。从身心关系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属于一个装饰过去的乌托邦,并无实在的所指。自万物有灵论(animism)——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命图式——诞生之后,身与心的裂痕便已经出现,感性生命就被抛入遮蔽—敞开的张力之中,有关审美的言说也具有难以消除的悖论品格。
原初形态的万物有灵论又被称为泛心理主义(panpsychism),因为它将整个世界当作精神显现的场所(Blackburn 275)。受其影响的人们相信精神寄寓于可见之物中,赋予后者生命力,支配其行动。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这种观点曾广泛流行于远古时代的西方世界。譬如,在新石器时期,某些头骨会被填上石膏,目的是封存死者的灵魂(基西克49)。这意味着对精神—主体的信仰: 尽管身体已经消亡,但灵魂依然活着。或者说,身心的生命之间具有无法抹去的时间差。当身体和灵魂被如此区分以后,二元论的雏形已经出现。如果后者充分展开自己的深层逻辑,那么身体必然被遮蔽乃至被贬抑。
公式(1)的allowedk=neighborsi-tabuk,代表蚂蚁k接下来爬行的下一路径,是邻居节点排除禁忌表爬过的节点,neighborsi指的是邻居路径节点集。α、β描述为各启发因子。ηij(t)表达的是启发函数值。
到了古希腊时期,这点已经清晰可见。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liad )中,心魂(psuchē)一词一共出现了33次,大都直接与思想和生死问题有关(Davis9)。它首先意指“生命的呼吸”或“内在的生命”。落实到具体语境中,它可以分别意指精神(spirit)、胸怀(breast)、心灵(mind)、心脏(heart)(9)。此种定位凸显了精神的意义,强调它是生命的本原和思维的器官。虽然荷马所描述的心魂还未彻底摆脱物质形态,但二元论图式已经廓然成形:“荷马区分了身体(demas, sōma)和心魂”,相信人死后心魂会从口中呼出,描绘了后者如轻烟般飞往冥府的情景(《伊利亚特》11)。当荷马做出如此划分时,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原型形象出现了: 身魂综体(the en-souled body)。人由心魂和身体组成,但二者并非平等的伙伴: 仅当心魂寄寓于身体之中,身体才具有来自心魂的活力;一旦心魂离去,它便立刻沦落为死物。譬如,《伊利亚特》中的赫克托耳被长枪刺中之后,“心魂飘离肢腿”,“死的终极将他笼罩”(606)。他曾经活跃的身体倒下了,任凭对手处置。敌人们跑来围住它,惊异于其柔顺品格:
“瞧哇,现在的赫克托耳容易摆弄,远为松软,
比之以前,他用熊熊火把焚船的时光。”(607)
评论:本年度的榜单让一些全球的经典优质葡萄酒产区重振声威,此外榜单上可见到不少新面孔,超过一半的葡萄酒是首次上榜百大,让人惊喜。
大卫·布勒东: 《人类身体史与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在荷马史诗中,有关身魂关系的言说并非无懈可击。虽然生命力的承载者被视为心魂,但人们施加影响的对象却是身体。当荷马极力渲染身体相互搏斗的场面时,一个问题已经悄然出现: 如果身体并不标志自我,那么,交战的双方为何都把矛头指向它?是为了破坏心魂的住所吗?假如心魂代表人的自我,这种破坏又有何实质性意义?为什么心魂离开身体后会变成虚影(eidōla)?倘若心魂在丧失身体寓所后必然飘向冥府,这岂不又反过来证明了身体的意义?在描述心魂的形态时,上述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
她言罢,我在心里思忖,心想展臂
(2)用水效率提高难度加大。随着三江平原等区域地表水灌溉逐步替代地下水灌溉,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难以持续提高,同时,灌区节水改造任务重、投入大、时间长、见效慢也是影响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原因。近两年,黑龙江省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逐年下降趋势明显(2016年度229 m3/万元,2017年度206 m3/万元;2016年度56 m3/万元,2017年度45.6 m3/万元),但是远高于国内先进地区。由于经济增长趋缓,有的地市甚至出现负增长,加之节水投入不足,部分地市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难度明显增大。
[Descartes.Meditations of First Philosophy . Trans. Pang Jingr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一连三次我迎上前去抢抱,服从急催的内心,
但她一连三次飘离我的手臂,像一个影子
或是梦景,悲痛加剧,折磨我的心灵。
我对她说话,用长了翅膀的语言说及:
“为何避我,母亲,当我试图抱你,
以便,即便在哀地斯的家居,我们的双臂亦能
综上所述,纳布啡可安全有效的用于剖宫产产妇术后镇痛,其术后PCIA联合舒芬太尼适宜的配比剂量为纳布啡2.0mg/kg联合舒芬太尼0.5μg/kg。
紧抱,在凄楚的梦中舒慰一起?
抑或,你只是个虚形,高傲的裴耳赛丰奈
把它送来与我,增剧我的悲痛,加深悲戚?(《奥德赛》332—33)
离开身体的心魂虽然变成了虚影,但却具有身体的形貌和姿态。既然如此,区分身体和心魂的根据何在?为何二者最终会分道扬镳?在荷马的时代,这些问题并未立刻被意识到,但已经潜伏于“文字的蜂群中”,随时会浮出海面。
从逻辑上讲,解决荷马身魂问题的路径有二: 其一,超越二分法,代之以一元论;其二,强调身魂之别,重新为二元论奠基。现在看来,荷马之后的希腊人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到了古风时期,哲学的诞生推动了身魂分野的进程。譬如,在米利都学派(Milesian School)的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看来,人类的灵魂是空气,将我们聚集起来,提供了呼吸的力量,而它自身“完全接近于非肉身之物(the incorporeal)”(Barnes26)。空气轻盈、透明、无限,迥别于沉重、晦暗、有限的身体。这个立场被毕达哥拉斯所继承和强化,引发出对灵魂的下述言说: 首先,灵魂是不朽的;其次,它会变成其它动物;再者,所有发生的事都会以固定的节奏再次发生,没有什么是绝对新的;最后,所有活的事物可以被归为同一种类(33)。不朽的灵魂会在不同的身体之间迁居,预先决定了各种事物的本性。这个阐释清晰地将灵魂与自我联系起来,强调它可以维持人“从出生(或此前)到死亡(或死后)的完美同一性”(Blackburn357)。如此言说的他为灵魂设定了一个对照物,凸显了身体的短暂品格。有死的身体无权代表人的自我,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当灵魂在宇宙中漫游时,身体虽然提供了暂时的驿站或保护性的外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或缺: 即使处于无身体状态,灵魂仍是自我的同义语。据说,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会记住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在冥府也不例外(Barnes34)。假定离开了身体的灵魂仍能体验世界,此类猜想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体验离不开五官的感受,告别了身体的灵魂如何能够单独感受世界?难道它也拥有自己的五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灵魂岂不就是缩微的身体(身体中的身体)?其独特性何在?显然,毕达哥拉斯的理论面临着自我驳斥的危机。在他所属的时代,这个危机并未被意识到,许多人依然沿用同一思路。譬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说“灵魂在冥府运用嗅觉”,但同样为说明这如何可能(Barnes64)。事实上,只要假定灵魂就是自我,那么,它就必然被视为相对自足的存在——不仅仅能够思考,而且可以感受和行动。然而,上述假定本身就是成问题的: 如果灵魂可以代表人出场,那么,它为何非要与身体结合?这岂不是可以避免的错误?后来,柏拉图(Plato)给出了一个牵强的答案:“如果灵魂是完善的,羽翼丰满,它就在高天飞行,主宰全世界;但若有灵魂失去了羽翼,它就向下落,直到碰上坚硬的东西,然后它就附着于凡俗的肉体,由于灵魂拥有动力,这个被灵魂附着的肉体看上去就像能自动似的。这种灵魂和肉体得组合结构就叫做‘生灵’,它还可以进一步称作‘可朽的’。”(《裴德罗篇》246B)灵魂与身体分别属于天空和大地,迥异的本性意味着它们的结合不可能长久。为了摆脱身体的牵累,哲学家甚至需要“练习死亡”(《裴多篇》80E)。这等于说灵魂与身体的结合是个错误,因而愈加凸显了二元论的困境。要缓解这种理论上的紧张状态,出路之一是强调身心结合的必然性。这正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言说策略。亚里士多德修正了柏拉图的思路,力图建立不偏不倚的人学图式。他将灵魂定义为“活的身体的原因(cause)和原理(principle)”(De Anima 415b),强调它只能寓于“身体的各部分之中”(413a)。只有当灵魂与身体结合时,人才会诞生。在论述结合的具体机制时,他强调身体的感觉机能,“所有非静止而又涵括灵魂的身体都不可能没有感觉(perception)”,因为这意味着它不能“回避某物或获得他物”(434b)。只有通过感觉器官(sense-organ),人才感觉到感觉对象(sense-object)(424b-425a)。对于审美来说,这种说法可谓意味深长。如果它的对象是可感的事物,那么,能感的身体(aesthetic body/perceptive body)就不可或缺。只有通过能感的身体,可感的事物才会向人显现,审美事件才会发生。这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中的潜台词。事实上,在其老师柏拉图那里,它已经被部分说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用最敏锐的器官来感受美[……]能被我们看见的只有美,因为只有美才被规定为最能向感官显现的,对感官来说,美是最可爱的。”(《裴德罗篇》250D)由于感官离不开身体,因此,可以肯定一个事实——身体参与了审美。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这个事实获得了进一步的肯定。谈论美的事物时,他所着眼的是能感—可感的关系,“动物的个体太小了不美(在极短暂的观看瞬间,该物的形象会变得模糊不清),太大了也不美(观看者不能一览而尽,故而看不到它的整体和全貌——假如观看一个长一千里的动物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诗学》74)。“太小”或“太大”这种说法暗示了观看者的在场,牵连出能感的身体。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话语中,我们可以领受到一种比较完整的身体学。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二元论已经具有了新的形态,身心联合说已经成形。这并非一人之功,而是许多哲学家努力的结果。在亚里士多德写作《论灵魂》之前,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都曾强调身体的意义,认为“人们变换身体状况时也就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形而上学》74)。到了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Epicure)等人反复重复上述信念,“存在总体由物体和虚空所构成。物体的存在处处都可以得到感觉的证明。理性在推论不明白的事情时,也必须根据感觉。”(伊壁鸠鲁 卢克莱修5)由于感觉的产生依赖各种生理器官,因此,对感觉的重视必然牵连出身体之爱,“灵魂是感觉的重大原因;但是,如果灵魂不被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包住,就不能进行感觉。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向灵魂提供了这一必要条件,而且因此分有灵魂的某些功能——虽然并不拥有灵魂的所有能力。”(13)只有当身体存在,人才能感觉。一旦身体消亡,感觉也就随之化为乌有。从恩培多克勒到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温和的二元论形成了连贯的谱系。
到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延续了这种温和的二元论立场。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写道“下面,我们思考肉身性生物(corporeal creatures)和精神性生物(spiritual creatures)的区别: 首先,在《圣经》中,纯粹的精神性生物叫做天使;其次,完全肉身性的生物;第三,肉身和精神性的组合物,这就是人。”(Aquinas480)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强调审美离不开身体性感受(Ecoo79)。由他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身心联合说在中世纪的影响。
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乃至托马斯·阿奎那,弱二元论(温和的二元论)逐渐取代了强二元论,理论的重心则因此向身体位移。虽然这种变化推动了身体的出场,但二元论图式预先规定了解蔽的限度。要彻底敞开身体的意义,言说者就必须越过二元论的边界。对于前现代西方美学来说,这是未曾完成的事业。
二、 二元论的困境与身体美学的诞生
在前现代形态的二元论中,身体被置于遮蔽-敞开的辩证运动中。遮蔽它的企图总是遇到层出不穷的困难,引发无解的悖论。在试图走出困境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逐步承认身体的地位和功能。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遮蔽—敞开的张力开始获得了空前的强化。由于现代性开始兴起,一种新的生存风格出现了,“厌恶独尊的权威,嫌弃唯经典是从而崇尚对事实作客观的研究,这些都象征着近代的曙光。”(沃尔夫507)随着这种精神的增殖,二元论图式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做客观的研究”意味着一种重视经验的立场。它树立起新的尺度: 一切都要接受经验的检验。二元论同样需要寻求经验层面的支撑。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找到身心层面的连接点。事实上,这个工作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启动。为了解释二元如何相互作用,鸿学硕儒们提出了许多假说: 1.柏拉图曾经假定“联结灵魂和身体的那些生命纽带仅仅地维系在髓上”(《蒂迈欧篇》73B);2.亚里士多德设想灵魂凭借“精炁(生命原炁)”在身体内引起诸动变(《动物四篇》703a 264);3.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家盖伦(Claudius Galenus)提出“灵气”说,猜测后者赋予血液以活力(沃尔夫506)。不过,这些假设又会引出新的问题: 假若“髓”“精炁”“灵气”能够连接身心,那么它们必然是半身体半精神的存在,但宇宙中存在这种跨界的事物吗?显然,对它的证明必然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 必须首先证明二元论正确,才能证明“灵气”或“精素(archei)”存在,但有关它的假设恰恰是为了证明二元论。吊诡的是,进入近代以后,此类思路依然延续下来。16至17世纪的部分西方学者仍相信“活力灵气”的存在,认为它会联结身体和灵魂(沃尔夫532—33)。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他“仍然坚持灵魂束缚在肉体中这种中世纪的观念”,“费尽心机地按照这种和他的二元论哲学相吻合的观点来解释情感”,认定存在“活力精气”或“动物精气”这种媒介(686)。后者据说居住于“大脑正中央”,可以通过“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s)”将灵魂的影响辐射到全身(Descartes373)。然而,此说与其二元论立场相悖。在《沉思录》(Mediations )中,他曾强调身心之别: 身体“仅仅是一个具有广延而不思想的事物”,“我”(灵魂)则“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没有广延”(181)。既然如此,能够联结身心的东西必然同时具有和不具有广延性。这是典型的悖论。为了回避这个困境,他强调联结二者的腺体非常小,但再小的东西也是有广延之物,因此,这种辩护几乎毫无意义。只要他坚持灵魂“完全而且绝对地不同于身体”(181),那么,他就不可能走出困境。对此,其论战对手伽森狄(Pierre Gassendi)可谓洞若观火: 有广延之物和无广延之物的连接点既不可能是有广延的,也不可能是非广延的,因而不可能存在(伽森狄82)。甚至,当时颇为活跃的伊丽莎白公主也曾追问“既然灵魂缺少使一个身体作用于另一个身体的那种属性,那么,灵魂又如何可能作用于身体?”(斯特拉桑9)对于这些问题,笛卡尔的解释几乎陷入了怪圈。后人用“笛卡尔循环”(Cartesian circle)来指称其论证,可谓精准之至。
从根本上说,笛卡尔困境折射出了二元论的悖论: 倘若身心根本不同,它们就无法相互作用,当然也不可能联合为人;要是它们本性相同,将它们划分为两元同样悖理。正因为如此,寻找中介的工作必然徒劳无益。出路是超越二元论而非补苴罅隙,是进行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在为二元论辩护的过程中,笛卡尔曾经将身体定位为“我还不认识的东西”(《第一哲学沉思录》359)。此话道出了二元论的根本成因: 对身体的无知。那么充分认识了身体以后,情况又会如何?笛卡尔本人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谈论精神活动的机制时,他曾反复强调腺体的重要性,认为后者是灵魂居住的首要席位。腺体是一种重要的生理器官,可以汇集由神经系统传到大脑的感觉。对腺体的分析牵连出以身体为关键词的话语体系,涉及心脏、大脑、神经、四肢、躯干、体液等身体性存在,最终引导出肯定身体的结论:“我们在这个地方明明白白地说吃饭只应归之于肉体;至于感觉和走路,我也绝大部分归之于肉体;关于那些东西,我归之于灵魂的仅仅是一个思维。”(355)当灵魂只剩下思维一个功能之后,下面的结论已经水到渠成: 只要证明思维也是身体的功能,有关灵魂的假说便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在他和同时代人谈论大脑、神经、腺体时,身体能思维的可能性已经显现出来。如此这般的身体绝非仅仅“为主体提供了坚实性与面孔”(布勒东79),相反,它很可能就是主体本身。在谈论审美问题时,笛卡尔几乎完全“从身体出发”,“我们一般会把我们通过内感官或理性判断为适合或不适合我们的东西称为好的和不好的,但是,我们也会把通过我们的外感官——主要是我们的视觉,只有它更值得考虑,而不是别的——而呈现给我们的事物称作是漂亮或丑陋的。”(《论灵魂的激情》55)对于二元论来说,这是个吊诡的结局。
从功能的角度看,笛卡尔所说的灵魂更接近后人所说的“心”(mind)。他归之于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思维。强调灵魂具有思维能力是一种古老的做法(如荷马史诗中就经常出现“他思考斟酌,在心里魂里”(《奥德赛》160)这样的表述),但笛卡尔将这种立场推到了极限。由于他的言说,传统的身魂(body-soul)关系开始转化为身心(body-mind)关系,二元论则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嬗变。到了斯宾诺莎(Spinoza)这里,这种转变的结果已经获得了清晰的表述。在他的《伦理学》中,灵魂一词已经消失无踪,代替其位置的是心灵概念。写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时,他又强调心灵“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思想的式态”(80)。与此同时,被保留下来的只有思想-广延的二分法: 虽然思想和广延同属于同一实体,但它们仍是分立的式态(80)。显然,这种划分仍会面临致命的反驳: 既然广延和思想不过是同一实体的两种属性,那么,为何还坚持有广延之物不能思想?如果广延和思想截然不同,那么,心灵又如何能够影响身体?为了自圆其说,他又援引了元气说,断言心灵可与通过中介来影响身体(144—45)。不过,此类假定同样会招致新的诘难: (1)假如元气同时具有思想和广延两种属性,那么,它的存在意味着二元论根本无法成立;(2)倘若元气仅有广延或思想一种式态,它就不可能联结身心。这个笛卡尔曾经面对的悖论注定无解。要走出困境,道路只有一条: 放弃有广延之物不能思想的偏见,建立全面肯定身体的一元论。事实上,斯宾诺莎本人也想统一身心,曾使用过“这一躯体的心灵”之类表述(174),并试图解释“心灵[……]如何起源于躯体”和“它的变化如何取决于躯体”(171)。在阐释审美现象时,他也与笛卡尔一样诉诸身体:“外物触于眼帘,触动我们的神经,能使我们得到舒适之感,我们便称该物为美;反之,那引起相反的感触的对象,我们便说它丑。”(《伦理学》42)由于身体各不相同,因此,审美必然具有个体差异。相关论述虽不完整,但留下了建构身体学的重要线索。从身心观的角度看,斯宾诺莎是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见证了二元论的衰微,预示了身体学的兴起。
斯宾诺莎去世于1677年。此后不久,英国科学家威利斯(Thomas Wilis)开始研究人与动物的大脑,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灵魂”是高度发展了的生理体系,“人与动物都有灵魂,而灵魂就是肉体,可以直接运用器官”(桑内特338)。到了18世纪,威利斯的后继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活蛙实验,进一步巩固了上述发现,“从神经系统的角度看,身体不需要‘灵魂’也能感应。由于所有的神经节似乎都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因此,灵魂应该是到处盘旋而非停留一处,经验观察无法将灵魂安放在身体里。”(339)依赖日益发达的解剖学,人们敞开了身体的内部结构-形态。随着不可见者变得可见,身体吊诡性地获得了返魅的机缘: 被考察的逝者的遗体,但被揭示的是活人的秘密。当身体的复杂和丰盈呈现给哲学家时,一个全新的前景展现出来: 无需借助心灵之类概念,我们就可以建立完整的人学图式。在1748年发表的专著《人是机器》中,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La Mettrie)便演绎了从身体出发的可能性。写作此书时,他谈到了自己对解剖学的信任,“通过从人体的器官把心灵解剖分析出来”,我们在有关人的问题上“接近最大程度的或然性”(梅特里17)。依据这样的理由,他宣称“医生是唯一无愧于祖国的哲学家”,并把自己的书献给葛廷大学医学教授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9)。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他援引威利斯的著作《论脑》,大量使用脑髓、上丘、下丘等生理学术语,最终得出了肯定身体的结论: 身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支撑它的是其他物质而非心灵(20)。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名词”,它所指称的不过是“身体中那个思维的部分”(53)。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假设“人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实体”(13),身体组织“便足以说明一切”(53)。通过这样的论述,他演绎了解构二元论的路径。此后,类似的话语形成了连绵的谱系,推动着身体的返魅进程。譬如,霍尔巴赫(D’ Holbach)继续使用身体-机器隐喻,认为“我们知道和感觉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强调是身体在感觉、思想和推论、受苦和享福(霍尔巴赫91)。再如,狄德罗(Denis Diderot)也提出了一元论的人学观念,“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教黄雀用的手风琴是木头做的,人是肉做的。”(狄德罗132)肉做的人是“一个有感觉并且有适于记忆的机体的生物”,可以把“它所得到的那些印象联系起来”,“凭着这个联系形成一个是它的生命史的故事”,“获得它的自我意识”,并因此“作出否定、肯定、推论、思维来了”(125)。与霍尔巴赫一样,如此说话的他已经涉及了身体的主体性问题。如果说笛卡尔假定主体性属于灵魂,那么,他们则开始归还理论对身体的债务。随着相应探讨的深入,身体开始展露自己的主体形貌,而美学恰好诞生于这个过程中。
到了18世纪中叶,有关身体的言说已经蔚为大观。随着身体地位的提高,作为一个学科的美学——感性学(Aesthetics)——应运而生。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腾(Alexander Baumgarten)正式提出了美学概念,“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嘉腾13)。尽管鲍姆嘉腾措辞谨慎,但弘扬感性认识的意志还是显现出来,“低级”的感性竟然与“高级”的理性类似,这种说法本身就折射出时代语境的变化。按照鲍姆嘉腾的解释,“感性认识是指[……]表象的总和”(18)。表象的获得离不开感官,而外在感官属于身体,因此,对感性认识的重估具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身体话语的兴起。对此,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美学是作为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在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腾所做的最初表述中,这个术语首先指的不是艺术,而是如古希腊的感性(aisthesis)一词所指称的那样,是人类全部感知觉的领域,它与概念思维更加精妙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Eagleton13)在鲍姆嘉腾的言说中,“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神的作用”经常被相提并论(鲍姆嘉腾23)。虽然他还习惯性地谈论精神的绝对地位,但感性-理性的二分法已经获得了温和的表述。尤其重要的是,他提到“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并且强调“这完善也就是美”(18)。这意味着人可以通过审美活动塑造自己,如提高感受力的敏锐性等。出于这样的理由,他“提倡进行审美训练”,并设专节进行论述(18—33)。在这种论述中,身体美学的萌芽已经产生。
经过一番梳理,本文重构了二元论走向衰微的过程,再现了身体美学的诞生踪迹。剩下的问题不是如何为此身与心的平衡,而是继续归还美学对身体的债务。如果不存在“内在的人”,那么,二元论就仅仅属于福柯所说的乌托邦。只有彻底解构它,美学才能真正回到其起源和本体。但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完成,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不愿意放弃对精神主体的想象,二元论则趁机维持其残存形态。进入21世纪以后,借助赛博空间、电子人、网络等时髦话语,柏拉图主义又借尸还魂,身体美学则不能不应对由此而产生的挑战。它所建构出的话语体系不但要具有解释力,还必须满足芸芸众生对终极关怀的需要。属于它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不过,鲍姆嘉腾本人对此并未获得清晰的认识。在他那里,感性学的建构还处于自我压抑状态,作为“低级认识论”,它还需要以理性为模板(鲍姆嘉腾称逻辑学为美学的大姐),渴望在后者的统领下变得明晰(17)。这种压抑同样反映了身体话语的地位,在鲍姆嘉腾写作《美学》的十八世纪中叶,身体还没有完全展示自己的主体形貌。进入19世纪以后,情况出现了明晰的变化。经过一些哲学家的努力,身体的主体身份获得了明晰的表述。在1837年出版的《对莱布尼兹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中,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写道“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肉体本身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肉体,它不仅是被观察到和被感觉到的东西,而且是观察者和感觉者,因此,它不仅是观察和感觉的对象,而且是观察和感觉的原因,用唯心主义的语言来说,它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主体-客体,正是由于肉体是它自己的对象,因此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与我们同一的肉体。”(费尔巴哈213)主体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就是能感觉、观察、意识自己的身体(214)。在确定了身体同时具有主体-客体双重身份以后,二元论的悖谬进一步显现出来“首先把肉体和心灵分裂开来,然后又想使这种分裂协调起来,这种做法是何其荒谬!”(214)由于这种错误,人们在思维时“流浪在他乡异域”(303)。现在,返乡的时刻到了,理论应该回归身体-生活世界。这是费尔巴哈未曾言明的潜台词。虽然他于1872年去世,但身体的复兴之路并未终止,美学的重建进程依旧在持续。
在费尔巴哈去世10年后,尼采(Nietzsche)出版了诗体著作《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 ),气势磅礴地唱出了身体的颂词:“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30)人不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而就是身体。作为拥有感受和思想的复合物,身体是“未被认识的圣人”,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我(ego)(30)。它为自己创造了“意志之手”(the hand to its will),为自己创造了精神(31)。它渴望,它追求,它越过自己。它是生成者、战斗者、评估者、万事万物的赐福者(72)。如此被描述的身体不正是后人所说的“主体性的身体”(subjective body)或“思想的身体”(mindful body)吗?通过尼采激情洋溢的言说,身体的主体形貌被还原,理论开始追求“大地的意义”(73)。大地是身体的家,是日常生活的场域。当它的意义成为追求的对象时,美学必然“以身体和生理学”为出发点(The Will to Power 271)。此说可能出乎很多同时代人的预料,但牵连出一整套奠基于身体的美学话语: 美诞生于赠予的行动;赠予者就是身体;唯有当身体生命力丰盈的状态,周围的事物才能变得完满、富有诗意、“美”(273)。换言之,美出自身体的美学状态(aesthetic state): 当身体活力(bodily vigor)因丰盈而满溢,这种状态就会出现(422)。美学状态对应着身体的自我确证,完全属于生活世界。落实到感性层面,身体的意义更加清晰可见: 作为创造者,身体既拥有“统治元细胞”的力量,又向外部世界发号施令,因而其感觉已经是“同化和吸收过往事物”的结果(273)。感性是身体的感性,是身体确证自己的活动。在强调感性活动对身体的归属时,下面的结论已经不言而喻: 如果说美学是感性学,那么它必然回到身体。尼采不但基本完成了解构二元论的原初筹划,而且标画出身体美学的基本形貌。对于西方近现代美学来说,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三、 对二元论的持续解构与身体美学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
尼采去世于1900年。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身体美学的建构并未立刻兴起,二元论也没有完全退出理论剧场。背后的缘由可谓复杂,涉及信仰、社会分工(劳心-劳力)、文化传承、认知科学的局限,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身体美学建构的不完善: 1.到了尼采这里,身体美学依然没有形成连贯的理论话语,呈现给世人的仍是零珠散玉般的论述;2.涉及人的超越性时,它没有给出较为完备的解释,更没有形成可以替代主流宗教的信仰体系;3.与此相应,二元论尽管备受质疑,但它对永生的承诺仍然吸引着芸芸众生。只有在继续解构二元论的同时揭示身体的超越性,美学建构才能最终走出过渡状态。
在20世纪初的西方,多个流派继续聚焦身体,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现象学(Phenomenology)。现象学力图发现“在一切思想之先”的东西,诉诸于“原初给予的直观”,力图“在机体的自性中”把握其本质,而这无疑会推动身体主体性的敞开——与想象中的灵魂相比,身体具有可见可感的特征,因此,上述立场必然使天平继续向身体这边倾斜,二元论则会被进一步解构(《纯粹现象学通论》61)。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这里,这个逻辑线索已经初露端倪。当他试图对世界进行抽象时,他发现了一个比笛卡尔的我思更基本的存在:
在这个自然的被本真把握到的躯体(koepern)中,我就唯一突出地发现了我的身体(Leib),也就是说,作为唯一的身体,它并不是单纯的躯体,而恰好是一个身体,是在我的抽象的世界层次之内的唯一的客体,根据经验,我把诸感觉看作是一个客体,尽管是以各种不同的隶属方式(如触觉的领域、冷暖的领域等)。(《生活世界现象学》158—59)
这个唯一的客体具有以下特征: (1)“我可以直接地处理和支配,尤其是可以在它的每个器官中起支配作用。”(2)“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器官必定会成为一个客体,而这个客体也必定会成为一个起作用的器官”(159),它就是身体。由于“我总是能够借助于这一双手来感知另一双手”,因此,“身体总已经向后回溯到了它自身”(159)。身体能感受而又被感受,形成了自我反射的环状结构:“当我用我的右手触及我的左手时,我的躯体显现两次,一次作为‘探索者’,一次作为‘我所探索者’。”(《现象学的构成研究》380)至少就感觉层面而言,身体同时是主体-客体。通过诸如此类的推理,胡塞尔再次确认了“主体性的身体”(subjective body)。虽然他还使用“我的身体”这种古典式表述,但二元论在他这里已经被削弱了。譬如,他认为“主体的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取决于身体和心理两种因素,也就是说,身体已经被当作联合中的一方(61)。这种定位中,身体的意义再次凸显出来。不过,胡塞尔并没有因此彻底超越二元论,相反,他依然将人定位为“心理物理统一体”(275)。在承认了身体的主体性之后,保留二元论意味着一个难题: 身体是否属于自我的构成?如果不属于,主体性理论就难以自圆其说?倘若属于,又该如何假设二元论前设?对此,他并没有给出完满的解释。要解决相关悖论,就必须在胡塞尔止步的地方前行,而解构二元论则是最为紧迫的任务。
胡塞尔去世以后,其他现象学家开始从事这个工作。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于1945年出版《知觉现象学》,要求“重返现象”(return to phenomena)(Merleau-Ponty1)。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表述,预示他将审视所有的偏见(当然也包括对身体的看法)。通过分析感觉、注意、判断,他发现所有的知觉都与“活的身体”(the living body)密切相关: 离开了感觉器官(如手和眼睛)、神经系统、大脑,我就无法感知什么,因此,经验首先是身体性经验(bodily experience)(87)。那么,如何才能认识“活的身体”呢?他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除非使身体使行动起来,除非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我就不能理解活的身体的功能”(87)。此处,他使用了“我是……身体”这种表述。如果它成立的话,那么,二元论就必然被证伪。与胡塞尔不同,梅洛-庞蒂强调“没有内在的人”(the inner man)(xii)。他认为,“内在性源于人类身体的物质性安排,而不是出现在它之前。”(Johnson124)这意味着他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二元论。于是,如何回答下面的问题便至为关键: 身体能否承担被归于精神主体的大任?在《知觉现象学》中,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1.“它移动自己并且观看,它将物安置在自己的周围”(124)。2.身体是“被观看的观看者、被触及的触及者、被感受的感受者”(124),能够在自我感受的同时摄取世界的秘密。3.身体犹如世界的心脏,“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与之构成一个系统”(235)。4.“我的身体不仅赋予自然对象以意义,而且将之赋予词语之类的文化客体。”(Merleau-Ponty273)身体同时具有主体-客体双重身份。它就是自我(self),拥有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因此之故,我们完全可以把身体定义为主体-客体。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更多的属性会被归还给身体,二元论则会被彻底解构。不过,由于英年早逝等原因,梅洛-庞蒂同样没有完成这个工作。
在梅洛-庞蒂去世7年后,另一位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出版了《身体哲学与身体现象学》,力图从“主体性身体的角度”建立“主体性的一般本体论”(general ontology of subjectivity)(Henry222)。这是一种回到原初之物的努力。首先,他认为“原初的生命”(the original life)只能是“身体的生命”(the life of body)(105)。这并非是对人的降格,而是对人的赞誉,因为“原初身体”(original body)或“绝对身体”(absolute body)是“存在于处境中的主体”(191)。它“使用椅子”,“走向烘干机”,“打开门”(192)。它总是组织起属于自己的世界,维系“它与世界的超越性关系”(193)。总之,原初身体就是行动的身体,是做事的主体。行动是主体性的行动,是身体的自我确立-塑造。根据上述阐释,他拒斥身体与主体性的二分法(61),反对“对身体和精神的传统区分”(221)。在他看来,当且仅当原初的身体被遮蔽,人们才会仅仅聚焦于“客体性的身体”(objective body),但后者绝非身体的原初形态。为了解蔽纠偏,米歇尔·亨利力图建立“主体性身体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subjective body)(105)。后者属于本体论的一元论(ontological monism),是绝对的人类知识(88)。虽然这个学术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身体的复兴之势已经彰显。对于美学建构来说,这意味着转折的机缘。
在梅洛-庞蒂和米歇尔·亨利的言说中,下面的命题已经呼之欲出: 身体在审美中能够扮演“主体性角色”(subjective role)。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定位推动了身体美学的建构,不但使之获得正式的命名,而且把它升格为一个学科。在1992年发表的《身体美学: 一个学科建议》中,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写道:
身体美学可以暂时定义为: 对经验和使用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sensory-aesthetic)鉴赏和创造性自我塑造(creative self-fashioning)之中心(locus)——的批判性和改善性的研究。(Shusterman267)
此处,locus是个多义词,同时具有“中心”和“场所”之意,解读者可以游移于两种所指之间。依靠这种微妙的修辞学实践,他强调了身体在审美过程中的地位: 它既是审美活动发生的场所,又是自我塑造的中心;既是审美活动的承担者,又是其目的。如此言说的舒斯特曼属于实践美学(Pragmatist Aesthetics,国内通常译为实用主义美学)传统,但又说出了梅洛-庞蒂和米歇尔·亨利的未尽之言——他同时熟谙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和尼采、梅洛-庞蒂、福柯的著述,力图将它们的综合到一个新的话语之中。后者不止步于认识的场域,不满足于文本的生产,而是指向身体的自我改善(somatic self-improvement)(276)。它延伸到实践维度,力图建立“训练的或锻炼的身体化形态”(a corporeal form of training or exercise),强化身体的感觉敏锐性、活力、美好程度(276)。通过诸如此类的表述,舒斯特曼凸显了身体在审美实践中的主体形貌。在强调身体的地位时,他以赞赏的语气提到了尼采、梅洛-庞蒂、分析哲学:
尼采和梅洛-庞蒂展示了身体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心性(ontological centrality),即身体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被建构性地投射出去的焦点(focal point),分析哲学则考察作为个人身份尺度的身体和作为解释精神状态的本体论基础(譬如它的神经系统)的身体(270—71)。
运用战略管理的思想,根据高校自身的发展目标,对资产管理工作进行准确的定位,统筹资产管理工作,制定详细可行的资产管理规划。坚持勤俭办学,科学决策,优化资源,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伊壁鸠鲁 卢克莱修: 《自然与快乐》,包利民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结 语
killall & iptables -D INPUT -s 198. **.98.245 -j DROP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ristotle.De Anima .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86.
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年。
[Aristotle.Poetics . Trans.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 - -: 《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 -. Metaphysics . Trans. Miao Liti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 《动物四篇》,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年。
[- - -. Four Animals . Trans.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狄德罗: 《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鲍姆嘉腾: 《美学》,简明、王晓旭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Baumgarten, Alexander. Aesthetics . Trans. Jian Ming and Wang Xiaoxü.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7.]
Blackburn, Simon.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其次是以情起句。如晁端礼《卜算子·恩义重如山》起句就运用两个比喻,将如山似海的恩义与情意表现得无限深沉。又如琴操词中开门见山地亮出全词的基调——离别,紧接着一个“怯”字又映入眼帘。主人公为何而怯呢?原来喝完这杯酒,我们就将分别远去。又与首句的离别相呼应。再如施酒监所作《卜算子·赠乐婉,杭妓》,首句正面描写两人情深意切,“恨”句又从侧面烘托两人相见恨晚,情意绵绵。
他们凝视它,感慨赫克托耳曾经拥有的健美和豪强,“边说边捅一番”(607)。被凝视的身体是审美的对象,也是无力抵抗伤害的客体。在这个意味深长的事件中,史诗中的身体出现于二元论图式中,展示了在其中的位置和命运。
[Breton, David. Anthropologie Du Corps Et Modernite . Trans. Wang Yuanyua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1.]
Davis, Michael. The Soul of the Greeks .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年。
抱住死去的娘亲,她的魂灵。
BIM技术在实际进行施工阶段运用时,其与传统施工方式不同,其能够对建设项目施工阶段进行不同方位的施工模拟,以给予施工方真实直观的施工效果图,使得施工方能够及时对施工流程进行调整,避免产生较多突发性的安全事故。其次,在运用BIM技术进行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时,施工单位可以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将相应的信息输入到三维模型中,然后导入对应的BIM施工管理软件,以全面化、准确化与真实化的模拟建设项目的整个施工过程与施工现场,进而最大程度的了解建设项目的实际施工情况,及时控制各种潜在的施工问题。
- - -: 《论灵魂的激情》,贾红鸿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年。
[- - -. The Passion of the Soul . Trans. Jia Hong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Descartes.Key Philosophical Writings .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7.
保尔-亨利·提利·霍尔巴赫: 《健全的思想》,王荫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年。
[d’Holbach, Paul-Henri Thiry. Le Bon Sens . Trans. Wang Yint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Barnes, John. Early Greek Philosophy .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
[Diderot, Denis. An Anthology of Diderot ’s Philosophy . Trans. Jiang Tianj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Eagleton, Terry.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0.
Ecoo, Umberto. 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微课的呈现形式多样,“Photoshop平面设计”课程内容梯度层次丰富,具有较强的延伸性,由于教师自身水平和软硬件条件限制,拍摄资源种类比较单一,课堂新授型较多,而且方式不够灵活多变,没有做到群体与个体学习相结合,需要发展综合性、实效性更强的微课资源及运用途径。
为了探索MOOC学习平台的结课率,笔者在开学期向教务处申请面向全校师生开设网络公选课“计算机网络基础及应用”,让学生自由选课,自主学习。学生选修该网络课程后还可以选修其他的传统公选课,不占用公选课名额,同时不对学生设置硬性考核要求,通过能获得1.5学分,没有通过下次仍然可以继续选修学习,充分给予学生选择权,学生可以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选择是否坚持学习。课程考核分数由2个维度组成:课程视频学习进度(50%)、互动频率(20%)以及考试(30%),学生达到60分即算结课。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第一节比赛,辽宁就领先山东队13分之多。去年还是总冠军级别的球队在新科冠军面前毫无一战之力。
如此说话的舒斯特曼属于一个历史悠久的谱系,延续了肯定身体的思想脉络。焦点、中心、尺度、本体论基础这些词汇原本都用来形容“精神(灵魂或心)”,现在则被归还给身体。在身体被如此赞赏之时,二元论即便没有被完全解构,其中心也已经完全向身体方向倾斜。由于舒斯特曼的努力,鲍姆加登美学中的潜台词被说出,“审美训练”落实为身体的自我塑造。虽然舒斯特曼有时还会谈论“对身和心的整合”(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xiii),但他显然仅仅是在使用一种习惯用法。如果身体是焦点、中心、尺度、本体论基础、主体性角色,那么,“心”就几乎失去了全部领域,所谓的身-心关系实为身-身关系。除了回归“能思的身体”(mindful body),已经变成残存物的心没有其他出路。这是舒斯特曼文本中的潜台词。它虽然未被说出,但肯定身体的传统已经在他这里结出了美学之果。
Z40 2.48 mmol Zn(NO3)2·6H2O与 19.84 mmol HmIM分别溶解于50 mL MeOH后,升温至60 ℃,充分溶解后,前者迅速倒入后者,并持续搅拌60 min。离心操作后于60 ℃真空烘箱中干燥24 h得白色粉末[11]。
[Epicurus, and Lucretius. On Nature and Pleasure . Trans. Bao Li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4.]
费尔巴哈: 《对莱布尼兹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涂纪亮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年。
[Feuerbach, Ludwig, Andreas. Narrative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Leibniz ’s Philosophy . Trans. Tu Ji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伽森狄: 《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庞景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Gassendi, Pierre. Qeuves de Descartes . Trans. Pang Jingr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Henry, Michel.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荷马: 《奥德赛》,陈中梅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3年。
[Homer.Odyssey . Trans. Chen Zho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3.]
- - -: 《伊利亚特》,陈中梅译注。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7年。
[- - -. Iliad . Trans. Chen Zho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7.]
胡塞尔: 《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Husserl, Edmund. Phenomenology of Consciousness and Sociology of the Life -world . Trans. Ni Liangkang and Zhang Tinggu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 -: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年。
[- -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 - -: 《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 - -.The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Phenomenology . Trans. Li Youzhe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3.]
Johnson, Galen. A. ed. The Merleau -Ponty Aesthetics Reader .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约翰·基西克: 《理解艺术》,水平、朱军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3年。
[Kissick, John. Understanding Arts . Trans. Shui Ping and Zhujun.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2003.]
朱利安·奥夫鲁瓦·德·拉·梅特里: 《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
[La Mettrie, Julien offroy de. Men is Machine . Trans. Gu Shoug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Nietzsche, Friedrich Wihelm. The Will to Power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 - -. Thus Spake Zarathustra .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 limited, 1997.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年。
[Plato.Complete Works of Plato . Trans. Wang Xiaoc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理查德·桑内特: 《肉体与石头》,黄煜文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Richard, Sennett. Flesh and Stone . Trans. Huang Yuwe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Shusterman, Richard. 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 New York & London: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斯宾诺莎: 《伦理学》,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Spinoza, Baruch. Ethic . Trans. He L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 -: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顾寿观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年。
[- - -. 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stand . Trans. Gu Shoug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安德鲁·斯特拉桑: 《身体思想》,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Strathern, Andrew. Body Thoughts . Trans. Wang Yewei and Zhao Guoxin.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Thomas Aquinas, St.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 Vol. One-II.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97.
亚·沃尔夫: 《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下册)》,周昌忠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年。
[Wolf, Abraham. A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16 th &17 th Centuries . Trans. Zhou Changzho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Title : The Decline of Dualism and the Rise of Soma-esthetics in Western Aesthetics
Abstract : Dualism has long been dominan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and it has established a hierarchical schema from the day it was born. The mind is imagined as a subjective role, while the body is regarded as a passive object that needs to be driven, enriched and guided. From the point of logic, a paradox is inherent to the schema: if the body and the mind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they canno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f their nature is the same in essence, it is equally illogical to distinguish them.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is paradox,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ody exposes itself, especially in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times when natural science continues to reveal the attribution of mental activities to the body,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he deconstruction of dualism. Along with the decline of dualism, the body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heories gradually assumes the subjectivity of its own, and a revival of the body develops in the new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s. The mid-18th century sees the aesthetics in the form of body discours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sees Nietzsche outlining the prototype of soma-aesthetics, and the 20th century, driven by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phenomenology, pragmatism and cognitive science, sees soma-esthetics upgrading to a discipline.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this process will continue and the era of soma-esthetics has just begun.
Keywords : dualism; paradox; body; subjective role; aesthetics; soma-aesthetics
作者简介: 王晓华,文学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邮政编码: 518060。电子邮箱: wangxiaohua9@163.com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体论美学视野中的西方身体艺术研究”[项目编号: 17BZW067]的阶段性成果。
Author: Wang Xiaohua , Ph.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of soma-esthetics and soma-poetics. Address: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3688, Nanyou Road, Shenzhen 518069,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wangxiaohua9@163.com This artical is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17BZW067).
(责任编辑: 王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