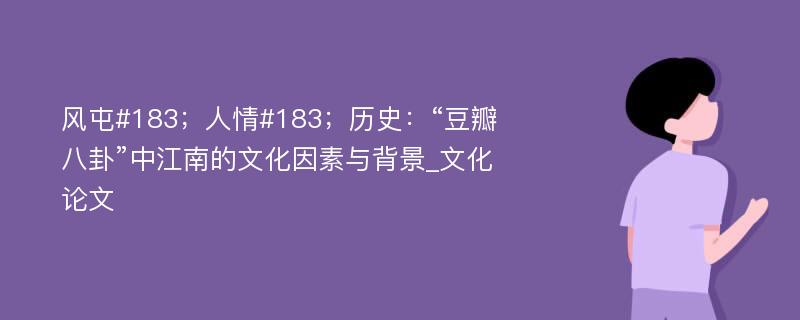
风土#183;人情#183;历史——《豆棚闲话》中的江南文化因子及生成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风土论文,因子论文,闲话论文,人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小说的文化内涵往往是很复杂的,作者的身份经历、知识背景、地域文化等,都会在作品中留下印迹。对《豆棚闲话》而言,江南文化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① 这从本书第一则的开篇即可看出:
江南地土洼下,虽属卑温,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当空。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浃背,头额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无处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凉亭水阁,摇扇乘凉,安闲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发披襟,逍遥于长松荫树之下,方可过得;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或拿几株木头、几根竹竿搭个棚子,搓些草素,周围结彩的相似。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
由于这个江南“豆棚”是作者有意设定的一个小说叙述场景,因此,它的存在与变化对全书有着一种多方面的隐喻作用,它是悠闲的、众声喧哗的,也是季节性的或者说临时的。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浸淫其中的风土、人情以及历史等江南文化因子,得到了或隐或显的表现。
一、解惑豆棚
《豆棚闲话》的康熙写刻本题“圣水艾衲居士编”、“鸳湖紫髯狂客评”,而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刊本题“圣水艾衲居士原本”、“吴门百懒道人重订”。胡适《〈豆棚闲话〉序》中说:“鸳湖在嘉兴,圣水大概就是明圣湖,即杭州西湖。作者评者当是一人,可能是杭州嘉兴一带的人。”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此书的《出版说明》则说:“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如果艾衲居士所题圣水即指此,那么他可能是杭州人。”比胡适的“杭州嘉兴一带”又进一步缩小到了杭州。而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提到此书“或云为范希哲作”,不知所据,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因为范为杭州人。美国学者韩南则提出另一个杭州小说家王梦吉可能是《豆棚闲话》的作者。③
上述推测主要是围绕“圣水”即杭州这一说法衍生的,但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问题。杜贵晨就指出:“‘圣水’指‘明圣湖’和‘圣水池’未免过于牵强;倘确指此二处,则作‘圣湖’、‘圣池’较为自然。”“若以‘圣水’指‘明圣湖’,恐古今皆不知所云,‘圣水池’的情况当亦如此”。他还以清初孙学稼自号“圣湖渔者”为证,说明“明圣湖”的省称。④ 而范希哲一号“西湖素岷主人”,径以“西湖”标榜的小说家也极多,取意于“明圣湖”又改作“圣水”,确实过于缠绕。
有鉴于此,杜贵晨据《水经注》及《豆棚闲话》中有“在下向在京师住过几年”语等,认为“圣水”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而作者的籍贯也应是房山县。不过,这一说法也存在问题。即以“圣水”论,有此称者不只一处。比如绍兴就有一处圣水,宋代嘉泰间曾任绍兴府通判的施宿撰《嘉泰会稽志》在介绍秦望山时说:“秦望山在县东南四十里,旧经云众岭最高者,舆地广记云,秦望在州城南,为众峰之杰……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谯,岘中有大城王,无余之旧都也,句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山有三巨石屹立如笋,龙池冬夏不竭,俗号圣水,傍有崇福侯庙。”⑤ 秦望山为会稽名山,与府治相对,又称南山。其中提到“龙池冬夏不竭,俗号圣水”,令人关注。这一记载在后来的《会稽县志》中也可见到,如明张元忭撰《会稽县志》卷二“山川”即有类似文字,⑥ 说明这一称谓源远流长,久为人知。如果杭州的“圣水池”可以为艾衲居士择取,绍兴的“圣水”也有同样的理由用来冠名取号,甚至可能性更大。
说艾衲居士为杭州人,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明清之际另一部小说集《跨天虹》题署“鹫林斗山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由于艾衲居士(老人)并非显赫人物,这不太可能是托名。所以,这个“鹫林斗山学者”应与艾衲居士有某种关系。《古本小说集成》影印《豆棚闲话》之《前言》(曹中孚撰),在提到艾衲居士时,除了明确说“从署名前所冠之‘圣水’,可知其为浙江杭州人”外,还进一步推测:“这种署法与另一种小说《跨天虹》卷前署名中之‘鹫林斗山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鹫林”当指杭州灵鹫峰,即飞来峰),在手法上,有它的共通之处。”按,“鹫林”一词并不多见,《全唐文》卷一八三中录王勃《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文中有“痛鹫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芜”。此处“鹫林”非指地名,当指佛寺而言,如同“鹫山”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灵鹫山的省称,因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居住和说法多年,因代称佛地。而作为寺庙名的“鹫峰”则屡见不鲜,各地均有,如《全唐文》卷七四三录裴休《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序》中有“有大禅师,法讳希运,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鹫峰下”;北京西城内原来也有一处鹫峰寺。所以,仅据“鹫林”,就认定指杭州鹫峰寺,证据是不足的。何况即使此“鹫林”就是指杭州鹫峰寺,也不足以证明艾衲居士的籍贯。《跨天虹》与《豆棚闲话》在文体、语言、叙述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别,作为小说作者的“鹫林斗山学者”应该不是艾衲居士的另一化名。
值得注意的是,《豆棚闲话》的评点者是“鸳湖紫髯狂客”,重订者是“吴门百懒道人”。“鸳湖”为嘉兴鸳鸯湖省称,“吴门”则为苏州,或特指江苏吴县,这些地方都距有“圣水”的绍兴不远。这其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倒是值得求索的。
这里,我们不妨再分析一下豆棚。豆棚本身没有地域性,北方也常见,连清代帝王诗中,也可见到这种民间风物,如《御制诗集》初集卷四三《村行》:“韭圃松畦生意足,豆棚瓠架叶声乾。”同书三集卷六○《西直门外》:“匏架豆棚一例好,豳风图里课农行。”⑦ 不过,杜贵晨先生却认为小说中的豆棚“不是著书的当时当地(指江南)习见之物,触发作者的应是北方的豆棚”。这可能就有些绝对了。他的一个根据是《豆棚闲话》的《弁言》所引的一首诗,艾衲居士是这样交待的:
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册,其所咏古风、律绝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脍炙人口,惜乎人遐世远、湮没无传,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诵其一二联句,令人神往。
余不嗜作诗,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以补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诗一首弁之,诗曰:
闲着西边一草堂,热天无地可乘凉。
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
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反生香。
晚风约有溪南叟,剧对蝉声话夕阳。
照杜先生看来,“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所描写的“正是北方少雨,池塘水浅,林木懒长的状况”。其实南方伏旱时节,池塘水浅并不足为奇。实际上,所谓《豆棚吟》中的这两句诗,又见于钱塘僧人止庵的诗作,正是南方写实。据杭州人郎瑛记载:“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钱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业者也,遭时不偶,遂□首而肆力于诗云……止庵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小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⑧ 这一故事流传较广,明万历年间进士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中也记载钱塘僧德祥止庵被诏至京,以赋诗含讥讽被戮事,所引诗与《七修类稿》相同。⑨ 这一材料不但说明“池塘”二句所描写的情景是南方的,还表明《豆棚闲话》将此诗说成徐菊潭作,有几种可能:第一,历史上确有一个徐菊潭,止庵化用了他的诗句。第二,有关止庵的故事是编造出来的,编造者借用了徐菊潭的作品。第三,止庵可能就是“徐菊潭”的法名。如此,由于艾衲居士称其为“吾乡先辈诗人”,则此诗可为艾衲居士是钱塘人作旁证。第四,徐菊潭是艾衲居士杜撰出来的,在杜撰时化用了止庵的诗。此四种可能性中,我倾向于最后一种。
关于豆棚,还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那就是小说中写的是什么“豆”。除了前文所引“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外,第八则又写:
若论地亩上收成,最多而有利者,除了瓜蔬之外,就是羊眼豆了。别的菜蔬都是就地生的,随人践踏也不计较。惟有此种在地下,长将出来,才得三四寸就要搭个高棚,任他意儿蔓延上去,方肯结实得多;若随地抛弃,尽力长来,不过一二尺长,也就黄枯干瘪死了。
第九则云:
只有藊豆一种,交到秋时,西风发起,那豆花越觉开得热闹。结的豆荚俱鼓钉相似,圆湛起来,却与四、五月间结的瘪扁无肉者大不相同。俗语云:“天上起了西北风,羊眼豆儿嫁老公”,也不过说他交秋时,豆荚饱满,渐渐到那收成结实,留个种子,明年又好发生。
从上述引文可知,艾衲居士写的是藕豆,又称羊眼豆。此豆原产印度尼西亚,15世纪初引进我国,以其实形酷似湖羊之眼而命名。各地均有出产,但江南一带似乎更盛产,特别是湖州、乌程一带,尤为著名土产。明成化《乌程县志》卷四豆类下介绍:“羊眼豆,一名黑稨豆,架棚蔓生。”⑩ 乾隆《乌程县志》卷一三“物产”:“白稨豆,又名羊眼豆,有赤白二色,俗又呼沿篱豆,亦名蛾眉豆。”(11) 清顺治四年张履祥的《补农书》上记载:“予旅归安,见居民水滨遍报柳条,下种白扁豆,绕柳条而上,秋冬斩伐柳条,可为制栲栳之用。每棵可收豆一升。”(12) 这也是江南一带种植白扁豆的实况。另外,《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四卷中则对这种豆类有更详细的描述:“扁豆二月下种,蔓生延缠。叶大如杯,团而有尖。其花状如小蛾,有翅尾形。其荚凡十余样,或长或团,或如龙爪、虎爪,或如猪耳、刀镰,种种不同,皆累累成枝。白露后实更繁衍,嫩时可充蔬食茶料,老则收子煮食。子有黑、白、赤、斑四色。一种荚硬不堪食。惟豆子粗圆而色白者可入药,本草不可入药,本草不分别,亦缺文也。”《豆棚闲话》第十则中引《食物志》对扁豆的记述,与《本草纲目》的上述记载几乎完全相同。(13)
这里,我还想补充讨论一下“豆棚”的象征性或隐喻意义。从古代文学作品来看,“豆棚”首先是农村生活的一个典型场景。文震亨《长物志》卷二“花木”中即有“豆栅菜圃,山家风味”的说法。对于小康人家,“春韭秋菘转瞬过,豆棚雨足麦风和”,“雀舌宜烹竦雨夜,豆棚欲话晚凉天”是一种安逸的生活景象。(14) 但对贫寒人家来说,种豆却可能是赖以为生的一种手段。《郎潜纪闻三笔》卷二“沈徵士不以贫窭废学”介绍吴江沈彤冠云,虽家计贫甚,但精揅六经,“尝绝粮,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斋絮衣,纂述不倦。其所著《周官禄田考》诸书,皆有功经学。所遇如此,所诣如彼,孤寒牢落之士,无自摧颓矣”。
在明清小说中,有关豆棚的描写也时常可见,如《欢喜冤家》第八回叙东阳县中一人姓崔去杭城途中投下宿店,其中就有“牧子牛衣,避在豆棚阴里”等描写。《八仙得道》第六十九回叙湖南省内,宝庆、常德一带地方“诚夫因不耐孩子们烦躁,独踞短榻,在那豆棚之下躺着,离开众人约有百步之远。躺了一会儿,清风顿起,神意俱爽。诚夫不知不觉跑到梦里甜乡去了”。文言小说中也有类似描写,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叙王生“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
其次,豆棚也是江南文化的一个意象。虽然各地都有豆棚,但在与江南有关的文学创作中,其出现的频率似乎更高一些。在明清江南一带的诗人笔下,经常使用豆棚的意象。如明代浙江嘉善人钱继登有[浣溪沙]词:“蝉避浓炎静未哗,东邻伊轧缲丝车,豆棚瓜架野人家,翠荚嫩堪浮茗气,黄鸡肥欲待姜芽。闲搔短发日西斜。”(15) 清初江苏宜兴人陈维崧的[城头月]《月下》词云:“冰轮偏向城头挂,河汉寥寥夜,一片关山,千秋楚汉,万帐更齐打。何如移向东湖舍,照豆棚架,草响溪桥,水明山店,儿女追凉话。”(16) 清初杭州人厉鄂有一首专写扁豆的[河传]词:“风飐月暗曲廊斜,别梦依依谢家,牵牛篱落挂青花,天邪,豆棚闲着他,豆花八月吹凉雨,秋深处,剪响裁吴纻,犀镇帷,换袷衣,依稀,一檐香又肥。”(扁豆又十五首见《灵芬馆诗话》)(17) 清代浙江海宁人查慎行的《豆棚为风雨所坏》则全面地描写了搭棚种植丝瓜扁豆的情形:“平生乏鲜肥,肉食非所慕,偶然营口腹,蓄念计必误。春种瓜豆苗,爱养邻孩孺,插竹就茆檐,缚绳使之固。初看弱蔓引,渐喜众叶布。丝瓜夏蚤结,落蒂甘于瓠。藊豆开独迟,白花待秋露。及兹绿垂荚,采摘在晨暮。夜来风雨狂,倾倒莫支拄。老饕自安分,物理庶可悟。托名得蛾眉,吁嗟难免妬。”(18)
第三,由于田园生活一直为文人所向往,所以,豆棚有时又成为体现文人闲散生活情趣的象征。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八载:“陈一夔,华亭人,与苏去二百里,于赵栗夫固乡人也。两人交甚厚,若兄弟然,无一会不俱者。一夔好作诗,酝藉典则,时有真诣语……田园意屡见。时各有互相赠答诗,一夔赠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豆棚瓜蔓共萧疏。胸中富有书千卷,谁笑家无儋石储。’栗夫得诗,仰面抚掌大笑,连称妙甚。众客传观,皆赏以为雅制。栗夫答云:‘风流故与时情别,樗散偏于酒趣深。未老便为投绂计,知公天性在山林。’君谦笑云:‘一夔未去,若据君言,则是一夔即今就去也。’栗夫戏曰:‘吾欲促其去耳。’筵中为之一噱。”(19)“豆棚瓜蔓共萧疏”中流露出来的潇洒之气,油然而生。
明代茂苑叶舟校《镌钟伯敬先生秘集》十七种之《谐丛》中有一条记载:“张灵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张方坐豆棚下,举杯自酬,目不少顾,其人含怒去。复过唐伯虎,道张所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讥我’。”(20) 豆棚下张灵的高傲,正是当时一些文人共有的情态。
《豆棚闲话》继承古代文学的传统,又有所发挥,在这部小说中,“豆棚”同样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学意义:
其一,它是书院与书场的结合。作品第一则有一个人物说道:“今日搭个豆棚,到是我们一个讲学书院。”可见其书院性质。但同时,这个空间更是一个书场,所以,第二则云:“再说那些后生,自昨日听得许多妒话在肚里,到家灯下,纷纷的又向家人父子重说一遍。有的道:‘是说评话造出来的。’”第八则云:“昨日,主人采了许多豆荚,到市上换了果品,打点在棚下请那说书的吃。”第十一则云:“今日还请前日说书的老者来,要他将当日受那乱离苦楚,从头说一遍。”第十二则云:“自从此地有了这个豆棚,说了许多故事,听见的四下扬出名去,到了下午,渐渐的挨挤得人多,也就不减如庵观寺院,摆圆场、掇桌儿说书的相似。”这些说法,都显示了豆棚作为一个书场的特点。
不过,小说中的豆棚又不是一般的书院或书场,它还是作者虚拟的一个饶有新意的公共舆论空间,第一则还有这样的描写:“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在接下来的各则中,我们看到,豆棚下不仅有讲故事的,也有围绕故事展开的思想交流。话题广泛,议论风生。来这里的人既是听众,也是讲者,有着平等的言论权利。显然,这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舆论空间。作为理想,它又与中国古代无是无非的桃花源境界相通,第九则众人道:“我们坐在豆棚下,却象立在圈子外头,冷眼看那世情,不减桃源另一洞天也!”
其二,在《豆棚闲话》中,作者还随时将豆棚与特定题材的主旨联系起来,用豆棚作为阐释与叙事的引子。如第四则《藩伯子破产兴家》事涉果报,故一开始就写道:
古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分明见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根,积得一分阴骘才得一分享用,人若不说明白,那个晓得这个道理?今日,大家闲聚在豆棚之下,也就不可把种豆的事等闲看过。
第八则的开头,则是作者借题发挥:
若论地亩上收成,最多而有利者,除了瓜蔬之外,就是羊眼豆了。别的菜蔬都是就地生的,随人践踏也不计较。惟有此种在地下长将出来,才得三四寸就要搭个高棚,任他意儿蔓延上去,方肯结实得多;若随地抛弃,尽力长来,不过一二尺长,也就黄枯干瘪死了。譬如世上的人,生来不是下品贱种,从幼就要好好滋培他,自然超出凡品;成就的局面也不浅陋。若处非其地,就是天生来异样资质,其家不得温饱,父母不令安闲,身体不得康健,如何成就得来?此又另是豆棚上一样比方了。
第十则批判苏州浮华空虚的社会风气,作者又写道:
这也是照着地土风气长就来的。天下人俱存厚道,所以长来的豆荚亦厚实有味。惟有苏州风气浇薄,人生的眉毛尚且说他空心,地上长的豆荚,越发该空虚了。
从这些描写看,豆棚不只是一个空洞的空间,作者还尽可能使之与情节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其三,在《豆棚闲话》中,作者的描写还与豆类生长相联系,从而赋予了作品一种既有写实性,又有象征性的时间感。我们看到,第一则所写二月中旬搭棚种豆,与前引《本草纲目》所写“二月下种”一致,随意中体现出一种生机与期待。第三则的描写是:“自那日风雨忽来,凝阴不散,落落停停,约有十来日才见青天爽朗。那个种豆的人家走到棚下一看,却见豆藤骤长,枝叶蓬松,细细将苗头一一理直,都顺着绳子,听他向上而去,叶下有许多蚊虫,也一一搜剔干净。”第六则的描写则是:“是日也,天朗气清,凉风洊至。只见棚上豆花开遍,中间却有几枝,结成蓓蓓蕾蕾相似许多豆荚。那些孩子看见,嚷道:‘好了,上边结成豆了!’”到了第九则:“金风一夕,绕地皆秋。万木梢头,萧萧作响,各色草木临着秋时,一种勃发生机俱已收敛……豆荚饱满,渐渐到那收成结实,留个种子,明年又好发生。”第十一则继续围绕“秋”叙述:
所以丰年单单重一“秋”字。张河阳《田居诗》云:“日移亭午热,雨打豆花凉。”寒山子《农家》诗云:“紫云堆里田禾足,白豆花开雁鹜忙。”
为甚么说着田家诗,偏偏说到这种白豆上?这种豆一边开花,一边结实。此时初秋天气,雨水调匀,只看豆棚花盛,就是丰熟之年。可见这个豆棚也,是关系着年岁的一行景物。
到了第十二则,作者进一步写道:
老者送过溪桥,回来对着豆棚主人道:“闲话之兴,老夫始之。今四远风闻,聚集日众。方今官府禁约甚严,又且人心叵测,若尽如陈斋长之论,万一外人不知,只说老夫在此摇唇鼓舌,倡发异端曲学,惑乱人心,则此一豆棚未免为将来酿祸之薮矣。今时当秋杪,霜气逼人,豆梗亦将槁也。”众人道:“老伯虑得深远,极为持重。”
不觉膀子靠去,柱脚一松,连棚带柱,一齐倒下。大家笑了一阵,主人折去竹木竿子,抱蔓而归。
从搭棚种豆到拆棚去蔓,时序上经历了羊眼豆的一季完整的生长期,兴致勃勃的开始,小心谨慎的结局,又扣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有趣的是,《豆棚闲话》问世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有一部文言小说集《小豆棚》体现了作者的效仿之意。而“豆棚闲话”本身,也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组,如《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中有“当下那尹先生便把这段公案照说评书一般……那些村婆村姑只当听了一回‘豆棚闲话’”。不知文康是否是袭用了《豆棚闲话》书名。但在顾震涛《吴门表隐》前面所引的诗中,也有“赢得村翁传故事,豆棚闲话晚凉天”的诗句,这种江南情景,却是与《豆棚闲话》相近的。
总之,盛产于江南的羊眼豆及豆棚的建筑,加上前面提到的会稽“圣水”以及“吴门”、“鸳湖”等,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地域范围。如果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与这一地域也有重叠之处。虽然《豆棚闲话》涉及的地域较广,作者在第三则中也说到书中朝代、官衔、地名、称呼“不过随口揪着”,不可过于指实,但其间隐约还是有一定的方位感的,如第一则“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第四则“在下去年往北生意,行至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地方”,第六则有“那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与那河南信相州交界地方,叫做恨这关”,第八则“中州有个先儿,那地方称瞎子”,第九则“在下向在京师住了几年”。这些表述都显示出叙述者以这些地方为外地的口吻,而其叙述立场显然是基于南方展开的。进而言之,十二篇作品中,只有一篇提到西湖,并没有以杭州背景的作品;与苏州及相邻地区有关的题材、描写与语言,则在在提示我们,艾衲居士及其同好们,当在狭义的江南一带寻找。
二、数落苏州
《豆棚闲话》第十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最后的总评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艾衲偏游海内名山大川,每每留诗刻记,咏叹其奇,何独于姑苏胜地,乃摘此一种不足揣摩之人?
很可惜,我们无法查证艾衲居士遍游海内名山大川的诗句。但是,这篇小说对苏州社会风气的辛辣讽刺,在整个《豆棚闲话》中确实相当突出。作者在开篇通过人物之口提到苏州风气浇薄时,这样确定了此篇故事的目的:“姑苏也是天下名邦,古来挺生豪杰,发祥甚多理学名儒,接踵不少。怎见得他风气浇薄?毕竟有几件异乎常情、出人意想之事,向我们一一指说。倘遇着苏州人嘴头刻薄,我们也要整备在肚里,尖酸答他。”这使我们想到第二则有一个与此相对的说法,当西施故里的“乡老”称西施只不过是个“老大嫁不出门的滞货”,大扫了一个来此寻美选女的“吴中”士夫宦的兴,众后生拍手笑道:“这老老到有志气占高地步,也省得苏州人讥笑不了。”时刻防备着应付“苏州人嘴头刻薄”。这种有意与苏州不良风气区隔的叙述立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作者就是苏州一带的人,这样的叙述与篇中所引的苏州竹枝词一样,体现了作者的刻意自嘲。这是可以找到旁证的,例如冯梦龙生于苏州(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人),天许斋本《古今小说》又是在苏州刊印的。此书卷九《吴保安弃家赎友》中,在“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处有一眉批:“苏州人尤甚,可恨可笑。”这一批语是借题发挥的,与作品所述人物的籍贯及活动范围并无关系。而我们知道,如果这一批语出于冯梦龙之笔,(21) 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下笔之际似乎也是针对着当地的读者群。事实上,艾衲居士对苏州的认知可能相当深细,如《豆棚闲话》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描写了空青产生的传说及其治眼疾的神奇功效。所谓空青,据说是一种碳酸盐类矿物蓝铜矿的矿石,成球形或中空者,在传统医学中经常使用,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明目。早在宋词中就有“明眼空青”(黄庭坚),“休觅空青眼自明”(向子諲)的词句,《普济方》、《本草纲目》等书也有记载。但《豆棚闲话》此则故事由苏州城展开,却令人想到《吴门表隐》卷一中的一条记载说:“空青膏治目疾如神,东白塔子里赵渊世传。其九世祖瑢,正统初遇仙所遗。”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作者生活在离苏州不远的乡间,对苏州人怀有某种“敌意”。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就是上面提到那个有着“圣水”的西施之乡或盛产羊眼豆的乌程等地。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这篇小说也是全书地域色彩最为鲜明的。这首先表现在小说的语言上,虽然在其他各篇也时有方言词汇,但本篇苏州方言的运用,却极为突出,如下面一段:
却不知老一早已梳洗停当,正在厨房下就着一个木盆洗脚,连声道:“不要进来。”强舍早已到了面前,吃了一惊道:“老一,我向来在你个边走动,却不晓得你生了一双干脚。”老一道:“小乌龟又来嚼蛆哉!那亨是双干脚?”强舍道:“若勿是干脚,那亨就浸涨子一盆?”老一挠起脚来,把水豁了强舍一脸。骂道:“臭连肩花娘,好意特特送个孤老把你,到弄出多呵水来!”老一道:“真个?”即便拭子脚,穿上鞋与那衫子,出来接着。我不懂吴语,从相关文献中得知,“那亨”、“若勿”之类都是苏州方言。而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有意将方言、方音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刻画巧妙地融为一体,如篇中有这样一段:
马才道:“咱也不耐烦呷茶,有句话儿问你,这里可有唱曲匠么?”和尚语言不懂,便回道:“这里没有甚么鲳鱼酱。若要买玫瑰酱、梅花酱、虾子鲞、橄榄脯,俱在城里吴趋坊顾家铺子里有。”马才道:“不是。咱今日河下觅了一个船儿,要寻个弹弦子、拨琵琶、唱曲子的。”和尚方懂得,打着官话道:“我们苏州唱曲子的,不叫做匠,凡出名挂招牌的,叫做小唱,不出名、荡来荡去的叫做清客。”
马才是“西北人”,他与本地和尚的对话反映了不同口音造成的误会,而这种误会不但增强了叙事的本真性,而且点出了和尚的油嘴滑舌,突出了马才作为外地人而受骗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说,作者在引述苏州竹枝词时说的“略带吴中声口,仍是官话,便于通俗”,也可以看作本篇最基本的语言风格。也就是说,作者在运用方言的分寸上掌握得较好,而运用方言的主要目的则是强化地域性。
对于这篇小说来说,地域性更突出地表现还是在入木三分地刻画苏州的世态人情上。作者以虎丘为背景,这是苏州最为著名的景点,但在艾衲居士看来,这一景点多少有点名不符实:“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一时也说不尽。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实际上,其他小说家也有类似的批评,如清代李百川《绿野仙踪》第十回也描写人物“后到苏州,又看了虎丘,纯像人工杂砌,天机全无,不过有些买卖生意,游人来往而已。心中笑道:北方人提起虎丘,没一个不惊天动地,要皆是那些市井人与有钱的富户来往走动,他那里知道山水中滋味”。虽然景致不足为奇,这座虎丘山却“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砑光的人”,他们的买卖“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仅外地人称之为“空头”,《豆棚闲话》还特意引用了20余首“本地有几个士夫才子”所作的竹枝词,“数落”虎丘山沿岸商家。姑举3首,以见一斑。如《茶叶》诗:“虎丘茶价重当时,真假从来不易知。只说本山其实妙,原来仍旧是天池。”《相公》诗:“举止轩昂意气雄,满身罗绮弄虚空。拚成日后无聊赖,目下权称是相公。”《和尚》诗:“三件僧家亦是常,赌钱吃酒养婆娘。近来交结衙门熟,篾片行中又惯强。”竹枝词讽刺了苏州虚多实少的社会风气。这是一个背景,也是一种态度。在做了上面的铺垫后,作者的笔锋转向了重点讽刺的对象:
更有一班却是浪里浮萍,粪里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块,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叫做老白赏。这个名色,我也不知当初因何取意。有的猜道说这些人,光着身子,随处插脚,不管人家山水园亭,骨董女客,不费一文,白白赏鉴的意思。一名蔑片,又叫忽板。这都是嫖行里话头。譬如嫖客本领不济的,望门流涕,不得受用,靠着一条蔑片,帮贴了方得进去,所以叫做“蔑片”。大老官嫖了婊子,这些蔑片陪酒夜深,巷门关紧,不便走动,就借一条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叫做“忽板”。
就情节而言,本篇并不复杂。作品叙西北商人马才到苏州寻欢作乐,与清客们发生冲突,将清客们打落水中。老清客贾敬山得知此事后,欲筹组清客联盟,恰好有人通报,谢任回家的通政刘谦,路过苏州,有意买些古董和唱戏的小子丫头。贾敬山当即凑上去,要将外甥女和邻家小囡假意卖给刘公。又有一个叫顾清之的清客主动要求为刘谦所买丫头小子教戏。贾敬山揭露顾清之行为不轨,刘谦得以发现顾与自己宠好的小子在行苟且之事,于是更加信任贾敬山,贾由此深得刘谦信任,赚取不少好处,但所得银子竟为贼所盗偷。因交不出刘谦要买的两个丫头,以致赔了亲生女儿,并与顾清之一同发配京口。
对于所谓的“苏空头”,作者是十分轻蔑的。这在《豆棚闲话》第二则就有表现,其中嘲笑吴王夫差是苏空头:“(西施)学了些吹弹欲舞,马扁的伎俩,送入吴邦。吴王是个苏州空头,只要肉肉麻麻奉承几句,那左右许多帮闲篾片,不上三分的就说十分,不上五六分就说千古罕见的了。”
实际上,这也不只是作者个人的态度,在一些明清笔记文献与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关苏州社会风气浮华的记述与讽刺。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三有所剖析:“姑苏虽霸国之余习,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为拙也!”
在众多记载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苏空头”的制假贩伪,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假骨董”条就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不但骨董如此,日常交易也如此。明代叶权《贤博编》说:“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挦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前引假茶叶竹枝词,在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六一回还有详细的揭露:“近来,吴门有数百家以泡过茶叶晒干,妄加药料,诸般制造,竟与新茶无二。”
“苏空头”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据《绣谷春容》所录“金陵六院市语”记载,“言说谎作‘空头’”。对此,在明清文学中也常有描写,如《陶庵梦忆》卷二《鲁藩烟火》记载一苏州人,自夸其州中灯事之盛,人笑其诞。这似乎成了外地人心目中苏州人的一个形象特征,《笑林广记》卷一二有一个“两企慕”的笑话,就嘲笑苏州人的夸口:“山东人慕南方大桥,不辞远道来看。中途遇一苏州人,亦闻山东萝卜最大,前往观之。两人各诉企慕之意。苏人曰:‘既如此,弟只消备述与兄听,何必远道跋涉?’因言:‘去年六月初三,一人自桥上失足堕河,至今年六月初三,还未曾到水,你说高也不高?’山东人曰:‘多承指教。足下要看敝处萝卜,也不消去得,明年此时,自然长过你们苏州来了。’”(22)
所以,在《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苏州人文若虚,在荒岛上看到一个巨大龟壳,大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世上人那里曾看见?说也不信的……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与人看看,省得空日说着,道是苏州人会调谎。”
明代以来还有不少笑话对“苏空头”加以讽刺。如明代“陈眉公先生”辑《时兴笑话》卷下有一则“苏空头”:
一帮闲苏州人,谓大老官曰:“我为人替得死的。”一日,大老官病将笃,医生曰:“非活人脑子不能救矣。”大老官曰:“如此我得生矣。”遂谋之苏人,苏人曰:“非是我不肯,我是‘苏空头’,是没有脑子的。”(23)
值得称道的是,《豆棚闲话》在讽刺艺术的运用上,也有创造性,如作品描写贾敬山得知有个刘谦要在苏州买些文玩古董,寻添几个小子丫头,“不觉颠头簸脑,不要说面孔上增捏十七、八个笑靥,就是骨节里也都扭捏起来。连声大叔长、先生短,乘个空隙,就扯进棚子里吃起茶来”。而他的介绍人向刘谦称扬道:“他技艺皆精,眼力高妙,不论书画、铜窑、器皿,件件董入骨里。真真实实,他就是一件骨董了。”但是,当刘谦叫书童取那个花罇来与贾敬山赏鉴时:
那书童包袱尚未解开,敬山大声喝采叫好。刘公道:“可是三代法物么?”敬山道:“这件宝贝,青绿俱全,在公相宅上收藏,极少也得十七、八代了。’”刘公笑道:“不是这个三代。”敬山即转口道:“委实不曾见这三代器皿,晚生的眼睛、只好两代半,不多些的。”刘公又取一幅名公古笔画的《雪里梅花》出来与看,四下却无名款图书。敬山开口道:“此画公相可认得是那个的?”刘公道:“宋元人的。不曾落款,到也不知。”敬山道:“不是宋元,却是金朝张敞画的。”刘公又笑一笑,道:“想是这书画骨董足下不大留心。”
这一段描写极为生动,活现出贾敬山的“空头”本质,其讽刺手法也富有创造性。
苏州的世态人情当然不是孤立的,作者在小说中写道:“俗语说的甚好—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都是有名无实的。”这一俗语又见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见虚诈不实的风气相当普遍,因此,本篇虽是针对苏州的不良风气有感而发的,但它的意义却不限于一时一地。
三、唐突西施
如果说《虎丘山贾清客联盟》反映了现实的世态人情,《豆棚闲话》的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则是以历史人物及故事为题材,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阐发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是文学史上的热门题材。据记载,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人。其地在今河南南阳一带,但《范少伯水葬西施》却强调“即今吴江县地方,原自姑苏属县”,意在拉近主人公与苏州的联系。范蠡出仕越国。公元前494年,句践伐吴,范蠡谏阻,不听,遂遭失败。范蠡随句践质吴三年,夫差劝其弃越投吴,委以重任,范不为所动。含垢忍辱,卑辞厚赂,终使句践化险为夷,平安返越。及归国,与文种鼎力辅佐越王。句践奋发图强,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兴越灭吴,完成句践称霸大业。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乘舟浮海,离越适齐,化名“鸱夷子皮”,经商治产,获利千万,受任齐相。后弃官散财,间行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逐什一之利,复赀累千万,自号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和《货殖列传》及《越绝书》、《吴越春秋》均有记述。
西施,姓施,名夷光,又称西子。春秋末期越国句无(今诸暨市)苎萝村人,以家住村西而得名,秀媚出众。句践自吴归国,卧薪尝胆,誓报吴仇。闻吴王淫而好色,乃使相者于苎萝山下得西施,“饰以罗觳,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吴王大悦,认为“越贡二女,乃句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对西施宠爱有加。西施身在吴国,一心向越。句践灭吴班师回越,携西施而归。一说被越王视为亡国不祥之物,沉于江中;另一说为西施归越后随大夫范蠡驾扁舟入五湖(今太湖),不知所终。(24)
与《介子推火封妒妇》《首阳山叔齐变节》一样,《范少伯水葬西施》也是一篇历史题材的翻案小说。作者在展开叙述之前,特别提到了此一题材的经典作品《浣纱记》,但作者只将其看作是“戏文”,却自我作古地通过人物之口说:
我却在一本野史上看见的,却又不同。说这西子住居若耶溪畔,本是一个村庄女子。那时做官的人看见富贵家女人打扮,调脂弄粉、高髻宫妆,委实平时看得厌了。一日山行,忽然遇着淡雅新妆波俏女子,就道标致之极,其实也只平常。又见他小门深巷,许多丑头怪脑的东施团聚左右,独有他年纪不大不小,举止闲稚,又晓得几句在行说话,怎么范大夫不就动心?那曾见未室人的闺女就晓得与人施礼,与人说话?说得投机,就分缕所浣之纱赠作表记?又晓得甚么惹害相思等语?一别三年,在别人,也丢在脑后多时了,那知人也不去娶他,他也不曾嫁人,心里遂害了一个痴心痛病。及至相逢,话到那国势倾颓,靠他做事,他也就呆呆的跟他走了。可见平日他在山里住着,原没甚么父母拘管得他,要与没识熟的男子说话,就说几句,要随没下落的男子走路,也就走了。
接下来的故事框架虽然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但人物的动机、行为方式与作者的叙述方式都有了变化。特别是“功成身退”之际:
那知范大夫一腔心事,也是徼悻成功……到那吴国残破之日,范大夫年纪也有限了,恐怕西子回国,又拖旧日套子断送越国,又恐怕越王复兴霸业,猛然想起平日勾当有些不光不明,被人笑话……故此陡然发了个念头,寻了一个船只,只说飘然物外,扁舟五湖游玩去了……平日做官的时节,处处藏下些金银宝贝,到后来假名隐姓,叫做陶朱公。“陶朱”者,逃其诛也。不几年间成了许多家赀,都是当年这些积蓄,难道他有甚么指石为金手段,那财帛就跟他发迹起来?许多暧昧心肠,只有西子知道。西子未免妆妖作势,逞吴国娘娘旧时气质,笼络着他,那范大夫心肠却又与向日不同了,与其日后泄露,被越王追寻起来,不若依旧放出那谋国的手段,只说请西子起观月色。西子晚妆才罢,正待出来举杯问月,凭吊千秋,不料范大夫有心算计,觑者冷处,出其不意,当胸一推,扑的一声,直往水晶宫里去了。
在上述描写中,西施不仅不美丽,而且是“一个老大嫁不出门的滞货”;范蠡的清高形象也受到了玷污,而范蠡谋害西施,更彻底颠覆了《浣纱记》中的爱情叙述。虽然作者的这种描写可能更符合历史的事实,但这并不是作者的目的。作者的目的是与本书的其他篇目、特别是那几篇历史题材作品一样,是为了“解豁三千年之惑”,启发人们以更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我在《一队夷齐下首阳——谈〈首阳山叔齐变节〉》(《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一文中曾说:“艾衲居士正是力图以常人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将被时间过滤成观念和符号的人物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于是,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悖谬、真实的虚伪和人性的矛盾,而这可以说是超前的逆向思维所赋予作品的深刻的启发意义。”他对西施故事的重塑,也是如此。
其实,本篇的翻案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为了给翻案作注脚,艾衲居士借老者之口称:“《野艇新闻》有《范少伯水葬西施传》,《杜柘林集》中有《洞庭君代西子上冤书》一段,俱是证见。”这两篇作品也无从查证,不知是作者的狡狯之言,还是确有这样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徐石麒的杂剧《浮西施》,居然也描写了范蠡将西施沉于湖中的情节。可惜他的生卒年也不详,所作与《豆棚闲话》之先后及是否有影响关系,难以遽定。不过,如果从更开阔的视野考察,范蠡与西施的故事确实存在着翻案的基础。
如上所述,西施的结局中,历史上就有两种说法,而本篇也可以说正是捏合这两种说法,又加以发挥而成。而艾衲居士很善于在历史叙述的缝隙中寻找想象的空间,与《首阳山叔齐变节》一样,他也追溯至传统的经典。《孟子》卷八《离娄章》下孟子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对此,作者加以曲解,说这是因为西施“葬在水里,那不洁之名还洗不干净哩”。另一个曲解是:“他若不葬在水里,当时范大大何必改名鸱夷子?鸱者,枭也;夷者,害也。西施一名夷光,害了西施,故名鸱夷。”
实际上,在历史文献中,还存在一些对此一本事的更明确的异说,尤可注意的是,这些异说也与江南一带有关,它们也可以说构成了艾衲居士翻案的又一思想基础。如周密《齐东野语》卷七《鸱夷子见黜》记载:
吴江三高亭祠鸱夷子皮、张季鹰、陆鲁望。而议者以为子皮为吴大讐,法不当祀。前辈有诗云:“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盖深非之。后有戏作文弹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圣经是诛。今有窃高人之名,处众恶之所,有识之士,莫不共愤,无知之魂,岂当久居。”又云:“范蠡,越则谋臣,吴为敌国。以利诱太宰嚭,而脱彼勾践,鼓兵却公孙雄,而灭我夫差。既遂厥谋,反疑其主。鄙君如乌喙,累大夫种以伏诛,目己曰鸱夷,载西施子而潜遁。”又云:“如蠡者,变姓名为陶朱,诡踪迹于江海,语其高节则未可,谓之智术则有余。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泽三高之首。况当此无边胜境之土,岂应著不共戴天之讎。”云云。
虽然吴地有祭祠范蠡的,但从周密所引批评诗文可知,也有不少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并由此对范蠡的品节加以质疑。
张岱的《夜航船》卷四《考古部》有“女儿乡”条则提到:“吴败越,句践与夫人入吴,至此产女而名。今误传范蠡进西施于吴,与之通而生女,殊为可笑。”从这一记载我们可知,民间甚至有范蠡与西施私通而生女的传说,不论其倾向性如何,至少它表明范蠡、西施的故事在历史上是有附会和改动的。
在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变异以及发挥改造的可能。翟灏《通俗编》卷二二《妇女》引《复斋漫录》云:“情人眼里有西施,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其答益公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斯为得。’”(25) 这一流传久远的谚语与黄庭坚的诗,无非是说西施之美,出于主观。《豆棚闲话》中说:“那时做官的人看见富贵家女人打扮,调脂弄粉、高髻宫妆,委实平时看得厌了。一日山行,忽然遇着淡雅新妆波俏女子,就道标致之极,其实也只平常。”强调的也是这种主观性。李渔《十二楼》之《奉先楼》第一回中更有一段否定西施的言论:“当初看做《浣纱记》,到那西子亡吴之后,复从范蠡归湖,竟要替他羞死!起先为主复仇,以致丧名败节,观者不施责备,为他心有可原;及至国耻既雪,大事已成,只合善刀而藏,付之一死,为何把遭瑕被玷的身子依旧随了前夫?人说她是千古上下第一个绝色佳人,我说她是从古及今第一个腆颜女子。”这一说法,与艾衲居士的思路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清况周颐《餐樱庑随笔》第十一则提到“大底刻溪之士,好为翻成案杀风景之言,往往莛可以楹,西施可以厉”。不知况周颐是否有所指,但也说明“西施可以厉”在翻案文学中是不足为奇的。
在《范少伯水葬西施》最后,还有一段对苏轼西湖诗的评论,这一评论,我们在明嘉靖进士唐时(浙江乌程人)人的《与徐穆公》信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翻案之论:“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为誉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则寓乎其间乎?可见古人比类之工,寓讽之隐,不言西湖无有丈夫气,但借其声称以誉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耳。”(26)
对艾衲居士来说,对西施故事的翻案不仅有一定的基础,也许还有现实的意义。甲申之变以后,明朝官员降清者不计其数,《豆棚闲话》中说范蠡“以吴之百姓,为越之臣子代谋吴国,在越则忠,在吴则逆。越王虽在流离颠沛之中,那臣子的本末、君臣的分际,却从来是明白在心里的”。这样的议论,在清初是发人深省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作者影响较大的可能还有另一种来自民间、传之久远,而且与江南有关的文化传统。作者为了“证明”范蠡水葬西施的真实性,又说:
至今吴地有西施湾、西施滨、西施香汗池、西施锦帆泾、泛月陂,水中有西子臂,西施舌、西施乳,都在水里,却不又是他的证见么?
本来,据历史文献记载,绍兴一带有大量越国遗迹,其中又有很多涉及西施故事。它们都可能强化作者的认识、触发作者的想象,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嘉泰会稽志》等书记载“苦竹城”为范蠡子之封邑;“美人宫”则是句践教习美女西施、郑旦之所。此外,还有“西施山”等。但是熟悉江南一带自然环境的作者,却没有提及上述地名,而是有意罗列了与上述“水”有关的地名与名物。
这些与水有关的地名,有些是名胜,如锦帆泾。《吴郡志》卷一八:“锦帆泾,即城里沿城濠也。相传吴王锦帆以游,今濠故在,亦通大舟。间为民间所侵,有不通处。”袁宏道《锦帆集》中也有一篇《锦帆泾》专记其地。但西施湾、西施滨、西施香汗池等地,未于文献中查证,不知是否确有其地。至于艾衲居士提到的那些名物特产,虽出于后人的附会,却也屡见记载,如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称:“天下凡物之尤美者,皆托喻西子,如称藕为西子臂,吴人呼河豚腹腴为西子乳,吾乡海错有西子舌是也。”
所谓“西子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六云:“‘一弯西子臂,七窍比干心。’咏藕诗也。相传卫文节公作,未知是否。”可见此一说法早已产生。
所谓西施舌,实为一种海产品,似蛤蜊而长,壳白,足突出长二寸许,如人舌,肉鲜美。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四引《诗说隽永》云:“福州岭口有蛤属,号西施舌,极甘脆,其出时,天气正热,不可致远。吕居仁有诗云:海上凡鱼不识名,百千生命一杯羹,无端更号西施舌,重与儿曹起妄情。”(又见《诗话总龟》后集卷四九)西施舌甚得食客发好评,如明周亮工《闽小记》卷二载:“画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闽中海错,西施舌当列神品。”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也说:“所谓‘西施舌’者,状其形也。白而洁,光而滑,入口咂之,俨然美妇之舌,但少朱唇皓齿牵制其根,使之不留而即下耳。此所谓状其形也。若论鲜味,则海错中尽有过之者,未甚奇特,朵颐此味之人,但索美舌而咂之,即当屠门大嚼矣。”清代词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九还有一首[清波引]专咏西施舌。
所谓“西施乳”,实为河豚腹中肥白的膏状物。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四称河豚“吴人珍之,目其腹腴为西施乳。予尝戏作绝句云:‘蒌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时,甘美远胜西子乳,吴王当日未曾知。’虽然,甚美必甚恶。河豚,味之美也,吴人嗜之以丧其躯;西施,色之美也,吴王嗜之以亡其国。兹可以为来者之戒。”(又见《诗话总龟》后集卷四九)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李时珍《本草纲目》鳞部卷四四、谢肇淛《五杂俎》卷九物部一、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七、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等也都有记载和描写。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还说:“夫西施,一美妇也,岂乳亦异于人耶?顾千载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则夫差之亡国非偶然矣。”
有关这些物产,梁辰鱼《浣纱记》第三十四出《思忆》有一段插科打诨:
[净]不要说大王爷见了娘娘欢喜。就是我前日娘娘要我做嘴。我勉强与他做得一做。满口儿都是香甜的。[末]说谎。难道娘娘要你做嘴。[净]你不晓得,福建前日进一种海味,唤做西施舌,被我偷些尝尝,妙不可言,这就是与娘娘做嘴一般了。[末]好话。[丑]娘娘前日乳痒,也央我搔乳,我便吮他一吮,不觉满身都麻瘼了。[末]又说谎,难道娘娘要你搔乳?[丑]不瞒你说,前日吴淞江进上河豚白来,唤做西施乳,大王爷吃剩了,也被我尝得一尝,妙不可言,这便是吃娘娘的乳一般了。[末]一发好淡话。若依二位这等说,我也曾枕娘娘的臂哩。[净、丑]却怎么?[末]前日金坛进上莲花藕,白又白,嫩又嫩,唤做西施臂。常时伏侍大王爷在水殿上,到夜间困倦打盹,就把他来做个枕头,这就是枕娘娘的臂一般了。(27)
这段台词充满戏谑的意味,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上述材料,意在说明,西施早已成为古人的一个“意淫”的对象,而这种轻漫、随意,也形成了对其故事加以改造乃至颠覆的氛围。《世说新语·轻诋》有一句“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施也!”可见,“唐突西施”是古已有之的,只是有的唐突可能是无意的低水平的,或是狎玩的,鸳湖紫髯狂客在第二则、第七则的评语中,两度使用“唐突西施”一词,却表明了这是艾衲居士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追求。
综上所述,豆棚之设展示了江南的自然特点及文化基础,对“苏空头”的批判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江南特定区域的世态人情,而西施的故事则反映了江南文化的历史传统,正是风土、人情、历史,构成了《豆棚闲话》与江南文化的不解之缘。换言之,没有江南文化的影响,就不会有《豆棚闲话》这一富有特色的小说产生。
注释:
① 关于“江南”的范围,历史上有变动,其政治、经济、文学、气象、地理意义也不完全一致,本文指今苏南、浙北一带,参见《江南到底在哪里?》,《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3期专辑中诸文。
②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4页。
③ 参见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译本),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1、225页。顾启音在中华书局2000年版《豆棚闲话·醒梦骈言》前面的《豆棚闲话序说》中,持相同观点。
④ 参见杜贵晨:《论〈豆棚闲话〉》,《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除本文涉及的作者地域性问题外,杜贵晨有关小说中陈斋长与作者的关系论述,富有启发意义。
⑤ 此据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嘉庆刊本。
⑥ 此据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万历三年刊本。
⑦ 《御制诗集》,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参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另据《明史》,德祥有《桐屿诗》一卷,未见。
⑨ 《豆棚闲话》中第二则提到《野艇新闻》、《杜柘林集》等,均无从查考,可能也是作者杜撰。又第十一则引寒山子《农家》诗云:“紫云堆里田禾足,白豆花开雁鹜忙。”亦未查得出版。元剧《四丞相高会丽春堂》第二折曲词有“紫云堆里月如眉”句。《高启集》卷一七《偶睡》中则有“白豆花开片雨余”句。
⑩ 此据《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26辑影印本。
(11) 此据《续修四库全书》七○四史部地理类影印本。
(12) 此据《四库存目丛书补编》第八○册影印本。
(13) 《豆棚闲话》所引《食物志》未详何书,李渔《闲情偶寄》中也曾提到过《食物志》。
(14) 两诗分见《天咫偶闻》卷九、《履园丛话》卷八。
(15) 此据见《明词综》,又见《御选历代诗余》卷七。
(16) 《陈迦陵文集》,《四部丛刊》本。
(17) 《樊榭山房集集外词》,《四部丛刊》本。
(18) 《敬业堂诗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按,《本草纲目》中白藕豆—名娥眉豆。
(19) 《列朝诗集》丙集第六、《明诗综》卷二九均录有陈章此诗。《列朝诗集》丁集第十六引邹迪光《沈长山山庄绝句三首》有“豆棚欹侧侵书架”句,宋荦《西陂类稿》卷九《过北兰寺四首》有“豆棚连曲牖,竹径转虚堂,图史心无着,茶瓜味总长”句,都表现了相同的情趣。
(20) 此据陈维礼、郭俊峰主编:《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1卷,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6页。按,张灵,字梦晋,明中叶苏州画家,与唐寅比邻相善,又同为府学生员,故交谊最深。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子”,性落拓嗜酒,好交游,醉即使酒作狂。
(21) 胡万川《三言叙及眉批的作者问题》(台湾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认为,“三言”的编、叙、评、校均系冯梦龙。袁行云《冯梦龙“三言”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和陆树伦《冯梦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也认定,“三言”所署评校者“绿天馆主人”、“可一居士”、“无碍居士”、“墨浪主人”都是冯梦龙的化名。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杨晓东《〈古今小说〉序作者考辨》(《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就认为“绿天馆主人”应是江南名士叶有声。另外,从话本小说来看,提及苏州的作品不少,《喻世明言》5篇、《警世通言》9篇、《醒世恒言》5篇、《初刻拍案惊奇》8篇、《二刻拍案惊奇》9篇,“三言二拍”合计有36篇,这在话本小说中数量属多的。
(22) 此则笑话《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4卷所收《笑林广记》未录,待查。
(23) 陈维礼、郭俊峰主编:《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1卷,第771页。另,这一则笑话又见于游戏主人辑《笑林广记》卷七“借脑子”,《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4卷,第149页。
(24) 关于西施的下落,历代说法不一,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八《范蠡西施》有辨析。而在宋元以来的戏曲当中,西施也有“妖姬”、巾帼英雄、覆国罪人等不同形象,清代徐石麒《浮西施》还有西施被斥为妖孽而沉江的描写。参见金宁芬:《我国古典戏曲中西施形象演变初探》,《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25) 据《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94册影印本。另按,或谓《复斋漫录》即吴曾《能改斋漫录》,但今本《能改斋漫录》未见此条。
(26) 周在浚编:《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赖古堂刻本。
(27) 《梁辰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