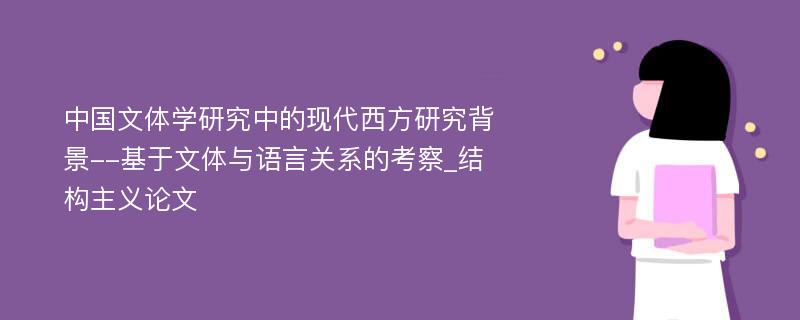
汉语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西学背景——基于文体与语言之关系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汉语论文,西学论文,背景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2-0164-08
汉语文体学研究的三大分支(文艺学、语言学和文学史)①,不约而同地关注文体理论之中的语言问题,关注文体与语言之关系。究其根源,既是对自身文化及文学传统的赓续,更是对西方20世纪以来文学及语言学理论的借鉴。诚然,中西文体学理论有着各自的传统:在西方,是肇始于轴心期时代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在中国,同样是肇始于轴心期时代的孔儒的“慎辞”心态,和庄子“得意忘言”旗帜下的“三言”驰骋。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语境下汉语文体学研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一方面秉承了自身的理论传统,同时与西方现代文化及文论的语言学转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厘清汉语文体研究的现代西学背景,则难于把握文学及语言学理论的中外交汇和古今通变对汉语文体学之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制约及影响。
就语言与文体的关系而论,语言既是构成文体的基本要素,又是同一类文体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还是新的文体取代旧的文体以及不同文体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准。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对中国文体意识和文体理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语言层面,并表现为对语言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体和文体学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源头上考察,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孕育及诞生即以“语言”为其胎记:一个是1915年成立的,以雅可布逊(又译为雅克布逊或雅科布森)为领袖的莫斯科语言小组;另一个是1916年成立的,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人物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出现于20世纪初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虽然在俄国国内只存活了十多年,但她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批评的源头,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的发展走向,还和新批评及语言结构主义一起,影响到近三十年来中国文论文体意识的复苏和成熟,影响到汉语文体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一、语言表达激活思想
在中国古代,《尚书》的“诗言志”是文学理论的开山的纲领,稍后有《乐记》和《诗大序》的“(诗和乐)吟咏情性”,再往后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言志也好,缘情也罢,文学作品总是想着要表达出什么,总是想着要怎么去表达。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维克多·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将文学要素表述为“什么”与“怎么”:
其实,艺术中这种“什么”与“怎么”的划分,只是一个约定的抽象。爱情、郁闷、痛苦的心灵搏斗、哲学思想,等等,在诗中不是自然而有,而是存在于它们在作品中借以表达的具体形式之中。因此,从一方面看,形式与内容(“怎么”与“什么”)的约定对立,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融合于审美对象。在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同理,任何形式上的变化都已是新内容的发掘,因为,既然根据定义来理解,形式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那么空洞的形式是不可思议的。②
人们习惯于将“诗”(文学)所言说的“志”或“情”称之为“内容”,而所谓“内容”能够独立存在吗?不能,它们只能“存在于在作品中借以表达的形式之中”,因此,离开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去谈“内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日尔蒙斯基关于文学艺术作品之“什么”与“怎么”的划分,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可表述为“说什么”与“怎么说”,或者表述为语言的言说对象与语言的言说方式。正是以“语言”为中心,维克多·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还谈到了文体的分类,将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分为实用语、科学语、演说语和诗语,并指出“科学语是无形态语言”,而“诗语是按照艺术原则构成的。它的成分根据美学标准有机地组合,具有一定的艺术含义,服从于共同的艺术任务”③。文学文体(诗语)与非文学文体(科学语)的根本区别在于语言,前者依据艺术原则并根据美学标准,而后者是无形态的。可见语言是文体构成的基本层面,因而也是文体划分的基本层面。
维克多·日尔蒙斯基在《论“形式化方法”问题》一文中,还提出“作为程序的艺术”的重要命题:“艺术中的一切都仅仅是艺术程序,在艺术中除了程序的总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别的东西。”④论及“程序”在艺术中的特殊地位,日尔蒙斯基引用了俄国形式主义创始人雅可布逊的一句名言:
如果文学科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把“程序”看成是它唯一的“主角”。⑤
“程序”(device)这个词,亦可译为手段、方式、技巧、途径,等等,比如,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论代表作《作为程序的艺术》,又被译为《作为手法的艺术》,还被译成《作为技巧的艺术》。关于“程序”的诸多译名,均可归于“形式”一类,而形式主义之为形式主义,就在于他们将程序、手段、方式、技巧、途径等属于“形式”(亦即“怎么”)范畴的东西,看得比结局、目的、意图、思想、效果(亦即“什么”)更为重要,将文学的“怎么说”(言说方式),看得比“说什么”(言说对象)更为重要。此外,日尔蒙斯基讨论“程序”等“形式主义方法”,还引用了康德的美的公式:“美是那种不依赖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并认为康德“在这句话中表达了形式主义学说关于艺术的看法”⑥,从而将形式主义的美学渊源追溯到德国古典美学。
俄国形式主义对“形式”的看重,是出于对文学研究之独立性的追求。文学研究(我们今天称之为“文艺学”或“文艺理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是自足自立、自成体系和自成格局的,她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落到实处就是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关于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也有一句名言:“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⑦什克洛夫斯基指出:由于艺术是独立的世界,因此“我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是文学的内部规律”;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因是形式,“新形式不是为了表达内容而出现的,它是为了取代已经丧失艺术性的旧形式而出现的”⑧。
什克洛夫斯基这里所说艺术性,也就是文学性。文学性的根本问题是语言形式,俄国形式主义认为,只有陌生化的语言形式才能产生文学性。所以,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文学之不死生命的获得,最为关键之处就在于:不断地用新的语言形式取代旧的语言形式,用新的文体取代旧的文体。关于后一种“取代”,中国古代文论称之为“破体”。所谓“破体”,就是文学语言之陌生化,就是文学性之生成,就是文学形式之通变。佛克马《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在评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特尼亚诺夫的文体理论时,也谈到了“破体”问题:“按照特尼亚洛夫的看法,既不能给文学,也不能给体裁下静止的定义。体裁是漂浮着的系统,在适当时候放弃某些技艺,吸取另一些技艺。正像我们大家都从文学史中看到的,体裁在某一时刻出现,会在不同的条件下消失。……只有在跟传统的体裁对抗的情况下才能看到新体裁。他大胆地概括说,当一种体裁衰落时,便从文学领域的中心转入边缘地带,而新的文类现象则会从文学的落后地区涌现出来,取得其中心地位。”⑨从根本上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或者说,文学语言陌生化的陶钧熔铸,需要破体,需要不断地用新的语言形式取代旧的语言形式。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的旗帜上没有任何政治城堡的颜色,但一定醒目地书写着两个大字:语言。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性(文学语言陌生化)的标举,对文学之独立性的追求,是对它之前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反拨。在后者看来,思想和情感是最为重要的,语言只不过是用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目的是最重要的,而工具是不重要的。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语言)表达比思想和情感更为重要。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艺术语与实用语》提出“表达意向”这一概念,指出与实用语相比,艺术语“更加重视表达本身”,“这种对表达的高度重视被称为表达意向”,甚至认为“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本体价值”:
不要以为,“表达意向”会有损于思想,会使我们只注意表达而忘记了思想。其实正相反,注意表达自身,更能活跃我们的思想,并迫使思想去思考所听到的东西。反之,那些司空见惯的、呆板的话语形式,仿佛在麻痹着我们的注意力,无法唤起我们任何想象。⑩
这里的“表达”是一个名词,意即“表达意向”或“表达自身”(在后面两个词组中,“表达”作定语),也就是前述“言说方式”亦即“怎么说”。表达者对“表达”的重视,可以活跃表达者的思想;而具有文学性(亦即陌生化)的表达,又可以激活读者的思想、兴发读者的情感,最终产生良好的鉴赏效果。相反,那些机械呆板、司空见惯的表达,只会使人昏昏欲睡,感到味同嚼蜡。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将文学鉴赏的愉悦形容为“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如果春台堆满瓦砾,乐饵是嘈杂的声响和馊了的饭菜,鉴赏者还会有丝毫的欣乐吗?鉴赏的效果也就是作品思想和情感内容的传达还能够如期完成吗?
由此可见,拙劣的语言表达可以毁坏或消灭思想和情感——这是从消极的层面考察表达与思想的关系。还有一种积极的“消灭”:以悲剧艺术为例。鲍里斯·埃亨巴乌姆《论悲剧和悲剧性》指出:“死在戏台上的主人公的最后一声叹息,在观众中唤起的便不再是眼泪,而是掌声。……观众被请来接受‘内容’,而事实上,内容却被形式‘消灭了’”。(11)按道理说,艺术作品中“死亡”这一内容,引出的鉴赏效果应该是“眼泪”,但接受者却报以“掌声”。显然,观众的掌声不是对“死亡”这一具体内容的反应,而是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嘉奖。当“掌声”取代“眼泪”时,艺术作品的“内容”即为“形式”所消灭。这也就是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所说的:“艺术家的真正秘密在于用形式消灭内容。排斥内容和支配内容的艺术愈是成功,内容本身也就愈宏伟、诱人和动人;艺术家及其行为也就愈引人注目,或者说观众就愈为之倾倒。”而艺术形式(在文学作品中是语言形式)正是在对内容的消灭过程中,激活了思想和情感,征服了观众和读者。
二、文学是语言表达的完美形式
中国古代文论历来有“辨体”的传统,也就是分辨或辨析文体的传统,比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辨析33种文体的区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析24种诗歌体貌的特征,严羽《沧浪诗话》专门有《诗体》一篇,在时代、地域、作家等不同层面分辨不同的文学之体。在某种意义上说,英美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建立在“辨体”的基础之上的。新批评的理论奠基人约翰·克娄·兰色姆在《诗歌:本体论札记》中细致分辨了“事物诗”、“柏拉图式的诗”和“玄学诗”这三种诗体的区别及特征(12)。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辨体”一样,兰色姆的“辨体”也发生在文学的内部,也发生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
兰色姆将非文学文体称之为散文(即科学文体),他在《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一文中,用政府打比方来说明文学文体与科学文体的区别:
诗是一个民主政府,而散文作品——数学的,科学的,伦理学的,或者实用的和俗文的——是一个极权政府。民主政府的企图是要尽力有效地行使政府的职权,它受一种良心上的限制,那就是,它不想压制它的成员——公民,使他们不能自由发挥他们个人独立的性格。但是极权政府……把它的公民只看作是国家的机能部分,他们的存在,完全看他们对政府的总目的各自所作的贡献而定。(13)
兰色姆用这个比喻,是想说明在文体构成(即部分与整体之关系的问题)上,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文学文体的各个部分(一节叙事或抒情,一个意象或意境,一句隐言或妙语,等等),既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有着独立之生命和独特之魅力的个体,犹如民主政府中的自由公民。而科学文体中的各个部分是没有独立价值的,犹如专制统治下的懦弱的任凭驱遣任人宰割的子民。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文学文体中的“部分”有着自己独立于“整体”的生命?问题的答案还是在“语言”。科学文体中的语言仅仅是说明总目的和完成总任务的工具,离开了“整体”,“个体”(语言)没有任何意义;文学文体的“个体”(语言)当然也要为整体服务(所谓言志或抒情),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文体的艺术,语言本身,以及由语言所构成的体裁、体貌、体性、体势,等等,有着自己独立的生命和价值。我们看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各体作品,一首诗或许早被人淡忘,但其中的诗眼却千古流传;一出戏或许已无人知晓,但其中的一只曲子(唱词)或一段宾白却被广为吟诵;一部长篇小说或许无人能记得全部的故事或结构,但其中的某一个人物性格某一个情景或某一段对话却永远地耳熟能详甚至刻骨铭心……凡此种种,谁使之然?语言,文学语言。
兰色姆接着还用了一个“房子”的比喻。他说:“一首诗有一个逻辑的框架(Structure),有它各部的肌质(Texture)。”根据兰色姆这段话的上下文,所谓“肌质”也可以理解为细部及细部的描写或修饰。在兰色姆看来,科学文体的肌质(细部描写)与其总的框架是不能分离的,而诗的特异性即在于肌质与构架的分离,而且肌质远比构架重要。“如果一个批评家对诗的肌质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等于在以诗而论的诗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只是把诗作为散文而加以论断了。”(14)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其实就是读出作品的肌质,读出作品的肌质美在何处妙在何方。
辨析文学文体与科学文体的区别,是新批评的一项重要工作。被称为“新批评之父”的瑞查兹也谈到科学文体与文学文体的区别,他说与科学语言相比,“诗是语言表达的最完整的形式”,因为诗的语言并不需要科学意义上的规定性和单一性,而应该是多义的甚至是含混的。瑞查兹的学生燕卜荪发展了他的观点,提出含混理论,写出《复义七型》(15)。后来韦勒克和沃伦合写《文学理论》,也强调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含混性和暗示性。
新批评的另一位重要理论家艾伦·退特,在《作为知识的文学》一文中着重讨论诗与科学(实际上是诗作为文学文体与散文作为科学文体)二者之间的差别。艾伦·退特讨论问题的方法是驳斥,一一驳斥文论史上的关于文学文体与科学文体之分别的种种谬误:比如,马休·阿诺德认为文学与科学的差别只不过是前者罩上美丽的语言外衣而能感动人而已;莫里斯认为诗歌文体与科学文体的区别只是语用学意义上的,前者使用句法面而后者使用语义面;柯尔律治认为这两种文体的区别在于科学追求真实而文学追求快感,等等。而退特认可了瑞恰兹后期的理论:“诗是语言表达的最完整的形式。”关于诗之完整与科学之完整的区别,退特指出:
(诗)在富有想象力的伟大作品中达到完整的状态,并不是实证主义科学所追求的那种实验完整的状态。……科学的完整是一种抽象,包括了专门化了的方法之间的合作的完美的典型。没有一个人可以体验科学,或体验一门科学。因为《哈姆莱特》的完整不是实验所决定的状态,而是被体验到的状态。简而言之,那是一种神话式的状态。(16)
文学文体的完整性是体验的,是神话式的,这就回到了原始思维,回到了诗性智慧,回到了文学文体的诗性言说方式。
体验式和神话式的言说方式,常用的修辞手法是隐喻,因此“隐喻”是英美新批评的一个关键词。隐喻的主体分为喻衣(彼类事物)与喻旨(此类事物),而隐喻的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单个词语,如“山脚”、“针眼”、“浪花”和“海笑”,等等;也可以是一种文体,如寓言。就后者而言,《庄子·寓言》篇的“寓言十九”,也可以说是“隐喻十九”。新批评的两位核心人物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比喻性的空间客体”,是一座“词语雕像”(相当布鲁克斯所说的“精制的瓮”)。因此,批评家一头用“意图谬见”斩断作品与作者的联系,另一头用“感受谬见”斩断作品与读者的联系,然后专气致柔,用志不分,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文本分析也就是细读。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理论虽然有诸多缺陷,但对文学隐喻乃至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结构的高度重视,对于我们的文体和批评文体研究是有启迪作用的。俄国形式主义也讨论隐喻,比如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词义的变化(诗学语义学·转喻)》一文,专论隐喻中之一种:转喻。托马舍夫斯基指出:“在转喻中,词的基本意义被破坏了,而通常正由于破坏了直义,才能感觉到该词的次要特征。”(17)比如一首俄语诗歌中的两句:“蜜蜂飞出蜡制的僧房,去寻觅田野的贡果”,对于蜜蜂而言,“僧房”和“贡果”都是“转喻”,都是对于“直义”(即“蜂房”和“花蜜”)的破坏,而正是这种“破坏”成就了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因而成就了诗歌的文学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经典中,充满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所说的转喻、借喻和换喻。
新批评理论家从语义分析出发,将文学语言提升到一个“本体论”的层次,并由此而自称之“本体论批评家”。约翰·克娄·兰色姆在一篇题为《征求本体论批评家》的文章中指出:“我认为,诗歌的特点是一种本体的格的问题。它所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是客观事物的层次,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科学论文来处理的。……诗歌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就此而言,这个知识从根本上或本体上是特殊的知识。”又说:“从本体论角度看,(诗歌)它是要把比较繁杂的世界及较为出人意外的世界带入人们的经验,从更多的方面来进行论述。”(18)
作为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流派,英美新批评于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取得主导地位,于二战结束的1945年衰败于美国。20世纪上半叶,英美新批评对中国文论的影响是零星的个别的(如对钱锺书的影响);直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新批评文论才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批评)它死了——死于自己的巨大成功”,因为,“不论我们是否乐意承认,我们现在全部属于新批评派阵营,我们在阅读诗歌时,已经无力回避对诗中的含混性等质素的喜爱与赏识”(19)。新批评的“巨大成功”,当然也包括它在20世纪中国文论界的成功。因为我们今天对文学语言及语言研究的重视,对文体及批评文体研究的重视,其中不乏新批评的理论影响。
三、语言突出及其诗性功能
陆机作《文赋》,一上来就在“序言”中表达他的语言焦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正文中又以垂钓和射猎为喻,再说语言之痛苦:“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而《文赋》的后半部分提纲絜领地分析“作文利害关键”,不厌其细地指责各种“文病”,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如何“以文(言)逮意”的层面来消解语言焦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孔子“慎乎辞”,到王国维“著一字境界全出”,对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即便是老庄“知者不言”、“言不尽意”一路,也只不过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突显语言。而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这三家文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
我们在前面提到雅可布逊的莫斯科语言小组,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雅可布逊还有他的语言小组,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雅可布逊1920年代迁至布拉格,转向捷克结构主义,从而将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克学派和现代结构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成为由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雅可布逊后来加入美国籍,成为俄裔美籍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后期的理论有明显索绪尔印记,如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对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尤其是对语言组合关系的两个向度的区分,均成为雅可布逊后期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元素。
先从索绪尔的语言组合关系理论说起。索绪尔将这两个关系表述为横组合关系与纵聚合关系:前者是句段关系,即一个句子在时间上的呈现,也就是句子中的字词按先后顺序一个挨一个地排列;后者是联想关系,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句子中已经出现的词与尚未出现的词之间的共时关系。作为结构主义理论家,雅可布逊由索绪尔的“两个向度”引出对语言“诗性功能”的研究,他提出一个著名论点:“诗性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向组合轴”(20)。雅可布逊认为,日常语言的使用中,言说者只需从选择轴(即纵向轴)中选取一个能够表意的词放入句段(即横向轴)中即可,也就是孔子说的“辞达而已”;而选择轴中,其它词语(即未被选入横向组合轴的)只在想象中展开。但是,在诗性语言的使用中,言说者为了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常常将选择轴中大量的词同时引入句段,如诗歌中的排比对大量同义词或同声(同形)异义词的运用。
如果我们将雅克布逊的这种语言结构分析的方式由一个单句扩充为一个文本,则可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中找到更多的例证。比如,《周易》用许多象喻来说明一个道理,所谓“义虽不变,象可博取”(21);又比如,《庄子》讲“逍遥游”这个道理,一口气用了五个寓言:《北冥有鱼》、《蜩与学鸠》、《汤之问棘》、《尧让天下于许由》和《肩吾问于连叔》(22)。如果仅仅是出于“达意”的目的,一个“象”或一个“寓言”就足够了;而《周易》和《庄子》为什么要同时用多个“象”和多个“寓言”呢?在雅可布逊看来,语言在结构中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传达功能”,辞达而已,能把意思说明白就行;另一种是“诗性功能”,即强调语言自身,或者说突显语言自身所具备的诗性即文学性。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向组合轴,从根本上说,是把对语言自身(即诗性功能)的展示和强调,看得比语言的“传达功能”重要得多,也就是将“怎么说”看得比“说什么”重要得多。对“诗性功能”的看重与对“传达功能”的看轻,这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说到底,这样做是要削减语言对于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突显语言自身的诗性魅力。因而,“突显语言”的结果,必然是对语言“诗性功能”的发挥。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批评家自觉选用文学文体来书写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之所以这样做,也有“突显语言”而发挥其“诗性功能”的用意。因为,如果仅仅是出于“达意”的目的,他们完全可以以“论(理论文体)”来论文,而无须以“诗”(文学文体)来论文了。
不过,雅克布逊对索绪尔“语言向度”的阐发,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诗性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向组合轴”适合于散文体(如前举《周易》和《庄子》),而不适于诗体(尤其是格律诗)。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格律诗,对每一句的字数有严格的规定,也就是对横向组合轴有严格的字数约定,作者根本不可能将纵向轴的对等原则引入横向轴,而只能在纵向轴的众多可能中选取其中的一种。当然,格律诗的这种选择不同于日常用语的选择。对于日常用语来说,选择的标准很简单:达意即可。而对于格律诗而言,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陌生化的过程,也就是诗性即文学性的生成过程。
就读者的这一方面而言,在诗人已经完成的诗句中,读者能够看到的只是横向的组合轴(即句段);而纵向的聚合轴并未也不可能实际呈现,而只能存在于读者的想象和猜测之中。比如,陶渊明的诗“悠然见南山”,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也只能是“悠然见南山”这五个字的依次排列或曰横向组合;至于那个“见”字可以或可能用“看”或“望”或别的什么字,也就是陶渊明已用的“见”字与未用的那些字共同构成纵向的聚合轴,而这个“纵向轴”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从语言层面说,格律诗的创作过程,说到底就是如何从纵向轴中选择最恰当最有表现力或者说最具陌生化的字或词安放于横向轴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古代文论常说的“推敲”、“琢磨”、“苦吟”、“瞑思”的过程,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炼字”或“捶字”的过程。而纵向轴上的最佳选择,放在横向轴中就是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所说的“捶字坚而难移”;而这样的作家就成了被刘勰所推崇的“雕龙奭”了。因此,格律诗创作对纵向轴诸种可能的精选,也是对语言的突显,对诗性功能的阐扬。
关于语言的“突出”,捷克结构主义者穆卡洛夫斯基亦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诗性的言说,总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突出话语”,“将言语自身的行为置于最突出的地方”(23)。受捷克结构主义的影响,后来法国结构主义,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还是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研究,所关注的都是作品的语言形式,所突出的都是文学结构作为“语言”的意义,所证明的都是优秀作品在语言和结构上的成功。当然,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不同于她之前的英美新批评,因为前者并不局限于单个作品的机械而烦琐的细读,而是在一个整体结构系统中去认识文学作品(“言语”)的内涵,透过具体的个别的文学现象去把握文学内在的普遍的本质。
结构主义从空间上经历了由索绪尔语言学到捷克结构主义,再到法国结构主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其实早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结构问题就受到重视,如托马舍夫斯基在《诗学的定义》中指出:“诗学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24)就对结构的重视而言,结构主义可以视为“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25)。无论是对语言自身的突显,还是对语言诗性功能的阐发,都需要在结构中确认,在结构中完成。笔者近日看了一个小品,男女演员依次用三种剧式(琼瑶言情剧、金庸武侠剧和《大长今》式的韩剧)来表达同一个剧情。这一对演员很好地把握到三种剧式在语言和结构上的差异,然后用夸张变形和调侃嘲讽的喜剧手法,表现出这三种剧式的缺陷。琼瑶言情剧,其对话是嗲声嗲气加上甜得发腻,其结构是无端的煽情加上无端的争吵,而这一切都是由叫喊式的台湾腔国语完成的;金庸武侠剧,其对白是武林流行套话和江湖专门术语的堆砌,其结构则是故弄玄虚的动作加上故弄玄虚的宾白;而《大长今》式的韩剧,其人物对话是喋喋不休、绵绵不绝,其语言结构是毫无必要的反复质疑和毫无必要的反复诘问。小品是语言类节目,更是一种语言艺术,而正是凭借语言突出,才使得这个节目具有一种特别的诗性功能。
注释:
①关于汉语文体学研究的三大分支,参见李建中《文体学研究的路径与前景》,《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
②③④参见[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1、220—221、360页。
⑤[英]安纳·杰弗森、戴维·洛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⑥参见[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5页。
⑦⑧[俄]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文:沉思和分析》,苏联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5页。
⑨[荷]佛克马、易布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页。
⑩[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3—84页。
(11)(12)[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页。
(13)参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71、95页。
(14)(15)(16)参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5、155页。
(17)[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7—88页。
(18)参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8页。
(19)[美]兰鲍:《现代精神: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连续性论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1页。
(20)[美]罗曼·雅科布森:《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参见塞比奥克编《语言文体论集》,麻省理工学院1960年版,第358页。
(2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
(22)后面的三个也可视为“重言”即借重古贤者之言。
(23)[捷克]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言和诗歌语言》,载伽文编《布拉格学派美学、文学结构主义与文体论文集》,华盛顿乔治敦大学1964年版,第43、44页。
(24)参见[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6页。
(25)[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标签:结构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体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