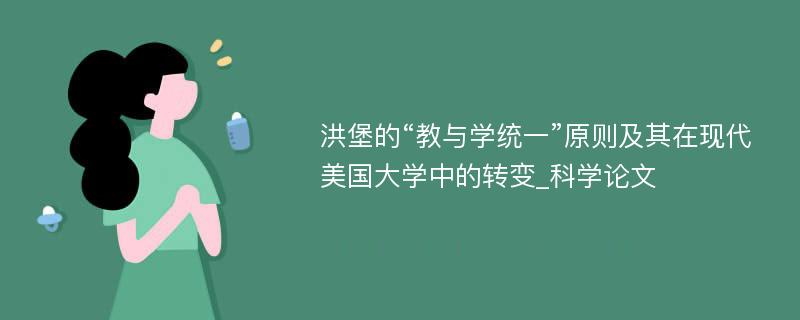
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统一”原则及其在美国现代大学中的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科研论文,在美国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2)02-0026-07
最初的大学把教学作为主要活动和职能,科研游离于大学。洪堡把科研引入了大学,并使它和教学统一起来。那么,他如何构建了这种统一的?后来的人们践行其原则时,是如何和怎样产生了变化?
一、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统一”,如何可能?
我们认为,要理解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统一”原则,必须首先理解其教养观和科研观。
(一)教养:精神力量发展和道德完善
洪堡主张,大学不但要发现知识,更要使人获得“教养”(Bildung)。他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中指出:“高等学术机构的作用,由内而观之,在于沟通客观的学术和个人的修养”[1]。在洪堡看来,大学“无非是具有闲暇或有志于学术和研究之辈的精神生活”[2],闲暇的精神生活是“不求外在的目的”的,它仅仅出于“对活动对象本身的兴趣,或出于德行的理由”[3]。
那么,洪堡所说的“教养”该作何理解呢?洪堡认为,教养是比文明和文化这两者更高尚的状态,因为“当我们讲到德语的Bildung(教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同时还连带指某种更高级、更内在的现象,即情操(Sinnesart),它建立在对全部精神、道德追求的认识和感受的基础之上,并对情感和个性的形成产生和谐的影响”[4]。这样,“教养”不仅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唤醒与发展,而且意味着道德的完善。
洪堡生活在德国古典哲学繁荣的时期,据贝尔格所言,“哲学方面洪堡先受到康德,然后又很快受到菲希特、舍林、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的影响”[5]。与这些先验哲学家一样,洪堡也认为精神高于物质,因为现象世界的一切只有在精神中才能得到完满的解释。洪堡指出,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虽然很多现状处于因果链条之中,但很多进步却难以对之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存在着一种从本质上说不可能被完全把握,从作用上说则不可能被预先测知的精神力量”[6]的缘故。
洪堡认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表现为一种向前推进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是一个目的系统,万物均在无限的时间序列中无尽趋向那一永远无法企及的终极目的。相反,世界存在一个初始的原因。这一原因之所以是初始的,是因为它是自主的、独立的,它自身之外没有原因;但它却是万物的原因,世界中的一切,无论是精神的东西还是物质的东西,都由它产生。这一初始原因就是“精神力量”,万物由之出发。
洪堡对这种作为初始原因的“精神力量”作了详细的探索和描述:
首先,精神力量具有创造性:“在人类隐蔽的、仿佛带有神秘色彩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力量是真正进行创造的原则”[7]。精神力量内在于人心,它蕴含着创造的生命力,因为它本身即来自于生命;这种具有创造性的精神力量一旦触及与它遭遇的东西,无论那东西是已知还是未知,都必然地起作用。
其次,尽管精神力量“不可索解”,但它贮存着认知的能力。“它从内向外控制着所有既存材料,把材料转变为思想或者使材料隶从于思想”[8],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精神力量是自由的,它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和直观形式独立地作用于外在世界;并且其作用的程度越强烈、方向越明确,人们由此获得的关于外在世界的观念也越明了、越丰富。事实上,在认知过程中,精神力量正是以其“全部的努力和高度统一性”[9]作用于提供给它的对象。
在洪堡看来,既然精神力量具有如此卓绝超群的性质和能力,它就可以而且应该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他说:“我们也可以而且理应把哪怕已抵达最高发展阶段的精神个性看作对一般人类本性的某种限制,看作一条个人必须遵循的路径”,于是“使人真正成其为人的精神力量,便是有关人的本质的简明定义”[10]。由此,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实现就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唤醒和发展,“如果个人或民族缺乏一种天才的召唤力,那么,思想就会像闪烁的煤块一样,永远不能燃起灼目的光焰”。[11]
在洪堡那里,精神力量不仅表现为超越具体民族或个人的“人类精神”;也表现为每一具体民族或个人的“精神个性”或“精神特性”。人类精神与精神个性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一方面,由于人类精神是高度完善的,洪堡把它看作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12],从而精神个性因分有人类精神而是其所是:“任何个别的特性只有倚仗一种优势原则,也即排他的原则,才能够成其为精神个性”[13]。精神个性是作为一般的人类精神的具体存在。人类精神将其本质扩展、渗透到精神个性之中,从而使每一具体的精神个性显示出一般人类本性。因此,精神力量的作用“不仅见于思维和艺术表达领域,而且也十分突出地表现在个性的塑造(Charakterbildung)上”[14]。体现着一般人类本性的精神个性(或个人),在与他人联系的中,传递着作为一般人类本性的人类精神,他将自己内在的感觉、情绪、思想通过语言向他人表达,并借此引发他人的回应、理解。这样,“个性逐渐变得完善和细腻,从而使心灵的各个不同方面平衡和一致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高度统一的、一如造型艺术所具备的形象”[15]。
另一方面,精神个性又受“整体性原则”所限制,“由于这种原则的作用,若干精神个性可以重新结合为一个整体”[16]。因此,在现实中,个人不单纯以独立的个体存在,而且也以“类”和“族”的方式存在。这在洪堡看来是一个自豪和令人兴奋的发现,他似乎由此看到了属于德意志的民族性。贝格拉是这样描述洪堡当时的情景的:
当洪堡现在开始发现“德国性格”是民族的个性而普鲁士则是它的体现时,他就像受到了一种陶醉的主宰,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在长期干巴巴地钻研故纸堆之后来创造现实的陶醉。但这种民族性同时也牵连进了所有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正是他长大20年之久的指路明灯[17]。
但由精神个性聚合而形成的整体,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和价值诉求等基础之上的。洪堡认为,由于个体会不断地形成新的整体,因此整体性只能是一个永无止境、终不可及的追求。也就是说,人类精神永远是精神个性目标。他在《论历史学家的任务中》写道:“历史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实现一个通过人性体现出来的(人类精神的)理念”[18]。如前所述,精神力量是一个万物由以出发的初始原因,它是自由的,也是一般的人类本性。如果把这种作为自由的一般人类本性作为所有精神个性始终追求的终极目标,精神个性的实现就具有了一种道德的意义。
洪堡主张,大学通过培养人,使人具有“教养”,从而间接地为国家服务:
就总体而言,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19]
(二)科学研究:教养的实现途径
在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中,科学不是作为大学的目标被强调的。如前所述,以精神力量的发展和道德的完善为旨归的教养才是洪堡大学的根本目标。周川认为,洪堡将科研引入高校未必单纯是为科学着想,他全力倡导大学的科研,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在于完人的培养,在于新人文主义教育目的的实现。[20]陈洪捷也指出,洪堡强调科研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修养”。[21]因此,在洪堡的思想中,教养才是大学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他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中已经明确陈述了如此观点:“所谓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22]
洪堡之所以强调科学,是因为科学天然就是精神和道德教化的手段,它是“并非有意地、但自发合乎目的地得到准备的材料”[23]。但这样的科学必须是“纯科学”。“纯科学就是哲学”[24]。按照洪堡关于“精神力量”的陈述,精神个性是由人类精神塑造的,而作为个体的精神个性在追求作为人类精神那一“整体性”时,必然形成作为类族的精神特性。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特性是哲学的,“德国人善于思考的国民性格天然就具备这种资禀”[25]。一般人类本性是一种无限,对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来说,只能越来越近地趋向它,但永远达不到。正如康德所言,“灵魂不朽”。一般人类本性不像自然之物那样能被我们知觉到,相反,它没有实在性。按康德的说法,它只是一种必须做出的“悬设”。它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只能从哲学上加以把握。洪堡说道:
“为能卓有成效和强劲有力地主导普遍的教养活动,一个民族不仅要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取得成就,而且首先需要倾全力于追求构成人类本质内核的精神,这一精神在哲学、诗歌和艺术中最清晰、最完整地自我显示出来,从而对民族的思维和情操产生影响。”[26]
我们认为,根据洪堡的教养观,其“纯科学”之说是相对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科学之“纯”,不仅在于“为科学而科学”,更在于科学对于人的救赎意义。从远而看,洪堡的人文主义理想来源于古希腊,他向往完美的古希腊人。从近而看,洪堡深受康德的影响,康德关于认识的“哥白尼式革命”,使人获得了作为认识者的主体地位;在康德的概念中,人是知识的创造者,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要求自由,也确证自己的自由。
在洪堡那里,作为教养之手段的科学并非静态的真理。相反,坚持静态的科学观,并以现成科学知识的传授作为主要教学活动,恰恰迎合了实用取向的专门学校的目标追求。洪堡坚持,科学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事实,必须“把学术视为尚未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27]。这样,只有把科学看成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究活动才有益于实现教养的目标;因为教养是以精神力量和道德为旨归的,而二者均来自于内心。从表面看,内在的东西似乎只能从外部加以充实,但洪堡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假象:
“人的内部所没有的东西,从外部是不可能添加进去的;凡从外部进入内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支点,借助它,内部的东西始终完全依靠自身所独有的富足的源流发展起来。”[28]
由此,大学要达到人的教养的目的,必须以科学研究作为手段,从人的内心去充实他,因为教养是内在的,而科学研究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活动。洪堡强调:
“一旦停止了对学术的真正探索,或者认为学术无须来自精神深处,只需众多资料的堆积而成,那将是无可挽回、永远地损失。不仅是学术的损失,因为学术长此以往将徒有其表;这也是国家的损失,因为学术只有来自内心并作用于内心,才能改变人的性格,而国家正如人类一样更加关注性格和行为,而不是知识和言语。”[29]
综上所述,正由于洪堡主张科学是一种探究活动,并天生地是教养的手段,从而使教学与科研二者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由于科学研究对于教养的功用,从而使它成为大学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在洪堡大学中,教师和学生都是研究者;对大学生而言,“听大学讲座本身其实只是偶然的;真正所需要的是,年轻人在学校和进入社会生活之间有几年能专心致志地在一个地方进行科学的思考”[30]。惟其如此,学生才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学会独立地进行科学探究、自主地作出科学结论及其解释,并形成对科学的最深沉、最纯净的认识;教师和学生则能在互动式的科学研究中,分享彼此的“精神个性”,作为类族之“精神特性”的形塑也由以可能,继而在不断超越中无限抵近柏拉图理念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这才是教养的真正内涵。
二、洪堡“教学与科研统一”原则在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中的改造
洪堡“教学与科研统一”原则使科学研究成为大学主要活动和职能。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是理性从神性争取权利的重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洪堡原则推动了大学的现代化运动。但观念是一回事,实践却是另一回事。不说在其他国家,即便在德国,洪堡原则也没有被贯彻得太久。“柏林大学以洪堡所精选的教授于1810年十月正式开学……它对洪堡为它策划的道路并没有坚持很久”,“在短短几十年内,实际的做法远离诸如费希特(Johann Fichte)、谢林(Friedrich von Schelling)和施莱尔马歇(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思想上的创立学说的前辈以及洪堡的设想”。[31]但洪堡原则毕竟推动了大学的科研活动,教授或科学家致力于科学研究,催生出更多、更深入的专门化的学科,逐渐地,“新一代的自然科学家极力投入基本的实验室工作,并讥笑纯理论的或整合性的理论构建的企图”[32]。
洪堡原则所蕴含的理想确实令人欢欣鼓舞。19世纪末,美国人模仿德国大学把科研引进大学,从而诞生了一批不同于殖民地学院的新式大学。但“德国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模式在传入美国之前都经过了重大的调整,以便能够适应美国的环境”。[33]
被誉为其时美国大学“施洗约翰”的特潘(Henry P.Tappan)是第一批留德的美国教育改革家,他近乎顶礼膜拜地向往柏林大学的教育理想,希望新式美国大学将“把美国变成一片盛产学术大师的国土”[34]。但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的身上又被美国传统湿湿地浸润着。特潘把他的教育目标称为“哲学的和理想的”,“这种教育观念不仅仅是要向人们传授手艺、技艺或专门职业,而是要把活力、真理和知识赋予他们灵魂,并且给予他们在一切正确的事情上充分运用自己的所有才能的力量。”[35]
作为特潘最著名的弟子的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在教育观念上深受其老师的影响,但他同时又是追求实用性的教育家卫兰德(Francis Wayland)的弟子。因此,怀特设计的大学“实质上比特潘的大学更加注重实用性”[36]。在康奈尔大学中,怀特强调学科平等,从而使应用科学具有与学术性科学同等的地位;他主张不仅进行普通教育,也进行专业教育。在特潘思想的影响下,怀特也赋予其大学以道德使命,他强调,“康奈尔大学是一所基督教性质的、无宗派主义的、致力于高尚的道德价值的、崇尚自由尤其是科学探究自由的大学”[37]。
尽管怀特的康奈尔大学吸收并践行了洪堡思想,但他更多地把科学研究和“实用性”联系起来,这是迎合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它标榜以生物进化论为其科学根据,并继承了进化论关于自然界不存在一个恒定不变之秩序的思想。由此,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没有永恒的知识,知识仅仅是康德所说的“实用的信念”,是采取行动以达到目的的工具,简言之,即“技巧和技术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经验,需要行动和实践检验”[38]。当它在指导行动达到目的有用时,它就是真的:“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39]。实用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论虽然与人相联系,但它只涉及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评判或检验是否为“真”的尺度。这样,实用主义主张的知识只是相对的;它声称的人本主义不过是一种“伪”人本主义,它抛弃了人对于科学知识的能动作用。因此,当实用主义和科学研究联姻时,科学研究无益于实现洪堡主张的通过科研实现人的本质规定性,从而科研的教化作用被消解。
在康奈尔大学创建的稍后几年,美国人创办了霍普金斯大学,这是一所集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新式大学,研究生教育为教师和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合适的平台。虽然吉尔曼希望按照洪堡原则来组织这所大学,并声称:“如果我们将要组建的这所学校不能把发现和传播真理作为唯一的目的,它就不配被称为大学”[40];但“他对德国先例的热衷还是有力地体现了一种倡导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的理想”。[41]
价值中立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只涉及“是”的问题,并且不能从“是”中推断出“应该”来,事实与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可逾越的世界。美国人深受英国经验论传统和培根主义的影响,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取决于对事实的不带偏见的观察,而不来自于康德的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性。这种对事实进行客观观察的强调不可避免地削弱科学与道德相关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科学不承载道德意义,科学中没有伦理关怀;相反,道德关怀必然影响科学家对事实的解释,从而不能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因为“没有事情比把道德考虑加进一种本质上非道德的实际研究更容易把人引入歧途”[42]。这样,客观主义的科学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分离,即便大学把二者同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也必然失去了洪堡意义上的内在契合。
三、结语
大学诞生之初,教学就是大学的主要活动和职能,而教学则是以知识为中介的。中世纪的知识模式是“教条的”和“解释学的”[43]。中世纪知识论认为,上帝是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由于上帝的崇高性,感官不可能认识上帝;即便理智,也必须凭借上帝之光才能理解上帝的旨意。因此,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是封闭的,它只限于帮助学者理解认识上帝,科学研究则被排除在大学之外。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理性的作用被人们重新认识。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强调了理性在认识中的决定性作用,从康德的“我思”、费希特的“自我”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肯定了自我意识在认识中的优先地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认识论遵循柏拉图主义传统,他们一致认为,世界存在一个初始原因,认识就是要认识这一初始原因。由于初始原因是万物的原因,却不以别的东西为原因,因此它是绝对自由的;这样,人的认识必然是自由的,也在认识中确证自己的自由。由此,知识就具有了上帝意义上的救赎性质。知识论的变化,必然带来大学理念的转变,因为大学毕竟是处理知识的场所。康德在其《学科之争》坚持用哲学取代神学的优先地位,就是要确立理性的大学理念。
洪堡深受这些哲学家的影响。我们认为,洪堡的“精神力量”类似于康德的“我思”。在洪堡那里,精神力量不可索解,但它具有创造性、认知性,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大学教学就是要唤醒和发展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是自由的,因此其实现必然具有道德意义。洪堡把教学所要达到的这一目的称为“教养”,从其内涵可知,洪堡大学的教学具有与中世纪大学教学不同的意义。由于精神力量具有创造性和认知性,因而精神力量的唤醒和发展必然通过科学研究才是可能的。这样,洪堡就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并作为实现教养的有效手段,从而使科研和教学内在的统一起来。
洪堡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是理性继康德之后的又一次胜利,人们纷纷为洪堡原则的理想欢呼。美国人试图用洪堡原则来改造其旧式学院,但当它和美国传统结合时其原有的内在统一性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了(如上所述)。美国的知识模式不仅是客观主义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因此美国大学的科研有着与德国大学科研不同的意义。具体而言,当科学研究与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知识论结合时,它就只是纯粹“为科学而科学”,而消解了洪堡科研所蕴藏的道德意义;当科学研究与市民社会取向的知识模式结合时,它必然催生大学在教学和科研之外的另一职能——服务。
综上所述,由于教学和科研都是通过和对于科学知识的,二者的关系和性状必然受知识模式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知识模式的变化来考量大学中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应对由此产生的其他方面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