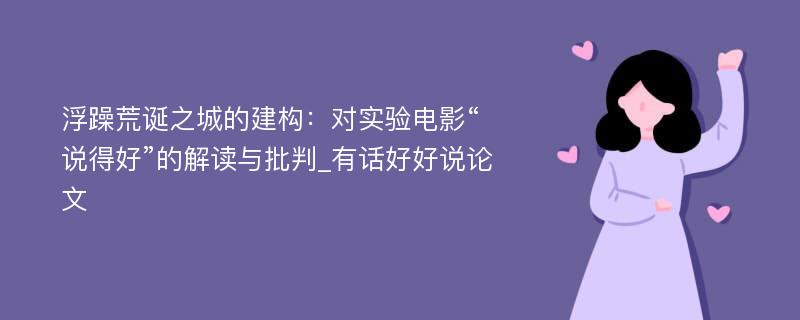
都市浮躁与荒诞的营建——实验电影《有话好好说》的解读与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论文,浮躁论文,批评论文,都市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依然宣称“我不想重复自己”的张艺谋,引人注目地拍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影片《有话好好说》。这部改编自述平的小说《晚报新闻》的电影一反导演获得巨大成功的新旧农村题材老路,是一部由“‘三个男人一个女人’的故事改造而来”的“关于男人的故事”的当代都市题材电影。对《有》片,张艺谋自己认为:它“是一部很风格化的电影,是少数派电影,不是主流电影”;“从手法到意识都打破了我过去的影片”,“它具有探索、试验性质,很具有个性,不是常规的娱乐片,它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兴趣。”因而,循导演主观意图,结合影片客观实际,对《有》片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和评析,无论于观众的欣赏认识还是于国产电影的创作总结,都很有必要。
都市的浮躁与荒诞
《有》片在叙事表层讲述了一出不无闹剧色彩的喜剧故事。个体书商赵小帅在多次谈朋友告吹的情况下对新结识的女青年安红狂追不舍,不惜花钱雇民工在其所住楼下反复高喊:“安红,我想你!”甚而叫民工拿通俗情歌《牵挂你的人是我》的歌词当诗向楼上高声宣读。这一出格之举惹恼了安红的新情人——安达娱乐公司的老板刘德龙,遂率众暴打赵某。自卫中,赵某抢来围观看热闹的电脑爱好者张秋生新买的手提电脑作武器砸人摔坏,并发誓剁下刘某右手……影片在赵某是否会剁刘某之手的悬念释解过程中,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三个男人”的“噱头”。
由于表层叙事的随意简单及其喜剧色彩,《有》片可以让人不加思考地乐呵呵地观看和欣赏。然而,在深层意蕴上,该片则不动声色地阐述了一个较为严肃沉重的主题——都市的浮躁与荒诞。它传达了现代人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和感觉。同时,影片表层叙事的极为风格化则使这一主题得以强化,让每一个深入思考者不能不严肃面对。这即张艺谋所谓的“把雅和俗看似对立的双方结合在一起,雅俗共赏”。现代都市的浮躁与荒诞极为抽象,外延无拓展性,但却有着丰富深邃的时代内涵,一如张艺谋所说:“主题是多义的,当代意识很强”。
通过对《有》片影像符号相似性转喻及其所指意义系统的细致考察,可发现其多重意旨。
一、现代都市人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公众道德和人生原则。置身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和众多传统美德沿袭的国度,人一进入社会也就进入传统文化和道德营造的氛围,并确立作为社会人所生之为人的根本,进而使社会的安宁、和谐得以实现,然而因转型期的现代社会中不少都市人信仰缺失,浮躁庸碌、困惑迷惘、我行我素、感性冲动,“老子天下第一”之风愈刮愈烈,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失落了应该承继的传统美德和应该坚持的人生原则。女青年安红的恋爱观是随意扭曲的,与赵某表示亲热,便是要“比试比式”床上功夫;赵某追女朋友也追得离谱,我行我素到了不顾整幢楼居民安宁的生活秩序,雇人在楼下狂喊“安红,我想你”,继遭至居民的谴责甚以污水相泼;在被另一感性冲动很不理智者刘某聚众暴打之后,固执到难以理喻的赵某便发誓剁刘某之手并切实付诸实施;本为阻止恶性砍人事件发生而耍酒疯的老实人张某,在受到“老子天下第一”者酒馆“二大爷”的捏鼻灌醋、脱光衣服等严重人格污辱和肉体摧残之后,也鬼使神差地提刀要找躲得无影无踪的“二大爷”拼命,并情急之下砍了阻止自己的已不欲剁人之手的赵某一刀。
二、现代都市人安宁的生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浮躁的动荡不安的因素侵入到个人生活领域。女青年安红的家因其随意的个人恋爱问题带来的副面效应而变得动荡不安;安红同楼居民们安宁的生活,也因其不无感性冲动色彩的恋爱而受到外来因素的侵扰遂充斥烦燥和愤懑;老实巴交的电脑爱好者张某,从未“惹过谁,招过谁”,却因围观打架而使新买的手提电脑成为废品,自己安宁的个人生活也从此动荡起来,烦躁、无奈、委屈、愤懑接踵而至;不仅如此,张某也因自身境遇的逆转而从一个老老实实、劝人向善者变成一个在公共场所穿着背心、裤衩提刀找人砍杀者,并被派出所治安拘留。
三、现代都市不少人的社会生活较大程度上是随意和惘然的,他们难以找到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由于外部世界千变万化,难以捉摸,不少现代都市人对所置身的社会缺乏了解、认识;对其感到困惑,产生怀疑,对自身也缺乏信心、勇气;自身和社会生活显出惘然和随意性,他们没有明确的行为目标和意识目的,在纷繁复杂、冷漠世故的社会中难以找到自我位置。《有》片中赵某和张某在故事快结束时也不知道各自的姓名,原因自然亦是那“忙忙叨叨的当代生活”。也因如此,散淡迷惑的赵某在谈了两个吹了一对之后,对新结识的女朋友尽心尽力狂追,不管自身的行为是传达了对女友的爱还是对女友的伤害,杂乱无章,匪气十足,随意所为。结果当然只能是告吹。刘某率众暴打赵某是感性的冲动行为,要为此付出精神的(被赵某追得到处躲藏)物质的(付赵某五万元赔偿金)以及肉体的(脑袋被掉落的音箱砸得鲜血直流)惨重代价。显见,这些事件的行动主体在行动中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着应该做的事,亦不明白自己是否会实现某种目的。其行动陷入杂乱混沌的迷狂状态,不了解自己,不认识世界。
四、现代都市人因自身行为的随意性及荒诞性,在很大程度上显出散谈的“多余人”色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叛逆着这个社会,与其格格不入。《有》片中的安红和赵小帅则是现代都市“多余人”的代表。在恋爱问题上安红所显示出的随意性和叛逆性是令上了年纪的人吃惊的——“睡就睡”,“比试就比试”;她在处理自己与赵小帅、刘德龙的关系上的摇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赵小帅“猴急”之后狂追女朋友所显露出的随意性与荒诞性足以说明他自身的凄凉境遇;对自己摔坏张某电脑的诡辩也显出他缺乏理性的是非观念;为报复逞能剁刘某之手的实际行动则标示他并无明确的生活目的;虽经派出所拘留教育,仍义无反顾地要剁刘德龙之手,反显出他以此为荣、以此为乐的心态。安红、赵小帅是符号的化身,他们隐喻出现代都市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困惑、迷惘、浮躁、无奈、动荡、不安、混乱、狂放的荒诞境遇。
黑色幽默的夸张变形
鉴于随意简单、荒诞偶然的故事表层与多义复杂、严肃沉重的深层意蕴之间的矛盾,《有》片要求一种适合的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及叙事风格——它不可能是写实的,也不可能是悲剧或正剧的。导演采用了外向型、夸张型手段,将影片定位于黑色幽默,并引进了“MTV”的方法。他认为,“关于风格,我觉得这部电影不是写实的。……有一定的荒诞性和夸张性。……生活中有偶然、有巧合,但是把这么多偶然和巧合搁在一起,也就比较组织的、人为的,戏剧的。”“幽默感是我们提前定好的,希望能让大家笑一笑,轻松一下。而且这种荒诞和变形的东西必须和幽默结合,否则就变成另外一种特沉重的东西,……我们必须使电影带有喜剧色彩,保持幽默感。”诚如导演所言,影片仅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细节真实之上,它将生活中的荒诞情景放大,使夸张、变形的故事具有不可逆转的荒诞感、偶然性,从而使整部影片富有喜剧、闹剧色彩和动荡不安的浮躁感——独特的观点,动荡的影像,巧合、偶然、简单的荒诞故事,盲目、无奈、感性的灰色人物,主观假定的叙事场景,非常规的摄影机运动,镜头、景别的反常处理,机位、角度的随意变化,失去平衡的不规则构图,贯穿始终的悬念设置,北京琴书的滑稽配乐,环境音响的主观营造——张艺谋比较成功地建构了一部另类的都市“黑色”喜剧。具有一定真实基础的细节夸张与整体叙事的荒诞之间的张力,使人明显感到影片的“黑色幽默”风格。
一、独特的叙事视角:疯子的视点
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罗伯特·维内,1919)展示的是疯子眼中的世界:奇异、恐怖的故事是以疯子的视点用夸张、变形的视像来叙述的。比照于此,可以认为《有》片亦是以疯子的视点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展开叙述的。只是《卡》片“用一个序幕和一个结尾来说明:片内出现的奇异景象,乃是被卡里加里博士送到精神病房关起来的疯子眼中所看到的世界。”而没以语言形式交代的《有》片则以夸张、变形的影像符号及躁动不安、稍显混乱的程序编码进行了潜在的置换:
叙述者→摄影机→潜在旁观者
─────────────→
摄影机的主观视点
潜在旁观者→观众→现代都市人
──────────────→
观众的主观视点
夸张、变形、动荡的影像世界
─────────────→
现代都市人→疯子的主观视点
在此,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摄影机的非常规运动(主观视点)标识了自身潜在旁观者——观众的身份,而观众所标识的现代都市人看到的是夸张、变形、动荡的影像世界(疯子的视点)——现代都市人是犯有轻度癫狂症的疯子。在疯子眼中,人物是灰色的,不高大,不英雄。赵小帅、安红、张秋生、刘德龙等饮食男女,没有让人感到其高尚、伟岸、英勇和表范,更多的是困惑、盲目、感性和迷狂——拼命追求的得不到;不招惹谁时招惹了谁;想保身的保不了身;要安宁的安宁不了。同时,疯子眼中的动作场景也是主观虚拟、不无假定性的。张秋生在饭店阻止赵小帅砍人不成装疯卖傻“一掀桌子整个光线都是彩色的,整个儿变了,这东西谈不到写实”。善于躲在幕后板起面孔嘿嘿发笑的张艺谋,借助《有》片,实实在在地幽了现代人一默——“有话好好说”让你轻轻地流下苦涩的眼泪。
二、动荡不安的影像
确立了疯子的视点,夸张、变形、动荡的影像便是必要的。在具体拍摄《有》片中,张艺谋“要求摄影机追着演员跑,不少画内人物动作和画外摄影机的运动,在较大程度上营造了动荡不安的影像世界——赵小帅急匆匆紧追前面所结识的亦急匆匆奔走的女友安红;刘德龙率众暴打在街头苦等安红的赵小帅;赵小帅狂追刘某砍手;赵小帅与安红共处一室的温馨之举被张秋生打断后决定重来一次时擦燃了火柴——动荡的火苗占据了整个银幕;给某大姐过生日的人们在饭店一边狂跳一边大唱《九九艳阳天》;张秋生在饭店外抢大哥大打电话;赵小帅要砍手;张秋生在饭店装醉耍酒疯掀翻一张张餐桌;张秋生受饭店“二大爷”污辱之后提刀到处寻找“二大爷”……这些叙事段落的画内人物动作是狂乱不羁、动荡多变、潜存诸多未知因素的;画外摄影机的运动也是不稳定、随意变化并与画内动作相互相合的,它们弥漫着烦燥、不安的气氛,给人强烈的骚动、浮躁之感。显然,这种有意为之的艺术处理,传达了张艺谋所要传达的“一种动荡的浮躁感”及“对当代都市的一种感觉”。实际上,这在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处于转型期的现代都市是浮躁且动荡不安的——尚未完全从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的都市人,面对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及逐渐增大的工作压力,不由自主地陷于传统文化与物质利益的裂变之中不能自拔,行为盲目冲动、缺乏理性,内心困惑迷惘、骚动不安。无疑,这是张艺谋营造动荡不安的影像世界的真正目的。
三、摄影机的非常规运动
影片因确立了“疯子”的主观视点,也因摄影机的潜在旁观者即观众——现代都市人的身份,把摄影机隐匿起来,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显然达不到所要达到的视象效果,也与影片风格的特质相悖。张艺谋在片中大胆采用非常规的“追拍”方式,即用手提摄影机追着动作着的演员近距离拍摄。这种连续的“追拍”,便轻意打破了传统的场景切换方式——以全景或特写等无方向性的景别切换转场,使前后画面在光的方向上相接——而自然较多运用了以往电影禁忌的连续快速左右摇摄,即持续来回的“甩”以及在技术上禁忌的运动镜头(这些方式过去只是在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大力反传统的让一吕克·戈达尔的影片,当代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一些影片及近年音乐电视MTV中出现过)。当然,这些是张艺谋主观意图的体现。他说:“我过去从来没有使过这种完全跳轴的光线不接的方法。我们这次就是故意用很多生硬的方法把它们搞在一块儿。”在《有》片中,这种摄影机的非常规运动随处可见,赵小帅把装疯乱掀餐桌的张秋生拽上饭店阁楼捆在椅子上至下楼与一群搞生日聚会的人们边跳边唱《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及随后饭店“二大爷”与服务小姐欲报复偷窥张秋生等段落,都集中运用了持续左右“甩”及不管进光、虚实和越轴的拍摄方式(赵小帅与边跳边唱的人们之间及被捆住的张秋生与偷窥的“二大爷”之间的来回“甩”,赵小帅强捆张秋生在椅子上及疯狂跳唱的人们的进光、焦点不实与越轴镜头等),使人明显感觉到摄影机的存在。摄影机的非常规运动表明摄影机已作为影片角色参与剧情——它要发言,它要表演,它要说明导演所要说明的现代都市人喧嚣、彷徨、迷狂、混乱的生存状态。
四、夸张、变形的镜头语言
“电影创作者给镜头中的材料,给本来可以客观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加上了一定的态度。”《有》片非写实的“黑色幽默”风格一确定,其夸张、变形富于抽象的风格化的表意功能的镜头语言便随之确定了。这正如张艺谋所说:“我们首先确定这电影的风格,确定了这电影不是完全现实主义的,不是写实的,那么我们就确定镜头……一开始就定好让镜头有夸张和变形感。……基本上使的是0.9mm左右的广角,所以摄影师对演员就在眼面前近拍,这样才能拍到大近景。”在影片中,夸张、变形的近景、特写及二者延伸出来的大近景、大特写通片可见。许多段落中夸张、变形的近景与大近景、特写与大特写占了所用景别的多数,成为体现镜像风格的主导。引导注意力、强化视角效果的夸张、变形的近景、特写运用,将故事发生的直接指向物质现实的本色背景从主体(人物或物质对象)与陪体(环境)的画面系统中剥离出去,让表意性的人物的脸部及人物与物质对象的局部夸张性、变形性地占居银幕的全部或大部,处于低、高调的亮区。很明显,将直指物质现实的背景剥离,是不让它们冲淡创作主体现代都市浮躁与荒诞感的表述;而凸现人物脸部及人与物体的局部打破视觉经验则使浮躁与荒诞感得以强化,从而实现导演表达主观意图的目的。
五、机位、角度的随意变化及不规则构图
在普遍认识上,一部电影在开场十分钟内要让观众明白这部影片要叙述的主要故事趋向;整部电影的叙事也要借鲜明的画面及其明晰稳定的构图适合观众视觉习惯使观众审美自然顺畅地实现。然而,《有》片是反常规的,它没有让观众在开演十分钟内明白影片的主要故事趋向;它也没有迎合观众的视觉习惯,也没有延续正向的审美进程——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整体叙事的反观及创作主体主观意图的把握而实现的(观众的审美进程是逆向的)。这是导演有意设计的。拍摄机位与角度的随意变化及画面的不规则构图使影像失去平衡,重心倾斜。抬头喊叫的人们、旋转倾斜的高楼、舞拳飞腿的群殴、你追我赶的奔跑、边跳边唱的狂欢、掀桌打碗的醉疯以及寻人砍杀的“复仇”都以随意变化的机位、角度和打破常规的构图凸现了重心倾斜的不平衡画面。这些失去平衡的画面间断连接的故事其实是一整体隐喻——故事展现的世界是现代都市人心理世界的外显,是物质重压下异化精神之光的折射。它标明置身浮躁、荒诞世界中的现代都市人的心理是失衡的,其心路历程及生存境遇也是混乱、恍忽、捉摸不定的。
六、累积式故事叙述:设悬→释悬
悬念作为推进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往往成为累积式故事叙述的契机——设悬到释悬,借助悬念层层展开,直至豁然开朗或嘎然而止。以悬念展开的累积式故事叙述,能够不断撩拨观众的神经,如抽丝剥茧;还能在观众的观赏兴奋点低落时再次吊起观众胃口,使之重入梦境;这能标明导演个性和叙述风格,形成张驰相间的节奏。《有》片是借助悬念进行累积式故事叙述的。用张艺谋的话说:“电影的故事性比较强,故事推进节奏比较快,有一定的悬念,有一定的突变,……这个电影的故事可以抓住观众,不会让观众觉得沉闷。”其实斯坦利·梭罗门早就指明了:“绝大多数伟大的喜剧艺术家看来都是用累积法来创作自己的段落的。他们这样做有一个明显的原因:表演的喜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累积逗笑的情境。”当赵小帅被刘德龙率众暴打之后发誓剁刘某右手的悬念一设置,观众的神经便系在了“赵某真能剁下刘某之手”的悬疑上了。随着故事的推进,计谋很久的赵某在安达娱乐公司刘某的办公室真的挥刀剁手了(第一次撩拨观众神经);虽未能遂愿并因扰乱治安被派出所拘留,但其与张秋生在饭店就餐时挑明非剁刘之手不可的谈话,又使以为可“有话好好说”了因而稍稍松驰了神经的观众紧张了起来(第二次撩拨观众神经),而将碍事的张某捆在阁楼上之后,赵某目视餐桌对面的刘某数钱的同时几次抽刀欲剁之情境,则将观众的紧张情绪推向了极至(悬念释解前又一次撩拨观众神经)——掉落的音箱很巧合地将刘某的头部砸得鲜血直流代理实现了赵某剁手之欲望的释悬是嘎然而止的,其未尽之味则是张某敢不敢赌剁手之游戏了(释悬后再次撩拨观众神经)。以悬念展开的累积式故事叙述,在营造紧张、惊恐氛围之时,暗示出现代都市人生存境遇浮躁、荒诞背后的危机。这应是创作主体主观意指的。
七、色彩、配乐与环境音响的主观假定
在《有》片中,色彩、配乐与环境音响的假定性是创作主体精心设计并有意凸现的。装醉耍疯的张秋生一掀桌子,整个光线立刻变为彩色是色彩的主观假定,它直接标明非写实的视像风格。在安红书市寻找赵小帅、张秋生寻找赵小帅的家及张秋生饭店寻找“二大爷”砍杀之时,北京琴书“找媳妇难”及“没招惹谁偏生是非”的滑稽配乐是无声源音乐的主观假定,它直接强化故事的喜剧氛围和矛盾冲突。赵小帅随张秋生到安达娱乐公司找刘德龙要砍其之手的过程——进门、转弯抹角、穿堂入室——响彻着刘德龙在幽僻的办公室打电话的声响是环境音响的主观假定,它亦直接夸张性地强化戏剧冲突。色彩、配乐、环境音响的假定性在较大程度上造就了影片的艺术性,而有别于违背生活细节真实的虚假。作为阐明都市的浮躁与荒诞、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喜剧电影,《有》片的艺术性要求色彩、配乐、环境音响等技术上的假定性基于细节真实的服务。换句话说,电影艺术媒介不可或缺的两个特性——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相辅相成,促成了《有》片的艺术性;故事的荒诞感、喜剧的闹剧色彩及现代都市人内心世界的浮躁感因之得以凸现。
媒介本性的误识。
作为一部国内“独一份”的极具个性的实验电影,可以预见,《有》片会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诚如,电影手法的运用上,影像风格的把握上,剧作故事的开掘上及喜剧形式与主题的结合上,影片都有不尽人意之处。对此,张艺谋并不讳言。“我自己有很多遗憾,比如说剧本可以弄得再有意思一点儿,在风格的把握上,在分寸的注意上,……有很多遗憾。”“在剧作上更严谨、更有趣一些。喜剧形式和主题的结合上更好一些,影片的质量还会提高一点。”审慎分析影片,可以发现,影片的不足主要在于对电影叙事媒介本性的误识及因之导致的对电影艺术手法、技术手段的误用。电影中,人物动作居于主导地位,人物动作节奏主导着导演叙事节奏和观众心理节奏,直接影响着整部影片的感染力、吸引力等。对电影导演来说,正确把握电影叙事媒介本性及影像系统性质,并确立与之适应的艺术形式,尤其是人物动作的方向、节奏的人性等是必须的。而对媒介本性的误识及对人物动作的把握不当,将会在不同强度上颠覆影像系统性质及既定视像风格,破坏观众审美进程。这也是不少观众难以真正实现对影片认同的原因。
一、缺乏画内动作的画外动作,使动荡的视像难以为观众接受。如果立足视觉形象角度,电影就是一系列间断拍摄的运动画面的连接。在运用运动画面展示人物动作时,画外摄影机的运动必须有画内人物动作的支持、配合,即画外动作必须建立在画内动作有未知因素的基础上。若画内动作是封闭的、内指的,画外动作就不便进行,也就是摄影机应保持稳定、以形成平稳、明确的影像。只有在画内动作有未知因素也即有画内诱导动机(心理动机、叙事动机)时,符合风格需要的画外动作才是必要的。要知道:“一部影片中的运动应当有特定的电影意义,而决不能只是单纯的动力学活动。”《有》片当中,赵小帅在安红房间坐在门旁与坐在床上的安红对话、安红说与其”比试“床上功夫的段落,赵小帅坐在街旁防护拦上等安红的段落,赵小帅与张秋生坐在饭店餐桌旁吃饭、谈话的段落,赵小帅在饭店看对面的刘德龙数钱的段落等,画外摄影机的不断晃动是不妥的,原因是这些段落的画内动作是单一、清晰的,并不潜伏可变的未知因素,其动作曲线基本停顿。不妥当的画外动作使这些叙事段落的影像动荡不稳,背离了观众的视觉经验,使其难以参与审美。评论界曾有人指出,《有》片在风格及手法上模仿了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一些影片。在此且不论这种说法的真伪,而引伸开去——喜欢采用“MTV方式”拍摄影片的王家卫,虽然在不少影片中采用既有画内动作又有画外动作且动荡不安的画面段落进行叙事,但对画内动作缺乏未知因素、曲线停顿、方向内指的叙事段落,其画外动作则相当节制,即尽可能地让摄影机保持稳定,让平稳的画面清楚、明了,从而让观众的接受自然、顺畅、无疑,这种动静相宜的拍摄方法是理智的,是值得借鉴的。
二、过多方向不接的运动镜头连接使一些叙事段落显得混乱。电影总要以运动画面叙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尽可能地清晰,能够被观众很自然地接受,进而在观众接受过程中使电影艺术创作最终完成。这要求电影摄影、剪辑要使前后镜头的方向相接,使运动合乎现实逻辑与视觉经验,不使运动的视像混乱、颠倒,不让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为圈内人所熟知的常规。虽然,为实现导演的艺术构思及影片的独特风格,个别画面段落可以打破这一常规,但决不能使这种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假如一部影片充塞前后方向不接的运动镜头,影片便很难被欣赏、审美。《有》片作为夸张、变形的“黑色幽默”影片,试验性地运用一些方向不接的运动镜头段落是无可厚非的。然也不能不指出,由于片中因摄影机的越轴而导致的方向不接的画面段落过多,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叙事线索的明晰性,违背了观众的视觉经验和欣赏习惯;有的段落甚至中断了观众的审美进程。拍摄过《筋疲力竭》(1960)这部电影史上著名影片的让——吕克·戈达尔破天荒地在自己的影片中大量运用方向不接的运动镜头,不管观众的好恶及日常现实逻辑。但戈达尔的这种做法在当时乃至后来都引起了很大争议。褒扬者认为其革新了电影美学;批评者认为其影片毫无章法、一片混乱。这里且不论争议本身的正误。事实上,一方面戈达尔作为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载入史册;另一方面,戈达尔的这种做法以后几乎无人问津。可见,不谈极特殊的个例,保持运动画面的方向衔接是合乎电影叙事媒介本性的。
三、简单的故事没能成功承载实验性的风格,颇给人强作戏之感。以“黑色幽默”风格展示现代都市的浮躁与荒诞,对于叙事艺术的电影,必然要求故事本体有展示这种浮躁与荒诞的充分性,即通过对喧器纷繁的故事的充分叙述,让人自然而然地感到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是一个浮躁荒诞的世界,夸张变形,复杂多变。说到底,对一部影片的彻底把握,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故事上;导演的风格和意图,最终还是要借助所叙述的故事及如何叙述这个故事体现出来。毕竟,“电影是作为一种叙事艺术而存在的”。《有》片在如何叙述故事方面做了很多,但在所叙述的故事方面,则稍欠充分,即故事开掘得不够,其纷繁复杂性不充分。影片开场线索较多,节奏较快,戏味较足,开启了一个充分展开故事的广阔空间。然随后的张秋生找赵小帅索赔电脑与赵小帅找刘德龙砍手直至张秋生出门找大哥大“告密”的故事发展过程,线索较单一,情节较简单,节奏较平缓,不少故事段落主要不是靠动作而是靠语言完成(与叙事媒介本性相悖),戏味不足,似有强作戏之感。虽之后的影片结尾浓墨重彩,线索多头并进,紧张的节奏快速展延,戏做得较足,但它毕竟不能完全弥补故事发展历程开掘不足的缺憾;较多得益于艺术、技术手段的独特风格也受到了影响。
四、不够充分的喜剧因素与主题之间尚未形成饱满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独特、新奇往往是在矛盾双方的相互反衬、相互对比中体现的。《有》片的故事题旨集中于现代都市人的浮躁与荒诞。这一主题是严肃沉重的甚而是富有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色彩的。影片故事内容的表层——浮躁、荒诞的现代都市具有喜剧色彩,而影片故事内容的深层——现代都市的浮躁与荒诞则不无悲剧性。这种表面喜剧实则悲剧的故事题旨,若用悲剧的形式来体现,则会因其与故事内容的表层相悖以及形式与题旨之间缺乏张力而难以给人实在的叩人心弦的艺术感受。但如果采用喜剧形式,则会因其与故事内容的表层协调以及形式与题旨之间相互比衬的矛盾张力而达到出人意料的审美效果。可喜的是,《有》片采用了夸张、变形的喜剧形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充分的喜剧因素并没贯穿影片始终。影片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叙事段落较为简单,喜剧成分、气氛、效果不够充分,其与深层悲剧性题旨之间的张力也不够饱满。这就使主要靠故事本体之外的手段营造的艺术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故事发展过程的视觉冲击力、情绪感染力也相对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较高层次交流。
注:引文参考书目:《电影艺术》杂志,《世界电影史》,《电影的观念》,《多维视野的统一——电影节奏的逻辑起点初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