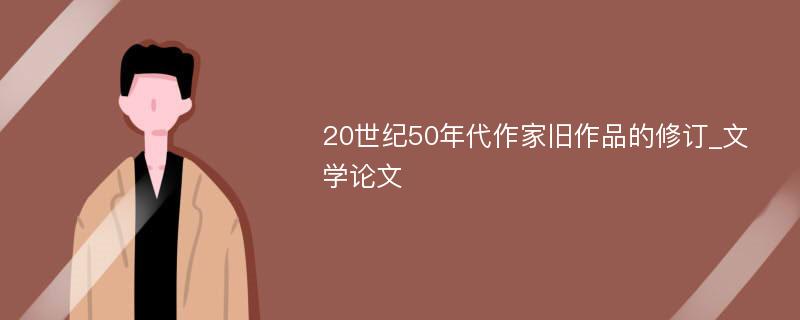
五十年代作家对旧作的修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作论文,五十年代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刚成立不久的共和国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个“绿皮书工程”,即给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出版选集、选本和文集,也许是取五行以绿色象征春天吧,这批书多用绿色做封面。它与重点编注的象征经典化的棕色《鲁迅全集》,以及用质朴的农民生活木刻为封面图案的解放区文艺“人民文艺丛书”鼎足三立,以出版行为来设计和建构共和国初期的文学模式。
“绿皮书工程”意味深长。由于它选录的是一批代表性作家在三四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品,而且又由作家本人做了不少带实质意义的选择和修改。这些绿皮书也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价值的现象,有价值的事件,有价值的个案。它们的价值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察:1)现代文学版本学的价值;2)现代作家在修改过程中曲折地透露出来的精神文化学的价值;3)三四十年代文学名家名作在共和国初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被接受的程度和方式的文化接受学的价值。对这些绿皮书的研究,是具有非常充分的历史实证品格和非常深刻的文化变迁意义的课题。可惜我们的学科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注重原版书和原始报刊,当代文学研究注重批判运动思潮和新出现的作家作品之时,使这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事件和个案,除了在一些作家传中简略提到之外,几乎成了我们正规的文学史研究的“三不管地带”。
文不厌改,本是文学史上的常态。中国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关“不朽之盛事”的文学立言事业,岂可等闲视之。杜甫开创的苦吟诗风,以及欧阳修、王安石修改诗文,都是文坛千古流传的佳话。曹雪芹在悼红轩里,对他的《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使他的不朽名作“字字读来都是血”。当然秦王嬴政的相国、“亚父”吕不韦聚集三千门客编写成《吕氏春秋》,还要在咸阳市门上悬赏千金,说是谁要能够增损一字,就奖赏千金。对于这位做生意做到把秦国都收入囊中的吕不韦,你就是能够改他的文章也不敢去改,这实际上是中国古老的书籍炒作或者作秀。不过,无论古今,正常状态的修改,是一种高度的生命投入,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精品意识的体现。50年代老舍写《茶馆》,先写一个初稿找一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行家来讨论,选择堪称杰作的第一幕第二场作为底本,然后进行重写,四易其稿,终于创造出以三个时代横断面跳跃联接的新的戏剧美学形态。
然而,50年代“绿皮书工程”的大修改,已经偏离了正常状态的修改,是常态和异态并存,甚至常常是异态压倒了常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情境和文化思潮变动激烈,简直是波澜迭起,天翻地覆,非常态的修改是不时出现的。曾经写过《从军日记》的谢冰莹,在30年代应良友图书公司之约,写了一本《女兵自传》,后来她脱离北方左联,在改版时就删去一些控诉军阀暴行的激烈言词。张爱玲50年代在上海《亦报》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结尾是曾在陕北为人民做事的许叔惠,在建国初期把一班上海朋友带到东北支援建设。她离开内地后,把这部小说改成《半生缘》,结尾做了巨大删节,改成许叔惠到美国留学。在急遽的社会文化变动中,这些作家改变了自身的人生轨迹和人生形态,因而在新版著作中不可避免地改变其生命的投影。
修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今天质疑昨天,是昨天蜕变成今天。这里的昨天、今天,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既有主动的,也有无奈的;既有欢欣的,也有痛苦和惶惑的,其间还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中间状态。这就使得修改成了一种复杂的文化。当然下面所讲的绿皮书,有的是其他颜色的封面,修改40年代也包括作于二三十年代,但40年代依然被公认为杰出的作品。在50年代绿皮书的修改潮中,郭沫若依然采取主动的弄潮儿的姿态。他在一些关键的观念上修改了早期的作品,因而也修改了他早期的思想文化形象。本来,他1928年版的《沫若诗集》,把《女神》中的《匪徒颂》混杂地歌颂资产阶 级学者罗素、哥尔栋和列宁的地方,修改为歌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巨炮之教 训》中借列宁之口,呼唤着“为自由而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修改 为“为阶级消灭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为社会改造而战”,——这就已经给 一些批评家造成错觉,仿佛他在五四时期已经追求马克思主义了。
但是人名和政治口号的改动是容易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改动就困难得多。郭沫若1924年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接触马克思主义,50年代就自称这“以后便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他1925年12月出版《文艺论集》的时候,在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还认为“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 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 围中”。这要到1958年出版绿皮《沫若文集》第10卷,才改为“文艺如由真实生活的源 泉流出”,“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 要有生活的源泉”。另一篇《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原版说:“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 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精髓所吐放的光辉,人类不灭,人性是永恒存在的 ,真正的文学是永有生命的。”到1958年的文集就改作:“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人生虽 然随时代而转变,但转变了的时代面貌却被保存于文学之中,而为后代借鉴。因而文学 永有生命。”这类改动或借鉴了当时与之对立的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文学观,或借鉴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生活为文学的源泉的观点,只能看做30年后 郭沫若文艺思想变迁的材料,看做他对文学的有了新认识之后的一次“自我化妆”,已 非1925年的原貌。如果依据这些材料去谈20年代郭沫若的文艺思想,是会造成失误,甚 至留下笑柄的。
在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文艺界波澜迭起的批判《武训传》、 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的政治标准逐渐被强化、片面化和极端化。 给一批著名作家出选集、选本和文集本来是颇具规模的文化建设性举措,但在这样的文 艺片面政治化的气氛中,作家们未能从容地、深思熟虑地清理和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 就急于动手修改早获公论的名作,也只能是用一些初步学到的理论概念和社会要求,对 本来具有生命完整性的艺术品作一些削足适履式的删节和修补。文艺这只脚是讲究个性 和多样性的,鞋子却是别人按主流观念的尺寸做成同一个号码,即使穿鞋的人是真诚的 ,也难免要屈起脚趾或塞上棉花,难免有许多勉强、无奈、尴尬和痛苦。老舍在1955年 修改出版《骆驼祥子》,做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修改:1.在当时谈“性”变色的气氛中, 对祥子与虎妞、祥子与暗娼夏太太、祥子与下等妓院“白房子”的“白面口袋”之间的 性引诱、性心理和性行为暗示等文字进行成段的删节,其中不乏相当微妙的笔墨,都作 为“不大洁净的语言”舍弃了。2.对“革命者”阮明的无赖、变节和死亡的情节全部删 去,大概是担心被人猜测为影射共产党,因而在新版中就根本没有阮明这个人存在。3.删掉结尾的一章,因为这章写祥子堕落成“文化城中的走兽”,在吃喝嫖赌的深坑中打 滚,有丑化劳动人民之嫌。其实这一删节在1951年已经开始了,只不过1955年删得更彻 底。它不是给小说安上光明的尾巴,而是割去尾巴成为“秃尾巴”。对于小说的结尾删 除黑暗,装点光明,乃是50年代这批绿皮书的常例。老舍式的修改与郭沫若式有很大不 同,他大体上是只删不增,更无意地从本质上改动某些关键词,使人误认为他是一个先 知先觉者。
绿皮书的修改,多是政治性的,甚至为了政治的明晰性,不惜损伤作品的艺术完整性和多样性。曹禺对《雷雨》、《日出》的修改,大概考虑到这些剧作还在演出,还要面对政治热情极其高涨,又极其挑剔的观众,而且他本人的自我解剖又极其严峻、极其痛心疾首,因此改动戏剧情节强化阶级斗争意识。《雷雨》中的侍萍不再是含垢忍辱地承受命运折磨的宿命论者,而是再度见面就怒斥周朴园是“杀人不偿命的强盗”,使周萍成为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乃是“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它的结局是周萍、周冲、四凤都没有死,从而以阶级学说的简单推断消解了悲剧的震撼力量。《日出》的修改也突出阶级斗争的主线,它把金八写成日本人纱厂的总经理,杀害小东西的纱厂工人身份的父亲,最后是地下革命者方达生率领纱厂工人把小东西从金八的虎口中救 出。这种修改倾向从观念出发,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了原作的诗性智慧和悲剧力量,使30 年代作为中国话剧真正成熟之标志的这两部杰作在某些方面水平的滑坡,令人联想到20 年代后期多少带有幼稚病的革命文学,尤其是早期革命文学所主张的源于日本纳普的“ 文艺是宣传的工具”的观念。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时或是循环的,时 或是螺旋式。在一种政治力量和政治观念的作用下,我国革命文学的观念在时隔四分之 一世纪之后,又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反刍现象”。
一个新政权建立的初期,致力于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乃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但是随着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代的历史转折,如何处理好政治价值体系和文学观念体系之间的整体性和差别性,不是早已有了结论,而是要长期摸索的历史课题。截然地割裂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或者简单地等同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利于整个共和国事业的健康 、协调和持续发展。而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后者的危害更大。50年代的 绿皮书作家多处在文学创作成熟到火候的时期,以1955年为标界,年纪较长的被称为“ 郭老”的郭沫若63岁,被称为“茅公”的茅盾59岁,其余老舍56岁,沈从文53岁,巴金 、沙汀、艾芜51岁,曹禺45岁,还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候补委员。当这批作家 的文学思维趋于炉火纯青,驾驭笔墨得心应手,已经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写出精品杰作, 因而需要更广阔的文学创作空间的时候,却以一种把文学过于等同于政治的观点,使他 们在修改旧作中装扮自己、割去尾巴或掉入幼稚观念的反刍,进而在写作题材和创作方 法上改弦易张。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在炉火纯青后另起炉灶,得心应手之后另学手艺 ,其间所造成的作家创作生命史上和文学发展史上的遗憾,是值得后人深刻反省的。和 平建设时期的大国文学,应该有大国的风度和气象,尤其是在政权巩固和发展之后,应 该允许更加广泛的自由创造,更加丰富的美学精神的探索,用以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 的伟大作品,让世世代代的人们为之自豪和神往。这就是我们反省50年代作家对旧作修 改这桩文学史公案所得到的一定体悟吧。
2002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