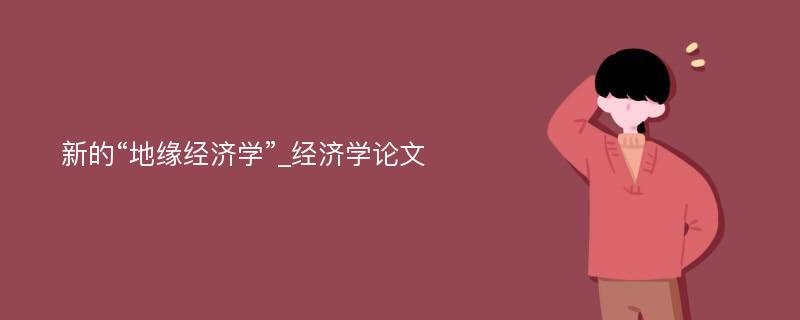
新兴的“地缘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适时产生,为新形势下对外扩张提供理论;
影响颇深,或许会成为各国行为的“指挥棒”。
在走向21世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国际关系和各国的内外政策都在经历规模空前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历史性大调整。适应这一大调整的需要,各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说纷纷涌现。地缘经济学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新学说之一。
大国新需要的产物
美国一些从事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主张,在两极格局结束之后,美国应当放弃以军事实力作为全球称霸的主要手段,而应以海外投资、出口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工具。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被称之为“地缘经济学”。
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勒特韦克先生是该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当遏制共产主义是对外事务军乐队的指挥时,经济政策排在了后面。这种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直到下个世纪,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学中,资本是火力,对市场的渗透取代了国外的基地和驻军。可以这么说,战略核武器的对应物是类似产业和投资政策之类的东西。美国面临的政策问题的中心是建立地缘经济威慑力量。过去靠武器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另一位创始人美国兰德公司前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地缘经济的时代,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商业与技术力量同军事力量一样,都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地缘经济学如同地缘政治学一样,就其创始者的初衷而言,都是适应西方大国对外扩张需要的产物。19世纪末期诞生的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德国学者拉策尔等人声称,国家系一种具有生物属性的“社会有机体”,其活动和兴衰取决于所据“空间”的地理位置和范围大小,国家的发展自发地要求向外扩展“空间”。地缘政治学适应西方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一经提出,迅即风行欧美。如今,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的新形势下,地缘经济学的倡导者们则主张,西方大国应转而依仗金融和经贸优势去抢占世界市场,从而保持和扩大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强权地位。可以说,这两种学说都追求同一个目标,只是因为形势不同而手段各异。
顺应主旋律
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从广义而言又均有其合理的内涵。地缘政治学可理解为从地理条件、位置和环境的角度去解释、观察和处理国际关系,并在这个意义上为各国所广泛使用。地缘经济学则可理解为从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从这点来看,地缘经济学顺应了当今经济竞争渐渐上升为世界主旋律的大趋势,因而引起世界各国越来越大的关注。
经济对于各国一向都是综合国力的主要基础。不过,在两极体制结束之后,经济的基础作用更加突出。无论未来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21世纪都将是“经济第一”的世纪。各国谋求经济利益的需求将优先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世界舞台上的重头戏由“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经济振兴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赛的主战场。发展经济是整个世界喊出的最强音。
两极对抗时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军备竞赛和全球争霸,拖挎了一个超级大国--前苏联,削弱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与此同时,二次大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埋头致力于振兴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综合国力呈赶超美国之势。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各国清醒地认识到,致力于军备竞赛和全球扩张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和综合国力的过度消耗。而经济实力的多中心化又构成了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主要基础。
当然,军事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建立、维持和加强正当防卫所必需的国防力量。不过,国防建设只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正当防卫为目的。如果一个国家将军事实力当作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把过多的资源用于谋求军事优势和对外干涉,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必将受到削弱,最终所付出的代价必将大大超出对外扩张所获取的暂时利益。前面提到的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削弱,就是明证。
有鉴于此,两极对抗消失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日显重要,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外交关系等均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并服务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地缘经济学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作用和影响上升
地缘经济学虽问世不过两三年,但已取得了与地缘政治学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成为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这有助于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并加速新经济格局的建立。
为顺应地缘经济变化的大潮,世界各国下大气力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把增强本国综合国力和谋取经济实惠摆在国家战略中的最优先位置。美国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安全第一”的政策,推行“克林顿经济学”,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扶植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尽管“克林顿经济学”在推行中遇到重重阻力,还是对美国的经济振兴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99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3.6%,增幅列西方各大国之首,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超过日本,夺回冠军宝座。日本受“泡沫经济”危害,1991-1993年爆发“平成危机”,出现负增长,国际竞争力由连续8年的第一位下降至第三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和企业界采取了一连串的紧急对策,力求逐步解决银行系统脆弱、工业投资过度和劳动力过剩三大结构性问题,力争恢复竞争力的优势。1994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5%。西欧国家也在积极解决困扰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改革福利和劳工制度,进行结构性经济调整。1994年西欧经济回升,各国平均增幅约为2%。一些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实现经济从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一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了新的认识,正开始调整政策。独联体和东欧诸国也在致力振兴经济,多数东欧国家1994年经济已走出低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在地缘经济学的影响下,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区域集团化进程加快。在这方面,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1)欧、美、亚三大经济圈三足鼎立之势正在形成。1993年1月,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建成,在12个成员国之间实现商品、劳务、资金和人员的部分或全部流通。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美、加、墨三国将于15年内分阶段取消关税壁垒。1994年11月15日,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二届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茂物宣言》,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2)经济区域集团化由小到大,由初级到高级,由经济合作到政治合作。1994年11月,欧共体改名欧洲联盟后,积极开拓新边疆。1995年1月,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的加盟,使欧盟成员国增至15个;同时,欧盟还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7国联合建成了欧洲经济区,东欧6国取得了欧盟的“联系国”地位。欧盟将逐步实现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最终建立“统一的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区正积极向南扩展。1994年12月10日,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34个与会国就2005年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亚太经合组织也在不断扩大,其成员已由1989年初创时的12个增至目前的18个。
(3)不同发展水平与体制国家兼容,区域集团间排他性与开放性并存。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的建立,开创经济水平悬殊国家组成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先例。中国及中国台湾省同时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则是地缘经济因素超过地缘政治考虑的一种表现。区域性经济集团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集团成员间的互惠实际上是对集团外国家的一种歧视和对其他集团的一种竞争。然而,这些集团不可能对外封闭,而只能对外开放,各集团间的相互合作也在加强。
地缘经济学强调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程度日益加深,从而促使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主要表现在:(1)资金流通和生产经营全球化。跨国公司已由60年代末的1.8万家增至目前的3.7万家,这些母公司还控制着分布于160多个国家的20余万家分公司。(2)国际贸易和市场竞争全球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进展是,1995年1月1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3)科技合作和信息传播全球化。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正伴随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增强。新的信息媒介的发展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大。在21世纪的信息世纪中,人类生活和工作的一切领域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4)人类面临全球化挑战。21世纪将是全球性问题“大爆炸”的世纪。人口、环境、资源、生态、贫困、动乱、冲突以及道德沦丧、吸毒贩毒、疾病蔓延、恐怖暴力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正给全人类带来更大的困扰。这些共同性的挑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人类正以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眼光和全球性合作去应对。
地缘经济学正推动“多个力量中心”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建立。西方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美国的优势地位将继续相对削弱,日本和德国加紧赶超,西方大国在“以资本为火力”向国际市场的大进军中相互碰撞日益突出;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在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上升;俄罗斯经济跌宕起伏,综合国力有可能渐趋恢复,并维持与独联体各国的“特殊关系”;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逐渐上升,与发达国家的鸿沟缩小;发展中国家分化加剧,部分国家迅速崛起,逐步跨入新兴工业国行列,部分最贫穷国家却相对更加贫困;就地区而言,东亚的发展仍领先,拉美形势看好,非洲经济上升缓慢。
总而言之,地缘经济学在兴起,其发展尚待进一步跟踪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