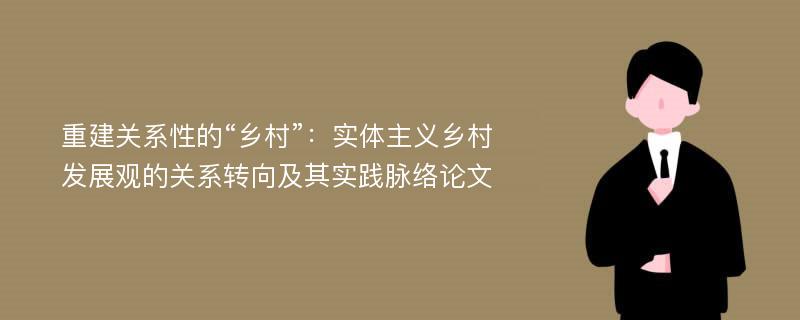
【村落发展与乡村振兴】
重建关系性的“乡村”:实体主义乡村发展观的关系转向及其实践脉络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乡村研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仅是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而在更深层次包含了对总体性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关注。“乡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一种极具争议的理论建构。在全球乡村经历开放式转型的背景下,有关于乡村及其发展的一些传统理论假定需要得到批判性的检视和挑战。实体主义乡村发展观的关系转向为此提供了一种关系性的理论框架来重新理解、描述和建构乡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重构一种关系型的乡村治理体系,其对象不再简单是“人”或“物”,而是涉及城与乡、本地与全球、人类活动与自然社会系统等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空间关系。
关键词: 乡村发展;实体主义;关系转向;实践脉络
一、转型社会的乡村发展:实体主义的传统假定及其挑战
无论是在早期的研究中,还是在当下的著述中,“乡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一种极具争议的理论建构。“乡村”的概念非常复杂、不精确,同时充满了不同历史时期特殊的时代意涵和理论指涉。尤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话语以及乡村发展实践的塑造下,全球的乡村发展已经呈现出理论立场和实践脉络的多元主义。
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阈中,乡村内在地包含了物理性、物质性、自然性、政治性、社会性以及文化性等多重属性,同时也在多元的知识维度上被理解,并且表达出极为不同的乡村性意涵。其一,物理乡村性(Physical Rurality),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居住形态,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注] ① 社会学视阈中的“村落”,则主要落脚于其共同体的社会属性。 。自魏晋南北朝隋唐逐渐形成以“村”称乡间聚落以来,乡间的大小聚居地,通常都可称为“村落”或“村庄”[2],其具有现象的真实性以及感官的视觉性。其二,物质乡村性(Material Rurality),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强调了乡村作为一个资源和资本运作体系的存在。基于不断变化的物质特征和资源结构,乡村在历史上被视为生产的特殊节点,乡村消费功能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被强调。其三,自然乡村性(Natural Rurality),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乡村的空间构成来自人类、非人类主体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活动及其相互关联。其四,政治乡村性(Political Rurality),作为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乡村被视为一个多主体间权力和资源斗争的微观单元,强调乡村内在的权力属性。其五,社会乡村性(Social Rurality),在西方的语境中,乡村主要表达的是与地方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一种传统社会经验,它基于本地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与城市社会和大众社会相区别。在中国,乡村既是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农村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基础。其六,文化乡村性(Cultural Rurality),作为一种符号意义的呈现,乡村在文化上表征了以其为基础的传统价值构造和文明形态,它也被视为理解社会文化变迁乃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如同乡村概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一样,乡村发展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进程。 整体而言,当今世界的乡村社会集中面临着许多困境,比如经济衰落、人口外移、老龄化等。关于中国村落兴衰的讨论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而展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82年至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2.1亿人增加到7.9亿人,城市化率从20.9%提升到57.35%。而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的行政村数量由732万个减少至589万个。2017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6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注]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研究院,《2018—2023年中国智慧农业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81126/1459421137475.shtml. 。超过2.8亿农民离开他们生活的村落,前往城市务工经商[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 。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构成一体两面变化的是传统村落在空间格局、要素结构和组织关系等方面加速解构和重构,并呈现出不同的转型面向: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大量转移、土地的大量被征收使村落功能面临边缘化风险;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活动的扩张、正向外部性的获得以及现代性的再嵌入使村落产生了抵抗边缘化的能力。“传统乡村将向何处走,又将如何走?”的提问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乡村转型的讨论[3],也同时成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和实施的重要现实背景。
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乡村发展旨在通过重新激发乡村的经济—社会活力来解决乡村社会集中面临的诸多问题[4]。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乡村发展观,形成不同的测量指标来引导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比如着力推动中小规模非农公司发展的芬兰“新乡村范式”[5],推动城乡关系整合的美国“乡村综合计划”[6],等等。事实上,乡村发展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还包含了对总体性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关注,其更深层次地根基于特定乡村发展观的知识基础之上。因此,关于乡村及其发展的一些传统理论假定首先需要得到批判性的检视。长期以来,乡村社会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构造,自然、土地、人口、组织以及本地社会在特定乡村空间交织。主流的乡村观来自对地域空间的领域想象。乡村被建构为一个带有封闭性和边界性的“空间容器”,认为里面装载着一个具有历史稳定性的乡村社会。然而,这种思考乡村的方式与实体主义的理论假定紧密相关。
乡村被视为一个自发形成的边界实体,乡村发展在理论上被置于科层化的空间结构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乡村在本体上被假定为长期形成的,具有相当程度稳定性和聚集性的社会实体,并具有明晰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在这种领域式的空间想象中,乡村在理论上被理解为固定、静止的绝对空间和功能性的实体——具有综合政治、经济、社会的功能。在此基础上的乡村发展导向也长期是一种基于“地点”的发展策略,强调在特定领域内的地点塑造。更进一步地,乡村还在理论上被置于科层化的空间结构中。一方面,乡村长期被视为一个与“城市”相区别的社会实体,并从他者的视角中建立其基本的意义。不仅仅作为一种二分法的框架中被建构为“城市”的对应物,更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关系填充了科层本质。在城市—乡村连续统中, “城市中心主义”[注] 城市中心主义是“中心地点理论”的遗产,它确立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非中心,聚焦于核心驱动的区域发展方案。 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带来了地理空间的科层化,预设了城乡之间非平等、非对称的空间关系,更在实践中不断通过资源与权利的不均等分配造成了乡村社会的现实边缘化。另一方面,乡村作为一种本地社区,被强有力地置于“村—乡镇—县市—区域—国家”的科层空间尺度中,并作为政治和行政单元被识别。
第一,质疑实体主义空间观确立的空间本质,重新将传统被边界分割的地域实体视为开放、流动、关系性的空间形式。关系取向理论质疑传统对于“空间”和“地点”的理论判断,尤其是从边界(领域)或者是科层(尺度)的结构形式来描述空间的方式。拒绝接受固定和局限的空间假定,而强调空间与地点的实践和建构。关系主义的空间理论将“空间”首先赋予了相对的特质(与绝对空间相对),其次赋予了关系特质[13]。空间具有网络化的本质,其边界表现出多孔的特质。关系主义理论并不关注特定的结构形式,而是将所有空间形式之间的空间联系发展为自身理论的重点。由此,空间的主要表达形式从传统的领域式结构转向了网络和关系流的生产。
社会科学研究中关系取向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被视为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演进的具体表现之一。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乡村研究对传统研究的最大反叛恰恰来自关系取向乡村发展观的出现。它极大地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实体主义乡村发展观,重新开启了对乡村的关系性思考。
实体主义的乡村观在功能上假定了一个具有功能维持和自我整合的客体。政治地理学思想的介入强调了乡村空间内在的物质性以及可视化的乡村发展。国家权力的地理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依托于边界的地点空间来加以装载和运作,更多地关注乡村在资源接近性和资本生产问题上的实体功能,强调乡村空间内在的物质基础尤其是经济资源的分布,关注于农业生产的变迁,并通过文化和政治支持来促进农业资本的积累。乡村发展的重点因此落脚于其中经济过程和物质资源结构的变化。政治地理学思想的介入,一方面将乡村视为城市发展的资源和引擎的物质实体,另一方面又偏向选择具有空间选择性、城市优先以及促进聚集为特点的城乡发展策略,由此在实践中阻碍了更大意义上的空间整合和城乡交互发展。“城市中心主义”的空间发展思路附属于特定的地理经济逻辑,更严重的是将乡村性视为与现代性相对抗的产物,引致了农村发展问题不断被再生产。
中国涉及乡村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宏观政策制定,整体上经历了从单点到系统的乡村发展规划。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涉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协同、关联和整体重建。2018年、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又再次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来为乡村振兴确立制度保障[注] 参见人民网,《习近平: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9-03/09/content_1912726.htm. 。已有的探索聚焦于实践靶向,对乡村振兴的路径和行动焦点展开较多研究,然而较少聚焦于讨论乡村振兴所关联的更大的结构性关系。乡村振兴需要被纳入更广泛的关系系统加以研究,其本身需要建立在一系列空间关系调整的基础上。
第二,拒绝接受任何给定性的空间本质,而将要素放在关系本身的建构和生产中,进一步来讨论社会空间关系的异质性。关系取向理论将“关系”本身视为理论的起点,将理解“空间”的重心落脚于网络、联系和流动性上,由此打破了科层化的空间关系,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这样的二元论在网络关系中成为平等的互动主体。拒绝任何本体论上的实体主义假定,转向关注空间的社会建构以及知识、意义、身份的多元形式参与。空间不仅有物质维度,也同时有观念维度,共同构成了空间完整的关系属性。
二、关系性地思考“乡村”:乡村发展理论的再出发
聚焦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寻找并理解乡村的结构本质,简化或弱化乡村的社会过程。作为一个分析单元的“乡村”成为离散、预先给定的分析单元,乡村发展在理论与社会实践总体性的互动联系相分离。实体主义的乡村观对乡村采取一种总体、稳定、结构性的空间描述方式,将人、地点、组织、观念等要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同时,实体主义倡导了一种特殊的“群体主义”——预先假定乡村中的群体存在,表面上关注到不同层面实体变量对群体建构的影响,但实际上却简化或弱化了群体建构和维持的过程[7]。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产生了与具体情境性要素相分离的抽象本质,将乡村建构成为由一系列内在特点构成的静态、抽象、原子化的分析单元。对静态内在结构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实体边界的强调构成了实体主义乡村观的重要理论特质。乡村研究中因此常见用个案研究方法来散点式地理解并描述独立的乡村故事,而对于乡村与乡村之间的关联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联系如何在微观情景中具体呈现,乡村研究始终在个案之间缺乏相互对话,并难以在理论上协调好共同性与多元性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空间”的再概念化:关系取向理论的介入
信息技术、现代交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去规则化、权威的转移以及物资、资本与劳动力在地域之间前所未有的流动强度带动了全球社会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卡斯特尔所言的“空间的湮灭”[10]。现代社会穿透了原有的地域空间之间的边界,不同空间规模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形态,使得我们不得不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重新去思考理解和改造世界的眼光,空间理论中的“关系转向”[11]正是这一背景下的思想产物。
(2)实现对电力通信设备实时或准实时的状态感知,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设备的健康状况,并基于通信设备的健康状况历史数据,为运维巡检人员提供该设备的健康状态趋势结果。
关系取向的空间理论首先对传统空间性的理论表达——实体主义空间观发起抨击,认为现代社会的空间性既不能被视为边界性的领域实体,也不能通过结构性的“地貌学”[注] 也即集中于描述空间的高度、深度、大小以及接近性。 来描述。关系取向的空间理论[12]关系性地来思考空间[11],转向对于空间实践关系的深层表达。整体而言,关系取向理论在重新理解“空间”概念方面突出地表现出以下特点:
(1)运用完全静态信息博弈模型。及时对农户利益所得进行定期审计和按照当下趋势制定合理的销售对策,以求达到不浪费资源的高效销售与合作。
公路与城市道路对于圆曲线最小半径的规定存在差异,经对比分析,城市道路规范对最小圆曲线半径限制更为严格。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时,既有道路局部曲线段曲线半径不能满足城市道路规范值时,必须对既有道路平面线形进行调整优化,令圆曲线半径满足城市道路圆曲线最小半径与不设超高(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规定。
在理论上,实体主义乡村观能够对静态的乡村结构予以描述,而无法对乡村社会的建构过程、变动特质以及极化现象的产生给予理论上的回应。在实践上,以“地点”为基础的实践取向,忽略了在更大范畴中地点在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关系中的嵌入性[6],较少能够关注网络关系本身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助益。比如在现有的乡村发展政策和项目中,较多的关注在特定地点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扶持、居住环境改善以及社会福利传送,而较少重视城乡互动的乡村发展规划和区域性的乡村合作计划。“乡村”的传统假定与当前发展现实之间的张力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追问:究竟是什么重新构成了乡村?而我们又如何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重新理解、描述和建构乡村?除了实体主义乡村观之外,乡村及其发展是否可以有一个补充性甚至是替代性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启发我们的想象?对此我们既需要对以往的乡村发展观进行批判性的检视,也同时需要思考新的概念和理论视角。
第三,关系取向的空间观不仅带来了本体论上的竞争性陈述,同时也呼唤关系性空间实践和空间认识论上的变动。空间如何被人类基于不同的社会利益而积极地塑造,成为关系取向的重要理论焦点。关系取向理论带来了整合取向的空间认识论来对空间关系进行考察,尤其观察到空间生产中边缘化和抵抗的关系过程以及空间行动者中的少数人群。同时,关系取向理论所强调的通过社会建构主义路径来理解“空间”,实际强调的是理论的多元主义,引入更加复杂和多面的内容来解释变化中的空间。
(二)乡村发展观的关系转向
关系性地来思考空间在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同时成为引领未来乡村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在过去十年间,关系理论对于乡村发展理论和乡村研究的影响尤为显著。可以说,关系理论重新改写了我们对于“乡村”原初的思考和概念化方式,重新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赋予传统乡村空间一种动态的关系性解读。关系主义理论使得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拥抱新的理论导向,也在乡村研究中开始倡导重新认识“关系性的乡村”及其重要性[14]。与“乡村”的实体主义认识不同,关系理论认为并不存在天然整合的乡村空间,即使是前工业时期的乡村也不是一个整合的边界实体。尽管关系理论并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整体的理论旨趣是反对并试图超越“作为一种领域的乡村”这一空间概念,并将乡村重新概念化为一个混杂的网络空间。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聚焦关系取向乡村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脉络:
要借助互联网的优点,把电视台节目的传播做到最大化,全面提高节目的传播度,使节目的受众群体不再是电视机前的用户,更要让互联网用户也能够及时获取电视节目中的信息,从而提高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扩宽受众群体。要加快节目的更新换代,发挥优势,打造节目品牌,立足眼前,放眼社会现象,结合当代形式,结合各个社交平台,例如微博、豆瓣、知乎等新媒体,在其中寻找大众接受并喜爱的节目题材,不能一味地选择抄袭优秀节目,获取流量,要做有想法、有创新、有责任感的新节目,为大众带来优良的电视节目的同时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形成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必然要求将乡村振兴重新置于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之中。全球化力量与乡村的交互将使乡村呈现出全新的地方性特质。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认为乡村既不是全球化的滞后者或被动反应者,也不是全球化力量的从属者或对抗者。相反,重塑乡村的全球化力量只有通过地方微观政治的协商、混杂、操作才能得以显现。因此,在开放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振兴究竟应该是更多的本土导向还是全球导向,究竟应当遵循边界封闭的原则还是边界开放的原则,这将是一个需要顶层设计着重回应的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根本性地将乡村空间视为一个永恒开放的生产过程,乡村才能够真正立足于与全球的各种关联之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应当倡导嵌入全球网络的“地点”新发展[22]。一方面,在乡村振兴中应当使人们看到全新的乡村地方性——它并不生成于特定的领域空间,却能够看到更大社会经济过程在地方层面的特殊型构,乡村振兴因此表现出宏观力量影响下的本地特殊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应当能够让乡村成为新的行动表征,提供一种离散的视角来窥见本地与世界的实践互构。
由图3可知,由于示例飞机最大飞行高度较低,其驾驶舱和客舱压差峰值较8000ft高度下主风挡破裂小。在决定是否在驾驶舱门上设置泄压板时,可选取两者中较严酷的压差峰值,与驾驶舱门结构承载能力进行比较。当压差峰值超过驾驶舱门结构压差承载限值时,则需在驾驶舱门上加装泄压板。
第一,从乡村空间的构成来看,关系取向理论主要依赖两条思考进路来完成本体论上的理论转型:一条思考进路是将乡村视为由要素流动和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结构,关注空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关系理论认为乡村的物理空间被多重关系所穿透,乡村本身的地理空间也不断地处于变动之中。乡村因此具有离散而不是聚合的结构特点[15]。另一条思考进路是将乡村视为一种关系实践的空间过程,认为乡村是在特定时空中被有意图建构的产物,在权力关系变化中的乡村因此具有永恒的流动性而非稳定性。在这里,乡村同时在空间结构和空间过程的双重意义上具有开放和流动的属性。
止水位置自上而下分别设在∅244.5 mm技术套管与∅139.7 mm生产套管之间的环状间隙,取水段上部,具体深度为1559.34~1575.08 m。
第二,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强调乡村空间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态、预先给定的本质,更加强调乡村空间所呈现的开放、连续、动态特征。关系性的乡村开始识别乡村空间的交互性,同时它将乡村发展视为各主体之间共同建构的空间生产过程和实践。关系取向理论将乡村发展视为一个乡村空间变迁的持续过程[16],关系本身的建构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心。一方面,乡村发展必须纳入日常社会生活和地方情境加以考察。另一方面,乡村空间依赖于社会生产模式,即便是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也必须同时关注其时刻嵌入社会文化的交换。
第三,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在后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强调乡村发展的内在分化和差异。在不同的社会空间情境、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文化交换中,乡村性的生成和流变都具有差异的表现。乡村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一个分化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增加复杂性和异质网络的空间。作为意识形态或知识的乡村话语同样会对乡村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话语生产进行基础性检视。为此,如何能够更好地理解乡村发展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成为重要的理论议题。Cloke和Murdoch分别发展了“混杂理论”(Hybridized Theory)[17]和“理论的多元主义”(Theoretical Pluralism)[18]来综合乡村研究中的诸多理论资源并调和其中的理论关联,从而以多维的视角来重新阐述乡村空间的复杂性。
三、关系取向的乡村振兴:实践脉络与行动导向
然而,与实体主义乡村观形成张力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日益显现出开放性和流动性。从乡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与外界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乡村社会在人口转型、社会异质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城乡趋同使得传统地域社会的构成要素不断扩散,共同性不断丧失,城与乡、城市生活方式与农村生活方式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空间中日益增加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将至少在三重意义上改变着传统乡村的空间组织形式和生活样态。第一,开放性和流动性突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带来了地域因素和超地域因素的交汇。全球化和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乡村的社会构成方式。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外部参与度和依存度增加,领域式的封闭性治理在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方面的效能将集中面临挑战。第二,开放性和流动性将集中改变农民及其所在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个人生活显现出“脱域化”[注] 吉登斯用“脱域”来形容人们走出原先生活的地域而进入流动的状态。参见Giddens A,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Polity Press, 1992. 和个体化的趋势。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经验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农民群体能够在流动社会中获得超越于当下和当地的经验,极大地解除了人与特定物理地点之间的依附和捆绑关系[8]。第三,开放性和流动性将在根本上改变乡村空间的组织形式,带来了一种总体性的超社会性。“网络”[注] 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提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来临。他认为当前的社会由不同的网络形式所组成,比如商业网络、沟通网络、消费网络、亲属网络、网络国家(例如欧盟)、草根网络等等。 正在成为社会构成的新形式[9],地域社会开始被多重流动网络构成的复杂设置所替代。人们可以通过流动而不是稳定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注] 新近的研究认为认同产生于持续的情景变化之中,而不是产生于一个静态的物理结构。在传统的理解中,流动性往往被描述为形成认同感的对立面,却忽视了认同的流动形式。 。
(一)城乡关系的空间调整与重塑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城乡关系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资源和权力分配上形成的非对称结构以及城乡公共服务的错位供给[19]。在理论上,我们对乡村的定义和想象一开始就嵌入关系的视角,相对于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而提出。然而,传统比对性和二分性的乡村发展观无论对于理解乡村还是指导城乡社会发展都有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关系取向为乡村发展理论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分析工具来提醒我们识别城乡空间之间的多元网络形式以及城乡空间结构交互而形成的新空间[20]。伴随着农村和城市之间持续的空间交互(行动者、商业、贸易、文化、日常生活实践的对流),城乡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并且型构出全新的社会空间形式。在实践上,它也启发我们应当将乡村振兴重新纳入城乡交互的区域发展框架中。在这里,城乡交互并不意味着原有边界性的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之间的互动,而是指二者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新空间,它具有全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并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其中可能包含了新的合作,也可能包含了新的冲突。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在促动城乡关系的调整和重塑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兼顾地域性治理和流动性治理的能力[21]。对于未来的乡村发展而言,基于地点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与关系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相结合。乡村振兴因此需要一个更加连贯和合作性的关系治理框架,比如探索跨行政管辖范围的合作治理、在更大空间实现城乡互动的区域治理等等。当然,这离不开更高层面的整体协调与合作规划。
(二)本地—全球关系的空间调整与重塑
在文化形成过程中,楚国人首先吸收了苗族文化,融合了百越文化、夷濮文化,巴蜀文化和氐羌文化,又汲取了中原文化的养分,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5]。楚国的文化心理表现出崇火尚凤、亲鬼好巫,追求浪漫的文化特征,与对神龙崇拜,对鬼神敬而远之的中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接近鬼神,崇拜神灵,尊敬巫术的楚国个性文化,却包含对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理性思考。因此,在楚文化中,不仅追求长生,而且还有僻静境界的想象力,强烈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豪感,也有文化的开放和宽容。既是“信巫鬼,重淫祀”之乡,又是中国道家文化孕育与生存之地。表现出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而楚辞神话细腻地表现出这种文化特征。
不同融资渠道分别可以用于建设、运营、规划,且彼此不能混同。对于特定融资渠道用于再生水项目的融资份额一般也规定上限。对于基金的资金回收和持续运行实行谨慎的管理,对于各类融资适用于再生水项目的条件、申请程序等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三)人类—自然—社会关系的空间调整与重塑
乡村空间的形成来自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体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混杂装载。伴随着技术、生态有机主义的倡导,在全球环境变化以及食品安全考量下的乡村振兴必须首先来重新思考人类行动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中,乡村振兴的行动重点首先是在时空中重构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紧密关联和良性互动。乡村振兴必须考虑乡村发展的产业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涉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结构性调整。同时,乡村振兴也必然包含人类行为与其所嵌入的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调整。流动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背景来帮助我们看到关系性的乡村是如何通过个人的流动性来塑造的,而个人的流动性恰恰又是不受乡村空间束缚的。乡村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归属于“人”,乡村发展只有关涉人的日常生活,乡村的外显发展才能够与内生发展真正联系起来。
乡村振兴旨在为未来乡村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23],“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无法脱离关系取向的理论关照及其实践指引。正是在关系取向乡村发展观的影响下,乡村振兴具有与实体主义理论倡导较为不同的实践导向:乡村发展应当突破行政性的地域边界,不应该割裂地来看待乡村,而是需要将其放在更大的区域发展框架中加以思考和推进。乡村发展必须使区域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聚合成为可能,以区域来开展社会动员,驱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应当同时关注乡村所具有的地域性的本质和关系性的本质,政策本身既需要嵌入特定的地点,也需要使地点与地点之间的政策流动性成为可能。近年来,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策略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倡导中,同样能够给予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启示:比如在乡村发展上倡导网络式发展的行动策略[24],将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与自上而下的规划发展相结合,将乡村发展的横向网络与纵向网络相结合。为此,乡村振兴应当着力于通过关系机制来促动合作性的行动逻辑而不是传统科层和地域治理的行动逻辑[25];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新乡村空间”的规划,建立在对传统空间概念的重新理解和思考上,以关系性的理解重新认识乡村“空间”与“地点”[26]。传统乡村规划者习惯与传统的空间概念打交道,尤其是带有明晰边界的空间(国家、区域、地方)。在当代社会,“新乡村空间”的规划和塑造在实践中带来了新的乡村图景,其更多地关注多元行动者参与下的乡村空间的共同建构以及乡村边界的开放性。乡村规划的重点从可视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样态转向了非可视化的多元网络交互关系。
四、简短的讨论与总结:我们应当如何想象并实践“乡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的乡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式转型,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中国市场化、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农民市民化战略的快速推进,乡村在城镇化的影响下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转型。这不仅表现在乡村形态上的变化,也表现在乡村人口结构、经济生产方式和村民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社会交往、利益关联以及公共生活村民上的全面转变。二是从当前乡村发展现状而言,流动性的剧增已经构成了中国乡村研究无法忽视和逃避的社会现实。当代乡村社会变得越来越存在于流动所带来的空间扩张中,并且突出地表现在内在的多元性和外在的关联性。中国乡村的巨变及其所带来的转型问题在现实层面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基本背景和出发点,也在理论上促使我们重新想象并描绘一套人们如何在乡村中生活以及应当在怎么样的乡村中生活的图景。
乡村大转型同样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去农业化”“去乡村化”以及乡村社会再分层的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全球乡村的人口状况和经济社会特征。在过去十年的乡村发展研究中,如何引导乡村的再生发展成为乡村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乡村社会学开始在新的理论范式中重新描写乡村性的新特征,并带来有关乡村性的新话语。现代主义者宣称全球的“去农村化”与逆城市化之间的张力使越来越多的乡村研究者寻找并重新定义“乡村性”。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同时发生在一个历史时间段中。尽管城市化强有力地冲击着乡村,乡村仍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背景下顽强存留。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认为现代化并不会彻底消解农村。相反,在一些国家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一些农村社区实现了快速的人口和经济发展。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当代社会必须要在深远、广阔以及多元的发展趋势中重新“寻找乡村”。
如何引导乡村的再生发展是困扰乡村研究当前最重要的实践难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努力通过改革去回应乡村所遭遇的挑战,但在实现乡村永续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显然始终面临阻碍。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以往对于乡村的基本知识想象可能成为我们实践最大的阻碍。本文认为正是在“乡村”的传统假定与当前发展现实之间的张力之间,更需要一系列的知识追问: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想象并理解乡村?对此我们既需要对以往的乡村观进行批判性的检视,也同时需要思考新的概念和理论视角。
相较于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实体主义假定,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避免了“地域”成为固化的治理容器,赋予了实践性和主体间性,并且在多元视角和建构视角中看待乡村及其发展。乡村振兴的“乡村”也应当突破封闭的地域空间载体,被纳入能够促动空间资源的合作治理以及各要素有序流动的区域治理网络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地点乡村能够嵌入更大的关系网络的统筹得以发展。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更加强调一种“去科层化”的空间关系,强调乡村发展通过空间关系的调整来促动社会包容和社会整合。关系取向的乡村振兴因此倡导政府的角色从刚性的边界控制者转向治理网络的组织者和治理实践的推动者,通过合作治理的模式来推动多元社会资本的利用以及开放共治格局的产生来活跃乡村网络。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重构一种关系型的乡村治理体系,其对象不再简单是“人”或“物”,而是涉及城与乡、本地与全球、人类活动与自然社会系统等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空间关系。
然而,关于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及其实践导向,仍有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反思和讨论的问题:首先,关系取向中的“关系”本身仍然是充满争议的。乡村发展中强调的“关系”究竟是现实的关系还是非现实的关系,前者是行动者或制度在客观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联,而后者包括了一系列主观、情感、心理、认知、文化的非现实关联。乡村振兴需要积极建构的究竟是客观关系还是主观关系?其次,乡村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进程。尽管乡村发展根植于特定的边界地点,然而乡村发展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去面对当前乡村所嵌入的一系列关系性进程。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因此必然要求在乡村发展中需要结合地域治理和跨地域治理,在相关政策上也必然要求整合政策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政治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以及社会心理要素的系统配合。这在实践上需要跨越行政区域来促动乡村发展,当然这将集中面临结构和文化上的挑战。另外需要思考的实践问题是,如何超越行政权力的边界限制而扩展乡村治理的能动空间?这又需要有多层次、弹性的政策和治理安排。再次,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在强调不同空间尺度之间关系网络的同时,可能弱化乡村发展中“人”本身在理论中的重要性。在理论和实践中需要同时回答的问题是,乡村发展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主体?需要在城乡关系、本地—全球、人类行为—自然社会环境的各种关系中塑造什么样的“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自身独特的阶段性特点,也需要立足乡村自身发展的现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总体上是基于乡村人口大量外移以及老龄化相对突出的特点上[27],如何使这部分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同样是实践上的难点。最后,关系取向的乡村发展观没有在关系的方向和力量的配置上予以更多的讨论。乡村振兴究竟是要走依靠内生资源、地方行动者带动的自下而上的路径,还是要走依靠外部资源、国家和区域行动者带动的自上而下的路径?这两者之间又如何在村一级层面得到互补与合作?乡村振兴又如何实现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的结合?这些无疑都是待回答的难题。
参考文献:
[1]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J].中国史研究, 2006(2):85-100.
[2]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J].历史研究,2007(2):78-87.
[3]文军,吴越菲. 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7(4):22-45.
[4]Ray C.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U[M]// 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The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278-291.
[5]Niska M, Vesala H T, Vesala K N. The Use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Rural Development? Two Readings of Rural Business Owners’ Values[J].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6(6): 581-595.
[6]Brown D L, Shucksmith M. Reconsidering Territorial Governance to Account for Enhanced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in America[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2017(1):282-301.
[7]Desmond M. Relational Ethnography[J]. Theory and Society,2014(5):547-579.
[8]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3):207-230.
[9]Larsen J, Urry J, Axhausen K. Mobilities, Networks, Geographies[M]. Aldershot: Ashgate, 2006.
[10]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2000.
[11]Massey D. The Political Challenge of Relational Space: Introduction to the Vega Symposium[J]. Geografiska Annaler, 2004(1): 3-78.
[12]Massey D. For Space[M]. Sage: London, 2005.
[13]Jones M. Limits to Thinking Space Relationall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in Context, 2010 (3): 243-255.
[14]Woods M. Rural[M]. Routledge, Abingdon, 2011.
[15]Hedin K, Clark E, Lundholm E, et al. Neoliberalization of Housing in Sweden: Gentrification, Filtering, and Social Polarization[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2):443-463.
[16]Katz C. On the Grounds of Globalization: a Topography for Feminist Political Engagement[J].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01(4):1213-1234.
[17]Cloke P, Goodwin M. Conceptualizing Countryside Change: from Post-Fordism to Rural Structured Coherenc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2 (3): 321-336.
[18]Murdoch J. Networks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4): 407-419.
[19]文军,吴晓凯.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错位及其反思——基于重庆市5村的调查[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2.
[20]Heley J, Jones L. Relational Rurals: Some Thoughts on Relating Things and Theory in Rural Stud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3):208-217.
[21]吴越菲. 地域性治理还是流动性治理:城市社会治理的论争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51-60.
[22]Woods M. 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4):485-507.
[23]林聚任,梁亮,刘佳.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文明建设——基于山东省的调查[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58-167.
[24]Shucksmith M. Future Direc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R]. Dunfermline UK: Carnegie UK Trust, 2012.
[25]Enrico G. The Rescaling of Governance in Europe: New Spatial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e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6(7): 881-904.
[26]Healey P. Urban Complexity and Spatial Strategies: Towards a Relational Planning for Our Times[M]. London: Routledge, 2007.
[27]贺雪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11-116.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2019)04-0028-09
收稿日期: 2019-03-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业转移人口的乡城流动性及其分类治理研究”(18CSH01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大都市郊区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及其流动分化研究”(2017ESH008);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晨光计划”(17CG22)
作者简介: 吴越菲,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李凌)
标签:乡村发展论文; 实体主义论文; 关系转向论文; 实践脉络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论文; 社会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