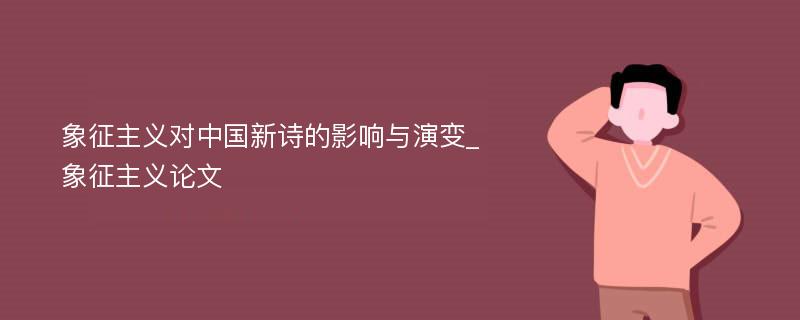
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中国论文,象征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0)02—0095—05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大旗挥引下,在创作的思想、内容、文体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世界各种新潮派别,新鲜观念纷纷涌入我国,其中,尤以诗歌的流派异常活跃,诸如:唯美派、未来派、唯人生派、象征派等等。这些流派被我国不同人生态度、不同艺术追求、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审美标准的诗人所吸收并消化,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与影响。新诗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它在各个历史阶段,合着时代的节拍,表达出不同的音调和心声,闻一多先生说,“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1]可以说, 新诗的各种潮流和派别是构成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新诗在外来流派的诸种影响中,受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尤为重大(当然并不排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主流作用),这已经在理论界形成共识,“五四”时期《新潮》杂志的编者罗家伦曾撰文认为:“《新青年》上有些新诗就是采用西洋Symbolism(象征)的方法写成的。”[2]源于美国爱伦坡、始于法国的波德莱尔和奈瓦尔的象征主义, 很快被衍化为19世纪末法国文学艺术的主潮,继而以强劲的势头辐射欧美,波及全球。从艺术的角度考察,象征主义反映的是人类借助于具体可感的现象世界,探索无限而超越本质世界的思维能力,是人类主观认知客观的基本思维模式,它注重文本意蕴传达的朦胧性、暗示性和隐藏性,强调借助象征意象以及“客观对应物”来间接表现作者意旨,这些都为20世纪的诗学开辟了一条使文学审美内涵进一步向复杂化与丰富性拓进的新的艺术通道。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应该是“五四”革命落潮之后,这时期不仅有大批西方象征主义名家名品以及一些相关的文艺理论被大量译介过来,而且国内许多名家好手、青年诗人都纷纷写出象征主义诗歌,即使思想界的先驱鲁迅也有“荷戟独彷徨”的心境,郭沫若在壮阔飞动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之后,写出黯淡的《星空》,认为自己是一个“受了伤的勇士”,“一只带了箭的雁鹅”,这种情况下,新诗就自然由浪漫主义的反抗吼声转为颓废感伤的情调,一部分失望苦闷的青年,从歌吟时代反叛传统,转而浅斟低吟挖掘自己。饶孟侃曾批评说:这些诗人们“硬是把个人片面的直觉当作真实的情绪,用一种不自然的方法表现出来,这种假的或不自然的情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感伤主义”,“差不多现在写新诗的人没有一个没有沾染着一种感伤的余味”[3],这主要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许多青年精神上的失落与被称作“寂寞荒街上的沉思者”与象征主义诗人们的神秘象征世界“交感相融”[4]。
使象征主义在中国真正扎根的第一人是李金发,而他所代表的象征主义新诗被朱自清先生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的“一支异军”。李金发在留学法国时是学习雕塑艺术的,后来他迷上了波德莱尔的诗,西方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这份精神遗产,成了他孜孜追求的生活和创作的美学准则,于是他模仿法国象征派艺术方法,来表达自己颓唐的感喟和幻美的追求,青春的热力和异国的情调,他的诗才被唤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连续写了《微雨》、《为幸福而歌》和《食客与凶年》三本诗集,他在遥远的海外将这些诗集寄给祖国,它们很快出版了。这些被称为“别开生面”的诗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由他开始,诞生不久的新诗,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主流中,才开始出现了一股象征主义潮流。李金发在审美追求上与波德莱尔相一致,在思想倾向上,主要抒发与现实对立的、非理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苦闷与要求;在艺术手法上,他较全面地对法国象征主义艺术进行移植,强调以象征、暗示、联想、幻想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李金发在《自挽》一诗中,表白出自己是“爱秋梦与爱美女之诗人”,这也可以笼统地看作是他对于诗歌内容追求的主要倾向和特征:歌唱人生和命运的悲哀;歌吟死亡和梦幻;抒写爱情的欢乐和失恋的痛苦;描绘自然的景色和感受。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李金发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不过,他的诗意象之间跨度和跳跃距离较大,加之披上一层神秘色彩,用语文白夹杂,读起来比较难懂,因此他得到了一个“诗怪”的称号。
二
一个流派有它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它作风相近的诗人群,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主义也一样,它虽然没有一个以共同的杂志为中心的诗人群,与他诗风相近的诗人却为数不少,如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人就是,他们被称为“创造社最后送出的三位诗人”,作风上更近于象征主义,稍后蓬子以及胡也频早期的诗作也明显带着象征主义影响的特征,蒲风在他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中,曾列表归纳了象征主义诗人,除了上述诗人外,还有戴望舒、施蛰存、梁宗岱、冯至等人,这种罗列虽然有不科学的地方,但蒲风的意图毕竟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在20年代的诗坛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象征主义创作的潮流。
王独清接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既表现于抒情的格调上,也表现在语言艺术的追求上。他提倡写“纯粹的诗”,要“努力于艺术的完成,以做个唯美的诗人”,他还说:“要是可以不管文学史上的年代与派别是以个人的爱好而定过去诗人底价值时,那我在法国所有的一切诗人中,最爱四位诗人作品:第一是 Lamartine,第二是 Verlaine,第三是Rimbaud,第四是Lafargue。”[5]他认为拉马丁表现的是“情”,魏尔伦所表现的是“音”,兰波所表现的是“色”,拉佛格所表现的是“力”,由此他认为:他理想中最完美的“诗”便可用一种公式表示:
(情+力)+(音+色)=诗[5]
王独清对于所谓“纯诗”的追求,带有浓厚的唯美主义色彩,在思想感情上如他后来说的:“我过去的倾向是经过浪漫蒂克而转成Decadent(颓废)的,不消说,我过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与颓唐的氛围里面。”[6] 浮浅的浪漫情调和颓废色彩成了他诗歌泛滥的主调,过分的虚无和感伤减弱了他诗的抒情意义,即使从艺术技巧上看,他对文学语言的追求也显得轻浮与雕琢,而缺少现实与质朴的特色。一句话,离开比较充实的内容去追求技巧形式的完美,所产生的果实是不会丰硕的。
冯乃超接触法国象征主义作品时,正在日本帝大念书,后来,他带着象征主义诗风加入了象征主义的行列,并出版了诗集《红纱灯》,爱情失意的痛楚和人生苦恼的哀怨,几乎成了冯乃超这本诗集的一个不变的格调,诗人在代表他思想情绪的序曲里,用最凄婉感伤的调子唱出自己的心曲。冯乃超留日时曾学过美学和美术史,艺术趣味的深厚素养,使得他对诗歌语言的表达非常注重色彩感,同时,他的这种色彩感又有别于李金发,他在注重观念联络的新奇,用形象暗示情调的同时,更加追求诗歌语言音节的美感和色彩的丰富,正如朱自清所说:“冯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7]
穆木天的诗歌追求音乐美,强调诗歌应具有音乐与情绪律动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同时又应该是空间万有的种种律动在人心中的反映,是内在生活的真实和象征。他在1926年发表的《谭诗》一文,是比较早而且比较全面地探讨象征主义理论的文章,他把“纯诗”表述为“纯粹的诗歌”,主张诗歌要远离社会功利性而表现月光的波动与心灵的交响,在创作中穆木天也实践了这种美学主张。后来王独清又写了《再谭诗》,他们的探求为新诗艺术美的建设作了尝试性的开拓。此外,象征主义还有深受李金发直接影响的诗人胡也频、石民等,和直接吸取法国象征主义的蓬子、戴望舒等人。
象征主义对我国新诗的影响,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主要是它除了歌吟梦幻、死亡、仙乡、颓唐之外,一些诗人还表现出对古代文明的怀想和对近代文明的诅咒,特别是稍后一些诗人吸收象征主义而又发展了象征主义,这应该看作是对象征主义诗歌社会批判性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即使是在思想影响上,象征主义诗歌所给予中国青年诗人的乳汁,也不完全是“世纪末的毒液”,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的事实。
三
象征主义带给了中国诗人深层表现的艺术方式,同时,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被引入,也照亮和选择了中国古典诗学与之适当的结合,为中国诗歌带来了崭新的艺术视野,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等人对象征主义诗艺的探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戴望舒从1922年一开始写诗,便关注着李金发的新诗路,同时他直接读了魏尔伦的作品,从中找到了对抗直说的浪漫主义适中的艺术尺度,并在移植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诗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他一出现,在诗坛上的表现就非同凡响,《雨巷》一诗,初次显示了诗人的艺术功力和才能,使其得到了“雨巷诗人”的称号。稍后不久,他又成了新诗另一流派——“现代诗派”的领袖。从20年代中期到末叶,戴望舒的出现,他对诗歌追求从象征主义诗艺发展的内部进程来说,对于李金发过于晦涩的诗风以及明显的欧化倾向应该看作是一种纠正,在具体实践中,他通过融合象征主义与古典诗歌意境的方式,在30年代的作品中,力图勾勒出寄情山水的闲逸图,杜衡称他的诗是“象征主义的形式,古典主义的内容”。其实,戴望舒本人的价值意义也正在这里,他把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进行融合,并从中感悟出中西方具有普遍美学价值的东西,找到古典诗歌意境与西方象征主义以及意象派的亲合性,并将它推向世界文学领域,看来,他被公认为现代诗派的领袖并非偶然。
卞之琳的诗讲求“戏剧性处境”,同时追求哲理的感情与升华,与戴望舒相比,卞应该是一个理智型的诗人,袁可嘉认为他的诗具有“融古化欧,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卞之琳主要受后期象征主义瓦雷里、里尔克、艾略特等人影响,他在回顾自己创作中说“喜爱提炼”、“期待升华”,可见,诗人“倾向于对普通人生世相中升华出带有普遍哲理性内蕴”[8],尽管“五四”早期白话诗,特别是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白话诗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意象和象征的表述手段来传达哲理的意蕴,但未免有些直观浅显之嫌,只有到了卞之琳这里,抽象与哲理的升华才较为圆满地进行了有机组合,单就现代哲理抒情诗而言,卞之琳的作用极其巨大。
冯至在40年代则专注于物象的沉思,代表作《十四行集》可以说代表了他一个沉思的时代,他也是接受了后期象征主义,深受后期象征主义大师里尔克的影响,如里尔克从普遍的事物中领悟到充沛的诗性一样,冯至带着重新发现的惊奇去观照常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事物,这种“新的发现”,既是他对大千世界生命的追问,又是诗人哲理的感悟。李广田称冯至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9]。冯至“新的发现”既是对诗人的发现又是对哲理的发现,在日常印象中,诗人构建了有超越意蕴的哲理空间,唐湜曾对冯至与里尔克的诗在艺术上作了一番比较,“如果里尔克的沉思是一种隐喻,主客观对等的互相化入,浑然为一,那么冯至的诗还是有明喻,主客观非对等的比拟”[7], 这段论述可以说是对冯至诗歌艺术的恰当概述。
相对来说穆旦却要复杂得多,他的诗表现了超凡的营造性和想象力,并在象征与意象中贯注了强大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索,他的诗,甚而可以看作是40年代力图把握历史与超越人生的“史诗”意向。正如叶芝所说,“诗人应有哲学,但不应表现哲学”,“穆旦的诗歌总体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思辨色彩,其诗的背后,总潜隐着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支撑和对个体生命的体验与赞美,并显示出对复杂历史与现实图景的负载与超越”,“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个体感性生命存在的逼视”[10],以及试图把握这种历史秩序的意向本身。
四
象征主义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摸索出了一条相对艰难的纯诗之路,他们不仅给中国新诗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新风,而且他们将独特的、中国化的意象融入象征主义诗歌中,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作了贡献,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意象艺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当然,从主客观两极角度进行考察,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对意象的选择既是一种必需,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说象征主义的基石是意象的话,那么,意象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就连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等也对中国多姿多彩的象征艺术赞不绝口。李金发虽长期生活在国外,但他对中国岭南一带的民间歌谣一直钟爱不已,他还曾亲自采编出《岭南情歌》。王独清、穆木天自幼饱读诗书自不必说。可见,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并不是对传统进行了全盘否定,而是在对象征主义诗歌偏爱中,依然贯注着民族审美心态与传统的文化情结,在李金发等人的诗作中,其许多诗歌中的意象就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只不过他们诗中的意象基本上都是灰冷阴暗的,寒夜、冷月、死亡、坟墓等在他们的诗歌中比比皆是。中国象征主义诗人对阴冷意象的采用直接效仿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曾宣称:“‘欢娱’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则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11]不过,虽同为阴冷意象,中、德象征主义诗歌传递的仍然是各自的民族文化思想与人文精神,德国的象征主义诗人的颓废是对生存命运的关怀,对社会本身的批判。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远离故土,国内时局的波诡云谲,揉合着他们人生的失意、爱情的苦闷。他们的困惑与迷惘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忧患以及失意等仍是中国古典意象化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阴冷的意象超出了传统诗歌的美学范畴,但它毕竟为传统的中国诗学拓宽了艺术审美上的视野。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国初期的象征主义诗歌突破了传统诗歌中意象组合的程式化,他们在意象的组合上不追求形式的“关联”,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都自有相适相联相互契合的内在规定性,因此,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同来”[12]。他们也会在找到意与象的联系间找到一种常人没有的征服快感,那种貌离而神合的意象,给人一种飘忽朦胧的感受,同时也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意象的跳跃突转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意象组合的重要特点,诗人们追踪着自我独特的感觉,将内心抽象的情绪外化为一个个鲜明可感的意象,并顺着情感的走向将诗组成有机的整体,如李金发的名诗《弃妇》,在意象的多层转换与跳跃中,意象之间的排列绝不是依据前因后果方式的直线思维,而是有纵贯交错的内在情绪,诗的意境也正是靠这种内在情绪获得丰富扩展的,还有李金发的《联之秋》、《夜之歌》等诗无不表现出这一特点。因而,意象的跳跃突转可以说是象征主义诗人用来提高诗语的密度与诗情浓度的一个重要手段。
综观现代新诗发展的历程,虽然象征主义在中国诗坛上的出现与成长稍迟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但它凭借多层次的美学功能与奇特的创作手法,丰富了我国新诗的审美内涵,在中国诗歌领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互渗透、融合,以至于现代新诗史上许多作家都借鉴并吸收象征主义艺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这里,它为我们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一条值得思索的方法论:科学地看待文学流派发展中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现象,那种把文学史上纷繁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单地归为主流与逆流的争斗未免有些保守化、公式化。规律的意义应该是使复杂的历史现象条理化、理论化,而不是把丰富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
收稿日期:1999—07—12
标签:象征主义论文; 李金发论文; 诗歌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戴望舒论文; 冯至论文; 卞之琳论文; 王独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