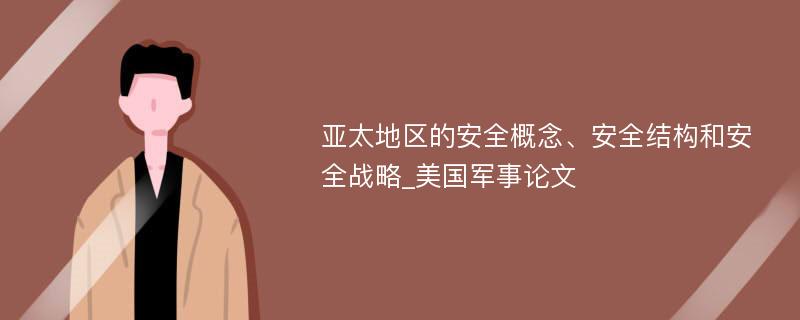
亚太地区安全观、安全结构和安全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战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安全问题是冷战结束以来太平洋两岸热烈讨论的话题。在关于冷战后亚太安全的形势、前景、机制、政策、战略等各种要素中,安全观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亚太安全各种理论、政策、战略的出发点。因为有什么样的安全观念,就决定着在该地区希望和促使形成什么样的安全结构或秩序,也就决定一国会奉行什么样的地区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七、八年来,太平洋两岸的一些人仍习惯于用冷战时期的观念和思维来看待和处理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问题,用旧的观念来解释新的现实,用过去的战略来规划未来。为了整个亚太地区现在和未来的安全与稳定,亚太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现在有必要努力探索地区安全新观念,实现安全观念的现代化,并以此认识和处理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问题。
五种安全观
无论是冷战后的今天,还是冷战时期,甚至本世纪以来,关于亚太地区安全主要有如下五种观念或思维:
(一)霸权稳定。这是一种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思维。这种观念认为整个地区置于一个强权统治之下才最安全。历时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一就是这种“霸权稳定”观。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亚洲,搞日本统治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基础之一也是这种观念。二战后,美国长期奉行独霸亚洲的战略,把苏联及中国等视为对美地区霸权的威胁,加以孤立和遏制。
70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各国实力的增强,地区格局向多极化倾向发展,霸权主义处在衰退过程中。但是,在地区安全战略思想中,“霸权稳定”观仍在一定程度上顽固存在,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冷战后的今天,美国一方面对独霸亚洲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放弃地区霸权心态和战略目标。亚太许多人士也仍然担心日本一些势力不能正视历史,不放弃统治亚洲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战略。太平洋两岸还有一些人散布“中国威胁论”,硬说中国有独霸亚洲的“地区野心”。可见,“霸权稳定”观尽管古老和不合时宜,但仍然残存在一些国家的战略思想和一些人的思维习惯之中。
(二)同盟安全。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的现实中,即使追求“霸权稳定”的国家也时时感到单靠一国的力量无法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同盟合霸”或“主从合霸”就成为不得以而求其次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冷战后,美国称霸亚洲战略日益面临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大的挑战。在美国内,即使是在近几年经济较好的情况下,要大幅度地增加军费开支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能维持每年2600亿美元的规模就已经不错了。美国内经济的压力和反对过多承担海外责任的“孤立主义”压力将是美称霸亚洲的永恒障碍。在亚洲,日本、韩国、东盟与中、印等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使各国人民越来越不愿接受超级大国对亚太事务的统治,反对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
在这种国内外压力下,美国虽仍没有完全放弃称霸亚洲的战略目标,但越来越试图通过美主导下的双边联盟弥补独霸能力的不足。这种同盟安全并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它的双边性质,也不是确保同盟国之间的安全,而是通过联盟达到合霸或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的目的。
(三)均势稳定。地区霸权不可取,因为大多数国家不情愿接受霸权;同盟安全满足了同盟双方的利益和要求,但同盟往往以针对第三方为存在的条件,必然造成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反对,并有可能导致与之对立的同盟的出现,对整个地区安全也是不利的。于是,尽管流行多年的“均势理论”不再那么时兴,但太平洋两岸仍有不少人认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力量之间的均势。不管现在该地区力量格局是三极、四极,还是五极,力量格局的态势可以改变,但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意义没有也不会改变。
(四)集体安全。集体安全观认为霸权、同盟、均势都是旧的观念,在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今天都是过时的东西。用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方法都无法达成地区安全的目的。安全是所有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应当采取集体的形式来解决共同的安全问题。这种集体安全观不包括两、三个国家间的安全安排,它主张地区内多数国家或所有国家参加的、有一定约束力的多边安全结构。集体安全观的信奉者把联合国看作是最具全球性的集体安全形式,而北约则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地区集体安全组织。
(五)合作安全。合作安全同集体安全的区别是前者不拘泥于形式,而主要通过地区各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实现各国的安全利益,并达成地区安全的目的;后者则要求有较为固定的形式和有约束力的机制。合作安全也赞成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但认为其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相对固定的,也可以是松散的。它重视安全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
安全观和地区安全结构
上述五种安全观,是亚太地区、太平洋两岸关于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思维。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亚太地区各种政治势力正进行各种努力,以期建立符合各自安全观念的冷战后地区安全新秩序或新的结构。
(一)霸权体系。在这一框架内,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主要依靠一国的力量,其它力量和形式的存在只是对霸权力量的支持和补充。这种结构“需要”和允许某一国家充当整个地区安全保护者或维护者。一国认为其有权为了地区安全的名义对地区各国间纷争、甚至各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包括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二)双边同盟结构。这种结构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建筑在一两个或几个军事同盟的基础上,把这一两个军事同盟作为地区安全的保护神。此种同盟不但有保护同盟各方安全的义务,同时被赋予维护整个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或功能。在这种结构中,双边军事同盟成为地区安全框架的核心,其它安全合作形式仅是对其双边同盟的配合和补充。这种把一两个军事同盟作为整个地区安全框架和保证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双霸结构”或“合霸结构”。
(三)中美日(俄)大国均势结构。“均势结构”的信奉者认识到“霸权结构”和“同盟结构”的排他性及因而造成的对抗性和不稳定性,因此认为均势结构最具稳定性和合理性。“均势结构”可使亚太地区各种力量之间,特别是该地区三、四个大国之间维持一种战略力量的平衡,靠这种战略平衡来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只要大国之间存在力量和战略关系的大体平衡,整个地区就不会有大的危险。这种结构既对超级大国各自进行牵制,也对其它力量进行制约,还通过大国间的平衡促使中小国家无法采取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四)北约模式和欧安会模式。集体安全结构的信奉者认为霸权、同盟、大国均势等安全框架都是依赖少数国家,因而是脆弱的和消极的。真正积极的、靠得住的还是集体安全结构。“亚洲北约”结构会成为能真正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机制。如这种有约束力的集体安全形式不会在近期内为亚太各国所接受,那么,一个类似欧安会式的较为松散的泛地区的安全组织形式应是可取的。“欧安会模式”的追逐者希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成为这样的亚太安全泛地区组织。“北约模式”同“欧安会模式”的区别是:前者试图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解决地区安全问题,而后者的主要作用或功能是对一些安全问题进行多边讨论,通过有关决议,以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并为有关行动提供法理依据。
(五)安全合作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亚太地区出现不同于历史上的安全合作机制。这种机制还在探索中,现在还难以说清楚它究竟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结构。目前亚太地区出现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代表了这一探索。总的趋向是通过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间平等的对话,达到增加相互理解和信任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目的。
安全观和地区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太平洋两岸不少国家以各种安全观为基础和出发点,以建立符合自己安全观的地区安全结构为目标,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亚太安全战略。
(一)“领导战略”。这是美国政府一直奉行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在亚太,这一战略的内容和目的就是要通过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式的“交往”及其存在,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和其它方面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①a]“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既是美亚太安全战略的目标,也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在美国看来,亚太地区要保持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和平与稳定”才算真正的安全与稳定。“民主国家间不打仗”,只有西方式民主,才会有真正的安全与稳定。[②a]而要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就一定要有人出面领导,在亚太乃至全世界,唯有美国“有意志、也有能力”领导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因此,领导作用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义不容辞的责任”。[①b]
既然美国以亚太地区“领导”为己任,它就感到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力“保护亚洲”。既要保护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也要管东北亚(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各区域的安全事务,甚至还要管台湾海峡等其他国家内部的事务。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美国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经济和军事能力,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很多问题上起某些主要作用也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现实。但美“领导战略”造成的问题,是美国自己往往不能表明其“领导”地位和作用与地区霸权、地区统治究竟有什么区别。如果以超级大国自居,凭借自己的实力优势,习惯于对别国发号施令,要求别的国家在内外事务中按美国的意志、标准和条件行事,否则就对别国进行制裁、威胁甚至动用武力。这样的“领导”和霸权统治毫无区别。
美国人往往沾沾自喜地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是得到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欢迎和支持的。事实并非如此。否则为什么菲律宾几年前把美国兵从克拉克和苏比克赶走,为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拒绝接受美军的“战略物资储备”,为什么日本和韩国人民不断要求美国撤走驻在他们国土上的美军基地?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起建设性作用,最好还是放弃霸权、“领导”心态和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学会同亚太各国平等合作。
(二)“双锚战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相互依赖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安全变得愈益复杂和多样化,美国的“领导战略”越来越面临挑战。因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实际上也逐步演变并呈多面孔。“双锚战略”就是其一。它是对“领导战略”的支持,其内容是通过加强美日、美澳等双边军事联盟,形成美亚太安全战略的北南两个“锚”,以支撑美国的亚太“领导战略”。[②b]美国还在寻求建立第三个、第四个和更多的“锚”。美国这种针对具体国家的双边军事安排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它造成其它国家的更不安全,最终也将损害包括美日在内的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三)“均势战略”。东南亚和亚太地区有的国家如新加坡的一些政治家、战略家始终相信均势原则没有过时,仍是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③b]太平洋彼岸也有些美国人士如基辛格博士持有这样的战略思想和主张。[④b]他们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取决于美、中、日三国间的均势。他们主张三大国应当维持他们之间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的平衡,防止出现其中两方结盟同第三方对抗的战略态势,因那样必然造成大国间的对抗,造成整个地区都要受大国对抗的影响,因而使地区安全与稳定难以维持。还有些人士认为俄罗斯也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力量之一,亚太大国之间的力量均势也应包括俄罗斯的力量和影响。
(四)东盟ARF战略。自从“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以来,它就成为亚太地区唯一一个各国政府间讨论安全问题的对话机构。东盟建立该论坛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参加的机构,以推动关于地区安全的对话与合作,进而达到在亚太地区增加了解和信任,减少误解,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短短三年多来,“东盟地区论坛”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它几乎包括了该地区所有的国家,现暂不是正式成员的国家也在积极申请。该论坛对地区安全形势和各国的政策、建立信任措施、海上抢险和救助等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和探索,增进了各国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了解和信任。
中国的亚太安全观和地区安全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及地区多边合作进程的发展,中国同亚太各国一起积极探讨有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符合冷战后时代发展的新的安全观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地区安全战略。
(一)安全观念的发展和现代化。中国没有固守冷战时期留给世人的传统安全思维,而是通过同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和借鉴符合冷战后形势的安全观念和战略思想。中国支持和倡导综合安全、相互安全、同等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等有利于地区各国和整个地区安全的观念,反对地区霸权、强权政治、军事同盟等旧的和危害他人安全的冷战思维。中国以言行证明自己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同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中国主张在包括安全问题的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几个大国主导地区安全事务;根据事情的本身是非处理地区内大小国家的关系,不搞“大国均势游戏”那类东西。
(二)综合安全战略。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提高“综合国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后不久,[①c]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形成了“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其主要内容就是根据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各国发展战略思路,以及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和争霸的历史教训,认为安全问题并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解决安全问题,武器、军队越多不等于更安全,而是要通过和各国改善和发展政治、经贸关系,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三)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在综合安全、相互安全、同等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等新的安全观的基础上和综合安全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冷战后几年来,中国主要是通过与本地区和其它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实现增进自己和整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在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达成地区安全目标方面,中国同其他国家一起做出了突出的和实实在在的贡献。
在太平洋两岸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大谈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时候,中国在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中苏围绕边界领土的纠纷曾是两国关系和整个地区安全一大难题和危机,两国曾为此爆发过武装冲突并存在着全面战争的危险。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上少有的严重的安全问题,中苏及后来的中、俄、哈、塔、吉等国不是按旧的思维,突出各国间的矛盾,立足于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领土纠纷,而是从维护双边关系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冲突。在短短的几年中,中、俄、哈、塔、吉五国就基本解决了长达几百年的领土纠纷,并就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达成了协议。4月,江主席又前往俄罗斯,同俄、哈、塔、吉四国签署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议。中、俄、哈、塔、吉以实际行动,为地区以和平、合作手段解决领土纠纷并建立安全信任措施树立了榜样。
中印边界冲突也曾是两国和地区安全的一大问题,两国为此还发生过战争。但近年来,两国本着和平、合作的愿望,求同存异,在边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同意维持现状,并就在实际控制地区建立安全信任措施达成了协议。
在南海,尽管中国有充足的历史和法理根据,证明整个南沙群岛和西沙、中沙、东沙群岛一样属于中国,但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在有争议的中国领土南沙地区的岛礁中,中国实际控制仅是极少数,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中国对有争议的问题采取克制的态度,表现出中国和平与合作的诚意。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所谓的“台湾问题”作为地区安全问题,并以中国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来判定中国对地区安全的态度。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既然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中央政府以什么样的手段对待“台独”倾向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在主权范围内对“台独”倾向采取各种必要的行动和中国对同其它国家的纠纷采取和可能采取的态度完全是两回事,其性质和范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一个是内政性质和范畴的事,一个是外交性质和范畴的事。世界各国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两个不同领域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不同的。故意混淆两者间的不同,除了别有用心之外,就是暴露出一些人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支持“台独”的真实面孔。
对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努力,中国近年来一直抱着积极支持、积极参与的态度。中国现在是亚太所有地区安全多边对话合作机构—“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的成员,并为推进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包括最近同菲律宾共同主持“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北京会议。
(四)有限的防卫力量。中国不否认一定的国防力量是各国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国家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国防现代化自然而然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中国坚持“综合安全战略”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投入国防现代化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极其有限的,流行的方针和口号是“军队要忍耐”。
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称中国国力增强、军事现代化后必然要用武力解决同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必然要扩张并称霸亚洲和全世界。这完全是居心叵测!只要看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就可一目了然。中国18年来的发展、崛起和实力的增强,带来的是中国和亚太所有国家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恶化;是中国同各国政治、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的发展,而不是更多的矛盾对抗;是中国与各国对话合作的态度和方针,而不是中国对各国的敌意和敌视;是中国同地区各国间更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而不是“称霸”和“扩张”。硬说中国未来注定要称霸、扩张,显然是别有用心和站不住脚的。
注释:
[①a] 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Washington,D.C.1995.p.i.,and 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Washington,D.C.,1995,p.l.
[②a] Deputy Secretay Talbott,"Support for Democracy And the U.S.National Interest,"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March 18,1996,Vol.7,No.12,p121.
[①b] President Clinton,"American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August 5,1996,Vol.7,No.32,p.401.
[②b] 李学江:《美国的“两只锚”》,《人民日报》1996年8月6日,第6版。
[③b]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1月17日。
[④b] "Kissinger Urge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National Interest,"USIA Bulletin ,July 14,1995,p.12.
[①C]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