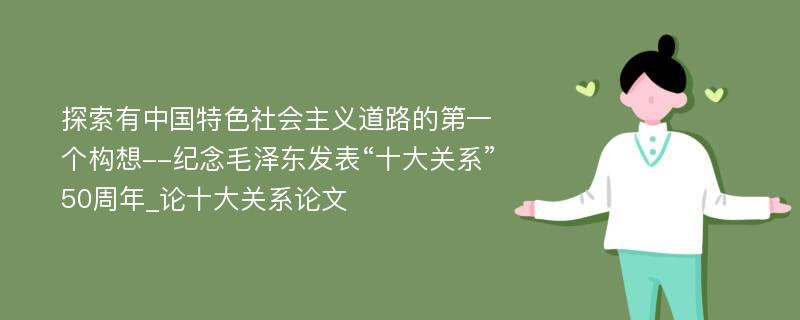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构想——纪念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五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最初论文,道路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演:一次是在1956年4月25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次是在同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讲话的主旨在于提出突破苏联僵化模式束缚、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根本问题,其基本精神、十个标题完全一致,具体内容、侧重点有所不同。《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构想和中国改革之路的最初源头,重新研究其提出、解决和遗留的问题,对今天深化改革仍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强调在和平与发展新时期以苏为鉴、走出新路
《论十大关系》提出:国际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因而需要根本克服战时形成的苏联传统体制的历史弊端。对于国际形势、世界格局的这种判断,成为中国共产党决心突破苏联传统模式、走自己新道路的一个重要支点。
从1947年起,西方帝国主义者首先发出了“打破苏联铁幕”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对形势判断失误和作出激烈反应,世界从战后和平气氛迅速转入美苏对立、东西对立、两大社会制度对立的冷战气氛。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基本判断,这是1947年后第一次改革浪潮戛然而止、苏联战时体制逐步蜕变为僵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由于种种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一度处于冷战气氛的漩涡甚至首当其冲的前沿,新中国建立之初就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战火一度烧到中国门口。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冷战气氛开始缓和。1956年初,毛泽东等敏锐作出战后国际形势将出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的判断,这是提出《论十大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客观描述了这一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1] (P236);“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它提到中央全会,大家也想一想这个问题”[1] (P237)。薄一波的回忆录印证了这一点:“到1955年底和1956年年初,我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2] (P485)
以此为背景,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第二次改革浪潮。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对苏联国家垄断、排斥市场的战时体制进行反思的历史课题。赫鲁晓夫的历史性功绩是打破禁锢、揭了盖子、捅了蜂窝,但由于把深刻性的体制问题肤浅地归结为“个人迷信”问题并对斯大林采取简单否定、个人攻击方法,因而使改革流于表面,处于混乱、失控状态,无法解决社会主义体制转变问题。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当时没有表态,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3月17日晚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点意见作为“破题”。他说,现在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是说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要破除迷信;说他捅了娄子,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3] (P4-5)。
3月19日和24日,毛泽东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比较系统地谈论了斯大林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着重讲了关系全局的四点意见,其中作为总结性的第四点更突出强调了以苏为鉴、走出新路的基本态度,首次表示要下定一个大决心,坚决反对硬搬苏联的教条主义,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说,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 (P6-7)。根据政治局、书记处集体讨论的基本观点,中央委托陆定一等五人小组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准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4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他画龙点睛地提出了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新路的问题,表达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决心: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3] (P9-10)。在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以苏联历史经验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像走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道路那样,走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十大关系,一个宗旨,就是以苏为鉴,走出新路。《论十大关系》开门见山地亮出其思想宗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 (P23)以苏为鉴像一根金线贯穿十大关系,反映到十大关系的方方面面。十大关系的最后一条——“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了对待苏联经验、外国经验的基本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好处都要学,但要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决不能机械照搬、简单移植,对于不足之处则要扬弃,“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4] (P41)最后,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大胆解放思想,走自己道路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 (P42)
二、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抓住影响我国全局的十大关系
与上述广阔的世界背景相呼应,《论十大关系》还有深刻的国内背景。新中国的快速发展,积累了有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丰富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重要的历史铺垫。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写作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基本国情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以系统辩证法的独特方式抓住了影响全局的十大关系。
毛泽东早在1955年就对中国农村展开过系统调查研究。以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契机,毛泽东搜集、整理了农村材料176篇、近100万字,逐篇撰写了编者按。1955年9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了内部初编本;12月,又经删改补充,尽量反映近半年的最新进展、最新经验、最新问题。12月27日,毛泽东为新编本改写序言时,提出了全书的思想主旨并首次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农业与工业等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局问题。毛泽东把这次编辑文集作为对中国农村的一次系统调查,并把它同写作《论十大关系》联系起来,作为建国11年中的两次重大的国情调查。毛泽东在1961年3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说,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了一本书,叫作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与34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与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2] (P382-385)。从时间、内容、主题和目的上看,这两次调查是衔接的。
毛泽东率先强调要对中国经济建设全局作出系统调查研究开风气之先。1955年12月5日—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对32个部委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其大体顺序与大致范围是:城市建设——工业部门——农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1955年12月21日—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先南下、后北上,按照北京——武汉——杭州——南京——天津——北京的线路,一路体察民风民情并与干部谈话,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毛泽东等开展对34个部委的调查研究,其大致程序是“先总后分、系统推进”:先由主管部门的国务院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再对该口所属的各部委做更细的调查研究,最后再回归全局、综合判断。在3月下旬听取中央各部委汇报的同日,毛泽东同意杨尚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向中央作情况汇报的建议,中央开列的各地经济工作汇报,包括目前主要经济情况、“一五”期间主要经验教训、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等十项内容。从4月下旬开始,各地陆续来京汇报情况,到5月2日毛泽东再次发表十大关系讲演时,已听取了湖北、广东、武汉、广州四个省、市的汇报,并先后收到河北、湖南、天津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书面汇报提纲。1956年2月—3月间,李富春副总理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业交通部门的200~300个重要的大中型企业、建设单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情况,总结经验。一声令下,雷厉风行,很快就有几百个大中型企业的情况汇报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中南海,报给党中央、毛主席。
《论十大关系》包含的哲学思辨智慧首先来自于实践,来自于调查研究的源头活水。在1959年2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描述了这一理论构想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5]。
《论十大关系》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早在1949年12月,周恩来就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为题,提出了左右全局的六大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1] (P1-14)。刘少奇在1951年写了《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基本任务》,提出要特别注意不同于以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干群矛盾、公私矛盾、国家与企业等新形势下的特殊矛盾。这些智慧的水滴为《论十大关系》做了必要的历史铺垫,而毛泽东总其大成,把全党全民的智慧水滴汇成了一个总体构想。
《论十大关系》以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创新的哲学智慧,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水平。《论十大关系》体现了一种综合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系统、总体辩证法思想有机地熔为一炉。它不是通过层层展开的概念分析逐步地走向有机总体,而是通过十大关系直觉顿悟式地上升到对整个系统的总体把握,其中前五个关系是经济建设中的五大矛盾,后五个关系是政治生活中的五大矛盾。
三、确立社会主义建设重点论与两点论和谐结合的对立统一观
《论十大关系》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高度,提出了重点论与两点论和谐结合的对立统一观,为从理论思维上突破苏联僵化模式、建立中国新型体制奠定了最初的方法论基础。
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了一些弯路,有许多矛盾没有处理好,以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僵化模式。这里的原因复杂多样,从哲学高度来探寻,主要是抛弃了列宁活生生的、对立统一的具体辩证法,在方法论上把矛盾对立的斗争性加以绝对化、凝固化的形而上学倾向。
彻底克服苏联僵化模式的根本弊端必须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克服形而上学方法。首先从哲学高度提出这一课题的正是《论十大关系》。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是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突破苏联僵化模式、创立中国新型道路的哲学宣言。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把《论十大关系》蕴含的这种哲学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4] (P194);“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4] (P195)。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论十大关系》的姊妹篇,二者堪称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两论”。如同《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尤其是有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论奠定哲学基础那样,《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最初的哲学奠基。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辩证法核心的思想,特别注重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矛盾特殊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有必要“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4] (P213)。
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矛盾特殊性是什么?解决经济建设、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方法是什么?《论十大关系》首先从哲学高度提出了这一时代课题,并向解决这一重大哲学课题迈出了第一步。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矛盾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矛盾斗争性与矛盾统一性的相互关系、相互联结上,矛盾斗争性和矛盾统一性是矛盾统一体诸方面的双重关系,并且是矛盾关系最基本的两个方面。不过,矛盾关系的这两个方面的联结与比重却不是死板划一、僵死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变化的。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对抗性的矛盾占据突出地位并因而成为主要矛盾,革命的辩证法重点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性、矛盾诸方面的对立斗争性,注重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取代一方、一方吃掉一方;矛盾的统一性固然也有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但毕竟是次要的,只占从属地位。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思想重心根本转变了,其重点研究的对象已从对抗性矛盾转向非对抗性矛盾;矛盾斗争性依然存在,依然不可忽视、不容抹煞,但强调的重点、注视的焦点却转移到矛盾统一性方面上来,特别注意寻求矛盾诸方面的相互依存性、相互渗透性、相互联结性,以便达到矛盾统一体诸方面的共同发展、和谐一致、有机统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4] (P213)。
《论十大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起了最初的奠基作用。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既是突破苏联传统模式、探寻中国新型道路必须解决的十个基本矛盾,又是中国必须在经济建设中认真处理好的特殊矛盾。这十大矛盾的本质特征,就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矛盾、新问题,所以说它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实践论”、“新矛盾论”。这十大矛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辩证法,特别是作为重点的前五个矛盾,都是专门讲经济辩证法的,专讲经济发展中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新观念,解决这类新矛盾的新方法就是不要过分夸大矛盾斗争性,不要过分强调一方吃掉一方的对立性,而是要注重分析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寻求矛盾统一体诸方面的共同发展。
尽管在《论十大关系》中,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并没有全面展开,对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也未作出明确的哲学概括,但在方法论上却内在地贯穿了一条思想主线,这就是注意寻求重点论与两点论的和谐结合,寻求这种对立面和谐结合的恰当尺度,寻求对立面结合的中介桥梁。重点论旨在强调重点性,在矛盾群中有主要矛盾,在矛盾诸方面中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决定事物性质中起主导作用。两点论旨在强调全面性,在矛盾中有不同的方面,在矛盾关系中也有不同的方面,在矛盾统一体的普遍联系中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方面,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把握矛盾的各个方面、各种中介、各种联系。从表面看,重点论与两点论是对立的,但辩证思维却要求寻求这种对立的和谐结合,既反对单打一式的重点论,也反对平均用力式的全面论。《论十大关系》在处理工业与农业、东部与西部、中央与地方、国防与建设、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上,都贯穿了重点论与全面论和谐结合的新观念、新方法。
总之,我们曾在革命战争的辩证法中突出强调重点论,强调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中,我们更需要强调重点论与全面论的和谐结合,更要注意寻找对立面统一的中介尺度。
四、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
《论十大关系》以苏联为鉴戒,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严重压抑地方、企业、个人积极性的苏联僵化模式束缚,开创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对十大关系起着统帅、内在规范和总体驾驭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4] (P23)
这个基本方针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与思想锋芒,实际上却有极其鲜明的针对性,锋芒直指苏联僵化模式的根本弊端——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大大压抑了各个地方、企业、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我们通常称苏联僵化模式为“权力过于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说法不是一个揭示本质的科学抽象,只能说是一个笼统直观的混沌表象。这种说法之所以普遍流行和广为接受,是因为它虽然比较表面,但毕竟抓住了苏联模式相当典型的外部特征。这种模式的深层本质是国家垄断制:国家作为独一无二的唯一主体,占有一切主要生产资料,而任何企业、劳动者个人都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国家通过行政指令性计划,直接组织生产与分配,任何企业、个人都没有重大决策权;国家是社会生产的计划控制中枢,市场机制名存实亡。由此,必然造成国家的主体化与企业、劳动者个人的客体化,国家成了至高无上、包罗万象、独一无二的能动主体,而企业、劳动者成了缺少主体性的被动客体。基于这种深层本质和结构表现出来的历史表象、外部形态,就是只有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有积极性,而为数众多的地方、企业、个人则没有多少积极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症下药、有的放矢,针对的正是这个传统模式的深层痼疾。不过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毛泽东只是点出了极为典型的外部症状,没有作出具体深入的病理分析。他着眼于从外部改变症状,因而提出了对症治疗的基本方针。
这个基本方针具有许多新特点。1.要求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按照这个基本方针要求,我们不仅要有中央一个方面的积极性,而是要有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集体与个人、工人与农民、东部与西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整个体制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把直接的与间接的、现有的与潜在的、内部的与外部的积极因素全都充分调动起来。2.要求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国内国际都存在一些消极因素甚至是反动势力,“左”的教条主义与僵化模式是到处树敌、“唯我独革”、打倒一切。新的基本方针则要求化敌对为中立、化阻力为动力、化腐朽为神奇,总之是千方百计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3.要求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怎样发挥两个积极性、多种积极性、一切积极性?单靠国家强制、死板划一的方式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十大关系无论是讲经济建设的前五个关系,还是讲政治建设的后五个关系,都包含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思想几乎呼之欲出。在4月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本文做了重要发挥,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补充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 (P54)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毛泽东趋向于把这一方针扩展到政治思想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4] (P278-279)。总之,这一基本方针立足于中国国情,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低起点与大目标”的尖锐矛盾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以体制、人的积极性优势,化解资金、文化上的相对劣势;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主要途径,实现后来居上的赶超目标。
这个基本方针用朴实的语言提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的思想主旨,试图既超越苏联模式的近代工业化道路,又超越西方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道路。纵观世界历史,苏联模式与西方模式代表了近代工业化中的不同模式和道路。苏联模式的近代工业化道路重点是发挥国家的积极性、主体性,特别是中央政权在国家工业化基本建设中的主体性、积极性,但却严重压抑各个地方、广大企业、劳动集体、众多劳动者个人尤其是广大农民的主体性、积极性,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工业化超高速发展,但历史后遗症严重,农民被挖得太苦,民生改善不理想。西方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道路特别强调发挥资本的积极性,以资本资源的高投入求生活资料的高消费。当时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五亿农民的东方农业大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特别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积极性,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是一件命运攸关的头等大事。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决不能简单照搬苏联模式、西方模式,必须走出中国式的新道路。
根本突破苏联僵化模式束缚,走出一条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主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主旨。
标签:论十大关系论文;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斯大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