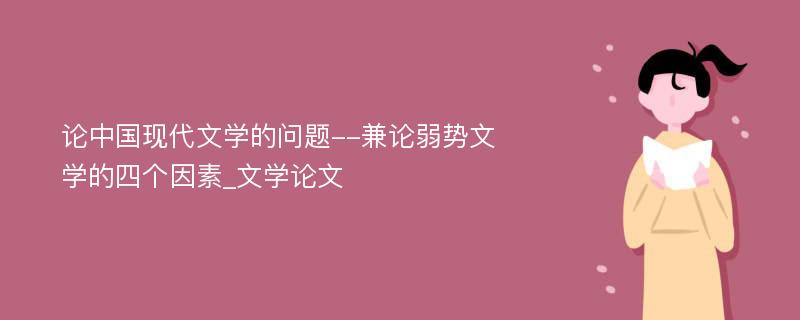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笔谈——论文献薄弱的四个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现代文学论文,薄弱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文献问题。常见的突出问题有:使用史料时粗枝大叶,张冠李戴,史实讹误;不重视触摸、鉴别原始资源,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从而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不能自拔,被人牵着鼻子走;混淆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破坏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在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编辑过程中,不加说明就任意删改原作,造成了如鲁迅所说妄行校改的灾难性后果。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1](P185)
文献问题不仅仅指文献使用过程中的具体差错,而且还表现在对文献缺乏准确、深入的阐释,文献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死材料,而未能融入作家真切的生命体验,开掘出文献背后的精神,打开文献潜在的历史内容,它所直接生发的新的意义,没有给研究者提供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美国文学史家韦勒克批评说,文献工作者“他们往往过分集中于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略从材料中可能获得的最终含义”[2]。
造成现代文学研究文献薄弱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困扰,也有研究主体主观唯心史观膨胀所引发的弊端,以及传统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无法适应现代文化变革的需求,等等。
第一,战乱直接制造了文献的散佚和毁灭。军阀战争、特别是20世纪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对文献史料的破坏更是灾难性的。正如一则历史文献记载:“凡是日寇的炮火所到,日寇的铁蹄所到,不仅我们那里的男女同胞,或万、或千、或百、或无数的生命,横遭惨酷无伦的殷灭、屠杀和奸淫;……而且我们那里的文化,不管旧的或新的都横遭惨酷无伦的毁灭,都为之荡然无存。”该文还指出,北平自去年8月以来,是沉沦在日本强盗的炮火铁蹄之下了,“学府变成了日寇的兵营,万千学子和优秀的文化人士从那里逃亡出来,失学、失业和流浪;百年来新文化的文献,革命的文献被迫于数日之内焚烧殆尽”。[3](P12-13)北平是这样,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文献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侵略者的占领也使研究者的生活陷入困境。没有尽头的流亡、流浪生活使他们失学、失业、贫病交加,根本无法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等琐细繁重的工作。如胡风所说,“炮声一响”,“门窗颤抖”,他们“跑向战火纷飞的战场”,“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走向困苦的“长长的旅路”。[3]战争使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第二,研究主体文学观念偏狭,研究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如果说战乱是造成20世纪上半叶文献遭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下半叶出现的诸多文献失误则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偏狭有关。革命的胜利造成了一些人的错觉,甚至以为在学术上也可以心想事成、随心所欲,什么事不凭材料而靠主观想像就可以做得到;加上运动不断,一场一场的运动使研究者处于一种像沈从文所说的“避灾免祸”的精神状态。“避灾免祸”的心态助长了不尊重史料的媚俗趋时倾向的发展。还要看到二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大潮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暴发户心理,反映在研究上就是浮躁、急功近利风气的膨胀。出版物越来越多,但水分也越来越大。如果说主观主义盛行、搞运动使研究者处于“避灾免祸”的状态,被迫启动其生命自我保护机制,不在乎史料,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那么经济收入上的反差,则使一些人很难认真地坐冷板凳,再甘心寂寞地去做文献、史料搜集、研究这类工作了。
第三,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的干预。20世纪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代。党派利益、政治利益至上的格局,在一定语境下对公正、公平的学术研究造成了伤害,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学术规则受到了漠视。由于学术分歧受学术以外意识形态分歧所左右,一些研究成绩斐然的文学大家,有时他们也混淆文学论争与政治斗争的界限,不能以事实为根据客观评价文学的是非功过。他们以语言霸权心态从事的研究,结论当然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这些文学指导者所做的报告、撰写的某些文章,火气很盛,对论战对方充满剑拔弩张的敌意,而无学术论争心平气和的真诚。这些文章由于居高临下的咄咄逼人和文献的疲软而失去了亲和力。
第四,传统文献学有关文献整理、校勘的方法不能适应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新的现代文献学尚未建立,这也是造成文献问题日益突出的因素之一。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带来了文献工作的复杂性。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在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5],期刊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这就使作品、史料的校勘和传统的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从事校勘的学者多湛深经史,校理群书,无不精密。但他们的校勘,多限于考订文字,订伪补脱。新的时代对校勘的要求已经不完全是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校勘开始和社会调查、访问知情者等多项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运用新的校勘手段,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以《师陀全集》的整理为例,在“以期刊为中心”的研究现实面前,就出现了较传统文献校勘远为复杂的情形。
一是同名异文。即作品篇名相同,而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篇文章。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师陀以芦焚的笔名在解放区和上海分别发表了两篇内容各异的散文《八尺楼随笔》。多亏笔者亲手核查了两篇《八尺楼随笔》,才避免了把两篇文章当做一篇的差错。二是异名同文。这一现象在师陀的作品里出现几十篇之多。有时一篇文章三次改换题目。在阅读作品时如不加以考辨,就会使研究者误以为是不同的文章。三是作者署名相同而实际上是不同作者之文。1942年3月、4月就有人在上海《中华日报》连续发表署名芦焚的论文《诗与节奏》;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有又名“向烽”的芦焚在活动;在杭州的刊物上也还出现另一个芦焚。假芦焚的招摇过市,才逼使芦焚发表声明,改笔名为师陀(注:参看《致“芦焚”先生们》(载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马兰》)。师陀在文中声明,要将笔名芦焚,奉送给“汪记《中华日报》上的‘芦焚’”。)。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提醒人们,只有加强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才能避免因署名相同而造成的错误。四是声东击西,以假乱真。1943年3月,芦焚发表了一篇通讯《华寨村的来信》。人们知道,华寨村是师陀家乡村庄的名字,即河南省杞县华寨村。《华寨村的来信》除了说明自己在河南乡间的苦闷心境外,特意抄录一段上海小报消息,描述芦焚在乡间“养鸡种豆,弃绝笔墨”的情状。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师陀从来没有回过故乡,怎么会从华寨村给上海写信,并有小报记者的这段消息?带着疑问笔者专程请教了师陀。原来,这篇故意制造的小报消息,完全是师陀自己一手炮制,以便在生存空间逼仄的上海保护自己,迷惑敌人。多亏访问了作者,这团乱麻才没有打成死结。五是作品体裁互换。师陀突出的艺术风格是小说的散文化,散文的小说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有点像散文,散文又往往像短篇小说,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既然没有一篇合乎规定的标准,我便把它们称为‘四不像’”[6]。实际上,体裁互换曲折地折射出了作家的美学追求。我们尊重作者对文体的理解,但在收入全集时则要核对作品发表时的情况,原发表时是小说归类于小说,是散文编入散文集,而不在意作者后来的变更。六是版本问题。现代不少作品鸿篇巨制,其版本校勘更非传统校勘经验所能范围。上述六种情况,都是在传统文献学中较少遇到或根本不会发生的新情况。针对这些新的变化,与现代社会的文学研究相适,应该在实践(包括古人和今人的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建立起新的现代中国校勘学。对诸如现代校勘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对象,现代校勘学的原则与方法,现代校勘学的基本操作规范等问题,在取得一致认识或接近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7]
上述四个方面存在的原因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在一段时间内,非文学因素对文献工作的干扰曾经居于决定性的地位;随后,研究主体漠视学术规范问题又升为主导地位。各种因素纵横交错,彼此勾连,形成了文献建设长期滞后的局面。
文献薄弱的原因当然不止以上四端。比如文献档案管理制度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同样是现代文学文献匮乏的原因之一。一份普通的文献,一旦被列入保密范围,就解密五日,其保密时间之长,常常以30年、50年为计,从而使一些文献在研究者视野之内消失。文献档案部门或借口保密把借阅者拒之门外;或缺乏服务意识,甚至在潜意识里把文献据为部门所有,奇货可居,惟恐研究者窃了他们的看家宝贝,抢了他们的饭碗。文献本为研究之公器,却变相地为单位或私人所占有、所攫取,迫使研究者为了查寻材料,不得不奔波于旅途,往往被搞得身心疲惫,却收效甚微。档案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献问题的解决就永无时日。还应该特别提及人们对文献研究的偏见以及那种贬损文献研究者的根深蒂固的陋习。默默无闻地致力于文献建设者,却时常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讥讽、嘲笑,可能也是许多人不屑于史料工作的一个原因。鲁迅曾经动情地描述过他搜罗《小说旧闻抄》史料时的心情:“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但在以得之难也,颇也珍惜。”当《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鲁迅“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重复寻检之劳焉而已”。但鲁迅治史料的辛劳却不被时人理解,他对此感慨系之,“而海上妄子,遂腾簧舌,以此为有闲之证,亦即为有钱之证也”。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形,韦勒克就指出过史料工作者“曾受到过不应有的嘲笑,说他们学究气”,“往往被称为‘高级校勘’(higher criticism)这个不甚恰当的术语”。[2]因此,加强文献工作,首先应该做的是转变人们的观念,走出轻视治文献者的误区。
用宏阔的眼光来看,文献问题既包含文献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一代青年学人的培养问题。一方面通过文献教育和文献训练夯实青年学人的学术根基,另一方面培养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夯实基础不只是指知识的纯史料性扩张。文献的把握应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进行,开掘出文献本身所渗透着的现实生活的脉动,鼓励他们用学术的方式关注学术,关注学术前沿。把夯实基础与关注学术前沿统一起来,是我们培养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学术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从根本上克服文献薄弱问题的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