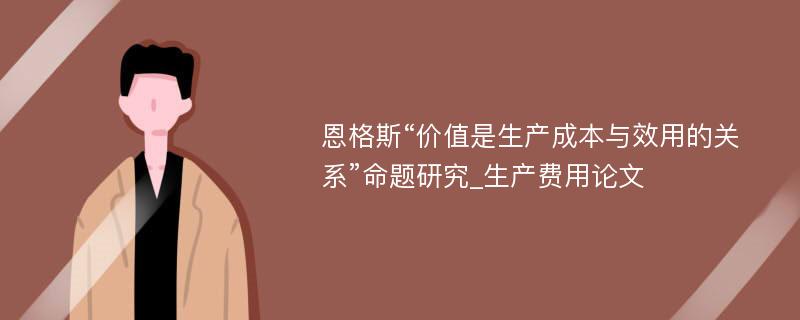
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命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效用论文,命题论文,费用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的一个命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命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没有区分作为交换价值基础的价值和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恩格斯提出了两种不同含义的价值,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但在具体论述时却没有将二者严格区别开来,也是造成对这一命题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源。文章在区分两种不同价值的基础上,论证了恩格斯后来在什么意义上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肯定,又在什么意义上对这一命题是否定的,并对这一命题在今天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作为交换价值基础的价值 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
●作者简介:1936年生,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提出来的。针对李嘉图、麦克库洛赫的生产费用论和萨伊的效用论之间的争论,恩格斯认为,“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因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因素分开,……双方都毫无结果”,因此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1〕的观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前苏联,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大纲》的价值含义“尚不能说是正确的”〔2〕;而在我国, 人们的看法则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持肯定态度〔3〕,有的持批评态度。〔4〕但是,从我国30多年的争论的情况来看, 争论双方往往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真正的交锋并不多。因此争论时间虽然已长达三十五、六年,但所取得的进展却并不大。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争论,基本上是重复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论点和论据,很少有新论点、新论据提出来。这种情况表明,有关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命题虽然是一个讨论了几十年的问题,但它依然是一个需要花很大力气进行研究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的症结
经过反复阅读恩格斯的原著和有关资料,我逐步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要解决恩格斯《大纲》中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命题的是非,必须区分价值的两种含义,即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和作为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这前一种意义的价值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家几乎把它看作是唯一的价值;而对后一种意义的价值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人们几乎不把它看作是价值。应该说,正是恩格斯的《大纲》给我们提出了价值的这两种含义。他写道:“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 ”〔5〕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私有制下,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作为交换基础的价值,“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时,价值这个概念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它的真正的活动范围。”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价值的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解决物品应否生产的价值,它适用于一切社会,包括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没有商品生产的未来社会;一个是运用商品交换的价值,它只适用于私有制消灭之前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应该说,恩格斯关于价值的两个含义及其活动范围的提出,是恩格斯天才思想的表现。后来的事实也表明,马克思完全接受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且给予了进一步的发展。问题在于,恩格斯在《大纲》里虽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却没有赋予两种价值以明确的不同的定义;其所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似乎既是对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而言的,也是对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而言的,而且主要是对后者而言的。我认为,这正是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根源或症结之所在。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上述看法,在他们看来,价值就是价值,不应该有不同的含义,更不应该有不同的定义。其实,一词多义是一种极常见的语言现象,而用同一术语来表示不同的内容也是各个学科都存在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里曾谈到经济学中两个不同的“必要劳动时间”,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特殊的商品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作一比较。”〔7〕显然, 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的,它对于我们认识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两种不同含义的价值,无疑是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事实上,不论是在汉语里还是在其它语言里,价值一词都是多义词,具有多种含义。根据《辞海》的解释,在汉语里,价值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英语、德语、俄语中的价值也和汉语中价值的含义差不多,一般也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重要性、有用性、意义等,一是指商品交换之所值。可见,恩格斯在《大纲》里提出两种价值不仅从经济学上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语言上来说也是说得通的、无可非议的。
恩格斯在《大纲》里提出两种不同的价值是他的一大贡献,而他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来定义,两种不同的价值却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长期以来关于恩格斯价值定义的争论正是由此而引起的。肯定恩格斯价值定义的人以恩格斯后来对这一定义的坚持和马克思对这一定义的肯定作为自己的有力论据;而否定恩格斯这一定义的人则以恩格斯后来对《大纲》的自我否定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这样的争论当然很难令对方和读者信服。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价值,弄清恩格斯的价值定义对两种价值的适用性。实际上,恩格斯后来对价值定义的坚持和马克思对这一定义的肯定是就作为解决物品是否应该生产这一意义上的价值而言的;而后来恩格斯对《大纲》的自我否定则是就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来说的。只有把这两者区分清楚了,不同观点的争论才有解决的希望。
二、事情的一面:恩格斯的坚持和马克思的肯定
现在我们先讨论事情的一个方面: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始终坚持他的价值定义的?马克思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肯定恩格斯的这一定义的?
我们知道,恩格斯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一定义的坚持主要体现在《反杜林论》的一个脚注里。这个脚注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8〕这个脚注中所说的“1844年已经说过”的话显然是指《大纲》里说的“在私有制消灭之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那句话。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坚持的,并不是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而是作为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价值。如果我们把这个脚注和它所引出的正文加以对照,就会更加清楚这一点。《反杜林论》里那段正文是这样说的:“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需给产品规定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须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9〕乍看起来, 恩格斯在正文里讲的话和他在脚注里讲的话似乎是矛盾的:在脚注里,恩格斯认为“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而在正文里,恩格斯则认为在未来社会“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但是,只要我们稍微仔细对照一下正文和脚注,就不难发现,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正文两次讲到的“价值”,是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而脚注所讲的“价值”则是作为解决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价值。前者在未来社会当然不再存在,而后者则不仅存在于私有制社会,而且也存在于未来社会。从这里显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恩格斯所坚持的是什么意义的价值了。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上述论述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这一意义上的价值,仅仅考虑“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各种消费品的效用”,才能“最后决定这一计划”。这就清楚地说明,恩格斯是坚持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来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的定义的。
应该指出,不仅恩格斯始终坚持了《大纲》的价值定义对解决生产问题的价值的适用性;而且马克思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早在1844年,当恩格斯的《大纲》刚刚发表,马克思就写了一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在《摘要》里,马克思在摘录了恩格斯的定义以后写道,“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生产的问题。”〔10〕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一书里,马克思在自己执笔的部分又强调说,“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11〕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只讲到劳动时间,而未讲到效用,似乎与恩格斯的定义是不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讲到了“实现真正的人类发展”即满足需要的问题,那就应该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
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里,关于价值的论述虽然主要是就作为商品交换的基础的价值而言的,但是,无论是在第1卷,还是在第2卷、第3卷,马克思也多次就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进行了论述。比如在第1卷论述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时, 为了和商品生产进行比较,马克思讲到了孤岛上的鲁滨逊、昏暗的中世纪、农民家庭和自由人联合体,这里当然不存在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但他也说到了“价值的一切本质规定”。〔12〕显然,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来说的。针对孤岛上的鲁滨逊,马克思还写道,“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困难的大小。”〔13〕而对于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写道:“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14〕。他还指出,“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15〕在第2卷里,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谈到,“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时间不断地或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16〕他还强调说,“这种情况是由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17〕在第3卷,马克思更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 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薄记,将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18〕我们说,《资本论》里的这些论述,不仅充分肯定了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而且也是对恩格斯这一思想成果的进一步的论证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脚注里说“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那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总之,从一个方面说,即从作为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价值来说,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它不仅为恩格斯所始终坚持,而且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的肯定和进一步的论证。
三、事情的另一面:马克思的保留、否定和恩格斯的自我否定
以上所论述的,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这就是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对于作为商品交换的基础的价值来说却是不正确的。
我们知道,《大纲》中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是针对李嘉图的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和萨伊的价值由效用决定这“两个跛脚的定义”提出来的。应该说,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相提并论统统说成是“跛脚的定义”,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对萨伊的效用论,恩格斯批评说,“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也是“跛脚的”有什么根据呢?《大纲》说,“假定某人花了大量的劳动和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也要按照生产费用来计算吗?经济学家回答说,决没有这样的事,谁愿意买这样的东西呢?于是我们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臭名远扬的效用论,而且碰到了随着‘购买’而来的竞争。这样就形成了尴尬的场面,经济学家一刻也不能忠实于他的抽象了。……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19〕其实,李嘉图强调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但并不否定使用价值或效用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里,他就明确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20〕在这里,李嘉图既肯定了效用是价值的前提,也否定了把效用作为价值的一个要素的观点,因此,对李嘉图的价值论来说也就不存在《大纲》所说的那种“尴尬的场面”。至于竞争,在讨论价值的现象形态时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讨论价值的本质时却是应该加以舍象的。价值本身乃是科学抽象的产物,将其说成“不实际的东西”而加以否定,显然是不科学的。
这里需要着重讨论一下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价值定义(就其作为商品交换的基础而言)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其作为商品交换的基础而言)是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恩格斯《大纲》的价值定义却是劳动和效用共同决定价值,二者显然是矛盾的,不能调和的。从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不可能赞同恩格斯的价值定义,而只能采取保留和否定的态度。
有一位论者说,马克思在为《大纲》一文写的《摘要》里曾经“一字不漏地摘录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段话”,而且“当马克思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经济学家时,他仍然称赞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并且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价值定义曾提出过什么否定意见”。 〔21〕我认为,这样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诚然, 马克思确曾作过《大纲》的摘要,并且“一定不漏地摘录了”恩格斯的价值定义,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的观点,更不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当1844年初写作《大纲》的《摘要》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还没有形成,即使在这时,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价值定义也作了保留,而并未完成肯定。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摘要》里确实摘录了恩格斯的价值定义,但那是就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价值而言的,至于《大纲》中涉及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所讲的话,如恩格斯说的“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以后的一大段话,马克思都没有加以摘录。这决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马克思的保留。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的“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22〕这句话里清楚地得到说明。
可以说,马克思对恩格斯价值定义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里,马克思在自己执笔的部分写道:“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和效用来确定的。后来才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23〕这些话不太容易理解。过去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提法,与《大纲》中的提法显然是对立的”,“在新的提法中,在否定效用论的同时,劳动价值论仍然被否定了——只是采取了《大纲》相反的形式”,并且认为“这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否认商品内在价值的存在有关”。〔24〕看来,这里存在着误解。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价值并不是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而是作为解决生产问题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而与生产费用和效用无关也不是否定恩格斯《大纲》中的价值定义(就其解决生产问题而言)。而是说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不可能由计划来规定,只能由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来确定。应该说,在这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当马克思在同一本书中谈到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时,就表现出了与恩格斯不同的观点,他十分明确地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这一点甚至连批判的批判也不会不了解。”〔25〕也许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最早以明确无误的语言来阐述劳动价值论,而对《大纲》中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来定义商品价值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列宁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这句话而在《“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认定,“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理论了。”〔26〕这是非常正确的。
继《神圣家族》以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里更明确地指出,“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李嘉图体系”,“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27〕书中还说,“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28〕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充分肯定和崇高评价,和恩格斯在《大纲》中把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和萨伊的价值定义一道说成是“跛脚的定义”显然是根本对立的,理应看作是对《大纲》批判李嘉图价值定义以及用萨伊的效用论补充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的一个否定。至于说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曾称恩格斯的《大纲》为“天才大纲”,以及在《资本论》里多次引述《大纲》的观点,这当然是事实,问题是,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马克思对于恩格斯《大纲》中有关价值的定义(就其作为交换的基础而言)是肯定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字来看,“天才大纲”的说法并不是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著作本身作出学术性的评价,而只是在谈到他与恩格斯的交往时用的一个很客气的说法。在马克思的叙述里,我们看到,只是在恩格斯的《大纲》“发表以后”,马克思才开始了他和恩格斯之间的不断通讯交往。但是,使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马克思“一样的结果”的并不是《大纲》,而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9〕可见用“天才大纲”来证明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价值定义是没有说服力的。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确实多次引述过《大纲》,我查了一下,一共有四次之多,但却没有一处是肯定恩格斯那个价值定义的。相反,我们倒是看到,无论是在《批判》里,还是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的价值时,所下的定义都是和恩格斯《大纲》里的那个定义相对立的。在《批判》里,马克思说,“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30〕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又一再强调,“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31〕这些论述,对任何一个稍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
事实表明,马克思从恩格斯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一价值定义(就其作为商品交换的基础而言)之始,就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而在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更一再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价值定义曾提出过什么否定意见”是没有根据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不仅马克思对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价值定义是保留的、否定的,就是恩格斯本人,在其后来的著作里也进行了自我否定。在其主要著作《反杜林论》的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五章“价值论”里明显地改变了他在《大纲》里提出的关于价值的观点。在这里,他写道,“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32〕显然,这和《大纲》里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它是“跛脚的”,主张用萨伊的效用论来补充的观点相比,可说是发生了180 度的变化。谁又能说恩格斯没有抛弃他早期的观点了呢?
除了著作,在恩格斯的信件和传记材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这种自我否定。1871年4月13 日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指《大纲》——引者)重新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这里讲到“完全过时”和“许多不确切的地方”,显然是包括其价值定义在内的。其后,1884年,俄国一位艺术家兼学者叶·埃·帕普利茨致信恩格斯,提出要将《大纲》译成俄文。恩格斯在复信中再次对《大纲》进行了自我否定,他写道,“虽然我至今对自己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它带来的好处多。”〔34〕应该说,这里说的“完全陈旧”、“缺点”“错误”“很多”以及“误解”等,也是包括价值定义在内的。
再后来,1889年,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为恩格斯写一篇传记,传记草稿曾送恩格斯审阅,恩格斯在草稿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文章(指《大纲》引者)很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来论证社会主义。当时,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很肤浅(例如,关于李嘉图只引用了麦克库洛赫的简单化的解释)。这里,除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即将同马克思成为它的创始人)的萌芽,也还有某些错误。不过这些萌芽还没有超出恩格斯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形式。”〔35〕在这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恩格斯讲到当时他“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很肤浅”,他不是从原著而是从麦克库洛赫的解释间接了解李嘉图的。看来,恩格斯对李嘉图的错误批判,其根源正在于此。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恩格斯早年对政治著作的了解似乎主要是间接的。〔36〕应该说,这一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恩格斯在其著作、信件和传记材料中所进行的自我否定,最好不过地说明,《大纲》中关于商品价值的定义是错误的,它反映了恩格斯早期著作的不成熟性,不能作为成熟的价值理论看待。
四、余论
以上我们回顾了有关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一命题争论的历史,并根据《大纲》的论述对价值的两种不同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恩格斯的价值命题在什么意义上是正确的,在什么意义上是错误的。同时还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论证了在作为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对《大纲》价值命题的坚持和马克思对这一命题的肯定与发展;论证了在作为商品交换的基础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对这一命题的保留、否定和恩格斯对这一命题的自我否定。从表面上看,这里进行的是一场名词概念之争,但是,由于价值范畴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而经济范畴乃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进行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清楚了。
从理论上说,区分两种不同的价值,弄清《大纲》的价值定义对这两种不同价值的适用性,对于我们坚持劳动价值论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科学社会主义又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起点和中心发展起来的。可以这样说,没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正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正确认识价值的两种不同含义和恩格斯的价值定义的适用范围,坚持劳动价值论,其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除了对《大纲》的价值定义本身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外,在价值理论领域还有其它一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学术界。比如价值是历史范畴还是永恒范畴问题,又比如决定价值的是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都是长期争论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区分两种不同的价值,明确“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一定义的适用范围,能为我们提供一把解决问题的极好的钥匙。以价值是历史范畴还是永恒范畴来说,这是一个从50年代就开始争论的问题,至今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大多数人认为,价值是商品生产范畴,而“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37〕因此他们认定价值是历史的范畴。而另一些同志(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为代表)则以《大纲》、《反杜林论》中的一个脚注和《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价值决定”的一段论述为根据, 主张价值是永恒的范畴。这就是所谓“价值规律万岁论”。其实,争论双方所讲的价值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所讲的价值是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它当然要与商品生产共存亡,因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后者所讲的价值,乃是作为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价值,它与生产的一定形式无关,即使在商品生产消失以后也将继续存在,当然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可见,只要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是可以获得解决的。
再以是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还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问题来说,这也是一个争论多年的老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另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与价值的实现有关,而与价值的决定无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决定价值或共同决定价值。这就是关于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的争论。实际上,这个问题同样可以用区分两种不同价值来加以解决。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乃是决定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的劳动时间;而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是作为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价值的劳动时间。应该说,后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生产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无关,它存在于一切社会,任何社会进行生产都要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大纲》中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能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进行交换的问题。”〔38〕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称做“第二种含义的”是不恰当的。尽管这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此重要,但是它对于决定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来说却只能是前提,而不是本身的一个决定因素。道理很简单,任何商品都必须具有某种使用价值,必须有效用,只有在各种效用进行了相互比较并和劳动时间进行了比较之后它才能被生产。这当然是前提。但是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说,它作为交换基础的价值却只能由劳动时间决定而不能由效用来决定。因此商品的价值只能由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能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如果承认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能决定价值,那就是承认除了劳动耗费,还有其它因素也能决定价值。这只能导致对劳动价值论的背离和否定,当然是不可取的。不过,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直接由计划决定的,它要通过竞争,通过价格和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的背离,也就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间接地把必要的比例分配给各不同的生产部门。从这方面说,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不仅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要通过“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而且“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要通过“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才能实现。但是,在非商品生产的社会,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不会存在,而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不会消失。实际上,所谓“第二种含义的”才是真正首要的,第一的;而所谓“第一种含义的”才真正是派生的,第二的。
从实践上说,区分两种不同的价值,认识《大纲》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命题在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方面的作用,对于指导现实的经济工作也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意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而对作为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问题的价值则认识得很不够,不能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来解决生产问题,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重视产值却轻视效用,生产一些有数量而无质量或质量很差的产品。结果产品生产了,“价值”也“创造”了,但是,产品卖不出去,价值实现不了,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今天,当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时候,“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在解决生产问题上的指导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不仅要生产出一定数量、一定价值的产品,而且要考虑它的费用(成本)、效用(使用价值,质量),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有效的,有价值的。
应该指出,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从实质上来说乃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这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不说自明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有人曾提出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马克思反驳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都知道。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39〕应该说,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就很不容易了。然而如果我们甚至在理论上都没有弄清“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解决生产问题的准则,那么其对实践的危害就更不堪设想了。今天,我国的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对市场经济来说,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配是通过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或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实现的。在这里,市场机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复杂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也正是在这里,“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40〕对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利用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作为宏观调控的有力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今后必须着力做好的一项工作。
注释:
〔1〕〔5〕〔6〕〔19〕〔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04—605页。
〔2〕布留明:《经济学说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页。
〔3〕孙冶方:《论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9月;《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作源:《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61 年11月26日;何炼成:《价值学说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罗郁聪:《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卓元:《社会主义的价格理论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蔡继明:《垄断足够价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石再:《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光明日报》1961年6月19日;卫兴华:《关于效用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商德文:《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 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杨致恒:《〈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载《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论著概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蔡中兴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大镛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12〕〔13〕〔14〕〔15〕〔3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第243页、第94页、第93页、第95页、第96页、第52—53页。
〔8〕〔9〕〔32〕〔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348—349页、第348页、第231页、第347—348页。
〔10〕〔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页。
〔11〕〔23〕〔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2页、 第39页、第61页。
〔16〕〔17〕〔4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96—397页、 第397页、第350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3页。
〔20〕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版,第7页。
〔21〕蔡继明:《垄断足够价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9页。
〔24〕卫兴华:《关于效用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
〔26〕《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27〕〔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9页、第93页。
〔29〕〔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第1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2页。
〔35〕(德)曼·克里姆:《恩格斯文献传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114页。
〔3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15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
标签:生产费用论文; 恩格斯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反杜林论论文; 资本论论文; 神圣家族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