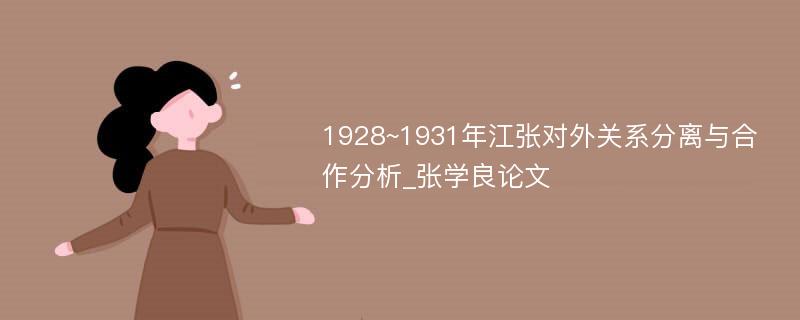
试析1928—1931年蒋张在东北地区对外关系上的分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分合论文,关系论文,试析论文,年蒋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近三年的时间里,纳入南京国民政府体系的东北地区,对日、对苏的交涉与冲突俱来,从未间断,成为当时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焦点之一。作为这一地区对外关系主角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东北集团,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一个欲利用外交麻烦来控制地方,一个想把棘手的外交问题推给中央,既有所合作,又颇有分歧,既多有对抗,又有所妥协,构成二者关系中一个独特的方面。本文试对此略作述析。
一、南京“以外交解决东北”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政学系头子杨永泰便向蒋介石献上“削藩”策。其中,对东北主张以“外交解决”。〔1〕据此, 南京政府剥夺东北的外交权,插手甚至操纵东北的对外交涉,鼓动东北挑起对外冲突,但又不完全负责,蓄意使东北在对外关系中陷入困境。同时,限于当时东北及国内、国际环境,对东北集团的自主行为,虽表不满,又不得不做某些妥协。
控制东北的外交机构和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是掌握东北外交权的根本。易帜前东北设有独立的外交机构——东北交涉总署和各地交涉署,东北交涉总署直接听命于东北最高当局,各地交涉署受东北各地方政权的领导,独立进行对外交涉。易帜后,南京就试图剥夺东北的外交权,拟在原东北交涉总署及各地交涉署的基础上,先设特派交涉员和各地交涉员,均由南京政府外交部直接任命,作一个过渡。对原东北当局委任的交涉员,“如果成绩卓著者,得由外交部加委连任,资望不符,成绩未著者,应立即撤换,另由外交部委任。”〔2〕到1929年底, 南京便下令裁撤东北交涉总署及各地交涉署,并规定:“(一)交涉署裁撤后各地方所有外交案件统归中央政府处理,地方政府不得对外设立类似交涉署之机关,以免分歧。(二)外交部对于各特别市或市县政府办理外人事务认为必要时得直接指挥。”〔3〕1930年1月,南京政府在沈阳、哈尔滨各设一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办事处,由外交部直接任命两名特派交涉员,分驻沈哈,“承外交部部长命令办理一切外交事务”。〔4 〕 3月18日,东北交涉总署正式撤销。南京政府通过裁撤东北原外交机构,设立由南京直属的外交机构和直接任命的外交官员,将东北的外交权收回。
在这一时期关于东北问题的对苏、对日交涉中,南京亦处处显示其中央的领导地位,插手乃至操纵对外交涉大权,不许东北单独对外交涉。早在东北易帜前夕,南京即向东北宣布:“以后东三省之外交事件,一律移归中央办理。”〔5〕1929年2月21日,也就是东北易帜还不到两个月,南京政府外交部便电令东北当局:“东省经办之外交,无论何国,凡从前与各该省长官订立协定者,本部概不承认,统一而后之交涉须赶速抄同原咨于本月内完全移交来部。”〔6 〕中苏因中东路问题矛盾不断激化,南京要求东北听命中央。外交部长王正廷多次强调“对俄问题,当由中央直接交涉。”〔7〕中苏军事冲突发生后, 南京惟恐东北与苏联直接媾和,蒋介石于7月27日致电张学良:“凡既经由中央接手 之外交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认定中央为交涉对手,以保护国家威信。”〔8〕其后,南京又向东北“保证至交涉前途,将来无论如何, 中央自负责任,虽有失当,决不诿诸地方”,〔9〕直到1929年12月22 日《伯力草约》签订前,南京一直把持着对苏交涉,不许东北染指。对日交涉亦是如此。1929年7月10日,王正廷在北平与新闻记者谈话时说: “统一外交为国家既定方针,是以东省外交问题,例如,日本在东省要求之土地商租案及满铁问题等其他一切问题,当由中央直接交涉”。〔10〕在中日铁路交涉中,南京明确表示:“移诸中央对日折冲,若其不可能时,由铁道部特派代表赴沈,参加交涉,不容东北单独处理”。〔11〕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 “交外交部查明交涉”,〔12〕外交部随即致电东北政委会,指出:从万宝山“鲜农退出”和“撤回日警”,“由部照会日方”,“至朝鲜仇视华侨案,当由部另案交涉”,〔13〕把持此案交涉权。
但在实际交涉过程中,南京又不完全负责,甚至撒手不管,蓄意使东北陷入外交困境。中苏交涉中,南京就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外交措施。1929年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南京, 提出解决中东路事件的三项办法,并警告:“如果不得圆满答复,则将受迫其他方法以保护苏联合法之权利”。〔14〕对此,南京复文对苏联所提三项条件未予答复,只提出二项交换条件,于是,18日苏联公布断绝中苏关系。其后,南京请德国出面调停,亦毫无结果。10月,蒋、冯战争再起,南京对中苏交涉有所放手,1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近观俄情,或其有意与东北直接交涉,故对中央再三支吾,如有接洽机会,亦可与相机进行。”〔15〕中原大战时,南京为求东北支持,“中俄外交,政府内受牵制,未能尽力为东北助”。〔16〕在关于东北问题的对日交涉中更是如此,万宝山事件及由此引起的鲜人排华事件,发生“瞬已旬日”,南京也没有“妥善办法”。7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组就此开会,结果到会者仅“王正廷及秘书谢冠生,孔祥熙、宋子文等均在沪未归,乃改开谈话会,半小时即散。”据谢称,“朝鲜事件暂由外交部向日交涉,俟日方态度如何再定方针。”“如此重大之事件”,南京却“淡然视之”。〔17〕在随后发生的中村事件中,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其重视东北的严重形势,蒋介石极感不快,在复张学良的电文中只强调:“剿共必要,解决广东为必要,至于解决东北危机只字未提”。〔18〕可见,南京只图以外交控制东北,对东北的主权和安全并不关心。尤为可鄙的是,南京竟引诱、鼓动东北挑起中苏军事冲突,以此来削弱和控制东北。1929年7月7日,蒋介石在北平与张学良“协商有关中东路对策。”10日,“决定了为收回中东路驱逐有俄籍人员之共产主义者的方针,并立即付诸实行”。〔19〕事件发生后,东北当局力图以外交解决,曾与苏驻哈领事密谈,双方决定四项解决办法,经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时,即为蒋所破坏,使东北丧失了和平解决纠纷的机会。〔20〕蒋介石还有意促使中苏绝交。他在7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21〕同时,南京一方面极力鼓动东北对苏开战。就在苏联宣布断交的当天,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据其国内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遂敢向我宣战,中央对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22〕7月21 日,蒋又致电张:“中央对苏俄作战及军队调遣事,已有参谋部负责调制全盘计划,并派葛次长或刘局长即刘光亲送来辽,如有必要,全国军队可以随时增援也。”〔23〕24日,蒋再致张:“对于关内总预备队之计划,及万一开战时各种之接济,亦均已计及”。〔24〕这期间,张学良曾派王树常到南京力陈不宜对苏作战,胡汉民却说:“廷午你是军人,怎还怕事!苏联革命后兵力正弱,决不敢动。”蒋介石则说:“你不必再说,我已有电令给汉卿了”。〔25〕另一方面,在国内掀起反苏声浪,以此造成东北非战不可之势。7月20日,蒋介石向全国军队发出通电 ,谓:“此次事件为我国力争独立平等之关键,非举国一致,共同御侮,更无以自存于世界”。〔26〕22日,蒋又在国府纪念周上声称:“吾人为拥护国权,当然牺牲一切,无论如何亦应与之对抗”。〔27〕8 月16日,王正廷向记者宣称:“如俄人来打,决严重抵抗。”〔28〕但中俄战端一开,南京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在整个中苏战争中,南京未出一兵一卒,没援助东北一枪一弹,所谓接济东北军饷200万元, 还是编遣库卷,并非现款。〔29〕相反,在战事最激烈时,蒋介石却致电张学良“速借重炮若干营,由现有长官带来助攻潼关”,“速用全力最速时期以解决西北军是为要着。”〔30〕正如《大公报》当时评论道:“东北兴兵以来,独支四月,国府事实上未能负执行军事上责任,坐令敌军深入。”〔31〕致使东北军损失惨重,第十七旅全军覆没,旅长韩光第阵亡,第十五旅伤亡殆尽,旅长梁忠甲被俘;武器弹药损失无计其数,军费支出共达6000万元。〔32〕《大公报》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采取最可鄙之行动者乃是国民政府。国民非常清楚,不负责任地唆使地方政府当局挑起事端,这种罪责尤其重大。”〔33〕
诚然,当时东北毕竟姓张还不姓蒋,况且蒋介石集团与冯、阎、桂各派争斗正酣,无法全力解决东北,因此,对东北集团的自主行为虽然不满,但也不得不妥协。当张学良先斩后奏与苏联签订《伯力草约》后,南京反应极为强烈,指责东北“超越权限”,〔34〕声称“将该草约实行修正或废弃”,〔35〕胡汉民甚至说:“蔡某有几个脑袋,敢定这样协定。”〔36〕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对于东北当局恢复已裁撤的交涉总署,南京也只有默认。
二、东北对南京的依赖与自主
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蒋介石集团的慷慨承诺和卑劣做法,使张学良东北集团在对外关系中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经历了一个由希望、依赖到失望、不满和自主的过程。
张学良决心易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此摆脱东北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困扰,所以,在东北易帜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集团把南京视作对外的保护伞,处处表现出对南京的依赖与合作。第一,适应南京外交“统一”的政策,将东北的外交权上交南京。易帜后不久,张学良就公开表示:今后东北的外交“依中央政府之指令而行”。〔37〕当外交部要东北所经办之外交完全移交南京时,张学良立即命辽、吉、黑、哈各地交涉员将原案抄送到沈,汇册后于1929年3月1日移交南京。东北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员亦基本按南京意旨改革。第二,在对外的冲突、交涉中,此种表现更为明显。如前所述,中东路事件之初,东北力谋和平解决,并与苏联达成初步协议,张学良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希望得到蒋的认可,结果遭到蒋的否决,在此情况下,张仍向蒋保证:“绝不敢为局部交涉,致妨国家威信。”〔38〕同时命蔡运升“未得中央指示以前,勿与俄方商洽进行。”〔39〕他相信,南京定会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挽救危机。在以后的日子里,张学良不断向南京报告边境的情况,陈述事件的严重性,要南京尽快对此做出决断,指出:“这决非局部之事故,亦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案,详为指示,俾中央与地方连贯一气,相机应付;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自应预为虑及”。〔40〕8月20日, 奉命“辅佐”张学良主持对苏交涉的何成浚也向蒋介石汇报说:“汉卿态度颇镇静,确能遵照中央不屈不挠之办法解决一切。”〔41〕
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东北对南京的居心有所觉察,当时张学良曾气愤地说:“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42〕后来又说:蒋介石“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想“以外交解决东北”。〔43〕因此,在事关本集团利益的根本问题上,自做主张,对南京或阳奉阴违,或先斩后奏。这在对苏、对日交涉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到1929年11月,中苏冲突已见分晓,东北岌岌可危,张学良对南京不负责任的做法异常愤怒,当蒋介石电令其与苏重开谈判时,他回电说:“鄙意此事当初既由中央完全担任,而为时又逾数月之久,彼负有完全之外交,当局对本案应付计划,自必筹之已熟,兹虽小有波折,亦应别图良策,以善其后,若地方时机业已错过,实无术再事转图。”〔44〕他对南京已不抱希望,决定单独解决这一问题。12月3日,派蔡运升与苏方签 订《双城子草约》。随后,东北集团就与苏媾和达成共识,即:“对俄主和议,虽小有牺牲,亦必实行,以养元气”。〔45〕决定再派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谈判,越权予其全权代表资格。事后仅告知南京派蔡为中国代表,隐去“全权”二字,并要南京加委。南京虽认可,但对蔡的职权进行了限制,即:“商议正式会议之日期、地点及履行先决条件之方法……,无决重要问题之权。”〔46〕对此,张学良在表面上表示“秉承中央办理”〔47〕,但蔡仍是按东北集团的意志并以全权代表的资格签订了《伯力草约》,草约内容中“除规定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外,而载有数种事项,属于两国间之一般问题”。〔48〕正因为有了中东路事件的惨痛教训,东北加强了在外交管理权上与南京的争夺。1930年12月,张学良不管南京是否允诺,恢复了易帜前的东北外交总署,以王镜寰为署长,直隶东北政委会。在以后的对日交涉中,东北名义上仍表示外交归中央,但又强调:“关于东北地方之案件,由地方解决,国际交涉即由中央负责”。〔49〕尽量将东北的外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931年2月27日,张学良在同满铁理事木村就铁路问题会谈时表示: “关于此项问题尚未呈报南京;如果早日呈报,则有招致中央方面插手之虞,因此,可根据当地会谈进展情况,再向南京告之”。〔50〕中村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决定直接和日本交涉,不许南京外交部插手。〔51〕
客观地说,在统一国家中,外交属国家权力,自应为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所独掌,地方政府无此权,至多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参与一定的外交事务。因为在对外关系中,只有国家利益,不应有单独的地方利益或集团利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是一致的。但民国一代,国家不完全独立,没有真正的统一,在对外关系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处于极其复杂的局面。中央政府常常为某一集团、派别所控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不是代表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当然也包括地方局部利益),而多是从本集团、派别私利出发,不仅损害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损害了地方局部利益。与此相反,在关系到地方的切身利益时,地方政府自行处理对外关系也已司空见惯。这一时期,蒋介石集团和张学良集团在东北地区对外关系上的分合,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与地方集团利益冲突的反映。这种关系在同时期其它地方军事政治集团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中极为鲜见。蒋、张在对外关系上从集团利益出发,尤其是蒋介石鼓动东北挑起中苏冲突及对东北外交的不负责任,给国家民族利益造成危害。日、苏均利用南京和东北的矛盾采取分化政策,特别是日本,看到东北军在中苏军事冲突中的不堪一击,大大助长了其侵略东北的气焰,这是众所周知的。
注释:
〔1〕杨永泰呈献给蒋介石“削藩论”;“经济方法瓦解二集; 以政治方法解决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解决奉张”。见简又文著:《冯玉祥传》,(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92页。 另见黄旭初:《北伐完成后的第一幕悲剧》,原载香港《春秋》月刊,后经黄汇编所著各篇,未举例原刊时期及号数。又见:《顾维均回忆录》(1),第406页。
〔2〕《盛京时报》1929年1月21日。
〔3〕〔4〕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9), 第17、16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此书系影印, 无出版时间)
〔5〕(台)《革命文献》第21辑,第1807页。
〔6〕〔7〕〔9〕〔10〕〔11〕〔27〕〔28〕〔32〕〔35〕〔45 〕〔49〕《盛京时报》1929年2月23日、7月12日、9月13日、7月12 日、1931年2月14日、1929年7月23日、8月20日、12月12日、1930年1月18日、1929年12月10日、1930年12月13日。
〔8〕〔14〕〔15〕〔20〕〔22〕〔23〕〔24〕〔26〕〔30〕〔34 〕〔38〕〔39〕〔40〕〔41〕〔44〕〔48〕(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第241、212、249 、241—242、215、222、223、219、248—249、265、241、243、221、232、249、25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
〔12〕〔13〕王霖、高淑英主编:《万宝山事件》第123、13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6〕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五、六册合集,第12、7、278、137、137、31、31、31、23页,中华书局,1986年。
〔17〕《国闻周报》第8卷,第27期。
〔18〕〔29〕(港)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第159、102,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
〔19〕〔21〕(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三卷,第38、33、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3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260、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1〕〔33〕天津《大公报》1930年2月3日。
〔37〕《新民晚报》1930年1月18日。
〔42〕《张学良和东北军》(1901—1936),第174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43〕《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9页。
〔46〕〔47〕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第155、172、 155、156、198、407、415、421、378、240、240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
〔50〕《满铁史资料》,第二卷,路权篇,第三分册,第1063页,中华书局,1979年。
〔51〕(美)付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10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标签:张学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蒋介石论文; 大公报论文; 中苏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