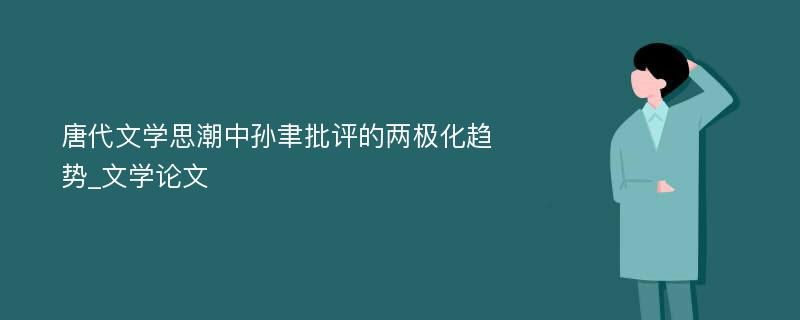
唐代文学思潮中宋玉批评的两极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两极论文,唐代论文,走势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5-0166-06
隋统一中国以后,面对南北文学融合中南朝文学的主流强势,如何抑制南朝文学、保护北朝文学从而维护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隋文帝抓住了南朝文学“浮华”的弱点,早在灭陈之前的开皇四年就下诏曰:“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特别强调要“屏出轻浮,遏止华伪”,来抵制南朝文学的影响。继而其朝臣李谔应势上书,王通更推波助澜著书立说,借君王圣旨,提倡儒家之“大道”,全面否定南朝作家。然而,在隋朝统治的30多年里,南朝的文风非但没有被遏制,相反的是它一直影响着隋代文学。唐王朝建立而后,面对着南朝文风的强势影响,则排除了隋朝出于维护政权目的而持有的狭隘的地域文化观念,为了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南朝影响下的文学现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一种是对先唐文学的彻底的全盘否定,一种是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这两种思潮都以先唐的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申诉自己的文学史学观,力图以史为鉴,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宋玉作为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就自然地成为了唐代文学思潮中的评论对象,并随着评论者立场、观点的不同,自然地形成了褒贬截然不同的两极走势。
一、唐代儒学复古思潮与其对宋玉及其作品的否定
唐代的儒学复古思潮,在有唐一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中都时有所表现,在这此起彼伏的儒学复古的浪潮之中,把文学视为经学的附庸,混淆了文学与泛文学、非文学的不同,用传统的经学理论来衡量文学,用经学的功利理念来要求文学,在这种语境下,宋玉甚至包括屈原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批评。
在初唐,王勃从儒家正统的“诗教”观出发评论先唐文学,攻击“缘情体物”的辞赋是导致国家动乱、衰亡的祸根,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这显然是过激的言论。王勃针对初唐“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杨炯:《王勃集序》)的文风,出于“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的思考,批评六朝以来的淫靡文风,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不加甄别地全盘否定,抹杀了屈宋乃至六朝的文学贡献,就走向了极端。其理论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以汉儒的微言大义的“诗教”观批评“缘情体物”的文学表现,忽略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理论的出发点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2.不顾文学发展的客观事实,夸大了汉儒对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片面批评,以主观印象为批评的依据,则必然导致其结论的错误。3.以曹丕的论断“文章经国之大业”为理论前提,但没有正确理解“文章”的所指,混淆了泛文学、纯文学、非文学的界限,把文学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误以为充足又必要条件的逻辑关系,出现了明显的逻辑错误。
这种不切实际的文学批评,是不可能发挥其引导文学实践之作用的。其实,王勃的否定论也未能贯彻到他的文学实践之中,王勃的诗与文都明显地带有齐梁以来华艳的痕迹。总之,王勃对屈宋辞赋乃至对文学的全盘否定,不仅无益于文学的发展,而且更不利于唐代新文学的创建。然而,由于儒学思想在文学史中的惯性作用,王勃肇起的“屈宋否定”论和“淫风危祸”论,却一直干扰着唐代的宋玉批评。
在盛唐,萧颖士论文以经为宗,但对于文采并不排斥,对屈宋以下的作家也未作一概否定。李华的《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记述了他对屈宋的批评:“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此外皆金相玉质。所尚或殊,不能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此后复绝无闻焉。”李华与萧颖士齐名,论文亦以经为宗,其特点是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作《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寖已微矣。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与李华同时的贾至,论文亦以经为宗,比萧、李更有甚者,他对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创作持有一种更为偏狭的态度,他在《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中说:“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盪而不返。”盛唐儒学复古思潮的先唐文学评论中的屈宋批评,虽仍有初唐王勃的遗响,但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承认屈原、宋玉“文甚雄壮”,“哀而伤”,比之王勃来说,已不是对屈宋以来的作家作品全盘的否定,而有了对形式与内容“二分法”的认识,这无疑是受到了盛唐形式与内容并重的新文学思想的影响,然而,这一进步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他们判断文章的根本标准仍然是“宗经”,并把汉儒评述的屈原的“丽以则”的“诗人之赋”也归纳在宋玉的“丽以淫”的“没其讽谕之义”的“辞人之赋”之中,一概斥之为“不能经”,或因之“六经之道遁矣”。所以从本质上讲,盛唐的儒学复古思潮仍陷于王勃的错误观念之中未能自拔。
在中唐,独孤及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的文学主张,主张文章以宗经为宗旨,以道德为根本,但不排斥形式华美,认同华实相符。然而,他对诗歌和文章的态度不同,对诗歌的“缘情绮靡”是肯定的,他在《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说:“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浸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而对文章则恪守“直而不野,丽而不艳”,绝不可“过”或“不及”的旧说,梁肃作《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引独孤及的话说:“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其症结在于:他初步认识到了诗的文学特征,要比萧颖士、李华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又有了进步,但没有认识到赋的文学特征,仍把赋混同于史论、政论甚或册、令、奏记等非文学文体,表现出对纯文学认识的局限性。更有甚者就是步王勃之后尘,没有尊重文学史事实,全凭主观意识来否定屈宋的文学贡献。稍后于独孤及的柳冕,以“君子之儒”自居,认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并发挥了王勃的“淫风危祸”论,他在《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说:“且今之文章与古之文章,立意异也。何则?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至于西汉,扬、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此说比之王勃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屈宋“亡国之音”之评,与汉人有异,与唐人不合,与今人更大相径庭,不仅违背事实,即便以儒学之观念衡量也言之太过。崔祐甫大历中所作《穆氏四子讲艺录》与学子讨论研学古文之经验,以自身体会说道:“欲以文经邦者宜董、贾,欲以文动俗者宜扬、马。言偃之文,郁而不见。卜商有《诗》序,其体近六经。屈原、宋玉怨刺比兴之词,深而失中,近于子夏。所谓哀以思,刻石铭座者取崔、蔡,论都及政者宗班、张,飞书走檄者征陈琳。曹、刘之气奋以举,潘、陆之词缛而丽。过此以往,未之或知。”其对屈宋的“深而失中”之评,当出于萧颖士“而不能经”之说,亦有汉儒“露才扬己”之意,承人前说,以己言言之,评语用词虽新颖,而所言实为旧说。中唐比较著名的诗人元稹对秦汉至南北朝的诗歌肯定的较多,甚至对“吟写性灵,流连光景”的宋、齐文章,也流露出欣赏之意,而对宋玉则是持批评的态度,他在《楚歌十首》(其四)中说:“襄王忽妖梦,宋玉复淫辞。”“淫辞”虽取于汉人成语,是为用典,但贬斥之义不言而喻,这种态度当源于他“直书其事”追求“实录”的诗歌精神。可以说,中唐儒学复古思潮基本延续了初盛唐儒学复古的文学思想,之所以出现“亡国之音”一类的极端言论,当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国势有关,安史之乱之后衰败之象萌生的中唐社会,让文人感到了国运的危机,有着以文章济世救国的历史传统的文化人的政治天真便又一次重现,满以为“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然而,朝代的兴衰却不是文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晚唐,唐王朝的夕阳西下已让无力回天的儒学复古思潮的追随者感到了无奈,他们于是不再天真地空谈,虽然仍以“宗经”为本,但对先唐文学史的批评已有了从臆断向客观现实回归的趋势。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后序》中说:“嘻!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与忠敬随之,是为理具,与运高下。采古作者之论,以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相如、扬雄、刘向、班固为世魁杰。然骚人之辞,怨刺愤怼,虽授及君臣教化,而不能沾洽时论。相如、子云,瑰丽诡谲,讽多要寡,羡漫无归,不见治乱。贾、马、刘、班,乘时若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奋然以拯世扶物为任,撰绪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则君臣礼乐,教化赏罚,无不包焉。”这段议论,单从屈宋的批评说,首先肯定他们“为世魁杰”,其次认同他们的作品于“怨刺愤怼”之中也“授及君臣教化”,只是“不能沾洽时论”,批评虽仍然有失客观准确,但是语气与初、盛、中唐相比已经平和了许多。
五代之世,天下割裂,北方五代战争频仍,南方十国相对偏安,而文学唯在西蜀、南唐,却又以“花间”、“樽前”之艳词传世。前蜀王衍时有牛希济偶作《文章论》,论及经学、文学与治国之关系,他说:“今朝廷思尧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学,以通经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杨孟为侍从之臣,使二义治乱之道,日习于耳目。所谓观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牛希济的这番论述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个中道出了儒学复古思潮排斥、攻击文学的根本原因。原来儒学复古思潮对屈宋伊始的历代文学的批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是出于“治乱之道”的考虑,以“化成天下”为动机。这便说明,唐代儒学复古思潮对屈原、宋玉的批评违背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失于科学。
总括唐代儒学复古思潮的文学批评,是以“宗经”为理论基础、以“诗教”观为判断准绳的。而这些思想都来源于汉儒,然而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却比汉儒走得更远。于此我们专谈屈宋批评问题。首先,汉人对于屈原和宋玉的批评是有区别的,司马迁认为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宋玉“祖屈原之辞令,终莫敢直谏”;扬雄认为屈原是“诗人之赋丽以则”,宋玉是“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认为屈原“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宋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然而,唐儒学复古思潮的倡导者将屈宋捆绑在一起,又将汉人对二者缺失的分别批评捏合起来,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由宋玉“丽以淫”评说屈宋“导浇源”以“淫风”,由屈原“露才扬己”评说屈宋“怨靡”,由屈原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评说屈宋“皆不能经”,由宋玉“没其风谕之义”评说屈宋“六经之道遁矣”,由屈原不能“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评说屈宋“不能沾洽时论”,甚至张冠李戴,《文选·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扬雄《法言》说:“(屈)原也过以浮,(司马相)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这里的“华无根”是批评司马相如的,独孤及却用到了屈宋身上。这样便完全混淆了原本就有失正确的汉人之说,使屈宋批评陷入了更为严重的混乱。其次,利用汉儒的理论生搬硬套地对号入座。如柳冕“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是从《毛诗大序》“至于王道衰,……而变风、变雅作矣”句化出,而“亡国之音”则是生搬硬套。《毛诗大序》引《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于是柳冕先不顾事实判定屈宋作品“哀而以思”,然后就给屈宋扣上了“亡国之音”的大帽子。如此评论,让人啼笑皆非。汉儒的屈宋批评已有失客观、公允,唐之效颦者就难免错上加错了。
二、唐代新文学思想与其对宋玉及其作品的肯定
唐代文学是在先唐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唐代文学之所以胜过以往任何时期而极大繁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一种新文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先唐文学的优长,开创了一代新的文学。这种新文学思想与儒学复古思潮不同,它不是全盘否定先唐文学,而是最大限度地汲取先唐文学的营养,特别是注意对纯文学成就的借鉴和发扬。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宋玉作为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作为在文学主题、文学表现等方面成就卓越的与伟大诗人屈原齐名的文学家,自然会备受创建新时代新文学的新文学思想实践者的关注。
唐代不同于儒学复古思潮的先唐文学批评最先是表现于史家的文学史批评之中,史学家们出于总结历史文化经验、发展新一代文学的目的,在“艺文志”、“经籍志”或人物传记中,纷纷发表各自的文学见解,评价历史上的文学发展和文学家的得失。就宋玉的批评而言,唐初魏征《隋书·经籍志》评论说:“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其中肯定了宋玉追随屈原创作“楚辞”能够“伤而和之”的文学创作。他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中又说:“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又肯定了宋玉激扬“清风”的文学成就。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评论说:“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宋玉南国辞人,追逸辔而亚其迹;大儒荀况赋《礼》《智》以陈其情,含章郁起,有讽论之义;贾生洛阳才子,继清景而奋其晖;并陶铸性灵,组织风雅,辞赋之作,实为其冠。”此中“追逸辔而亚其迹”则认定了宋玉与屈原齐名的文学地位,“陶铸性灵,组织风雅”则说明了屈宋及荀子、贾生的文学贡献。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评论说:“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几将圣。屈宋所以后尘,卿云未能辍简。于是辞人才子,波骇云属,振鵷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人谓得玄珠于赤水,策奔电于崑丘,开四照与春华,成万宝于秋实,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更作出了屈宋而来“文之所起,情发于中”的总结,不仅指出了屈宋作品抒发情感的特点,而且肯定了陆机“缘情”说所概括的文学的本质特征。总结唐初史家的宋玉批评,他们对宋玉的文学史地位、文学成就及作品的抒情特点都予以充分的肯定,他们的评论完全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关于宋玉的评价,修正了把“论文宗经”作为唯一标准的批评理念,开启了唐代正确评价宋玉的先河。这不仅有利于唐代文人在创作实践中对宋玉的借鉴与学习,而其不恪守儒家旧传统的文学观更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初唐与盛唐之交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公开说明,他的著述完全参照了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明了他和他之前的史家对刘勰文学观的认同与继承。刘知几也有关于宋玉的评论,他在《史通·载文》中说:“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辞》。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也。”刘知几的评论比魏征等史家显得更为具体,他认为《楚辞》中的屈宋之作“不虚美、不隐恶”,屈宋之人“俱称良直者也”,与初唐之王勃、盛唐之萧、李的“宗经”的文学观截然不同。他的正确的评价,源于他对文学与史学及非文学既相通又不同的特征的认识。他在《核才》中说“文之与史,较然异辙”,在《载言》中说“诗人之什,自成一家”,认为文学有着自己的特点;而在上引《载文》中又说“文之将史,其流一也”,认为文与史都具有“惩恶劝善,观风察俗”的批评社会的共同性。这种开创性的对纯文学的认识,不仅有力地纠正了儒学复古思潮论文宗经和泛文学观念所导致的错误的宋玉批评,而且对先唐文学的批评、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到了盛唐,大多数著名的文学家在他们的诗文之中,不仅将宋玉其人其事其作品作为掌故广泛地运用于创作之中①,而且在评论中表现出对宋玉前所未有的称赞和崇敬。李白和杜甫都对宋玉称赞有加。李白《感遇四首》(其四)说:“宋玉事楚襄,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子,恩情遂中绝。”在诗中,李白首先肯定宋玉的人格,称赞宋玉“立身本高洁”,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文士,其次肯定宋玉的文才,称赞他的辞赋“举国莫能和”,是一个文笔不同凡响的才子,第三说宋玉的失意是被谗的结果,与宋玉本人的“立身”及“赋”、“歌”无关。这种评价是全方位的,绝不同于儒学复古思潮中一些尚有文学意识的评论者仅仅是欣赏宋玉的才华。从李白的文艺思想而言,他与王勃不同,不认为《楚辞》是淫风的源头,而高唱“屈平词赋悬日月”;他也不同于萧、李,不认为宋玉背离了六经,“高洁”的评语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杜甫被公认是严肃的诗人,但他对于被讥为“淫浮”的宋玉的评价有甚于李白。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风流儒雅”之评已让世人耳目一新,“吾师”的由衷敬重,更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赞颂,这绝不是意识流式的随笔,当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评论。请看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这首诗突出地反映了杜甫的关于如何继承先唐文学遗产的文学思想,他尊重今人的文学创作,但也主张学习古人,因为古人的“清词丽句”,是宝贵的文学遗产,对于唐代新文学的开创具有借鉴意义,那么怎样学习古人哪?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窃攀屈宋宜方驾”,追攀屈宋,并希望取得与之并驾齐驱的成就,同时也认为齐梁文学存在着不足,故而不能步其卑下轻艳的“后尘”,而要批判地继承。在诗中,杜甫认为屈宋的文学创作是完美的,全不像齐梁文学优劣并存。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的正确的继承态度。如果说,李白还是停留在就宋玉评宋玉的层面,那么,杜甫则是把宋玉摆放在历经千年的先唐文学史之中,在同历代文学家的对比中更为有力地确立了宋玉的文学地位,更为准确地概括了宋玉“风流儒雅”的人品和“清词丽句”的文品。可以说,引领一代文学的李白和杜甫继承了刘勰的文学批评精神和《文选》的文学实践精神,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而杜甫自家亦以宋玉为师,实发前人所未发。如此之标榜,如此之提倡,其号召前无古人,其影响必震动文坛。从李白、杜甫的时代开始,儒学复古思潮对宋玉的否定虽然仍然存在,虽然还在延续,但已是晚秋蝉噪,绝不能代表唐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了。
在中唐,李白和杜甫对宋玉的赞誉、特别是杜甫师范宋玉的表述,得到了许多文人的认同,诗人把宋玉视为文学创作中可资学习的楷模,散文家把宋玉视为文学史中的一流作家,并相继提倡,以为指导,旨在提高文学创作水平,打造一代文学。孟郊在《送郑大夫鲂》中概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勉励同道时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勉矣郑夫子,骊珠今始胎。”他认为宋玉与李白同样有“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的大气魄,同样有“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的大手笔,同样有“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的大情怀,是文学创作的典型和榜样。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阐述文章义、理、词的关系,强调“词”的重要意义时说:“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子、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这里将宋玉列为先秦两汉优秀的文章家之一,推举为后学者学习的“师归”;将其文看做是“自成一家”且“不泯于后代”的范文,是能以“词”最大限度表现“义”和“理”的典范。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更加缩小了秦汉一流作家的范围,更加突显了文学的特征,他说:“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他认为“文学”的独特在于文之“奇”,“文学”的价值在于传之“远”。并认为宋玉的作品正具有“奇”“远”的特征,是秦汉以来传世的优秀作品的代表。孟郊、李翱、皇甫湜的宋玉评论,可以说是杜甫“师范宋玉”之号召的响应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可以想象“师范宋玉”在当时大概已成为一种文学时尚。中唐时,虽说儒学复古思潮又一度泛起,有许多古文家以“宗经”的传统理念批评宋玉,甚至出现了“亡国之音”的宣判,但事实上并未真正地“打到”宋玉,宋玉在中唐的文坛上,尤其在中唐贞元、元和以后文学向感伤、艳情、奇险风格转型之时,仍然有着不容忽视、不可低估的影响。
晚唐文学是承继中唐后期偏重于个人抒情、追求艺术之美的思潮发展而来的,绮丽、冲淡、超逸、香艳文学成为流行的时尚。在这一时期,更多的宋玉批评则表现为对宋玉才华的称颂与追慕。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写道:“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李商隐《宋玉》赞曰:“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日落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可怜庾信寻芳径,犹得三朝托后车。”于濆《巫山高》也称:“何山无朝云,彼云亦悠扬。何山无暮雨,彼雨亦苍茫。宋玉恃才者,凭云构高唐。自重文赋名,荒淫归楚襄。峨峨十二峰,永作妖鬼乡。”这些诗中的“艳”、“擅才华”、“恃才者”,都是强调宋玉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华。杜牧写其才华,重在突出其对李、杜、韩、柳的影响;李商隐写其才华,重在强调其高出唐勒、景差等同时的辞人;于濆写其才华,重在指出其“凭云构高唐”的艺术想象。温庭筠《河中陪帅游亭》说:“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满座山光摇剑戟,绕城波色动楼台。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飘荡似寒梅。”也是称赞宋玉的才华,并且自叹不如,而羡慕不已。在晚唐也有对宋玉的其他方面的批评,汪遵《郢中》诗,“莫言白雪少人听,高调都难称俗情。不是楚词询宋玉,巴歌犹掩绕梁声。”是借其对古代民间“巴歌”流传的贡献赞美宋玉既有大众情结,又有“曲高和寡”的文士情结,立意唯新。胡曾《咏史诗·兰台宫》:“迟迟春日满长空,亡国离宫蔓草中。宋玉不忧人事变,从游那赋大王风。”是对宋玉忧国忧民之情怀的肯定,立论坚实。这些诗与晚唐儒学复古思潮的“不能沾洽时论”的评说不同,以下些细节歌唱了宋玉关注世人时事的士人品格。
总结唐代新文学思想的宋玉批评,是在以一种向前看的意识审视先唐的文学史,注重的是对先唐文学成就的总结和运用,它没有去与儒学复古思潮进行理论的争论,去争辩是非曲直,而是专注于将先唐文学经验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努力于新一代文学的创造。因此,新文学思想的宋玉批评,并不像儒学复古思潮只作笼统地简单地“宗经”与否的判断,而注重作家与作品、内容与形式、文学性质、艺术表现、语言修辞等文学经验的总结,诸如“风流儒雅”、“立身高洁”的文学家修养,“圣贤心”的社会责任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创作态度,“情发于中”的抒情特征,“清词丽句”的语言,“奇远”的风格等等成为其宋玉批评的着眼点。这是贴近文学的文学批评,这是贴近文学自身特征与规律的文学批评,这是促成唐代文学发展与繁荣的文学批评。张少康、刘三富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论述“初盛唐的文学理论批评”时说:“简单地说唐初新文学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是在反齐梁文风中发展起来的,是不确切的。唐初新文学思想不仅是在充分继承齐梁文学的优秀成果、批评齐梁文学的错误倾向中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反对对齐梁文学全盘否定的错误文艺思潮中逐渐形成的。”[1]笔者基本赞同张、刘的观点,但觉得他们只着眼于齐梁文学为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从笔者对唐代的宋玉批评分析来看,他们的表述应当修正为:唐代的新文学思想不仅是在充分继承先唐文学的优秀成果、批评齐梁文学的错误倾向中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反对儒学复古思潮顽固宗经、否定文学特质的错误文艺思潮中逐渐形成的。如果这一修正是正确的,那么,唐代以新文学思想为基础的宋玉批评和儒学复古思潮的宋玉批评孰是孰非就不言自明了。这便又从理论的角度证明了,唐代新文学思想对宋玉及其作品的肯定才是唐代宋玉批评的主流,并代表着以文学理论观照作家作品的正确的宋玉批评。
注释:
①据我们初步统计,在《全唐诗》和《全唐文》中提及“宋玉”或“屈宋”的诗文就有141篇,引用宋玉及其作品中典故的尚未计算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