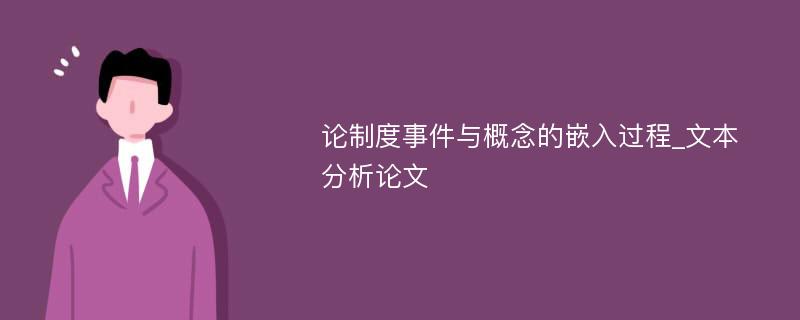
论制度事件———种观念嵌入过程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过程论文,事件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7)05-0009-06
制度虽然早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论题,但学者们对制度的理解却一直并不一致。传统的观点基于社会及其秩序建构的视角,认为它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1]7,或者是“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2]373,对于制度的形成则在“人为设计”或者“自然演化”上立论。这种观点可视为“客观论”,因为它将制度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新近的研究者正在进行角度的转换,将制度视为在个人心智中存在,并为个体所遵奉甚至崇敬的共享信念。这种看法可视为“主观论”,因为它强调共享观念在个体大脑心智中的存在。本文认同后者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事件”的概念,认为制度作为一种共享信念,是通过特定的“事件”契机的媒介而嵌入个体头脑,并在这种场景的再生中逐步强化,最终构成人们心智模式一部分的。制度生成是人们在制度事件中观察、思考、模仿等能动学习的结果,制度事件是制度生成的关键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们发出了要用“制度”来统摄社会科学的宏大意图①。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在面临经济学帝国主义攻城略地的情势下,也不甘落后,纷纷发展各自的制度理论。这些名目繁多的制度学派在抱持着“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共同结论的同时,对制度的作用、特征、演化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产生了“搭便车”、“路径依赖”、“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理性选择”等新兴的学术语词,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空间。然而,在这场涵涉广泛的制度话语下,一些有关制度的关键问题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解决。比如,关于制度的产生、演化及其变迁方式,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定论。
在早期的政治哲学研究者眼里,制度生成主要在“人为设计”和“自然演化”两种方式上展开讨论②。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如诺思等人,在基本认同上述观点的同时,特别强调“斗争、革命、征服与自然灾害是阶段的制度变动之源”[1]107。另一些制度经济学活跃分子,则注意到偶然事件(即小概率事件)的重要性,并以此解释对路径依赖的打破。与此类似,新兴的政治学领域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提出了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历史时间”、制度变迁的“常规时期”与“非常规时期”等理论阐释③,认为非常规时期(关键时期)的历史发展对制度变迁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以上理论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制度生成的探索,然而,审视这些理论,都具有宏大历史的特征,对制度观念向生命个体心智的嵌入过程尚无微观的、具有说服力的阐释。比如,“关键节点”是指的导致制度变迁的宏大历史场景(如抗日战争),但它本身并不能说明人们为什么认同新制度。同样,“偶然事件”向人们说明了打破路径依赖或制度锁定的方式,但并没有对偶然事件中制度如何生成作具体描述。总之,现有理论对新制度观念的内在转换机理没有清晰的说明,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缘于将制度视为一种纯客观存在的局限性。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些有深远见地的学者开始了学术思维的转向,开始关注人类的观念、信念、行为的心智模式的重要性。早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诺思就明确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已经向我们的感知投降,向我们的心智投降,有必要回到1920年哈耶克《感知的秩序》上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同时也不知道我们的心智。所以,我们必须从认知科学领域,从心理学领域再度挖掘对制度的理解”[3]。与此同时,青目昌彦在抱守着制度的博弈论经济方法的同时,也提出了制度是一种“共享信念”的结论。哈耶克更是早就提出了非理性的人类感知对制度的重要性。经济学的历史制度学派也强调了文化、历史与制度的关系,这些观点都深化了对制度生成过程的理解。
同样基于对制度的观念特性的思考,本文提出“制度事件”的概念,并结合认知心理学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对制度生成进行微观意义上的探讨。青目昌彦认为,制度是“经济行为者就现实中的博弈如何进行而达成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4]。本文推而论之,将制度理解为长期演化形成的,潜存在人们心智中的关于行为规范的共享信念。而制度事件则是指的制度生成的机缘——通过特定事件的示范,制度规则得以播扬,制度价值为人们广泛接受,从而促进制度权威的迅速形成。本文所表达的理论预设包含以下相互依存的几点:1.制度生成是外在观念和知识嵌入个体大脑,并构成我们认知模式的学习过程。而制度事件作为制度运行的“焦点”行动,知识实践的瞬间,以其具有的强信息、强映射、高烈度、情景化的“示范”特征,成为知识嵌入或者制度生成的基本模式。可以说,制度事件是演绎制度价值和规则的剧场,它创造了一种共同的判断结构。2.制度在本质上具有行动、实践的特征。外在的制度安排或价值诉求,只有通过特定制度事件的媒介作用,才能嵌入人们的头脑,成为一种观念共识。制度作为一套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体系,是无数代人通过长期的历史实践,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对周围事件进行观察、思考和模仿的结果。3.制度生成是将制度内置于当事人的认知结构,为当事人提供行为菜单的过程,也是一种制度传统,一种新的信仰与行为范型的形成过程。而通过制度事件的心理“定格”,使制度同人们的感知形成一种“非理性的情感连接”,从而产生一种近似于条件反射式的行为模式。如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所言,“一旦一种范型被当作‘自然的’而接受,‘自然的’几乎就相当于规范的和强制性的。”[5]267
二、制度事件:一种社会认知学习模式
在认知心理学看来,人类知识的获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间接经验。两者各有不同的知识形成样式,前者通过直接的感性体验,获得难以言传的默认知识(tacit knowledge),后者通过对榜样的观察、模仿、感染,形成映射效果,产生替代强化,实现对个体心理的嵌入。在这两种学习方式中,由于人类个体面临的特定时空与情景局限,直接经验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次要的,间接经验获取知识的方式是主要的。社会学习是一种典型的基于间接经验的学习,它通过对“榜样”的观察,将怎样反应才能被组合成新的反应模式的信息传递给观察者。看到榜样受到惩罚,与之相似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而看到榜样从事某一被禁止的活动而未产生不良结果,观察者的抑制就会解除。通过这一过程,“榜样”加强或者削弱观察者对已经学到的行动的抑制,并逐渐内化为认知符号,嵌入记忆,实现对自我行为的指导和调节,最终造成示范行为持久、可再现表象的产生。这样,就形成一个榜样观察→嵌入记忆→重复行为的关系链。正如美国认知心理学家班杜拉所言,“示范被证明是形成抽象的行动或依据法则的行动的高度有效之法。”[6]42
制度的生成是一种基于榜样示范的间接学习过程。无疑,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然而,仅仅存在一套外在的行为规则并无意义,制度建构的实质是要得到生命个体的认可,形成有效规制个体行动、甚至变成个体行为的一种条件反射的内化知识。而这一机能的最终实现,关键是要使制度在实践引致的行动中体现其存在。因此,制度在本质上具有行动的特征,是在行动中产生、修正、沉淀、变迁的。制度的生成是一个实践理性(行动)的过程。而制度事件正是这种提供“行动”、形成典型示范、展示榜样作用的特定场景。人们通过对制度事件的观察、模仿,形成关于制度的认知地图与行动模板(template),建构一套内在的自我监控体系,制度就在制度事件的重复刺激中逐渐嵌入人们的心智并最终制度化。更有甚者,制度性留存物通过与特定事件的关联,常常使制度获得某种“身份”特征,从而演化成为具有典故意义的象征符号,成为历史叙事的基本格式。
制度事件作为制度博弈的典型场景,一般而言,因其“实例”特征而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轰动性,因而形成一个引致关注的特定表演“场”,成为一个关于制度的信息密集场所。制度事件发生时,往往体现出完整的情节特征,从而形成深刻的情节记忆,并以其特定的时空场景,过程的鲜明性和精细性,构成思维的兴奋点,从而形成持久的记忆。
制度事件作为一种外在的信息嵌入,个体大脑心智能否充分吸纳这种外在信息,受信息冲击的烈度、强度、速度与振幅、强化的连续性等多种因素影响。这里,可以归纳制度事件作为社会认知学习模式的几个基本特征:
1.信息资讯越发达,制度事件的播扬速度越快,制度的认知学习越方便,制度型构过程就越短。制度生成实际上是在促进一种制度传统的形成。希尔斯认为传统的形成必须要“延传三代以上”。但在现代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一论断将打折扣。现代通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导致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从而形成对制度传播的一种“高带宽”交流,同时也导致人类储存信息的能力日新月异及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大,这些都使制度事件及其所标识的新制度观念能够得到迅速的传播,从而很快促进新的行动范型的形成。
2.制度事件的矛盾对抗程度越高,内部涉及相关因素越复杂,对信息接受者的心理撞击越深,制度化过程越快。制度事件作为一种榜样的机能价值的大小,要看其魅力,准确地说,看其影响力。冲突剧烈的制度事件由于其强烈的映射和情绪震撼特征,形成浓烈的信息编码和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从而加深了对个体心智撞击的烈度。个体在对这种强力事件的观察和学习中,获得了激活和支配自身行为的能力,从而迅速推进一种新的行动模式的形成。
3.同一个制度领域发生制度事件的频度,影响制度传统的形成速度,即使是通过制度事件“验证”已经形成的制度,也需要不时发生的制度事件检验其行动能力。社会学习是某些情境连接的结果,而行动的重复或频率将会强固其联结。同样,制度传统的型构受制度事件出现次数和持续强度的影响。在制度事件中所型塑的个体记忆模板,在时间的延展中会逐渐弱化与模糊,因此,一种制度即使在制度事件中已经生成,但此后如何长期没有制度事件对其效力进行检验,时间长了,人们就有可能对原来的制度淡忘,或者对制度的“执行力”表示怀疑。而制度事件的接连发生和制度效力的多次实现,将会强化个体的记忆,从而增加制度的“刚性”④。
三、制度事件的功能
我们将制度生成理解为外在规范对个体心智的嵌入,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向结构的转换。制度事件的功能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促进观念的嵌入。这里分四种情况来说明,其中前两种属于以文本为基础的正式制度变迁,后两种属于以观念共识形成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变迁。
(一)兑现制度文本
很多制度建构的第一步,是设计与制定制度文本。这种文本制度的出现,当然也是时势要求与价值传播的结果,是制度企业家顺应社会发展要求,致力改革的结果。然而,文本制度的出现及其向社会的传播,并不意味着制度权威化过程的完成。由于它尚未经历“实例”的验证,客观上人们可以对文本制度的可实施性表示怀疑,主观上制度还没有实现对个体的强力信息输入,尚未深度嵌入我们的心智,其记忆痕迹是简易、形式化、易于消磨的。可以说,仅仅有文本规定的制度并不是真正的制度,而只是一种“沉睡的制度”。而检验文本实效性的就是制度事件的挑战。通过制度事件,制度获得了一种“可执行”、“必须执行”的特征,并将文本的简单语义记忆(episodic memory)转化为具有特定时空背景的情节记忆(semantic memory)⑤,从而强化记忆的刻度和个体的体验程度(involvement)⑥。这种制度生成是“文本+事件”的过程。
对上述理论可以作一个更为现实的描述。文本制订之初,由于它具有不针对具体人的“匿名性”,人们在文本的通过上容易达成“抽象的”同意,但一旦有行动者“触网”,文本就获得了同某一个具体人际网络的关联,“犯规者”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对制度的态度就会转变,这时,“犯规”事件就会成为考验文本制度能否现实化的重要契机。在这种“以身试法”的过程中,只有文本坚守方获胜,才能说制度经历了“事件”的考验,制度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制度权威得以形成。可以说,制度文本规定的内在化是通过制度事件来实现的,制度事件是使制度普及社会传播,升华社会影响的必经过程⑦。
(二)催动制度降生
制度生成之后,随着时间的流转,组织结构的日趋细密,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导致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一过程中,原初制度的价值合理性逐渐丧失,新的制度价值取向日渐形成,但严重的路径依赖使制度转型发生困难。这时,通过什么方式来终结旧制度就比较关键,它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对已经编织成形的制度网络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具冲击力,具有高浓度、弥散性和深刻影响力的特定事件就会成为新制度破土而出的催化剂,成为人们认知制度的加速器,它打破制度的均衡态,击碎制度的既定网络结构,将新旧制度之间的价值紧张充分展现并迅速促成新型制度权威的形成,开启一个新的制度化时代。对于这种特定事件,制度经济学称为“偶然事件”,历史制度主义学者称之为“关键节点”或者“关键事件”,社会学则称之为“创始性事件”或者“克里斯玛事件”,其实都是描述了制度生成的一种类型,本文将之理解为“事件+文本”的制度生成方式。也即是说,在制度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致力于制度创新的政府顺势而动,将事件所表达的价值观迅速固定为制度文本。而此时,由于有制度事件在先,可以理解为现实的制度已经存在⑧。
对于靠制度事件打破制度锁定并导致文本出现的情况,制度事件是制度诞生的一个触发点。事件发生时,潜存在制度需求背后的各种利益、矛盾比平常更充分显示出来,是人们更深刻、全面的认识制度,感受制度价值,获得制度知识的特定时期。在认知心理学上,这是一个导致人们心理活动痛苦而激烈的“心理扰动期”,是人们的创造性能力发挥最为充分的瞬间,因而也是知识嵌入过程中心理升华的特殊时期。
(三)形塑制度传统
在制度理论家看来,制度不仅体现为以文本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体现为以观念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同样,制度生成未必一定体现为剧烈的、大规模的导致文本出现的正式制度变迁,它可能还体现为观念、意识与价值渐进转变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制度事件也未必总是体现为强烈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事件,它还可以表现为一些细小而琐碎的制度事件。其深刻的制度建构意义可能要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段才能够揭示。这些无数的制度事件形成制度变迁的河流,并在其超过临界点之后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制度,是一种通过渐进的边际调整逐渐实现的观念转换过程,是在“事件流”中实现制度建构的。历史久远的制度事件因为人们的口耳相传还将还得一种非理性的神圣特质(如基督诞生),构成文化与民族性格的一种心理性因素,并最终通过信仰、惯例等方式表达社会结构的一种向度。所以,有学者认为,制度文明的发展史是“千万次微小的反叛”的结果。“只有当认可一项经验的人数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该经验才会转变为一项内在的制度”。而“成功的制度会向越来越大的参与者群体‘殖民’”[7]121。这可以理解为一种“事件+事件”的制度生成方式⑨。
(四)引领制度走向
在社会认知心理学上,较高的社会地位往往能提高榜样行为的暗示(cueing)作用。出名人物的地位、智力与社会行动,对于观察者而言,具有更大的机能价值,从而有利于示范行为的泛化,形成普遍性行动准则,推动新型制度原则的生成,使之成为一个不可更移的刚性规定,并进一步提高新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神圣性和持久性。这种情况对于带有文化特性的深层次制度变迁有重要意义。对于已经嵌入民族心态深处的带有文化特征的制度传统,制度变迁要改变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其改变起来往往难度很大。这时,带有克里斯玛人格特征的伟大人物,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种意义重大的新传统,从而构成本文制度事件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改变,本文将这种克里斯玛领袖人物以自身模范行动推进新制度传统形成的方式称为“人格+事件”的制度生成方式⑩。
四、探讨一种制度生成的艺术
林德布洛姆在论及理性选择的局限时说:“人类的条件是:小的头脑,大的问题”[8]91。这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在面临一些复杂、深刻而宏大的问题时所存在的知识局限。制度的建构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对于现代制度发达的国家而言,制度可能表现为一种遗传信息,一种长久、自发、内生的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制度欠发达的国家而言,制度往往是外生的,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关键节点冲击后逐渐出现的,制度生成是一种外在观念嵌入大脑的过程。由于面临逼拶的时空场景,在制度欠发达国家,制度建构作为一种观念的移植和嵌入是非常艰难而又关键的事情。有感于此,政治学家罗斯金强调指出:“制度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它是由许多能力或强或弱的人小心地创造出来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原因指导其形成。他们常常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在一个纷乱的世界里,几乎没有比发展有效的政治制度更高的目标。”[9]278-279
制度建构是一种主客观因素互动的过程。在承认制度生成客观性的前提下,作为人的积极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活着的带有强烈求知欲和行为冲动的人类将最终确定制度。制度生成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规则与制度文本的设计产生,更是一个在人的行动引领下的制度化过程,是其现实价值的获得及其权威地位的树立过程,也是制度信息的社会传输过程。作为制度企业家的政治精英,是制度建构的主导力量。制度事件蕴含着制度建构的重要契机,制度企业家能否把握制度事件的契机,不仅考验政治家的能力和远见,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制度发展有幸还是遗恨的重要标志。
作为制度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政治精英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1.把握事件契机,促进制度生成。既然制度事件是制度生成过程中的常态,是制度生成过程中一种普遍的、促进制度权威实现的必然现象,那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把握的,利用并把握这种现象形塑制度,是卓越改革家的伟大之举。技术高超的政治家应该在制度事件发生时,趁势而动,迅速将其所表达的价值和规范“定型”,从而实现一个国家制度文明的跃进。反之,如果把握不好这种契机,就有可能拖延制度发展的进程,甚至会出现“逆制度化”现象,使原本尚未奠基的制度结构其生命力和价值意义重新消解,从而损伤人们对建立一个相应的制度社会的良好预期(11)。
2.根据情景需要,创造制度事件,促进制度发展。根据认知科学的观点,一切精神现象和智力活动,都可以最终还原成生理事件或物理活动,可谓之为心智事件,这种心智事件是一些体验片断进入一种实践的活动结构的过程(12)。制度事件其实也是一种心智事件,其实质是要创造一种特定的场景,通过“深刻印象”促进制度对人们的观念嵌入,这种场景是可以设计和创造的。制度企业家应该把握或者创造制度事件的场景,推动观念嵌入,促进制度发展(13)。
3.领袖人物以行动来形塑制度。领袖人物特别是克里斯玛人格领袖对社会、国家、民族秩序的建构常常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其特定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引导和推动制度传统的形成。必须强调的是,有时他们所要建构的新型制度,会受到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力,甚至也同他们自身利益相背离,这将构成对领袖人物人格、勇气、眼界、创造力和民族责任感的巨大考验。如果他们能够逾越这些物质性或精神性的障碍,愿意以身作则致力于新型制度的建构,国家的制度文明将得以跃进(14)。
收稿日期:2007-08-22
注释:
①1997年9月,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举行,提出要通过跨学科的制度分析,在新千年带来一次社会科学的整合,构建一个综合性、具有通论意义的理论体系。见吴敬琏主编《比较》第4期,第177页。
②比如密尔认为,关于政治制度一直存在着“两者互相冲突的学说”。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制度是一种发明创造的事情,人有权选择是否制作,以及怎样制作或按什么模式去制作。”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制度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它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参见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7页。
③参见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Critical Junctures,the Labor Movement,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另参阅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美国宪法设立了总统弹劾制度,由于极少动用这项制度,美国人把它形容为“生了锈的大口径枪”,以至于有人对这一制度是否顶用产生怀疑,并生出了试法和抗法的冲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对这一制度的挑战,而各方合力导致的制度维系方的胜利,进一步提升了这一制度的威望。参见[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下集,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⑤认知心理学家将记忆分为语义记忆和情节记忆,也可以称为语词代码和意象代码。语义记忆是对一般知识和规律的记忆,与一定的概念内涵意义有关,情节记忆与一定的时间、地点、事件的具体情景有关,是关于经验、事件的具体模态和细节描述,与视觉记忆、意象组合、回忆相联系。见[美]贝斯特:《认知心理学》,黄希庭,张志杰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⑥1949年3月,在中共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干部在建国后要保持廉洁、拒腐防变的政策和制度性规定已经形成,但事实上并没有“自然”阻止部分干部的腐化变色。使这一文本制度变成具有震撼力的现实是1952年对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的处以死刑,是它形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相关规定的制度化权威。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可以说是建国初期廉政制度形成史上的制度事件。
⑦必须强调的是,西方国家在长期的、耗时的历态过程(ergodic process)中,已经形成了“文本制度必须遵守”这样一种以信誉为依托的元制度规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制度事件对文本实现的意义。但在制度后发国家,形成这一元规则具有迫切的重要性。俄罗斯国家转型之初,经济立宪之所以难以形成,就是因为被锁定的自我强化的核心机制是非诚信的,这种非诚信经过数代人的复制和演化,也会变成一种传统,进入人们的内在基因。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
⑧2003年3月发生的孙志刚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以事件推动制度创生的制度事件。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打工,被收容遣送站收容,并被毒打折磨致死,在新闻媒体的介入下,事情披露出来,经过互联网的传播,引起国内外震动。后来在民间社会的呼吁下,在中央高层的强力干预下,事情终于得到了解决。该事件最终废止了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而终结了实行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并以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而代之。参见刘杰主编:《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04年》,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
⑨在西方,法治的社会传统已经形成,司法及法律精英在社会中具有权威地位,故在其制度发展进程中,制度事件经常以案例及其判例的方式出现,比如1873年法国的布朗哥案件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美国历史上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实质上实现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确立的米兰达规则(Miranda right)等都具有创始意义。参见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
⑩美国建国初期华盛顿推动的总统连任两届的宪法惯例的形成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首先,华盛顿开创了这个范例,其后的几位继任者作为有影响的开国元勋也积极遵循这一先例,第三届总统杰斐逊甚至明确地说,“华盛顿将军树立了8年任满后自愿退休的榜样。我要遵循这个榜样,而且再有几次先例就会克服掉稍后任何人力图延长他的任期的习惯。或许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意向,通过修改宪法来确立这个做法”。因此,“我决心在我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引退”([美]梅利尔·D.彼得森编辑:《杰斐逊集》:下,刘祚昌、邓红风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1333页)紧随其后的总统如麦迪逊、门罗等都效法华盛顿,从而使总统连任两届的惯例形成。
(11)1980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届中央领导集体,决定以公开司法审判的方式完结“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从而以典型事例的方式推动了“文革”后中国司法审判制度的初步建构。反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已经确立了一些良好的制度原则,如实行党内民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实行法制等。但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使中共八大制度化努力的意义被消解。当代中国也有不少制度事件机会,贺卫方就认为,“陈希同案件如果能以非常法制化的方式解决,将是一种制度变革的契机。”(贺卫方:《具体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12)见章士嵘著:《认知科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13)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徙木取信”的故事便是一个创造制度事件的典型。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推行改制的过程中,为了形成政令颁发而必行的氛围,用“徙木重赏”的办法来树立制度权威,“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14)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实现完全退休,就是对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事件。可以设想,在邓小平的典范行动之后,今后任何一届领导人都不太可能再回到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状态中去。邹谠在描述邓小平此举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时说“他时常表示的完全退休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制度化的进程也可以得到完成,只要他能使自己成为可有可无的人,只要他能够顶住一些人的劝阻和恳求,把自己的权力、权威、威望逐渐转移给一个在严格建立的制度工作的集体领袖集团。”(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3-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