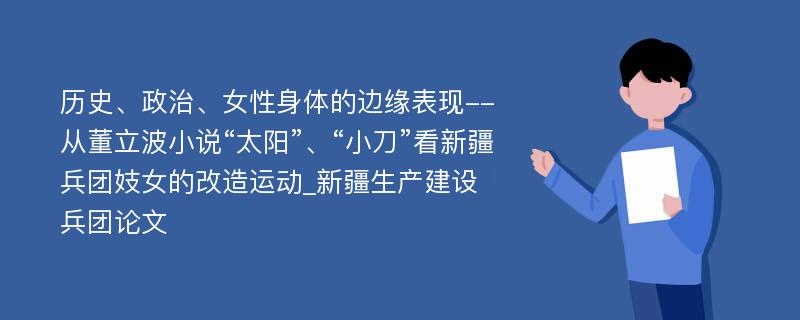
历史、政治与女性身体的边地呈现——从董立勃小说《烈日》、《箫与刀》看新疆兵团妓女改造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地论文,新疆论文,兵团论文,烈日论文,妓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3)01-0039-06
关于妓女题材的小说创作,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对妓女形象的塑造也有所不同。而妓女形象一直是中外文学家笔下极力关照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古至今,点缀于多数名家名作中,《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日出》中的陈白露、《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复活》里的玛丝诺娃、老舍笔下的月牙儿、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等,关于这些妓女形象的塑造与描写,在作家们心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知和审美定位,即她们虽卖身却不卖心,她们虽外显放荡但内有纯情,她们有着双面的性格与双面的人生。因此,对于妓女形象的塑造,在大多数作家的视野里,并非简单地从伦理道德层面去评判妓女们的好与坏,或是对妓女这一职业本身的批判,而是从时代、社会等多个角度去看待历史上产生于旧社会的娼妓制度。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娼妓制度,从本质上来看是残害妇女、毒害人民的人类的罪恶,这种制度危害社会,犹如鸦片一般致使一个个善良的女性走向堕落的深渊,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妓女改造运动是从制度上对娼妓制度的废置与消除。
然而,旧社会的娼妓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中国初期的妓女改造运动,尤其是身处这场运动的当事者——妓女们。长期的娼妓生涯,不仅使她们丧失了自食其力的生存意志和从事劳动生活的生存技能,还养成了她们依赖于这一职业的生活惯性与思维定式;况且,长期以来人们在传统道德伦理层面上形成的对娼妓制度和从事娼妓活动的妓女的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批评的态度,使她们在面对社会时也持有消极、颓废的态度。正是这些现实因素的存在使得新中国初期的这场妓女改造运动变成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场妓女改造运动,当代许多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如陆文夫《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就是在旧社会里饱受摧残的妓女,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的教育改造,在政府、社会以及自身的多重努力下实现了自我救赎,并获得了最终的幸福归宿;苏童《红粉》中的妓女秋仪与小萼也都被卷入这场教育改造的洪流之中,历经命运的起起伏伏;董立勃《烈日》中的雪儿和《箫与刀》中的冯可雪等五姐妹同样是这场改造运动的当事者,她们却各自走向不同的生命归宿。文学叙述尽管带有艺术加工的痕迹,却也是反映历史真实的一面镜子,作家们对这场妓女改造的文学叙述虽有想象的成分,但也从不同的层面间接地向人们呈现出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场妓女改造运动的某些镜像。
一、关于妓女改造运动
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学,文学是历史的载体,历史是文学的血液。历史也绝非是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的简单而轻松的跳跃,隐秘之中自有其契合之处,文学创作就是用独特的历史话语在书写。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妓女改造运动,活动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巨大,社会影响面极广。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废娼运动,各地在短时间内纷纷宣布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娼妓制度,目的是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一壮举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改造社会的决心和能力。”[1]1951年11月25日,上海市政府明文下令禁娼,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军曾豪情万丈地说:“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绝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刚进去(指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2]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和政府根除遗劣千年的娼妓制度和对妓女实施改造的决心。这场涉及全国范围的妓女改造运动,同样也波及地处边疆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然而,历史并非可以简单地加以复制,不同地域自然有其特殊的叙述话语,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妓女改造运动则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与时代情结。
从政治角度上看,妓女改造运动的实施目的在于体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优越性,在于体现党和政府对待妇女政策与旧社会的根本性差异,从而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主张;从现实角度上看,国家通过妓女改造运动,积极安置、解决改造好的妓女的出路问题,力争给这些旧社会的受害者寻找一个好的归宿,让她们在新社会能过上正常人享有的生活与幸福。而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身处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带,其事业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员补充。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难题,同时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实施的妓女改造运动和妥善安置改造好的妓女政策,“1955年3月,新疆地区要求上海送1500名改造好的妓女前来工作。经上海市委政法办批准,市政局会同新疆来沪接领的干部选送出改造好的妓女,以及教养院中养大的成年孤儿等1284人去新疆参加工作,支援边疆建设”[3]。同年4月,上海政府把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组织她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些西上天山的女兵其实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而当时鲜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4]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去边疆参加工作或参军是这些被改造过或已改造好的妓女们最好的选择,新的生活环境,新的生活人群,或许会让她们忘记苦难的过去,重新开始一段正常人的新生活。然而,当时国家在安置这些改造过或已改造好的妓女时也存在一些政策性缺陷,为了保证她们以后不再从事娼妓行当,“须函告当地政府和群众继续进行教育和改造”[5],也就是说,即使被收容的妓女获得安置,她们的个人档案也随即转到当地政府的公安部门,她们的行为会被告知当地的政府和群众,她们始终被贴上“妓女”这一标签,无法从根本上走出过去的阴霾,也为她们再次融入社会带来巨大难度。在这里,不论国家还是政府,只能从宏观层面去把握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和对待整个妓女改造运动,而要彻底实现自我的解放,只能依靠妓女们自我救赎,不断净化、升华自我灵魂与精神。当然,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实施的妓女改造运动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新中国要将妓女“全部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而成为“全世界没有先例”的“值得大写特书的历史事件”[6]。大规模的妓女改造运动在当时的中国,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党和政府势必要彻底废除祸害中国千年的娼妓制度。“当妓女作为特殊的被压迫阶层被纳入到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中去之后,国家主动介入的‘改造’落实到妓女身上,就并不是消灭,而是一场‘革命’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的‘救助’;这种‘救助’既体现为使妓女摆脱生存困境,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主体性的唤醒与重构为依归,重塑其精神境界,诞生出既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又具有主人翁感觉的新人。”[7]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开展的妓女改造运动,不只是一场改造妓女、废除陋习的简单运动,更是一场革命与人道主义的救助,让那些旧社会娼妓制度的受害者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做真正的国家主人。
二、董立勃独特的文学世界
作家董立勃作为第一代屯垦者的后代,他对新疆兵团的生活非常熟悉。在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董立勃都在竭力书写兵团第一代人的命运起伏,他的小说作品多数以描写新疆兵团社会及屯垦战士的戍边生产生活为对象,从还原历史的角度叙写了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疆建设兵团初期的生产生活状况,传达出一种屯垦战士的艰苦创业的时代精神。因而,西部的粗犷、军旅的豪气、流浪的传奇、女性的柔情尽显于董立勃小说的字里行间,尽管其小说故事情节不是很复杂,甚至可以说叙事结构比较简单,但文本背后却深藏着太多太多复杂的内容与意蕴,令人回味久远。身处西部边疆的作家董立勃,其在小说创作上可以说是个成功者,面对脚下的这片大地,他并没有被“西部”这个地理意义上显得更广的概念所驱使,身为作家的他跳出了模式化的西域风情描写,只是“单纯的”写自己愿意写的,写自己所要表达的,写自己灵魂深处那些无法挥去的生命记忆。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下的文学书写,使得他笔下的新疆兵团显得更加宏大辽阔,更加美丽妖娆,更加温情动人,即使是对近于原始的生产劳动的叙写,也尽显出一个别致的新疆兵团,一个意义上更真实的新疆兵团。
作家董立勃以其特有的历史叙事视角,走进新疆兵团建设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流金岁月,构筑了一幕幕独具边地色彩的文学世界。他的小说创作总是以特殊的地域、年代为叙事背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以50-70年代为时代背景;一个特定的地点,新疆下野地的小农场;一个基本的事件,逃离不掉的惨烈的暴力事件。”[8]逐渐形成其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董立勃的文学叙事的焦点不是关注当下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是聚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兵团最初创业年代,这种创作倾向,不是他刻意回避当下叙事,而是基于其与生俱来的新疆兵团的“下野地”情结。“下野地”对于作家董立勃来说,不仅是个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存在,还是曾经童年、青少年时期的生命体验与人生记忆,更是一种精神的凝聚、一种无法割舍的灵魂栖息之所。作家从小就生活在叫“下野地”的团场,这个团场是遍布天山南北无数个团场的缩影,童年的记忆都源自发生在屯垦战士身上的、日常生活的以及他们情感上的那些丰富而复杂的事,他目睹了发生在团场里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像他母亲和姨妈一般的女性们坎坷多舛的人生经历,而这些恰恰给正值童年的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生命烙印;青少年时期的他经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批斗和残杀场景在他心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使他无法回避人性之恶给社会及人们带来的悲哀与残酷。成年之后的他,生活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高考落榜,创作初期不尽如人意,经商失利等,这一连串的人生遭际让他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而思考所得就是其独特文学世界的出发点,也正是在历经磨难之后的董立勃,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我的文学创作之旅。因而,董立勃的小说创作既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别的历史背景及其特殊的人生经历的结晶,更是其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度思考之后的艰难抉择。
对董立勃而言,其小说中关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书写在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其在塑造的过程中更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董立勃在其小说中,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切入,赋予同一历史背景下程式化的女性多样化的人生,通过特殊年代下的“下野地”女人、组织原则下的“下野地”女人与暴力下的“下野地”女人的多重书写,构成了对那个特殊时代、特定地域中女性形象的完美刻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和平解放之后,进驻新疆的解放军官兵绝大部分就地转业,开始他们保家卫国、屯垦戍边的军垦人生。就地转业的解放军官兵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性,为了使他们能够安心扎根边疆、建设美好家园,国家以政府行为的方式从山东、湖南等地招了几大批女兵,分配到遍布新疆大地的各师、农牧团场,以帮助解决解放军官兵们的配偶问题,安定他们扎根边疆的军心。董立勃小说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这样的尴尬境遇与现实处境中,他把叙述的焦点聚集在“下野地”这个并不特别的基层团场,开始讲述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那些带着领章帽徽人们的坎坷人生。男人与女人的故事似乎不新奇,一个男人与一个妓女的故事也没什么特别,而一堆男人与一群妓女的故事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侧目。有一群身份独特、身世惨痛的女性尽管同是穿着军装,却不能和普通的女兵享受一样的人生待遇,她们似乎带着几分神秘,却又有几分悲凉,她们就是被改造过或是已被改造好的妓女。她们中间没有一个自愿去当妓女的,她们是为生活、为社会所逼迫的,或因为贫穷,或因为恶霸流氓,她们均来自黑暗的旧社会,是封建的旧社会把她们推进了娼妓这个肮脏的火坑。不容置疑,本质上她们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她们虽是妓女但更是黑暗旧社会的受害者。当她们走进新社会,我们的党和政府力争把她们从旧社会的“鬼”变成新社会的“人”,让她们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让她们做一个对垦荒事业有贡献的人。而对妓女改造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叙事在董立勃小说中并不多见,主要体现在其小说《烈日》与《箫与刀》中。之所以董立勃在其小说世界里出现妓女的身影,并非是他的突发奇想,或说是他的特立独行,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与渊源。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妓女改造运动波及新疆兵团,而以新疆兵团为基本叙事背景的董立勃小说也或多或少有着这一历史事件的点滴痕迹;作家董立勃对妓女形象的塑造与描述,既丰富了西部文学人物长廊,也从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曾经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妓女改造运动。
三、妓女改造运动的边地呈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组织,“它以亚军事化组织形式将就地转业的解放军和部分起义官兵组织起来,结构和建制几乎沿用和完整保留了军事化组织的基本形态:师、团、营、连、排、班、组。随着这种军事组织形式的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也顺延下来。在这里服从上级的命令是理所当然的,个人服从组织是不容置疑的”[9]。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女性资源严重短缺的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兵团,婚姻资源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分配(或再分配)是新疆兵团初期无数青年男女爱情悲剧、命运悲剧的始作俑者。作家董立勃小说大都是描写屯垦战士的戍边及生产生活的,而他少有的关于妓女形象的叙事则显得分外珍贵,尤其这些妓女形象也被赋予了多重的社会意义。
(一)“身体”的工具性
作为妓女题材的小说文本最引人关注也是运用最为广泛的符码是“身体”以及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性”。学者黄金麟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身体”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身体的形成不单涉及一个生物体性的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力量,正试图透过它们所能掌握的细微管道,在肉体毅然存在的前提下,主管或影响身体的建构过程”[10]。因此,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妓女改造运动,既是医治妓女们生理上的疾病,也是拯救她们灵魂上的病状。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说,“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女性的欲望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11]。女性生理上所具有的特点,与男人的对抗,必然会使她们屈服于他们,进而成为他们享乐的工具;而作为妓女,正是因为她们所从事的这一职业的特殊化,使得她们自然沦为男人的玩弄工具。董立勃在其为数不多的小说文本中,并非是特地为了写妓女而作,多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妓女改造这一问题上,可是依旧逃不过对妓女的“身体”与“性”的描写。小说《烈日》中的雪儿、《箫与刀》中的冯可雪等,她们既是旧社会造就的妓女,更是经历新社会改造过或已改造好的来开荒队从事垦荒事业的女人。生活在旧社会大房子里的冯可雪们,充当的是男人享乐的工具,可她们中没有谁甘愿做男人取乐的工具,“家没有了,房子没有了,亲人死的死,跑的跑。一个人要活下去,就得有地方住,有饭吃,有衣穿。到处跑,找住的,找穿的”[12](P16)。旧社会里她们被生活所迫,一步步沦落为妓女,最终成为男人取乐的工具。《烈日》中的妓女雪儿,从大上海来到开荒队,本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在与佟队长尽享鱼水之欢中她以为得到了幸福,以为已寻觅到了真正的爱情。可当这份所谓的幸福与爱情遭遇到权力试图对“身体”进行占有时却变得虚无缥缈,雪儿的“身体”被当作拉拢权力的砝码,佟队长不仅将雪儿拱手让出,还说“你完全可以就当被狗咬了一次,你反正已经被狗咬了多少次了,也不在乎被狗多咬一次”[13](P167)。自始至终,佟队长没有忘记雪儿背后“妓女”这一标签,雪儿只是他满足性欲的“身体”工具。冯可雪们的无奈、雪儿的最终死亡,只因她们是“妓女”(哪怕是改造好的也不例外),正是这一身份标签的存在,使得在权力驱使下的男人们对她们“身体”的欲望更加肆无忌惮,她们“身体”终究挣脱不了充当男人取乐工具的宿命。
(二)婚姻选择的被动性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诞生初期,和以往的“战斗”不同的是,年轻女性不能单凭个人意愿选择婚姻对象,其必须是“看上谁了要向党支部汇报,不能自己胡来,必须由组织出面安排男女见面以至结婚”[14],而这却和新疆兵团这一特殊的组织体制密切相关。伊里加蕾说:“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同商品无异,她们的价值由男性主体的需要、欲望而定价。”[15]这些女兵是政府从内地募招来疆给老兵解决婚姻问题的,这一出发点决定了她们身份的特殊性——满足欲望的商品,从本质上剥夺了她们自由婚恋的权力,从而助长了男兵们对她们的占有欲。这些女兵作为政府给男兵们“买来”的商品的这一特殊性,让男兵们自然认为占有她们是理所当然的,这也从根本上注定了这些女性婚姻选择的被动与不幸。而身为妓女的雪儿、冯可雪们作为被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力图改造的对象,本来就低人一等,她们在从旧社会的“鬼”改造成一个对社会有意义、对垦荒事业有贡献的人的过程中,更加举步维艰,自由难控,又何谈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力。
《箫与刀》中的果子、木子是妓女,是新社会教育改造的对象,婚姻选择对她们来说就是服从组织,上级要求开荒队解决士兵们的个人问题,“原以为娶老婆是个人的事,没想到一下子变成了任务,变成了有政治意义的任务”[12](P155)。至于让谁娶老婆,谁有资格娶老婆,不是个人说了算,依旧要听组织的。因为老班长是开荒队的老革命,他有资格娶老婆,木子要服从组织安排嫁给老班长,“我是开荒队的人,我听组织的”[121](P163),这就是被改造过的木子的婚姻观,无可奈何之下被组织决定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被赋予组织化的层层管理,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兵团诞生初期的婚姻状况。然而,这种被选择的由组织安排的婚姻并没有给木子甜蜜与幸福,等待她的却是走向死亡。当老班长在新婚之夜看到身上一块布都没有遮的木子时,“他就像被雷劈了一样,先是身子一阵震颤,接着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嘴巴动着,好像要说什么。可是不等话语出口,整个人就站不住了,瘫在了地上”[12](P172)。诚然,在革命年代由于革命斗争的激烈与残酷使得大多革命者忽视了身体、甚至性的存在,当真正的女性身体出现在眼前时,变得慌乱而不知所措,甚至因过于激动而导致生命的死亡。随着老班长的死,木子也因此含冤而死。相比木子而言,果子似乎是幸福的,经由组织介绍嫁给了牟首长,有了和木子不一样的婚姻生活。董立勃小说中所叙述的开荒队的婚姻,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组织的事。那些从内地招募进疆的年轻女兵和经过改造后的妓女们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单纯的”,她们骨子里还是相信婚姻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道,而当她们只身来到新疆兵团,一个人无亲无故,自然也就把这份信念托付给组织,也就自然顺从了“组织之命”。
(三)爱情的悲剧性
董立勃小说中关于西部爱情的文学叙述,总是带着几分苦涩与艰辛,历尽坎坷与酸楚。在一望无垠的大漠戈壁荒滩上,那些脱去戎装的军垦战士与招募进疆的女兵及改造过的妓女们共同演绎出边地世界男男女女关于爱情的悲欢离合。作为“无根的漂流者”,荒野上年轻女性更需要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家,她们坚守着一份执著,力图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下野地”,谈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奢望,如同镜中花、水中月,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挡住她们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与向往。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真正爱情,对那些曾经饱受男人伤害的妓女们来说,同样有着无比的诱惑力,尽管她们早已不再相信爱情,但是她们从内心深处渴望真爱的到来,即使为这份真爱去死,她们也无所畏惧。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不会轻易坦露真爱,爱情对于她们来说是无比神圣而崇高的,“在她们心里边,爱是天上的云,只能在空中飘来飘去,就算是有时候看见了,也离自己很近了,可真要伸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着。一阵很小的风,就会把它吹得没有了影子。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她们什么都说,就是不说那个爱字”[12](P65)。当真爱来临时,她们又不知所措,不敢面对真爱发生的事实,可一旦真爱遭遇夭折,她们却用女人仅有的尊严,甚至生命去捍卫。
《烈日》中的雪儿,一个倔强而十分懂得自重的女人,尽管曾经饱受男人的伤害,但她却始终去期待属于自己真爱的到来。起初,像雪儿这么漂亮的女人来到开荒队,佟队长不敢相信,因为漂亮的女人是不会来到“下野地”的。那些从山东、湖南来的漂亮女兵在乌鲁木齐一下车就被挑走了,最后到下野地的女兵几乎没有像雪儿这样漂亮的。满心疑惑的佟队长最终从刘主任那里知道了雪儿的真实情况,而此刻佟队长所呈现出的是,“你现在和营地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一样,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垦荒者,这里所有的男人,都是你的兄弟,这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你的姐妹。只要你不说,这里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去”[13](P93)。由衷的默许让雪儿分外惊讶而感动,也从此时开始一份爱情之花从雪儿的心中悄然绽开,“那时候,说让我们到新疆,一个个哭天喊地,像是要来送死一样。要是知道这个地方有你这样的人,不要逼,我自己往这跑”[13](P102)。正当雪儿感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爱情来到身边的时候,却被骆副场长到开荒六队来而彻底改变。当骆副场长借口和她谈工作,借酒逼雪儿与之发生关系时,雪儿奋力反抗,毅然拒绝了骆副场长的无理要求,此刻的雪儿试图坚守和佟队长的爱情,可最终却被佟队长背叛,“你反正已经被狗咬了多次了,也不在乎被狗再多咬一次”[13](P167)。这件事让雪儿彻底清醒,她也彻底认清了佟队长的邪恶嘴脸,她的心变得比古尔图河的冰还要冷。曾经背负的“妓女”标签并没有从佟队长眼中抹去,当权力与感情发生冲突时,佟队长自然会放弃雪儿,走向权力与职位。当认清了佟队长真实面孔之后,雪儿毅然坚决地和佟队长断绝了来往,开始了和吴克的真爱之旅,在佟队长凭借着权力给吴克定了反革命罪,公开了雪儿的妓女身份后,雪儿最终选择与吴克双双跳入雪山谷底。雪儿来自大上海,是经新中国改造过的旧社会的妓女,曾经的遭遇使她备受伤害,她也因此变得异常敏感,她悉心地维护着作为女人仅存的尊严,正如她说,“我不要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把我当一个真正的女人”[13](P122)。一个妓女追求真爱的征途如此艰难而曲折,但她不需要凌驾于人格尊严之上的施舍的爱情,终以悲剧人生而谢幕。
四、结语
“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做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16]建国初期那场轰轰烈烈的妓女改造运动,如同奔腾的洪流席卷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这场运动的当事人——妓女们作为旧社会的受害者却经历了无比艰难的人生转型。废除娼妓制度,拯救妓女于水深火热之中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也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具体措施。这场妓女改造运动尽管带有妇女解放的光环,但也被打上了政治的时代烙印。董立勃的小说《烈日》、《箫与刀》呈现的就是这场妓女改造运动当事人所经历的不同的人生遭遇和不同的人生归宿,从中夹杂着权力对这场运动至高无上的掌控,而操纵权力组织者的个人欲望凭借自身的乔装打扮,个人欲望被披上了“组织”这一合法的外衣。这些权力的掌控者打着“改造妓女”的幌子,以权谋私,对这场妓女运动的少数当事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甚至是生命的消亡,而这些也是权力操纵下的“妓女改造”的另类结果。妓女改造的实质是为了让那些旧社会的受害者通过教育改造,从心理上走出旧社会的阴影,让她们在新社会的阳光下重新做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从而最终成为新社会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建设者,真正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主人翁。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处边地,但依旧是这场改造运动的实施场域,尽管其中存在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新疆兵团的妓女改造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这股浪潮不断前进,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这里赢得了尊重,获取了新生的希望和信心,从这里开始了新社会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历程。
标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论文; 董立勃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