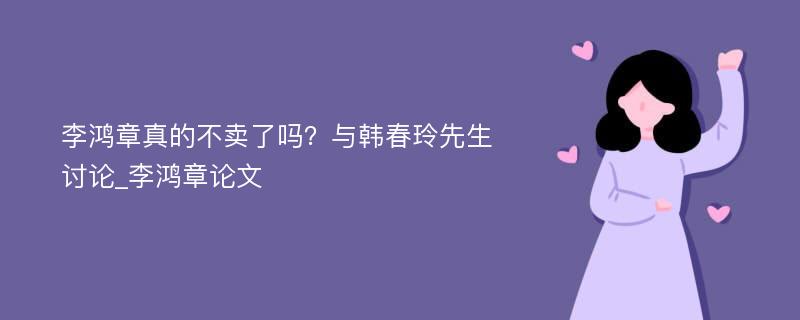
李鸿章真的没有卖国吗?——与韩春玲老师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师论文,李鸿章论文,韩春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仔细看了《历史教学》2004年1期上海大同中学韩春玲老师《以“真的是李鸿章卖的国吗”为例,看中学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一文,首先我非常赞赏韩老师在历史教学改革的创新精神及驾驭课堂教学的应变能力。尽管我未身临现场,从学生在课堂上的热烈发言,不难看出这是一堂较成功的研究性历史课。不过,我仍有几个问题,想与韩老师探讨。
问题一:应慎言“李鸿章无卖国之行”的论断。关于李鸿章卖国的史论,并非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已故的老一辈史学大师范文澜、翦伯赞老先生等都有著述论证。毋庸讳言,这些老学者、治学的严谨态度、博大精深的史学功底都是令当代诸多史学研究者敬仰的。他们用详实、严密的考证所得出的中国近代史的结论岂能轻易推翻?故至今全国的历史教材无论什么版本,尽管提法与过去有较大变化,然都没有公开平反李鸿章的内容,即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近十几年虽有大篇幅为李鸿章平反的文章见之报刊,但几乎全从洋务运动的角度为其说话的,对其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味妥协退让政策、签署丧权辱国条约与贪污受贿之间的联系等污点,却从清朝国势衰弱的大背景为其开脱,而对早先论著中有关李鸿章卖国的史料则多半采取回避态度。韩老师引用的陈旭麓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从外交到战争》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均离不开这几种思辨方法。我承认历史学界有为历史人物翻案成功的例子,譬如秦始皇、曹操、武则天,那是封建社会与当今不同时代对共同的史实评判标准观念变化所致。而关于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评判标准,这一百年来莫非真的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李鸿章的翻案是在未能否定卖国事实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以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来否定其卖国罪行,又使历史重入了实用主义的窠臼。难道历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那么,李鸿章究竟有无卖国罪行?这与马关签约时奴颜媚骨是否有某种联系呢?范文澜所引用的一段史料很有说服力: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奏参李鸿章折:“……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至于这一史料的可信度百年来从未遭到质疑,不然,就是李鸿章不说,其亲朋好友也早就为其辩解了。还有,以张謇的人品也不会干诬陷人的卑鄙勾当。要不然,我们不能想象:为何伊藤博文要把原清朝谈判大使张荫桓、邵友濂赶回,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在谈判席上竟然会如此的卑躬屈膝。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全权大使,当此民族危机来临之时,理应据理力争,哪能任由日本狮子大开口!近代国际战争因战败而签约的例子甚多,从未有《马关条约》如此苛刻的。李鸿章签约时的窝囊表现,区区草芥平民也能做到。这只能理解:张謇等人的奏折内容,恰是李鸿章之软助。况前有曾纪泽虎口索食而使沙俄改定条约,后有杨儒以生命保东北疆土事做反衬。曾、杨赴俄谈判时的险恶处境并不亚于李鸿章,以被迫无奈为其鸣冤叫屈难以说得过去,说他“尽了自己的力量使得中国少受损失”更是违背客观事实。(有关杨儒的事迹不妨参阅顾廷龙主编的1982年版《中国近代史词典》:“……1896年任驻俄、奥、荷公使。1900年,沙俄趁义和团运动之际出兵强占中国东北,次年一月被任为全权大臣,赴俄淡判。谈判中,沙俄提出侵占东北条款,迫使其签字。杨儒不畏强暴,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拒绝签约。1902年2月,死于俄京任所”。)
问题二:“生十一”所用的材料《中俄密约》李鸿章受贿300卢布之事不是孤证。除当时的《字林西报》,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提供的沙俄政府的宫廷档案:中俄密谈前,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唐斯基公爵即得俄财政大臣维特同意后,与财政部总务厅长罗漫诺夫、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罗特斯坦商定:由华俄道胜银行拨出三百万卢布,作为行贿专款,名曰“李鸿章基金”,由沙皇尼古拉二世特降密旨批准。该计划是:(中国允许俄国建造自西伯利亚至海参崴)铁路合同批准时付一百万,路线看定时付一百万,铁路完成时付一百万。此材料在《搜狐网·中国近代史资料·中国龙志》上也能查到。否则,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早就为李平反了,根本不必等到现在。
此外,还有《合肥地方志》为实证: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李鸿章用巨额资产买房置地。合肥东乡半数以上的田地和房屋都成了李氏的私产。死后,其子在东郊大兴集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享堂’。李家至今保存着李鸿章去世后其子孙遗产分配的合同。合同中提到李家在合肥、巢县、六安、霍山都有大量田产,在扬州有当铺,在庐州府、江宁、扬州、上海等地有大批房产”。今天上海华山路的“丁香花园”就是李在世时为其小妾丁香购置的第一座具西洋风格的豪华别墅。李鸿章有横财,在当时是人人皆知的事,故民间流传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确实,中国近代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是丧权辱国的根由,但李鸿章是那拉氏一人之下腐败代表的第二人,对此难辞其责。
问题三:整堂课上,如聂劝犁先生在点评中所提到的:韩老师明显偏向“褒李方”。这就使得本来可以更加精彩的一堂课大打了折扣。其表现为:上课伊始,韩老师强调的是“论从史出”。可在辩论过程中,当褒李方美化了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的表现而贬李方正处于劣势时,却不去点破。作为局外人一眼就能看出,韩老师实际上已给李鸿章下了不是卖国贼的结论。这样做对贬李方来说是不公允的。虽然大同中学的学生思辨能力较强,但在功底悬殊的历史教师面前,他们已无招架余地,其结果自然是褒李派大获全胜,贬李方一败涂地。历史课的教学目的之一是为了弘扬民族正气,毕竟李鸿章并不是那种廉洁自律、体恤民情的清官,更不是气节崇高、忍辱负重的爱国志士。即使无卖国行为,褒扬此类历史人物的做法也有违历史教学的宗旨。
总体上而言,我认为聂幼犁先生的点评基本是客观的,也较中肯。尤其在点评中显示了知识广博、文采丰茂、细致入微的专家风采。这里,我怀着敬意就历史上“国”的概念与聂先生商榷。诚然,历史上可称为“国”的有多种,对此我并无疑义。一个王朝是国;一个政权也是国;甚至封建帝王把“朕”当作国家的象征。清朝一度也代表中国,不过这些都是狭义上的“国”,或者是“小中国”的概念。与聂先生稍存异义,我更看重的是广义上的“国”,即“大中国”的概念,即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千万平方公里疆土之泱泱大中华。“大中华”为我中华各民族共有的国,而非某朝、某家、某人独有的国。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王朝都不过是中华大好江山一段时期的掌管者,而非所有者,此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大中华”与“小中国”之间的权益有时是矛盾的,有时却又是统一的。由此,我们是否能这样定义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凡能够为了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一切的是爱国主义者,“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等都是值得讴歌的爱国志士;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就是卖国主义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那拉氏,为做洪宪皇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袁世凯,为得到“西原借款”不惜出卖东北、内蒙、山东大量权益的段祺瑞则都是应受鞭挞的卖国贼。自然,我说李鸿章卖国,表面看他是出卖了清朝的疆土,实际上却是卖大中华民族的权益。
上述仅仅是我一家之言。限于涉足史学的面实在太狭窄,所发议论极有可能存在纰漏,兴许是否谬论也未可知。如有不礼、不敬之处,还望韩老师、聂先生海涵。更望能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