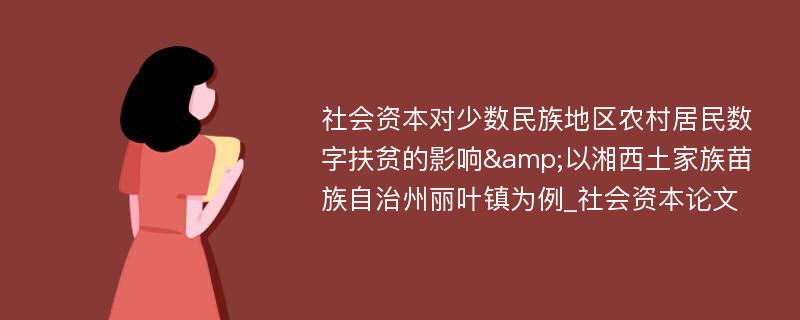
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数字化脱贫的影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里耶镇的田野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家族论文,湘西论文,研究报告论文,田野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的数字化程度差距呈现逐步拉大的趋势。2009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0681亿,占全国网民的27.8%[1];2010年底,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25亿,占全国网民的27.3%[2];2011年底,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36亿,占26.5%[3];2012年底,农民网民规模达到1.56亿,比例略升到27.6%[4]。虽然农村人口上网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重总体上是下降的。
城乡居民间数字化差距显著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田野研究和案例分析,讨论社会资本能否对缩小差距产生影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以期为数字不平等研究及信息扶贫政策的出台、执行与评估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本研究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作为中国社会数字化贫困现象的主要人群。数字化贫困(digital poor)是数字不平等的学术话语体系从数字鸿沟研究中继承而来的概念。现有研究提及影响数字化贫困的社会资本相关因素包括社会位置[5]、感情支持[6-7]、社会网络[8-9]、技术支持[10]、共同体验[11]、社会机构环境[12-13]等。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社区成员及组织获取和利用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有积极影响,内部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也称联结型社会资本)和强关系(strong ties)正在推进ICT在社区内部的应用进程[14]。社区成员间的强关系可以直接通过为社区技术中心(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CTC)创造好的口碑,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光顾其公益技术培训[15]。不仅如此,同事、亲戚和朋友等强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还能够通过技术支持、感情强化(emotional reinforcement)[11]和期待[16]为社会个体提供数字化脱贫的动力和竞争力。已经实现数字化的朋友也作为一种新型社会资本吸引着其社会关系进入数字化世界[9]。同事间的日常交流活动也可以为社会个体提供非正式信息,由此而积累的数字化媒体知识帮助其解决实际IT难题[11]。
内部社会资本可以使外部植入社区的公益信息技术项目真正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外部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也称桥接型社会资本)能够为社区带来外部资源和支持。社会资本通过社区技术中心将其携带的资源转换成个人、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虚拟力量(cyberpower),这三种力量会回馈社区,自下而上地推动民主和社会包容等价值观的实现[17]。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都能够在社区技术中心公益项目的发起和维持方面发挥直接作用[18-20]。社会资本的存量会对社会个体学习数字化技能的速度产生影响,一个人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广度越大,其学会使用数字化媒体的速度就越快,从而获取在线服务的可能性越大[21]。
现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公益社区数字化项目和社会个体实现数字化脱贫是否存在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差异性,已经在社区、个别群体以及社会个案层面得到初步的印证。但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村社区及其居民的机理还没有得到解释。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社会资本是否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实现数字化脱贫存在直接影响?社会资本能够多大程度上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数字贫困状况?
研究对象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数字贫困阶层。以下任意一种或三个条件皆缺乏的情况构成本文界定的数字贫困阶层:(1)尽管能够接入ICT,但缺乏动机、愿望和数字化素养;(2)拥有动机、愿望和数字化素养,但无法接入ICT;(3)拥有动机和愿望,但是缺乏数字化素养,并且没有条件接入ICT[22]。摆脱上述三个条件的行为,即被我们看作数字化脱贫。
社会资本的含义是社群成员凭借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获取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各类资源的能力[23]。具体形式包括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24]。前者指从组织或社群内部获取资源,后者指从组织或社群外部获取资源[14]。本研究以家庭为标准,将内部社会资本界定为从家庭成员中获取到的社会资本;将外部社会资本界定为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社会资源的社会资本。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田野研究法,通过访谈、电脑培训实验、介入观察、问卷和行动式研究(action research)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的居民进行研究,调查时间为2012年5月12日至5月27日,其中电脑培训历时3天,访谈历时12天,笔者收集到15份培训实验情况表、34份访谈记录以及64份有效问卷。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首先是发放100份问卷,回收问卷67份。之后根据数字贫困阶层的标准筛选出合适的15人选进行培训,每场电脑培训的人数是4人,地点为当地的网吧。当培训结束后,进行培训实验效果的访谈。另外根据有效的64份调查问卷抽取部分进行深入访谈或者偶遇方法进行深入访谈。
3 电脑培训项目与案例分析
3.1 里耶镇基本情况介绍
里耶镇位于湖南省武陵山腹地,湘、鄂、渝、黔四省市在此交界,隶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与王村、浦市、茶峒并称为湘西四大古镇,依酉水河而建。据龙山县政府网站公布,里耶镇现有居民7556户,27 119人,其中75%左右为土家族,另有一部分苗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少部分。由于经济、政治等条件限制,农村与城市间的信息差距扩大。里耶镇由于其自身的地理位置较偏僻,交通阻塞,经济发展滞后,因此互联网的使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可能有重要价值。
据当地居民介绍,从来没有民间志愿组织进行过电脑方面的培训,只有2009年政府部门曾经在林业局进行过电脑培训,但一期毕业之后便取消,再无任何其他社会机构进行过相关的电脑技能培训。通过实地走访发现,2009年至今龙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直在进行免费的电脑技能培训,通过当地电视台、网站以及干部下乡宣传免费电脑培训的相关信息,但在里耶镇能知道与此相关信息或者直接参与培训的人却少之又少:2009年接受培训的200人次中,里耶镇居民参加培训的不超过5人。民间志愿组织的缺乏导致村民获得外部型社会资本的机会大大减少,也是导致数字贫困的重要原因。村(社区)里公务以纸质告示公开,或是由村(社区)干部直接挨家挨户通知,极少或者不用网上公开。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得知,里耶镇现有网吧11家,大多分布于正大街两旁,有大的广告牌标示,网吧内有饮料和方便面供应,其中几家网吧有被子提供给通宵上网者。
此次田野调查地点为里耶镇。初步制定计划是对里耶镇的样本居民进行培训,地点为网吧。选择网吧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是当地的网络覆盖率不高,网吧是唯一适合培训的场所;其二是所选择的网吧空间开阔,管理较好,不存在安全隐患;其三是受访者愿意去网吧这样的公共场所接受培训。
3.2 里耶镇电脑培训结果和研究发现
笔者直接进行一对一培训观察和访谈的人为15人,其中包括1名医生、1名网吧清洁工、2名私营业主、1名退休公务员和10名耕田的农民。参与培训的15名人员均是自愿参加培训并拥有学习和使用信息技术的动机和愿望,但却缺乏使用信息技术的技能;或者是拥有学习和使用信息技术的动机和愿望,却没有条件接入ICT设备;尽管有4人家中有笔记本电脑,但却因为缺乏使用电脑和网络的能力而无法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缺乏数字化素养。总之,培训的15人均符合“数字贫困”定义,他们基本能代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数字化基本状况。
在实验培训前预设的培训内容为招工信息的查找、邮箱的申请与使用、如何在网上销售柑橘等农作物,但参与培训的人员主动提出要学习更多的内容。因此根据参加实验者要求,电脑培训的主要内容有:电脑的基本操作(开机关机、鼠标使用、输入法的选择、USB接口的使用、DVD驱动光盘的使用、对话框的移动)、文件的下载与保存、网站网页的浏览(网页的选择、打开与关闭)、娱乐聊天视频通话、浏览在线休闲娱乐视频网站、如何在网上写博客微博、如何玩小游戏(农场、斗地主)、如何在网上购买东西、如何开网店等。以上所有的培训内容均为接受培训的居民主动提出,这是符合社会资本中社会资源的概念定义的,并且培训人员与接受培训者之间属于外部社会关系,即受训者通过培训人员这一类桥接型社会节点而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社会资本在ICT使用过程中不仅提供上述技能方面的直接支持,还带来感情支持和共同体验。5月13日观察过程中,接受培训的W告诉笔者:
“我今年50多岁了,大女儿在外地参加工作,儿子还在上大三,退休在家没事可干,闷得慌。白天就在外面走走,晚上回家看看电视,一天也就过去了……家里有电脑,但就会开机关机,看电视(这里是指看视频的意思,笔者注)也很无聊。我儿子叫我申请QQ,这样可以视频聊天,你帮我弄下可以吗?还有那个上网买东西,我看见别人买了件衣服很漂亮,那个我也想学……”
当天参加培训的P是一位年轻时尚的妈妈,在外打工多年,回家结婚生子,孩子还未满周岁。她主动要求培训人员教其如何写博客、上网买东西,以前打工时已经学会使用QQ聊天,曾经上百度搜过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当谈及为什么参加此次培训时,她告诉笔者:
“打工回来后没有工作,结婚后也一直在家带小孩。我们这边交通闭塞,什么消息都传不过来,外面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待在家里没事,女人还是得有自己的事业,经济上得独立点,不然在男方家里也很吃亏,他不会说你什么,但是就是觉得没有自己赚钱花钱那么随便……我想自己开个网店卖东西,我们这边的特色农产品很多,像腊肉、芍粑粑、包谷、辣椒都很不错,还有橘子什么的,可以放到网上去卖……这次的培训很好,你们也为我带来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对我的帮助很大……”
在第三天的电脑培训中有一位中年女性Z,同其他电脑初学者一样,首先教她基本的电脑操作,她显得十分兴奋,每教她一项她都会主动要求自己单独完成一次,当操作正确的时候她会等待培训者的表扬,然后很骄傲地说:“原来电脑不难啊”;当忘记所教步骤的时候,她会眼巴巴地望着培训者不停的问:“我是不是很傻啊?”她用键盘输入数字时小心翼翼、用劲十足。需要输入文字时,她犯难了:“这怎么办啊,我都忘光了,不会啊。”旁边有人提醒说Z高中成绩很好。Z说:“高中的时候特别刻苦,天天都只看书背书,老师发的资料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那时候还没电脑、手机这些,资料就只有几本书。复读了两届,还是没考上,同班同学几乎全都考上了,就我一个没考上……现在他们有当老师的,当干部的,反正都是走得很好的人……特别怀念高中,当年的同学写了本书《那年·那月》就是写的我们高中,还有照片。可惜我的照片都被烧了,一张也没留下……现在,就想好好地学学电脑,其实我什么都想学,学会之后在家里买台电脑,也可以和以前的同学在网上联系、看看他们……”
从以上的3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培训人员培训的内容多是应参与实验的人员要求而设定的,不仅是利用数字化技术解决工作、生活上的困扰,同时也把此次培训当成是获得感情支持和共享共同体验的机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缺少足够的经济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更多的是依赖于外部社会资本。经过15天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我们发现一个现象:越是贫困的人,对电脑的欢迎程度越高,在培训过程中更愿意提问。通过深度访谈后得知,这类人在平时生活上很少求助于人,经常被动接受一些帮助,但是却对电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认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小,仅限于同村之间,十分缺乏内部资本,所以当有一个很好的社会节点来连接时,他们往往收获更大。
由于研究时间和研究资源的限制,笔者无法直接证明外部社会资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改变现状,脱离数字化贫困。同时,信息技术的掌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短短的几天培训不能让15个人全部实现数字化脱贫。但是在15个人的实验中,也有经济能力较强并且学习能力较强的3个人能直接证明通过免费电脑培训(属于外部社会资本),已经实现数字化社会中从数字贫困阶层向上层的流动。在后期的培训效果访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H女士和其先生已经申请开淘宝网的店铺,并且能自己在网上做广告、与同类商家价格进行对比等,日化产品的网上销售将逐渐变好;W女士告诉笔者,她现在也能跟儿子视频聊天了,没事的时候也会上网看看新闻、看看电视剧;最值得一提的是Z女士,在后期的访谈过程中,Z女士欢快地告诉笔者现在她已经能独立上网找东西、聊天了,也希望以后自己的先生能学会在网上管理村务,考虑到在网吧不大方便,准备几天内就买电脑。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F村村民几乎全部搬到县城居住,他们既非移民搬迁,也非共同商议决定,而是一家一家向城里搬,5年之间基本上全部来到县城或租房子或买房子,并且在县城时也是在同一个社区内。我们曾探讨过其中的原因,有两点:家中有孩子,为了孩子的未来,得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读书;亲友在县城,县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家中有20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比没有的家庭更抵触电脑,但想买电脑的人数也更多。同时,这些在家带孩子的妈妈也大多能成为舆论领袖,经常能传播各种信息。笔者曾考虑过:虽然现在他们仍处于数字化社会的贫困阶层,如果是对这些带孩子的妈妈首先实现数字化脱贫,是否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数字化不平等的问题?笔者也认为,农村小群体之间联系紧密,生活状态相似,内部社会资本在实现数字化脱贫过程中发挥作用,有可能一个人实现数字化脱贫,会带动所在群体的数字化脱贫。因此,外部和内部社会资本对不同时期的数字贫困阶层有不同的价值。
接受培训的15人均是自愿参与实验。有10人是直接与笔者联系参加电脑培训,有1人是因为笔者在其店铺购买纪念品了解到相关信息而主动要求接受培训,有1人是在借用场地时了解到相关信息而主动要求接受培训,有3人是因为做访谈时了解到相关信息而想要参加。对于以上的15个人来说,本次培训相当于外部社会资本对其起到的作用。笔者曾对这15人做了深度访谈以及实地考察,发现家里只要有孩子,孩子全都会上网,但并不大愿意教自己的父母或者祖辈们上网,久而久之长辈们也不愿意向家中孩子求助,大多数会选择向朋友寻求帮助。同样的,从今年的春节至今,15人仅送人情的平均份数为30份左右,其中最少的为15份,最多的高达50份,大多数送礼都是本镇人;走亲访友的次数也较多,亲友也多在周边,近的仅一墙之隔,远的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但是,这种“强联系”并没有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贫困状态的改变带来多大的好处。几个接受培训的人说:身边能上网的朋友并不多,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大家的水平差不多。从这点来说,“弱联系网络可能比强关系网络更有利”[25],并且“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弱关系所联系着的社会资本”[26]。但是,如果说强联系便于内部交流沟通,当小群体内部人员有人实现数字化脱贫之后,那么终将带动群体其他人实现数字化脱贫。
4 结语
通过15天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电脑培训志愿者作为外部社会资本对数字化脱贫——尤其是提高数字化兴趣、素养和技能并且提供共同体验和情感支持——有关键的推动作用。虽然由于电脑太贵而没有购买,但是当地公共网吧较多,每小时的价格从2元到3元不等,应该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经济条件不是决定数字社会中数字贫困阶层向上层流动的唯一关键因素,导致当地人群处于“数字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互联网接入技能以及数字化素养,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重要问题,那么实现脱贫将不再困难。外部社会资本如公益组织机构电脑培训、图书馆电脑技能培训等能改善数字贫困的状况。在接受培训的15人中,有3个例子直接证明了从数字贫困向上层流动。但由于学习能力以及经济能力差异,剩余的13人在互联网的使用技能以及ICT的接入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实验访谈以及问卷中可以得出结论:通过这种非营利性的电脑培训,在不考虑经济资本的因素下,应该能实现数字化脱贫。数字不平等受多方面的影响,在数字化社会中,我们把具有“缺乏动机和愿望、缺乏数字化素养、无法或者没有条件接入ICT”中任意一点的人群都确定为“数字贫困”,而社会组织或机构提供的电脑培训(即社会资本)培养了数字贫困人群的信息技能和信息素养,可以有效地解决阻碍其数字化脱贫的两个因素,为缓解数字不平等的状况和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尽管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直接确定社会资本能多大程度上解决少数民族数字不平等问题,但至少能确定社会资本对改变数字不平等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在少数民族的农村这一特殊情境中,不能仅仅考虑外部社会资本对数字化脱贫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得考虑到内部社会资本在其过程中所起到的自助和资源传递价值,也可能农村的内部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更加有利于数字化脱贫。
在以后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还有:在经济资本等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利用社会资本多大程度上改变少数民族居民数字贫困现象?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全方位发展?非营利性组织机构能否彻底实现当地居民的数字化脱贫?在当地没有图书馆的背景下,图书馆能否作为这一社会节点起到作用?等等。
感谢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何晓凤同学在田野数据收集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