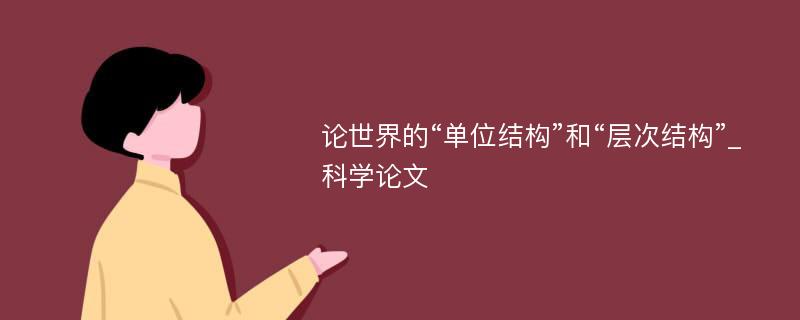
论世界的“单元结构”与“层展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单元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7-0013-05
量子力学一直被视为“神秘高深”的自然科学,许多人文学科研究者对其退避三舍,或者视之为“科学主义”产物而排斥之。其实这些看法都是误解。其所谓“神秘”实质上源于我们深受直观本体论影响,把本来违背客观事实的事情视为当然,而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出于事实的真理视为“怪异”。全面道出其中原委非本文所能,这里只就空间可分性问题进行讨论,或许人们从中可以悟出其中哲理,看到量子理论从最基本的相互作用的实际出发,不仅在认识论上富有说服力,而且在本体论上展示出极其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
一、“空间可分性”的条件与世界的层次结构
《庄子·天下第三十三》中说道:“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曾经被人视为包含辩证法的“真理”,但其实这是一个直观唯物主义的歪理,其“真理性”只是来自于人们脱离实践过程的直观想象。因为它包含着一个逻辑悖论:有限的东西里竟然会包含着无限个元素。也就是说:一条直线由无数个静止的点所组成。正是这个悖论,产生了“飞矢不动”的诡辩,产生了微积分理论中关于“无穷小”的逻辑困难,后来又产生了量子力学中的一系列“发散性困难”,如无穷大的质量、无穷大的电荷等。“实际上,在量子场论中所有主要的发散困难都与场的无穷多自由度相连系。”① 而自由度之所以无穷多,是因为人们只是数学地设想空间是可以无穷分割的。
那么,这个悖论的产生原因何在?其因有二:一是人们把上述分割过程仅仅看成头脑中的直观想象过程,而不是实践操作过程;二是正因为基于直观想象,人们总是想把运动(用直线表示)归结为静止(用点表示),认为事物每时每刻都处于某个“静止的点”或“静止的状态”上,运动无非是用一个“静止状态”取代另一个“静止状态”。于是,所谓运动也就由无穷多个“静止状态点”所构成。
量子力学打破了这种直观唯物主义的空想。如果我们不是把事物当作直观对象,而是作为实践对象,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上述分割,就会发现:几何的分割过程不是抽象的想象过程,而是需要在现实的过程中,通过强大的相互作用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人们在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时,没有考虑到:如此不断分割下去,分到分子原子层次,就不得不采用新的手段来分割,以至需要用电子加速机的巨大能量来“日取其半”,而且分割到一定程度,连巨大的电子加速器也不可能继续分割下去。因此,在某种特定的“能量集中度”条件下,空间距离只能分割到某一程度为止,由此得到在这个条件下“不可分割的最小长度单元”(cutoff)。必须忽略这个单元的内部细节,把它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比其小的空间尺度在这个分割过程中是无意义的。例如,一滴水含有14000亿亿个水分子。因此,对水滴的直径的度量,以及对水滴的运动距离的度量,如果精确到分子尺度便毫无意义,至少必须以亿亿个水分子集合所占有的空间为单位。至于以什么样的长度单位作为它的cutoff(“不可分割的最小长度单元”)则取决于这种相互作用运动的能级——相互作用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量的数量级。小于这个数量级的相互作用量(能量或动量)是不能达到这个分割精度的,因而相对这个分割精度来说是无意义的,因而这个最小的相互作用量便构成这个分割过程中的量子——最小的相互作用单元。
如果我们以这个不可分割的最小空间单位作为基本单位来度量长度,芝诺悖论便不存在了。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来说,假设这个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是Δx,其相互作用动量的最小单位(即相互作用时动量交换的最小单位)为Δp,那么,就必然有下述不确定性原理:ΔxΔp≥h,这里h是“普朗克常数”。也就是说,由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量决定了其可以“分割”的空间尺度的大小。在一定的相互作用量条件下,产生了最小的空间尺度(cutoff),小于这个空间尺度的空间长度是无意义的。这样一来,任何有限空间的长度便只能用有限的数目来衡量,无穷大“发散困难”也就不存在了。实际上,对空间的分割程度(也即对空间的分辨率)取决于实验中进行这种分割的能量的大小。分割时空是一个整体过程,需要一定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能量单元。这个能量单元的能级决定了对空间长度的分割程度(分辨率),从而决定了某一不可分割“最小长度单元”(cutoff)。一旦有了这个最小不可分割的空间单元,上述种种发散困难也就不存在了。特定相互作用中空间的最小不可分割单位的存在,必然导致相应的时间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光速短时间在这个相互作用中是不存在的,将这个最小不可分割的单位对应于相应的不可分解的时间单元。二者结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不可再分解的“时空单元”。
由于不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事物之间交换的最小能量与动量单位(单个最小的不可分解的能量子所具有的能量,而不是能量总量很低)的不同,从而导致相互作用的不同深度,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最小空间尺度,这就导致了“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相对性。在低能量级别的相互作用中不可分割的最小时空单元,在高能量级别中却是可以分割的。例如,宏观世界所发生的能量交换过程(如机械分割过程),其最小能量交换单位的能量很低,所以其不可再分解的最小空间尺度较大。而在较高能量级别的相互作用(如电子层次,其交换的能量是光子)中,这个不可分解的时空单位便可以分解为更小尺度的时空单位。而在更高能级的原子核内部相互作用中,这个不可再分割的单位又可以分解为更小的时空单元。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事物的层次结构:上一层次不可分解的单元,在下一层次被分解,由更小的不可分解的单元所组成。
而在量子理论诞生之前,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直观想象,构思出按照几何分割得到的世界:世界直接由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如“点”或“原子”)组成静态结构。这种静态结构常常也分为各个层次,但是所有层次的现象归根到底由最基本的层次所决定。一旦最基本的层次决定,整个世界结构与各个层次的现象也就全部决定了。例如,人体归根到底由各个原子所结成,各个原子的排列组合决定各个分子结构,进而决定各个细胞的结构,细胞结构决定各个器官,而各个器官决定了整个人体,所以归根到底人体现象(甚至包括人类精神活动)是由原子层次的结构决定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还原论”。由此构成的世界只能是无层次的世界结构,各个“层次”只是基本物质的分层次的组织方式而已,它们归根到底由最基本的层次所决定。
真正能够揭示世界层次结构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是量子理论。尽管量子理论的数学形式比较深奥,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被层层数学符号所遮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外在的数学符号而直视其实际意义,将会发现这样的深刻思想:采用抽象的直观想象来对世界进行纯几何的“分割”(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在客观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体现于测量仪器与微观粒子的相互作用过程)现实地分割事物。现实世界的分割是一个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同级别的相互作用过程生成了不同层次的现象界。于是我们看到,世界不是从宏观形态一直可以还原到“点”为止的机械的“连续体”,而是由一层层的令人惊异的结构所组成的层次结构,各个层次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于是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现象不再是由最基本的层次决定,而是由各个层次的相互作用过程所生成。由此,我们看到了由各个层次的相互作用生成的无限丰富多彩的多层次世界。
二、各个层次间的“脱耦”与“耦合”
量子理论(含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根据各个相互作用中不可分割的能量单元(量子)在量上的能级,来区别各个不同层次。每种能级的相互作用产生相应层次的物理过程,产生相应层次不可分割的最小时空尺度,进而产生各个不同层次特有的物理现象。如电磁相互作用的电磁场的能量被“量子化”为光子,带电荷的粒子(电子、质子等)通过交换光子而发生相互作用。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下述重要的关于客观世界图景的哲学观念:
第一,世界的层级结构及其“脱耦”。各个不同相互作用级别的不可分割的最小能量单元不同,从而使得其能够分辨的时空尺度各不相同。现在我们分析由此产生的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由于其最小的不可分割的能量单元所含有的能量小,它不能分辨由高能级所生成的更小尺度的时空尺度,因而在这一层次无法表现出更小尺度中发生的现象,即它与更高能级与更小尺度的层次的现象是“脱耦”的。而量子能级较低的层次中不可分割的时空尺度,在该层次中是可分辨的,因而其内部结构与现象将在该层次呈现,因而同一客观过程将在这两个层次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现象,从而该层次与较大尺度层次的现象也是“脱耦”的。这就是说,宇宙中任何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最小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量的数量级,而到达相应的不同时空尺度之中,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进行。能级越高,就越深入到越小的时空层级中,从而被闭锁在这个时空层级,不影响比其大的尺度中的相互作用。能级越低,则其能够到达的时空尺度越粗,无法识别和表达某尺度内部的精细结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各个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各行其是的图景,能级的差异成为不同层级内部相互作用之间相互“脱耦”的重要机制。我们将其称为各个时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系统的“鲁棒性”(Robustness):某一时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系统的状态,不会因其下一级时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的涨落(摄动和干扰)而改变,因为后者中的涨落发生在其大时空尺度相互作用中“不可辨认”的领域。因此各个时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保持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这里,“鲁棒”一词是Robust的音译,词面意思是“健壮和稳定”。而作为科学术语的鲁棒性指的是系统的健壮稳定性,即控制系统在某些因素的摄动下,维持某些性能的特性。正是这种“脱耦”切断了高能物理学对其他层次(其能量要小得多)的影响。人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忽略种种微观细节(其能量远大于某特定截止值)对问题的影响。
第二,尺度对称性——自相似性。各个不同能级的同一种相互作用,在相互“脱耦”的同时,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我们称为“自相似性”,这是因为这些不同尺度上的相互作用方程,又遵循着共同的相互作用定律。这就是说,物质间的某种相互作用对不同尺度是对称的,具有相似的表现。
我们知道,在经典相互作用理论中,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是空间距离的函数,这个空间距离可以无限分割,点与点之间相互作用的“点模型”是唯一的图景。相互作用方程不存在层次上的差别:从最大的太阳系天体到最小的原子尺度上的同一种相互作用(如电磁相互作用、引力相互作用)都会遵循同样的方程。这必然引起我们前面提到的类似于芝诺悖论的“发散困难”。而在量子场理论中,经过某种数学手段(被称为“重整化”,涉及数学细节太多,这里不作介绍)处理后,这个共同的相互作用方程则裂变为各个不同能级层级的相互作用方程:在某一尺度单位A[,1]上的相互作用强度用参数μ[,1]来表示,它不考察各个“尺度单位内部”相互作用;要研究这个“尺度单位”内部的结构,必须进行“细视化”,即建立“次级尺度单位”A[,2],这个尺度单元上发生的相互作用方式与比它大的尺度完全相同,而强度则变为μ[,2],因而是大尺度上的相互作用的“自相似”变换所得。如此不断进行下去,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层层嵌套”的相互作用图景,这就是量子场论中相互作用的时空层级图景。这里的“层层嵌套”,是说它们的相互作用方程相似:遵循同一相互作用方程,只是具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强度。如果把参数的变化也定义在尺度变化基础上,那么不同层级的相互作用方程将完全一样。这就是粒子相互作用方程对“尺度变换”(又译标度变换)下的不变性。必须指出,这种“粗视化”与“细视化”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客观的自然过程,因为它们由各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本身客观地决定。
于是,各个不同级别的“时空尺度单元”之间进行相互变换,所展示的物理现象仍然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相互作用在不同能量层级上的表现形式。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对称性——在时空尺度(又称“标度”)变换下保持着相互作用的不变性,此称“标度不变性”。换句话说,即不同层次的相互作用仿佛是某一层次相互作用的放大或缩小。这种对称性,反映了宇宙时空结构的重要特性,为我们揭示自然界奥秘提供了重要途径。
第三,不同层级间的耦合作用。量子力学虽然给出了各个尺度上的相互作用过程之间的“脱耦机制”,但在一定条件下,不同尺度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又存在耦合现象。各个不同尺度上的事件间的“脱耦”与“耦合”的微妙而复杂的机制,产生了大千世界层出不穷的复杂现象。
首先,如上所述,各个层级中的相互作用是同一相互作用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表现,因此它们彼此同根:根源于同一相互作用。因此,各个层级中的相互作用现象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我们姑且称之为“同根性耦合关系”。
其次,各个大尺度上运动过程由小一层级的尺度单位所构成,这些小尺度单位内部发生各种现象是大尺度运动过程所不能觉察的。但是,小尺度单位内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自由随机运动与相互作用运动之间的矛盾,虽然不能在大尺度层级上表现出来,但会影响其他小尺度单位,形成相对于这个大尺度的“微扰”。而该微扰能够影响的范围我们用“关联长度”来描述。一旦达到某种条件(临界条件),某种符合一定条件的微扰能够最充分地吸收能量而产生出正反馈式的扩张过程,这时“关联长度”将迅速变大,来自于下一层级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微扰”将迅速地通过这一层级的宏观尺度表达出来。于是就实现了从下一层级向上一层级的表达,这是两个层级问的重要“耦合”机制。例如,生物DNA的生理表达就是这种“耦合机制”。二级相变也是通过这种耦合机制所形成的。这时候,局部微扰所构成的“涨落”会迅速扩大为宏观状态。我们姑且称这种耦合机制为“微观涨落与宏观表达的耦合关系”。
第三种耦合机制,可以称之为“中介环节耦合关系”。它表现为:微观小尺度范围的事件,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影响大尺度中的上一层次的物质过程。最常见的现象是生物体中的微观层次过程,通过产生一系列中介物质(酶)而决定生物的宏观性状。在社会生活中,微观层次通过中介性物质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美国的911事件是社会生活的微观事件,而其通过新闻媒介影响整个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系统的社会生活。
三、“还原论”与“层展论”
正因为不同层次之间可以通过上述三种方式相互耦合,所以宏观层次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微观层次的事件来部分地说明。这是还原论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的根本原因。然而,这并不能将所有现象都归结为低层次的物理相互作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卡丹诺夫说得非常清楚:“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表明,不同的聚集层次自然地成为不同科学家群落的研究对象。据此,一组科学家研究夸克(一族亚核粒子),另一组,原子核;另一组,原子;另一组,分子生物学;另一组,遗传学。在这一序列中,后面的部分是由前面层次的对象所构成。可以认为基本性依次序而递减。但是在每一层次中总有新的而且激动人心的有效普遍原则,却并不能由更加‘基础’的科学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来。从这一系列中最不基础的层次开始,我们可以一一列出这些科学中的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结论,诸如孟德尔遗传律,双螺旋,量子力学,原子核裂变。谁最根本?谁最基本?谁推导了谁?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将科学知识区分等级是十分愚蠢的。宁可说在每一层次的普遍原则中都会呈现宏伟的概念。”②
实际上,量子理论给我们展示的世界图景从根本上否定了还原论的可能性。由各种不同质的相互作用及其不同级的最小能量单元(以及相应的时空尺度)层层分立而构成的“层级结构”,它们之间既相互脱耦,也相互耦合,从而造成了新的物质结构与性质不断涌现。③ 这种与还原论相对立的观点被称为“层展论”(emergence theory)。“emergence”即新事物新性质不断涌现的过程,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冯端将“emergence”译为“层展”,另一著名物理学家于渌先生则将其译为“呈展”。由于“层展论”要比“呈展论”多一层含义,而且符合该理论原意,故我们采用冯译“层展论”④。这是主张各个层次之间“脱耦”与“耦合”相统一的理论。在这个层展论图景中,由能量级所开拓的层级结构实质上成为一切高级运动形态的舞台。粒子之间在各个能级上的相互作用为各个层级中的各种运动形式提供了基础性能量来源。而这些能量表现在各种组织结构中,各种运动形式之中。20世纪后半叶蓬勃兴起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各种自组织理论,自然地以这个层级图景为背景,探索了新的运动形态与物质结构如何在这个背景上生成。而在这些自组织过程中,粒子给在各个不同层级所提供的相互作用能量成为创造性能量,它们不断在各个层级上产生出新的性质,产生出其他层级上不具有的新的相互作用新形态。于是,同一相互作用在不同时空尺度上进行的“层级结构”,在自组织过程中被生成为“层展结构”,无限丰富的新的运动形态、新的结构及其新的性质不断被创造出来。
注释:
① 朱洪元《量子场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② Leo P.Kadanoff,Chaos.A View of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The Great Ideas Today,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86,p.86。
③ 冯端,金国钧《凝聚态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物理学进展》,2000,(1)。
④ “emergence”一词的原意是“浮现、露出、出现”等,指的是“原先没有的东西的突然产生与呈现”。它与“development”(发展)不同,后者一般指“已有的东西的展现”。这个词的中文译法有好几种,80年代时常译为“突现”,近来一些文献将其译为“层展”(冯端,全国钧:《凝聚态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物理学进展》2000年第1期)。有时也译为“呈展”。一般说来,“展”字的意思是“原有的东西的展开”,而emergence原意为“原先没有的东西的突然产生与呈现”。下面我们将指出,新事物本身是从某种微小的“涨落”展示为宏观态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展”字是很传神的。然而这个作为微扰的“涨落”本身又是由随机自由运动创造出来的,“展”字似乎未能包含这个意义。而我们在未能寻求到更好的译法之前,按照冯端的译法,将此词译为“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