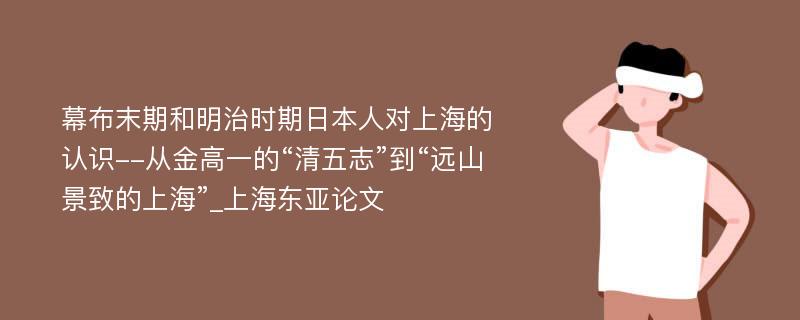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明治论文,日本人论文,远山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1)03-0031-08
上海在中国本土的重要性,大概始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掌控了台湾并于二十四年解除了海禁、在上海设立了江海关之后。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又在江浙沿海一带设立海禁,上海港随之关闭,其重要性尚未充分显现就立即淹没了。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拓展在远东的市场,派传教士探查中国沿海各港口,由此了解到了上海在地理上的优势位置,并于翌年的1832年派职员林赛(H.H.Lindsay)率领“阿美士德”号轮船专程到上海对黄浦江水道等进行详细的测量和调查并汇总成书面文献呈报给公司,于是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英方所要求的五个开埠港口内,上海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翌年,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开始了近代化的演进,它在中国以及远东乃至世界上的地位,日益彰显。
日本在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扩张,已从或由西方传教士直接带来或经由中国传来的西方人编制的世界地图及全球地理的书志中开始逐渐了解到了外部的世界,1695年西川如見(1648-1724)依据利玛窦(Matteo·Ricci)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J·Aleni)的《职方外纪》刊行了两卷本的《华夷通商考》,上卷均为有关中华十八省的中国地志,新井白石(1657-1725)完成于1713年的《采览异言》中依然有相当的篇幅是对中国地理的描述,但里面都未提及上海。只有在少量的漂流民记中偶尔会有些语焉不详的记述。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其时尚未成为一个通商大邑,另一方面也由于自17世纪开始的锁国时代,遮蔽了日本人对外界的充分认识。幕末的日本人开始注意到上海,大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鸦片战争的消息通过抵达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撰写的“唐风说书”传达到了日本,据此出现的由岭田枫江撰写、1849年刊行的《海外新话》中,提及了与此次战争相关的上海[1];二是1854年、尤其是1859年日本被迫开国以后,大量欧美的商船开始来到横滨、长崎等开放港口,而这些船只的相当部分是由上海驶来的。此后,幕府意欲模仿西方,以海外贸易来振兴日本①,同时也借此观察因长期的锁国政策而十分疏隔的实际的外部世界。当时的日本人获知,在上海有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的美国等国派驻的商馆,适宜于派遣官方的贸易商船。于是有了文久二年(1862)的“千岁丸”上海之行[2]。近代日本人与上海的关联也由此正式开启。
对于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人口十余万人的上海县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1855年2月签订的《上海华民居住租界条例》标志着租界华洋杂居格局开始形成;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1845年、1848年、1849年先后出现的英、美(1862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代表着一个新的上海,这完全是一个由西洋人开发建设并在司法行政上加以独立管理的存在,虽然日后居民的大多数是中国人,但是起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西洋人,这里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8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期以后,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或由官方派遣,或由民间自发,或是两者交杂,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陆续来到上海,或短期滞留,或长期居住,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
一、幕末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867)
1862年“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应该是近代日本人首次造访上海。关于这次上海之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②,本文不拟详细展开。这次航行的文献记录,主要是随行商人和侍从(多为下级年轻武士)所撰写的航海日志和日记等,多年之后得到陆续刊行,其中有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1839-1867)的《游清五录》(具体为《航海日录》、《上海淹留日录》、《长崎淹留杂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1916年收入《东行先生遗文》刊行);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记》(1926年刊行);中牟田之助的《上海行日记》、《自长崎至上海航海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收入《子爵中牟田之助传》,1919年刊行);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和《没鼻笔语》(1946年刊行)。虽然每个记录者的视角和经历稍有不同,但获得的见闻有相当的趋同性。以下,本文依据这些文献对“千岁丸”随员的上海认识进行粗略的考察。
在《上海杂记》中有一段上海的沿革和概况的叙述,译录如下:
“上海古时位于禹贡扬州之地,属吴。吴灭后划入越,越灭后入楚。秦时始置郡县,即会稽郡。至元时设松江府,上海隶属该府,至今无改。其地位于海之上方,通往港口之海口处,曰扬子江。此江甚阔大,距左岸之宽度约三十町(日本长度,共约3 270米——译者),右侧则望无际涯。唯可见三两洲渚而已。但水浅,能行船舰处宽不过一里(日本里,1里约相当于4公里,下同——译者)半而已,且水色浑浊呈泥浆色。沿此江前行十里许,左侧为吴淞江(疑为黄浦江之误——译者),沿此前行六里许即至上海沪渎城。上海面向黄浦江。”③
此段叙述还提到了《上海县志》,显然这是参考了中国文献记载并经作者实地考察而写出的文字,虽然还有些舛误,却是至此日本文献中对上海历史与地理的最初的完整描述。
高杉晋作的《航海日录》五月六日(旧历)条中记述了初入上海港时的感觉:
“朝早,川蒸汽船来,引本船,左折溯江,两岸民家风景殆与我邦无异。……午前渐到上海港,此支那第一繁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黄昏归本船甲板上,极目四方,舟子欸乃之声与军舰发炮之音相应,其景如东武火灾之景,实一愉快之地也。入夜,两岸灯影泳水波,光景如画。”(原文为汉文)[3]84
1862年时,沿黄浦江一带的租界也只是雏形初具,但沿江一带的楼房和江面上桅樯林立千帆竞发的繁盛气象,还是令开国不久的日本人惊讶不已。但这只是当时上海的一面,或者说是西洋人上海的一面。上海县城或是中国人集聚区的景象,也同样令日本人感到震惊:
“上海市坊通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尘粪堆积,无处插足,亦无人清扫。或曰,出市街即为旷野,荒草没路,唯棺椁纵横,或将死尸以草席包裹,四处乱扔。炎暑之时,臭气熏鼻。清国之乱象,由此可知。”[4]
“上海中,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冲鼻,其污秽难以言状。”[5]
“每街门悬街名,酒店茶肆,与我邦大同小异,唯恐臭气之甚而已。”(原文为汉文)[3]84
上海旧城,街巷狭隘污秽,大概原本就有,但如此难以忍受的状态,应该与太平军的进攻破坏以及苏浙一带的难民大量涌入有关。而这一乱象,恰被“千岁丸”一行的日本人所目击,见诸笔端,不免有些骇人。加之本地中国人吸食鸦片现象的蔓延,使得幕末的日本人通过上海现场所获得的中国印象,相当负面。
另一令这些日本人感到惊愕和悲哀的现象,是洋人在上海的飞扬跋扈和中国人的退让低下:
“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属地,又可也。”(原文为汉文)[3]87
“去此到孔圣庙,庙堂有二,期间空地种草木,结宏颇备,然贼变以来英人居之,变为阵营,庙堂中兵卒枕铳炮卧,观之实不堪慨感也。英人为支那防贼,故支那迁圣孔子像他处,使英人居此云。”(原文为汉文)[3]89
在上海逗留期间,“千岁丸”一行考察了英法和中国的兵营和武器,结论是:
“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坚强可知也。”(原文为汉文)[3]90
经过近两个月的察访,高杉晋作在《外情探索录》的“上海总论”里,归纳了自己对上海的认识:
“上海位于支那南部海隅僻地,为英夷所掠夺,津港虽繁盛,皆因缘于众多之外国人商馆,城外城里亦多外国人商馆,由此繁盛。观支那人之居所,多贫象,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或一年之中皆居船中,唯富有者在外国人商馆内谋事并居住其中。”[3]120
这段文字差不多也是“千岁丸”一行的日本人对上海的通识。
此后的1864年3月至5月(元治元年二月至四月),幕府又派遣官府商船“健顺丸”航行上海,目的依然是贸易和实地调查。这次航行留下的记录仅有一份幕吏的上海视察复命书《黄浦志》④,从文献的种类以及文字的量而言,远逊于“千岁丸”之行,但依然留下了有关上海的珍贵记述:
“二月二十九日(旧历,下同),(部分人)下榻于旅亭(原注:即阿斯托尔宾馆。引者注:英文名为Astor House Hotel,中译礼查饭店,现名浦江饭店),此上海第一旅亭。其西有新大桥(引者注:现今外白渡桥),乃西人所设,须投钱十五文方可过桥。……三月朔日,有旅亭小童,约五、六岁,导引我等至街头,途中若遇支那人,小童斥骂,皆纷纷避走。支那人竟如此恐惧西人。……三日,至道台馆舍,馆设在城内,抵达后应宝寺(原注:即道台)亲自出迎,引入客室,对话间小吏站立左右,喋喋杂谈,似不知礼。……九日,城内散步,城内街道狭窄,难容两人并行。人家重密,苍生数百,杂沓蹂躏。…廿一日,在支那人街散步,道路观者如云,道路英国番兵以鞭笞驱散,已而又云集,犹如蚊蚋之趋于残肴。…四月一日,观支那剧场(原注:剧场名回美园),与我国歌舞戏略同。场中点五色灯火,客座又点红蜡烛,或五人,或十人,登场,或悲,或骂,或哭,或怒,其形状实令人绝倒,然其衣裳器物颇美丽。”[6]133-142
在日记体的《黄浦志》之后,还附有一“见闻书”,对上海有简略的概述。现译述其大要如下:
“上海江(应为黄浦江——引者)与洋子江(应写作扬子江)源流相异,在吴淞(原文汉字为‘胡桑村’,但据其所注的读音假名,应读作Wu-song——引者)合流。吴淞有法国人阵营及炮台。上海乃外国船辐辏之地,多外国居留人,当今停泊的外国大船百余艘,常滞留于此,六七年前不过五六十艘左右,年年船数大增。上海港于西历一八五零年左右外国人开始来此居住,一八五二年开始渐趋隆盛。奉行(幕府的官名——引者)称道台,管辖一州一府,居住于上海城中,此上为抚台,州府十个为一省,由总督管治。上海城有外濠,积瓦垒土筑成城廓,八方有门可通行,城廓内广约四五町(1町约100公亩——引者),内有繁盛街市,有法国军营,常驻兵卒,道路皆狭隘。城外支那商店亦鳞次栉比,其中大商有十四五家。房屋皆为两层,楼下为商店,楼上居住。其中三层楼房亦有七八家,此为妓楼茶店料理店。”[6]149-150
此外还有较为详尽的有关通货、物产、关税等的介绍,这些有关上海的记叙虽有少许舛误,但较之“千岁丸”一行的记述,有较大的补足,在某些领域也更为详尽,对上海的认识,似也更加全面。
以后在幕府时代,还有1865年4~5月的“北京号”(英国邮船)和1867年2~3月的“恒河号”(英国轮船)的两次上海之行,但人员规模要小得多,只是派使者搭船来上海购买船只武器,之后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文献,至少笔者迄今尚未发现,也不详一行对于上海的认识如何。另岸田吟香(1833-1905)在1866年来上海居住了9个月,曾留下《吴淞日记》,此文献笔者正在搜寻中。
二、明治前期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8-1888)
明治以后,新政府积极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力图将触角伸向海外。1875年2月,在此前已有英国人和美国开设的航线的情形下,明治政府下令三菱汽船会社开设了上海至横滨间的定期航路,一年多之后,以低廉的票价击垮了英美两家轮船公司,垄断了日本各港口至上海的航线,来往于各地与上海的日本人也因此逐年增加,并出现了在上海定居的日本人。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调查统计,1870年在公共租界内居住的日本人有7人,1875年增至45人,1880年又增至168人,1885年猛增至595人[7]。有关上海的信息,也以各种方式传递到了日本。
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的两个意义正在逐渐凸现。一是日本国内主张中日联手振兴东亚的兴亚派试图以上海作为前沿阵地,扩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二是上海作为重要商港的价值正在被日本人所认识,试图以上海作为主要的通商口岸,通过贸易来增强日本的国力。
1884年8月,早期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九州改进党主要人物日下部正一(1851-1913)等决定在上海设立一所东洋学馆,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在海外设立的第一所学校,其设立的目的,在其“趣旨书”中有如下的表述:
“欲保全我国永久独立之体面,须细加考量东洋政策之得失与否。盖东洋之神髓,在于清国之头上,其与我国之关系,可谓辅车相依,唇齿相保。……然如此邻近之清国,所闻可谓寥寥,此洵一大欠缺。我辈首先须通晓清国之政治人情风俗言语,方可知活动神髓手足之妙。由此,在此设置一大学校,培养大成有为人士,以达长江一浮千里进、力挽东洋之衰运之理想。”[8]
这所学校后来设立在上海虹口乍浦路第23号馆。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在上海建立这样一所学校,在“趣旨书”中作了如此的解释:
“清国上海,乃东洋之咽喉,金穀辐辏之所,人才荟萃之地,与我国并非远隔,一棹易至。在此置校舍,江湖同感之士来此学习,是乃真正报国之本。”[8]
经过二十余年不算很密切的交往,日本人对上海已有了如此的认识。
后来抵达上海办学的大内义映等获悉上海本地人对东洋的理解只是日本、并无日语中的东亚之意,于是在同年11月初将名称改为“东亚学校”,不久又改为“亚细亚学馆”,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清学”(中国语文和古典)、“英学”(英语和数学)和世界历史等。从其所开设的课程,也可看出上海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独特性。后因经营困难等原因,一年后的1885年9月学校被迫关闭⑤。
这一时期来上海的日本人中,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用汉文撰写的《观光纪游》无疑是值得留意的文献。冈千仞1884年6月5日抵达上海,在上海盘桓将近两个月,留下了《航沪日记》和《沪上日记》,此外还游历了苏杭、京津、粤港一带,共历时近一年。冈千仞虽是习修汉文儒学出身,却具有世界眼光,留意海外风云,曾与人合作编译了《美利坚志》和《法兰西志》,因此他对上海的观察,比较深刻犀利,感悟也胜常人一筹。他在《航沪日记》的小引中说:
“上海为古沪渎……今多单称曰沪。道光廿二年始许欧人纳租居市。西连长江,负苏杭,东南控闽越,万舰旁午,百货辐辏,为东洋各埠第一。”[9]9
冈千仞游历上海时,与高杉晋作等的上海之行已相距二十余年,太平军之乱早已平息,租界建设可谓日新月异,华埠市面也较前繁荣:
“出观市街。分为三界,曰法租界、英租界、米租界。每界三国置警署,逻卒巡街警察。沿岸大路,各国公署、轮船公司、欧米银行、会议堂、海关税务署,架楼三四层,宏丽无比。街柱接二线,一为电信线,一为电灯线。瓦斯灯、自来水道,皆铁为之。马车洋制,人车东制。有一轮车,载二人自后推之。大道五条,称马路。中土市街,不容马车,唯租界康衢四通,可行马车,故有此称。市街间大路,概皆中土商店,隆栋曲棂,丹碧焕发,百货标榜,灿烂炫目。人马络绎,昼夜喧阗。”[9]16
但上海旧城内的景象似乎尚无根本的改观:
“观城内。从小东门而入,市廛杂沓,街衢狭隘,秽气郁攸,恶臭扑鼻。得城隍庙,门画人物,庙列塑像,香火熏灼。庙背东园,广数十亩,池水环流。一楼曰湖心亭,石桥盘曲,曰九曲桥。池上列肆,鬻书画笔墨、古器物,稍有雅致。唯不栽一卉木,无些幽趣。”[9]19
以上引述的,多为日本人来上海的踏访记或考察录,直观的描述比较多。1888年出现了一部由日本大藏省刊行、井上陈政(1862-1900)撰写的《禹域通纂》,这可谓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部综合性专著,上下两卷总共2 347页,卷帙浩繁。1882年3月,首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期满归国,陈政随其来中国留学。他在中国前后总共6年,不仅阅读各类典籍书志,且南起广东,北至直隶北京,东起上海江苏,西及山西陕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时时注意以典籍稽考实地的勘踏,以实地的考察来修正典籍的记载,最后撰写成煌煌两大卷《禹域通纂》。该书对于上海的记述篇幅不算多,除了在兵器制造部分对江南机器制造局等有所涉猎外,有关上海的文字主要出现在“通商各口概说”部分,择要译述如下:
“上海属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治,位于吴淞江与申江合流处,东经一百二十度二十八分,北纬三十一度十四分。依据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江宁条约通市,港内水深数寻至十寻以上。船舶直接停靠埠头,货物搬运等尤为方便。港地分为三个租界,港南为上海县城,县城以北为法租界,租界南面以河沟为界,北部至吴淞江为英租界,吴淞江以北港岸一带为美租界。其中英租界地域房屋壮丽,商贾辐辏,居港内之首。其次为法租界,多巨商仓库等,美租界早年颇为荒芜,近来屋宇渐次鳞比,呈繁庶之状。本港位居支那南北之要冲,乃全国货物辐辏之区,贸易繁盛,洵亚洲之冠。故欧美巨商及清国殷商均汇聚于此,驰骋市场。船舶有各轮船公司,所有船舶均可进行沿海运输,进出船舶日益增多。港内人口清民十四万七千余人,居留外国人三千有余,本邦人七百人许。一八八五年进出口总计五千零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两。”[10]
这也许是至此日本文献中出现的对上海、尤其是上海港口功能所作出的最为完整的描述,意味着在18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上海的关注,已经更加集中于它在贸易运输上的国际化地位。
三、明治后期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89-1911)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均以战败而告终,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蔑视倾向也由此日益抬头。尽管如此,主张致力于东亚、尤其是中日联手来抗衡西方的亚洲主义思潮或势力依然在日本朝野赢得了较大的共鸣。上海本身的发展,并未因这两次战争而受到阻碍,至世纪之交,上海在中国、远东乃至世界上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充分关注。
一个重要的明证是日本先后有两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在上海开设。中法战争之后不久,具有参谋本部背景的荒尾精和根津一在获得了朝野一定的支持之后,费尽千辛万苦于1890年9月在上海开设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这实际上是一个教育机构,其开设宗旨大抵与东洋学馆相近,其选择上海作为开设地点,也是因为上海同时兼具了中国的现场和世界的窗口的性质。开设的课程有中文、英文、商业地理、支那商业史、簿记学、经济学、和汉文学、法律学等,初有学生150余人,教职员20余人。该机构在风雨苍黄中维持了将近4年,于1894年8月解散。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中日关系反而出现了缓和,1898年东亚会和同文会统合为东亚同文会,力图通过在中国和韩国兴办教育机构来培养致力于东亚振兴大业的人才。初始因办学设想得到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大力赞同,1900年5月同文书院在南京揭牌,但东亚同文会的领袖旋即意识到该机构在南京难以展开,加之北京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日本担心租界之外的中国局势不稳,遂于1901年4月在上海开设了东亚同文书院,南京的书院并入其内。该机构后来发展为获得日本文部省认可的正式大学,同时也是日本在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一直持续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
上述的两所机构,在明治后期,编撰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尤其是有关中国经济贸易的卷帙浩繁的综合性大著,分别是1892年8月出版的《清国通商全书》(共三大册、2 324页)和1907年以后陆续出版的12卷本的《支那经济全书》。这两部著作的编撰地都是在上海,毫无疑问,有关上海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
《清国通商全书》中,有关上海的记述出现在第一编第三章廿五港中,但相比较其他港口,对上海的记述要详尽得多,共占有46页,因此在本文中无法详细引述,只能稍稍截取几个场景,以管窥其一斑:
“(上海)地势极为平坦,四望茫茫,无连天山冈,唯浊流纵横,颇煞风景。人口加上城内几达六十余万,百货辐辏,规模宏壮,港湾良好,帆樯林立,实为东洋第一贸易场。”[11]73
“县城位于浦江西岸,周围三里(日本里——引者),郭门有七,曰大东、小东、小南、大南、西门、老北、新北。大东、小东及新北三门内,为城内大街,颇为繁华,然皆狭隘污秽。上海之贸易,悉在外国人居留地内,县城之买卖,仅止于若干杂货零售而已。”[11]73-74
“(经多年规划和建设,租界)已自沼泽草莽之地一变而为楼厦栉比,高耸云霄,道路清洁,车马络绎,设有电线、电话、电灯、瓦斯灯、自来水道,地上地下纵横交错,房屋构造皆壮丽。”[11]80-81
在这里,由上海所凸现出来的中国的落后羸弱和西洋的先进强盛无疑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惊叹和深思。这里所呈现出来的上海的画面,已经不是静止的、平面的、断裂的,而是凝聚了动荡的时代风云,交叠着东方和西方、前近代和近代的多重元素。
此外出于通商全书的特点,该书还对上海租界区域的年财政收支、土地税、轮船公司、银行、货币、码头设施、市内交通、海关税、进出口物品的种类和金额、港口的年吞吐量等都有一定的介绍。
与通商全书相比,《支那经济全书》更具有实地调查报告汇编的特点,这是在东亚同文书院上百名师生历时十余年的各地调查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著,有关上海的著述,散见于各个篇章中。如第一辑第二编第二章,记述了上海租界的土地租借和田地房屋的制度;第三编“劳动者”中,记述了上海劳动者的来源、种类、劳动时间、就业年龄、工资及支付方式、劳动者的风俗习惯等,细致而详尽;在第五编“物价”中详细列举了20世纪初期上海的物价表;在第六编“人民生活程度”的第三章中,详细叙述了上海的商人、买办和上流阶层的生活状态;第二辑第一编第二章中介绍了上海的商业习惯;在第三编“买办”的第五章中,详细列出了上海各行各业的买办和外国商人的收入;以及上海的海关制度、厘金税和落地税,上海通往各地的航路、商业会馆和公所等[12],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上海很高的理解度,甚至也是今天研究近代上海演变的极具价值的重要文献,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引述。
三大册的《清国通商全书》和12卷本的《支那经济全书》中虽然有不少有关上海的详细记述,但并不是研究上海的专门著作。相对而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好几本以介绍上海为主的资料翔实的著作,主要有藤户计太编撰的《支那富源 扬子江》(1901年)、远山景直、大谷藤治郎编著的《苏浙小观》(1903年)、平山胜熊编著的《南清的富源》(1908年)、上海出品协会编著的《扬子江富源 江南事情》(1910年)。其中《苏浙小观》一书的大部分篇幅与上海有关,说其为有关上海的专门著作也不为过,但名副其实的第一部专门介绍和研究上海的著作,当推明治40年(1907)出版、由远山景直所著的《上海》。
作者远山景直自号“长江客渔”,据其在例言中所述,1886年时初来上海,之后又时常买棹西渡,1905年秋又再度来到上海,在沪留居将近一年,查阅多种文献(上海县志、日本领事馆报告、工部局档案等)并作实地勘踏,将所闻所见随时笔录,积240余条,遂整理成《上海》一书,共421页,并附20余幅照片和详尽的上海地图。
作者在该书中设立了164个条目,从历史沿革、地理气候、语言、居民、各租界的行政管理体制、公共设施、主要轮船公司和港口设施、银行钱庄、货币一直到上海人的日常衣食住行,包括小菜市场、牛奶棚、各色店铺、酒馆茶楼、戏院书场、妓楼烟馆、上海人的新旧习俗,都有极为周密的记述。比较可贵的是,作者对渐趋成熟的上海日本人社会有较为完备的描述,包括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各类洋行公司、教育机构、编辑出版的报纸、日本商店、日本旅馆、日本医院、日本人俱乐部、日本自警队等等,尤其是商店部分,可谓网罗了几乎所有在上海开业的日本公司和商店的资讯,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虽然该书称不上是一部严肃的研究著作,但也不是一部肤浅的走马观花式的见闻杂记,它更多流露出的是一个有些旧文人修养、又沾染了些商人习气的普通日本人对上海的态度。就总体而言,他觉得上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上海的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甚至觉得上海将成为一个单独的邦国:
“想来在不久之将来,禹迹神州将建成一世界共通之上海国,业有近来公共租界行政之发达、商业机关之完备、因时势之需而渐次勃兴之诸工业、将江南之富连成一体之金陵苏杭铁路,已具备不可轻侮之资质,其前途可瞻;远有人种之混血、风俗及生活交融之趋势,事态若如此演进,浑然一体的上海国亦将渐渐雄踞于世。”[13]
透过上海,作者期望中国能发生基于外部压力的国运改革。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一般日本人对于当时上海的感觉。
自幕末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至明治落幕的岁月,正是日本结束锁国政策、逐步走向世界、并最后得以在东亚的舞台叱咤风云的半个世纪。而中华帝国尽管也标举过“洋务”,试图重振雄风,无奈由于因袭过重,中枢腐朽,在西洋帝国和东洋帝国的夹击下,国运日衰,日暮途穷,最后沦落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的“脱亚入欧”派自不待言,已经视中国为弊帚弃履,不屑一顾,即便是亚洲主义者,到后来,其使命与其说是联手中国,不如说是改造中国,即便联手,日本也须是盟主,因为中国已经无力扮演主角。尽管上海在近代的崛起,似乎像是从一堆曾经锦绣如今却褴褛的衣衫中突然冒出的一颗珠玉,只是不仅这颗珠玉的光色与衣衫的整体是如此的不协调,而且这光色多半也来自外界物体的折射,并非从衣衫本身透发出来。1862年“千岁丸”一行初次来到中国,首先是从上海看到了破衣烂衫的中国,又从上海看到了不同以往的珠玉(尽管当时也许还只是一块璞玉,直到最后它也未能成为一颗完美的宝玉),并且看到了制造珠玉的强悍的力量,日本人由此逐渐惊醒,希冀自己也能变得强悍起来,与洋人一样来主宰中国。虽然并非所有乘坐“千岁丸”的日本人都从此萌生了这样的欲念,但日后日本试图对中国进行武力扩张的行为,真的可以追溯到这次“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然今之清人,徒以其众多之兵而自夸,却弗知已显衰弱之耻。今至上海兵营而观其状,见其兵卒皆弊衣垢面,徒跣露头,羸弱无力,皆状若乞丐,未见一勇士。若如此,则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征彼,则可横扫清国。”[5]45
当年“千岁丸”一行还曾对洋人在上海的傲慢举止颇觉愤懑,这是因为其时“尊王攘夷”的思潮还颇为兴盛,最初的这些下级武士,也大都是“尊王攘夷”派,但1863-1864年之间的“萨英战争”中遭到了英国猛烈炮击以及高杉晋作的“奇兵队”等与欧美四国联合舰队交过手之后,这些“攘夷”派充分领受了西方人的强悍,很多人日后成了西洋文明的拥护者,也因此,明治以后来到上海的日本人,对由西洋人主导建设的租界的新气象大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对西洋人的新文明表示了真切的服膺,他们试图通过上海这一独特的存在来反观日本本身,思考日本的命运,也就是从上海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新旧文明交融冲突的实态中来寻找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上的坐标。他们最初的努力,是到上海来兴办教育机构,通过上海来促进与中国的贸易,但渐渐地,帝国主义的色彩就日益浓厚了。
注释:
①在安政六年(1859)2月12日箱馆奉行致幕府的申禀中有“以万国互市为富国之本”的语句,幕府后来采纳了这一建议。见春日徹:《一八六二、幕府千年丸の上海派遣》,载田中健夫編:《日本前近代の国家と対外関係》,东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561页。
②除以上引述的春日徹:《一八六二、幕府千年丸の上海派遣》之外,外山军治为《文久二年上海日記》(大阪,全国書房,1946)所做的“解说”,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の研究》第三章“1862年幕府貿易船千年丸の上海行き”(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等都是这一课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中国则有王晓秋的《幕末日本人怎样看中国》(收入《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记述甚详。
③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收录于《文久二年上海日記》,大阪:全国書房,1946年,第12~13页。本论文所引述的日本文献,除原文为汉文外,均由笔者直接译自原文,考虑到幕末和明治时期的文体风格,大都译成浅近的文言文。另,所有原文中出现的对中国的称谓如“支那”、“清国”、“中国”等,一切悉照原文,以存其历史原貌。
④此报告的手稿本藏于东京帝国图书馆(现演变为国会图书馆),后被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新村出所发现,将其整理并稍加注释刊发于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编辑出版的《商业与经济》第五年第二册(1925年2月)上,另取名为《元治元年に於ける幕吏の上海視察記》,本论文的引文即源于此。
⑤有关东洋学馆的部分,参考了佐佐博雅:《清仏戦争と上海東洋学館の成立》,载国士舘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第12号(1980年1月),小松裕:《中江兆民とそのアジア認識——東洋学館。義勇軍結成運動とその関連》,载《歴史評論》,第379期(1981年11月)。
标签:上海东亚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上海论文; 高杉晋作论文; 日本人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