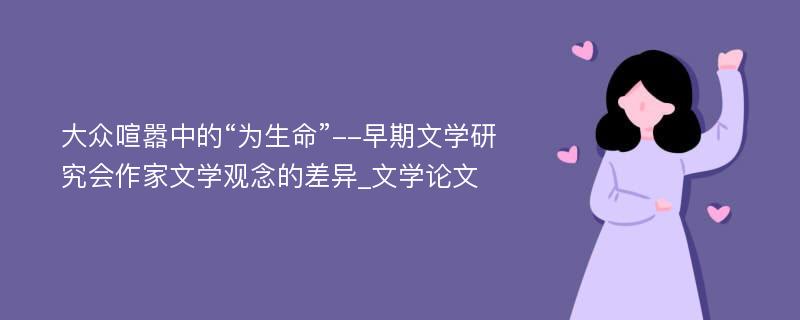
众声喧哗中的“为人生”——前期文学研究会作家文学观念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研究会论文,差异论文,观念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4)06-0122-04
文学研究会直接继承了《新青年》“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构造成一种现实 主义的理论,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现实主义 成为中国现代主流文学观念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很多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叙述中,一 提起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念,就简单地说是“为人生”的,是现实主义的。其“为人生 ”的现实主义倾向被夸大了,忽视了这个松散的文学社团在“为人生”这个共同倾向下 的文学观的复杂性与差异性。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历史 进程的认识。正如鲁迅所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1 ](P255)
一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注重文学社会功利性的文学社团。作为其骨干和主要批评家的郑振 铎、茅盾,于20世纪30年代曾分别指出过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倾向。郑振铎在《中国新文 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以确定无疑的口气告诉我们:文研会的刊物《小说月 报》和附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 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着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海派’文人 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他们提 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 写作”。因此他又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是他们的共同的见解。”[2]茅盾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却说,文学研究会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 性质,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集体的行动,没有提出集体的主张,会员个人 发表过许多不同的文学意见;只是《文学研究会宣言》里有一句话:“将文艺当作高兴 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3]“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 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 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他们的说法并不一 致,且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们都肯定了文学研究会成员有着共同的“为人生 ”的文学观念。
对于文研会的作家来说,“为人生”只是一个笼统的倾向,关于什么是“为人生”, 怎样才能“为人生”等等问题,他们都缺乏明确的概念。而且,他们的文学观也并不都 是现实主义的;就是同为现实主义,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论来源。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 理解和有限的外国文学理论的知识来表达他们的认识,态度常常犹豫不定。文研会始终 没有真正的代言人式的理论代表,茅盾和郑振铎的主张不过是在众多声音中凸显出来了 而已。文研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醒目标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塑造的结果。一方面 ,是带有更鲜明的社会倾向性的批评家茅盾、郑振铎后来的陈述的塑造,他们说话的时 候,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文坛的主流;另一方面,又是长期以来主流文学观念下的文学研 究和文学史的塑造。
文研会的一些重要作家持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表现论的文学本体论。冰心说:“能表现 自己的文学,是‘真’的文学。”所以,她号召文学家创造“真”的文学:“发挥个性 ,表现自己。”[4]王统照说:“我们相信文学为人类情感之流不可阻遏的表现,而为 人类潜在的欲望的要求。”“主义是束缚天才的利器,也是一种桎梏,我们只能就所见 到的说出我们愿说的话,决不带任何色彩,虽然我们并不是天才。”[5]庐隐说:“创 作家的作品,完全是艺术的表现,但是艺术有两种:就是人生的艺术(Arts for life's sake)和艺术的艺术(Arts for art's sake)。这两者的争论,纷纷莫衷一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两者亦正无偏向。创作者当时的感情的冲动,异常神秘,此时即就其本色描写出来,因感情的节调,而成一种和谐的美,这种作品,虽说是为艺术的艺术,但其价值是万不容否定的了。”另一方面,“创作家对于……社会的悲剧,应用热烈的同情,沉痛的语调描写出来,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绝大的慰藉,一方面引起其自觉心,努力奋斗从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负创作家的责任。”[6]她的话反映出把“为人生”与“为艺术”结合起来的企图。
冰心、王统照、庐隐的文艺本体论包含着他们对文学功用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文研 会主要成员更其明确的文学功用观。胡愈之认为,“文学家创造出诗的世界,想象的世 界,把想象的世界,想象的人物,想象的事情安插进去。这种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的补足 (Complement)。我们对于物质世界有所不满时,可以在想象的世界中,寻得慰安之物” [7]。他强调的是文学对人生的慰藉作用。李之常则坚持工具论的文学观:“今日底文 学底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人生的,为民众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绝 不是供少数人赏玩的,娱乐的。”[8]
同是文研会成员的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对文学的要求,说“ 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他还批评郑振铎不曾把他提倡的“ 血泪”的真实意义——文学的阶级性——指示出来[9]。而叶圣陶曾试图调和“为人生 ”与“为艺术”的分歧:“艺术究竟是为人生的抑为艺术的,治艺术者各有所持,几成 两大派。以我浅见,必具二者方得为艺术……真的文艺必兼包人生的与艺术的。”[10] 文研会成员文学本质论与功用观的不同印证了茅盾所言文研会没有集体的主张,会员个 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文学意见的话。
不仅理论话语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倾向,文研会作家的创作也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冰心、王统照(还有早期的叶绍钧)对爱与美的憧憬,庐隐所表现的情感的苦闷、焦灼 ,许地山的宗教意识对作品的渗透和异域色彩,都表现出鲜明的浪漫抒情的倾向。在艺 术手法上,象征主义的手法和抒情性描写随处可见。他们表现人生的理想,但这些理想 不是通过客观的描写,而是通过理性化的形象和结构,通过叙述者的明确宣示。
不过,文研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主导倾向也并不如茅盾所说的那么低调。周 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 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工一样。”这话说得很朴实,但十分重 要,标志着中国文人观念和身份的重大变革,里面也包含了“为人生”的意思。无疑, 这种主导倾向在茅盾和郑振铎的文章里表现得最突出。
二
茅盾表现出了高度的“为人生”的自觉。他明确地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就是要“ 表现人生、指导人生”。他在和创造社成员论争时表示:“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 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 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 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的,他的创作不能不对于社会的腐败抗议。”[11]他一 以贯之地要求文学的理想性,把新文学当作宣传新思想的工具。他说:“中国自有文化 运动,遂发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两个词,……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 学做宣传。”[12]这个最基本的文学价值取向来自对《新青年》时期文学革命观念的继 承。
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理论代表,其贡献在于替“为人生”提供了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论 基础。中国新文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尽管这个理论不免粗枝大叶。 茅盾早期的文论是其文论最有个性、朝气和创造力的时期,不作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 从建设能够满足社会进步需要的新文学的立场出发,择取异域营养,建构自己的现实主 义文论。他的现实主义文论围绕文学与人生这个轴心,其基本结构有三个支撑点:一是 真实性,他提出向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学习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二是时代性 ,强调文学描写社会环境,反映时代精神,他这个命题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泰纳的艺术哲 学;三是理想性,这方面的楷模是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三个 方面都贯穿着“为人生”的功利主义的要求。
显然,茅盾对文学本体的认识是再现论的,而郑振铎则持表现论的观点。郑氏对文学 的定义是:“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 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13]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文学是人类感情 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价值,就 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14]所以,他把自己的观点与传道的文学和供人娱乐的文学 区别开来。他所表述的文学观显然来自托尔斯泰的“情绪感染说”。托尔斯泰认为:“ 艺术是这样的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 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所以,艺术的价值在于它 “是生活中以及向个人和全人类幸福迈进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际的手段,它把 人们在同样的感情中结成一体”[15](PP47-48)。与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把情与理对立 起来不同,郑振铎在他信奉的表现说里加入了“思想”的成分,这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对 文学的一个普遍要求。郑氏对情感的强调也反映出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但 他反对自我表现,因为自我表现终带着自私的色彩。为了更好地回应社会功利性的要求 ,他用美国文学理论家汉特的理论对托尔斯泰的“情绪感染说”进行了改造。在《文学 的使命》中,他说:“文学的真使命就是: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欲以作者的 欢愉与忧闷,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来慰藉或提高读者的 干枯无泽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16]这样就为文学表现时代性内容开了方便之门 。
于是,他就具体地提出了表现时代内容的要求。他在《血和泪的文学》中提出“我们 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文章没有理论上的说明,理由只是基于对现实的感受 :“萨但(Satan)日日以毒箭射我们的兄弟,战神又不断的高唱它的战歌……。”短短4 50字的文章竟用了9个感叹号,5个问号,可见主张的急切。他在《文学与革命》中进一 步表达了对社会革命的诉求:“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动人,最容易 沸腾人们的感情之火。”“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就是需要这种憎恶与涕泣不禁的感 情的。所以文学与革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 是现在的中国文学家最重要最伟大的责任。”这种对文学的要求是基于一种道义感。这 种道义感是中国现代对文学提出社会功利性要求的最普通然而又似乎最冠冕堂皇的根据 。虽然表现时代内容的功利性的要求难以避免地会走向工具论,但由于所持的情感本体 论的制约,他注意与工具论保持距离。郑氏为了避免工具论的嫌疑,甚至不愿在“人生 的文学”前面加一个“为”字。他有这样的话:“平伯兄说:‘我认为文学应该是off life(人生的——引者)不是for life(为人生——引者)。’这句话最妙!可以打破一切 人生的,或艺术的争辩了。”[17]他一再声明自己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绝不强人 以必同,因为文学是情绪的产品,不能强欢乐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欢笑 一样。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在茅盾的文论里才得到了最鲜明、最集中的体现。正是因 为其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他很快便走向了激进的革命文学。1923年左右,革命文学的 幽灵开始在中国文坛的边缘徘徊。1923年到1926年间,一部分从事宣传工作和青年运动 的早期共产党人发表对新文学的杂感,提出新的文学主张。1923年第10期、第11期的《 中国青年》分别刊登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新诗人的棒喝》和萧楚女的《 诗的方式与方程式的生活》。茅盾写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积极响应邓中夏、 萧楚女的文学主张:“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 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 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把共产党人的文艺主张揉进自己的文章,更突出了对 文学功利性的要求,这是他向革命文学趋同的第一步。1925年,以发表《论无产阶级艺 术》为标志,茅盾迈开了走向革命文学的第二步。他自觉地用阶级的观点对以往的文艺 进行修正、改造。茅盾把“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要求嫁接到他的现实主义文论上,从 而在其理论的内部完成了向革命文学转变的准备。这是革命文学的暴风雨到来之前从天 际传来的隐约的雷声。
收稿日期:2004-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