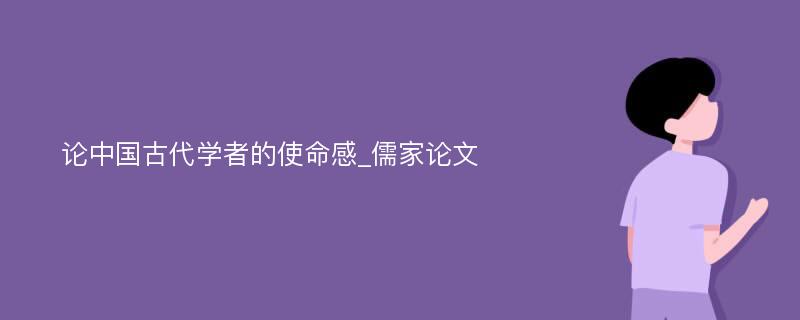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使命感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036-05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简言之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即古人说的“士君子”)以坚守、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基本准则(“道”)为己任,是一批具有自觉使命感、责任感的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不仅为同时代的世人所称道、景仰,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
士、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故本文先对士的产生、演变作一简要回顾。在商周,士是负责各种具体事务的最低一级贵族。这种士,史界多称为“贵族士”。到春秋时代,士的地位、构成开始发生变化。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随着旧制度逐渐瓦解,旧贵族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一些平民的地位则因社会变动得以上升。于是,士这一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层,人数不断扩大。而且,士的构成也逐渐多为知识人,这同社会变动过程中的文化下移有直接关系。自周室东迁之后,周王室日渐式微,周初的一些封国也先后灭亡。于是,“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一步步被突破,出现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状况。乡校与私人办学的兴起,使长期被“官府”垄断的知识文化流布于民间。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才能且有信念、理想的新型士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由于社会有需求,这批新士人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与农、工、商并列的“四民”之一,且成为四民之首。
新士人的产生,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而赋予新士人灵魂、品格、理想的则是孔子和原始儒家。他们是特殊士人精神的塑造者。正是他们提出了理想士人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后世优秀士人所坚守,成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
孔子和原始儒家对士的根本要求是使自己终身成为道的坚守、维护、弘扬者。《论语》一则言“志于道”(《论语·述而》),再则言“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正是此意。“士志于道”就是说,作为一名真正的士,应终身不懈地向往、追求、维护道;而且,由于“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士又应是道的弘扬者。总之,真正的士是离不开道的。
所谓“道”,简言之即社会的基本价值、基本准则,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得以正常运转并发展的根本保证,所维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自然,孔子所说的道乃是那时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孔子和原始儒家要求士志于道,即是要求士成为那时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维护者。所以,孔子和原始儒家从一开始塑造理想士人,便赋予他们使命感、责任感,勇于承担责任的担当精神。
孔子和原始儒家认为,由于道要靠士去贯彻、落实、维护、弘扬,因此,士首先应是一个自觉接受、拳拳服膺道,能将道落实为自身实际行动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孔、孟、荀对士应具有的品德作了多方面的说明。为节省篇幅,下面主要举《论语》为例。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矣。”(《子张》)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孟子》的相关记载有:“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将士分为从政的“仕士”和在野的“处士”。荀子认为,“仕士”应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富”当作“可”,可贵系指道德),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而“处士”则是“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著是”当作“著定”,意为有定守而不随流俗)。
孔、孟、荀对士的要求虽包括才干、能力,但主要是道德。士自然必须恪守基本道德(如仁义、孝悌、忠信、友爱、宽厚、守礼、知耻、远罪),理应是这方面的楷模。但作为士,又应是“德盛”者,尚应有更高要求,比如“见危致命”、“临难毋苟免”(《礼记·曲礼上》),在“天下无道”时能“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由于士无恒产,因此,对士而言,为守道、行道而耐得住穷困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孔、孟、荀一再指出:“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如果贪图安逸生活(“怀居”),以恶衣恶食为耻,便“不足为士”了。孔子所以一再盛赞颜回之贤,原因之一就是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本人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却觉得“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他们都是以道德理性的实现、满足为乐,而不在乎外部物质生活环境的优劣。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真正的士君子所担心的乃是道能否实现、落实,不受损害,而不是自身的贫穷。
孔子曾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就是说,欲想安人、安百姓,前提是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德之人。而《大学》讲修齐治平的次第,则更明确地指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认为欲治国平天下当从修身做起。孔子和原始儒家既赋予士人守道、行道、卫道、弘道的责任、使命,自然要对他们作道德品质、理想人格的塑造。这是因为,士人只有具有高尚的品质,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使命;只有具有高尚的品质,才能获得社会的信任、景仰,从而产生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显然,只会夸夸其谈而不实有其事、实有其德,是不能取信于人、取信于社会,从而完成自己的责任、使命的。所谓“铁肩担道义”,没有一副铁肩(自身硬)是担当不了道义的。应该说,后世优秀的士人都是“德盛”者,他们都能正确地处理公私、义利、理欲、苦乐、荣辱、生死关系,将天下国家置于一己之上,受到社会的景仰,因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守道、行道、卫道、弘道的责任、使命,成为古代社会的脊梁。
孔子和原始儒家对新士人的塑造,从一开始即郑重赋予使命感、责任感,让他们懂得自己是一批肩负重任的人。《论语》有云: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的士人一直以这段话自策、自警、自勉,直到今天影响犹在。所谓“任重道远”,不只是落实、推行、弘扬仁德,使之普及于社会,更有治国平天下的要求、责任,意味是深长的。高度自信且极度豪放的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此语虽狂,但透出的则是冲天豪气和胸怀天下的高度责任感。后世士人也有类似的壮志豪言。比如,东汉末的著名“党人”陈蕃,在少年时曾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列传》)。另一“党人”范滂也是青年时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诸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志向。后世一些有志之士的确是“身无半文而心忧天下”。诚然,以为仅靠自己和自己的同道者奋斗即可平治、澄清天下是不现实的,“舍我其谁”一类话更是表现了某些士人的自大、狂傲,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责任、使命的高度自觉,看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社会安危、国计民生(自然也包括对朝廷、社稷)的深切关怀,所反映的乃是可贵的以国事、民事为己事的精神。
西汉的董仲舒曾对士作了这样的解说:“士者,事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后来,东汉的《白虎通》、《说文解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这一解说为后世所认同。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危机也渐露端倪。要求变革的思想家包世臣为了激励知识分子走出故纸堆,关心国计民生,担负社会责任,他又对这一传统说法作了新的解释:
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安吴四种》卷十)
就是说,士虽无专事,但一切“民事”均应是士人所应关心、从事的事。这就把士人的责任明确化了。这一解说虽晚,但这一认识应该说早就有了。比如,明末东林书院那副人所熟知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是此意。在中国古代,士人的责任感是越来越自觉的。明代中晚期著名思想家吕坤曾说:
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呻吟语·应务》)
此四者大体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将四者定为士人的“责任”,反映了认识的深化。
早在先秦,士即有“仕士”与“处士”之别,即在朝、在野之分。对于在位的“仕士”来说,他们的责任自然更大。吕坤认为,当官只是尽责,“治一邑则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则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则任天下之重,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事失理不遑安食”(《呻吟语·修身》)。“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呻吟语·治道》),必须把官职的高低看作是责任的大小。视当官为尽责,反映的正是古代优秀士人的责任感。至于在野的优秀士人,他们虽无职务,但同样关心民生朝政。这便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明末以顾宪成为首领的“东林党”人,他们虽退居东林书院论学、讲学,但“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因而招致宦官集团的仇视。东汉末的“党人”因拒绝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合作而退居乡里,但并未忘怀朝政。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树立风声,抗论惛俗”,一时形成“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他们“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义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列传》),受到时人和后人的景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赞叹说,那些忧国忧民之士“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古代优秀士人使命感、责任感的最好概括。
到了近代,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权利义务观的影响,他们对人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作了更好的表述。梁启超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1900年,正值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年代,麦孟华改写顾炎武的名句,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清议报》第三十八册,《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它迅速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责任观同中国古代优秀士人的责任观是一脉相承的。
自孔子起,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士人始终将守道、行道、卫道、弘道视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它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是文化传承。《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始终以传承、弘扬上自尧舜下至文武周公的精神、文化为己任。为此,他整理删定六经,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诸多孔门弟子以及后起的孟、荀对于整理、阐释、传播上古文化和孔子学说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传统为后世士人所继承、发扬,他们一直以“为往圣继绝学”、继往开来为自己的责任、使命。这种薪火相传的事业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不曾中断。秦始皇焚书,使中国上古典籍遭到全国性的空前浩劫。项羽火烧咸阳,又使秦宫所存典籍再毁于火。上古典籍得以流传至今,全赖汉初一批年事已高的经师口授。一幅“伏生传经图”足以令人动容。自宋以来,随着书院兴起,私人讲学盛行,刻印书籍规模日大,这种文化传承的实绩更加明显。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历劫难而从未中断,同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以传道为己任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其二是对社会的批判。优秀士人始终以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基本准则为己任。在政治上,他们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让民众丰年温饱,灾年免于死亡。家给人足、天下太平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可是,由于诸多统治者的自私、短视、贪婪、暴虐,他们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使得“道”不断遭到背离、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大致说来“天下无道”之日多于“天下有道”之日。而且,由于“道”带有理想性,难以逐一落实,故而即使在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日,背离道的举措和现象也会时有发生。因此,为维护道而批判现实,为坚持“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理念而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一大重要任务。面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他们或是作苦口婆心的劝诫,陈说利害,提出建设性意见;或是慷慨陈词,作猛烈抨击,以期引起震动。从流传至今的历代“名臣奏议”、诸多名士文集,我们都能见到这类政论,一些文字至今仍使后人震撼、感动。为维护道,古代士人表现了可贵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从把持朝政的种种邪恶势力(外戚、宦官、权奸、佞臣),到为恶一方的豪强和虎狼之吏,都是他们批评、抨击的对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孝经·谏诤章》),明确认为,当君父违背道义之时,所从的是道义而不是君、父。所以,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这类犯颜直谏,其尖锐程度往往令人吃惊。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这对维护社会正义,伸张社会正气,兴利除弊,协调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都曾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屡屡摆脱社会危机,由乱而治,这同一代代优秀士人持续的社会监督、批判是有关系的。
其三是道德教化。为求“道”的实现,中国古代士人在作社会批判的同时又自觉从事道德建设,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但这项“以教化民”的工作,主力军、施行者还是士人。对于这项使命,士人是自觉的。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后世也有“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明儒学案》卷六十)之说。在中国古代,优秀士人既是帝王师也是庶民师,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后世的乡学、社学既是普及文化的场所,也是“导民善俗”、“以成其德”的场所,而主其事者主要是乡里士人。自“乡规民约”兴起后,它对提升民德、建立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曾起了重要作用,而其倡导者也是士人。著名的《蓝田吕氏乡约》便是北宋理学家吕大防、吕大钧兄弟发起制订的。中国士人多重家教,他们曾制订各种家训、家规。这类规、训不仅影响一家、一族、一方,甚至影响后世。比如,《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曾国藩的家训等便产生了这种影响。明清的文士曾留下了一批“清言”集(例如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等),其中诸多清新隽永、意味深长的名句、警语、格言对于人们陶冶情操、怡情养性、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均有启迪,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宋元以来,戏剧、小说、说唱艺术兴起。这类文学形式固然以娱乐为主,但又明显具有“觉世”、“醒世”、“警世”的意图、功能。创作这些作品,也是士人为教化所做的工作。
其四是匡救社会危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家国情怀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得更为炽烈。由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所决定,中国古代社会屡屡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由于士人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洞察力并熟悉历史经验,他们是社会危机的最早察觉者,是人群中的“先知”,是最早敲起警钟的人。在危机刚露端倪之时,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呼吁、推动者。在中国古代的几次变革中,士人均起了这样的作用,而在近代更为明显。鸦片战争前夜,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危机也已显现端倪,呼吁清朝政府主动“自改革”的便是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士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呼吁、发动变法维新更是人所共知。而到危局已现之时,优秀士人则是勇打先锋、率众力挽狂澜的领头人。东汉末,由于桓灵昏淫、宦官专权,暴风雨(黄巾起义)即将来临。这时,起而抗争、力图匡救的乃是李膺、陈蕃等“党人”。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包围汴京,昏庸的宋钦宗为向金求和竟罢免抵抗派首领李纲,自毁长城。危急之时,“太学诸生陈东等上书于宣德门”,“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迫使钦宗收回成命。明末“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清初江南士人的抗清斗争,都具有这样的性质。至于近代的“公车上书”更是如此。在这些时刻,为了匡时救世、力挽狂澜,不少优秀士人甘冒杀身灭族之险,真正做到杀身成仁、以身殉道,他们的使命感、担当精神以最炽烈的形式得以显现。
士虽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社会阶层,但它毕竟从属于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因此,他们所坚守、维护的“道”只能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他们的使命、责任其指向只能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社会秩序。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道”,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只能是某一社会、某一时代的基本价值、准则。这种历史局限是不言而喻的。自从中国近代出现了新的经济、政治力量,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士人转化为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是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代言人,阶级属性发生了变化。他们自觉继承并大大发扬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担当精神,但两者所坚守、维护的“道”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乃是他们欲图建立、并正在建立中的新型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他们所担负的乃是在中国建立新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振兴的新使命、新责任。概言之,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始终未变,但其具体使命、责任则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
最后尚需述及的是,由于儒家是封建等级制的维护者,因此,他们的责任观是受等级地位限制的,不妨将其称之为“等级责任”观。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篇、《宪问》篇)。在他看来,众多的“不在位”者既不必谋政也不应谋政,他们与政是没有关系的。对此,后来朱熹作了更明白的解说。他认为,所以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因为人们身居不同等级地位是“各有分限”的,所以,“田野之人,不得谋朝廷之政”(《朱子语类》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不在其位章》)。所谓“田野之人不得谋朝廷之政”,在中国古代几成定规,影响所及,更使得不少家庭、家族的家规、族规严格规定家人、族人“不许谈朝廷政事”。这种“莫谈国事”的训诫、禁忌势必严重扼杀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使他们对国事采取与己无关、漠不关心的态度。到近代,这种观念受到严复、梁启超等新学家的严厉批判。他们指出,那时中国人之所以爱国心薄弱,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漠然不少动于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同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是分不开的。经由近代新学家的批判,随着“主权在民”说开始在中国传播,这种观念的影响逐渐削弱。而随着西方近代权利义务观的输入,人人皆有应享之权利和应尽之义务的观念逐步取代了中国古代那种“等级责任”观。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使命感论文; 读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后汉书论文; 士志于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