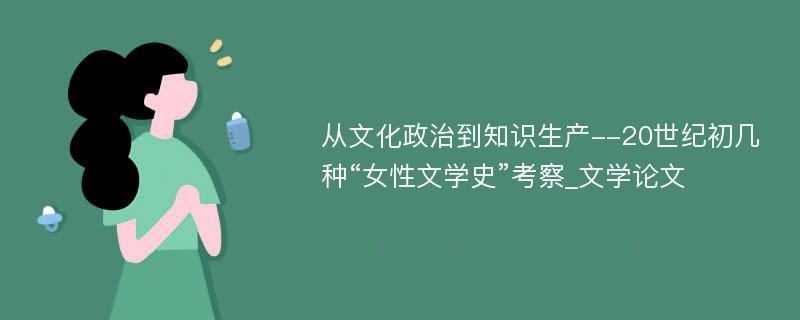
从文化政治到知识生产——对20世纪早期几种“女性文学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文学史论文,政治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性别研究进入文学领域最直观的体现,“女性文学”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成为一个具有较大的挑战性而使用频率颇高的“新兴”概念。如何来理解这一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特定的文学现象,显然是我们分析“性别”与“文学”关系的重要前提之一。
作为一种参照,可以注意到,早在20世纪早期,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1916)、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1930,初版名为《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及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1927)、《中国妇女文学史纲》(1932)等一系列著作,就已经在“妇女/女性文学史”的格局中基本构建起了“妇女/女性文学”的概念,并从此概念入手,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风貌,为处理“性别”与“文学”关系初步确立了实践意义上的范例。
然而,有意味的是,这样的“妇女/女性文学”历史资源似乎并没有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得到充分的重视。作为一种例证,通常,我们会将1981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朱虹教授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① 一文,作为“女性文学”概念在中国登堂入室的起点。② 在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性的绞合中,在知识生产的断裂中,如何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对“女性文学”做一种整合性的理解,显然就成为今天的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重要命题。
搁置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一系列相关的疑问也就油然而生:在20世纪早期,“妇女/女性文学”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境中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的?它所指称的文学现象是否与1980年代之后经典西方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相一致?如果存在着差异,我们今天又如何来理解这种差异?等等。
一
作为“妇女/女性文学”诞生的重要场域之一,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较为完整地提供了20世纪早期文学界之于“妇女/女性文学”的最初想象。
对于谢无量来说,“妇女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他关注的焦点,显然首先是与“妇女”在晚清以来被重新发现、重新定位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中国妇女文学史》序言中指出:
天地之间,一阴一阳;生人之道,一男一女。上世男女同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又倡男女平权。上世男女同等者,自然之法也;中世贵男贱女者,势力之所致也;近世复倡男女平权者,公理之日明也。③
尽管谢无量还是以传统的阴阳学说为起点来阐释两性之间的关系,但可以发现,自“男女同等”、“贵男贱女”到“男女平权”的两性关系的梳理,更多涵盖了晚清以来以“妇女解放”为核心的“现代”性别意识,这显然构成了他讨论性别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谢无量并没有仅仅将性别问题局限于性别文化内部来进行讨论,在他那里,性别关系不仅成为阐释天地变化规律的一种依据,而且也被用来理解从“上世”、“中世”以至“近世”的历史演进脉络——很显然,在“男女同等”、“贵男贱女”到“男女平权”的两性关系演进与“上世”、“中世”以至“近世”的历史演进之间,作为两者可以有机结合的隐性逻辑,晚清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历史进步论观念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将两性关系理解为是和历史同步螺旋式发展的,因而男性和女性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平等的关系才不能被简单地处理为是具有永恒的稳固性的,才不是一种刻板的权力等级关系,而是依据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而可以加以调整和改变的。在这样的逻辑中,大致可以发现,至少在谢无量的论述中,妇女解放思想实际上要搁置在晚清以来盛行的进步论史观格局中进行阐释,才获得了自己的存在合法性。
以上述写作初衷为起点而展开的对于“男女平权”这一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建构,其间的复杂性也就值得细细体味。作为阐释“男女平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如何理解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显然是论述者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话题。谢无量指出:
“夫男女先天之地位,既无有不同;心智之本体,亦无有不同”,④ “体力之不齐耳,至于心智之在内者,固不能有所损”。⑤
在他看来,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可以做一种两分法的区分,一方面,他承认两性之间的确存在着体力上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两性在更为重要的“心智”上,则是相同的。这种颇具近代西方“科学”色彩的两分法,显然是谢无量汲取了晚清以来时人对于两性看法的结果,在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中,早已有类似的表述。⑥ 当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在这样的层面上被讨论的时候,可以说,谢无量其实是通过“世界所公认”的“常识”,强化了“心智”在建构人种优劣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而淡化了男女之间本来存在的“体力”差异,从而构筑起了女性可以与男性“平权”的逻辑起点,即,女性可以通过发展“心智”来“忽略”“体力”差异而达到“平权”的可能。
建立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在理解两性之间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关系的时候,作者反思的目光自然就会越过“体力”这样单纯的生理因素,而落在那些影响、制约女性“心智”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上。在谢无量看来,之所以会形成男女不平等,其历史根源在于,“由数千年以来之境遇、习惯、遗传有以致之”⑦,而其中,妇女“教育”的缺失就成为最关键的原因。谢无量指出:
“欧美诸邦,凡男女皆较之学,则女子之才能,已往往与男子争衡,任职受事,敏达不减男子”,⑧ 而“考诸吾国之历史,惟周代略有女学,则女子文学较优于余代。此后女学衰废,惟荐绅有力者,或偶教其子女,使有文学之才,要之超奇不群者,盖亦仅矣。”⑨
在这里,通过将培养女性“心智”的“女学”搁置在纵(历史)横(地域)的坐标轴上,同时策略性地将“女子文学”当作“女学”最重要的内容和结果,作者在“女子文学”、“女学”、“男女平权”与“社会发展”几者之间建立了逻辑关联,并由此发掘出了中国妇女为何落后、中国社会为何衰微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谢无量之所以强调女学,其意图并不在于恢复已有的自周代已降的女性文学传统,更为深层的缘由,是想以西方女子教育为比附,真正走向男女平等的文明社会。这样的话,“女子文学”和“女学”的意义显然就会被放大——“女学”不仅承担了妇女教育的功能,更为重要的,还成为了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而“女子文学”作为验证“女学”兴衰的主要场域之一,也就间接地与社会进步发生了逻辑上的关联。当“女子文学”和“女学”在这样的层面上被讨论的时候,其在中国历史语境中最终的缺失,也就不只是指向了男女不平等,而必然会带来对社会/文化不平等的反思和拷问而指向未来更为合理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
由此,谢无量何以要书写“妇女/女性文学史”,在性别文化的维度上,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至少包含了这样几点内容:以男女两性关系的历史演变为切入口,以历史进步论为核心,来论证“男女平权”的必然性;以“心智”、“体力”两分法为进口,引入西方“科学”视野,来为“男女平权”确立理论依据;以“女子文学”/“女学”的兴衰来考察社会历史行进的合理性,进而探索“男女平权”基础上的社会/文化重建的可能性。
如何来评判谢无量的上述论述?应该说,谢无量对于“妇女文学史”写作意图的阐述,特别是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存亡有机勾连在一起的论证思路,相当完整地汲取、延续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论述。比如梁启超在论及妇女/妇学问题重要性时就指出: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⑩
而倡导女权最为用力的金天翮更是认为:
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11)
正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晚清以来,“妇学”、“妇女/女性”、“救亡”、“新中国”等一系列概念在被使用的时候,总是被不容置疑地赋予了某种清晰的递进式逻辑关系,性别问题以及由此生发的妇女解放运动,因而被熔铸进了鲜明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色彩:当性别问题不仅仅在家庭、伦理内部进行讨论,而是因为妇女被当作未来的“国民之母”而被放大为“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的时候,事实上,“妇女解放”就被赋予了某种强有力的合法性;“妇女”本身也就不只是一种边缘的亚文化的存在,同样也可以翻转为一种有力量的、可以影响甚至是可以改造主流社会/文化的资源了。高彦颐(Dorothy Ko)因此总结道:
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时期(1915-1927),有着落后和依从的女性身份,一直是一个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紧迫问题。当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时,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被男性外国强权“强奸”和征服。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也对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来说,女性启蒙成了一个先决条件。(12)
当“妇女/女性”无论是在社会实践中还是在文化象征的意义上,都成为晚清以来“中国”的代言符码的时候,那么,经由对“妇女/女性”的启蒙和改造通往“现代中国”,也就必然成为晚清以来的知识界在处理妇女问题时心照不宣的潜在价值指向。
将谢无量之于“妇女文学史”的写作意图搁置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考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所呈现出来的性别立场,正表现了“妇女问题”之所以会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得到重视、得以呈现的特殊性所在:即,性别问题在晚清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建构息息相关的重要社会问题,“妇女/女性”也好,“妇女/女性文学”也好,因而才会成为知识界在参与“救亡”运动时反省并改造已有的知识生产的重要资源;“男女平权”这样的思想意识的产生,由此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中国妇女群体内部产生,而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在遭遇到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后重估/重述历史的结果。
二
作为“妇女/女性文学”概念得以诞生的另一维度,在20世纪早期,“文学”以及“文学史”为何会横空出世,而成为当时人们讨论性别问题的重要领域,显然也值得进一步深究。
谢无量这样来规定“妇女文学史”的基本研究范式:
兹编起自上古,暨于近世,考历代妇女文学之升降,以时系人,附其制作,合者固加以甄录,伪者亦附予辨析,固将会其渊源流别,为自来妇女文学之总要。(13)
当谢无量以“考历代妇女文学之升降”作为书写“妇女文学史”的“文学”基本出发点的时候,可以发现,他的关注重心其实不是落在“文学”作品本身,而更多是放在不同时代的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上,其中,“存真辨伪”是手段,归纳总结“渊源流别”则是归宿。因而,如何以文学作品为有效切入口,在线性的时间序列内来叙述文学的演进过程,才是书写者关注的焦点所在。
有意味的是,谢无量对于不同的“文学”潮流内在演变规律的把握,又总是自觉地与周代以降的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考察密切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他对“文学之升降”的理解,由此也就与其对“妇女/女性”问题的关注相仿佛,更多指向了那个隐匿在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背后却决定了其兴衰成败的更大的历史逻辑的描述与剥离。这种以时间为脉络、以文学为场域、以总结历史兴衰为旨归的“妇女文学史”写法,因此就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而与传统的基于文学文本搜集整理基础上的“文苑传”、“诗词文话”有明显的区别。
这样的对于“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基本价值指向的设定,在1920年代以后的其他书写者那里得到了延续。对于宣称“似赓续谢史而作”(14) 的梁乙真来说,“取清代妇女文学,汇合成编,以诗为径,以史为纬,知人论世之外,兼广春秋笔削之意”(15),更成为自觉的追求。当“知人论世之外,兼广春秋笔削之意”成为主要的写作目标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妇女文学史”的写作就成为一种颇具史家讽谏意味的手段,而具有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写作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汇编清代妇女文学的背后,其实是暗含着书写者意欲在“诗”与“史”的交织中重绘中国历史/文学地图的野心。
而谭正璧之所以要继续撰写“妇女/女性文学史”,其意图也没有超脱上述范畴,仍然是落在考察隶属于“妇女/女性文学”的各种文体、流派的内在演进脉络上的:
谢、梁二氏,其见解均未能超脱旧有藩篱,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故其所述,殊多偏狭。本书则以时代文学为主。例如自宋而后,小说戏曲弹词居文坛正宗,乃专著笔于此。(16)
谭正璧显然不太满足于仅仅形成一种“妇女/女性文学”的“总要”或汇编,而更强调要透过“妇女/女性文学”的视野,去辨析和重新定位每个时代的“文坛正宗”。如果说在谢无量、梁乙真等人那里,“妇女/女性文学”对于描绘历史/文学行进路径而言,更多具有“破”的意义的话,那么,谭正璧已经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已经开始关注引进“妇女/女性文学”的维度到底能发掘哪些历史/文学史的新貌。由此,像“小说”、“戏曲”和“弹词”这样的文类,尽管没有被历朝历代的主流文坛所重视,却因为与“妇女/女性文学”有重要关联而被发掘出来,并被推举到了“文坛正宗”地位。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谢无量等人之所以要撰写“妇女/女性文学史”,从“文学”的范畴上来考察,主要是与其对文学描述/归纳方式的变革以及通过这种变革所希冀达到的重新观照历史的企图息息相关。由此,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就是,为何在谢无量等人眼中,“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功能会如此类似于前面“妇女/女性”所被赋予的角色,而总是要指向沉重的“史学”目的呢?
如果扩展一下视野的话,就可以发现,这种“以文观史”的企图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与晚清以来以“文学史”为核心的西方“历史”叙述规范的中国化潮流息息相关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史”这样的西方学术范畴何以能在晚清中国逐渐深入人心直至完成本土学科建制,构成了理解“妇女/女性文学史”何以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
作为一种舶来品,“文学史”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国,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常常被理解为,在晚清中国,“传统的史学遇到了科学史学的强力挑战,以政治为核心的历史观念逐渐瓦解”,使得“文化史观代替政治史观,以多种领域的历史描述取代帝王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描述”成为可能,(17) 作为文化史的重要形式之一。“文学史”也就在学术嬗变的意义上获得了“跨语际实践”的契机。
而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文学史”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还与“史学”在晚清所受到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密不可分。在晚清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语境中,基于“国粹以历史为主”、(18) “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19) 的普遍认识,“史”从“经”、“子”、“集”各部中脱颖而出,而格外受到重视,成为“保天下”的重要途径。“文学史”显然也被赋予了这样的功能——按照中国文学史最早的编纂者林传甲、黄人(20) 等人的说法,是借助“文学史”这种新的媒介,可以重新建构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在传统文化大厦面临倾覆的危机时刻,在“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21) 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界共识的前提下,藉由“文学史”而进行的文学传统的清理显然具有了文化保存/再造的意味,在“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22) 的意义上就潜在地与“救亡图存”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而对于胡适这一代五四学人来说,提倡“文学史”的用意则更进了一步:
现在谈文学的人大多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因为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故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23)
在胡适看来,“文学史”的出现不仅仅是收录和描述历朝历代的文学状况,更为重要的使命,是要建立“历史进化”的观念,并在此观念下,为今天的文学/生活的变革寻找到历史依据。这样的理解,不仅呼应了自《天演论》以来的晚清学界对于中国既有历史观的挑战和质疑,(24) 而且试图更进一步,希冀在以“历史进化”为核心的新的历史观的建构基础上,激活被湮没的另类文学传统(如白话文学),甚至再造新的时代文学,为当时的社会转型提供文化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史”这一范式所具有的“明变”“求因”(25) 的功能,最终其实指向的是对“旧的”、“死的”文学的颠覆,以及对“新的”、“活的”文学的召唤和形塑。因此,晚清以来的知识界对“文学史”这一文学研究范式的倡导和实践,不只是体现了新旧两种历史观的更迭,更隐含着时人企图借助“文学史”进行“救亡”与“启蒙”的努力。
如果说“文学史”的应运而生寄寓着晚清以来的学界试图通过转变学术范畴/范式以应对学术/社会的多重危机挑战的话,那么,它也就必然与前面谈到的“妇女/女性”所承担的使命殊途同归,融汇贯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经历了从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救亡重心变迁之后,知识界对于“妇女/女性”与“文学”/“文学史”这两者的强调其实都覆盖着晚清社会危机时刻对于知识生产体系更新的要求,一种希冀以新发现的知识视角、资源和路径去回应和介入变动的社会现实的企图。
因而作为两者交集的结果,“妇女/女性文学史”的诞生,其意义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内来加以分析,而更应该当作一种文化政治事件来加以理解了。谭正璧因而这样来描述“妇女/女性文学史”:
所谓女性文学史,实为过去女性努力于文学之总探讨,兼于此寓过去女性生活之概况,以资研究女性问题者之参考……故女性文学史者,女性生活史之一部分也。(26)
将“女性文学史”、“妇女生活”和“妇女问题”看作是彼此打通,甚至是可以致密缝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对于“妇女/女性文学史”的理解,显然正体现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知识界对于拯救时局的“现代”知识的期待,是“知识”与“社会”应该互动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
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由此可以说,无论是从纵向的时间脉络中去摸索各种文体的更替历程(如《中国女性文学史》),还是从横向的地域文化背景出发去把握文学流派的变迁(如《清代妇女文学史》),在回应晚清以来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的层面上,谢无量等人的“妇女/女性文学史”与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俗文学史”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分享了晚清以来从另类的看似“边缘”的视野和资源对历史/现实秩序的质疑,都尝试在“时间”、“进步”、“发展”的脉络中来为历史/文学重新编码,同时也都试图复原被原先主流的文化/文学秩序镇压的文学的多种面向……在这个前提下,可以看到,尽管“妇女/女性文学史”具有一种亚文化色彩,但其问题意识、基本形态和价值指向却因为包孕着“现代”文学研究者重构文学/文化秩序以救世的努力,而与正在形成的其实越来越趋于主流的“现代”社会/学术形成了内在呼应性。
三
当“妇女/女性文学史”的发生被看作是一个汇聚了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学术转型和文学重构等多重意味错综复杂交织的结果的时候,很显然,进入这样的“妇女/女性文学史”遴选视野的“妇女/女性文学”,其基本内涵与价值指向当然也会被赋予某种复杂性,而需要我们细加梳理了:搁置在晚清以来的中国语境中,“妇女/女性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是如何被设定的?今天的我们又如何来评判这样的“妇女/女性文学”概念呢?
在20世纪早期的三本“妇女/女性文学史”中,可以看到,不同的著者对于“妇女/女性文学”的理解因时代、角度的不同,是存在着内在差异的;但如果进一步推敲,又会发现,在基本立场、内涵设定与功能定位方面,这些理解却又不乏共识。大致说来,以下几点共识颇为耐人寻味,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在“妇女/女性文学”创作主体的理解上,无论是谢著、梁著还是谭著,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全体女性作家。也就是说,作家的自然性别构成了他们甄别“妇女/女性文学”的第一要素。这种看法和我们今天通常从“女性意识”(27) 或者“女性主体”(28) 这样的“女性主义”立场上来判定“女作家”是否是“女性作家”,来认定“妇女/女性文学”的本质属性,显然是颇有差异的。联系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不难发现,这种将全体女作家的创作纳入“妇女/女性文学”的做法对于当时既有的文化/文学秩序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谭正璧曾经回忆,当时的国人认为其编撰这样的女性文学史是为了“取悦女性”,“而讽以何不另编男性文学史”。(29) 当全体女作家的创作不分良莠、不论贵贱甚至不辨性别意识地成为像“文学史”这样的新兴学术研究的对象的时候,可以说,它本身就以对固有的文化秩序的强烈冲击而制造了一个超出了我们今天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妇女/女性文学”范畴的更为阔大的空间,一个企图通过为全体女性正名而指向的“同为人类、悲乐与共”(30) 的“平等”、“博爱”的乌托邦空间。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女性文学史”的书写者们对由此而被“发现”的“妇女/女性文学”,大都用了一种貌似公允的方式作了其实并不是太高的评价。谢无量认为:
然自来文章之盛,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者,莫不有境遇之差有以致之。(31)
而谭正璧后来更是直言不讳地说:
若问封建时代女性的作家在文学上的贡献有些什么?那真如近人辉群女士所说:“真是我们妇女界的一件耻事”。但是,这并不是女性内心的弱点,这是长期受了男子的束缚与社会上的不平等境遇所造成的结果。(32)
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将妇女文学的羸弱归咎于妇学传统的中断或者男权文化对于妇女才华的遮蔽,对“妇女/女性文学”的重视才是有意义的,对其的整理和研究才会被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做;至于“妇女/女性文学”概念的引入,是否真的可以导向对妇女文学的新的价值评价,甚至导向对整个中国文学阐释方式的重塑,等等,却常常是语焉不详的。在这样的叙述逻辑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们对待“妇女/女性文学”的矛盾与纠结以及由此形成的“妇女/女性文学”概念的内在分裂——一方面,在攻击和颠覆旧的知识体系、回应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的文化政治意义上,“妇女/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的价值被放大,也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另一方面,在“文学”/“知识”的内部,“妇女/女性文学”的被贬斥,却分明显现出,“知识”应与“社会”一体化的新的“知识”生产的要求,并没有真正打破传统的知识格局所规定的知识间的不平等关系,因而“妇女/女性文学”的价值在新的知识体系内部依然无法得到认可。
这就是说,尽管“妇女/女性文学”在新旧知识体系的转换之间扮演了类似于推进器的角色,但是,它其实只是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获得了自己的正当性,却并未在知识的层面上取得实质性的正名,也就因此不能在“文学史”所代表的“现代”知识生产格局内赢得应有评价和位置。“妇女/女性文学”这种“名”和“实”分裂的尴尬情形,类似于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状态,相当清晰地折射出,在晚清至五四的知识转型期,由于因社会危机而产生的知识更新要求与知识体系内部的自我调整之间的不平衡性,谢无量等人所代表的现代文学/知识界无法弥合在“新知识”评价上的内外分裂,因而出现了双重标准;由此导致像“妇女/女性文学”这样的概念,并未实现从文化政治到知识资源的有效转换,因而只能在功能的层面上被使用,其潜在的巨大能量就无法被真正激活。
与这种对“妇女/女性文学”的历史位置的定位相呼应,在“妇女/女性文学”的边界设定上,各位著者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开放姿态,也很值得体味。对于谢无量来说,“妇女/女性文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边界是不同的。在唐代之前,“妇女/女性文学”主要被理解为是隐藏在帝王将相帷幕后的后宫权贵女性们的往来唱和,宫怨情仇,间或有一点民间女性的诗文,也常常被他放在论述的边缘;而在宋代之后,“妇女/女性文学”才有了一种向民间取材的倾向,因此像朱淑真这样出身中等家庭的民间女词人,才会被他以专章加以讨论。尽管如此,仍可以发现,像“宋之宫廷文学”、“明之宫廷文学”之类尽管乏善可陈,却依然会被他大张旗鼓地置于每编之首。而在梁乙真的视野中,“妇女/女性文学”似乎需要被搁置在男性导师的统领和引导之下,才能浮出历史地表,他认为:
原夫一代学术文章之盛,必有魁硕杰出之士,以树其风声。于是下焉者,靡然影从,如丸之走坂,水之就下焉。有清一代,二百余年间,其妇女文学之所以超迈前古者,要亦在倡导之有人耳。西河渔洋,树之于前;随园碧城,崛起于后,而期间复有毕秋帆、阮云台、杭堇浦、陈其年、郭频伽……诸人之推波助澜。于是闺檐英奇,玉台艺乘,遂极一代之盛矣。(33)
因此,每一章节设计,他都采取了类似于“袁枚与妇女文学”、“阮元与妇女文学”这样的标题,充分彰显男性导师在塑造“妇女/女性文学”方面的重要性。谭正璧对于“妇女/女性文学”的边界处理则又是一种路数。他喜欢将“妇女/女性文学”作品与女作家的生平事迹进行“知人论世”式的对应性解读。尽管按照通常的说法,女作家一般都是生活在“内闱”中的,但在谭正璧的视野中,帷幕内外并不意味着绝然分隔,而是具有某种相通性的;女作家的生平事迹因而并不只是个人闺阁内的爱恨情愁,而是因为承载着时代社会的大变动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的缩影。例如在论述李清照时,谭正璧就将“靖康之耻”理解为李清照命运转变的关键点,并将其作为李清照文风从“欢娱”变为“颓丧”的最为重要的缘由。(34)
无论是将“妇女/女性文学”放在何种格局中,显然,三位著者都提供了与我们今天强调的“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的“妇女/女性文学”概念所不一样的边界处理方式,其中隐藏着一种通过向公共(男性的、主流的、国家的)领域延伸、渗透来达到提升“妇女/女性文学”意义的目的。这样的开放化边界处理,其正当性或者可以援引高彦颐对于传统中国妇女的生活特质来加以理解:“把家庭和政治强加界线是误解的,因为一方面它忽视了家和国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忽视了家庭内、外的男、女之间的相互作用。”(35) 当妇女生活本身具有与国家、男性等多种维度的互动性的时候,“妇女/女性文学”当然就不能被僵化地理解为是局限在妇女闺阁之内的创作,而更应该在强调其与外部世界的交叉、重合、叠加等层面上来加以定位了。
问题在于,如何切实把握住这种“公”(国家)与“私”(家庭)互动所形成的讨论“妇女/女性文学”的新空间,而规避掉简单从“公”或“私”的一端来定位“妇女/女性文学”所可能出现的偏狭和断裂?对于三位著者来说,显然,如何在“公”(国家)与“私”(家庭)互动的“现代性”要求与“家国一体”甚至以“国”取代“家”的传统格局之间,建立必要的区分,这方面的考虑应该说还不是很充分。在单向性地引入了“公”的资源来扩展“妇女/女性文学”的阐释空间后,事实上,谢无量们同时也默认了对“公”的过分看重和对“私”的简单贬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所暗含的价值评判落差,仍然被简单复制到了对“妇女/女性文学”的概念的命名中,并落实为以单一的“公”领域的文学生产要求去苛求事实上游弋在既不是“公”又不是“私”而是“公私兼顾”暖昧地段的“妇女/女性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尽管已经以暧昧的边界制造了“妇女/女性文学”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把握可能性,但是谢无量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一种建构“妇女/女性文学”本土独特性的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矛盾情形中,在确立“妇女/女性文学”价值高下的标准上,著者们也就普遍会在“文学”与“道德”之间小心翼翼地谋求平衡。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如何对待像薛涛这样的妓女作家。谢无量用了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相对主义策略,对薛涛的文学价值作了颇有意味的肯定性评价:
名妓工诗亦通古义,转以男女慕悦之实,托以诗人温厚之辞。故其言雅而有则,真而不秽,流传千载,得耀简编,不能以人废也。(36)
将人(职业)与文分开,将形(诗人之辞)与实(男女之情)分离,谢无量完成了对薛涛文学价值的评析,这种评析尽管逻辑上相当完满,却也不免陷入了对“妇女/女性文学”所隐含的“妇女/女性”与“文学”这两个维度的分裂。谭著有意思的地方,是对薛涛是否是妓女进行了详细辨析,指出“在唐、宋时女子之入乐籍,全是以她的艺术,并不如后世娼妓之必兼卖淫,但因多与男子交接之故,所以后人竟视之和娼妓一样”。(37) 他还特别用“白衣处女”形容其诗作。(38) 在谭正璧的视野中,道德化和纯洁化,显然仍然可以与“才华”有机结合,用来评价女作家的创作成就。
可以看到20世纪早期的“妇女/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们对于中国传统的才女文化/标准的一种自觉承袭。作为一种体制之内可以容忍的特殊的文学产品,通常,传统语境中的“闺秀”、“才女”诗集/文集总是混杂着“才华”与“正始”(美德)的双重要求。例如,完颜恽珠在编撰《国朝闺秀正始集》时,会强调“凡篆刻云霞、寄怀风月,而义不合于雅教者,虽美弗录……庶无惭女史之箴,有合风人之旨尔”。(39) 这样的编选标准,既指向了文采,又突出了儒家主流规范对于妇女伦理道德要求,由此遴选出来的女性作家/作品,当然在价值指向上就具有一种内在的悖论性了:既有以“才华”彰显女性个性,从而试图逸出传统文化之于女性种种规范的努力;同时又企图以对“正始”的强调来获取正统权力体系对于女性作家的认可与支持。
当然可以认为,“对这些享有特权的才女来说,儒家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力量,既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机会”,(40) 从而在现实生存的策略上,发掘出“文学”、“才华”并不必然与“道德”对立甚至还有对于“道德”的有效利用的一面;然而,谢无量们对于薛涛这样的个案处理却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必须看到,在评价薛涛这样的在正统文学秩序内颇有争议的女诗人的时候,研究者更强调的其实并不是“妇女/女性文学”的参与者们对于“道德”的利用、修改甚至僭越,而恰恰是要通过将“才华”与“身体”的剥离,彰显背后“道德”强大的操控能力——某种意义上,“才华”只有附着在纯洁的“身体”上,其价值才能得以确认。也就是说,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像薛涛这样的作家,其文学才华只是构成了她进入文学谱系的一种基础;至于她是否可以被论证为一个有价值的作家,更多还是要立足于其人、其身体是否可以经得起“道德”的检视。
这种“人”与“文”的分裂以及由此企图通过“道德”重新扭结两者的努力,在晚清以来的中国语境中,显然焕发着别样的复杂意味。可以分辨出,这种思路背后所隐藏着的被晚清以来的危机社会所激活、所挪用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救世观念,如何曲折地附着于同时却又改造了女性“才华”这样的“现代性”、“个人性”的资源,成为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界评价“妇女/女性文学”的主要依据。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薛涛这样的妓女作家才会被阐释为是具有道德自律性的,其才华才会被赋予某种合法性,才能既作为“妇女/女性”的代表同时又作为“文学”的典范而被危机现实所接受。这种处理方式,相当明显地呈现出晚清以来的学界特别是文学界,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既要反传统又要倚重传统、借用传统的悲情与困境,是谢无量们因为过多地强调“妇女/女性文学”的文化政治意义而必然出现的首鼠两端式的断裂。
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知识”应与“社会”互动的知识更新方式的结晶之一,“妇女/女性文学”本来正可以表征这样一种新的现代“知识”概念的呱呱坠地——在内涵上,这种新的“知识”可能溢出了原来的经史子集格局,却又不完全认同于西方学术传统,而是在晚清以来特有的社会/文化危机的意识的激活下,对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进行反省、切割和重组后,一种更具有现实回应性和知识敏锐性的产物。然而,“妇女/女性文学”这一“知识”生产个案表明,当研究者们大多从“妇女/女性”、“文学史”这样富有文化政治意味的问题/范式出发,自外而内地来建构“妇女/女性文学”的形象和内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何来处理“名”/“实”、“公”/“私”和“人”/“文”这样的涉及知识内外的种种关系,20世纪早期的“妇女/女性文学”研究者并没能在“文化政治”与“知识生产”之间寻找到彼此可以推进的合适资源、路径和方法,因而往往只能在象征的意义上暗示新的知识生产格局的正当性,却无法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真正生产出与此相匹配的新的知识。
注释:
①(27) 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③ 关于这一点,已有较多的论述,如降红艳:《“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61~74页。
③④⑤⑦⑧⑨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1933年重版,第1、2、2、2、2、1~2页。
⑥ 金天翮指出:“据心理学而验脑力之优劣,以判人种之贵贱高下,此欧洲至精之学说也。今女子体量之硕大,或者不如男人,至于脑力程度,直无差异,或更有优焉。此世界所公认也。”《女子之能力》,见《女界钟》(金天翮著,陈雁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5页。
⑩ 梁启超:《变法通议》,载《饮冰室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0页。
(11) 金天翮:《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版。
(12)(35)(40) 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2、14、17页。
(13)(31)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绪言》,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3页。
(14)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4页。
(15) 王蕴章:《清代妇女文学史·王序》,载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页。
(16)(26)(29)(30)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初稿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影印。
(17)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7页。
(18) 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转引自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第172页。
(19) 刘光汉:《论古学出于史官》,转引自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第172页。
(20) 一般认为,林传甲于1904年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黄人于1905年撰写了规模更为庞大的《中国文学史》。参见戴燕:《文学史的权力》之“附录二: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写作”、“附录三:文学史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21)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目次》,第24页,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83页。
(22) 黄人:《中国文学·总论》,第3-5页,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82页。
(23)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第74页。
(24) 严复在分析“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的“世变”时,将“中西事理”的理解差异作为其中的内在归结:“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也。”严复:《论世变之亟》,《直报》(天津)1895年2月4日。
(25) 梁启超比较新旧“史家”后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第6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页。
(28) 刘思谦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一文中指出:“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32)(37)(38)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叙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影印,第13、174、180页。
(33) 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215页。
(34)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影印,第218~229页。
(36)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第二编·第五章》,中华书局1915年版,第123~124页。
(39) 完颜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序》,转引自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24页。
标签:文学论文; 谢无量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平权运动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