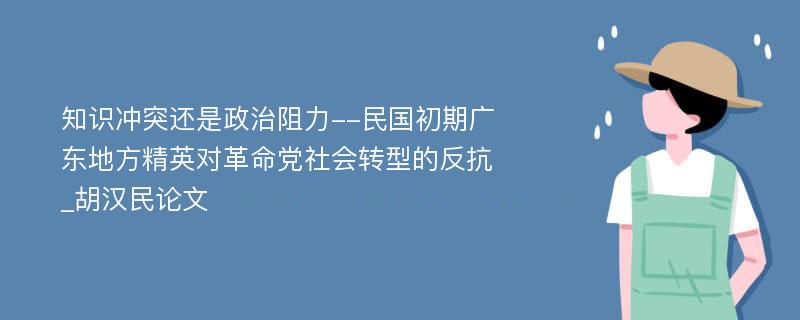
知识冲突还是政治反抗——广东地方精英对民初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抵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党人论文,广东论文,冲突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1[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147-09
1911年广东光复后,革命党人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军政府,由同盟会—国民党中政治上最接近孙中山的人物执掌政权,尽管他们执政仅一年零八个多月,却为建设新社会付出了很大努力,是革命党人很重要的一次执政实践。不少学者对革命党人掌权的广东军政府做过研究。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考察其时广东军政府社会文化改造之努力与社会回应,讨论革命党人与广东地方精英的关系,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动中知识与政治的影响。
一、清末广东地方精英的“趋新”与社会参与
本文的“地方精英”指接受过相当程度教育,并在地方社会有影响力的群体。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精英”一般指士绅。晚清以后,留学生、新式学堂毕业生等拥有新知识背景的群体大量出现,尤其是科举制度废止后,新教育空前发展,学生规模急剧壮大,新式学堂学生也在地方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晚清广东有一支庞大的士绅队伍。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广东的正途与异途绅士合计有110705人,家庭人口达553525人,属于全国士绅较多的主要省份。[1]广东的新式学堂发展也很快,1909年广东的新式学堂学生超过8万人。[2]尽管从教育背景看,清末地方知识精英可以分为传统士绅、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等几类,但从知识体系而言,地方知识精英难以清晰地划分“新”与“旧”。不少科举体制下的士子,也通过新式学堂接触新的知识体系。据清末两广学务处统计,广州所办各类师范科毕业的681名广东籍学生中,正途士绅占50.4%,1907年设立的广东巡警学堂中的367名学生,都是有功名的“贡监生员”。③1906年设立的广东法政学堂,官额外,另“由各厅州县各保送绅士一名”[3]。广东为近代得开风气之先之区,新知识、新观念较早进入,广东也是近代维新——立宪派、革命派主要人物的故乡,地方精英易于接受新知识,因而在他们身上新旧知识体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和《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等商人团体出版物,都可以反映出商界上层中、西学问都具有一定水平。④
“趋新”意识很强的地方精英,在清末广东社会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7年11月广州地区士绅成立了立宪团体自治研究社,尽管被认为是保守性较强的政治结社,但在普及宪政知识、推动地方自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努力。1909年成立的广东谘议局是清末地方知识精英极为重要的政治舞台,全部来自士绅阶层的94名议员,以谘议局为阵地,在整顿吏治、改良税制、振兴工商业、兴办学堂,以及维护社会治安和改良社会风尚(如禁烟禁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4]顺应时代变化,不少士绅投身商界、学界、报界。受新思想绅商的影响,商界社会参与意识明显增强,成立了政治性组织粤商自治会。⑤粤商自治会、广州总商会、九大善堂等机构都是清末广东很活跃且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1910年广州17家报纸中,8家有“商办”背景,[5]这些商办报纸在传播新知识、开启民智、改变社会观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清末广东学界的社会参与也表现不俗。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广东各地学生富有激情又不失理性与文明。[6]1907年维护西江缉捕权风波中,学生亦是主力军,且表现得比商人更为激进,从维护国家主权高度成立了“国权挽救会”,出版了《国权挽救报》。[7]对于社会问题,学生也并未漠视,1908年学生李鉴渊等曾“以盗风猖獗事,具禀督辕”[8]。这些都显示出广东地方精英很强的社会参与意识。
因为接受新知识、新思想,一些士绅转变为革命派,或同情革命。1904年保送到日本学法政的56名官绅中,就有胡汉民、朱执信、汪兆铭、古应芬等日后同盟会的著名人物。同盟会在海外与康梁立宪派斗争激烈,但在清末广东,立宪派一些人物与革命党则保持良好关系,辛亥革命之前,谘议局副议长丘逢甲已明显同情革命,与邹鲁、朱执信、高剑父、姚雨平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9]据说丘逢甲“喜欢革命党人”,邹鲁曾介绍朱执信到丘任职的两广方言学堂“共事”,丘也多次庇护邹鲁等人。⑥就是深受康梁思想影响的澳门子褒学塾(万木草堂入室弟子陈子褒创办)学生,不少后来也参加了同盟会,其中一些女学生还是军政府女子北伐队的骨干。[10]
从政治立场来看,清末广东的地方知识精英大体可以分为忠清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几类。忠清派重要人物不多,邓华熙、梁鼎芬在广东并无很大影响力,江孔殷深得末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器重,但并非革命党死对头,“曾为革命党尽力不少”[11]。在广东光复中,谘议局消极对待对绅商各界的“独立”,全体议员“皆避匿不出”。[12]正是这种消极态度,使得作为清末重要民权机关的谘议局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立宪派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为革命党人掌权减少了阻力。广州地方精英中的绅商和新知识分子,则频繁活动施压,迫使张鸣岐、李准等人接受脱离清政权的大局。早在1911年10月底,当谘议局还在模棱两可时,“粤垣经绅商学界齐集文澜书院会议宣布独立”[13];并派出粤商自治会人物郭仙洲等前往香港联络革命党人,表示商民赞成共和的政治立场。1911年11月9日绅商各界集议,决定以谘议局为办事总机关,每团体各举五人,推举张鸣岐为临时都督,并拟延请著名革命党人来粤协助张鸣岐办事,[14]最终促成了广东于“刀不血刃”中光复的大好局面。⑦各地士绅不少附从革命,或协助革命党人夺取州县,组织新政权;或与地方官吏合作反正;或领导州县光复。⑧
以绅、商、学为主体的地方精英,也并没有成为旧专制政权的殉葬品。独立之初,一些传统精英也愿意与新政权合作,还得到了任命,丘逢甲曾被任命为教育部长,黎国廉出任过半年多的民政司长,粤商自治会骨干黄景棠、陈惠普等也曾有过任职。民国初年广东商、学等界仍很活跃。据调查,1912年12月广州城迁出闭歇店铺150间,迁入新开289间,增加了139间。[15]受政权更替影响,商业有所变化,但商人规模似未出现大的波动。粤商维持公安会在这个期间成立,民国初年成为左右地方政局的商人组织。学界、商人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1912年“中国同盟会粤支部”有会员128人(注册会员49人,加盟会员79人),商界有48人,工商界加盟的有32人,是各界中最多的,其次为学界,有28人。[16]学、商界不少人通过同盟会进入了省议会。地方精英的社会影响力民初犹在。
二、民初社会改造与地方精英的“不合作”
拥有新知识与革命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执政后即面对恢复社会秩序和建设新社会两大任务。秩序重建上军政府沿用清朝旧法,实施“清乡”,但效果不著。⑨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划,革命政权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扫除积弊”。[17]广东军政府一经建立,便着手改造社会,以“扫除积弊”。然而,革命党人的社会改造却阻力重重。这里以教育、女权、风俗、社会风气、市政等五个方面的改造情况,略做说明。
1.推行新教育
钟荣光任教育司长后,开展了一场以引进西式教育制度为目的的教育改造运动。⑩内容包括:整顿教育机构,设立督学局;重新划分全省为14个学区,将各地中学收归省管;重视社会教育,增设社会教育课,加强体育会、音乐会、改良风俗会、图书馆等建设;整顿规范小学教育,“无论公立私立之校,校中管理教授,一切由校长主之”;加强师范教育,且“令每县各立一女子师范”;支持留学;规范教育经费,严禁地方士绅霸收祖尝学谷及书田花红;树立新学风,销毁宣扬科举功名的旗杆、牌匾;严禁读经等等。(11)新政府对教育改造寄予厚望,钟荣光也满怀激情,但在推行14个余月后,钟荣光不得不带着“建设无多”的无奈辞职。[18]
新教育之推行并不顺利。督学局本为各地教育行政机关,意在统一管理教育,“惟因教育经费,时时与地方顽劣绅耆冲突”,一些局长也纷纷向临时省会提议裁撤全省督学局,“省会一再函知都督,饬司照行,审计分处,且要求都督将广州市督学局立令裁去”。[19]在各界压力下,1912年冬,督学局陆续裁撤。中学收归省立后,厉行改革,“于是不良之学风,尽行发泄,罗定、潮州则有鼓众罢学之事;梅县则有开会演说,反对省立、塌楼伤人之事;琼崖教员,则因索要薪水,起诉法庭;各县中学之由县呈请改委校长者,若顺德、新宁、香山等,亦暗潮不免”;教育司提倡中学内设立师生恳亲会、学生自治会、学校体育会等,也被指责为“不务大而务小”、“废时荒学”。[20]教育司下令广州严禁私塾读经,甚至请警察厅出面“勒令解散”[21],教育会会员冯愿却公开发布文告抗议。[22]禁收学谷花红,销毁旗杆牌匾之令,更是遭到地方士绅的拼命抗拒,或围攻殴打,或危言恐吓,或置若罔闻,或阳奉阴违,“沿袭如故,所在多有”(12)。甚至一些学堂新毕业的学生还在家乡染指学田。[23]
2.尊重女权,倡导男女平等
革命党人早期领导的反清运动中不乏妇女的身影,广东光复后,广东军政府还组织了“女子北伐队”。1911年12月24日成立广东省临时议会,选举的120名代议士中有10名女性。女议员的出现,被视为革命政权尊重女权的重要体现,“称盛一时”[24]。1912年警察厅长陈景华倡导创立“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收养教育地位低微的婢女、妾侍、尼姑、童媳等妇女,规模一度达600多人在院,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展现了革命政权“尊重女权”的新气象。新知识阶层也以革命理想推动着社会婚姻观念的改变。由孙中山外甥杨某带头,香山乡村出现新式婚礼,“一时乡里莫不啧啧称羡,行将率为婚礼之模范”。[25]同时,在广州城内,改良婚嫁的宣传也正在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26]
然而,新的男女平等观念仍遭遇着社会性别偏见的顽固抗拒。女议员在议会中时遭取笑,[27]1913年2月成立的正式省议会也再没有女议员。广州总商会各善堂曾联合致函都督府指责女子教育院掳禁良家婢女,“何异公家夺人民子女代养媵姬”,属“不应为而为之事”,且“尊卑倒置,尤为不成事体”,一些报纸也别有用心,借机造谣生事,嬉笑怒骂地打击。[28]男女自由婚姻仍不为社会认同。新会县外海乡陈姓男女同姓结婚,不仅被“送官讯办”,且“远近传为笑话”。[29]县知事凌某娶年轻女仆为妻,报纸以讥讽语气报道。[30]一女生“因性染自由,为翁姑逐出”,亦被报纸挖苦。[31]警察厅禁止茶楼酒馆男女同座,报纸对之予以赞扬。[32]此类新闻,当时报中并不少见。受社会观念的制约,新政府对男女同校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新制高等小学,无男女不能同校之文,教育司察其学生年龄,及该地方风气,时有准其同校者,否则照章另设女子高等小学”[33],在推动女子受教育权的同时,却在男女观念上因循守旧。革命党人无法完全摆脱旧有传统观念的干扰,不得不以矛盾的方式演绎着对社会的改造。
3.革除迷信陋俗,传播科学新知
鉴于民间通用的旧历书宣扬封建迷信,“闭塞民智,蛊惑人心”,教育司于1912年下令禁止刻印发行,代之以新历书,“添入世界之新事业,本国之新建设,凡为人民所当知者,附于日历之前后”,而各书坊“以二年通书,早已出版为词,稍有违抗,限制不尽”。[34]为了推行新历法,新政府通令学校改用公历,并取消传统节日假期。1913年春节前,教育司通令各学校,阴历新年一概不准告假。[35]而当日广州就“有公立小学数所,学生请假过半”,“更有一校,教员学生全不上课”。不仅学校如此,“商家仍用旧历,不顾反对中央;报馆则旧历元旦前后,休业十天,新历只元旦休业一天”。[36]
革命政府曾发布命令禁止端午、七夕节等传统民俗,[37]实际却未能切实落实。广州郊区高塘、江村等村乡民不顾禁令筹备龙舟竞渡,“赶搭戏台,及发帖柬,邀附近各村龙船,届时前往赴会”,佛山叠滘乡“各坊连日斗赛龙船,佛山人之往观者络绎于道”。[38]陈景华认为粤剧“劝奖奸淫”等“于风俗人心大有妨碍”,要求多演好戏,“唤起国民爱种尚武之精神”。[39]然“优界学界,各皆踊跃,所惜省教育会,为旧学家组织,屡生反对”,因而“成效未大著耳”。[40]
对于神灵祭祀,省临时议会专案讨论认为“除先师孔子发明儒术,尊崇已久,为吾国所应留存外”,其余“亟应全行废止,以化除迷信陋习”[41]。为禁奉鬼神,新政府封毁寺庙,而广州城内外各街“乃将各庙门额,改称孔子庙,以抵制之”[42],警察厅发觉后,规定“庙内仍有附设土木偶像,即行一律送厅”[43],不少街庙值事“又弃去孔子名目,改称某街某约议事所”,百般抗拒。[44]毁神而尊孔反映了革命党人传统儒家文化情结与激进革命的矛盾心态,尊孔被利用作为抵制改造的武器,也使革命党人的社会改造政令限于被动。香山拟拆学宫大成殿建初级师范学校,却引起“公愤”,官方不得不让步。[45]反对钟荣光的人,也借“取销尊孔”大做文章,致使其陷于被省临时议会纠举的政治风波中。[46]
4.铲除烟赌之害
晚清以来广东赌风兴盛,虽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广东谘议局通过禁赌令,但禁而不绝。独立后,“各属纲纪大弛,私赌林立”[47]。1912年总绥靖处发布谕令厉行禁赌,“如蛮乡巨族有敢庇赌抗捕者,格杀勿论”[48]。然而,“禁者自禁,犯者自犯,通衢孔道,公然聚赌,豪绅巨族,乃开票厂”[49]。赌博严禁不绝,不乏地方劣绅庇护者,番禺黄村“番摊鸽票花会牛牌骰钵,不分日夜,聚众私开。一二劣绅,欲得私规者,又复从中包庇”。[50]也有军人开赌者,“潮军督办行辕内,每日必大开赌场”[51]。顺德的地方民团不仅开花会、牛牌,还“日望政府严禁赌博,免他处开赌,饱其专利”。[52]官员、军队官长私自罚款、擅放赌匪之事,更是屡见不鲜。禁赌某种意义上成为地方官绅团军等牟利的途径,执行禁赌政令的人实即破坏禁令者。
军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烟,包括设立专门的禁烟局;制定《禁烟规则》、《禁烟章程》等;发布禁种鸦片令;收缴吸烟工具;打击鸦片走私等等。由于地方势力的干预,政令实行并不畅通,“四乡烟馆,焚煮自由,乡人吸食,从无牌照”[53]。报纸反映,1912年8月在粤汉铁路沿线的江村、高塘、新街、三华店、源潭、黎洞等处,“烟赌林立,闹热异常,赌匪烟精,如蚁赴膻”,“主其事者,是在土恶”,军队在黎洞私开烟馆,还被烟精殴打。[54]在省城广州,“所谓禁绝者,不过表面上烟店停止交易而已,而聚众私吸者如故,上门贩卖者日多”[55]。
5.城市之改造
1913年3月,军政府内务司计划改良广州市内街道,七十二行商人“多以此属于市政范围,非出自市民公意不可,现市政厅尚未成立,无从规划。当此商业凋敝,人心初定之时,正宜休养生息,以培元气,万不能遽事更张,致形纷扰”,集议反对。[56]
1913年5月,警察厅从拓展交通与改进治安着想,要求广州市内各街限期拆除街闸。[57]各行商人并不拥护,纷纷向总商会投诉,“以目下谣言迭出,宵小生心,猝有警告,无所防范为词,请从缓拆”,总商会因之“函请警察厅长暂从缓办,以顺舆情而安商业”。[58]一些舆论则借机批评军政府,《香港华字日报》的文章称:“不顺舆情,不安商业,奋其独断,操切从事,务必与商民争胜而后止,此岂共和政体所应尔耶?”[59]香港与广东关系密切,其报章舆论对广东社会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此批评,无异于推波助澜。
在商人的抵制下,街闸拆除很不顺利,各大街“均未遵行”。[60]官商双方不得不相互让步,妥协处理,“各街坊自愿将闸门之门楼自行拆卸,及夜间不闭门”。警察厅也表示,“如该街闸闸门尚非阻碍道路,暂仍其旧。惟各街闸之门楼,应将尽行拆卸,并令夜间各街闸一律开放,如有仍闭闸门以困人自困者,即必令拆卸,其夜间遇有盗贼,则由各站岗警察合力追捕,不得放弃责任”[61]。“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景华被龙济光杀害,一些被强行拆卸的街闸又很快恢复,如被陈景华亲自督拆的十八甫德兴桥脚闸门,“各处坊人以陈已枪毙,多有拟建回原闸以自防卫”[62];城内都督府、民政署附近德宣、洛城等街“从前街栅均经拆卸,现龙都督转饬各街栅仍照前安设铁栅,以期坚固而资控守”[63]。从市政建设角度而言,改良街道、拆卸街闸有利于交通与城市管理,革命党人未能充分认识当时社会的情势与利益关系,因而遭到了以商人为主的地方社会之抵制。
革命党人的军政府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还在其他多方面施行社会之改良,可皆因社会支持不够,成绩不显著。如禁卖“猪仔”,虽有孙中山的指令,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海口埠之猪仔店之营业依然如故”[64]。又如取缔娼妓,警察厅专门制订了《取缔娼妓章程》,可迫于娼妓的就业歧视,为解决财政困难,政府不得不改变初衷,变通办法,允许现存者领牌营业。[65]民国初年革命党从革新教育、改变观念、改良习俗、改进风气以及改造市政等多方面谋求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不可否认,对促进社会转型有积极影响。在有限的一年零八个月内,许多社会改造政策还未来得及调整与完善,激进的方式,不合时宜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改造遭遇了重重阻力,甚至招致非议,最终使他们丧失革命政权。1913年6月14日胡汉民被免去广东都督职务,“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钟荣光、廖仲恺等离开广东,1913年中秋节陈景华被龙济光枪杀。革命党人被迫转入与军阀的政治斗争中,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暂告结束。
三、新旧替换背后的政治排挤
由上述可见,军政府社会改造的阻力,主要来自于绅、商、学、报界等。本身具有“趋新”倾向的广东地方精英,为何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如此抵制?抵制的背后又是什么?无疑值得进一步分析。
钟荣光曾称,教育改造“结怨者,皆旧日文墨之徒”[66]。省城十善堂院会社也曾致函省议会,声讨“卫生司董洗病故之屋、剖验已故之尸”,“警察厅误会放奴,任巡士强牵婢女”,教育司“废祀孔圣,废读五经,不分男女幼孩,逼令就学”,为“弗恤民间习惯,强以夷俗施为”。[67]就建设新社会的出发点而言,革命党人确实希望借用西方文明改变广东社会的落后愚昧,军政府首任都督胡汉民曾表示,希望西方的风俗、方法、教育等通行于中国,“任内力行反对见笑于外人之事”[68]。表面上看,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在广东的社会改造是新旧知识体系的碰撞与较量,地方精英对革命政权的不合作与抵制,有知识冲突的原因。
不过,民初社会改造中的矛盾并非完全根源于新旧知识认同之对立。我们也看到地方精英以新知识反击政令的例子,如在反对改良街道时,广州商人运用了“市政”与“市民公意”之类的概念。改造政令也并没有完全体现新知识体系的影响。广东军政府与孙中山关系最密切,在胡汉民的主持下,广东军政府始终认真地执行孙中山所确定的内外革命政策。从现有的孙中山著作看,1913年以前,孙中山并没有一套建设新国家的理论与政策,更多是一种“革命程序论”,就革命后对“旧”社会的改造,只是简单地表述“扫除积弊”。对于如何建设一个新社会,并没有细致的方案,更没有在学理上阐释。[69]孙中山是第一次护法失败后才开始系统进行理论建设。革命党人靠民族主义动员民众,但在民权、民生主义等方面没有很多的理论准备。胡汉民、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陈景华等人虽然希望以西方的经验来改造广东社会,但他们还没有真正学会西方民主社会的建设理论,对建设新国家并无先进方略,在本身传统知识的影响下,更多的是借用儒家道德学说,糅合一些对西方社会的简单认识,治理社会。因而改造政令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如严禁读经而尊孔、开放女子参政而维持男女有别等。
实际上,民初广东地方精英的“不合作”,与革命党人的政治排挤有很大关系。革命党人建立军政府后,胡汉民依据“非同党不用”原则任命了军政府各厅、司主要领导,形成了以同盟会为核心的领导体制。各绥靖处处长、各县县长、各军队长官多为留学生以及新知识阶层。临时省议会选举出来的120名代议士,同盟会“其数得六十余人,实居全体代议士半数”(13)。广东军政府完全由革命党人掌权,立宪派被排斥。清末立宪派主要的政治舞台谘议局被取消,独立之初曾一度以“各界代表大会”作为议政机关,因旧绅商和旧谘议局议员越俎代庖而被抛弃,代之以“临时省会”,而临时省议会中“谘议局旧议员,断无使复活之理”。[70]革命党人与康梁保皇派的敌对关系,并未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缓解。新政府成立即宣布开除康梁省籍,虽胡汉民发布告示,宣称对保皇党一般成员不予追究,“凡不犯今日之刑章,决不追从前之毒恶”,但政治上排除原立宪派的立场很明显。[71]少数与革命党人关系良好的原立宪派士绅,参与革命政府时亦与革命党难以相容。军政府任命丘逢甲为教育部长,却绕过他任免相关工作人员,以致丘不满而不到部办公,并写信给胡汉民直言“不自由之苦恼”[72]。尽管胡汉民后来让步[73],但丘逢甲很快去世,影响极为有限。接近立宪派的黄士龙(原新军军官),虽在绅商支持下,取得参都督职位,却无法为革命党人所接受,胡汉民坦言:“黄为不利于政府之谋,直叛徒也,特以其恶未著,而商民愚暗,故不能取以明正典刑”[74],因而黄很快被排斥。
在清末极为活跃的商界领袖如黎国廉、黄景棠、陈惠普等,也被革命党人疏远。1911年11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香港续举代表人名》中尚有黄景棠,但是几天后的《粤军政府照会驻港筹款局员文牍》中已无之。[75]虽黄景棠被委任为“都督府九等顾问员”[76],实则被排挤,其主持的粤商自治会不复存在。陈惠普光复后组织过国民团体会,不久也被解散。到1913年黄、陈仍健在,但军政府时期几乎从政坛消失,与他们在晚清时期的表现判若两人。不过,1913年6月“粤东学界商界”致电陈昭常,政治上表态支持袁世凯,晚清新思想绅商的代表人物邓家让、黄景棠均有署名。[77]革命党人既然不能成功争取到邓、黄等人,怎么又能指望商界成为革命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呢?
地方士绅则在革命中遭受严重冲击。都督府布告称江孔殷为“劣绅”,“与我义军相抗者”,视之为革命党人的敌人。[78]有言论甚至将江作为“汉奸”声讨。[79]在民初收缴武器的运动中,民军前往其家乡“收缴江昔日清乡所用之枪械,均暂驻江氏大祠堂内”,勒限缴齐,声言“如逾限不缴,定以毒手对待,一时族人恐慌,多有先遁”[80]。民军到东莞收缴保安局枪械,“执独立旗帜”的匪徒将局正陈伯陶(前清在籍翰林)拘拿,勒缴银万两,“陈绅拒之,匪等即欲开枪将其击毙,嗣得众绅为之说情,卒被勒去银五千两”[81]。江、陈皆是在清末广东地方深有影响的士绅,他们的境遇对新政权争取士绅造成不利。独立后各属民军“纷纷向旧日官吏军警及绅士人等挟嫌戕杀”[82],康字营在顺德古坝大肆寻仇,“亡清旧绅,多有被其打靶者”[83]。另一方面,军政府又在文化、经济上推行打击士绅的政策,如规定“不得再藉满清科举功名盘踞学田,霸收祖尝”;命令烧毁所有故家高脚牌匾、资政荣禄第之类;规定将祠庙之牌匾旗杆等物拆除销毁,以免科举功名遗毒影响民众。[84]士绅控制的护沙局之类的机构也被取缔,如顺德护沙局,“素为劣绅魔窟,与亡清官吏,表里为奸,反正时已摧倒”[85]。革命风暴大大削弱了地方士绅的威权,“自反正以后,从前正绅,既多遭盗贼蹂躏,逃亡殆尽,其未遭挫折者,亦自以所得亡清头衔,不足以慑服乡里,且鉴于前车,不复敢挺身任事”[86]。尽管后来清乡中,不得不起用一些地方士绅,但士绅与革命政权的关系已经相当隔膜。
革命党人政权与新知识阶层之间亦是暗潮涌动。广东军政府依同盟会规定的“三权独立之制”而建立,但在权力实际运作上,行政与立法存在冲突,“政府应交议之事,有时不交议;有时省会通过之事,行文政府,而政府漫应之”,“而省会于政府交议之事,十宗驳还八九;有时函请政府执行之事,且令政府为难”。[87]胡汉民、陈景华等与省议会关系恶劣。临时省会以滥杀为由弹劾警察厅长陈景华,[88]陈景华则指责省会不作为[89];胡汉民否认临时省会的代表性,招致临时省会的弹劾,被指责为“实行专制”[90]。正式省会成立后,虽行政与立法机构矛盾有所缓和,但也有弹劾都督陈炯明事情出现。行政长官与临时省会的矛盾,并非完全个人意义上的恩怨,反映了新型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
掌权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发展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一旦报纸言论不利于自己,则采取高压封禁手段对待。1912年4月陈炯明以“希图摇惑众军,扰乱大局”罪名枪杀了《佗城报》编辑发行人陈听香,[91]并封禁《总商会报》、《公言报》等。1913年3月12日《新醒报》以讥讽语气报道警察厅与港英当局的一宗交涉,被陈指为“颠倒是非,藉端侮弄,实为扰乱行政”,而勒令停版,禁止发行。[92]报界强烈反弹,以“共和政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予以反击。[93]广东独立前社会舆论偏向革命,革命政权建立后,报纸的批评却越来越多。由同盟会员创办的《民生日报》基本上支持军政府,但在1913年以后,对军政府的批评也日见增多,在胡汉民被免职后,还出现了攻击胡的新闻。[94]
地方政权更缺乏社会基础。从考试章程看,军政府要求应考县长的知识背景是“东西洋法政学堂毕业”或“中国法政学堂正科及别科毕业”,旧官员无反对共和政体言行者也可以应考。[95]昔日熟悉地方社会的官员多被排挤,许多县长由平民出身的革命党人担任,“反正之初,县知事之来自田间者,殆十七八,流品既杂”[96]。新知县很难胜任工作,并不能很好地执行军政府的政令,各地民众控告县知事的新闻屡屡见报。[97]舆论甚至认为,民国的县知事还“不如旧政府之官吏”[98]。军政府只得不断更换县长,每县一年平均更换三次,可县政也全无起色。[99]革命党人未能在基层扎实根基。
晚清以后,地方精英上升的渠道已多元化,或商、或学、或军。但是,革命以后地方精英的发展途径并不见得有明显的增加。据赵连城回忆,不少同盟会员在革命后因无前途而相当消极,如对广东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的潘达微,郁郁不得志,常讲庄子与佛学;澳门同盟会主盟人林君复回到内地因不得志而削发为僧,脱离政治;一些女同盟会员,革命“成功”后反感到前路茫茫,甚至悲观失望而自动回家;女子北伐队的成员除了一些与要员结婚,解决个人“出路”问题外,绝大多数在工作、生活上都没有受到军政府的照顾。[100]一些地方精英甚至进入非正当职业群体,民初盗匪中也有受过教育的。经济文化事业并无发展,未能为知识阶层谋出路,尤其是中下层新式知识分子革命后出路并无拓宽。
时人曾敏锐指出,钟荣光“裁冗员,反对蓄妾,销毁伪职匾额旗杆,则取怨于前清士大夫;取缔小说时宪等书,则取怨于无知社会”,此钟荣光被攻击的种种原因。[101]1913年7月,陈炯明在对自己执政的总结中,亦清楚地意识到:“盗风未熄,吏治未修,商业未兴,民生未奠,余如教育实业,一切应兴应革之政,亦未遑整饬进行。夫我粤为财赋出产之区,亦人才荟萃之地,本无患财源之困乏,政事之不修,而现象如此者,岂非上下之情睽而未能相见以诚耶;夫情形隔阂则信用难孚,故举一事也,政府以为是者,而人民或以为非,提一议也,人民以为易,而政府或以为难”。[102]广东有组织的旧势力反抗并不严重,但激进的革命执政者既不能争取传统地方精英的支持,又不能团结新兴知识阶层与革命精英,本来就缺乏社会阶级基础的同盟会,无法动员可能支持改革的社会阶层,失败在所难免。
四、结论
近代社会的变革无疑是新旧之间的较量。尽管执政的部分革命党人并没有系统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经历,其思想意识中也存在一些传统观念,但是他们推行的社会改造政令,基本上印上了“新”的标识。在这个意义上讲,民初革命党人在广东的社会改造,其实也是新旧知识体系的一场大较量。然而,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传统知识精英对新知识并不陌生,很多还是新知识的热心传播者。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知识精英与革命党人的知识结构并无根本对立,清末广东士绅对新式教育的热心,谘议局议员对禁赌的执著,与民初社会改造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民初社会改造中的新旧之争,原本不应激化革命党人与传统知识精英的矛盾。换而言之,地方精英对民初社会改造的抵制,并非完全出于知识新旧之争,事实上,未能进入权力核心体系的新知识阶层,也不支持革命党人的社会改造。清末广东知识精英的“趋新”,本来为社会变革铺垫了基础,革命党人在政治上防范“旧”精英,使变革丧失原有社会基础,而排挤新知识阶层,又使变革无法拥有新的社会基础,民初的社会改造,实为革命党人孤军奋战的“少数人的事业”。
社会改造既是少数革命党人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也是反对势力的攻击点。1912年4月,孙中山充满信心地公开说:“鄙人抱三民主义,此次辞识[职]归来,实有无穷希望于吾粤。思以我粤为一模范省,诚以我粤之地位与财力,与夫商情之洽固,民智之开通,使移其嚣张躁妄之陋习,好勇斗狠之浇风,萃其心思才力于一途,以振兴实业,谋图富强,不出数年,知必有效。”[103]一年后,有立宪派背景的《时报》则刊登长文,攻击广东革命政府的政治为“民死主义之政治也”,革命政府的多项社会改造举措便是靶子。(14)就在广州商人因拆卸街闸之事与军政府警察厅“对峙”之期,广州商务总会、粤商维持公会等联名致电北京,承认大借款及举袁世凯为总统,申讨广东军政府,表明了与革命党人对立的政治态度。[104]知识的冲突只不过是政治反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就革命党人的力量及革命的社会基础而言,广东无疑是革命条件最优越的省份,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之失误。
注释:
①本文2008年11月曾提交“孙文·地域社会·知识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神户)讨论,承蒙绪形康教授、安井三吉教授、潘光哲博士、宫内肇博士等赐教,特此致谢。
②主要著作有周兴樑《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邱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Edward J.M.Rh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晓吟《民初广东军政府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叶少宝《民初广东军政府与龙济光政府维持纸币之比较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等。
③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156页。
④例如,粤商自治会主事者之一黄景棠,新、旧学问都有一定水准。参见邱捷《黄景棠与〈倚剑楼诗草〉》,《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⑤参见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⑥参见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26-34页。
⑦有关清末广州商界的政治动向,可参见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⑧参见贺跃夫《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⑨前人已做过专题研究,本文不再做讨论。参见邱捷《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和军政府的清乡》,《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⑩钟荣光自述:“一意施行民主国教育,学风之活泼,吾取美国,……学制之划一,吾终取法国”。见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广州铅印本,15页。
(11)有关军政府教育改造的主要内容,详参钟荣光《广东人之广东》,15-36页;周兴樑《民初广东教育改革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2)参见周兴樑《民初广东教育改革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3)转引自周兴樑《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214页。
(14)《民生主义与民死主义(续)》,1913年5月16日《时报》。《时报》虽在上海出版,但所载此文与广东的反对势力似有关联,文章开头即称:“倾粤人来,为余述粤事颇详,而皆不出乎民死主义之范围”。见《民生主义与民死主义》,《时报》1913年5月15日。
标签:胡汉民论文; 立宪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历史论文; 晚清论文; 军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