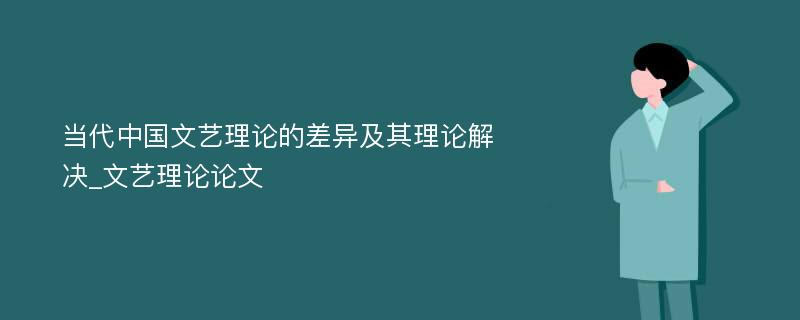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分歧论文,中国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4-0097-09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过去出现的一些理论分歧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把握文艺的理想与现实的发展、文艺的批判与现实的批判等关系上仍然没有超越前人的认识,甚至在一些方面有所退步。其中,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在从“审美反映论”到“审美超越论”的发展过程中就没有克服前人所犯的错误。这种“审美反映论”虽然主要是针对“文学主体论”完全否定“文艺反映论”而提出的,但却没有避免“文学主体论”否定“文艺反映论”所犯的根本错误。不过,与中国当代一些文艺理论家不同,王元骧既真诚地信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积极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可以说,王元骧提出的“审美超越论”走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反面是不自觉的。而王元骧文艺理论发展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是普遍的,但是,这种文艺理论现象却没有引起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重视。以往我们曾先后在《审美超越要建立在现实基础上》(《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嬗变》(《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等论文中对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提出了批评。但是,这些文艺理论批评一是没有全面解剖王元骧文艺理论的缺失,二是王元骧在反批评时没有正面回应这些批评,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也鲜有参与。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更系统、更深入地解剖王元骧文艺理论的发展,既全面剖析王元骧的文艺理论在哪些方面存在失误,也深入探究我们与王元骧在文艺理论上的分歧在哪里,并将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理论进行比较,总结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得失,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科学地总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经验教训,而且有利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更好地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艺界提倡一种“泛‘美’主义”或“泛审美主义”,严重地混淆了眩惑与真美。这种“泛‘美’主义”或“泛审美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肤浅的“感觉主义”或“感性主义”,即把凡是能够提供给感觉的感性呈现都称呼为美的呈现或美的创造,同时也就把随便的什么感性享受都一概称呼为审美。这种眩惑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媚美。19世纪早期,叔本华区分了媚美的类型并作了严格的界定。叔本华认为在艺术的领域里的媚美既没有美学价值,也不配称为艺术。叔本华将这种媚美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媚美。在历史的绘画和雕刻中,媚美则在裸体人像中。这些裸体像的姿态,半掩半露甚至整个裸露的处理手法都是意在激起鉴赏人的肉感,因而纯粹审美的观赏就立即消失了,而作者创造这些东西也违反了艺术的目的。还有一种消极的媚美。这种媚美比积极的媚美更糟,那就是令人作呕的东西。这和真正的媚美一样,也唤起鉴赏者的意志因而摧毁了纯粹的审美观赏。不过这里激起的是一种剧烈的不想要,一种反感;其所以激动意志是由于将意志深恶的对象展示于鉴赏者之前。因此,人们自来就已认识到在艺术里是绝不能容许这种东西的;倒是丑陋的东西,只要不是令人作呕的,在适当的地方还是可以容许的。①中国当代有些文艺作品严重缺乏感动人的真美,但却不乏叔本华所说的刺激和挑逗人的媚美。这种病态的文艺创作现象曾在西方现代艺术中泛滥。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就深入地挖掘了这种病态的文艺创作现象产生的根源,他认为“艺术家对社会的错误态度是他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厌恶;这个社会又同时使他与所处时代的巨大的、孕育着未来的社会潮流相隔绝。但这种个人的与世隔绝,同时也意味着他的肉体上和道德上的变形。这类艺术家在所处时代的进步运动中都做了徒劳的短暂的客串演出,而最终经常是成了死对头”。②而这种恶劣的艺术创作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坛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中国当代文艺创作由“外”向“内”转移的结果。在这种由“外”向“内”转移的过程中,有些作家不屑于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客观世界存在的真美,就只好以眩惑这种东西诱惑人心,这种个人化写作把个体审美意识与群体意识完全对立起来了。有人还在美学上对这种文艺创作的转向进行了所谓的理论提升,认为这是反叛艺术创作中的政治群体意识回到个人的审美意识。简言之,就是回到审美意识自身,并逐步走向现代审美意识的生成。这种美学理论把中国当代文艺进一步地引进了死胡同。为了抵制中国当代文艺创作这种病态现象,王元骧深刻地区分了“美的艺术”与“大众文化”,并鲜明地提出在“美的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两者之间,应该以“美的艺术”来提升“大众文化”,而不应该以“大众文化”来消解“美的艺术”。王元骧坚决反对审美的降格,而把“审美超越”视为“艺术的精神”,认为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使人在经验生活中看到了一个经验生活之上的世界,使人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幸福中免于沉沦,而使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种必要的张力,把人不断引向自我超越。③他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异化现象,即有些文艺作品沦为商品,变为休闲、娱乐、宣泄,仅仅满足于感官享受的工具,认为这不过是随着人的异化而来的文艺的一种异化现象。在这个基础上,王元骧深入地把握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规律,有力地批判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虚无化倾向,抵制了那些没有理论深度的文艺批评,唾弃了中国当代媚俗、低俗、恶俗的文艺作品。王元骧的这种文艺理论追求是十分深刻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元骧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没有达到更高的历史阶段,而是不自觉地背离了唯物史观,陷入了唯心史观。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深入地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很有必要的了。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真正避免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王元骧的文艺理论经过了两次较大转变。一是从认识论文艺观到价值论文艺观的转变。王元骧高度肯定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联系的。审美反映是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而审美意识形态则就审美反映的成果而言,它以“审美反映论”为基础和前提。王元骧认为“审美反映论”自然是一种认识论文艺观,但它与中国以往流行的认识论文艺观是不同的。这种“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反映的不只是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实是的人生”,而且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愿望,作家对于“应是的人生”的企盼、期望、追求和梦想。所以就其性质来说,不是一种“事实意识”,而是一种“价值意识”,它不只是认识性的,而且也是实践性的。④这样,我们就把以往对文学的理解单纯从认识论的视角而走向认识论与价值论、实践论统一的视角。二是从价值论文艺观到本体论文艺观的转变。王元骧认为价值论文艺观肯定了个人的需要、理想、愿望及个人存在的价值,与传统认识论文艺观相比,它大大深化和推进了人们对文艺本性的认识。但是,“当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凭什么来判断何种价值取向是正当的、健全的?何种价值取向是非正当、不健全的?这里就需要我们找到一个进行价值判断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把文学认识论研究经由文学价值论研究再进一步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研究”。⑤所以,王元骧在区分优秀的、伟大的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基础上提出,凡是优秀的、伟大的作家一方面都是直面人生的,哪怕是严酷、惨淡、血淋淋的生活也不予以回避;而另一方面又与一般作家不同,他在对现状的痛切的感受和描写中无不伴随着强烈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渴望。因此,他的作品在描写卑琐、空虚、平庸时又成了对卑琐、空虚、平庸的超越;描写罪恶、苦难、不平时又成了对罪恶、苦难、不平的超越;描写压迫、剥削、奴役时又成了对压迫、剥削、奴役的超越。这样,“我们就不仅可以把认识论文艺观与本体论文艺观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且也使得以往的价值论文艺观由于缺乏本体论的依据所可能导致的价值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使我们的文艺学成为真正有根的文艺学”。⑥我们曾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嬗变》(《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等论文中对王元骧文艺理论的这两大转变进行了把握。
可是,在这种文艺理论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王元骧却不自觉地背离了唯物史观,陷入了唯心史观。
首先,王元骧在历史观上背离了唯物史观,陷入了唯心史观。王元骧的这种“文艺本体论”是以人性论和目的论为基础的。王元骧认为:“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应是的人生’并非只是由于作家的创作活动,作家的审美情感激发下的艺术想象所赋予的;它同时也是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的显现,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尽管这些‘美的幻想’可能离现实很远,但却离心灵很近。一个文学作品,只有当它真实地显现了人的这种生存的本真状态,并启示人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去作深情的探询、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去作深刻的反思,引导人们朝着‘应是的人生’而不断走向完善,它才有可能是美的。”⑦而作为本体的人就是作为目的来追求的人。这就是“人的活动的特性就在于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就使得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它不只是消极地受自然律所支配,而同时还是积极地按自由律行事,它本身就是一个实现人的意志和目的的过程。这决定了社会史与自然史不同,对于自然史来说,起作用的‘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而在社会史领域活动的,则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⑧这种“目的论从自然观上自然是唯心的,但从社会历史观来看却是唯物的,因为历史就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人的活动”。⑨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方面,恩格斯虽然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这种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虽然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但是,这种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不是最终原因。恩格斯特别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精神的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精神的动力的动力是什么。这种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⑩
显然,王元骧没有超越恩格斯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了精神的动力,但却没有从这些精神的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其次,王元骧在美学观上背离了唯物史观,陷入了唯心史观。王元骧认为生产劳动创造美和美感。生产劳动何以会产生美和美感呢?王元骧认为“由于它改变了自然与人的对立和疏远的关系,使世界从‘自在的’变为‘为我的’,而成为‘人的世界’,与人形成一种审美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使自然成为美的对象”。(11)而“美从本质上说不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是事物的价值属性,价值属性作为由于事物满足人的需要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属性,它不是脱离人而存在,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的”。(12)这是把美的存在和美感的产生混为一谈了。的确,对于审美来说,人对美的认识和感受以及审美关系的实现都离不开实践的能动作用,审美的对象能不能产生美感,产生什么样的美感,都要受到人的实践的深刻制约,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世界的美一概都是实践创造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并不是直接改变了对象的审美性质,而是使人能够发现和欣赏这些本来就存在的美。对象的美要引起主体的美感,需要必要的主客观的条件,这和一个事物要被人们认识也需要相关条件一样。马克思谈到音乐审美,明确地把“最美的音乐”和“音乐感”区别开来,认为音乐美感的产生要有音乐和“懂音律的耳朵”这两个前提条件。他在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无动于衷”时还强调了审美态度这个必要条件。因此,不能把美的存在和美感的产生混为一谈。(13)而把美的存在和美感的产生混为一谈,认为一切美的存在都离不开人的实践,就背离了唯物史观,陷入了唯心史观。
再次,王元骧在文艺观上强调了作家对美的创造,而忽视了作家在艺术世界里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王元骧认为:“文艺以人为对象和目的,它不仅是描写人,而且也是为了人,使人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安乐中免于沉沦。而能否达到这一目的,作家是关键。”十分丑恶的现象经过作家“灵魂的炼狱”而获得“崇高的表现”,有一些英雄人物一经作者戏说就变得庸俗不堪了。(14)王元骧多次规定美的文学,有时认为美的文学是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的显现,但这种“真正美的、优秀的、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只是一种存在的自发的显现,它总是这样那样地体现作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梦想,而使得人生因有梦而变得美丽。尽管这种美好生活离现实人生还十分遥远,但它可以使我们在经验生活中看到一个经验生活之上的世界,在实是的人生中看到一个应是人生的愿景,从而使得我们不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对生活始终怀有一种美好的心愿,而促使自己奋发进取;在不论怎样幸福安逸的生活中始终不忘人生的忧患,而不至于走向沉沦”。(15)有时甚至认为美的文学是作家的理想、愿望的实现,“只要真正是美的文学,几乎都是由于作家的理想、愿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以实现,从而通过想象和幻想,把它幻化为一个美的意象,以求在心灵上得到满足和补偿的”。(16)其实,王元骧的文艺观经过了多次演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以“审美反映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王元骧转向了“文艺实践论”;到了21世纪,王元骧则转向“文艺本体论”。王元骧认为“文艺本体论”、“文艺实践论”是沿着同一轨道推进的,都是从“审美反映论”中生发出来的,是“审美反映论”已经蕴含了的,或者说是对“审美反映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在把握审美反映的特点时,王元骧首先认为能引起作家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的只能是人和人的世界,即使写到完全没有人出场的自然景物,实际上也是人的世界,即为作家的审美感知和体验所把握到的自然世界,所以作家不在对象之外,而就在对象之中。因而,作家不论描写什么,是人物还是风景,都无不打上他自己的烙印,把自己的心灵生活展现其中。这样,自然美的客观存在就被王元骧否定了。其次认为艺术展示的不是一种“事实意识”,而是一种“价值意识”;不是“是什么”,而是“应为此”。艺术就是由于这一点才能打动人。审美意识作为“价值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与一切“价值意识”、一切意识形态一样,实际上都是一种“实践意识”。(17)这样,社会美的客观存在也被王元骧否定了。
18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19世纪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虽然强调作家、艺术家的能动创造作用,但是他们都没有否定客观存在的美。席勒深刻地区分了艺术的庸俗的表现和高尚的表现。席勒指出:“表现单纯的热情(不论是肉欲的还是痛苦的)而不表现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叫做庸俗的表现,相反的表现叫做高尚的表现。”这就是说,席勒认为庸俗的表现就是没有表现对象超感觉的反抗力量,而高尚的表现则表现了对象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席勒在严格界定庸俗鄙陋的事物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卓越的处理办法。席勒虽然认为:“虽然有成千的事物由于自己的质料或内容而是庸俗的,但是,通过加工,质料的庸俗可以变得高尚,所以在艺术中讲的只是形式的庸俗。庸俗的头脑会以庸俗的加工作贱最高尚的质料,相反,卓越的头脑和高尚的精神甚至善于使庸俗变得高尚,而且是通过把庸俗与某种精神的东西联系起来和在庸俗中发现卓越的方面来实现的。”(18)但是,席勒却没有认为庸俗鄙陋的事物与真正伟大的事物取决于庸俗的头脑与卓越的头脑。一个诗人,如果他描述微不足道的行为,却粗枝大叶地忽略意义重大的行为,就是庸俗地处理他的题材。如果他使题材与伟大的行为结合起来描述,他就是卓越地处理题材。在这个基础上,席勒提出必须把思想的鄙陋与行为和状态的鄙陋恰如其分地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一切审美活动所不屑一顾的,后者常常与审美活动相处得很好”。例如,奴隶身份是鄙陋的,不过在存在着自由的情况下,奴隶般卑躬屈节的思想是可鄙的,相反的是没有那种卑躬屈节思想的奴隶职业并不是可鄙的。更确切地说,状态的鄙陋与思想的高尚相结合可能转化为崇高。真正的伟大只会从鄙陋的厄运中闪耀出更加壮丽的光芒。这就是说,席勒所说的艺术卓越的处理办法就是在对象中开掘出真正的伟大。别林斯基高度肯定果戈理,认为他在文艺创作中“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他愿意把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美的、人性的东西展露出来,但同时也不隐蔽它的丑恶。在前后两种情况下,他都极度忠实于生活”。(19)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甚至提出:“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20)因而,别林斯基认为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之所以使灿烂的肩章和多彩的制服黯然失色,是因为文学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别林斯基指出:“在这社会中,新生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出来,但被深重的压迫紧压着,找不出出路,结果只引起了阴郁、苦闷、冷淡。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21)与席勒、别林斯基相比,王元骧的审美反映论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
可以说,王元骧从“审美反映论”开始就背离了唯物史观,陷入了唯心史观。
最后,王元骧在思维方式上没有真正地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虽然猛烈地批判了过去相当泛滥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但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用“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代替“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用唯物辩证法代替它。有些人将辩证法和“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混同,认为唯物辩证法就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是绝对排斥“非此即彼”的。王元骧提出:“如果把辩证法,把对立统一理解为非此即彼,一方吃掉一方,当然有些不妥;但若理解为亦此亦彼,理解通过辩证思维,可以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使自己的认识更加全面、完整、减少片面性,并且使之不断地有所超越,有所前进,这不是很好吗?”(22)这是严重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恩格斯明确地界定了唯物辩证法:“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23)显然,“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我们曾经指出,这种“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在逻辑上表现为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立起来,甚至排斥形式逻辑。它只讲矛盾的双方共存和互补,否认矛盾的双方相互过渡和转化;看到了事物相互间的联系,忘了它们的相对静止;它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不但要从“非此即彼”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也要摆脱“亦此亦彼”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真正坚持唯物辩证法。由于在思维方式上陷入了误区,所以王元骧的文艺理论创新走过了头。
如果比较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就不难发现这两种文艺理论形态虽然在时间上前后出现并批判了不同的文艺现象,但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都是构想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艺术的理想世界。
我们曾经指出,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论”不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中,而是建立在理想世界里,并且这个理想世界是彻底否定和排斥现实世界的。也就是说,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所说的艺术活动是发生在理想社会里,而不是植根在现实世界中。刘再复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由于受制于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束缚,因此,往往自我得不到实现,自己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质,自身变成非自身。”(24)而在艺术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不再处于片面的对立之中,客体成为真正的人的对象,并使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艺术活动中,人自身复归为全面的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人总要受到社会和自然的限制,总是要感受到受限制的痛苦,因此,人总是要想办法来调节自己的认识和感情,超越这种限制。于是,他们就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超越手段,并通过它实现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实现的一切”。(25)刘再复的这种“文学主体论”将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了。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26)在这种残酷的异化劳动中,虽然工人自身异化了,但是人类却发展了。这种异化劳动虽然生产了赤贫、棚舍、畸形、愚钝和痴呆,但也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宫殿、美和智慧。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只是看到人的异化,而看不到人的发展,否则,就是片面的。显然,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论”只看到了人在艺术世界里的发展,而没有看到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发展以及这二者的联系,是相当片面的。
21世纪初,王元骧提出的“审美超越论”也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完成的,而是在理想世界中实现的。这种“审美超越论”认为文艺是人类为了摆脱和改变现状、实现生存超越愿望的一种生动而集中的表现。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呼唤和展示人所应该有和可能有的一种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应合和满足了人们追求这种应该有和可能有的生活的美好愿望。“伟大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人生理想往往由于离现实人生比较遥远,而被人称为‘乌托邦’,但我们绝不小看它对于人的精神所产生的感召的力量。”这种“美的艺术也正如这火光那样,它使人生活有了方向和目标,在逆境中因看到希望而不被苦难所压倒;在安乐中居安思危而免于走向沉沦。这种忧患意识对于激发人的生存自觉、警醒痴迷,特别是改变今天那些沉迷于物欲而不能自拔的人的思想方式和生存方式来说尤其需要”。(27)在这个基础上,王元骧对艺术进行了规定。首先,艺术表现了应是人生的愿景。王元骧强调文艺所反映的不仅是实是人生,而更是应是人生。王元骧认为“艺术源于人生存的需求,它在反映实是人生中让人看到一个应是人生的愿景,使人在苦难困顿中看到希望,在幸福安乐中免于沉沦。这样就与现实人生形成一种张力,引导人不断地走向自我超越”。(28)其次,艺术是想象和幻想的产物。王元骧认为艺术本身就是想象和幻想的产物,是由于人们的理想、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和满足,而把它们化为美的幻象来予以表现,以求给予人的精神以补偿、鼓舞和激励。(29)可见,王元骧的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在精神上可以独立实现审美超越;二是作家、艺术家不是消极地认同现状、屈从现状甚至谄媚现状,而是积极地改变现状,使现状变得更合理、更符合人们的理想和愿望。
王元骧看到了人在精神上可以实现审美超越,这是对的。但是,王元骧没有看到这种审美超越与现实超越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完全脱节的。尤其是王元骧没有看到文艺的审美超越所反映出的人的现实超越。而文艺的审美超越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而是反映了人的现实超越的,否则,文艺就完全成为作家、艺术家主观创造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我们曾经指出,在艺术世界里,作家、艺术家虽然可以批判甚至否定现实世界中的丑恶现象,但是克服这种现实世界中的丑恶现象却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能真正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文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可以超越邪恶势力,但绝不能超越正义力量,否则,文艺作品所构造的理想世界就完全成为与现实生活对立的另一个世界。人的自由解放的实现虽然存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两个层面,但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如果脱离物质层面而单纯地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人的自由解放,就是将文艺世界和现实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了,将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对立起来了,而不是将审美超越建立在现实超越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文艺不但应该促使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惊醒起来,感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而且应该反映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争取美好生活的努力和斗争,而不是引导人民群众陶醉和沉醉在审美幻想世界中。文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是在肯定正义力量的同时否定邪恶势力,不是构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如果认为作家、艺术家可以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理想世界,那么,作家、艺术家就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进行虚构和想象,甚至就可以向壁虚构了。这无疑是引导作家、艺术家回避挖掘、发现和塑造现实生活中的未来的真正的人。而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必然是一成不变的,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在现实生活中,未来的真正的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历史上,未来的真正的人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家、艺术家只有深入生活,不断地开掘和发现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未来的真正的人,才能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人物形象。
不过,王元骧提出的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那种把个体审美意识与群体意识对立起来的“现代审美意识生成论”的反拨。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坚决反对那种把个体审美意识与群体意识对立起来的“现代审美意识生成论”,强调了审美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认为对人来说,美所具有的最高的价值,就是通过对人的情感的陶冶,达到对私欲的超越,而使人不为物所役,亦即不做物质的奴隶,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尊严,维护自身生存的意义、价值的功效。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强调情感对欲望的超越,认为欲望与情感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都属于广义的情的领域,都由于在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才使人感到愉快。但欲望的满足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情绪反应,它的满足方式是占有、据为己有,它只是对个人才有意义,因而在欲望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不仅难以沟通,而且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而情感与对象的关系则是无私的,当人们对某一对象产生情感后,不仅不会以占有的方式来为自己享用,而且还会移情于对象,与对象处于融和合一的状态。这样也就消除了在欲望关系中人我与物我之间的对立而进入和谐的境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一个情感对欲望的不断超越的过程。因为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不可能没有物质的需求的,否则他就难以存活;但自从进入人类社会以来,人就不再是自然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个人,亦即处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为了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就必须要求人们不能只听命于一己的私欲,更要以社会的、普遍有效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不为物所役,不做欲望的奴隶也就成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文明的人与野蛮的人,作为“人的人”与作为动物的人的一个根本区别。而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建立,正是人类走向情感对欲望的超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飞跃。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强调作为“人的人”可以在精神上超越物质的匮乏,认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他不只是消极地听从必然律的支配,而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使生活变得美好。所以正是由于贫穷、困苦等生活压力,他们就更需要在精神上得到补偿、抚慰和激励。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高度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仅仅满足于甚至陶醉于那种精神补偿、抚慰和激励则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文艺的“审美超越论”没有看到人的审美超越不但是在人的现实超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反映这种现实超越,而且最终也转化为现实超越。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些严重的异化现象恐怕不是审美可以彻底根除的。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岂不是多余?!因此,重视审美作用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夸大审美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似乎审美可以代替人民对现实的实际改造,否则岂不是将人民引入虚幻的世界。
其实,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赫·马尔库塞文艺思想的翻版。与恩格斯要求艺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不同,赫·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只有服从自己的规律,违反现实的规律,才能保持其真实,才能使人意识到变革的必要。艺术是一种虚构的现实,“作为虚构的世界,作为幻象,它比日常现实包含更多的真实”。(30)在赫·马尔库塞看来,艺术所服从的规律,不是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是否定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因此,赫·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既成现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形象的乞灵。在赫·马尔库塞看来,“先进的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变成一个由腐朽的戒备森严的垄断阶级所支配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整体也包括了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阶级相等的需要和利益”。(31)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已为流行的需要体系所支配。而被剥削阶级即人民越是屈服于现有权势,艺术将越是远离人民。可见,赫·马尔库塞只看到了人民被统治阶级同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斗争的一面。也就是说,赫·马尔库塞在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力量时,不但没有看到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力量,而且完全忽视了文艺对这种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反映。而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必须深入地反映这种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否则,就很容易流于空洞和空疏,必然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嬗变》(《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等论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艺界围绕“躲避崇高”与“抵抗投降”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有些作家虽然抵制了“躲避崇高”这种“下滑”倾向,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艺的理想没有与人民的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在不断重复中吸收力量。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在肯定并提倡一种清洁的精神时就陷入了这种误区。张承志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反复地讲这样一个故事,即一个拒绝妥协的美女的存在与死亡,陷入了自我封闭。先是在《清洁的精神》(32)中,接着是在《沙漠中的唯美》(33)中,后是在《美的存在与死亡》(34)中,这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生逢乱世暴君,她以歌舞升平为耻,于是拒绝出演,闭门不出,可是时间长了,众人对她显出淡忘。世间总不能少了丝竹宴乐,在时光的流逝中,不知又起落了多少婉转的艳歌,不知又飘甩过多少舒展的长袖。人们继续被一个接一个的新人迷住,久而久之,没有谁还记得她了。美女这种对乱世暴君的拒绝虽然也是一种抗争,但是比较消极。因此,张承志的这种反复的讲在社会上的反响愈来愈微弱。在一定程度上,张承志的这种反复的讲不过是在自我重复中的自我封闭。与此相反,有些作家则在对中国当代文艺界的“个人化写作”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刘继明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小说自身构成了一个独立、足可以和现实相抗衡的世界。小说与现实就这样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分道扬镳了。与现实分手后的中国小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开拓出一片艺术的新天地,但另外一个方面,却也因此堕入了无边无际的价值虚空之中”。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的解放”,尽管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将某种合理的价值观推向极端,承认人的自利原则时,却又把向善、利他和道德上的自我升华等逐出人性的范畴,从而造成了对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另外一种遮蔽。刘继明还结合自己的创作发展对这种文艺的恶劣倾向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刘继明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而要搞清楚世界是怎么回事,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所以慢慢地,我又开始把目光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同时渐渐地对北村这样的作品以及我自己的那类作品不满足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进行价值空转,自我推演,跟现实是绝缘的”。(3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作家感叹文艺的边缘化。其实,这种文艺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一些作家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文学的方式和社会进行互动的结果。因此,在如何处理同现实的关系上,刘继明认为小说家不应该采取规避或者逃逸的姿态。也就是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单独完成,而是必须在与现实世界的互相缠绕乃至对峙过程中共生共荣,不断前行。中国当代一些作家的这种转向意味着中国当代文艺将在经历曲折后慢慢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
从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重犯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所犯的错误中可以看出,过去没有从理论上彻底解决的文艺理论分歧仍在制约着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我们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想解放的先驱》(《江汉论坛》,2011年第1期)等论文中指出,1986年至1988年,文艺理论家陈涌、作家姚雪垠与刘再复进行了一场文艺论战,这场文艺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陈涌、姚雪垠与刘再复在文艺理论上的分歧。陈涌、姚雪垠与刘再复的这种文艺理论分歧不是中国当代文论系统转换,而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在文艺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把握上不同。在对文艺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把握上,姚雪垠强调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反对离开现实单纯强调理想,认为脱离现实生活基础的“革命理想”是架空的。(36)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提出了“深入”与“跳出”的文学理论,认为“写历史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先研究历史,做到处处心中有数,然后去组织小说细节,烘托人物,表现主题思想。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也就是既要深入历史,也要跳出历史。深入与跳出是辩证的,而基础是在深入”。(37)这种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提倡作家、艺术家深刻地解剖现实。不过,这种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虽然强调了文艺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但却忽视了作家、艺术家对理想的主观追求和创造。而刘再复则过于强调作家、艺术家对理想的主观追求和创造,认为文艺的理想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是作家、艺术家主观创造出来的。显然,这忽视了文艺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只有从理论上彻底地解决陈涌、姚雪垠和刘再复在文艺理论上的分歧,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本来,这种文艺理论的分歧应该在理论上解决,但是,刘再复等人不是在文艺理论上解决理论的是非,而是以政治判断代替文艺理论的是非判断,甚至进行政治讨伐,这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家在遇到文艺理论批评时不是本着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追求真理、认真辨别这些文艺理论批评的对与错的原则和态度,而是追逐特殊利益,放弃是非判断。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不少机会就在这种没有充分展开的文艺理论争鸣中丧失。俄国19世纪中期大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尔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荫庇和鞭笞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做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38)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不能丧失别林斯基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要在健康而深入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的过程中促成对立的双方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彼此的局限,形成新的共识,达到新的团结。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注释:
①[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0—291页。
②[匈牙利]乔治·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48页。
③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第269页,第323页。
④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⑤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⑥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⑦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⑧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页。
⑨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249页。
(11)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8页。
(12)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13)曾永成、艾莲:《论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哲学失误和美学成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6期。
(14)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2页。
(15)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16)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17)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7-298页。
(18)[德]席勒著,张玉能译:《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19)[俄]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87页。
(20)[俄]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54页。
(21)易漱泉等编选:《外国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22)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
(24)红旗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编:《文学主体性论争集》,红旗出版社,1986年,第35页。
(25)红旗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编:《文学主体性论争集》,红旗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26)中国作家协会等编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27)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7页。
(28)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0页。
(29)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
(30)[美]赫·马尔库塞等著,绿原译:《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31)[美]赫·马尔库塞等著,绿原译:《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22-23页。
(32)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十月》,1993年第6期。
(33)张承志:《沙漠中的唯美》,《花城》,1997年第4期。
(34)张承志:《美的存在与死亡》,《新京报》,2004年10月10日。
(35)刘继明:《小说与现实》,《上海文学》,2009年第6期。
(36)姚雪垠:《姚雪垠书系》第18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37)茅盾、姚雪垠:《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38)易漱泉等编选:《外国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
标签:文艺理论论文; 文艺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王元论文; 刘再复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