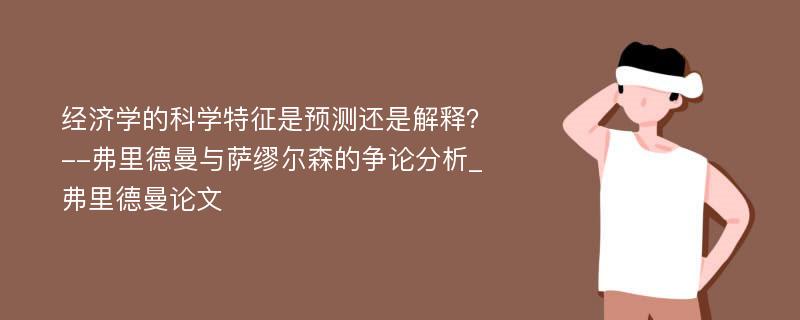
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弗里德论文,特征论文,科学论文,萨缪尔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9)03-0003-09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内部就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产生争论。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界内部更是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战。引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53年发表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这篇论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检验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科学的惟一标志是对其经济的预测与实际数据加以比较,经济学能否成为实证科学的重要特征在于这一理论能否预测未来。弗里德曼的论文发表后,在经济学界内部引发了一场有关经济学是预测经济未来还是解释经济现实的争论。纵观争论的全过程,支持者、反对者均有之,反对者中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论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事隔半个多世纪,重新回顾并反思这一争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仍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而不是‘什么应该是’一类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以正确的预测。这一体系的运行状况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①。
经济学的科学特征在于预测经济的未来,弗里德曼强调说这是经济学属于实证科学的必然属性:“任何政策结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基于对采取某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行动将产生的影响所作的预测,而预测则必须明确或不明确地基于实证经济学。当然,在政策结论与实证经济结论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两个不同的个体可能在对某一个别的立法的结果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其中的一个可能认为这些结果有利于平衡,进而拥护这项立法;而另外一个却可能认为这些结果是不合意的,进而反对这项立法。”这样的分歧是可以通过检验实证经济学的预测结果而加以消除的。弗里德曼例举最低工资的立法问题来论证他的这一主张:“一个明显的而且并非不重要的事例就是最低工资限制问题。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对这一立法的褒贬纷争,但人们在为所有的人争取到一个‘生存工资’这一政策目标上却形成了根本一致的意见。”②人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最低工资立法能否消除贫困有不同的预测。支持者认为法定最低工资会通过提高在最低工资线以下人的收入而消除贫困,反对者则提出法定最低工资会造成就业条件恶化而加重贫困。谁是谁非,只能通过检验其理论预测的结果而得以解决:“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人们一定会经过漫长的道路而趋于一致的。”③
对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在于预测未来,弗里德曼还论证说,实证科学理论由语言与实证假说体系两部分构成。作为语言部分它是判断实证科学是否合理的逻辑与事实标准。逻辑标准可说明语言中的命题是正确还是错误,事实标准能够说明“逻辑编排系统”的种类在实际中是否能找到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作为实证科学中的第二部分——实证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而暂时地得到‘接受’呢,还是遭到了‘拒绝’”。④实证假说体系与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第一部分内容只是作为实证假说的填充系统发挥作用,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则是“对某一假说的合理性的惟一有关的检验,是将其预测与实际情况所作的比较。如果该假说的预测(‘频繁地’或比来自于另一假说的预测更为经常地)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则遭到了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实践相抵触,那么它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度”。⑤
弗里德曼的上述论述,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并与波普尔的观点十分相近。弗里德曼自己也坦承他“对于科学哲学和合理有效的方法论的研究领域都很有兴趣,……我还发现我自己的观点和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很相似”。⑥波普尔认为,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方法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其命题能够被证实。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关键在于科学从逻辑上可以被证伪、反驳或推翻。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不能证伪,就属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一句话,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在于其能否被证伪的程度。⑦波普尔指出:“一个系统只有作出可能与观察相冲突的论断,才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实际上通过设法造成这样的冲突,也即通过设法驳倒它,一个系统才能受到检验。因而可检验性即等于可反驳性,所以也同样可以作为分界标准。”波普尔也强调在检验理论时,预测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科学假说的评价完全在于它所包含的预测,预言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验证科学理论:“如果我们有一种可独立检验而又为真的理论,它就会为我们提供成功的预测(并且仅仅提供成功的预测)。”⑧只有预测才能检验理论。波普尔反复强调,所有理论的真理性都不是常住的,真理性只寓于尚未被验证的谬误的理论之中,一个理论的被确认是暂时的,而被证伪则是必然的,一切理论迟早逃不出预言——证伪法则的范围。波普尔是从这一理论真理的暂时性出发,提出科学总是处于革命的状态,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提出假说和否定假说的过程。
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深深烙有证伪主义的印记。弗里德曼论述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是一种暂时被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⑨“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仅要求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并加以完善,还要求不断地创立新的假说。”⑩对于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约翰·伯顿有如下评论:“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对建立一种‘富有成果’的理论而言,其恰当的标准不在于理论假设是否是‘现实主义’的,而在于理论预见得到经验证实的程度。”(11)弗里德曼在创建货币主义的过程中秉持了这一原则,遵守了这一研究程序,对于自己的理论模式和基本假说提出了可检验、可实证的严格要求。如他提出了货币数量最重要这一基本原理和前提,由此出发提出了关于货币真实需求的货币数量假说、消费需求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之后,弗里德曼与其合作者对其假说又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资料、历史资料的回归分析,对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假说等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行了艰苦的验证和分析。弗里德曼从实证主义的原则出发,认为他的货币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相适应的条件之下,这些假设是永恒有效的,但当金融体制等其他变量发生变化之后,他的这些假设的有效性也会成为问题。他的货币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有边界条件的,不是永恒有效的。(12)
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预测功能,反复强调经济学的预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经济学的实证科学的知识也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任何理论假设都不可避免地——如果想要取得科学成果——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真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的目的不是复制充满五光十色的复杂事物的‘真实世界’,而是从一般事物中抽象出简单的模型,使我们能够预测它的行为。”(13)这种对预测力作用的强调必然导致一种结果,即一个暂定性的假说对于自称要给予说明的现象预测失灵后自然就会有人对这一假说进行修补直到有人提出新的假说,以至于无穷。弗里德曼以凯恩斯和自己的货币主义经济学为例加以论证说明:“正确的理论模式,是这个理论能作出可能被驳倒的预测,凯恩斯理论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它被驳倒了。我描述的理论也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即我们要经历加速的通货膨胀。”(14)弗里德曼认为自己的这一理论假说目前还没有被证伪,那就应被看作是正确的。
既然理论或假说的终极目的是对尚未观察的现象进行准确的预测,那判定理论或假说的有效性标准理所当然也必须以其预测能力来衡量。这一“尚未观察”的现象,弗里德曼认为包括尚未发生的现象、已经发生但观察尚未进行的现象、已经发生而且观察已经作出但利用理论或假说进行预测的人尚不知晓的现象这三种情况。弗里德曼强调“实际证据永远也不可能检验某一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当我们说到某一假说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时(并不十分准确),我们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15)。弗里德曼承认,社会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经受精确的实验检验,而“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我们的检验”。但在弗里德曼看来不能进行受控实验并不是社会科学的独有特色,自然科学中的某些部门例如天文学也同样不能进行受控实验。有控实验与无控实验之间的差异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没有哪一种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所以,不能进行受控实验并不是通过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成功来检验经济学命题的障碍:“实践所提供的证据是大量的,而且常常是确定的,犹如经过了设计的实验一般。”(16)他的结论是:从科学分析的角度看,理论假说只是对现实的抽象或虚假的描述,不能通过比较“假说”与“现实”是否一致的方法来对理论进行检验,而“只有通过考察该理论所取得的预测,对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是否是足够令人满意的,或者是否是比来自于其他假说的预测更令人满意来作出回答”(17)。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发表后,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围绕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之一就是经济学是解释现象还是预测经济未来。
对弗里德曼上述观点坚定的反对者以萨缪尔森为代表。萨缪尔森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测:“我认为‘理论’作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的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的东西。”(18)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只是对经济现实进行的解释,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也就十分重要。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这个理论暂时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和摈弃。
本文认为,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主要源于他们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弗里德曼除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外,方法论上还接受实用主义哲学工具主义的影响;萨缪尔森在方法论上更多的是表现为从操作主义向描述主义的转变。这一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导致两人分歧的重要原因。
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预测功能,认为只要理论与未来的预测相符就不必在意其假定前提是否现实,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工具主义观点。在工具主义者看来,理论最好被视为只是一种工具,工具主义者仅仅关注得自理论结论的有效性。依据这一看法,理论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工具非真非假),而只是产生证明为真的(或成功的)预测或结论方便而有用的工具。正像一个锤子适合某些任务而不适合其他任务一样,工具只涉及它对特定任务是否适合的问题,理论的正确与有效性应由其预测力来加以评判。对自己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工具主义特征,弗里德曼也供认不讳。博兰德在1978年3月将自己替弗里德曼方法论辩护的论文复印件寄给弗里德曼后,4月14日收到了弗里德曼的回信。弗里德曼在信中承认博兰德把他描绘成一个工具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信中还谈到了他为什么不参加之后对他批评争论的原因:“我已经读过你所提到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我从来不认为对这些批评进行答复是恰当的,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东西真的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和你一样,我也觉得许多批评者都是由于误解了我所说的东西而造成的,再者,读者自己能够做出判断。我必须承认,我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得出的如此印象:在作者的方法论观点与其实际的科学工作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作为一个工具主义者——你把我描述成为一个工具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方法论研究本身对于影响科学结论这一目标来说不是一项显然有用的活动,不管它们对其目的来说如何有用。不过,能有像你这样才华横溢、对此主题有所掌握的人写一篇对积累下来的各种批评的答复,我感到由衷的高兴。”(19)弗里德曼对能由博兰德这位才华横溢、对此主题有所研究积累的人来答复对他的各种批评感到由衷的高兴。马克·布劳格对弗里德曼方法论上的工具主义也有所批评,他说弗里德曼反对假说的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当于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理论只不过是制造预言的工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批准我们所做的语言的推理许可证”(20)。布劳格一方面同意弗里德曼:“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但也坦承“经济学家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因而,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论还大有存在余地”(21)。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则经历了从操作主义向描述主义的转变。布里奇曼1936年发表的《物理学理论的性质》一文中正式创立了操作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操作知识(包括实验室或仪器等工具操作、纸币或语言等精神操作),没有操作意义的概念就应当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波普尔也分析过操作主义的特点,即“这个学说是说,理论概念必须用测量操作加以定义”(22)。布里奇曼在其著作发表一年后,萨缪尔森就以《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理论的操作意义》为题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提出有意义的原理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且这个假说可以遭到反驳,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从物理学领域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以推导出经济学中“有操作意义的定理”。1963年5月,萨缪尔森在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批判中又从操作主义转向了主张描述主义。萨缪尔森在其名著《经济学》这一教科书中明确提出经济学的方法应该是一种描述主义的方法。操作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强调理论的可操作性,描述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强调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因而就要求理论的假设必须是真实的。描述方法包括观察、分析和检验三大要素。观察经济现实是为了占有大量的统计资料,分析则是使用逻辑和几何学的演绎法以及使用统计、经验推断的归纳法等对相关统计资料进行逻辑推理,最后则是检验,看它是否有助于说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萨缪尔森强调,经济学研究一定要在占有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抽象,略去某些不必要的细节,提出把各种材料和事实联系起来的简单假设和形式,再通过逻辑推理对以经验为依据的资料作出精确的判断,然后把其运用于描述和制定经济政策。他认为经过描述法推导出来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最终要看它是否有助于说明分析观察到的经济现实。他认为经济学家在经济分析中应尽量摆脱个人感情的价值判断,树立一种客观超然的态度。在强调经济学应当是一门实证科学、证伪主义对检验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上,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同。双方的分歧之一集中在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的特征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因此强调并坚持理论假设以及按照这一假设逻辑推演出的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即一切要以现实的经验为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萨缪尔森不能认同弗里德曼的看法。他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设与现实性的非相关性”命题概括为“F歪曲”,之所以用“F歪曲”而不用“Friedman歪曲”,是希望他的这一表述最好不是弗里德曼的本意。萨缪尔森认为F歪曲包含了如果不用比现实更简单的事物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就会收效甚微,并得出了理论前提假设与现实不符是理论的优点这一推论。萨缪尔森运用数学逻辑并结合效用和利润极大化原则对之加以驳斥,得出结论:虽然不现实的抽象假定经常是有用的,但“如果抽象的模型包含有经验上的虚假,我们就必须抛弃这样的模型,而不是对他们的不恰当的地方进行掩饰”,“没有完全准确性的事实不应该是放松经济学命题是否经验有效的审查标准的借口”(23)。之后,萨缪尔森又针对弗里德曼论点辩护者的辩护文章给予回应,反复强调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论描述经验现实而不断更替和日臻完善的过程,因此与经验现实的接近也就十分重要,假设、理论和结论都应与经验现实相符。他还认为,对可观察的现实通过方程式或其他手段进行较好的描述,是能在世间得到(或期望)的全部“解释”。(24)萨缪尔森的上述观点代表了西方经济学家中的主流看法。
早在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在其发表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过与萨缪尔森相近的看法。罗宾斯强调,要发现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必须依靠演绎推理的方法,而正确的演绎推理需要有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正确前提或假设,这些前提或假设来自经验生活。如果这些前提假设与现实相关联,来自这些前提假设的推论也就必然与相同的现实相关联。经济规律描述的是经济现象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假设和前提条件,从这些假设和条件得出的结论则必然是正确的。(25)他认为在经济学上的重要原理都是从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的,这些假说乃是众所周知的公认的事实,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经济分析的性质已昭然若揭。经济分析由得自于一系列假设的推论构成。其中主要的假设,涉及的是与人类经济活动有关的几乎普遍的经验事实。”(26)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基本命题如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是从“存在一个以上的生产的稀缺要素”和“简单而不可辩驳的经验”的假定必然地得出来的,这些假设有现实中存在的对应物,对此没有争论。正是由于这种来自正确前提与演绎推理的必然性,经济学才具有很大的解释分析功能。
罗宾斯还认为,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质的分析,而不是对经济未来进行预测。这是因为经济系统是开放的,会存在有许多不确定性,甚至对需求弹性的估计事实上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假如我们能一下子确定所有商品的需求弹性和所有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假如我们能假定这些系数是固定不变的,则我们确实便可以设想人们能进行大规模的计算,使经济学上的拉普拉斯能够预言整个世界在未来任何时刻的经济现象。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计算虽然对于预测特定情况最近可能发生的变化是有用的,但却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永远有效的。经济学上的拉普拉斯必然会失败,因为在他的体系中并没有上面假定的那种常数。”因此,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功能是解释分析经济现实。(27)
在这场论战中,许多经济学家对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的方法论集中进行了批评。弗里德曼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工具主义明显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两人都把理论视为假说。在杜威的心目中,任何理论是假设,是工具,其价值在于理论所能产生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工具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真假均不是判断的特性。工具只有有效和无效的区分,注重的仅是理论工具性的功效问题。因此杜威并不关注理性的、演绎的证明。在弗里德曼的心目中,假说与理论是一回事。弗里德曼关心的是理论的有效性问题,理论的有效性则看其预测与实际数据相符合的程度,预测是评价假说或理论的“工具”,而理论是预测成功或不成功的工具,假设的真假问题则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威布尔在其论文《杜威和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中分析了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关联,并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F—1:工具主义;理论是工具,是经济科学的工具、智力资本和“预测生成器”。F—2:短期预测成功;在短期,对经济模型的评价取决于其预测的成功性。F—3:可复制性;预测必须可复制,这有赖于经济研究的某种同质性假定。F—4:无限回归性;由于实证经济学和经验归纳方法得到工具主义的支持,无限回归是可接受的。F—5:认识论范畴的不可知论;因为归纳是无限回归并且不能被证明的,因此对真理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F—6:本体论范畴的不可知论;由于认识论范畴中的不可知论,对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现实性、最大化的合理性以及其他理论概念也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威布尔还评论说:如果说杜威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哲学家,弗里德曼则只能是方法论上的一个工具主义者;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杜威工具主义的一种范围更窄的特例。(28)
威伯也批评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错误。他认为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理论被认为只是在产生预测时方便而有效的工具,因此可以认为与理论有关的实体的存在性的命题的真假无关紧要。理论工具允许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只要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具有预测作用。威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一般认为没有解释力的理论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解释不能包含经验上已知为错误的前提。他以托勒密的地心说为例对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进行质疑:虽然通过选择适当的算法,托勒密的天文学说对天体运行位置的测定可以取得与现代天文学相媲美的精度,但现代天文学家绝不会考虑将托勒密的天文学说纳入科学知识的范围,因为其学说是建立在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假设之上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具有圆形轨道的宇宙。(29)
威伯设计了三条批判弗里德曼论点的路径:首先,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门科学学科实践的哲学分析会导致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抛弃,因为科学的主要目标并非预测而是解释。例如达尔文的理论并不会因为缺乏预测力而妨碍其取得正统科学的地位。(30)其次,他认为一些将弗里德曼肯定为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解释似乎理所应当地认为古典经济学在产生真实预测方面是高度成功的。但这种看法显然有问题。在威伯看来,大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作的是严格的分析,这些分析有的根本不具有经验的意义,比如一般均衡存在的分析性证明。他认为经济学实践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分析研究并不是着眼于经验检验而是作为为进一步争论提供分析框架的跳板。少数新古典经济研究涉及使用经验数据产生了检验假设重要性的夸张印象,威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很少涉及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检验而更多的是对理论的应用,例如对商品需求弹性的估计是对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而不能算是一种检验。其三,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评价理论的辅助标准:简单性、富于成果、逻辑完整性,威伯认为这些标准是相互冲突和模棱两可的(31)。威伯强调,如果经济学家想让经济学效仿其他科学,他们就应该知道,在科学实在论和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论战中,实在论已经胜利了。(32)他坚持对经济理论的评判应该看其对真实经济世界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和解释有多少逼真度为基础进行判断。(33)
仔细分析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等人之间的论争,不难发现弗里德曼的“预测”和萨缪尔森的“解释”之间二者词义上有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和混淆。例如弗里德曼所说的“尚未观察”的现象包括尚未发生的现象、已经发生但观察尚未进行的现象、已经发生而且观察已经作出但利用理论或假说进行预测的人尚不知晓的现象这三种情况,这其中的后两种情况就近似于萨缪尔森所说的“解释”范围。从逻辑上分析,解释和预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解释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后,预测产生于事件发生之前;解释是从一个需要解释的事件开始,找到一条一般规律以及逻辑上隐含着对该事件说明的一系列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再援引一个具体原因对一个事件进行说明,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把该事物统摄在这一普遍规律之下的过程;预测的过程则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及一组初始条件假说开始去演绎对一个关于未知事件的说明,是用来检验一般规律假说是否得到确认的办法。解释的前提假说必须强调其现实性,预测则不必,因为它主要关注预测未知事件发生的概率。
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科学特征在于预测未来还将面临如下的难题:我们如何知道理论已经产生了准确的预测?我们又如何知道理论的预测在将来也能满足?弗里德曼的预测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预测”一场赛马或总统竞选的赢家,或者说预测下周将是世界末日,那么这只不过是一个预言而不是科学预测。通常条件下,科学预测应是有条件的,并以此类假设的普遍规律为基础:如果A,则B。弗里德曼的预测理论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斯坦利就质疑弗里德曼:如果人们追求对所观察现象的真实解释,那么工具主义就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工具主义者只把眼光放在预测成功上,它无法把欺骗的相关性解释和成功预测中的真实性明确地区分开来(34)。斯德尼·舍弗尔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的失败》一书中对弗里德曼的预测说也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只有存在不受具体情况限制的普遍规律时科学预言才有可能,而由于经济系统总是向非经济力量和机遇的作用开放的,就不会有经济规律,从而也没有像这种规律的经济预言。”(35)舍弗尔为了否定弗里德曼对经济学预测特征的强调,进而也干脆否定了经济规律的存在,也有失偏颇。
客观而论,这场论战的结果无疑促进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使得“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发展产业”,(36)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兼收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两派的优点,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使得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获得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本文认为,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其功能主要在于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理论的创新也是来自于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判断经济学理论得失的标准也就在于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37)经济学若有预测功能更好,但不应将是否具有预测功能作为判断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特征的惟一标准或根据。工具主义在哲学上也是难以成立的。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用动态的经济发展去检验某一经济理论的预测成果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38)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⑨⑩(12)(13)(15)(16)(17)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193、194、195~196、197、227、230、196~197、199、230页。
⑥(14)布赖恩·斯诺登:《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王曙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153~154页。
⑦⑧(22)[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委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353页。
(11)约翰·伯顿:《注重实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J.R.沙克尔顿等编:《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2~63页。
(18)(20)(21)(35)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133、117、278~279页。
(19)(23)Boland,L.A.,1997,Critical economic method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12;中文译文转引自李和平著:《弗里德曼论点及其争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注①、166页。
(24)Samuelson,P.,"Theory and Realism:A 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1964,Vol.54; Samuelson,P."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Repl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1965,Vol.55.
(25)(26)(27)[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7、83、107页。
(28)James R.Wible,"The Instrumentalisms of Dewey and Friedman",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Dec.)1984.Vo18,no.4,p.1051.
(29)(30)(31)(32)(33)Webb,J.,"Is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A Special Case of Dewey's Instrumental Philosophy? A comment on Wible",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March)1987,Vol,21,p.396,p.408,p.409~410,p.420,p.421.
(34)Stanley,T.D.,"Positive Economics and its Instrumental Defence",Economica,(Aug)1985,Vol.52,No.207,p,311.
(36)Hands,D.W.,1993.Testing,Rationality and Progress.MD:Bownon & Littlefield.
(37)韦定广:《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50页。
(38)参见赵艳:《萨缪尔森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启示》,《税务与经济》2004年第2期;傅耀:《试析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标签:弗里德曼论文; 萨缪尔森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科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