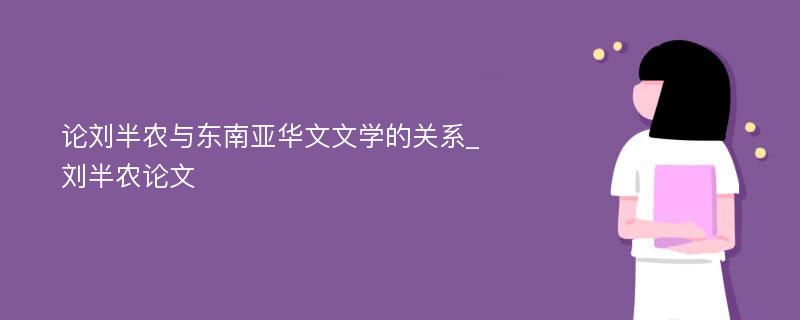
刘半农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关系谈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刘半农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刘半农(1891—1934)逝世70周年。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因为赴西北考察方言 染上回归热而以身殉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锋人物,五四白话新诗的 播种者,刘半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已获得人们的肯定。
然而,刘半农在文学革命和新诗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国内,他的影响远及海外 的东南亚地区,只是由于时光流逝、地域阻隔以及原始资料的尘封而不为人们所知。笔 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搜集到一些刘半农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关系的资料,现在 披露如下,以供学术界研究之用。
从刘半农长女刘小蕙回忆录《父亲刘半农》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来看,刘半农曾经于192 0年赴英国伦敦留学,以及1925年从法国获得国家文学博士后回国时两次乘船途经东南 亚(当时称南洋)。刘半农在回程中乘坐法国轮船Porthos经过马来西亚和越南时,曾创 作出与当地景物有关的诗歌,这就是《归程中得小诗五首》(注:刘半农《归程中得小 诗五首》,见赵景深原评、杨扬辑补《半农诗歌集评》,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年,第100页。)中的其四和其五:
其四 哥伦波海港
椰林漾晴晖,海水澄娇碧。
咿呀桨声中,一个黄蝴蝶。
其五 西贡
江上女儿愁,
江树伤心碧,江水自悠悠!
诗中的“哥伦波海港”应指“Kuala Lumpur”,即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西贡” 则是现在越南的南方城市。
尽管刘半农终其一生并未踏上东南亚的土地,但东南亚华文文坛却将他视为文学革命 的先锋,以及在取法民间歌谣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作为五四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刘半农在向域外诗歌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也将学习 的视野转向民间歌谣。从刘半农的《国外民歌译自序》来看,五四时期首先倡议征集民 间歌谣的是刘半农:
这已是九年以前(即1918年——笔者注)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 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 “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即北大校长蔡元培——笔者注)用北 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 五千份,分寄各省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注:刘半农《国外 民歌译自序》,见刘半农《半农杂文二集》,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9页。)
此后,全国各地的民歌民谣纷纷寄到北大,刘半农择优选刊,从1918年5月20日到1919 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共发表了他亲手编订、注释的歌谣148首。(注:徐 瑞岳《刘半农评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
1920年冬,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冬出版《歌谣周刊》,同时出版歌谣丛 书,共有《吴歌集》等8种。此时刘半农已赴英法留学,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北大歌谣研 究会的发展情况,将20首《江阴船歌》和论文《海外的中国民歌》寄回国内分别发表在 1923年第24期和第25期的《歌谣周刊》上。1925年刘半农回国后,于次年出版诗集《瓦 釜集》,被誉为是“用方言俚调作诗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成功者”。(注:渠 门《读<瓦釜集>以后捧半农先生》,见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1985年,第277页。)
由刘半农首开风气的取法民间歌谣的热潮,也传播到当时的东南亚华文文坛。1922年3 月10日,新加坡《叻报》在“特别记载”栏位上刊登《北京大学消息》,其中就有北大 “歌谣研究会”消息:“该校旧有歌谣研究之设,专用以采集各地歌谣,加以整理编辑 ,仿佛古人采诗遗义,其作用甚大。据闻所采到者为数已不少,近由该校教授会议决, 将该会并入国学研究所办理,性质相近,关系密切,合冶一炉,自属正当办法。”在刘 半农等人取法民歌民谣的影响下,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辟设“童 谣”栏位刊登歌谣和民歌体诗,吉隆坡《益群报》副刊《自由谈》也辟有“新歌谣”栏 位。
不仅如此,刘半农的一些著译作品也被东南亚的华文报章副刊所转载,而它们究竟是 被当地华文报章直接从中国报刊上转载,或是刘半农亲自寄给当地,现在尚无法作出结 论,只能期待将来更多资料的发现。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刘半农著译作品被当地报章转 载的资料:
1、《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论文)署名刘半侬
载1921年9月13日,10月3日至17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原载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20年新诗社出版部出版《新诗集》时作为“附 录”摘收,题目为《诗的精神上之革新》。)
2、《疗妒》(小说)署名半侬
载1922年8月19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原载1915年1月2日《礼拜六》周刊第31期)
3、《在山中往往来来的走》(译波斯民歌)署名刘复载1929年3月28日新加坡《新国民 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原载1926年8月7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第2卷第7号,初收《国外民歌译》第一集, 1927年4月。)
此外,作为中国白话新诗的播种者,刘半农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诗论也被东南亚的华 文报章副刊所引录,如马来西亚槟城《南洋时报》副刊《诗》于1927年1月30日在刊首 显著位置上刊登刘半农《<扬鞭集>自序》中的部分文字:“我可以一年不作诗,也可以 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为的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为的是有了感想肚 子里关熬不住。”《诗》副刊编辑的用意当是以刘半农有关诗歌创作的体会指导当地华 文作者进行诗歌创作。
更令人惊喜的是,笔者在1928年2月22日马来西亚槟城《南洋时报》副刊《怒涛》创刊 号上阅读到刘半农寄给该刊的一首《民间歌谣》。从《怒涛》编者拔其的编后语《最后 几行》中“本刊蒙半农先生由国内惠来《民间歌谣》一首,增光本刊不少;这是一篇极 有趣味的民间文学,请读者留意鉴赏吧!”(注:拔其《最后几行》,见《南洋时报》副 刊《怒涛》创刊号,1928年2月22日。)可以认定,刘半农与《怒涛》的编者有着直接的 联系。大概是编者拔其在创办《怒涛》时为了提高该刊的地位而向中国新文学名家刘半 农邀稿吧。笔者查阅了有关刘半农著作情况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均未见及这首《民间歌 谣》,因此抄录如下。从这首歌谣的语音看,其应属于闽南语歌谣:
天乌乌,云漠漠,
一阵畜生招摇过大路,
猪兄狗弟相照顾。
大×仔,真可恶,
乌呢衫,白绫裤,
拿把手杖量街路;
手杖拿来有格势,
目镜挂来乌水晶,
可惜肚内无半字!
看见女士目睁睁,头敲敲,
尿壶面,象管鼻,
十分殷勤展神气,
可恨女士不睬伊,
转与阿×做“猫戏”。
一月进贡念花边,
舅仔流濞,
外甥更流濞。
三保公,唔保庇,
有时抄文被人知,
舅仔听见真生气,
一五一十来教示:
你这外甥狗,
真正不知走,
这首《民间歌谣》篇末注有“未完”二字,显示尚未完全登载完毕,但歌谣中嘲讽市 井好色之徒的无赖相以闽南语读来十分生动形象。其中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刘半农身为 江苏江阴人,却收集闽南语歌谣供马华报章副刊发表,这实在有点耐人寻味。也许是应 《怒涛》编者拔其的请求,也许是刘半农自己考虑到新马两地闽南籍的华人移民较多, 而特意收集富有闽南地域特色的歌谣以飨新马读者,笔者只能在此进行推测,并期待将 来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在紧接着出版的《怒涛》特刊号中,编者拔其又说 :“本刊蒙半农先生允为本刊长期撰稿,此后当时时有先生的民歌民谣可读。”(注: 编者《最后几行》,见《南洋时报》副刊《怒涛》特刊号,1928年3月1日。)《怒涛》 编者邀请刘半农为该刊“长期”撰稿,而且点明是“民歌民谣”,可见他对刘半农在收 集和取法民歌民谣方面的成就是肯定和推崇的,而且有意借助刘半农的民歌民谣让东南 亚读者“鉴赏”这种“有趣味”的民间文学,同时也引导东南亚华文写作者借用或吸收 民歌形式。不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后来在《怒涛》上未能如编者所说的那样再有“( 刘半农)先生的民歌民谣可读”,上述尚未登载完毕的闽南语《民间歌谣》也没有了下 文。从刘半农的生平著述情况来看,1928年之后,刘半农更多的是从事学术研究,而极 少再进行文学方面的创作和译介工作,这大概就是刘半农没有继续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界 联系的主要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