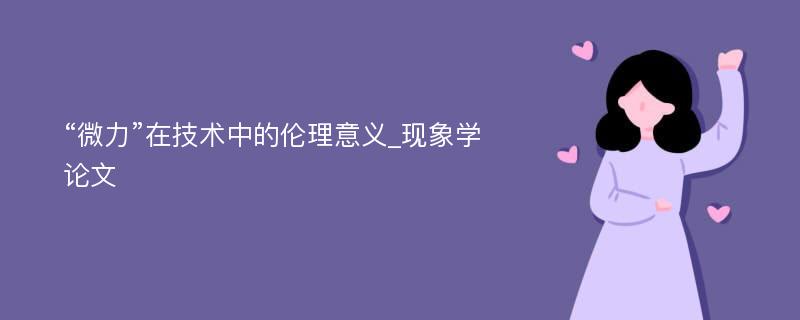
技术“微观权力”的伦理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伦理论文,权力论文,意义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对权力的关注是贯穿福柯学术思想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在福柯之前,“权力”概念始终没有超出宏观的“法权”范围。福柯的贡献在于把权力从“法权”中解放出来,提出了“微观权力”概念,重新解释了权力的产生机制和表现形态。这一思想为人们从权力的视角重新理解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技术是众多“微观权力”的一种。技术的“微观权力”体现在其“居间调节(mediating)”机制之中,这种机制的伦理意义在于,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技术产品可以实现对伦理行为的“激励”以及对非伦理行为的“抑制”。 一 作为“微观权力”的技术 福柯认为,“如果法律也许曾经使我们并不完全地描述某种基本上以剥夺和死亡为中心的权力,那么,新的权力手段则完全不同,它们不靠权力,而靠技术;不靠法律,而靠正常化;不靠惩罚,而靠控制,而且其涉及的范围及采用的形式都超出了国家及其机构”[1]。当然,“福柯这样说并不是真的认为权力机制与法权毫无关系,他只是借此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的表现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而分析法权的思维模式已不再适合分析新出现的权力机制”[2]。福柯的“权力”概念并非局限于人们通常理解的宏观的国家机器或政治统治。在福柯看来,“在这些看似宏伟的宏观权力理论大厦之下,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正以一种十分隐蔽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它没有法律的威严神态,也没有革命的激昂热情,但它却以一种润物无声的高超技巧塑造着每一个现代人的主体意识,从而将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监视、控制之下”[3]。福柯所说的隐蔽的悄无声息的权力运作,就是“微观权力”的表现,它在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很难被人们意识到。 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知识与权力》等一系列著作中,福柯对“微观权力”思想进行了不同侧面的论述。他认为,权力的本质是在关系中形成和运作的权力的关系网,只要存在关系的地方就会存在权力。它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人与物之间。“它作为一种强力意志、指令性话语和普遍的感性力量,存在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具有服务、影响、操作、联系、调整、同化、异化、整理、汇集、统治、镇压、干涉、反抗和抵触等多种功能属性。”[4]因此,“微观权力”在人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工厂、学校、医院、监狱、军营、技术、习俗、知识等实体中都渗透着权力的身影。比如,在工厂里,权力就体现为工厂主对员工的约束和管控;在学校里,权力就体现为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在医院里,权力就表现为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在监狱里,权力就表现为监狱管理人员对囚犯的管教与惩罚。而技术作为现代社会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在福柯看来,也是一种微观权力。他指出:“最重要的观点是必须把权力的机制和权力的贯彻程序看作是技术,看作是始终不停地发展、不断地被发明和不断地被完善化的程序。”[5]他受到马克思关于工厂统治技术观点的启发,“在有关‘性’的问题上尝试不再把权力从单纯政治法律的观点,而是从技术的观点去看待”[6]。尽管他在这里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技术”的,但他将技术视为一种“微观权力”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理解狭义的“技术”,即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技术。 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与技术哲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7]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权力”在福柯思想中的地位类似于“技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地位,权力和技术都以一种意志性力量规范和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行为,进而塑造着整个世界。但是福柯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地方在于,他对权力的具体结构以及如何影响某个实践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比较感兴趣,而海德格尔则以一种宏观的、形而上的视角来审视抽象的技术。按照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的理解,前者的研究更类似于“经验转向”后的研究进路。[8]“微观权力”不像政治权力等宏观权力那样只具有压制性和异己性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建设性(productive)”的特点。人类社会性的获得正是在各种各样的权力的“规劝”下实现的,人的本质是“权力”的产物,一个好的“权力”环境会造就出好的人格和素质;相反,坏的“权力”环境也会导致坏的人格和素质,技术的应用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与福柯类似,温纳也认识到技术中所蕴含的权力之维。他指出:“我们称作‘技术’的东西也是在我们的世界中建构秩序的方式。许多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技术装置和系统包含着以不同的方式规范人类活动的众多可能性。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蓄意地或不经意地,社会选择了某些技术的结构,它们将对人们如何去工作、交流、旅行、消费等等,产生长久的影响。”“如果我们用以评估技术的伦理和政治语言只包括与工具和用处有关的范畴,而不去关注这些技术物的设计和布局的话,我们将不能发现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相当重要的方面。”[9]一些人可以利用技术来实施或加强对其他人的控制,从而实现其预定的政治目的,“以至于它时常产出的结果被一些社会利益群体誉为美妙的突破,而对其他人而言则预示着压倒性的挫败”,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纽约长岛上天桥的设计中所蕴含的政治倾向。[10] 二 技术“微观权力”的内在机制 技术之所以被称为一种“微观权力”,其根据在于它对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居间调节”作用。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和法国哲学家拉图尔分别就技术在认知环节和行动环节中的居间调节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出技术“微观权力”的内在机制。 在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现象学传统中,伊德的贡献在于增加了一个技术的维度[11],提出了“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或“技术现象学”理论。在胡塞尔那里,“超验的自我(transcendental ego)”——即无实体的(disembodied)意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了梅洛-庞蒂那里,无实体的意识实现了“具身化(embodiment)”,从无形转向了有形;而伊德则进一步从身体本身走向身外的技术。可以说,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的发展,是对新的“预先被给予者”不断发现的过程。在伊德看来,能够影响世界显现的“预先被给予者”包括意识、语言、知觉、技术等要素。这样一来,外界信息进入人的意识,就需要首先经过技术的“转译”这一环节,然后才能进入人的知觉,再转译为语言,最终进入人的意识。伊德的技术现象学不同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技术现象学的地方在于,后者的技术现象学是以先验的视角把技术还原为它何以可能的条件,如海德格尔把它还原为“技术思维(technological thinking)”,雅斯贝尔斯则把它还原为“大批量生产系统(the system of mass production)”[12],而伊德的技术现象学由于吸收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成果,技术不再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具体的技术成为现象学的分析对象,并且技术也不再仅仅被看作负面的,人们开始用更加全面、中立的眼光来审视它。 伊德的“后现象学”指出,在通常情况下,人并非直接面对世界(人—世界),而是通过技术这一中介面对世界(人—技术—世界)。技术的居间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在转换人关于世界的感知方面具有“放大(amplification)”和“缩小(reduction)”的作用。[13]在这一调节作用下,世界的一些属性会得到彰显,而另一些属性则会被遮蔽。比如在使用一个红外仪器探测人的身体的时候,肉眼可见的大部分信息都会被它过滤掉,但它也会“看”到一些人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如身体的温度分布。伊德称技术的这种“放大”和“缩小”作用为“技术的意向性(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这也反映出,技术在帮助我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并非是中性的,而是能动地影响着世界哪些信息会被呈现,哪些信息会被遮蔽。当然,“技术的意向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在不同的使用情景中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多元稳定性(multistability)”。在伊德看来,一项技术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本质,它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与它所使用的语境密不可分。正如他所言:“一项技术可以以多种方式保持‘稳定’,它的本质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于不同的使用方式之中。‘技术的意向性’依赖于技术的各种使用方式。”[14]在具有意向性的技术的居间调节之下,世界呈现出与人们用肉眼直接观察它时不同的表象,这种现象在现代科学实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技术的这种居间调节作用是“预先被给予”的,具有以隐蔽方式干涉、控制、调整技术认知和实践活动的作用,这正是“微观权力”的体现。 与伊德主要关注技术对认知的居间调节作用不同的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重点关注的是技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这和伊德的“后现象学”正好形成对偶关系。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传统的超越。不过,与克服现代主客二分观念的“后现代主义”进路相反,他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15],主体和客体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现代的主客二分图景其实是一个幻觉。在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人和物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他用“行动者(actants)”和“网络(network)”来取代传统的主体和客体的表述。不论是人还是物,都是行动者,两者共同组成了相互交织的行动者网络,在行动者网络中扮演着对等角色。拉图尔举例说,如果一个人用枪杀死了另外一个人,那么是“人”还是“枪”导致了受害者的死亡呢?从物理的因果机制角度来看是“枪”,而从事情发生的动机来看是“人”。拉图尔认为,“枪”和“人”共同导致了受害者的死亡,两者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组成了一个复合的行动者——“枪-人(gunman)”。人的行为方式也可能被他使用的工具所塑造。“行动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结果,而且是个人的物质环境的结果。”[16]比如公路上限速的“减速坡”,它可以把司机的意向从“因为我有急事,要快点开”或“为了负责任的行动,要慢点开”,转化为“为了保护我的减震器,要开慢点”。 拉图尔指出,与认知领域中技术通过“放大”和“缩小”机制实现其意向性类似,在行动领域中,技术也能够通过“激励(invitation)”和“抑制(inhibition)”机制来实现其意向性。同样地,“行动者”也没有一个预先被规定的本质,它是什么取决于它当时所处的网络。另外,拉图尔还区分出了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四种居间调节样式:“转化(translation)”、“合成(composition)”、“可逆的黑箱化(reversible black-boxing)”、“委托(delegation)”。[17]“转化”即对原初行动计划或意图的转变。“合成”即某一行动依靠人的力量是不足以实现的,只有在其他技术的辅助之下方能实现。“可逆的黑箱化”的意思是,上面两种现象往往不被人所察觉,就像被隐藏在黑箱里还没有被打开一样。但是一旦技术出现了故障,人们就注意到它的存在,就像海德格尔从“上手(ready-to-hand)”到“在手(present-at-hand)”的转变。拉图尔用“可逆的黑箱化”来提醒我们,其他的行动者虽然通常并不为我们所注意,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会从背景中走到前台,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委托”即人们把某些任务交由技术去完成,比如上面提到的“减速坡”,工程师在设计它的时候就赋予它减缓车辆速度的任务,那么“减速坡”在工作的时候就完成了工程师交给它的使命。[18]在“行动者网络”中,技术物和人一样发挥着“行动者”的作用,实现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塑造。这种“塑造”也是“微观权力”的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干涉性和调节性。 三 技术“微观权力”的道德化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既然技术的“微观权力”机制体现在技术对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居间调节作用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权力机制来引导和规约人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发挥其有利的作用,从而使设计活动变成一种具有伦理意义的实践。与之相应,设计师也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责任,即他们不能只关心技术的实用性和美观性,而且还要关心技术功能对人的认知和行为所产生的居间调节作用,即技术的伦理性。用维贝克的话说,“如果伦理学是关于人如何行动的,设计师帮助塑造技术调节人的行为的方式,那么设计应该被视作伦理学的一种物化形式(material form)”[19]。 针对当前工业设计理念和实践很少注意技术物的居间调节作用的现状,维贝克提出了一种“物质美学(material aesthetics)”的设计思路。[20]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技术物具有两方面的效用:一类是实用功能(practical functions),又称第一功能;另一类是象征功能(semiotic functions),又称第二功能。[21]第一功能是技术物的存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能,如衣服的御寒功能、汽车的运输功能;但是在技术物提供的基本功能之外,还附加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如同样是衣服,有些衣服显示出“传统”的风格,而有的则显示出“前卫”的风格。购买者选择什么风格的衣服,就彰显出他/她的审美理念和价值追求,以及他/她试图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希望别人认为他/她是什么样的人。此时,衣服是作为一种符号而存在的。维贝克指出,技术物的居间调节功能既不属于实用功能,也不属于象征功能,它是实用功能的副产品。[22]因此,要把技术物的这种居间调节作用纳入到设计的考虑之中,就必须扩大传统设计美学的视野。 维贝克指出,自从大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以来,设计美学已经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转变,首先是工艺美术运动的“师承自然”美学,然后是包豪斯的现代主义机器美学,再后来是波普设计(pop design)的“用完即扔(throw-away)”美学,最后到后现代主义的“生活肖像(lifestyle iconography)”美学。在这种演变进化过程中,技术物的视觉特征越来越为设计人员所重视,这种“视觉主义(visualism)”在后现代设计思潮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技术物几乎完全成了体现生活品位和价值追求的手段。维贝克认为,这种以视觉为中心的设计美学理念太过狭隘。他从词源学的角度重新反思了“美学”的本来面目。英语的美学一词来自古希腊语aesthesis,意思是“感觉认知(sensory perception)”。[23]可见,美学的原初含义不是专指视觉上的联系,而是一种广义的感觉联系,其中还包括听觉的、触觉的、嗅觉的、味觉的联系。在某些技术物的使用中,触觉联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视觉联系,如沙发的柔软性、衣服的舒适度等。从技术物与艺术品的区别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说,技术物是介于自然物和艺术品之间的一种存在形式,不能把它等同于艺术品,因为它不全部是用来观赏的,而必须具有实用性。因此,工业设计不能像艺术品的设计那样仅仅关注技术物的视觉特征,应该把工业设计理念从单一“视觉”层面拓展到广义的“感觉”层面。 维贝克以环境保护方面的实践为例解释了“物质美学”的设计思路。他指出,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各种努力上,人们要么去设计和发明无污染的清洁技术,要么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引导人们养成环保的行为或生活方式,而很少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这种“双轨制(two-track)”策略是极为低效的。第一,单纯地关注设计和发明清洁技术本身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会抵消技术本身的优势。例如,节能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对电能的消耗,但是,正因为耗电量的降低,平均照明时间也比以前延长了,并且许多家庭把原来不需要照明的地方也装上了节能灯,这样,节能灯的发明不但没有起到节约电能的效果,反而助长了电能的消费。[24]这种效应被杰文斯(W.S.Jevons)称为“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或者“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第二,只注意从宣传和教育的角度来引导人们养成一种环保习惯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很多宣传形同虚设。因此,要想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很有必要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既注意技术本身的环境保护作用,又注意到技术会对行为产生的结果,把人的行为反应也考虑到设计的环节之中。[25] 把“视觉”拓展为广义的“感觉”,工业设计就可以和技术的居间调节作用建立联系,从而使技术的中介性在设计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设计就不仅仅关注技术物的第一功能和第二功能,而且还要关注功能的副产品——使用者与技术物的关系,以及技术物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塑造。“物质美学”使传统的工业设计有可能从对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关注拓展到对伦理功能的关注。用维贝克的话说,设计师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着伦理学家的工作,他们是“实践的伦理学家”。[26]他们的产品以一种物质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意味着技术的“微观权力”的道德化。它的功能不仅仅是约束性的、强制性的,还包含建设性的、引导性的作用。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技术产品可以实现对某些伦理行为的“激励”以及对另一些非伦理行为的“抑制”。 不过,目前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还没有认识到技术“微观权力”道德化的价值。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同一个工具既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这就证明设计者并不能预先决定工具的使用方式,因此技术是价值中立的,设计者不具有伦理上的责任。不可否认,“价值中立论”在近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起到了保护科学技术发展免受宗教干涉的作用,但是现在却成了工程技术人员推脱自身伦理责任的一个保护伞。“技术中介论”通过有力的论证展现了技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的塑造作用,因此它必然是负载价值的,那么责任就不仅仅是使用领域的事情,而且也是设计领域的事情。尽管设计环节并不能完全决定技术物如何被使用,但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物使用的方式,设计在其中具有一种“原发性的(seminal)”作用。“价值中立论”是把责任由设计环节向后转移到使用环节之中,因此责任只能由使用者来承担;而“技术中介论”则把责任的领域由使用环节向前推进到设计环节之中,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具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在这里,技术的“微观权力”和伦理责任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技术“微观权力”的伦理意义在中国当前技术实践中尤为重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所采取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开展思想品德教育,鼓励公民道德实践活动以及营造高尚的社会风气,这些措施和手段基本上都是以“道德内化”的形式进行的。而技术“微观权力”的道德化可以作为“道德内化”的一种互补手段,因为它是依靠技术本身的“微观权力”来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的。在一些人道德自律意识下滑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微观权力”的道德化来引导和调节人们的行为,并以此为手段来促进“道德内化”的实现,就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当然,既然人们可以利用技术的中介性来积极地引导人们的行为,同样它也可以被用于不道德的意图。因此还必须从社会宏观权力的角度对技术设计活动进行法律、伦理和政策的规约,以便更好地发挥技术“微观权力”的道德化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