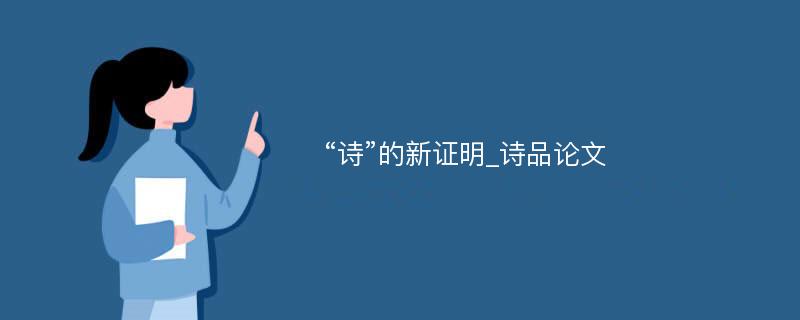
《诗品》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21-07
以今日言之,古代文论的阐释性研究已经相当深细,同时,文论的文献学研究仍然值得期待;在典籍基本问题尚待考证解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钟嵘《诗品》即属此例。是不是专评五言诗、传本序言位置是否古本原貌、初名是“品”还是“评”,这些都是《诗品》基本问题,也是疑难问题。研讨这些问题,需要细读文本,也需要观察角度调整和认知前提更新。据我们所察知,《诗品》原是一部有评论的诗选,并非单纯的诗评(参拙作《钟嵘〈诗品〉原貌考索》,刊《文学遗产》2010年第四期),而《诗品》总集文献性质的确认,应有助于视角转换和认知更新,并有话语基础重建的意义。
一、《诗品》条例:专录而非专评五言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中品序)这是《诗品》条例,对此论者没有歧议,但这句话的涵义为何,以及《诗品》是否严守此例,诸家说法不一:
1.许印芳《诗法萃编》:只评五言徒诗,不评五言乐府①。2.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李徽教《诗品汇注》、杨祖聿《诗品校注》:不仅评徒诗,还评乐府诗,并偶及四言②。3.曹旭的意见是:评五言徒诗,也评乐府,但不评四言、七言、杂言③。
本文认为,三种意见,第二种最近事实。《诗品》确是既评徒诗,也评乐府。五言徒诗自不必说,乐府也很显然,上品所评班婕妤《怨歌行》(“《团扇》短章”)就是。此外,还涉及四言。如“孝若虽曰后进,见重安仁”(下品《夏侯湛》),许文雨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认为夏侯湛(孝若)所作《周诗》乃四言,许说是。不过五言、乐府和四言还不是《诗品》评论的全部对象,《诗品》评语还涉及七言:“《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切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下品《释宝月》)《行路难》今存,是七言杂诗,《玉台新咏》卷九题释宝月作。《诗品》又说到赋:“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干。颜为诗笔,辄偷定之。后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下品《区惠恭》)
也许论者以为这三例是闲谈轶话,不是正面评诗之语,不能以此认定《诗品》评论超出五言范围,违了例。我们认为不能这么说。如《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中品《谢惠连诗》)这是谢惠连评语中的一段。不过这一段既不是评谢惠连诗,也不是评谢灵运诗,只是跟谢灵运一个五言名句有关的闲谈轶话,但也被研究者视为诗歌评论,被当作《诗品》“本事批评法”的例证④。这一段与上举三例不同的是,这一例是说五言诗,上三例不是。但总不能说讲五言的就是《诗品》评语,不讲五言的就不是《诗品》评语。只要是评语里的,无论是否评说五言,都应视作评语的组成部分,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双重标准⑤。另外,还应看到,评语述及四言、七言,并非钟嵘大意走神,而是有意为之,看下文举例可更明了:“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中品《沈约诗》)这是说沈约五言诗优于其他诗型和文体的制作。再如“元长、士章,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下品《王融、刘绘》)这是说王、刘五言诗不如其他诗型和文体的制作。二例都是在与其他诗型和文体的比较中评说五言诗的,“并有盛才,词美英净”更是正面对王、刘文章才笔的总体评价。此外,《诗品》还说到了论文著作:“观厥《文纬》,具识文之情状。”(下品《陆厥》)据陈延杰、许文雨和萧华荣先生说,“文纬”当是陆厥论文之书⑥。照这么说,《诗品》评说了著述文体。
四言、七言和赋,还有论述文字,这些诗型和文体都是钟嵘的谈资话题,当然也都是《诗品》的评论对象。评语如此,序言也是。“嵘今所录,止乎五言”——与“止乎五言”相对,中序所评《文士传》载文和“谢客集诗”就应不纯是五言诗;至于“颜延论文”、“挚虞《文志》”云云,评论范围更是超出了诗赋域界。
《诗品》里有这么多五言诗以外的评论,再要说它专评五言诗,显然讲不通;要是把这些评说都视为钟嵘无心误书,显然也说不过去。这是一个难题。在《诗品》为单纯诗评的认知前提下,这个难题无法解决,条例与实际评说之间的矛盾假象无法解释。如果改换认知前提,疑难便涣然冰释。《诗品》原来是有评有选之书,选的都是五言诗——“嵘今所录,止乎五言”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是专录而不是专评五言诗,那么评语里说到其他诗型和文体便不奇怪,《诗品》是否严守条例的追询也就有答案了。说《诗品》为例严,并非由于它专评五言诗;反过来说,《诗品》不是专评五言诗,也不能说它为例不严。判认依据不在“评”,而在“录”;“录”即收录、载录之义。《诗品》是诗选,钟嵘也是用表示“编录”意义的词来指称《诗品》结撰方式的,这就是“录”和“诠次”(“诠次”见中品序)。这两个词提示了《诗品》的文本构成和文献类别,我们以前没有留心。《诗品》中共有“录”字四处,另外三处是“嵘之今录”(序)、“诸英志录”和“不录存者”(中品序),四处都是指作品选录;《诗品》序文举称撰例三条,本文文首所引之外,另两条是:“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这两条也都是说作品收录。
重述本文观点:《诗品》严守“止乎五言”之例;是“所录”,而不是所评“止乎五言”。这就是《诗品》既评说五言诗,也评说其他诗型和文体的原因所在。
二、序言位置:吟窗本体式是原貌
(一)“上、中后序”商兑
《诗品》疑难问题中,序言位置最复杂,歧见也多。现存《诗品》序言共有四种样式:1.吟窗式(《吟窗杂录》本为代表)三序分列三品之首。今传吟窗本是删节本,序言亦经删节,但三序起首文字都与考索本相同。《吟窗》、《考索》都在宋代成书,今传《吟窗》系明本,《考索》为元本。2.考索式(《山堂考索》本为代表)以第一篇序(下文称“一序”)冠于书首,篇幅与《梁书·钟嵘传》所录相同;另外两序分冠中、下品卷首。3.诗话式(《历代诗话》本为代表)本三序合一,位于全书之首。4.诗平式(《钟记室诗平》为代表)以一序冠书首,此同考索本;所不同者,移中、下品序为上、中品后序。
诗话式出于晚近何文焕变制,且无版本依据,研究者多置而不议,本文也不加论列。讨论《诗品》序言位置,应以有宋本渊源的吟窗、考索二式为对象,而如果没有够硬的证据来支持新见,那么判认序言位置原貌,亦当在此二式中取舍。诗平式的“上、中后序”亦属变创,但近世多有同议附议者,而此式此议实有诸多难通之处。为本文观点叙述的方便,先对“上、中后序”的体式和附议略作辨析,以为商兑。
商兑一:“古人叙意,必附篇终”、“古人之序皆在后”属前提误设。
《钟记室诗平》把中、下序改为“上、中后序”,这一版本变创和相关表述得到了赞同,近来论者认定中、下序原为“上、中后序”,便是以张氏“古人叙意,必附篇终”一语为立论依据;此外,论者还以纪昀《文心雕龙·序志》评语(“古人之序皆在后,《史记》、《汉书》、《法言》、《潜夫论》之类,古本尚班班可考”)为据,认为下序“陈思赠弟”至“文采之邓林”为全书之论赞或总跋⑦。
《诗品》上、中品是否有“后序”,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以张锡瑜的话为前提依据则不对,且有以引证代替论证之嫌,这是一。第二,对“古本”应有分析,区别对待⑧。张氏、纪氏所称皆著述之书,《文心雕龙》亦著述之书,而作为选本的《诗品》乃编辑之书。至少从现存总集来看,序言都在书首,与《诗品》同时而稍后的《文选》、《玉台新咏》就是例证;要是往前推,序文在正文之前的体式可以追溯到西汉的《毛诗故训传》,习称的“诗大序”就在诗篇正文之前;此外,王逸《楚辞章句叙》也应属于这个类型,因为这篇文字虽然在《离骚》之后,却位列其他所有篇章之前。第三,若是按“必附篇终”的说法,则不但中、下序的位置不合理,就连论者认可的卷首主序也不应位在卷首。不在卷首,位置何处?既已有了后序,主序即应在“前”,而照“皆在后”的说法,主序又不可能在“前”。这样,《诗品》的主序便无处着落,论者的相关论点也可能因此而陷于窘境。因此,以“必附篇终”、“皆在后”为据,把中、下序移为上、中后序,是忽略了编辑之书的序言前置,不但理由不充分,而且前提就有误。
商兑二:撰例不应被摒于序言之外。
如中品序开头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这段话说的是撰例。但是照逯钦立、车柱环和曹旭的看法,只有“气之动物”至“均之于谈笑耳”一节(即《梁书·钟嵘传》所录)才是《诗品》序⑨,而这一节并不包括撰例所在篇幅,就是说,《诗品》的撰例与序言本来是分开的,撰例所在篇幅不具有序言的文体身份。
本文认为,把《诗品》的撰例与序文分开,这个说法理由不足。一是没有版本根据,二是没有其他理据。没有版本依据无可厚非,因为对文本的质疑往往是对版本的质疑,当然难有版本上的凭依,但也应有其他理据的支持。从文章史来考察,并没有序言拒斥撰例的规定或惯例,而从现存汉晋南朝的总集看,撰例都与序言同体共篇:
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王逸《楚辞章句叙》)
……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石崇《金谷诗序》)
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十四卷。(释僧祐《弘明集序》)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萧统《文选序》)以此观之,撰例都在序言中,而至迟在齐梁时候,陈述撰例已是总集序言的定式通例。《诗品》的撰例陈述也正合此例。说撰例不属序言,既不合《诗品》文本实际,也与总集序言惯例不合。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诗品》撰例及整篇中序原在何处,说详“商兑三”。
商兑三:中、下序与中、下品正文非不相关。
《钟记室诗平》把中、下序移作“上、中后序”,逯钦立、车柱环先生的意见相同⑩;中泽希男(11)、曹旭(12)也说两序与正文内容无关。
以与正文有无关联来定中、下序的位置是非,这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和合理的前提预设,但是,“上、中后序”的体式拟想和没有任何理据支持的版本变创,恰恰又背离了这个思路;不但偏离了前提规定的方向,而且走到了前提的对立面。两序与正文是否有关联,判断依据在文本,即中、下品文本。在《〈诗品序〉考》一文中,清水凯夫先生创造性地指出了两序与正文的对应性关联,为两序位置的原真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明(13)。本文赞同清水先生的观点,并结合对《钟记室诗平》版本变制和新近相关论点的评析,加以申述和补充。
先说中品序。我们知道,中序的重点是对颜延之、任防等人引领的用典诗风的批判:“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而颜、任二人就在中品,二人评语中也都有与序言相同的否定评价:“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颜延之诗》);“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任昉诗》)。对这两位代表作家,《诗品》序言和评语的论题相同且论旨一致,序与评不但有关联,而且有呼应。反观上品,没有一条评语说到哪位作家用典成习、哪个时期用典成风,当然也没有一条评语抨击用典成风成习,就更谈不到中序与上品评语有关联呼应了。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中序与中品无关,应是“上品后序”。至于“钟嵘觉得”“有必要”以“上品后序”解释齐梁无上品(14),此说近乎小说家言。齐梁无人入上品,原因不用再解释,中品评语已讲明:谢脁“出于谢混”,沈约“宪章鲍明远”。根据《诗品》条例,上品诗人须是“出于”《风》、《雅》、《楚辞》或上品前代诗人;“祖袭”上品诗人的不一定列上品(颜延之“出于”上品诗人陆机,仍在中品),“宪章”中品诗人的一定不列上品(15)。谢混、鲍照都列中品,谢朓、沈约自然就不能居上品了。当然,齐梁无上品无需解释,中序不一定就不作解释。到底有没有解释,判断应以文字为据。中序里无一字明说列上品的条件,也无一字明说齐梁人入上品的障碍,如何能说中序解释了齐梁无上品的原因呢?
再说下品序。下序的中心是否定声律说。根据钟嵘的表述,声律说的首倡者是王融,沈约、谢脁只是推波助澜而已:“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而王融就在下品。既然钟嵘把王融认作声律说首倡者,那么,以声律说评论为中心的序文不放在沈、谢所在的中品,而放在王融所在的下品,此正榫卯对接,顺理成章。就是说,下序与下品不是没有关联,是很有关联,而这应该是钟嵘出于文篇布局考虑的安排。下序与下品无关的意见,显然违背钟嵘本意。
新近论者认为下序应是“中品后序”,理由是下序意在攻沈,是沈约被置中品的解释(16)。论者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没有注意到下序不指名质疑沈约观点的同时,更指名引述了王融的声律言论(“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云云),否定了王融的声律鼓吹及所造成的诗坛效应(“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二是没有注意到钟嵘对三位声律说人物的比较估量:沈约并不是最重要的,王融才是首倡者和首席代表,沈、谢只是对波澜升涨有推助之功。再说下序里也没有沈约未列上而居中的解释。
下序与下品无关的意见,乃出于一种定见——沈约为声律论首要人物,而这一定见与钟嵘对王、谢、沈三人的比较衡估并不相符。决定下序位置的,总应该是《诗品》作者对声律论人物的比较衡估,而不是后人对沈约理论地位的定见。序文确认的声律论头号人物王融在下品,这就等于陈示了序文与下品的血肉联系,也就是此文置于下品的天然理由。后人可以说此文摆放“不合理”,却不应否认钟嵘的认识对此文摆放的支配作用,以及下序位置的原真性,正如可以说《诗品》的诗人定品多有“失当”,却不能因定品“失当”而否认《诗品》确然作了“失当”的诗人定品。
总而言之,中、下两序与两品的品论是关联呼应的;同时,这个互补性的关合不是巧合,而是《诗品》作者结构谋划、布局经营的结果,换句话说,两品卷首置序是出自钟嵘手笔的原本体式。而“上、中后序”则消解了原有的关联和互补,切断了传本两品连贯完整的脉络理路,当然,也与论者自己“复原”《诗品》文本体式的初衷相背——“上、中后序”,南辕北辙。
关于中、下品序言位置,我们的看法补述如上。顺带谈一谈下序尾文的篇幅归属。由于《诗品》原是总集,文本体式是序言、诗选、评语三位一体,序言分布是三品三序(参下文《吟窗式新证》、《〈诗品〉三序琐议》),所以“陈思赠弟”至“文采之邓林”一段就不是“全书的赞论”,是序言的赞论。
(二)吟窗式新证
前文研究了中、下序的原貌地位,所以这里只讨论一序是“上品序”还是“全书序”,也就是在吟窗和考索二式中作取舍。本文认为,吟窗式是原貌,这可以从一序内容是否完整和吟窗本“评曰”二字的标志意义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从一序内容不完整看吟窗式是原貌。
一序位置原貌,究竟是吟窗式还是考索式?从梁陈以后总集序言位置的惯例来看,考索式似乎有《梁书》引录的支持,因为《梁书》所录向来被看成《诗品》全书之序,而既是全书之序,自然就位在卷前书首了。但实际上《梁书》的引录既不能证明此文是全书序,也不能印证此序在《诗品》中的位置。如上所述,《文心雕龙》是著述书,《诗品》是编辑书,但《梁书·文学传》引二书序,导语都是“其序曰”:既不能从导语和引录看出二书在结撰方式和文本体式上的分别,也不能由此看出二书序言有前置与后置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即使《梁书》作者看到的是吟窗本,也不妨碍他把上品序当作全书序来引录;“诗大序”位在《关雎》篇名之后,但没有妨碍后人把这篇文字认作《毛诗故训传》全书之序(17)。
《梁书》的引录虽不能印证一序在《诗品》中的篇幅位置,却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篇幅单元,就是说,一序在《诗品》里与另外两序是分开的。正因为此序篇幅完整,便有理由审视其内容是否完整。以《诗品》全书序言视之,其内容并不完整,而特定事项缺位,在汉晋南朝总集的语境中就很难说是全书序。联系汉代以还总集序言的惯例来考察,可以看出,一序没有历来总集序言都有的编例说明。当然,有通例,也可能有例外。但是《诗品》一序不属例外,因为此序没有编例说明,是钟嵘本来就没有把这篇文章当作全书序来写。要是以此文为全书序,或者认为撰例陈述在总集序言是可有可无,他就不会在中序里补作交代了(这也可见陈述撰例是总集序言通例,也是序言作者共识)。不当作全书序,只能是视为上品序了。既然《诗品》作者视之为上品序,那么此文位置就应在上品卷目之下,不是上品卷目之上、全书之首,也就是说,存示一序位置原貌的是吟窗式,不是考索式。
第二,从吟窗本“评曰”的标志意义看吟窗式是原貌。
吟窗本的成书时间早于考索本(吟窗本成书于1194年,考索本成于1196年或之后)。当然,仅仅以此来证明吟窗式是原貌是不够的,因为吟窗祖本不一定早于考索祖本,但据已知材料,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考索本早于吟窗本的结论。关于吟窗、考索,究竟孰为原貌,吟窗本的“评曰”二字能够说明问题。吟窗本每条评语前都有“评曰”二字,考索本无;有无之间,因果存焉。二字非比寻常文字,它是贯穿《诗品》全书的格式化的符号,而且有《诗品》原初文本和原本体式的标志意义。如前所言,《诗品》原是一部有评论的诗选,并非单纯的诗评,而“评曰”是诗选之后、评语之前格式化的导语(参拙文《钟嵘〈诗品〉原貌考索》)。“评曰”既是《诗品》原初面貌的标志,那么很明显,一序位置原貌就不是考索式,而是与“评曰”共生共存的吟窗式。
(三)《诗品》三序的关系
中、下两序与两品正文是关联对应的。这个对接配置的态势,是清水凯夫确认两序位置原貌的依据,也是我们赞同清水观点的理由,但是,对两序两品关系的理解,也应避免刻板僵硬。实际上,所谓“中、下品序”,是放在中、下品的序,因为只是两序的重点内容与两品的重要诗人有关,并非全部议论都是对两品作家而发,就是说,两序的意义不仅在两品,还有关全书。中序里的撰例就是对全书而立:“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一品”就是指全书三品。要是以两序为两品专有,一是不能解释上品序与正文的关系,因为上品序与正文没有中、下两序与正文那样的对应关联;二是不能解释两序其他议论的意涵指向和存在意义。上品序里,有对玄言诗风的针砭,也有对中兴反拨的称美,但针砭和称美的对象都不在上品;下序“陈思赠弟”一段与下品正文也没有对接呼应的关联:这段类似赞论的评论文字,评论对象无一有关下品,显然不是下序的赞论,只能认作三序的赞论。因此,就其篇幅位置而言,三序分别是三品之序;就其意义功用而论,三序又都是全书序的一部分,是分处三卷又互相联系的整体。由此可以说一下何文焕《历代诗话》。《历代诗话》把三序合成一篇,违离了《诗品》原貌,但没有违离《诗品》原意。不过,说没有违离《诗品》原意是就序言自身而言;要是从中、下两序与两品正文的关系来看,无论是“上、中后序”,还是三序合一,都减弱了《诗品》章法的严整,从而削弱了《诗品》批评的锋芒。
三、《诗品》初名:未定之案
《诗品》另有“诗评”之名。二名何者在先?应该讲,还不能有定说。
曹旭梳理了诸家“诗品”名先的观点和理由,认为不能成立,而史籍记载可信,当从史料入手。他根据刘善经《四声指归》、《梁书·钟嵘传》、《南史·丘迟传》、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林宝《元和姓纂》和《隋书·经籍志》,认定“诗评”为早。至于《隋志》还有“或曰‘诗品’”的记载,曹旭说,称“评”者为多数人,称“品”者为少数人(18)。
我们赞同“从史料入手”,同时,本文认为,关于钟书初名,根据现存史料来作判断是困难的。把“诗评”定为初名,理由并不充分。
如果钟书在隋唐只有一名,没有异称,其称名也许就不成问题,但既有异名,二名孰先的问题就来了。认真地说,见于隋唐书志的“诗评”字样,只是现知较早的记载,只能证明曾有这一书名,并不能证明这是最早的书名。最早的记录与最早的书名之间是不能轻易划等号的,尤其是在书有异名的情况下。“从史料入手”并不错,但尊信史籍记载,不应超出其意涵和功效范围,不应超出史料证明力的极限。
至于多数少数之说,同样有待斟酌。多数人的观点未必就是真理。从对证据的认识和使用来看,以证据多少为判断依据,难以服人。在两种观点对立的情况下,对于支撑观点的证据来说,重要的不在数量大小,而在质量高下。这里所谓质量高下,就是能否独立和直接证明钟书初名,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这样证明力的材料;如果有,不用多,一条就够了,比如来自《诗品》自身,出于钟嵘笔下。相反,如不能直接证明《诗品》初名,那么,证据多与少,差别并不大。
在这里,对“或曰‘诗品’”这句话的解读很关键。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说叫“诗品”。《隋志》是在书籍著录时提到“诗品”之名的,所以“或曰”之“诗品”不是泛称,而是专指。第一,《隋书》是官史,从官史记载的严肃性来看,史官在官史簿册里记录无根传闻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既然记录在史,当有坚确依据;就书名记录来说,当有书籍实物依据。第二,相对于后世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之类专门目录而言,《隋志》作为普通目录,没有记录书籍异名的必要和体例要求。如果不是《诗品》确有异本异名,《隋志》应该不会记录“诗品”之名。要说相信史书记载的严肃可靠,也应包括“或曰‘诗品’”这句话在内。面对史志的不同记载,不应忽视记载过程与记载对象的区别。我们知道,《梁书》、《南史》始作于隋,《隋志》始作于唐,但这只说明二史的叙写过程早于《隋志》,不等于其所有的记载事项都早于《隋志》的记载事项;在《诗品》初名问题上,不能因二史草创在先而轻忽《隋志》“或曰‘诗品’”这句话的史料价值,从而认定“诗评”先于“诗品”。不要说还不能确认二史有关《诗品》的篇幅作于隋,即使相关部分作于隋,也只能说明二史的《诗品》记载早于《隋志》,并不能证明“诗评”早于“诗品”。再看《隋志》的两条记载。尽管“《诗评》三卷”与“或曰‘诗品’”在著录形式上有主次之分,但二者对书名的证明力是一样的,证明有“品”、“评”之名,不能证明“品”、“评”之先后。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隋志》中“诗评”和“诗品”是同时记录的。无论《隋志》撰者是否关注“品”、“评”之先后,没有明说总是事实。《隋志》对二名先后既未明说也无暗示,而后人仅凭著录形式的差异就对二名之先后作判断,理由显然不够充足。现存史料显示,钟书书名是隋唐之后由“诗评”主流变为“诗品”主流的,但既然这些史料不能证明“诗评”是初名,也就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隋以前由“诗品”主流变为“诗评”主流。
还有,如逯钦立指出的,吟窗本也称“诗品”(19)。《梁书》所录序文是唐本文字,而据曹旭考校,吟窗本比考索本更近于《梁书》,“《吟窗》本当去唐本不远”(20);可补充的是,是去题“诗品”的唐本不远。《隋志》所记“诗品”之名应该是有图书实物载体的,并不仅是“有的人”如此称呼而已。
综括言之,至迟在唐初,已有两个书名的《诗品》并存。在此情况下,“诗评”、“诗品”,孰先孰后,实难认定,以《四声指归》六书为据来确认初名是不够的。钟书初名,至今还是未定之案。
重申本文观点,如果能够独立和直接证明《诗品》初名,这样品质的材料便不用多,一条就够了,像下面例举的:
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谓之“风俗通义”……(应劭《风俗通义序》)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王充《论衡·自纪》)(21)
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僧祜《弘明集序》)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关矣夫,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文心雕龙·序志》)史料没有明指初名为何,而从文献性质与书名的关系看《诗品》初名,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诗品》是诗选,是作品汇录,而“品”适有“汇聚”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品者,汇聚也。”(22)因此,我们倾向于“诗品”是初名,“诗评”是后起的。当然,这是思路,不敢自必为结论。结论的最好支撑是有明确意涵指向的史料;史料阙如,是不能遽然下结论的。
收稿日期:2012-03-26
注释:
①许印芳:《诗法萃编》卷四,《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58册,第299页上。
②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第23页;李徽教:《诗品汇注》,韩国大邱:岭南大学校出版部,。1975年,第50页;杨祖聿:《诗品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第87页。
③曹旭:《诗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④曹旭:《诗品研究》,第159-160页。
⑤上述《释宝月》条和《区惠恭》条也被用作“本事批评法”的例证,见《诗品研究》第162页。
⑥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74页;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第146页;萧华荣:《文赋诗品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1页。
⑦曹旭:《诗品研究》,第87、89-90页。
⑧纪昀语虽未被直接用作“上、中后序”的前提依据,但鉴于此语的以偏概全和已经产生的误导效应,故在此一并论列。
⑨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逯钦立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5页;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导言》,曹旭选评:《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曹旭:《诗品研究》,第87页。
⑩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逯钦立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465页;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导言》,曹旭选评:《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第159页。
(11)中泽希男著、曹旭译:《〈诗品〉考》,曹旭选评:《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第150-151页。
(12)曹旭:《诗品研究》,第87页。
(13)清水凯夫:《〈诗品序〉考》,《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8、119、135页。
(14)曹旭《诗品研究》,第88页。
(15)在《诗品》中,“出于”、“宪章”和“祖袭”是同一含义,也可以说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16)曹旭:《诗品研究》,第89页。
(17)《文选》卷一《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李善分别注曰:“《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毛诗序》曰:‘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第21页上)注引两段文字在《毛诗》本集里都是《关雎》之序,序文第一句就直指篇名:“《关雎》,后妃之德也”,但李善仍称之为“毛诗序”,而不是“关雎序”——此序,《文选》也在录,也题“毛诗序”,不是“关雎序”。
(18)曹旭:《诗品研究》,第72-78页。
(19)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逯钦立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462页。
(20)曹旭:《诗品研究》,第64页。
(21)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册,第1194页。
(22)参考宗福邦先生等:《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