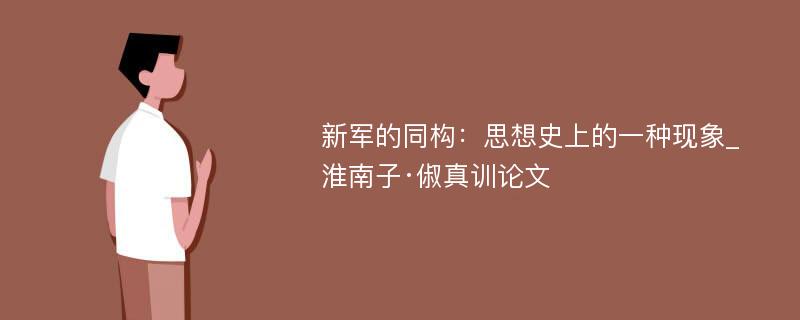
心君同构:作为一种思想史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构论文,思想史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心君同构,是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思想史存在的一种现象。所谓心,在古代思想体系中基本上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认识器官及其“知觉”、“思虑”等认识功能及作用,即所谓“知觉灵明”之心,也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以及荀子所说的“知觉闻见之心”;一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及情感意识,即所谓“义理之心”、“本心”、“良心”,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所说的“恻隐、是非、辞让、羞恶”等“四端”,也称“四心”。二者分别代表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本文所谓“心”或“心灵”,即熔铸其二义而言。所谓君,即传统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君主、君王。所谓“心君同构”,是指通过类比推理,在“心”与“君”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构、互动的联系。研究这种思想史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史上在圣化王权、制造圣人的同时,也对其心目中的思维器官——心灵——进行了加工,赋予心灵在认知世界中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无所不能、无所不到,恰如君主在人间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在先秦文献中,对“心”“君”二者在功能、性质上的同构类比随处可见。《管子·心术》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在职,管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心术者,无为而制窍也,故曰君。”(注:戴望:《管子校正·心术》,《诸子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9页。)发出指令,具有支配力、控制力,是“心君”的主要特征,所谓“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65页。)。这同韩愈在《原道》中所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不仅在思想内涵上接近,在用法上也类似。汉儒也有这种设喻:“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注: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第四十一》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页。)至于明儒,仍有这种思维痕迹,王守仁尝云:“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注:王守仁:《传习录上》卷一,四部丛刊本。)
有学者在研究了传统政治思维中君臣尊卑的多方设喻之后,总结出六种对应关系:1.帝王为天与臣民为地;2.君主为父母与臣民为子女;3.君为元首与臣为股肱;4.君为腹心与臣为九窍;5.帝王为御者与臣民为车马;6.君主为舟与臣民为水(注: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表面上看,虽然“君为腹心臣为九窍”同每组一样,都是以比喻来说明君主的权威,但它与其他五组是有区别的,道理在于这一组涉及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君为腹心臣为九窍”的比喻,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心灵为君主,感官为臣民”的尊卑模式。实际上,这种比喻已经遍布于传统思维的视野中。《帛书五行篇》就将这种尊卑关系描述得更为直观:“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诺,莫敢不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浅,莫敢不浅。”(注: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经二十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60页。)笔者以为,在传统思维中,这种象喻不仅是一种用以说明君主权威的简单比附,还有更深一层的涵义——涉及思维和精神现象,从而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
二
“心”与“君”之间存在性质、功能上的同构一致性,这种认识被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思想界普遍接受之后,就引发了对这种思想现象的深入讨论及细致描述。概括而言,此期思想家主要认为“心”、“君”二者存在着以下同构关系。
(一)心为身之主,君为国之主
对此,董仲舒曾有简练概括:“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注:董仲舒:《春秋繁露·通国身第二十二》卷十一,第182页。)心、君之间的相似性,首先体现于其在各自领域中的显贵至尊地位。所以,心君同构,就是以君主在国家中的显贵地位,来比喻心在身体中的至尊位置;或者反之,以“心”喻“君”。如荀子所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65页。)又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注:戴望:《管子校正·心术》,《诸子集成》第五册,第219页。)又如荀子则直接称之为“天君”:“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天论》,《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06页。)这是以“君”喻“心”。
反过来,也可以“心”喻“君”,如《管子》载:“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注:戴望:《管子校正·君臣》,《诸子集成》第五册,第177页。)董仲舒也说:“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第七十八》卷十七,第460页。)又如,《淮南子》云:“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肢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注:高诱注:《淮南子·缪称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53页。)
(二)心一,君一
既然“心”“君”各为其所在领域的惟一之主,于是,“心一——君一”就成为一个逻辑上的必然性命题。“一”是先秦两汉思想家极其热衷的一个命题,《老子》三十九章就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一”首先是宇宙之根本——“道”的特征,“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万事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注: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360页。)。具体而言,一是“心”的本质特征之一,“凡心之形,过知失生。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惟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注:戴望:《管子校正·内业》,《诸子集成》第五册,第270页。)。这恰如朱子所云:“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注:朱熹:《观心说》,《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四部丛刊本。)这种“贵一”的思想脉络一直延续到明儒心学,王阳明尝云:“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注:王守仁:《传习录上》卷一,四部丛刊本。)
这就很自然地推导出另一个政治性命题——君一,或一君,所谓“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徒。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命,令事自定”(注:王先谦:《韩非子集解·扬权》,《诸子集成》第五册,第30页。)。荀子也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术,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私其所积,惟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惟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离走,而是己不辍也。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58页。)后来,刘向在《说苑》中也说:“鸤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
(三)心知“道”,君通“道”
心、君的显贵与至尊,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有着许多合理性论证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可以直接通“道”。“君”之可以通道,自不必多言,这是先秦尤其是两汉思想家不厌其烦论证的一个命题,例如,“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注:班固:《白虎通义·圣人》卷四,四部丛刊本。),并赋予其以文字学的意义:“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注: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卷十一,第329页。)。而问题在于,“君”或“王”如何去“知”道、“通”道呢?当然是通过“心”的感悟和思维能力,于是,“心知道”就自然成为“君知道”的一个辅助性命题,所谓“人何以知道?曰:心”,“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则必合于不道人,而不合于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与不道人论道人,乱之本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64页。)。
如果说,通过“天人合一”,“君”与“道”有天然相通之处的话,那么,通过“心物合一”,“心”与“道”亦不无相通之处,“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注:王先谦:《荀子集解·正名》,《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81页。)。于是,“心知道”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论命题,而是具备了治理、掌管天下的内涵:“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于知道。”(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65页。)
(四)心无所不思,君无所不能
心、君显贵与至尊的另一个合理性论证,是二者都具有一种神秘功能,即心之“无所不思”,恰如君之“无所不能”;反之亦然。君亦被称为圣人、真人等,其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超乎常人生理限制的奇异功能,“是故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注:高诱注:《淮南子·俶真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26页。)。真人也是如此,“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注:高诱注:《淮南子·精神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03页。)。君者亦然,“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则无以曲直也,莫得其响,则无以清浊也;无以曲直,则其功不可得而败,无以清浊,则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注:高诱注:《淮南子·俶真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00页。)。这种特异功能来自于“助之者众”,《墨子》载:“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注:孙诒让:《墨子闲诂·尚同中》,《诸子集成》第四册,第53~54页。)
而“君”或“圣人”、“真人”的这种功能,恰恰是精神心灵的根本特征,《淮南子·精神训》所谓“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而“所受于天”,又是“天子”即君的基本特征,如《春秋繁露·顺命》载:“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二者的基本特征在于神秘性,如《淮南子·精神训》所云:“居而无容,处而无所,其动无形,其静无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沦于不测,入于无间,以不同形相嬗也,终始若环,莫得其伦。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在某种意义上,“君”与“心”实在难分彼此,又如《俶真训》云:“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而归于万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
(五)心静,君静
虚静,是先秦诸子关注的一个心智性命题。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讲:“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其源实出于先秦。此期思想家一致认为,虚静是一种圣贤之材具备的品质,不可多得。《礼记·乐记》中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淮南子·原道训》也说:“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这种品质实源于天,所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注:戴望:《管子校正·内业》,《诸子集成》第五册,第269~270页。)而源于天的理由在于,宇宙初始处于“静”态:“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若光耀之间于无有”(注:高诱注:《淮南子·俶真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20页。)。另外,也是出于对外物的观察,如《庄子·天道》对“水”的描述:“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又载:“人莫鉴于流沫,而鉴于止水者,以其静也。”(注:高诱注:《淮南子·俶真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29页。)“水静”和“心正”,有着一种微妙的联系:“水静则平,平则清,清则见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为正”(注:高诱注:《淮南子·说林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291页。)。而“心”无疑具有这种特征,试看:“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67页。)而“心静说”的关键在于要体会“道”之渊深,所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之?曰: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蔽》,《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64页。)。
而虚静同时也是人所应具备的品质,“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注:戴望:《管子校正·内业》,《诸子集成》第五册,第271页。)。由人之品质又扩展到君或人主身上,所谓“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其精神源头也在于虚无的“天”或“道”,“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注:王先谦:《韩非子集解·主道》,《诸子集成》第五册,第17~18页。)。《淮南子·精神训》也说:“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静漠者,神明之宅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君道与虚静之间内有一种天然联系,《吕氏春秋·审分览》尝云:“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所以,能虚,能静,是圣人和凡人的根本区别:“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之谓侈。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啬。啬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夫能啬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心之虚静,是为了更好把握真理;而君之虚静,是为了更好治理天下。所谓“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注:王先谦:《韩非子集解·解老》,《诸子集成》第五册,第101~102页。)。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保位权》中也说:“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声出于内,响报于外,形立于上,影应于下……故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之象。”
(六)“心”控制五官、肢体,“君”使役群臣、百官
先秦两汉时期,旧有的相对松散的君主专制崩溃,导致社会转型,最后整合为权力更为集中、控制更为严密的中央集权制。由于宗法制社会的根本性质没变,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是此期思想家的共识,《荀子·仲尼》所谓“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这也反映在对“心君同构”的认识和评价上,概括而言,即心灵之使役五官、肢体,恰如君主之使役群僚、百官;反之亦然。
对“心”而言,就是在感官和心灵的关系上区分出了严格的等级,导致一种“心灵尊贵,感官卑贱”的线性认识模式。这首先有生理及心理的依据,所谓“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注:《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贵生》,《诸子集成》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页。)。而这个“必有所制”,就是“心有所为”的最基本功能,所谓“耳目手足系于心矣。心有所为,耳目视听,手足动作。精念存想,或泄于目,或泄于口,或泄于耳。泄于目,目见其形;泄于耳,耳闻其声;泄于口,口言其事”(注:王充:《论衡·变动篇》,《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47页。)。对此进行系统总结的是《帛书五行篇》:“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诺,莫敢不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浅,莫敢不浅。”(注: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0页。)这首先是由于耳目各有自己的局限,所谓“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昌门之外,望太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太山之上,察白马之色,色不能见,明矣。非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何以验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见百里,则耳亦不能闻也”(注:王充:《论衡·书虚篇》,《诸子集成》第七册,第36页。)。而心灵的思维能力却能突破这种限制,是为“君子之学”:“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注:王先谦:《荀子集解·劝学》,《诸子集成》第二册,第7页。)“君子之学”的要紧之处在于能够“闻道”,据《帛书五行篇》载:
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知而行之,圣(义)也。
[说](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耳目也者,说(悦)声色者也;鼻口者,说(悦)臭味者也;手足者,说(悦)佚愉者也。(心)也者,说(悦)仁义者也。之数体者皆有说(悦)也,而六者为心役,何也?曰:心贵也。有天下之美色自(置)此,不义,则不听弗视也;有天下之美臭味(置此),不义,则弗求弗食也。居而不问尊长者,不义,别弗为主也。何(也)?曰:几(不胜,小)不胜大,贱不胜贵也哉!故曰心之役也。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人体之小者也。心,人体之大者也,故曰君也。(注: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61页。)
而有耳目参与的思维活动则是低级的,“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揌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 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注:高诱注:《淮南子·俶真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29页。)。这里,“圣人之学”、“达人之学”、“俗世之学”的分野就在于:学术级别越高,距离感官耳目就越远。
对“君”而言,君主、君王之使役百官、群臣,恰如“心”之使役五官、肢体,所谓“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注:高诱注:《淮南子·缪称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53页。)。心以一物之微,能控制全身各个部位;君以一人之微,能制约天下,关键在于控制全局的技术,所谓“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所谓“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注:《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诸子集成》第六册,第225页。)。而其关键在于治众若使役一人,“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诸子集成》第二册,第30页。)。对此,还有另一种比喻,所谓“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坒榱,短者以为朱儒枅栌。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注:高诱注:《淮南子·主术训》,《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47页。)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也有这样的表述: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也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及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注:《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卷六,四部丛刊本。)
当然,对此概括得最好的是董仲舒,他运用类比推理,以“心”喻’君”,以身喻臣,对“心君同构”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贱足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顺,若肢体相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气和平,形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体得以全;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心得以安;上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为伤也;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之丧。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卷十七,第460页。)
在此,共找出“心”“君”的15处相同之点进行类比,其重点在于论证君主治理国家的种种道理和技巧,可视为对先秦以来心君同构思想的一种经典性总结。
三
心君同构或心君合一,作为先秦两汉思想史中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探索它的意义在于,可以为先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开辟另一种视角,并对传统政治思维的逻辑方法有所认识。众所周知,在先秦两汉政治哲学中,“天”是论证王权合理性、合法性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天人同构”、“天人合一”或“天王合一”,是先秦政治思想史讨论的热门话题(注: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而笔者认为,“心君合一”,既是先秦两汉政治思维中的重要命题,也是论证王权合理性的另一种重要思想资源,其理论意义,并不亚于“天人合一”。
“心”在传统政治思维中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思维器官,甚至就是思想、意识本身,决定、控制、支配着人的各种行为,这种事实也像“天”一样,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所以,以“心”论“君”,恰如以“天”论“君”,是理解先秦政治思想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从人体外部寻找某种权威性证明的话,那么,“心君同构”则是从人体内部寻找某种合理性的依据。古人祟尚“具象思维”,因此,与难以捉摸的体外之“天”相比,体内之“心”不仅距离更近,而且可触、可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心君同构”或“心君合一”比“天人同构”或“天人合一”更具理论说服力。以“心”论“君”,恰如以“天”论“君”,是先秦两汉政治思维论证王权、君权合理性的又一种思想资源,其价值在于为王权政治提供另一种理论依据。
标签:淮南子·俶真训论文; 淮南子·精神训论文; 淮南子论文; 读书论文; 诸子集成论文; 思想史论文; 董仲舒论文; 荀子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