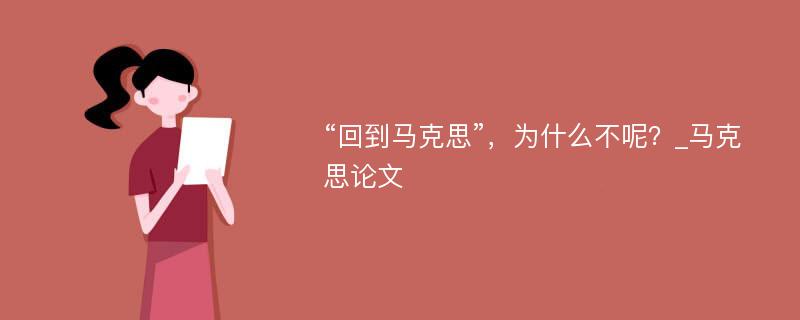
“回到马克思”,有何不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有何不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赞成者有之,批评之声也不绝于 耳。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的声音主要是立足于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认为对文本的解 读、理解,是一个效果历史事件、是一个无限的对话过程,我们总是从一定的前见出发 ,得出的结论总是具有很大的偏向性,我们到哪里去找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呢?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真理或意义就是在这永不可终止的对话中。也许我们不应该说“回到马克思 ”,而应该讲:“走近马克思”、“让马克思走近我们”,或者干脆直接去“建构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吧。
可是,这样一种态度不也是建立在伽达默尔的“前见”之上吗?为什么我们不反思一下 伽达默尔现代诠释学的界限呢?把现代诠释学无批判地运用到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上 ,真的就很恰当吗?
一、现代诠释学要诠释什么“意义”?
按照诠释学的说法,本文阅读的目的在于得到“意义”。那么,什么是“意义”呢?单 从这个概念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对伽达默尔的影响。
在谈到现代诠释学的思想来源时,人们往往注意到它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 的背景,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思想背景却被许多人忽视掉了,那就是新康德主义,尤 其是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西南学派。事实上,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就是对新康德主义 的一个反动。
由洛采首倡、他的学生文德尔班作和、经过李凯尔特的详细阐明,价值哲学成了西南 学派的镇山法宝。他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发现 普遍规律,而历史科学则是描述有意义的历史个体,因为历史是没有规律可言的。但是 作为科学,就必须是为了发现普遍性的东西,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他们认为,历史科 学也是要发现普遍性的东西,即每个历史个体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来之于历史个体本 身,也不是来之于研究者的主观评价,而是与普遍的价值相关联。所谓的历史科学,就 是研究者以一定的价值为目的,根据意义的不同评估所组织的目的论的体系。尽管他们 口口声声宣称价值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但是,价值的选择、意义的标定毕竟 是研究者自己的事,这样的“历史科学”又能有多大的客观性呢?
公正地讲,西南学派认识到了社会科学的真理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不是来之于对所予 事实的抽象,而是另有来源。但他们说不清这个来源是什么,就把它归于神秘的价值, 从而陷入到主观主义的泥潭。在新康德主义者这里,“意义”实际上是研究者主观赋予 的一种模糊的价值判断。但是,新康德主义所提倡的历史研究的对象以及对历史的看法 却从根本上规定了以后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包括伽达默尔本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目的是要批判德国的“唯心主义及其浪漫主义传统”,在《 真理与方法》中,他着力批判了西南学派在历史领域的表现——历史学派。他认为社会 历史科学的真理——意义——来自于历史实在。他说:“生活的经验和对柏拉图的研究 ,引导我很早就达到了这样的见解:一个单独命题的真理性,不能由它的正确性和一致 性的仅是事实上的关系来衡量:也不仅仅依赖于它位于其中的语境,而是最终决定于它 所确立的根基的真实性,并与它由之获得其潜在真理性的说话者本人连接在一起,因为 一个陈述的意义并不穷尽于被表述的东西。只有当人们追溯促使它产生的动因的历史, 并朝前展望它所隐含的意义时,它才会被揭示清楚。”(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 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9页。)关于这个意义“所确立的根基 ”,他说:“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 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 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注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369,336,3 87,701页。)也就是说,这种意义既是客观的,又有相对性。需要指出的是,受胡塞尔 的影响,“本文”的“意义”在伽达默尔这里意味着“本文”的概念、主题,而且,“ 意义”本质上意味着一个“理想统一体”。这个“理想的意义统一体”,是指文本在不 同时代的意义围绕同一文本形成的统一。
可见,那种认为文本的意义仅仅取决于阅读者的主观理解、仅仅存在于解释的循环中 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反对尧斯和德里达对于文本意义的相对主 义理解,认为我们只是“分有”文本蕴含的真理。以古典性为例,他认为:“古典性乃 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对某种不能被丧失并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的意识 ,……即一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这种当下存在对于每一个当代都意味着同时性。” (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369,336 ,387,701页。)
尽管伽达默尔力图而且事实上也基本摆脱了“意义”的主观色彩,但是,他对于历史 研究目的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新康德主义的视野之内。他认为历史的研究、本文的理解, 一句话,精神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发现某个现实个体的、具有很强价值色彩的“意义”。 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他对于本文意义、概念的掌握,他始终不能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在 一个具体的社会整体中确定一个本文、历史流传物的意义、概念,而是把一个孤立的本 文放在无限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它的“意义”,这就使“意义”缺乏确定性。这就是他 虽然一再强调本文的“真正意义”是真理,但他一直说不清这个真理的保证是什么的原 因。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一个历史个体的“意义”、概念、真理,取决于这个个 体在当时社会实践整体的位置,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历史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 对历史个体进行“评估”、确定其“意义”、概念,而是为了发现历史的规律。我们同 历史的统一也不在于“意义联系”,而在于社会生活的关联。当然,这些与本文的研究 不是太相关,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哲学诠释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对历史的理解方面 ,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异。
二、“意义”是诠释出来的吗?
既然文本的真正意义是指在文本直接表达的背后所蕴含的真理,即文本的主题、概念 。那么,我们如何获得“意义”呢?按现代诠释学的说法,要靠诠释。
为什么这个真理要靠“诠释”才能得到呢?这取决于伽达默尔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从根 子上说,这是来自于新康德主义的观点,即历史是无规律的。具体而言,这个态度直接 来源于狄尔泰。在狄尔泰看来,在历史科学中,历史事件的联系是意义关系。这种意义 关系来源于生命的创造活动。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意义整体。在狄尔泰这里,“生 命”不仅仅是指自然意义上的生命,而且主要是指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心理活动。因此 ,要获得历史的认识,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必须要用理解的方式去体验精神生活 的意义联系。这里理解的主体是经验性的个人。(注:以上参见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 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7页。)理解则是指理解主体通过外在感 官所给予的符号而去认识内在思想、或者一种心理状态的过程。
伽达默尔不赞成狄尔泰把理解仅仅作为精神科学的方法。他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把 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不是要不要理解的问题,而是你一直都是在理解 。但是理解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理解对象的不明确性。由于狄尔泰把社会历史领域的 客观关系看成“客观精神”,看成是不可捉摸的“生命活动”的产物,因此,他认为只 有靠理解的方法、通过体验才能认识其中的真理。后来的海德格尔之所以要在他的《存 在与时间》中引进诠释学也就在于此,因为存在是不可以直接认识到,它只能在此在与 世界的打交道的过程中被体验到。伽达默尔也一样,他认为:“不管是认识者还是被认 识之物,都不是‘在本体论上的’‘现成事物’,而是‘历史性的’,即它们都具有历 史性的存在方式。”接下去,他在谈到诠释学处境(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时具体解释说 :“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 这种处境,乃是一项绝不可彻底完成的任务。……所谓历史地存在,就是说,永远不能 自我认识。”(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 80,369,336,387,701页。)
由于伽达默尔抱有一种历史怀疑论的态度,认为历史就意味着“混乱和无秩序”,(注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369,336,3 87,701页。)因此,没有办法从整体的角度来确定部分的“意义”。于是,他又从胡塞 尔那里得到一个观点,认为意义是一个理想的统一体,不是主观的东西,也不是事物本 身具有的,是超越于主、客观的第三者,是独立存在的。那么,我们如何去发现这个作 为第三者的“意义”呢?伽达默尔既不愿意采用狄尔泰等人的心理体验方式,因为这在 他看来是主观主义的;他也不想完全采用胡塞尔的结论,即通过本质还原确定地把握“ 意义”。这在伽达默尔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解的主体是有限的、历史性存在的此 在,不可能达到胡塞尔的无前提状态。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虽然好,但不能明确理解 主体的普遍性。黑格尔的结论倒是客观,但又太绝对。科林武德的对话逻辑是不错的, 可是结果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重演说。于是,伽达默尔把这些人揉合在一起,他运用海 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作为前提,赋予它“前见”——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以胡 塞尔现象学的结论——主客体自在地关联——为理论依据,通过科林伍德的对话逻辑, 达到黑格尔的辩证结论,这个结论又被认为体现了狄尔泰的意义联系。好一个完美的组 合!他就是要用这个组合,让一个不确定的此在,从一个不确定的视域为起点,在一个 不确定的文本意义整体中捞出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来,捞出的东西就是“效果历史”。他 实际上最终仍然把这个结论停放在不确定的国度中。
这也就是他把对社会历史真理的认识求助于对话、求助于理解,最后达到一种效果历 史的基本思路。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伽达默尔一样,那么,我们不妨采取他的诠释 学的态度,这毕竟还指向了一个确定性的东西,这已经是在这种历史认识的基础上达到 的最好的结果了。可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能这样做吗?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一个文本的真理就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存在。“意 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页。)在一定的历史 阶段,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产生一定的意 识形式,而这些都是可以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线索,通过经验的考察确定下来的。因此 ,文本的真理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这是对的。在不同的时代,之所以发生这种意义转变 ,就在于文本开始时所反映的社会因素虽依然存在,但它在一个新的整体中的位置已经 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所谓“效果历史”的秘密,也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钥匙”的秘 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文本所反映的这个社会因素一直存在,随着社会结构 的变化,文本的意义就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伽达默尔的“恶无限”的含义。但他只看到 了这种开放性,却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在一定的社会阶段,文本的意义恰恰是可以确定 的。所以,他只好求助于“时间间距”,以一种消极等待的态度来对待文本的真理。其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
可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文本的真理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解的问题,而恰恰主 要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它取决于我们对文本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整体认识,也取决于我 们对那个使文本在今天仍然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因素的真正把握,这只有在对我们时代 的整体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哲学诠释学根本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也根本没有达到辩证的总 体性思维的高度,用诠释学的理论来对待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不觉得是用错了地方了吗 ?
三、我们不需要回到马克思吗?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种种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来分析、认识和解决。可叹的是,当我们转过身来,向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库中寻求帮助 时,我们却意外地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马克思已经被涂抹的面目模糊了。 于是,有没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竟然也成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理论界也对传统教科书进行了反思 。许多人把过去时代的种种思想领域的错误归于传统教科书的影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 值得商榷的,因为,思想领域的发生实践效力的种种错误行为本身,是不能简单地归咎 于某种教材、某种思想的,它自有其时代的根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看法。 但作为一种理论反思,它还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不幸的是,反思的结果却是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马克思”纷纷出现,谁要再讲有统一的马克思,就会被斥为“话语霸权” 。真是道术已为天下裂!当每一种对马克思的解读都自称是发现了“马克思的真精神” 、甚至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时,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们难道不应 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结论中有多少是来自于我们对于马克思文本的认真研究,又有多 少是来自于外来的观点、而我们仅仅是给它妆扮上马克思的语句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回 到马克思,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吗?
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要回到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是给燕妮写下火一样热情 的情书的马克思吗?是在莱茵报时期以自由主义者出现的马克思吗?是作为费尔巴哈的人 本主义的信奉者的马克思吗?恐怕都不是。尽管我们对这些时期的马克思仍是充满赞叹 之情,我们虽然爱之、颂之,但决不是我们要回到的马克思。我们要回到的马克思,是 作为那个说出时代真理的马克思,严格地讲,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
是的,回到马克思,决不是目的本身,回到马克思,也决不意味着仅仅回到马克思的 文本。回到马克思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但是,理论的 发展从来不是无根基的,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回到马克思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工 作。从本质上讲,我们今天的时代还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时代,因此 ,要深刻地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就必须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才有可能,这决不是匆匆忙 忙“联系实际”就能办到的,这就是理论的价值所在。我们上哪里去寻找这样一种理论 的制高点呢?回到马克思,不是一种最可行的选择吗?
发展从来就是自我发展,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的坚实地基上,面向我们时代的问题, 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撇开马克思所表述的时代的真理,以其他的什 么理论作为“原木”,嫁接出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论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它 总是可疑的,而且是极其可疑的!
试问:回到马克思,又有何不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