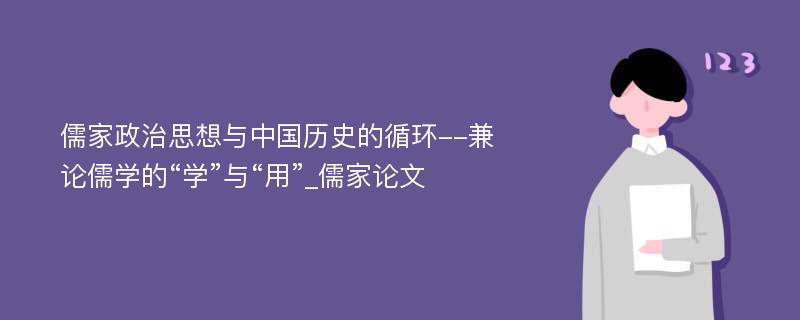
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循环——兼论儒术的“学”与“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儒术论文,中国历史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4-068-07
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与文化检讨和历史批判是不矛盾的。任何企图置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于批判、检讨之外的做法都是有害的,都是对民族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最大破坏。从来没有任何文化和任何阶段的历史能享受批判、检讨的“豁免权”。实际上,我们的历史充满了遗憾和遗恨,而传统文化更是有着很大的缺憾和局限。本文认为,中国历史的最大遗憾与中国文化的最大缺憾和局限就是没能走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一状况导致中国文化长期陷入一种历史因循而没能产生更大的实质性突破,从而造成近现代长期落后挨打的局面。对这一局面,儒家思想和儒家色彩的政治应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一、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与儒家历史循环论及复古理论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古代社会的中国人没能超越专制主义,没能摆脱集权专制,历史陷入因循、停滞,“儒学”不但无助于消除这些,反而对此有所助长。但就历史观而言,儒家思想是主张复古倒退和历史循环重复的。这就为中国历史的因循重复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同时为历史的变革突破设置了理论或观念上的障碍。
中国历史和文化裹足不前的时间似乎太长。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古代的封建社会》)说过: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当然,毛泽东所说的“延缓了三千年左右”主要指社会制度没能突破封建制(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哪一种都与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出现停滞不前的说法没有矛盾。所以,对此本文不予讨论。),或者说文化模式三千年没有实质性变化或突破,而不是说整个文化发展的停滞始于周、秦。但是,无论如何,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文化与社会制度处于一种超稳定的惰性状态则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种超稳定性,中国文化才没能突破其固有的模式而迈上一个新台阶。应该承认,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长时间的大的停滞,物质财富的建设和积累与破坏几乎对等,最后落得个“一穷二白”的结果,而精神文明也绝非进步的或增长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更是每况愈下。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及演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封建社会”的起始问题。如果说对“封建制”或“封建”的内涵或起始存有争议的话,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的超稳定状态或陷入因循、停滞状态的起始时间定得晚一些。不过,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从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辛亥革命被认为同属于一个大的社会模式或社会发展形态已是定论。尤其是就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而言,发展了两千多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是中央集权的高度皇权专制应该是没有错的。在这一慢长的历史阶段,只有王朝的更迭,而在文化模式与文明程度上没有实质发展或突破,整个价值体系也是如此。王朝的覆灭、政权的更迭往往意味着杀戮和浩劫,意味着文化积累的毁坏。正如范文澜所言:“中国历史的大部分,都是由‘残酷的剥削’、‘疯狂的屠杀’、‘军阀混战’、‘外族入侵’等悲惨事迹所构成的。”[1]中国历史和文化没有因政权的更迭而进步,反而是生灵涂炭、人道沦落、人性迷失、民族精神枯萎、物质创造不断遭到毁灭。悲剧和遗憾一直充满了我们的历史,而其原因又何其相似乃尔!可以说,政权的兴亡、更迭绝非偶然,其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其政治效果和最后结局也是一样的。正如元人张养浩(《山坡羊·怀古》)所感慨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长期的恶性循环,中国文化与民族性出现了严重的“退化”。
古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如同古代的历史、文化一样也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陷入一种僵化而缺少变革和突破。主宰古代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复古主义”、“英雄史观”和“历史循环论”。孟子(《孟子·公孙丑下》)在两千多年前所总结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还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由此观之,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以历史循环为必然,把社会发展看作在沙滩上建了再毁、毁了再建的“造房游戏”。古人的观念基本没有突破这一思路。
复古倒退是中国古代文人和儒家思想的固有观点,自孔孟起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关于政治,孔孟言必提三代,主张一切都要向三代看齐,所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零公》)他们主张社会倒退到尧舜的时代,将当时小国寡民的简单政治理想化并做出歧解。对此,后世儒者鲜有持异议者。一千多年后两宋的道学家将这种观点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二程、朱熹极力推崇三代之政治,对后世汉、唐时代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予以否定,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政治是“人欲治天下”而不若三代之“以仁政治天下”。[2]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社会变革几乎是不能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便可归结到这类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影响上。在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有“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3]等句。可见王安石是何等孤立。范纯仁向神宗进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刨克财利,民心不宁。”[4]王安石似乎成了儒学的叛逆、误国的大奸。知道银台司范镇攻击青苗法是“盗跖之法也”[5]。面对阻力,王安石曾痛苦又无奈地感叹:“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6]儒家的政治观及历史观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很难值得肯定的。
可以说,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目的与规律是什么始终缺乏一个明确而正确的解答,而只是模糊地把原始社会末期的简单纯朴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末倒置地把“治心”列为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第一出发点。历史的进步与进化、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没能成为传统中国价值观的中心议题,甚至基本不予讨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义利之辨”便可说明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大部仍停留在道德理想主义的虚幻上。
中国人的历史观、文化观是当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受挫、文化优越感消失之后才有所变化的。文化的危机和“西风东渐”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检讨并拿它与西方历史与文化以及西方的历史观、价值观作比较。关于中西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差异,近代著名的启蒙者严复曾有过精辟论断: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7]
历史陷入恶性循环是中国文化的遗憾和历史的悲剧。中国历史为什么没能摆脱这一厄运而“日进无疆”、常胜不衰?我们能认为这是必然的或合理的而不愿反思检讨?
二、政治制度的超稳定结构与“温和的专制主义”
传统文化的最大遗憾就是没能走出专制主义。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制度是非常典型的,并与儒术是密不可分的。儒术就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它可以称得上是“温和的专制主义”。对内统治它似乎是成功的,但这只对统治者有意义和价值。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价值体系,它没能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真正的理性机制,没能提供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以保护这种文化和种族不被征服。它是中国古代文化没能走出因循、停滞和专制统治的价值根源或观念根源。甚至,它不但是中国的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且就是专制制度本身。
范文澜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几乎牢不可破的封建专制制度。”[1]应该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超稳定的,专制程度是世界第一等的,而且办法极多。自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政权到清朝灭亡,这一极度专制的政体或政治模式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反倒是专制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这种政治模式存在时间之久远及人们对它的认可、认同堪称历史奇迹。
这一专制的模式的定型与秦朝密不可分。范文澜说过:“秦是一个短促的但有极大重要意义的朝代。秦始皇为统一事业作出了许多重大措施,建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8]虽然秦以后的各王朝的统治集团都谴责秦的暴政,但他们只是反对或不欣赏秦的具体做法,而对于这一制度本身,他们不光没有什么意见,反而视若命根子。自秦之后各王朝的政治制度与秦朝的政治体制是一脉相承、性质一样的。正如谭嗣同所言:“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9]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只是对这一制度修修补补,增加这一制度的安全系数或可靠性,而没有、也不准备对这一制度实行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儒学或儒术对这一专制制度的安全系数的增加起了相当大的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于法家思想,儒术不主张赤裸裸的强权,但它仍是专制主义的,区别只是多了些麻痹人的温和。可以说,正是儒术赋予了这一政治模式以“合理性”,使其能够如此久远地深入人心。儒术就是古代中国一切社会制度的灵魂,是它延缓了这种制度的寿命。
所谓“纯粹的儒家思想”或所谓的“原儒”、“醇儒”或许没有与官方意志、皇权专制完全合拍并彻底融为一体,所谓“纯粹的儒学理论”与官方哲学或许仍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所谓儒术绝对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和统治的“王牌”则是事实。今天,如果我们笼统地把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道德伦理体系,乃至整个社会模式和传统的价值体系统统归到儒术的名下也没有什么不可。毕竟。儒术就是或已变成纯粹官方的东西,而传统的政治模式也无不披有儒术的外衣。
实际上,把所谓“原儒”、“醇儒”与和专制统治融为一体的“儒学”体系区别开来意义并不大。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学、历史学意义上整体的儒家学说或儒家的价值体系已与孔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差别并不意味着孔子乃先秦“儒家”思想与后世“儒家”思想有根本区别。秦汉之后的“儒学”,乃至两宋之后的“儒学”,并没有发展到所谓“原儒”的反面。它们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尽管所谓“原始儒家”的某些重要、健康的精神被后世“儒家”抛弃了,但其基本精神却没有被抛弃。客观地讲,儒术在秦之后的发展应该说是先秦儒术的继续。汉儒也好,宋儒也好,都没有抛弃孔孟思想中最基本的成份。
儒术或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而不是一种和皇权专制相对抗或不合作的思想体系。李大钊说过:
自秦代封建专制后,汉承秦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之渊源,斫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秦政也。学以造乡愿,政以宿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且不堪也。[10]
实际上,尽管包括孔子本人在内的所谓“原始儒家”的思想有反暴政的一面,讲一些理性的、人道的原则,但他们根本不反对君主独裁和集权专制。孔子本人主张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当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说儒术不主张暴政。这样是说先秦“儒家”,同时也是说整个儒学的理论体系。一般说来,政治理论都是反暴政的,哪怕它本身就只能导致暴政。专制主义或专制统治的本性是残暴的,但它并不等于暴政。不是说只有暴政才是专制主义或专制统治,但是专制主义或专制统治必然导致暴政和乱政。从理论上来讲,任何政治都有一个所谓的“理性”出发点,有一个政治理念。暴政的结果任何人都清楚,统治集团也不希望出现。通常,任何政治思想都不会把暴政奉为理性和追求的目标。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也不例外。像儒术这种反暴政、比较温和的统治术还会为这种专制主义提供一种理论上的“高尚”的动机和“神圣”的外衣。暴政也是专制主义和专制统治千方百计设法避免的。因为暴政有可能造成自身的灭亡。秦王朝就是明证。儒术之所以被统治者看重,被奉为官方哲学,其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延长专制主义和专制统治的寿命。儒术也的确为专制主义和专制统治增加了理性,为其存在提供了些让人“信服”的理由。这种理论论证及理论输入很有效,为这种制度及专制主义“深入人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术说到底是一种“温和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更有效,更可怕。鲁迅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们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12]他认为,孔子思想与尊孔“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为民众本身,却一点也没有”[12]。在他看来,孔子思想和儒术是杀人的“软刀子”。[13]
固然,儒术,尤其是先秦孔孟思想,是有着人道主义的一面的。这正是它深入人心或获得认同的主要原因。但是,儒术虽然强调“仁爱”,但更强调等级制度与集权专制。孔子的“礼”里面就渗透了这种精神,更不用提汉儒及宋儒了。儒术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所谓“好的”作用只是增加了层温和或伪善的外衣,并没有改变这种政治模式或社会制度的专制、反动的根本性质。儒家的“温和的专制主义”政治尽管延长了统治政权的寿命,增加了统治的安全系数,但是,受益者仅仅是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与民族和文化的发展绝无好处。这就是儒术所谓“成功”的一面或“成功”之处。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一“成功”比不成功更糟。文化的惰性和民族精神的萎靡盖源于此。中国历史没有走出因循、中国文化没能产生突破的主要原因恐怕皆赖儒术所赐。“儒术治国”的理想或空想更是使中国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难以产生突破与变革。
三、理想与现实——儒学的自我矛盾
儒家思想是最好的思想、儒家政治模式是最好的政治模式曾是中国人坚信不移的理念或信条,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儒术治国”信仰的基础。不过,所谓“儒术治国”并没能落实多少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的理想,而真正的政治实践和“儒术”所许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发展目标又相差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术治国”仍是一个空想、一个神话。儒家政治理想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在现实中缺少对应,没有落实。也就是说,在社会制度上,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上,实行的并非儒术理想的那一套,而是另有一套。那是传统政治的纲,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但那些也叫儒术,而且是起着实际作用的儒术。这种儒术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或者说就是官方统治术。
所谓“儒术”也可分为理想主义和实际运用两部分,从另一角度,也可分为“学”与“用”两部分。即便是所谓“纯理论”,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也有空想和实用理论两部分。而儒家思想空想的部分往往被当作儒术的全部。严格说来,一般意义上的儒术基本上属于一种理想或空想,它落到实处的几乎没有,而真正处于实践操作层面的又不是儒家理想主义的高尚部分,而是一种统治术或权术。总的说来,儒术有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理想主义部分与实用主义部分相互矛盾的现象。前者是比较高尚的、动听的,而后者究其本质却是反动的或反人性的。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儒术却是后者,前者只是一种外衣,起迷惑人的作用。因而,要说儒家思想没有人道主义精神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它更充满了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人道主义精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而反人道主义的部分却在实践着。反人道主义窒息、压倒了人道主义。所以,儒学从根本上起一种消极作用,是为集权专制和等级制度服务的。
任何政治理论或道德理想都有空想和理想主义的一面。理想主义总有美妙和人道主义的一面。这正是任何空想或理想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其实,理想主义的特征就是“最好”,具有无限“可能性”,因为它只是许诺,是“空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但是,光有理想主义和空想的一面是不够的,还要看其可操作性及实践结果。对于儒术也是如此。儒术的理想主义部分很高尚、很动听,但这并不是现实中的儒术或儒术的实践结果。它只停留在典籍里和理论层面。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仍坚持这才是真正的儒术,而实践中的儒术不是儒术或是对儒术的背叛。这是儒术没有过时甚至永远不会过时的理论原因或出发点。比如熊十力先生就反对把中国文化的糟粕、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与反动归结到儒术身上。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是儒家故物也。”[14]郭沫若也反对批孔反儒。在他眼中,古代被神话的孔子和在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责骂、批判的孔子都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而是“一个歪斜了的影像”,他要做的是“他是怎样我还他怎样”[15]。在他看来,孔子思想和马克思也是一致的。在他的历史小说《马克斯进文庙》里,他让马克思向孔子进行一番问难之后,最后自己亲口承认孔子思想与他“不谋而合”,“是完全一致的”,并大发感慨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在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个老同志!”[16]总之,在许多人看来,孔子与儒家思想是清白的,与中国历史的悲剧、失败、停滞、倒退和文化的缺陷、糟粕无关,并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中国历史与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中一切成就和积极的方面都要归功于儒术或都是儒术的作用。
许多人仅仅为儒术的理想、空想或理论所吸引或迷惑,而对其实用理论及其实践视而不见,对所谓“儒术治国”的现状及结果视而不见,只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从理论到理论论证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及完美无缺,完全抛开历史现实。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有人和古人一样,也认为这种历史的因循和文化的裹足不前就是人类文化和政治的唯一模式。而有些现代人,竟把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切对传统政治、传统文化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进行终结的行为视为洪水猛兽。所谓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断了中国文化的根的说法不是一直很有市场吗?
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许多人没有跳出传统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圈子,习惯于纵向的自我比较;而有的历史研究缺乏整体意识,不能上升到整个政治、文化模式的高度,更不愿把当时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和全球文化的范围内进行比较。这样就永远陷在中国王朝更迭、历史循环的怪圈里跳不出来,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结果方面也没有形成突破和超越。只了解故纸堆里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研究者只是生活在当代的“古人”——站在古人的立场上评价古代的事。如此,这种历史研究与评判便跳不出传统的或“古典的”窠臼,永远停留在古人的水平线上。
中国文化的自我中心论和文化优越感是很强的。这也是有道理的,在古人的世界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无与伦比,即便与他们未知的文明相比也是相当领先的。如果近代没有西方文明的挑战,有什么人会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产生怀疑呢?我们的民族一直认为我们的文化是最好的,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政治制度、道德伦理都是这样。长期以来,我们周边文明的落后也的确给了我们这一文化滋生傲气的条件和理由。殊不知,我们的文化模式是有着很大的弊端和缺陷的,而且,问题早就暴露出来了。但我们却习以为常、浑然不觉,对文化模式的突破和政治经济的变革漠不关心,把与周边民族和外来文明的较量失败归结为偶尔的失误,最终这一文化终于落后、落伍了。所以,对于今人来说,我们对传统文化和古代历史的研究要有一种“时代感”和“世界感”。所谓“时代感”不是历史上搠,不是复古,而是向现代靠拢;所谓“世界感”就是把古人的历史、世界放在我们的世界中去衡量,放在全球范围内去比较。古人的世界是相当狭小的。他们可以对他们自己的观念和作为很满意。但是,今人进入古代就会超越古人的眼界,使古人的世界放大。这样,他们的局限就显露出来了。
在当代,儒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已经过时,任何以它充当当代价值观的主体的企图都是不合时宜的。儒学体系中某些令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极具价值的成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四、结语
对中国如此漫长的专制历史和历史循环,儒术应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同时,它也应对中国文化的衰败和民族精神的萎缩负责。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也是决定文化水平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对传统文化要抛弃什么的话,该抛度的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儒家政治思想之上的政治制度乃至整个儒术本身。专制制度是传统文化的形式或骨架;儒家的价值体系则是其灵魂。所谓“大酱缸”、“大染缸”大约可以理解为二者的相加。对于历史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共识。如果古人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与信奉的价值体系的局限,或对此无可奈何,那么我们现代人就应该为古人查找原因,算清这笔历史旧帐。否则我们这个社会观念的进步就可能受阻。
[收稿日期]1999-05-00
标签:儒家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儒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