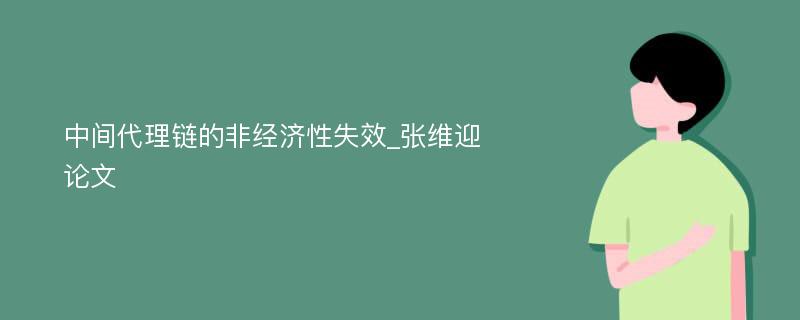
论中间代理链条的非经济性失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链条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 —5656(2000)03—0016—04
资本由非所有者经营,并非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独有特点,资本主义社会亦然,而且资格更老。因此,资本由非所有者经营,并非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其资本的委托代理关系“半身不遂”,然而这“不遂”的“半身”又不是在代理经营者一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代理经营者与资本主义企业的代理经营者并无区别,只要前有可观的利益,后有严格的监督,他们都同样有把受托资本“炼石成金”的能力。因此,问题就出在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一方,更具体些说就是,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理缺乏对经营者实施监督的激励,从而国有资本的经营者难以受到有力的所有者监督,进而导致了后者的经营激励不足。打个比喻就是,私人资本委托代理关系和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终端设备”代理人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什么性质不同和质量差异,而后者不能有效工作的原因只在于其上游供电设施的电压(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的监督力)不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代表的监督激励不足,以及如何克服这一弊端呢?
关于国有资本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张维迎博士曾做过一个较精彩的描绘(注:张维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1995,(4);或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他用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来定义企业的所有权,并把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描述为这样一种结构:“公有经济中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两大等级体系。第一等级体系是通过从剩余索取人(委托人)到中央委员会的授权链(delegation chain of power)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代理人方向是向上的(由下至上)。第二等级体系是通过从中央委员会到企业内部成员的授权链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代理人方向是向下的(由上至下)。”在这两个等级体系中,“除了两类特殊的局中人(剩余索取人和企业内部成员),每个局中人均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委托人的代理人,又是代理人的委托人。为方便起见,我们称剩余索取人为初始委托人(original principals),称企业的内部成员为最终代理人(ultimate agents)。‘上游代理人’(up—stream agent)和‘下游代理人.’(down—stream agent)则分别用来指有关代理人之前和之后的代理人”。其中,初始委托人的数量代表共同体的规模,最终代理人的数量(同时代表企业的数量)代表经济的规模。
张维迎博士首先假定,在此经济体系中,所有剩余均由代理人逐级传递给作为剩余索取人的初始委托人,归初始委托人所有。并且假定,“只有初始委托人有监督代理人的自我积极性,所有代理人(直至最终代理人)为初始委托人服务的积极性只能来源于监督。”在此假定基础上,他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1 )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受监督下的工作努力都随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而递减;(2 )最终代理人受监督下的工作努力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
得出第一个结论的理由是,在第一等级体系中,“当共同体扩大时,每个委托人分享到的份额减少,同时等级体系膨胀的结果使监督成本提高,因此最优监督积极性下降,代理人受监督下的工作积极性也下降。”得出第二个结论的理由是,在第二等级体系中,每个下游代理人的积极性一般总是小于其上游代理人的积极性,因此,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委托代理环节的增加,最终代理人的工作积极性必然不断下降。
将上述两个结论再高度概括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庞大共同体的公有经济是不可能有效运行的。”
同时,张维迎博士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出一个改革药方,那就是:将国有经济分割为一些较小的共同体,借以减少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环节,进而提高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工作激励。张维迎博士说道:“虽然分割并未增加每个委托人享有的剩余的实际份额,但是它通过使等级体系变得更为平坦(也就是缩短从委托人到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而提高了监督的总效率。”
将张维迎博士的上述论点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国有制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是因为国有资本所有者或上游代理人对经营者的监督无效,而监督无效的原因是上游代理人的监督激励不足,而上游代理人监督激励不足则又是导源于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多环节性。
的确,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全民不能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即国有资本的最终代理人直接进行交易,而是必须首先把他的资本委托给一个专业化的中间代理人,然后再由该中间代理人与最终代理人进行交易。在通常情况下,这个中间代理人就是政府(或称“国家”)。之所以如此,按照张维迎博士的解释,这或许是出于节约组织成本的需要。尽管如此,但是由于国有资本所有者人数和国有资本总量的庞大,这种中间代理职能也绝非是通过一个中间代理层次即可实现。就大部分国有资本来说,这种中间代理链条的环节都会达到多个。按照组织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原理,委托代理的环节越多,源自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和激励的作用就会衰减得越大。包括张维迎博士在内的许多学者们认为,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经营效率的巨大差距。
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十分值得怀疑的。监督和激励的作用有随组织层次的增多而衰减的现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说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经营效率的巨大差别完全或主要是由于这一原因所造成的,则极不符合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因为,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通用汽车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等这类“大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公司的效率,就应当是世界上最低的;而朝鲜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应当在我们之上。因此我以为,即使多层委托代理对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率确有影响,这一影响恐怕也是微不足道的,根本不足以造成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在效率方面的如此大的差别。因此,造成国有经济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那么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呢?
笔者认为,造成国有经济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多环节性,而是国有资本“中间代理链条”的非经济性失效。
我们知道,全民与中央代理人之间以及中央代理人与其下属的各级代理人(我们暂时把最终代理人除外)之间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事实上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合约关系,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权责制约关系。或者说,即使我们可以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全民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是一种经济性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但这种关系所借以构成的中间链条却是一种政治性的权责制约关系。(注:张维迎博士把选民与“人大代表”之间的政治性委托代理关系视为是一种经济性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观点,是大可商榷的。因为,全民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不能在所有权意义上被分解的东西,因此,全民资本并不是每一个公民的个人资产的集结,从而也并不存在一个以每个个体公民为初始资产所有者和初始资产委托人的委托代理过程。全民资本的初始状态就是国有资本。如果说全民资本确有一个初始委托人的话,那么这个初始委托人也只能是作为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的全民,而不能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公民。因此,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全民资本的经济意义上的初始委托代理环节的话,那么它至多也只能是作为整体的全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中间性的资本委托代理环节。虽然在全民与政府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金字塔式的逐级授权过程,但这种授权过程也只是一种政治性的个人意志的集中过程,而并不是一种经济性的财产权的集中过程。因为作为个体的每个公民并没有什么已经分解到个人手中的资本可委托给“人大代表”,因此他与“人大代表”之间也无从建立什么有确定价值标的的资本委托代理合约,从而也无从以任何资本增值和赢利指标来考核“人大代表”。因此,“人大代表”实质上只不过是全民在选择自己的初始资本代理人过程中的一个代理投票人而已。而全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则全然不同,前者把有着明确金额的资本委托于后者,并且可以以资产的增值和赢利指标来考核后者的代理行为,因此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这一委托代理关系链条能否是有效的,主要不是取决于它的经济性的运行成本(如代理环节的多少),而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性质和效率。如果政治体制的性质和效率决定这一权责制约关系的链条是低效的或无效的,那么无论其经济性的运行成本如何低,也不会使结果发生任何改变。根据我们对实际情况的观察,即使我们不能说代理环节的数量和与此相关的经济性运行成本对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体系的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这种影响与政治体制的性质和效率对之所形成的影响相比,也实不啻九牛之一毛。
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那种从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体系的经济性运行成本方面来寻找国有经济低效率的原因的做法,以及那种主张通过缩小共同体和经济的规模从而减少委托代理环节来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政策建议(张维迎 1995),都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而与此相应,那种以同样的理由所推导出的所谓“一个庞大共同体的公有经济是不可能有效运行的”(张维迎 1995)之看法,则也是依据不足的。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在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体系中,中间代理人(中央代理人及其下属各委托代理环节上的上游代理人)的监督激励水平,是由非经济的外部制度环境给定的,与委托代理关系链条的环节的多少没有多大的关系,且在政治体制给定的条件下,它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固定值。
委托人(或上游代理人)的监督激励水平对于代理人(或下游代理人)来说,则表现为一种“监督力”。所谓监督力,就是委托人保证代理人的行为不偏离委托人利益的能力。既然国有资本的中间代理人的监督激励水平是制度环境给定的和不能改变的,那么,中间代理人对最终代理人的监督力就必然也是给定的和不能改变的。
同时我们知道,如何选择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合约的最优形式,与委托人(中间代理人)对最终代理人的监督力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不同形式的委托代理合约对于监督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合约的不完全性越高,合约履行过程对于委托人监督力的需求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而完全合约的履行过程对于委托人监督力的需求则为零,也就是不再需要监督。因此,委托人的监督力越高,委托代理合约就越可以具有较高的不完全性;委托人的监督力越低,委托代理合约就越应当具有较高的完全性;而当委托人的监督力为零时,委托代理合约就必须是完全合约。因此,究竟应当如何选择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合约的最优形式,很显然要取决于我们对于国有资本中间代理人的监督力的估计或假定。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估计或假定当前我国国有资本的中间代理人的监督力水平呢?我的意见是,我们宁肯把它估计得低些,也不要把它估计得过高。我们以往的和现行的国有资本经营模式之所以不成功,其通病都是在于把中间代理人的监督力估计得过高。换言之,它们总是假定政府的官员有追求国有资本安全与收益的动机。而由这种错误假定所导致的通行做法则是:由政府的官员来与国有资本的最终代理人谈判和签订委托代理合约,用政府的官员(如政府派出的国有资本所有权代表或董事)来监督国有资本最终代理人的经营行为等。其效果会如何,实践已经无情地给了我们回答。然而,如果我们低估了中间代理人的监督力水平,却并不会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在较低的监督力水平下都可以有效运行的国有资本经营体制,那么在较高的监督力水平下其运行效率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根据对我国现实情况的观察,我认为,把我国国有资本中间代理人的监督力水平估计或假定为零,即便是稍低了点,也是比较贴近现实的。
如果我们假定国有资本中间代理人的监督力水平为零,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最优的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合约必须是完全合约。
尽管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张维迎博士的模型,主要是从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多环节性推导出代理人的监督和经营激励的不足,这一点与我们上面的分析不相一致,但是它所得出的最后结论与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的,那就是:要想使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率获得根本性的改观,最佳的选择只能是用完全合约来构筑国有资本的委托代理关系。尽管如此,但我们在上面所进行的分析也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指出了国有资本中间代理人的监督激励和监督力的外生性,从而提醒我们今后在对国有资本委托代理关系的效率进行研究时,避免继续将分析问题的着眼点投到无关紧要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环节数量上面去;并且它也提醒我们今后在设计国有资本经营体制模型的具体细节时,要严格遵守“中间代理人的监督力为零并且不变”这一给定前提。
收稿日期:20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