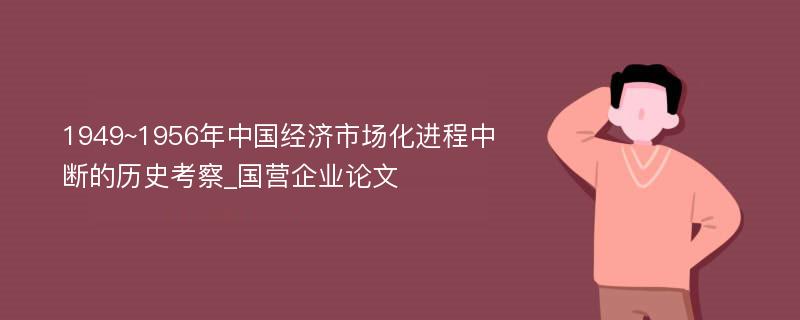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市场化中断过程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年间论文,过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1956年间,伴随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断了。随之而来的是20多年的市场化的断裂期。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才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为何发生这种历史断裂?这种断裂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哪些深刻影响?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中断过程,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1949~1952年:双重体制格局的出现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式微
1949~1952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市场体制因素和计划体制因素并存以及此消彼长的动态特征。一方面,计划体制因素作用的广度与深度逐渐拓展,市场体制因素作用的广度与深度则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双重体制因素在运作中出现诸多深层矛盾,并因此埋下了市场体制因素最终消亡的伏笔。
伴随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计划体制因素逐渐扩展。首先,建立了统一的宏观经济计划管理系统。1949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他中央财政经济管理部门。其次,统一了财政经济管理工作。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基本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是统一收入。财经工作的统一,“实际上是确立国家统一后的财经管理体制。……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版,上卷,8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再次,计划机制开始具体调节经济运行中的生产与流通环节。从生产环节看,国营工业企业的生产基本上被纳入计划范围,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计划管理,完成生产计划成为国营企业的根本任务。由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实施,大部分私营工业的生产被间接纳入计划轨道。这部分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0年约为29%,1951年达43%,1952年则上升到56%。从流通环节看,消费资料流通基本通过市场,但生产资料流通开始被纳入计划轨道。实行计划调拨的物资种类逐渐增加,1950年为8种,1951年增至33种,1952年达55种。
与经济计划化程度增强相对应的,是经济市场化进程出现逆转的苗头。这表现为,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体系中,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逐渐缩小,作用力度逐渐减弱。一方面,市场活动参与者的市场主体性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对市场活动参与者的调节作用减弱。国营企业作为国家计划的执行者,虽然参与市场活动,但它们已经成为行政单位的附属物,市场机制对它们的调节作用很小。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的实施限制了它们同市场的直接联系,导致私营企业对市场信号的敏感程度大为降低。另一方面,市场客体萎缩,特别是部分重要的要素市场萎缩。例如,由于计划调拨与配售的重要生产资料品种增加,生产资料市场的覆盖面逐渐缩小;由于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证券市场的关闭,金融市场也萎缩了;由于国家统一安排就业的制度逐步实施,劳动力市场也开始消失。
由于上述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过程,到1952年,中国经济体制呈现出典型的计划体制因素和市场体制因素并存的“双轨制”格局。据统计,1952年,工业生产中,计划机制起主导调节作用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7.8%,略低于市场机制支配的比重。在批发商业中,计划机制支配63.7%,市场机制支配36.3%。在零售商业中,二者的比重分别为42.2%和57.8%。从总体上看,到1952年,两种调节机制作用的范围与程度大体上是平分秋色,作用力度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但是,从趋势上看,两种体制因素在互相补充、互相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互相冲突、此消彼长的苗头。从外延上看,随着计划机制的扩展,市场机制退却。从作用过程上看,计划机制的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互相干扰,互相扭曲。例如,在稳定市场物价的过程中,出现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垄断市场的状况,割断了私营工商业与市场的联系,成为市场萎缩的直接导因之一。这种情况在“五反”后再度出现,并再次导致市场疲软。与此同时,私营商业收购并经营粮食,又直接影响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完成。总之,二者的矛盾已露出苗头,且潜在地发展着,矛盾发展的主流是市场机制的退缩。这为1953年以后市场体制因素的急剧消亡埋下了伏笔。
二、1953~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市场化进程的中止
1953年,伴随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一五”计划的实施以及“三大改造”的全面推进,上述两种经济体制因素的内在矛盾表面化、激烈化,其结果是:计划经济体制迅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迅速萎缩,到1956年,作为独立经济体制因素的市场基本消失,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止了。
1953~1956年,中国经济基本完成了计划化的过程,突出标志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
首先,在1949~1952年间形成的统一的、系统的宏观经济管理组织体系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条条”为主的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1953年,中央一级财经专门管理部门为15个,占政务院所属部门数的47%;195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5%。与此同时,中央一级经济决策与管理部门的权限不断扩大。在基建方面,“一五”时期,中央的项目占基建项目总数的79%;在工业方面,中央掌握的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9%;在财政收支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80%,支出占75%;在物资管理方面, 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增至227种。其次,形成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组织体系。1953年2月,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 分局发出《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要求“中央一级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1954年2月, 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各省(市)、直属市及县人民政府,应设立计划委员会”。通过这些计划组织体系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方式,指令性计划机制直接控制了大部分工业生产。1953~1956年间,国家计委统一下达计划的产品种类,从110多种增加到300多种。这些产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60%左右。再次,形成了政企合一的企业模式,企业经济活动开始呈现出预算软约束特征。国营企业的经营受国家计划控制,失去自身经济利益。虽然在1955年8月曾经规定, 企业可以保留40%的超计划利润,但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国营企业利润留成只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3.75%。企业财务计划成为国家预算的一个部分,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形成了国营企业不负盈亏的预算软约束局面。上述高度集中以“条条”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及政企合一的企业模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构件。它们的形成,标志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经济计划化的基本实现。
经济计划化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走向中止的过程。1953~1956年间,伴随计划体制因素成为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体系中的支配因素,市场体制因素逐渐被削弱,最终退出了经济体制领域。残存的市场因素,已经失去作为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体制因素的独立品格。
首先是市场联系被割断。经济单位同市场的联系是市场体制因素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然而,自1953年开始,主要由于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经济单位同市场的联系被逐渐割断。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统购统销制度构成合作社与市场之间的隔离因素。统购统销制度也割裂了私营工商业同农村市场的联系,中国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工业,对农产品市场依赖程度很高,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无异于国家操纵了私营工业的“生命线”。其次是市场主体最终消失。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运作的主体基础。1953年以后,国营企业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不复有市场主体特征。合作社本应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各类合作社大多是通过人为的“高潮”建立的,产权界定不清,加上合作经济被视为过渡经济形式,因此,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同上书,第454页。)因此, 合作社同国营企业一样,没有市场主体性。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在公私合营完成以后,私营企业主只通过定息对其资产保留名义上的所有权,再加上这类企业的主要目标也是完成国家计划,生产经营已经失去自主性,因而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国营企业”,(同上书,第426页。 )与国营企业一样,没有市场主体性。再次是市场体系的萎缩。市场体系是市场体制因素存在和作用的客体基础。1953年以后,各类市场进一步萎缩,甚至最终消亡。 在生产资料市场方面, 全国统配物资和中央部管物资由1952年的55种增至1956年的385种。商品市场出现成分单一、 经营方式单一、渠道单一和价格固定僵化的趋势。劳动力就业采取由国家统一安排就业的制度,劳动力市场消失。同时,由于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农村初级市场萎缩,最后是自由市场网络萎缩。自由市场是市场体制因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1953年以后,自由市场范围大为缩小。据初步估算,到195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自由市场交换的比重仅为21.2%。
总之,1953~1956年间,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计划化,与此同时,由于市场联系被割断,市场主体消失,市场体系与自由市场萎缩,市场体制因素赖以存在和运作的基础条件、主体基础、客体基础和主要活动领域基本消失,市场因素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因素,残存的市场因素只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附庸。计划体制因素与市场体制因素并存的“双轨制”格局最终被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所取代。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最终中断了。
三、历史的沉思: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断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在中断了20多年之后,由于70年代末期开始了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又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这20多年的断裂期与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20多年的发展停滞时期恰好吻合。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深层的历史关联性。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断裂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只有充分认识这些影响,才能充分认识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重新启动的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和固化的重要原因。前面的分析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的消亡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能迅速建立起来,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迅速中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前提条件。同样,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持续20多年的时间而未发生根本变化且曾得以强化和固化,又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处于中断状态有直接关系。这表明,在经济市场化未启动之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的。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割裂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与市场化之间的联系。历史进程表明:当年市场体制因素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试图通过全面计划建设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问题在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表明,工业化、现代化与市场化有着历史的共生关系。离开市场化,社会经济的发展难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的轨道,而离开这些方面的发展,工业化与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经济市场化中断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实质就在于经济市场化的中断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专业化、社会化,从而阻碍了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正因为如此,中国要真正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目标,实现经济市场化乃是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联系。经济计划的增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都表明,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机制与手段。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把市场看成计划的对立因素与异己物,从而导致在实践上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使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日趋僵化和固化。因此,在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或将二者对立起来,都是违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但由于改造过程过于迅猛,以致后期的改造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而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是中国“三大改造”急速推进并提前完成的直接推动因素。学术界多将“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归因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实际上,经济市场化进程式微、衰落与“三大改造”的急速推进与完成之间有着深层的、复杂的因果关系。市场体制因素的萎缩,从根本上限制了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空间,为“三大改造”的急速推进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加快了“三大改造”的推进。“三大改造”急速完成的直接后果,是过早地消灭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相适应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形成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单一所有制格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与“三大改造”急速推进和完成之间的这种关系表明,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化的推进与多元所有制结构的构建具有内在联系。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早结束的深层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曾设想过渡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持续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期,但实际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三年后就结束了过渡时期即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其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使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存在和发展的经济体制基础,当这两方面都不复存在的时候,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当然也就不可能按原来的设想以及中国国情的内在要求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在经济体制基础层面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阶段一样,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力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构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