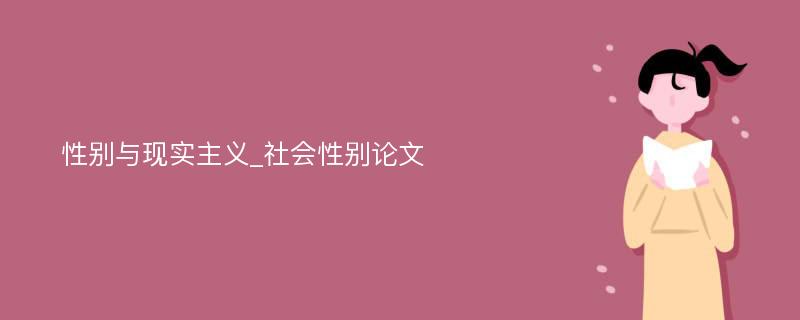
社会性别与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西方国际政治学一直被女性主义者称为“充斥着男性霸权主义”的学科,(注: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77页)。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为其主干的现实主义学说藏而不露的性别歧视内涵。沿着历史的轨迹向纵深探寻,便不难发现,它起始于为该理论奠定基础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性别关系现实及其所隐喻的对不同性质事物的价值判断乃至思维模式的选择。它突出地反映在有关思想家的一系列著述及国际关系发展的具体实践中。
一、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性别(gender)概念释义
“社会性别”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说中与“性别”(sex )相对照的一个概念, 系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 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被用来表示由社会造成的两性社会角色与地位的差别。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Scott)认为, “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 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方式”。(注: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45页)。这一概念表明,妇女的从属地位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作为认识与分析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范畴,社会性别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种族、族裔中有着各不相同的内涵。每一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着几种大相径庭的社会性别观,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因此,社会性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通过与阶级、种族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造成的人类不平等的其他社会机制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作用,与它们共同构筑起错综复杂的社会权力分配体系,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反过来,它也被特定的阶级、种族等社会利益集团用来作为表达自己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手段之一。
二、男性中心主义的奠基与拓展——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性别剖析
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开始萌芽的文艺复兴时期,新兴中产阶级为摆脱教廷对其谋求自身利益的严厉禁锢,努力从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挖掘中寻找精神武器。他们开始由以上帝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变对向来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界的敬畏为充分展现人对大自然的能动性,从消极地等待上帝的拯救与来世的幸福走向树立自救意识、积极追求个人在尘世中的现实利益。(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但是,在整个社会充满着破除旧秩序的不安与骚动之际,绵延数世纪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关系格局却未受到实质性的触动。受古希腊将妇女归属于同城邦事务相隔绝的家庭生活,把被概括为“不洁的、性的、肉体的”女性从政治话语中删除的政治传统的影响,男女被分别要求进入公共(政治与宏观经济)和私人(家庭)这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遵守迥然相异的道德规范,两者间控制与臣服的关系被主流社会视为理所当然。这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的先驱马基雅弗利(N.Machiavelli)对“非道德后果主义”的宣扬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马基雅弗利于中世纪后期撰写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人中强者——君主应当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最高利益的思想的宣扬与对妇女的歧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曾专门论及“国家如何因为女人而垮台”,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地将男子与妇女、公共与私人、公德与私德等相分离。(注: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80~81.)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他对政治和政治权利等的理解围绕着将妇女从有关战争和国家的“高级政治”中排挤出去而展开。这使以重视权力、利益冲突的政治观及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为特征,对后来的现实主义学说产生深远影响的“君主论”哲学染上了浓厚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它不仅意味着妇女无法进入当时以争取独立、谋求霸权和建立主权国家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领域,而且表示被划定为与妇女相关的一切,包括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均必须被拒于国际政治之门外。诸如此类的“男公女私”、“男女异德”的社会性别观被继他之后的霍布斯(T.Hobbes )等现实主义学说的其他奠基者所继承。 在霍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即此后的现实主义学说所指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妇女因易于被征服、成为奴隶,又不像沦落于同样地位的男子那样容易获得自由而不能进入社会契约——文明领域。 (注: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a Postmodern Era”,pp.80~81.)
如果将“男/女”延伸为一种认识和描述事物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来加以考察,现实生活中盛行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影响对它们意义的估量,并进而涉及人们思想方法的确定。在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中,以君主而不是上帝为中心,以及这些精明强干的世俗统治者必须以自由意志、理性和铁腕自救而不是等待上帝的宣示(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等思想所体现的新兴中产阶级矢志与教会决裂、挣脱上帝和自然界等外在力量束缚的强烈愿望,与男与女、“男性范畴”和“女性范畴”的割裂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排拒和控制相辅相成。这种以现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关系隐喻的对“公共/私人”、“形态/事体”、“君主/臣民”、“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的思考,使它们中的“女性”一方成为卑劣低下的象征。随着“公共”和“私人”两大领域分离的加剧以及在前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男子对现实利益争夺的日趋白热化,竞争、逞强、支配、占有等日益成为其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及其理想人格确立的基础。(注:周华山:《阅读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与之相对应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着眼于与“非我族类”的分离并对之加以控制的思维模式因合乎主流社会有关“男性气质”的定义而受到推崇,成为其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强调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整合、在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中定位自己的思维模式则被认定为来自妇女的家庭生活经验并受到贬斥。这一切突出地表现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中,并直接影响到妇女在其中的地位。
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史基本上是一部欧美列强为积累原始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输出资本、赢得高额利润而征服亚非拉民族和前者为争夺势力范围与世界霸权在彼此之间以及同敌对阵营展开殊死搏斗的历史。继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拖入空前的灾难后,苏美两国的冷战又造成世界局势的长期动荡与不安。在此期间,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令许多弱小国家沦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此间爆发的一场场流血和不流血的战争常常被与主流社会对“男子气”(保护弱小的妇女儿童、对上级、父辈和国王的忠诚等(注:参见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3页。)的宣扬相联系。 后者与尚武好战的民族主义互为依托,彼此建构,将妇女作为依附于男子——保家卫国的勇士的弱势群体排挤到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中心话题的边缘。20世纪50年代美国舆论对妇女以当郊外别墅中“快乐的家庭主妇”为荣的生活方式的大力宣扬同冷战初期国家在与苏联对峙中的扩军备战相呼应,力图以女性的“柔弱”反衬树立本国强硬的、足以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国际形象的必要性。同时,欧美列强将亚非拉殖民地“女性化”,即将其描绘为与理性、强健、尚武的西方形成鲜明对照的软弱和非理性的,有待于自己以充满“阳刚气”的“高级文化”加以启蒙和改造的“他者”,为对它们的侵略和统治寻找依据。战争期间针对他国妇女的暴力更使“妇女”一词成为弱小国家和民族遭受奴役的象征之一。
回眸历史,正视当前,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与未来走向所作的理论概括视“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斗争”为国际政治学的核心,而权力意味着人对人的控制。“由于各国以不同形式争夺权力,使国际关系充满了竞争、冲突和战争的阴影……解决权力竞争造成的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办法,是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75页)。在自我改进后的结构现实主义中,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生活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和敌视,一国保障自身安全的举措会导致各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论中虽未公开出现马基雅弗利式的厌女情结,但它们对“权力”的界定和对“自助”的伸张,明显地反映了西方白人中产阶级以在关系中支配对方的方式确立男性身份的价值观念及其男子“坚强勇猛、从不依赖他人”的行为方式,(注:周华山:《阅读性别》,第53页,第79页)。并始终沿袭着他们从自我利益出发,着重于对“他者”的排斥与压制的思维范式。以安全观为例,“一方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338页。 )这种导致国家间关系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所显示的对武力的崇尚和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男子气的相互建构形成了国际政治领域中男子对妇女、“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全面操控:(注:参见Cynthia Enloe,“ Bananas,Beaches and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4.)在被与社会性别划分相关联的“政治/道德”、“外交/内政”等二元对立中,分别被视做“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男性范畴”与“女性范畴”间被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同对外事务中的利益争夺密切相关的军事安全、冲突与协调机制、宏观经济等被奉为前者并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全球性问题、宗教与民族主义、微观经济等则被当做后者而忽略不计。国际政治舞台成为抽象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及其代表——以男性为主的国家领导人和职业外交家纵横捭阖的天地,而以职员、工人、服务人员等身份分布于政府机关、国际旅游业和出口加工业等国际政治的基础结构并维持其运作的妇女被作为非国际政治行为体——个人剔除出现实主义学说的视野。无论在实际生活还是在观念层面上,“妇女”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均被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貌似“性别中立”的概念及其表述所遮蔽和抹煞。它造成该理论内容的单调和思路的偏狭——“它把人类的历史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演进,基本上视为一种简单的循环,顶多是‘新瓶装旧酒’,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它“从不相信国家间的对立会消失,他们把霸权的争夺和强权政治看成大国外交的必然内容,也很少考虑民族国家之外世界政治中会出现什么有重要分量的行为体。”(注:王逸舟:《环球视点》,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因此, 它一方面保持了对国际事务中某些关键性问题的敏锐嗅觉,“另一方面却未能使‘次要’的矛盾和小的问题消失,而后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构成了当今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内容。”(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第358页。)
三、超越界限的探索——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的批判
自以争取男女平等权利为宗旨的妇女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以来,妇女始终积极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除努力争取进入向来由男子垄断的职业外交部门、创建和加入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展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社会运动之外,女性主义者对国际政治学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理论上的揭露和批判,以其对以社会性别为隐喻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的冲击引发出一场思想方法的革命。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杰·爱尔希坦( Jean
Bethke Elshtain)在《女性主义主题与国际关系》(注:Jean Bethke Elshtain,“Feminist Them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340~360。)一文中,借鉴结构现实主义创始人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 )在《国际政治理论》的结构分析体系,创立了反其道而行之的“认同政治”,变前者中对个人、国家和无政府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逐级筛选(抽象)为对上述三者的同时穿越,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意义建构与表述的方式剖析现实主义理论对妇女的歧视。就个人层面而言,她揭示了“正义战士”和“美好心灵”——国家为男子和妇女分别塑造的为国家利益行使暴力的战士和在家庭为之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的平民这两个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认同国家利益的典型形象。它们并不表示男女两性在本质意义上是什么,而是为确保作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男子和妇女在强调冲突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分别起到的主要和次要、骨干与辅助的作用。它不仅将妇女作为一个整体驱逐出国际政治的主流,而且令男子和妇女难以展现如爱好和平的男子、好战的妇女等其他形象,从而建立起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男子及与之相关的“男性范畴”、“男性气质”在国际政治学中的霸权地位。在国家层面上,爱尔希坦针对现实主义把不同类型的国家千篇一律地抽象为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之代表,将对狭义的自我利益的追求作为其不同行为的惟一出发点的片面做法,主张从各民族国家的战略文化即历史与经验出发,分析其作为一种集体认同的行为:“与其他社会相比,这个社会的公民如何在本国国内及与别国的关系中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集体认同在涉及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时,是否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而“当我们谈论这些在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中卓有成效的方法时,我们论及的是总体上将国家推定为既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是他(她)们在战争与政治的巨型史诗中所起作用的认同的一套又一套设想。”在这里,“男性”和“女性”系指被分别确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两种视角,它们被同时运用于对国家及其行为的考察,将使在国际体系层面上被现实主义视为毋庸置疑的一系列观念受到挑战和质疑,从中显示出问题的关键不是妇女是否应当进入国际政治领域,而在于后者本身对她们的排斥。
以爱尔希坦对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权力”的思考为例。该学派习惯于将权力等同于以拉丁语表示的“potesta”,即统治、控制和强制,但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却还有与之不同的另一种理解:代表着能力、效力和潜能的“Potensia”。二者在使用中呈现出具有明显反差的社会性别色彩:“男人是制度化的权力和统治力量的正式承担者,而女人则往往是‘非统治’权力的非正式的,因而是不受控制的承担者。”(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637页。 )这种制度化的正规权力以主权国家等高度集中统一的实体形式出现,压制了对“权力”的其他理解,吞噬并寻求消除未形成组织的分散权力。从这个角度上看,民族国家的建立导致曾为之而奋斗的妇女社会地位下降和形象被扭曲的怪诞现象便不再令人费解。妇女所参与的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包含着一种集体认同和人民对之加以保护的努力,然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建构却不能容忍权力的多元化,为此,它竭力剪除可能与自己竞争的社会组织和权力形式。在将权力集中起来,建立一种等级制结构的过程中,妇女被放逐到一个对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却常常被边缘化的特殊场所,进而从国家的视野中隐匿。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弱化“权力”概念中的“统治”含义,支持各类能够包容国际国内的权力与行动资源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以此开辟一个广阔的政治空间,建立一种复合型的政治认同。
从爱尔希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正力图以一种整合的、赋予女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取代前者中隐藏着“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内核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它所主张的既不是简单地让妇女通过“向男看齐”证明自己具有与他们同样的能力和才干,也绝非颠倒乾坤的“翻身”,而是彻底破除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中“男/女”、“男性范畴/女性范畴”、“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之间的隔阂,以证实这样一个道理:对该领域的研究如若排除了女性视角便难以卓有成效地进行。因此,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妇女及被与之相关联而受到鄙视的一切正名,更在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空间,促使其主体与对象的多元化。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吉米·乔治所指出的:“在重新塑造国际关系日程的时候,女性主义者清楚地说明,冲破性别障碍并不是要简单地扩大妇女的解放范围,相反,她们表达的,是一种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刻的哲理理解人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努力。”(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6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