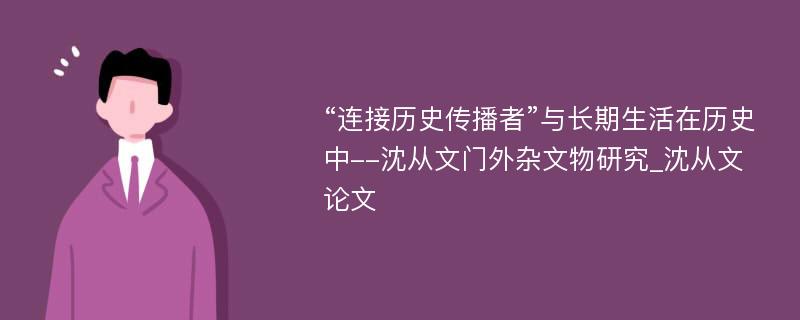
“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门外论文,杂文论文,长久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从文的前半生以文学创作成就伟绩,后半生以文物研究安身立命,一生的事业,好像一分为二,两种身份,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观察到另外的情形:作家也好,文物研究者也好,这两种身份是矛盾和统一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文学和文物这两个领域,创作和研究这两种方式,一般人在意和注重的是不同,是相隔,在沈从文那里,却是相通。不是表面的相通,是这个人在根子上看待世界和历史、看待人事和自我的意识、眼光、方法上的相通。他的意识、眼光和方法的独特,不仅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学,同样也造就了他在文物研究上的独特贡献。
更多的读者熟悉沈从文这个人和他的文学,相对地不太熟悉他的文物研究,那么我们就试着从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出发,逐步地走进他文物研究的世界。我想说的都是“入门”前的话,却是理解他的“专门”研究的重要基础,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以下简单地谈这么几个问题:
一、他这个人和文物研究是什么关系;
二、他的文学和文物研究如何相通;
三、他的文物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成就有什么独特价值。
明白了这几个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考虑,从他的文物研究,我们能否得到启发,更好地来理解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
一 远因和选择
沈从文为什么要研究文物?现成的答案,时代转折之际,“不得不”割舍文学,“改行”。来自政治的巨大压力,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这其中的一些情况,不少人已耳熟能详,我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人在巨大压力之下仍然是可以选择的,在看似完全被动、被迫的情形下,其实仍然存在着自主性,当然这种自主性受到严酷的限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维持。沈从文不是不可能继续当个作家,留在文坛上;事实上新政权的一些部门和个人也确实多次表示,希望他继续写作。但他十分清醒,他的文学和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无法相容的,如果他屈从外力的要求而写作,就是“胡写”;而“胡写”,他就“完了”。他是为了保持个人对于文学的挚爱和信念而放弃文学的。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不是从许多选项中挑了这么一个,而是,就是这一个。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我们来看看这颗种子在土里的历程。这个历程的时间还真不短。
《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本书的奇妙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讲,这里只讲和我们的问题有关的一个方面。这本书是沈从文三十岁写的,写的是他二十一岁以前的生活,他在家乡的顽童时代和在部队当兵辗转离奇的经历。不要说书中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写这本书时候的沈从文,也无法预知他后半生命运的转折。可是这本书里有动人的段落和章节,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要讲沈从文的书法历程,必得从这份早年的“产业”讲起。《从文自传》倒数第二章题为《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①
我们在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完成多年之后,细读他早年这样的文字,后知后觉,不能不感叹生命远因的延续,感叹那个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和三十岁的自传作者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了一个惊人的大伏笔。
从湘西来到北平之后,还不清楚自己未来事业的路在哪里的时期,摸索读书,其中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②
抗战后寓居昆明八年,早已确立了文学地位的沈从文,特别留心于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③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沈从文在极端的精神痛苦中写了两章自传,其中之一是《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和分析了美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他说,“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④
由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将来要选择的研究“对象”了。
二 杂文物和普通人,历史的长河和“抽象的抒情”
我一开始就说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文学相通,怎么个相通呢?
先看看他关注什么东西,简单罗列一下他的一些专门性研究:玉工艺、陶瓷、漆器及螺甸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当然还有历经十七年曲折、在他七十九岁问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代表性巨著。你看他感兴趣、下功夫的东西,很杂,所以他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但这些很杂的东西有个共同的地方,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你也可以说,他的杂文物,大多不登大雅之堂。这些杂文物,和他的文学书写兴发的对象,在性质上是统一的、通联的。沈从文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与一般文物研究关注的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这是一方面。
第二,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和研究,“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物的背后是人,举个形象的例子,“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⑤沈从文年复一年地在历史博物馆灰扑扑的库房中与文物为伴,很多人以为是和“无生命”的东西打交道,枯燥无味;其实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会看到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态。汪曾祺也说:“他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⑥也就是说,物通人,从林林总总的“杂文物”里看到了普通平凡的人,通于他的文学里的人。
第三,关于历史。文物和文物,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蕴藏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智慧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工艺器物所构成的物质文化史,正是由一代又一代普普通通的无名者相接相续而成。而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历史,才是“真的历史”。什么是“真的历史”?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在回乡的河流上有忽然通透的感悟: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⑦
这是一种非常文学化的表述,这样的眼光和思路所蕴含的对历史的选择取舍,对于承担历史的主体的认识,到后半生竟然落实到了工艺器物的实证研究中。杂文物所连接的物质文化史的长河,同样使他“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文物研究与此前的文学创作贯通的脉络如此鲜明清晰,实打实的学术研究背后,蕴蓄着强烈的“抽象的抒情”冲动:缘物抒情,文心犹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实物图像为依据,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探讨服饰的历史。在引言中,沈从文有意无意以文学来说他的学术著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⑧。这还不仅仅泄露了沈从文对文学始终不能忘情,更表明,历史学者和文学家,学术研究和文学叙述,本来也并非壁垒森严,截然分明。一身二任,总还是一身。
三 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是挂在很多人口头上的话。如何看待悠久的历史,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在观念上和兴趣上,都存在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观念和兴趣,都需要不断反省。现代史学的第一次重大反省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一九○二年写的《新史学》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梁启超受当时日本流行的文明史影响,责备中国传统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历史只为朝廷君臣而写,“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⑨严复此前《群学肄言》里也说,“于国民生计风俗之所关,虽大而不录”。⑩一百多年前新史学所倡导的引发激烈论争的观念,今天看来也许十分平常,不过如果再看看一百多年来一般人的历史观念和兴趣究竟有多大改变,仍然会觉得那些意见未必过时。
沈从文不一定清楚世纪之交那场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辩论,他凭借自己生命的经验、体悟和真切的感情,而不是某种史学理论的支持,30年代在湘西的河流上追问什么是“真的历史”,“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这个强烈的感受,恰恰呼应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连文字意象都不约而同:“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11)。而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学写作中,沈从文把满腔的文学热情投射到了绵延如长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乐上;一九四九年正式开始的杂文物研究,已经是非常自觉地把产生物质文化的劳动者群体的大量创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沈从文不是理论家,可是他的研究实践却强烈地显示出明确、坚定的历史观和物质文化史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研究不是文物研究的主流,不被理解是必然的。通俗一点说,沈从文研究的那些东西,在不少人眼里,算不上文物,没有多大研究价值。50年代,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什么“废品”呢?如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另一件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赦相近,花四块钱买来的。“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这一事件一方面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确实不被认同,甚至被排斥,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而安排如此形式的羞辱。“当时馆中同事,还有十二个学有专长的史学教授,看来也就无一个人由此及彼,联想到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还始终有大生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都未停止生产过。这个值四元的整匹花绫,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12)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沈从文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不仅他这个人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他的研究观念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沈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正统的)历史研究训练,他如何着手杂文物研究呢?笨办法:与大量实物进行实打实的接触,经眼,经手,千千万万件实物,成年累月地身在其中,获得了踏实而丰富的实感经验,在此基础上展开探讨。历史博物馆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他们觉得研究工作就是在书桌前做的。沈从文从一己的经验,体会总结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13)沈从文对王国维古史问题探索方法的呼应,不是理论上的选择,而是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他相信自己的这种笨方法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并且,“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静安先生时代工作条件便利了百倍,拥有万千种丰富材料”,可以利用的文物数量大大增加,“但一般朋友作学问的方法,似乎仍然还具有保守性,停顿在旧有基础上”。(14)与他的这种方法相比较,博物馆通行的两种研究方式,他以为都不怎么“顶用”:“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15)
新的文史研究必须改变以书注书、辗转因袭的方式,充分地利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充分地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才能开出一条新路。对这一主张,沈从文相当自信,反复强调。以服饰为例,“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作《三礼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官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这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一开篇即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所谈,不仅说明仅仅依靠文字之不足,而且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取舍选择,这样的取舍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观念有所偏离:“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16)事实后来终于证明,沈从文所主张的观念和方法,经过他自己的多年实践,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别人无从替代的贡献。
四 留给后代的礼物
一九四九年九月,沈从文致信丁玲,表示完全放弃文学写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头脑用到工艺美术史的探索研究上,只要环境能工作,或可为后来者打个底子,减少后来人许多时间,引出一些新路”。“且让我老老实实多作点事,把余生精力解放出来,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17)在个人处境那么不堪的情形中,他对新的事业却有如此非凡的抱负和强烈的自信:引出新路,留给下一代。
一九五二年一月,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人与历史:“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一通过时间,什么也留不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把特具的热情献给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献给了历史中留存下来的工艺器物,他的研究也因此成为“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18)。
沈从文以研究历史的方式,使自己长久地活在历史中。
①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②④⑤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3~24,20、22、23,23、22页。
③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0~161页。
⑥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晚翠文谈新编》,第191页。
⑦沈从文:《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188~189页。
⑧(1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⑨(1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3页。
⑩严复:《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12)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81、382页。
(13)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4)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312页。
(15)沈从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49页。
(17)沈从文:《致丁玲》(19490908),《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52页。
(18)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4),《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11页。
标签:沈从文论文; 文学论文; 沈从文全集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文物论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散文论文; 杂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