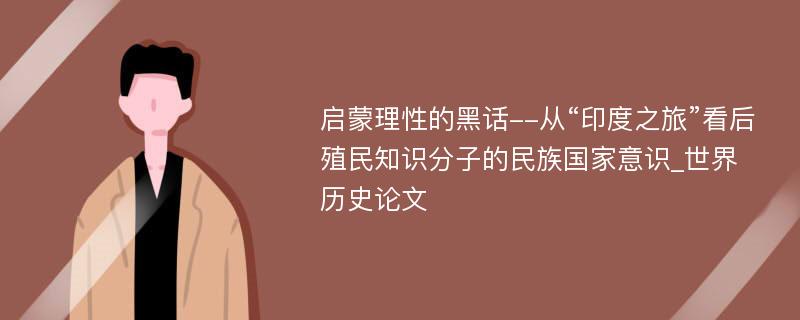
启蒙理性的黑色絮语——从《印度之行》论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絮语论文,之行论文,知识分子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3)03-0083-05
发表于《疆界2号》上的《黑人的身体:从康德和黑格尔到杜波伊斯和鲍德温》一文中 ,大卫·克莱尔将黑格尔和杜波伊斯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因为《精神现象学》中那著 名的‘主奴’辩证关系,而且是因为杜波伊斯和黑格尔两人都迎来了自我意识的双重化 ”。(Krell,2000:105)黑格尔和杜波伊斯都站在现代性形成的历史断裂处,一方面承 受着传统与现实脱节时的失重感,另一方面新奇地体验到现代性摧枯拉朽的力量。因此 ,大卫·刘易斯在《W·E·B·杜波伊斯:一个种族的传记,1868-1919年》中认为,杜 波伊斯在德国两年的求学使他在25岁这样的年龄醒悟到“生活中某种可能的美和优雅” 。(Lewis,1993:129)克莱尔在此实际上触及了与启蒙理性密不可分的两个问题。
首先是启蒙哲学对启蒙理性在构建现代性主体过程中的作用的关注以及启蒙理性的蜕 变。按照启蒙哲学家的设想,启蒙理性将促成现代性反思主体包容一切、自在自足的绝 对精神。可是,这种与现代性共存、与日俱增的理性反思意识并没有达到黑格尔所设想 的气势恢弘的绝对精神。恰如马克思·韦伯所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启蒙理性的分 裂、蜕变使得启蒙哲学家依靠启蒙理性重建现代性主体的理想归于南柯一梦。
其次,后殖民知识分子主体重构的过程也是脱胎于欧洲启蒙理性的后殖民民族主义对 启蒙理性进行颠覆的过程。这种后殖民话语中启蒙理性的自我颠覆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 层面。一方面,欧洲现代启蒙理性打破了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连续、确定和完整的传统 文化意识,在他们的主体世界中形成了欧洲现代启蒙理性和殖民地本土文化之间的张力 。另一方面,文化意识差异产生的批判意识使他们既对本土文化持批判态度,又不满于 殖民主义霸权。结果是这一类西化知识分子最终超越现代与传统、欧洲与非欧洲、白人 主子和非白人奴隶这类二元对立,挪用欧洲启蒙理性推动下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形 成新的民族主义。
在《地球上苦难的人们》中,弗朗茨·法侬描摹了后殖民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意识形成 的三个阶段: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对本土传统、历史和文化的重 新认识,以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Fanon,1967:178)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知识 分子诉诸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形成后殖民历史境遇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完成了启 蒙理性的自我颠覆。
从这一视角来分析英语文学叙事中主奴启蒙辩证关系和后殖民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意识 的演变,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1 924年)和沙尔曼·拉什迪的《午夜出生的孩子》(1918年)构成了反复再现、重写300年 来欧洲现代资本主义殖民历史上主奴关系的三部曲。这三部曲展示了欧洲现代性的咄咄 逼人之势,胎生于欧洲现代性的殖民主义自我对后殖民他者的影响,也再现了被压制的 、以后殖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后殖民民族—国家形式为核心的后殖民话语与殖民话语 间的张力。
《印度之行》则是这一历史叙事的中间环节,曲折地再现了后殖民民族主义意识的形 成这一转折点。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第三章“抵抗和对立”中,爱·萨义德认为E ·M·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的“关键是英国殖民者……与印度间持久的对抗”。( Said,1993:201)萨义德将小说中再现的印度次大陆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简约成殖民者和 被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却没有从具体、更深刻的后殖民历史语境来理解现代启蒙理性和 殖民奴役在殖民地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印度 医生阿齐兹印度中心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艰难诞生之中。
如果说杜波伊斯在德国两年的求学使他从康德、歌德和黑格尔的思想散发出的强烈的 时代精神中找到了开启他那被尘封的黑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促成了对自己种族多舛命运 的反思,福斯特则在自己的生活中认识了一位杜波伊斯式的人物。1906年8月,福斯特 拜访住在英国威布里奇的莫里森太太时结识了留学英国的印度伊斯兰知识分子马苏德。 如福斯特自己后来所言,马苏德将他从中产阶级闭塞的郊区生活和单调的大学生活中唤 醒,拓宽了他的视野,让他接触到新的文明。1912年至1913年间,应马苏德之邀,福斯 特与另外两名剑桥挚友第一次游历印度次大陆。正是在这期间,福斯特耳闻目睹了奥里 加尔(Oligarh)泛伊斯兰运动、运动领导人阿里兄弟被捕及受审等政治事件。他对马苏 德代表的印度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世界有了更透彻的了解。
游学德国的杜波伊斯和旅居英国的马苏德有着不同的生活际遇,他经历了现代欧洲与 被殖民者文化间巨大的差异带来的精神震撼。但从后殖民话语来诠释,两人的生活经历 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对启蒙理性的工具性挪用、对作为大写的他者之欧 洲这个中心的认识、质疑和反抗。在《印度之行》中,阿齐兹成了杜波伊斯、马苏德这 一类承欧洲现代启蒙理性之赐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虚构形象。他的印度中心主义式的民 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诞生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从殖民地边缘到欧洲中心的求学之旅成了他摆脱被殖民对象的狭隘和无 知的契机。他不仅掌握了欧洲先进的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而且受到了欧洲现代启蒙理 性的启迪。这种被殖民知识分子的欧洲化使阿齐兹的主体分裂成杜波伊斯所谓的双重意 识:欧洲现代意识和伊斯兰传统意识。
A·D·甘格里认为阿齐兹这一形象具有令人炫目的透明性,混合着西方文明和东方文 明。(Ganguly,1990:74)从文化差异反观阿齐兹这一文化主体,甘格里认为阿齐兹文化 身份隐含混合本质和双重意识。双重意识产生的文化差异感使阿齐兹无法完全融入现实 中任何一种文化,他的文化身份因文化差异处于错位状态。这种不同文化的多声混奏被 象征性地再现在阿齐兹的内心世界中。宁静的夜晚,阿齐兹在离英国人俱乐部不远的一 座清真寺中休憩:
他坐在寺院左边的矮墙上。脚下的地势斜伸向城市。夜色中,城市的模糊轮廓如一团 树影,隐约可见。静谧的夜里,许多或强或弱的声音传过来。在右边的英国印度殖民官 俱乐部里,英国人正在进行业余合奏表演。其他某个地方,印度教徒不停地敲打着鼓— —他知道他们是印度教徒,因鼓声的节奏不能在他的内心里产生共鸣,——此外,还有 人在死尸旁恸哭不止——他知道是谁死了,因为当天下午是他确诊的死亡。还有猫头鹰 的叫声,来自旁遮普的邮车的隆隆声……火车站站长的院子里的花发出阵阵袭人的芳香 。可是这清真寺——惟有它昭显着明确的意义。他摆脱了夜缠绵的引诱,回到这清真寺 ,并用意义打扮、装饰这座寺院。这可是寺院的建筑者始料不及的。(Forster,1992:1 9)
这从不同层面突显出阿齐兹内心世界的混乱。外在的世界在阿齐兹的主体中被重新编 排、组合。紧靠着清真寺的英国人俱乐部无疑象征着英国人的精神庇护所。伊斯兰教与 印度教势同水火。旁遮普邮车、延伸到印度次大陆腹地的铁路象征着现代欧洲文明的咄
咄逼人之势。猫头鹰和花代表着人的世界之外的动物和植物世界。外在的世界作用于阿 齐兹的内心世界,形成不同的心理情绪:英国殖民者俱乐部中喜庆、欢闹的氛围,欧洲 文明震耳欲聋之声,夜色呵护下宁静、神秘的清真寺,对死者的悲哭映衬着他内心深处 因伊斯兰的沦落而无声的悲泣。
在英国统治下的钱德拉普,阿齐兹进入了文化意识的嬗变的第二阶段:与明达医院代 表的英国殖民权力机构的认同和被殖民奴役的印度人身份造成他主体世界的进一步分裂 。
一方面,以特尔顿先生为首的殖民官僚冥顽不化地恪守英国公立学校精神,主张对印 度实行强硬的直接统治策略,强调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当穆尔太太、阿德 拉·奎斯蒂德小姐和阿齐兹在菲尔丁的学校里聚会时,罗尼·希斯罗普来带穆尔太太和 阿德拉·奎斯蒂小姐去看马球比赛。阿齐兹遭到罗尼的傲慢对待。在罗尼·希斯罗普的 眼中,阿齐兹属于“被宠坏了的西化”的印度人。(Forster,1992:77)特尔顿太太则 认为,在印度的英国人比绝大部分印度人优越,西化的印度人将抹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间的差异。她对穆尔太太说:
不管怎样,你比他们优越。请记住这一点。你比任何印度人都优越,除了寥寥可数的 几位王妃还算与我们地位平等。(Forster,1992:41-42)
另一方面,阿齐兹也无法完全认同旧的生活习俗。印度传统的包办婚姻使他与妻子两 人间缺乏爱情基础,西化的他试图追求超越婚姻之上的爱情。西式医学训练使他成了等 级森严的英国印度殖民行政当局辖下驯服的工具。在英国人眼中,他是为明达医院工作 的一名印度医生,是卡伦德尔少校手下一名被英国化的下属。可是,满腹诗才的他内心 又充溢着激情,常常情不自禁地追抚昔日伊斯兰帝国的光荣。
阿齐兹主体世界中矛盾的两极似两股奔涌却无法融合的炽流分解了他本应完整的文化 意识。双重文化意识造成的矛盾化为摩罗巴岩洞中的两股火焰:
……划燃一根火柴。转瞬间,就像被禁锢的精灵,另一股火焰从岩石的深处蹿起,冲 向岩洞的表层。整个圆形的岩壁无比地光洁柔滑。两股火焰奔向对方,努力想结合在一 起。可这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一股火焰呼吸的是空气,而另一股呼吸的是岩石。(
Forster,1992:125)
然而,阿齐兹的主体世界并不单纯是被各种文化力量肢解、分裂。当他既不能与殖民 统治者的文化完全认同,又无力响应激进的伊斯兰独立运动时,阿齐兹走上了一条独特 的肉体、精神复苏之路。他开始进入文化意识嬗变的第三阶段: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
阿齐兹起初答应与另一位信仰印度教的医生帕纳·拉尔一起去参加在英国印度殖民官 员俱乐部举行的联谊会。可是临到联谊会快开始时,他突然“被一种厌恶感攫住,决定 不去了”。(Forster,1992:55)参加穆尔太太、阿德拉·奎斯蒂小姐、戈德波尔教授和 菲尔丁的聚会后,罗尼的粗暴无礼和戈德波尔教授对印度教中牧牛神黑天的神秘赞歌在 阿齐兹身上引起他早就预料到的病痛。当他躺在床上假装生病时,从殖民行政官邸的教 堂和英国传教士的教堂传来的悠长的钟声使他在迷糊之际隐约地感到对印度社会现实的 不满和恶心。
这种不满情绪浓缩在挂在他卧室天花板上的一团苍蝇这一意象中:“(电线)并没有通 电,一群苍蝇反而占据了这里,电线上挤满了他们黑黝黝的身体。”(Forster,1992:1 01)苍蝇这一意象在此是一个所指意义模糊的能指。它既不单指印度的土著人(尽管有着 黑黝黝的身体)、也不仅指英国殖民者(尽管他们像苍蝇似地拥到印度)。在感觉层面上 ,这一意象投射出阿齐兹此时此地亲身体验到的萨特式的恶心感。在更深的自由—人文 主义思想层面上,它却表现了人类四分五裂的可悲现实。
阿齐兹体验的恶心感只不过是反抗意识的萌芽。反抗意识的发展在控告他对阿德拉· 奎斯蒂小姐犯有性骚扰罪的法庭审判一幕达到了高潮。他那黝黑、非白种人的身体处于 白种男人和女人的审视中,遭受着英国印度殖民司法体制的规训和羞辱。这样,恰如酷 热的旱季笼罩着整个印度次大陆,阿齐兹对卡伦德尔上校的反感、不可名状的恶心感变 成了对整个英国殖民当局的仇恨。他惟一的选择就是离开英国人直接统治下的钱德拉普 ,到仍享有自治权的土邦莫去。他终于能直面印度被殖民统治的苦难现实,进而反抗英 国对印度的殖民奴役。他设想整个印度次大陆超越宗教纷争和信仰分歧而走向团结,呼 唤新的印度民族—国家的诞生。
诚然,这种乌托邦式的印度中心主义明显与其他伊斯兰知识分子狂热的泛伊斯兰民族 主义相左。阿齐兹恪守的民族主义观念超越宗教差异和历史宿怨,其目的是努力拯救所 有惨遭种族歧视、殖民权力压制和宗教纷争之苦的不幸的印度人。与此相反,泛伊斯兰 民族主义企图将整个近东的伊斯兰信徒团结起来,具有极端的宗教狂热倾向。这两种迥 然不同的民族主义意味着推动被殖民民族独立事业的民族主义意识是一个具有多项所指 意义的能指。英国殖民当局利用这种被殖民民族内部民族主义的分歧,在他们中间播下 仇恨、分裂的种子。《印度之行》中伊斯兰教信徒和印度教教徒间的冲突以及1947年8 月15日的印巴分治只不过是宗教狂热和极端主义负面影响的两例。
阿齐兹对伊斯兰文化和历史的非极端宗教政治认同决定了他的印度中心民族主义的独 特内涵。他的思想常沉溺于两个长久不衰的传统伊斯兰诗歌主题:伊斯兰的沦落和爱情 的短暂。他刻意将古代一位德干国王墓碑上的一首诗选作自己的墓志铭:
啊,我逝后无数的岁月风霜
不停地摧残烂灿的玫瑰,迎来送走明媚的春光,
但那些深深体悟我心灵的人——
他们会临拜我的墓地。(Forster,1992:19)
阿齐兹在伊斯兰诗歌艺术中不仅感受到一种感伤和苦难并存的审美体验,而且达到了 对伊斯兰历史的诗性认识。诗性的审美体验和历史意识也就摆脱了纯抽象、个体情感的 范畴。诗既激发高贵的情感、极度的欢欣,也紧紧地与伊斯兰文明连接在一起。诗既将 他的心灵世界抬升到空灵、永恒之境,也驱散了严酷的现实投射在他心灵上的巨大阴影 。
阿齐兹让伊斯兰的历史通过诗言说自己,在历史的诗性言说中最终与伊斯兰历史中独 特、被排斥的苏菲神秘主义传统达到文化认同。《印度之行》第二章中阿齐兹静夜光顾 的清真寺就是他体悟苏菲式神秘天恩的场所:
他坐在那里,目光所及是三重拱门。拱门上悬挂着一小盏灯。月亮照亮了拱门的幽暗 处。……这里就是伊斯兰,是他自己的国家。伊斯兰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也不仅仅是战 斗的呐喊,它意味着更多,还要更多……伊斯兰也意味着对精美、永恒生命的态度。他 的肉体和灵魂在伊斯兰中找到了归宿。(Forster,1992:19)
这里的拱门、灯和月亮在阿齐兹的个体灵魂中开辟了一个苏菲主义式的体悟、感知上 帝神秘精神的存在空间。上帝的精神像灯光、月光一样驱散了黑暗,照亮了心灵最深处 。苏菲们虔信上帝就是光:
上帝是天上和地上的光;
上帝之光如壁龛里
放置的一盏灯……
(Arberry,1995:50-51)
正是在这个独特的象征性存在空间,阿齐兹摆脱了现实生活的苦闷和彷徨,在上帝之 光和爱中实现了精神回归。
伊斯兰诗歌和苏菲主义在阿齐兹的文化意识中内化。他以回望的方式寻找文化之根, 在超验、神秘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英国殖民权力对他的审判和羞 辱却使他从感伤和怀旧情结中猛然醒悟。印度法官达斯先生要他为一家月刊写诗时,他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诗缺乏个人经历的滋养,不能反映真实的生活,仍局限于伊斯兰的衰 亡和爱之短暂这样陈腐的主题。他“渴望谱写一曲新歌。千百万人会为之欢欣,在田野 里纵情歌唱。用什么语言来创作这首歌呢?它又将向世界宣告什么呢?他发誓去了解除穆 罕默德信徒以外更多的印度人,永远不再回头”。(Forster,1992:268)阿齐兹终于意 识到伊斯兰传统的局限性。为了从更广阔的层面上了解印度社会,他前往莫。正是在莫 ,阿齐兹告别了旧我,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激情,憧憬到印度的希望和未来。他终于能超 越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宗教纷争,对印度教宽仁以待。他的诗也一扫以前的颓废之 气,转向呼唤将东方女性从封建深闺制下解放出来这一现实主题。
综观阿齐兹民族—国家意识诞生的三个阶段,他的文化身份也经历了三次边缘化。欧 化教育和英国印度殖民权力机构(明达医院)的规训使他有别于其他印度人,可非白种人 身份又使他受尽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歧视、奚落和不公正待遇。向伊斯兰的诗、历史和苏 菲主义的精神回归使他不能完全融入现实生活,游离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他的伊斯 兰文化身份、所接受的现代欧洲医学规训使得他的文化身份在信奉印度教、传统、落后 、千疮百孔的莫第三次被边缘化了。
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他的心理世界承受着不安、恶心、沮丧、欢悦和希冀等情感的考 验。最终,他的声音再也不是少数者、历史和虚无主义式的审美情感的虚假声音。他从 生活的苦难经历中学会了着眼于未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声音呼唤着新印度的诞生。阿齐 兹民族—国家意识被重铸的艰难过程就是被奴役的印度人逐渐学会言说自我、用具有强 烈凝聚力的印度民族—国家理念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过程。他的后殖民民族—国家意识 的核心就是印度中心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印度集体文化自我。这种集体文化自我与整个印 度次大陆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理念相契合。
在小说中,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刻暗示着阿齐兹后殖民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对 阿齐兹的审判和莫老国王的去世。钱德拉普的印度人自发的游行庆祝以及一年一度为牧 牛神黑天诞辰所举行的庆典无不洋溢着狂欢精神。受殖民奴役的印度人对殖民权力和旧 的封建统治无情蔑视、肆意嘲弄。印度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狂欢节式的庆祝不 仅催动着阿齐兹的新生,也是对印度自由灵魂的祈祷。因此,牧牛神黑天的诞生象征着 阿齐兹后殖民民族—国家意识的诞生。牧牛神的形象就是独立、自由、强大、蔑视强权 的新印度的化身。
已往的文学批评常将《印度之行》理解为英国人的印度之行。如果从阿齐兹民族—国 家意识的形成这一视角来解读,我们将从小说的题目中读出另一层新意。阿齐兹是被欧 化的伊斯兰知识分子,是诗人,是被英国殖民权力规训的医生,亦是为民族独立而战的 斗士。印度之行也是阿齐兹的印度之行——一条通向理想、信仰中真实印度的旅程。在 这条路的尽头是另一个独立、团结一体、摆脱了大英帝国的奴役、超越了宗教纷争的民 族—国家。
不同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对以民族—国家理念为核心的后殖民民族主义持不同的 批评态度。弗朗茨·法侬在批判第三世界的泛民族主义时认为,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 应以民族—国家模式为基础。然而,另一些后殖民理论家则意识到民族—国家模式的局 限性。(Payne,1997:425)因此,像斯比瓦克、哈米·巴巴、周蕾和斯图亚特·霍尔这 些文化批评理论家力图突破传统与现代性、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这类后殖民理论宏大 叙事,转向关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被边缘化的少数者群体。
从杜波伊斯式的泛民族主义、阿齐兹的民族主义到霍尔的少数者话语的转向勾画出后 殖民批评话语的历史轨迹。也正是从后殖民批评话语的历史性和欧洲现代启蒙理性在由 被殖民的本土知识分子阶层推动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历史性的自我颠覆来看,我们不 应对民族—国家这一理念和民族主义情绪一概排斥、一笔勾销。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系的莫利兹奥·维罗里教授说得好:“……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着正 面的作用,因为,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上的自治、本土生活方式 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效仿别的什么国 家了。”(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2000:177)
同样,也正是由于后殖民批评话语的历史性、异质性,我们应认识到启蒙理性自我颠 覆的历史性和多样性。杜波伊斯是在为千万个黑人的灵魂祷告,将他们的亡魂从黑色的 大西洋此岸超度到彼岸——那片黑褐色的非洲大陆。20世纪初期的马苏德和阿齐兹这类
印度知识分子是在借用西方现代性孕育的思想、政治话语来铸造未来民族—国家的灵魂 ,自下而上地从政治、宗教、思想和哲学层面上颠覆欧洲霸权。在20世纪80、90年代, 爱·萨义德、斯比瓦克、哈米·巴巴、周蕾和斯图亚特·霍尔这批来自第三世界的后殖 民批评家则以不懈战斗、强烈的政治关怀和批判的姿态活跃在西方学术阵营。
收稿日期:2002-10-30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阿齐兹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