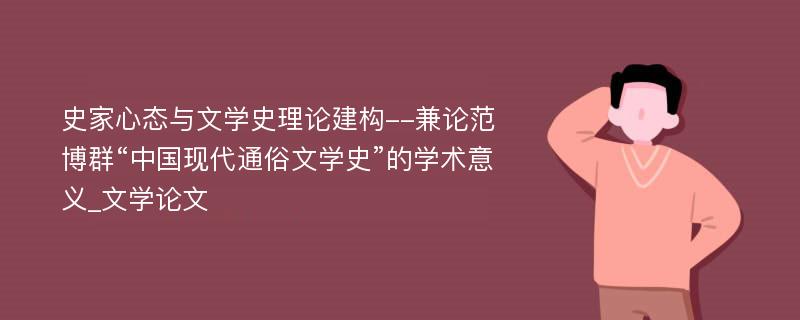
史家心态与文学史理论之建构——兼谈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① 的学术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史家论文,中国论文,通俗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6-0102-06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超过干部之上,② 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不外一是文学历史的阶段性的呈现,一是文学类型的历史表现这两种基本模式,前者强调文学中的历史性,后者则重视历史中的文学性。通常在讨论文学史时,还有史家和阅读者两个层面的文学史话题,形成了文学史专著和文学史教科书两种主要类型,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问题:是个人治史还是集体编撰历史,文学史是表达个人化的精神心灵还是表现文学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百余年来,前半段相对侧重文学史自身写作,后半段多于文学史自身问题的讨论。后者主要表现在20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理论探讨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大家这么关注文学史写作的问题。我们现在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或曰价值标准多重性可能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文学史百年的写作经验到了需要认真总结和思考的时候了,而且也具备了反省文学史写作在理论与实践上相结合的条件。研读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结合自己文学史研究的体会,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一部文学史的真正价值,首要的是史家的主体意识应由心而发,去感应生活和时代,打捞和触摸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是由史家心的感悟和理解完成转换的,从而形成有特色、有个性、有读者的文学史。
一
史家心态即文学史作者的心灵状态,但是心往往源于境、受动于境。人的生存环境决定人的所思、所言、所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只是孤立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习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并没有人注意每个时代中的文学史家身与心。甚至文学史家也更看重社会和时代对自己的要求。就以建国后(现当代)有影响的文学史家为例,王瑶、唐弢、张毕来、刘绶松等老一辈文学史家的写作基本都是服务于新中国建设初期高等教育的需要,受教育部的行政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或“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③ 作为写作者“也并非自己觉得很胜任,只是因为工作分配关系,必须把它当作任务完成的”。④ 王瑶等先生最初编撰文学史的“任务”意识,是与建国初期社会文化整体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决定了“新文学”的命名、文学史的内容和形式。一个明显的例证是,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其文学史分期和纲目俨然成为一部《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学版,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同样,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情境,且不说80年代初期因高校教学需求导致一大批“拨乱反正”的文学史应运而生,就是至今仍然在产生影响的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反映着著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作者们在“后记”的开篇直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正酝酿着突破。为了突破,不仅需要在学科前沿阵地进行新的探索,而且要求及时地把有的成果用文学史教材的形式肯定下来,普及到广大初学者中间,同时作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⑤ 固然,从社会政治任务到学科建设使命让文学史撰写的出发点有了巨大的转变,在“使命”中多少有了史家一定的身与心主体意识的驱动,文学史写作在向着她自身的世界走近;但从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太重的外部因素影响着史家焦虑的心,写史并不超然和平静。这种状态从上世纪90年代末洪子诚、陈思和两人同期同名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可以进一步感受到变化。洪子诚说:因为发现了70年代末他参与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有“许多缺陷,许多需要修正之处”,所以“重新修订编写,就提到了日程”。⑥ 陈思和说:他编写的这本文学史是“大学初级教材”,“只是一部给文学爱好者、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阅读的书,所以努力写得简洁好读……”⑦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作为大学教授迫切要编写适合学生需要的文学史和尽快修订旧的不适用的教科书,因而较少先前的社会历史使命感,更多表现出高度自觉的“岗位”意识。需要指出的是,从“使命”意识到“岗位”意识依然反映着史家的焦虑,不同的是从社会使命到定位于大学教师的责任,史家开始重视自己的岗位身份。而从服务于普泛性统一社会需求到身份的认同,正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学史外部环境的要求在逐渐减弱,身份认同才使得史家主体意识能够逐渐强烈起来,准确定位的身份也才使得他们的心态更加平和起来,他们撰写的文学史也就越来越看重自己的特色。
当文学史写作走到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范先生的这部鸿篇巨制的文学史,并回顾他前后20余年为完成此项工程而进行的扎实工作,不难发现它已经填补了传统现代文学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范先生治文学史的意识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1980年代初期领衔国家重点项目,并以此为特色申报博士点,先期出版系列资料编选、作品大系成果,以及主编130万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⑧ 巨制的问世等,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获得了各种高层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奖项。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新文学史不约而同地增加“通俗文学”章节,这就足以证明范先生的存在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这部范先生20余年执著从事的史著,其价值和意义还远不在于文学史给了通俗文学的“正名”、“一个说法”、“找回那一半”等等现有评述,而是作者完成了与前面文学史编写者相同经历体验过程,相同身与心的变化调整过程。他有过从“任务”、“使命”到“岗位”意识的工作姿态和写史经验,现在进入了从教授岗位退休的新角色认同。“我退休后没有别的什么能赖,但我成了‘时间富裕户’——‘光阴大款’,‘时间就是本钱’,我可以将‘本钱’投到精耕细作的二期工程(指《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作者注)中去。”⑨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尊重时间,尊重生命为前提的文化人,一个有着明确学术理念和丰厚知识积累的学者。他不在乎外界说什么,也不受限于岗位对于他的规约和定量,产生了可以在时间和知识的海洋中自由探索的真正的学者心态。这是社会的安定和谐与自身的安静平定营造了读书写作,毫无功利的治史氛围。正因如此,这部通俗文学史的成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文学史著作内容的尝试形式的改变,而是在文学史书写中由于作者身与心的姿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自由学术空间,给我们提供了多有启发的文学史写作新思考、新方法、新经验。
二
历史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历史。当然,当史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史家时,其立场和心态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不同境遇下史家历史观的不同,每个史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理解历史的路径。至今,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太多的话题和遗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史家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需要文学史承担的角色大大超出了文学史本身。在“任务、使命、岗位”意识下,王瑶、钱理群、洪子诚、陈思和等史家努力完成了富有个性和特色的文学史,还一直能够被读者不断谈起已经是不容易了。从范先生的文学史写作实践和他对文学史理论的思考来看,一方面由于他本人经历过与上述史家相同的文学史写作过程,不乏对过去经验的吸收;一方面又相对比较早地转换了角色,无岗位压力(退休),使得他有富裕的时间更有不受任何干扰的空间,去反思他走过的学术之路,清理他积累的丰厚史料,理解他心目中的通俗文学的历史。“要自己独立写出一部晚清民国通俗文学史来,我过去主编过通俗文学史,但主编与自撰是不同的。”⑩ 范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总结出这种不同是什么,但是这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简称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下同)却已经说明了一切。从范先生作为自由学者的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这部通俗文学史努力在找寻自己描述文学变迁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对象的寻找过程,是文学史生态的还原过程。文学史写作最重要的是文学生态意识,而非文学观念先行。范先生最初并没有要写文学史、打捞被遗忘的通俗文学作品,文学史产生于文学现场和历史史料生态完整把握之后。史料编选、小报期刊、作品的收集整理,乃至插图的作家肖像、创刊号的原始版本寻觅等,这些实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从而奠定了文学史的丰厚基础。这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前就有《古小说钩沉》一样。“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是文学作品选编在先,而经过历史的积淀越加呈现出这些史家之眼光。文学生态是什么?本质上是有作家个体的写作和群体的活动而发散、生成的文化语境,一个互动平台的文化场域。插图本通俗文学史最大限度地逼近了现代文学生产、消费、传播之完整生态。读这一文学史,著者在现代“通俗文学”爬梳剔抉的清理和历史理性的辨析中,呈现出史家构史、述史的独特风采,这种文学史的视阈和理论的思考,应该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现代名家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前辈文学史家著作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也与新时期以来黄修己、洪子诚、杨义、钱理群、陈平原、陈思和等文学史家一样,予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具有独特的学术创新。
其二,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立足文学本身构史,改变文学史“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叙述模式。这里并不是说通俗文学是市民化、民间化,或非启蒙、非精英等简单划线和归类,而是超越了主流、支流独立意识的文学史书写。范先生在这部文学史中,表面看仅仅侧重以小说、小报期刊、电影为构史中心,有失文学史的完整性。但是,这恰恰表现了史家尊重“现代通俗文学”生成的本体世界,通俗文学的流传不在贵族的诗歌、散文样式中,甚至也不是非要出现现代话剧文学创作的形式。现代话剧是思想启蒙者引入的“舶来品”,应该说一开始就与通俗无缘。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书写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断代、文体样式、群体、思潮演变史等既定文学史叙述模式,但这些在这部通俗文学史中统统被打破了,通俗文学回到了它自身的清理和陈述之中。确切地说,没有从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出发,而是回归文学的历史,即作家作品基础上的通俗文学类型,构置文学史的平面,而在作家作品的独到感悟和睿智解析中包裹着史家深沉而理性的历史思考。
其三,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第一次还原了现代通俗文学叙事主体的位置,造就了一种面向多元读者的文学史著范本。我认为这一点是范先生写史与过往文学史最大不同之处。正是文学原生态和文学本体中心意识的坚持,使得寻找现代通俗文学自身轨迹和问题成为了叙事重点。这部通俗文学史叙事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没有从外部变革缘由中确立起源、发生和发展的通俗文学史的叙述线索,而是通过《海上花列传》的六个“率先”的开创性细致辨析,寻求出一条可视文本的通俗文学与中国现代化之接轨。这较历史教科书生硬划线更容易让人接受。2、没有史家全知全能意识,如并不急于判断谁是大家、并不断言文学史一定是进化发展,而是有什么就写什么,尽可能地逼近文学史原貌。小报、期刊是通俗文学的生存基础,范先生就用了五、六个章节在重点清理;20年代因是通俗文学的繁荣期,就用了七、八个章节论述作家作品,相比之下,30、40年代只有三、四章的篇幅。与已有的文学史体例相比,少了必然性、模式化的书写格式,更多了历史的鲜活和文学的真实。3、写通俗并没有唯“通俗”而独尊,不以俗与雅,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主流与边缘等二元对立叙述,坚持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多元共生之观念。通俗文学长期被遮蔽的本质根源正在于文学史一元观。比如,《新声》与《小说月报》两杂志在1921年对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丰富而复杂内容的揭示,在现在新文学史一面之辞中是不可能看到的。还有1909年《小说时报》上陈景韩《催醒术》小说的发现,并没有否定《狂人日记》的深度和价值,却体现了对“狂人谱系”的呈现和联系。还有将徐舒、无名氏、张爱玲、张恨水等新文学作家与通俗文学作家置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对此,范先生诙谐地说:“是文学领域的‘一国二制’”。实为文学雅俗合流、共生共存的典型案例。
其四,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写作标志着“文学史的重写”从理论探讨到实践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关于文学史的写作,很多学人一直在探讨专家学术型、教科书型、普及型等多种类型的可能,谋求文学史的多样性叙事。这些年,因为文学史的著者或曰史家主要来自在岗的学者教授。而文学史的需求者主要是接受知识的学生,所以,文学史的重写总是徘徊于教科书和学术专史之间,造成彼此互不认可的尴尬局面。现在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范先生的身份虽是教授,但不在岗位,这使得他的心态平静而超然,学者的本能又使他多了一些史家的自觉和严谨,更能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真正的文学史个性化不在文学史自身内容的类型差异,更在于如何呈现文学史家的心态,同时史家不能有先验的观念,而应该平静地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耐住寂寞打捞归理历史,沉下心来体验和理解历史,真诚地与历史对话。范先生治史吸取了前辈史家尊重史料客观性的经验,又非常注意从史料学把握文学进程,真正进入海纳百川、多元治史之境界。
三
范先生治史仅仅是通俗文学史的个例,还是具有普遍的文学史写作的意义?今天我们谈论更多的是范先生拓荒通俗文学,可是文学史的任务不只是在填补文本或史料的空白。文学史理论也不在阐释文学史写作的ABC,或者文学历史如何可以多元编排等等。范先生的治史经验提醒我们“文学史”的范围不止于“通俗”文本的补缺,给近现代通俗文学一个名分。范先生以自由学者的治史心态,将某些文学史规律性的问题浸透于历史本身还原性的追寻之中。他注重对通俗文学机制的整体运作中一些特殊性现象的探索,对文学进程给予某些具有启发性的解释,最值得文学史研究者认真总结。
文学史的描述方式和作家作品的判断,是文学史写作的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许多文学史已经约定俗成以历史为线索、以文学为标准来叙述文学史时,必然形成了今天统一模式的教科书和大同小异的各种版本。文学史不是文学与历史两者的相加,文学与历史也不是一个主观一个客观的区别。文学史的特殊性我觉得是其包容历史元素的文学文本辨析和理解,或者是其过去痕迹的文本人文性观照和镜像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的写作就不应该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范本,即便是教科书也应该针对受众的不同而写,应饱含撰史者情感和主体意识。一直困扰史家的问题是历史中客观性内容的一面是否就可能被削减,历史可以被任意地主观化?我是认同这样一些回答的。美国著名的新批评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文学史“作为一种艺术来探索文学史,就是要把文学史与它的社会史、作家传记以及对个别作品都加以比较和区分。”“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这个过程。”(11) 德国当代文学理论家汉·乌·古姆布莱希特在《文学史——消失的总体性的片断》中说:“‘历史’与‘文学’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史。”“它们都使‘文学’脱离了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它们都把文学视为认识这个总体性的中介,这一中介摈弃了那种文学即历史的‘征象’的观点,为发挥其无与伦比的认识价值,它几乎无需专家的阐释。”(12) 如果说理论家的表述还很抽象,那么再来看看文学史家在写作的实践中又是怎样理解自己的文学史的。这里选取国内三种现代文学史为蓝本来阐释我的观点,并与范先生的文学史相比较——之所以选取这三种文学史,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它们至今为止已经被读者认可,有一定生命力;二是它们都有明确的文学史理念和实践,无意中与国外文学理论的观点相契合。
1947年蓝海(田仲济)完成《中国抗战文艺史》一书,其时由于文艺中心由集中到分散,以及交通不便等许多原因,抗战文艺史料面临着难以保存的危险。“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便是企图弥补一部分缺陷,保存一部分史料,使她不至全部失散”。而为了治史“不至失真,在写作时,我力避发抒自己的主张,尽量引用各家的意见”。(13) 这是国内第一部现代文学的断代史,已被学界认为“现代文学史研究上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研究抗战文艺史必读的入门书”。(14) 1989年陈平原出版《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给自己定下的写作路子是“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学史,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变”。(15) 正是这一写作原则使它成为最早在国内现代文学类型史上有着重大突破的史著,它提供了重新梳理从晚清到五四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典型案例,其意义绝不仅仅在小说史本身。2008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版)问世。1984年他出版“简史”,1988年二次修改,现在是又一次大的改动。这是一部历经20余年读者和学界反复审视,更凝聚了作者本人文学史写作实践和长期思考的现代文学史。第3版不是简单2版的重新印刷,“我在‘以人为本’思想启发下,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全人类性’命题,希望从‘人的觉醒和解放’的角度来审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让人们看到一种文学史阐释的实践”。(16) 史家以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再次尝试和改写文学史写作之路,令人耳目一新。
综合上述,这三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写作,之所以具有永恒的学术生命,其核心所在,既分别在史料的基础(田仲济著《中国抗战文艺史》)、文学史现象的把握(陈平原著《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文学史观的尝试(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版))方面各有独特见长,又在每一部文学史写作中将三者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范先生的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写作,甚至超越他之前的文学史经验,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于其厚重扎实的通俗文学史料基石,准确切入和归理通俗文学自身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以及作者心中久存的“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的努力实践,通过通俗文学发生、发展的辨析,真正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生态。为此,这一共同的文学史写作经验证明其三者是文学史理论建构的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这是之一。之二,这几部文学史成功的探索和实践,说明文学内在整体运作机制的尊重和文学历史自身演变规律的把握是相互联系的。且不说他们统一的注重占有史料上的用心用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自己文学史描述的话语和路径。抗战中崛起的各种通俗文艺与新型文艺,以及报告文学所直观地揭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新发展的路向,呈现出文学史的别具一格,更贴近文学历史的真实。由小说市场的拓展、集锦和片断的结构类型、文白并存的体式等形式变化镶嵌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交汇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而托起了现代新小说的诞生。描述小说史,尤其清理一段转型期的小说史,走进了文类自身的文学现象,也就还原了她生生不息的历史河床。同样,范先生的通俗文学史辨析现代传媒制造的小报潮和文学期刊三波高潮,精细地解析通俗文学的作家作品,并配置一幅幅弥足珍贵的插图和照片。这不正是找准了一个现代文学史具有典型案例的“总体性的中介”吗!黄修己的“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文学史观的探索,固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也可以讨论,但是通史的13个章节列目分期不落同类文学史的窠臼,自成体系,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概言之,这些鲜明个性的文学史著作,以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和认识,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史描述方式,也就是真正进入了文学与历史的内在整体关系的探寻,从而尝试性回应了古姆布莱希特所说的“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关系史的阐释和梳理。最后,再次强调我的观点:这几部文学史的成功,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恪守自由学者(心态)姿态,在不自觉中探求了文学史写作的自觉。田仲济定位战时写作文艺史的原则,不失真,保存资料,正是严谨学者的治史;陈平原虽然在岗位写小说史,本质却是文学文体研究的学术追求;黄修己在接近退休时完成了再改自己文学史的任务,所得、所思、所感集一个学者“快要半个世纪了”(17) 之学术大成。正是这样的姿态成就了文学史的自觉,文学史要想真正区分社会史、思想史,必须在此境界中才可能像探索艺术一样研究文学史。
注释:
①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② 杨义:《文学研究走进21世纪》,《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④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⑤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64页。
⑥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⑦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代后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435页。
⑧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版。
⑨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序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⑩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代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8页。
(1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2-293页。
(12) 凯·贝尔塞等著:《重解伟大的传统》,黄伟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4页。
(13) 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上海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165-166页。
(14) 钱理群:《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
(15)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卷后语》(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6)(17)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