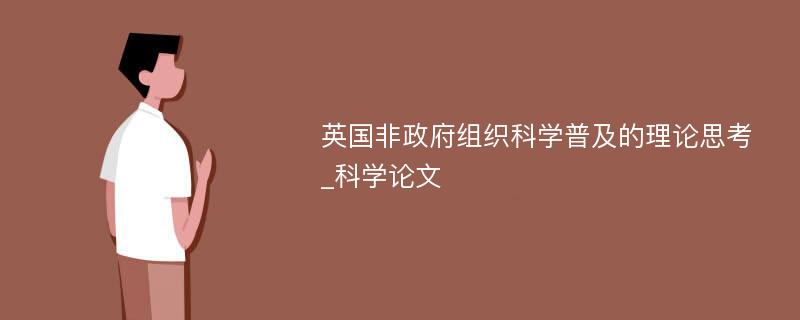
英国非政府机构科普工作中的理论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政府机构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06)01-0047-05
在英国的科普工作中,非政府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与中国不同,在英国,很少有“科普”一词,他们更多运用的是“公众理解科学”。如皇家学会除了做了开展或者参与大量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工作外,在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方面也有新的突破,从而为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这里则重点分析一下英国非政府机构的公众理解科学工作中所体现出的理论观念。
1 皇家学会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开创了英国的科普理论先河
向公众传播科学总与科学的自身发展紧密相连。自从科学产生以来,不同领域的学者一直探求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然而表明公众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明确标志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英国才开始有意识、有组织地研究如何向公众传播科学。1985年,皇家学会发表报告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1]。报告发表后,政府陆续开展或者委派其他机构开展科学家的科普职责、科学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公众理解科学的途径由“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逐渐转向了“科学家与公众进行交流对话”,目的是要消除科学界与公众之间久已形成的疏离感。不少大学还开设了科学传播专业,培养科学编辑、记者等。著名高校,如牛津大学还设有“公众理解科学教授”的职位。
报告认为,改善公众理解科学是国家繁荣昌盛、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以及丰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大多数人都不是科学家,但是科学发现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如同喜欢音乐的人不一定就是演奏家或者作曲家;而科学也是如此,不一定非得是职业科学家才能享受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喜悦。”[1] 报告就公众理解科学的发展针对不同的对象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这些对象包括科学共同体自身、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最后,报告还提出,为了充分体现皇家学会在公众理解科学工作中的突出作用,皇家学会有必要成立一个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其责任就是:对公众理解科学的进展以及它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进行监控并对其作出评估;向科学研究机构提供关于如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建议和指南,同时也对皇家学会的活动进行监督。
“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第一次对“公众理解科学”做了明确的定义,在世界科学技术普及史或科学传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不断被人们引用和提起。这份报告最终促成了1986年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研究院和英国科学促进会联合组成的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PUS)。
尽管这份报告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措施因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社会方面的发展变化,已经不适合现在科普的发展了,但是这份文献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并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态度的跨国比较研究开辟了道路。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公众理解科学被纳入到政府所考虑问题范围之内,并公开宣布了它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工程与技术中的责任。
2 两个重要的调查
从“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发表以来,英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以及科学家在公众理解科学中的重要作用也引起了重视,甚至还为此做了多项专门的调查。这些调查进一步深化了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工作。
2.1 “科学与公众”对公众展开的科普调查[2]
(1)调查背景
长期以来,向公众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然而,不管哪种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活动往往倾向于向公众提供科学事实,而对科学的伦理、社会及相关的政策问题则讨论得非常少。公众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更没有得到科学传播工作者的重视。实际上,关注公众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将有助于科学传播工作者更好地理解相关人群,从而能够有利于促进公众对相关讨论的参与。调查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和兴趣,为如何让广泛的公众参与科学争论提供了参考系。
鉴于此,在科学技术办公室(简称OST)和威尔凯姆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① 的联合赞助下,一项旨在帮助科学传播工作者了解公众需要的科学信息的研究于2000年开始进行。这一调查同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和政府白皮书“实现我们的潜能”被认为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磋商时期开始的标志[2]。报告认为,目前科学政策中的问题是如何开展科学家、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并在政策决策中考虑公众的观点。政府与威尔凯姆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让公众参与进来,这就意味着需要倾听公众的声音,而不能仅仅听那些被证明是“科学的”声音。
(2)调查对态度进行了分类
此项调查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对英国公众进行了态度分类。通过将公众对40道态度问题的回答进行的因素分析,定量研究调查将公众划分为六类群体。分别为:有信心的信徒(confident believers)、技术信徒(technophiles)、支持者(supporters)、忧虑的人(concerned)、拿不定主意的人(not sure)以及认为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not for me)。
有信心的信徒:这部分人非常积极、自信,对政治及科学带来的利益都感兴趣,愿意遵循规则体系,并且相信他们能够影响政府。这些人往往比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年人居多,大多生活在英国南部。这类人占17%。
技术信徒:这部分人一般在科学上受过良好教育并支持科学,但对政治家表示怀疑。他们相信自己知道如何获取所需信息。这类人占五分之一,占最多数。
支持者:这类人较年轻,他们往往对科学、工程与技术表示“震惊”,不过相信自己能应对飞速的变化,也相信政府能控制事态。尽管他们如其他人一样,表示对医学感兴趣,但是他们往往对物理学更感兴趣。这部分人占17%。
忧虑的人:这部分人多为女性(60%),他们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所有热点问题表示关注,他们也知道科学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小孩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对权威则表示怀疑。从社会层次、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来看,他们代表着一般公众,但是他们往往更以家庭为中心。这部分人最少(13%)。
拿不定主意的人:这部分人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最低。他们既不“反对科学”,也不“支持科学”。这一群体占17%,往往家庭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最低(有点手艺或者没有任何手艺的工人,生活依靠社会福利)。他们的观点往往不成熟:既不“反科学”也不“支持科学”。这主要是因为科学的好处并没有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认为跟自己没关系的人:他们对政治和科学不感兴趣,但是对科学带来的好处比较赏识。这一群体占15%,主要包括那些年龄在65岁以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和社会低层的年轻人。同拿不定主意的人一样,这部分人对政治和科学都不是特别感兴趣。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赏识科学给未来带来的好处以及对年轻人的重要性。
(3)调查中的发现
这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英国人为科学成就感到“震惊”。他们看到了科学带来的好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认为科学与技术正在为健康、轻松和舒适的生活创造条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声称他们对科学不感兴趣,也不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同意认为科学成就被夸大了。五分之四的人同意认为,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英国人有必要开发科学技术。给基础研究投资的必要性也同样得到了重视:72%的人同意认为,虽然基础研究不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对其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
不过对于科学应用以及社会是否能够控制科学的担忧仍然存在。在问到受访者是否认为科学带来的好处大于它们带来的害处时,他们的态度模棱两可:43%的人同意这样的观点,17%的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没表态。
对于政治家支持科学的目的同样存在着模棱两可。受访者中有近一半公众(43%)同意认为政治家支持科学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近四分之一的人没有表态,而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对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控制科学的问题,也存在着担忧,只有十分之三的公众不同意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意味着政府无法合理控制它,而有十分之四的人同意这种观点,说明某种程度的模棱两可。
关于研究机构可能是“关起门来”做事也有担忧。近三分之二的人同意认为那些约束法则无法阻止研究工作者的这种行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科学家好像在做新实验时不考虑实验带来的潜在风险。不过只有36%的人担心科学正在失去控制,没有办法阻止它。
一般来说,科学家备受尊重:84%的人认为科学家与工程师给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科学与工程是非常好的职业,科学、工程与技术将为厚待提供更多的机会。尽管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科学家想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但是同样比例的人同意认为科学家还是应该更多倾听普通人的看法。
(4)调查的意义
我们知道,某些科学传播活动适合某一群体,而不适合其他群体。这次调查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使得进一步的科学传播活动能够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从而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科学讨论提供一个框架。
这一调查报告分析了人们对科学所持有的不同态度,目的就是要给未来的科学传播政策和实践策略提供信息,并试图通过调查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和兴趣,为促进公众参与科学争论提供指导意见。通过调查,报告认为,要想实现真正的对话,科学争论就必须具有包容性,即,需要在争论中考虑到公众的观点,而不能让公众认为其权利被剥夺了。开展科学家、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并把公众的观点考虑到决策中,这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说,任何调查背后都有某种理论体系做基础。而这个以公众为对象的调查,其理论基础则体现了“科学地理解公众”的思想。以往,不论是英国,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的调查几乎都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即公众掌握科学知识的调查。而这一调查则突破了这一传统,首次开始关注公众对科学所持有的态度,从而公众也就成了被理解的对象。这一调查的意义在于给公众理解科学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即,在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中,公众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科学知识、科学信息的对象,他们对科学也应该是有自己的偏好的。只有真正了解公众如何看待科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公众理解科学。
2.2 科学家在公众争论中的角色[3]
(1)调查背景
如果说在英国的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中,公众正在转变其被动地位的话,那么,科学家在这一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则几乎一直未发生改变。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科学家在这一关系中的角色已经得到了理解。作为科学的“创造者”,科学家无疑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调查科学家对公众理解科学的认识和看法,作出相应对策,是做好科普工作的有效途径。而过去,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调查对象经常是公众,却很少有针对科学家的调查研究。“科学家在公众争论中的角色”这一调查报告则给公众理解科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它首次调查了科学家如何看待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在世界科普调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调查是MORI(market &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受威尔凯姆信托基金会的委托,于1999年12月到2000年3月期间所做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调查对象则是那些得到学术团体、慈善机构和工业界资助的科学家。
此项调查的目的是要了解:科学家是否认为他们最有责任、也最有能力向公众传播其科学研究及其影响;他们认为提高公众理解科学中的作用是什么,科学传播过程中有何障碍,以及如何才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众理解科学工作中。
(2)调查中的发现
调查说明,科学家认为他们和一般公众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如科学家认为,他们在自己眼中的形象要比在公众中的形象好;公众主要信任媒体、慈善团体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一些团体所提供的关于科学信息,而科学家自身则最相信那些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的科学信息。多数科学家能够认识到公众理解科学所带来的好处,并能认识到妨碍公众理解科学发展的因素。其中四分之三的科学家认为公众缺少科学知识、缺乏科学教育或缺少对科学的兴趣是一个障碍,而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认为媒体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关于科学研究带来的社会和伦理影响方面的传播,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向决策者和行外人士传播其研究及其社会和伦理影响。然而,很少有人认为科学家最适合这项工作。还有相当多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发表研究成果时,应报道其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影响。但是很多科学家认为他们因受工作时间的限制,很少传播其研究工作,甚至有时候连开展研究工作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所以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对向公众传播科学研究的社会和伦理影响负有主要责任。然而,较少有科学家认为他们最适合做这项工作。调查发现,有一半多的科学家参与过科学传播活动。相比之下,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传播其研究的科学事实和影响的人以及那些接受过培训的科学家比较有可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同样,那些有教学与研究经验的科学家,以及那些有过与公众交流经验的科学家都更有可能参与这样的活动。
关于科学家科学传播能力方面的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科学家认为能够传播科学事实,尽管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具有能力。但是当科学家被问及他们如何看待传播研究带来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时,他们不太自信了。有62%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够向公众传播工作中的社会和伦理影响,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在这方面非常有能力。多数科学家既没接受过与媒体打交道的培训,也没有接受过与公众打交道的培训。
(3)调查的意义
这一调查让我们重新对科学家在公众理解科学中的地位做了反省。作为公众理解科学学者或者我国所说的科普工作者,在做具体科普工作或者公众理解科学的同时,应该首先了解这一工作中的各种角色。毫无疑问,在公众理解科学中,科学家是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是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工作者所必须深入了解的一个重要群体。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公众理解科学,他们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如何作用,他们如何胜任这份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也是每个科普工作者和公众理解科学工作者所必须了解的。通过调查了解科学家对其在科学普及中地位的看法,英国科普界就能具有针对性地充分利用科学家的科普潜能,而不是在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下,让他们参加一些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适合的科普工作。这样,处理科学家、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容易了,对于实现公众理解科学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而对于我国的科普调查工作也很有启发意义。
以上两个调查互相补充,不仅仅为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提供了调查数据,更重要的是,它从此使公众理解科学学界开始关注科学家和公众这两个不同群体如何看待公众理解科学工作、如何看待科学了。公众理解科学界会对公众和科学家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也让这两个群体之间加深了解。在科普活动中,如果不事先全面了解公众的忧患得失,不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其他,就难免会使科普活动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同样,对科学家有了深刻理解,就可以避免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失误,更有利于科学传播工作的开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调查所赖以支撑的科普理念:除了公众理解科学外,公众和科学家同样需要被理解。而这样一种理解是公众理解科学的前提。
3 总结
科普需要理论指导,没有理论的科普就像无头苍蝇,由于失去了方向,而不知道自己要飞向哪里。而英国的众多科普实践本身已经体现出很多科普理念。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理解公众成为公众理解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问题在转基因技术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英国公众抵制转基因食品的情绪相当强烈,政府在2003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虽然转基因农业能给英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但由于公众的抵触情绪,这些利益在短时间内尚无法体现。除了新闻媒体对引发或夸大这种情绪难辞其咎外[4],这一事实还说明,在科学传播中,作为利益群体,公众和科学家同样得到理解。
而自从“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发表以来,英国非政府机构在公众理解科学工作中贡献显著,他们都表现出对科普的极大热情和反省。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公众理解科学看成是对自身没有意义的工作,而是竭尽全力做好这份工作。他们愿意而且能够把科普当作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他们用事实和行动阐明了科普中蕴涵的理念,从而为更好的实现公众理解科学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威尔凯姆信托基金会是一个资助研究的独立慈善团体,是按照威尔凯姆(Sir Henry Wellcome)的遗愿成立于1936年的,其资金也来自威尔凯姆的捐赠,其使命是“培养并促进目的为改善人类和动物健康的研究”,它主要投资于医学研究。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它还调查当今科学研究带来的医学、伦理和社会影响,并为促进科学家,公众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