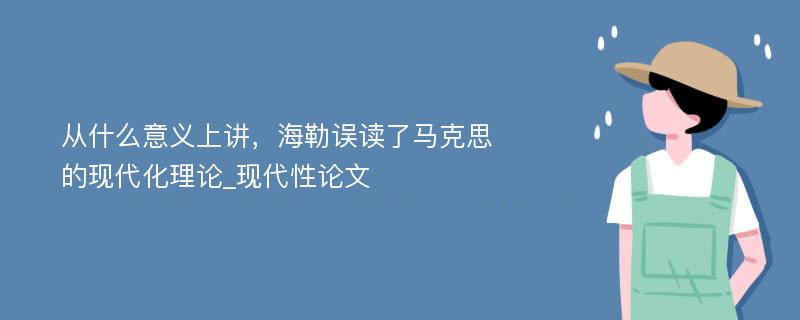
赫勒在何种意义上误读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误读论文,理论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现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汉娜·阿伦特哲学教授”。作为卢卡奇的学生和助手,她曾是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成员,并在哲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方面建树卓越。1984年,赫勒在国际著名刊物《论纲十一》(Thesis Eleven)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与现代性”(Marx and Modernity)的论文,详细探讨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其中既有肯定褒扬之意,也有指摘质疑之辞。赫勒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理解与质疑多为误读,这一方面源于她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对现代性所作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也与她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有关。辨析这些理论的真伪,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能有效抵御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一、未来指向的动态社会及其工业化逻辑
现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社会,这的确是马克思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P275)赫勒认为马克思精准地把握住了现代性的实质,在她看来,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正在于前者是矛盾的,后者是同质的,动态性构成了现代性动力和现代社会格局的重要特质。马克思的确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动态性将有利于保障现代人各方面潜能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取代封建主义(前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当然,马克思从来不会忘记在价值层面上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谴责,他多次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违背人性的一面,与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事业相抵牾。马克思这种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是赫勒始终无法理解的。赫勒还认为现代社会具有一种未来指向性,作为实存(“是”),它总是指向一种未来状态(“应该”)。这个说法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倾尽心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并撰写《资本论》就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是”必然因其内在矛盾而走向灭亡,取而代之的不是别的,正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应该”,可见现代性必然内含“是”与“应该”的张力。
赫勒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紧密相联,在他的理境中,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具有过渡的性质,终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她将马克思的观点归为三点:“存在于19世纪的那种现代性或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必须经历一场实质性转变;工业化的无限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联姻不能持久;工业化将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设限。”[2](P47)由此出发,她愿意承认如下事实,即现代性不等于资本主义,正是后者为现代性的发展设置了羁绊,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限制将被彻底摧毁。如果由此出发断言赫勒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完全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早在《历史理论》(1982)一书中,赫勒就阐发了自己关于现代性的独特见解,她提出一种关于现代性的“三逻辑论”,认为现代性并非受制于某种单一的逻辑,而是由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和制造工业三种逻辑构成[3](P283)。由此出发,她否认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P272)的说法,在她看来这种观点假定了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逻辑。更进一步,赫勒区分了市民社会逻辑内部的两种亚逻辑:一种是市场、私有财产排他特性、不平等与统治增长的普遍化;另一种是个体平等的自由(人权)在权力民主化、平等化和分权化过程中的展开与加强。①在她看来,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只涉及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两种逻辑,市民社会的第二种逻辑完全缺失,马克思将革命策略建基于现代社会根本矛盾的消除之上,同时又将根本矛盾简单归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矛盾,于是民主和自由便被前两种逻辑彻底掩杀了。我们认为,赫勒之所以强调现代性有三种逻辑,并不仅仅是想强调历史是由多元决定的,其深层目的还在于淡化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强调市民社会第二种逻辑的重要性。毋庸讳言,马克思决不会避而不谈自由与平等,但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如他所言,“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4](P264),同样,平等的观念也是历史的产物,抽象地理解平等必然会陷入荒谬。赫勒的问题就在于过分突出了民主的作用,在她那里,民主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凌驾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逻辑之上的“绝对”,一种新的神话,这就明显悖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还具有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明确的阐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P275-276)赫勒将现代社会格局在全球范围的布展喻作“蒸汽压路机”,认为“它一旦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确立,就会碾过所有的前现代文化和格局”[5](P77)。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的问题上,马克思与赫勒的态度迥然相异。马克思始终坚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这一过程将给人类带来无尽的苦难,并使财富成为贫困的源泉;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工业化的拓展使普通劳动人民走进公共场合,登上政治舞台,眼界和觉悟得以空前提高,社会关系得以空前拓展,自由得以空前扩大。总之,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和大工业具有相互矛盾的影响,它们既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最终将会给人类带来进步和自由。赫勒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比较悲观,她认为现代性既可以把人们带入天堂,也可以把人们引向地狱,未来快车的终点站既可以是共产主义,也可以是奥斯维辛或古拉格。总之,赫勒认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是不可预知的,人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信守承诺,为共在负责。不难看出,赫勒这种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异质的。
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与功能主义读解
区分合理性与理性化是韦伯的贡献。合理性 一般用于解释人的行为,理性化主要用于组织和制度层面,依据一定的规则,组织在运行时总是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偏离价值。韦伯对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专门作了区分,前者主要指由价值意识(宗教、伦理、道德、审美等)决定的行为,后者主要指内含预期目的及实现手段的工具性行为。在现代社会,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通常是割裂的,这主要表现为理性行动较少受到价值观念的引导,这也是现代性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理性化”或“目的理性”这样的概念,但却对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进程进行了批判:一方面他认为工具理性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个体自由的演进;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将会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人类深深地陷入异化境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探讨了理性化,但他却试图将康德化的韦伯与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嫁接在一起,最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概念。赫勒作为卢卡奇的得意门生,基本沿袭了这一错误倾向,她指责马克思对待理性化的态度含混不清:“一方面,他对那些不再与价值相关或从属于价值的效率大加赞赏,甚至称赞李嘉图对‘为生产而生产’的偏袒;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同韦伯一样对理性化表示担忧……最终不愿承认生产应该与一切价值脱离关联。”[2](P48)赫勒的这一说法恰恰表明她自己不懂辩证法,同时也暴露出她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狭隘性。我们认为,马克思对理性化的辩证解读其实包含两条线索:一个是从客体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进程所作的科学考察,其主要目的在于理解社会,分析统治社会的规律;另一个是从主体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进程所作的道德(价值)批判,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人性方面。这种看似“含混”的致思构设,恰恰蕴涵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之间的内在张力,彰显着马克思革命的批判精神。囿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范式,赫勒极力擢升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她显然没有看到,1845年之后马克思已经从人本主义的哲学人类学走向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正是这一理解上的缺陷,导致她最终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从功能主义角度理解现代性是赫勒理论的一大特色。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曾将前现代社会称为分层社会,现代社会称为功能社会。沿袭这一分析思路,赫勒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了全新解读。在她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范畴,一个人最终属于哪个阶级,要看他(她)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就这一点而言,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在前现代社会,一个农奴的命运在出生那一刻便被决定了,他(她)一辈子只能是农奴,除非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才可能获得自由;现代社会则不同,一个工人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判定标准就是他(她)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功能)。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赫勒举了一个人们生活中乘公交车的例子:假设在站牌候车的人可以任意选择一辆公交车乘坐,人人都想坐一辆更好的车(有座位且车内干净),但好车的出现是完全偶然的,因此对所有人而言乘坐好车的几率完全相同。赫勒用这个例子无非是想表明现代人必然处于偶然性中这一事实。她常用“信封”喻说来描述这种偶然性:现代人总是被抛入这个世界,该过程完全是偶然的,如同一封没有注明地址的信被投入信箱一样,它最终被寄往何处是不得而知的。总之,在赫勒眼里,偶然性既是人类的宿命,也为人类带来了自由。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看待偶然性及其与自由的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前后期思想是有变化的。在博士论文中,从“自我意识”哲学出发,马克思给予偶然性充分的重视,认为它体现着自由意志,可以为人们的行动自由提供论证。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实质恰好在于一种“偶然性的统治”。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6](P515)因此,赫勒对现代性的偶然性大加赞赏的做法,恰恰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资本论》最后一章,马克思提出“什么事情形成阶级”的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从功能主义和偶然论的视角出发,赫勒认为马克思基于劳动—资本关系的现代性分析是片面的,她反对将阶级限定在经济领域的做法,而是将它首先看成一个与民主紧密相关的政治概念。依她之见,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要素既不是经济状况,也不是政治条件,而是超经济—政治的民主,这就又回到关于市民社会第二种逻辑的论述上来。笔者认为,赫勒辐辏于民主概念,赋予其激进的内容,无非是要摒弃马克思的经济首要性原则和暴力革命论,因此,她必然心契于拉克劳和墨菲的如下论断:“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7](P198)当然,这已经是标准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了。
接着这一分析思路往下走,赫勒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人类解放事业天然代理人的说法不能成立。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拉克劳相似的论断:“工人阶级——像所有其他成分一样 ——是一种社会作用力,但此一作用局限于它自己的目标及可能性之内,它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普遍阶级’,并非是全世界人类解放的必然代理人。”[8](P67)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无法对此观点进行详尽的批判。正如密里班德(Ralph Miliband)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轻觑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的“优先原则”应基于如下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其他的集团、运动或者力量会有哪怕是很小的能力,能够如同工会工人一样向现存的权力与特权的组织发起有效的和强大的挑战”[9](P34)。尽管赫勒有时也强调历史的冲突特性并崇尚一种激进行动,但她的激进行动并不是一种革命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激进的民主运动。另外,赫勒的阶级概念也多与马克思相扞格。受汤普森(E.Thompson)理论的影响,她把阶级视为一个不间断的形成过程,既然阶级总是不定型的、在途中的,那么它就不能用来说明总体的社会。实际上,赫勒反对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她还反对具有普适价值的阶级概念本身,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普遍阶级,甚至说根本不存在可以揭示一切社会现象普遍基础的社会集体。确切些说,赫勒还是愿意保留阶级这个概念的,但她反对一切闭合的、普遍的、固定的阶级概念,因为这种阶级概念消除了一切社会反抗的可能性空间。正因如此,赫勒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表露出对结构主义的敌意,在她看来,结构主义通过寻求本质的结构制造了一个闭合的社会场域,根除了一切社会对抗的可能性,严重限制了左派的行动和政治分析能力,其根本祈向在于一种本质主义先验论。因此,只有脱离结构主义,拒斥“普遍阶级”,承认社会领域内对抗的多元性,在不同缝合点间进行有效接合,才能实现当前政治的根本转变。无需置辩,这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致思路径是完全一致的。
三、科学的魔咒与价值准则的多元化
强调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必然会认同“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说法。亲眼目睹并经历了二战带来的创伤,赫勒更倾向于站在悲观主义的立场上看待科学。与卢卡奇一样,她指责马克思将科学视为一种卓然独存于上层建筑之上的中性物的做法是一种“非统治的”、“纯化的”、“客观化的”知识论,指责“马克思从未想过科学将会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他分享了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宗教、政治和道德观念(不是科学)才行使着统治的功能”[2](P52)。在赫勒看来,现代性是这样一种社会格局,在这里科学大行其道,行使着解释世界的基本职能,人们相信“科学的”就是“真的”,这个着了魔的词汇可以激发出一种新的信仰,否认是其实际所是。通过合理化和最优化的概念,科学最终发展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与此相应技术想象成为统治现代人的支配性想象。②作为一个激进的学者,赫勒并不想让人们陷入绝望之境。阿多诺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果说阿多诺的名言贯涵着一种忧悒的悲观主义情愫,那么赫勒在《大屠杀之后可以写诗吗?》中的质疑则表明她实现了一种辩证的璞归:一方面,人们可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因为这场灾难足以让一切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烟消云散;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够而且应该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但只能书写萦绕于奥斯维辛周边关于沉默的诗。③赫勒之所以能够走出悲观主义与她对“诗”的独特理解有关,在她看来,“诗”代表着一种与技术想象毫无关联的反技术冲动,即一种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尚未泯灭的历史想象,它可以成为拯救人类的力量。总之,赫勒一方面认定技术想象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支配性想象机制;另一方面又指出现代人同时受到历史想象与技术想象的双重框范,任凭技术想象如何肆虐,人们总可以凭借历史想象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笔者认为,尽管赫勒在看待技术的问题上比阿多诺、海德格尔等人乐观,但并非没有缺陷,她最大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区分科学与科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用的关系,没能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剥离开来,这就难免将批判的矛头滑向物质生产这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这既与她对卢卡奇的盲目笃信有关,也与她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关,众所周知,后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批判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入手的。
现代性不仅促进了社会发展、制造了社会灾难,还导致了传统习俗和美德的丧失以及价值准则的普遍化。赫勒认为马克思总体上对现代性是持乐观主义态度的,通过细致比较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马克思将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视为消极的、反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彻底摧毁了这些观念,于是现代性便确当无疑地具有了一种历史合理性。对此,赫勒批判道:
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将在若干个不同方面执行普遍化的功能。他认为,资本主义将会统一全球: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所有国家将成为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在理论上支持殖民化的原因。资本主义将倾覆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业,从而为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扫清一切障碍。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个错误的预言。这种认为市场扩张将为现代性的出现提供充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是否应为该不足负责仍可讨论。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个由马克思创立的模式恰好是为了充当支撑其预言的理论工具,而非他用。然而,无论这两个概念中哪一个具有优先地位,都表明马克思没有打算考虑对于现代性产生同等重要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而这一点后来被马克斯·韦伯深深地强调了。[2](P53)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指认,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极大的误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确说过 “资本主义将统一全球”这样的话,但我们不妨揣度一下,当马克思称“资本主义将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时,他是在为之欢呼雀跃吗?当然不是。马克思要告诫我们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将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到全球各个角落,一方面给当地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但同时又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无数劳动人民陷入困苦境地。马克思从不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好的”,至少在价值层面上决不会这样认为。当马克思对我们说,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带来了人类进步,他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增加了个人的幸福,他只是想要强调,人们诸种需求和能力的扩展、社会活动和社会意识水平的提高,离不开资本主义市场和工业的发展,仅此而已,马克思决不会认为资本主义在其他方面也是进步的。显然,赫勒根本没有弄清楚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批判(抑或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从马克思对资本全球化进程的预测出发,她竟然得出马克思支持殖民化这一结论,真是荒谬之极。接着,赫勒又将批判的矛头向前推进了一步,直指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济首要性原则,她宣称马克思拘囿于历史哲学,根本无法回答“阶级为什么无法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在做什么”这一问题,认定市场扩张无法为现代性提供充足的基础,现代性的续存需要引入市民社会的第二种逻辑。更让人费解的是,赫勒还指责马克思陷入了一种绝对普遍主义,忽略了中产阶级、农民和殖民地居民等特殊群体,“总体上对政治问题反映比较迟钝,对民主政治的规划更是如此”[2](P53)。但事实上,马克思并未如赫勒所说从不关注特殊群体,并且常常缺乏一种民主精神。
最后,赫勒认为现代性将直接导致创造与阐释准则的消失,相对应的是,“对”与“正确”的概念将多元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点同样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摧毁了前现代社会一切特定的标准,艺术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主体,这种审美主体摆脱了一切传统宗教伦理的束缚,以自由人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中。马克思认为这种现代性悖论是历史性的,它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赫勒将现代性与真理的认识标准关联起来,目的是为了阐述一种多元真理观。在她看来,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一定会受到主体阶级立场的影响,一个阶级看上去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阶级看来则可能是错误的,因此现代社会的真理观只能是多元的、动态的。赫勒这种相对主义真理观由于否认了真理的一元性和客观性,必然会陷入自身矛盾中。
结语
赫勒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所有误读都源于她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误解。在她看来,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与其历史哲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从历史哲学(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出发,马克思一定会将伦理原则归于特定的经济(阶级)状况;另一方面,从现代性理论出发,他又将伦理原则归于社会的功能分工。赫勒的这一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诚然,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一定会将伦理原则建基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经济生活进程)之上,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原则,现代性理论也不例外,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要将伦理原则归于某种社会的功能分工,赫勒完全是在借马克思之口说自己的话。当然,赫勒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她为伦理学“松绑”,令其摆脱经济的束缚,为的是强调一种个性化的相对主义伦理学。与马克思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旨归的宏伟抱负不同,赫勒的伦理学是以康德伦理学为鹄的。它强调一种偶然性意识和伦理责任,反对一切历史必然性对个体伦理选择的蔑视,抵制所有自称拥有必然性知识的政党凭借手中特权对历史行动者自治权的篡夺。赫勒认为这种伦理学的实现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运动必须不再将自己视为绝对的,而是联系其他运动、社会和历史;第二,运动必须不再受自发意识控制,而这只有当历史不再是顺利进展的,而是进入革命或危机(新冲突)频发的时代才有可能;第三,伦理学只有在个体决定和实践作用不断增强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第四,要使伦理学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种对运动的意识、自觉和自我批判。[10](P28)大体上看,赫勒诉诸伦理学的初衷是为了抵制官僚主义,寻求一种真正的自由或自治,但她恰恰忽略了,任何个体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个体解放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与阿伦特一样,赫勒最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革命政治学,这个教训是我们应该反省的。总之,受卢卡奇、韦伯、康德、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影响,赫勒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解读必然戴着有色眼镜,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在她眼里至多是一种富有深刻洞见的片面性理论。但我们若能抛开成见,还是能在里面寻得一些有益启示的。
注释:
①参见Agnes Heller:A Theory of History,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2,p.284。另外,赫勒前后期对现代性三种逻辑的概括是不同的,在《阶级、现代性、民主》(1983)一文中,她将之概括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在《现代性理论》(1999)中,她又将之概括为技术、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以及政治权力。
②赫勒认为现代性有技术想象与历史想象两种想象机制,前者与行动有关,主要关注问题的解决,后者与回忆有关,主要关注解释和旁观者的创造,详见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③赫勒在文中详细探讨了四种沉默,它们分别是:无谓(senselessness)的沉默、战栗(horror)的沉默、凌辱(shame)的沉默和负疚(guilt)的沉默。详见:"Can Poetry Be Written After the Holocaust?"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pp.393~401。
标签:现代性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文化论文; 卢卡奇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