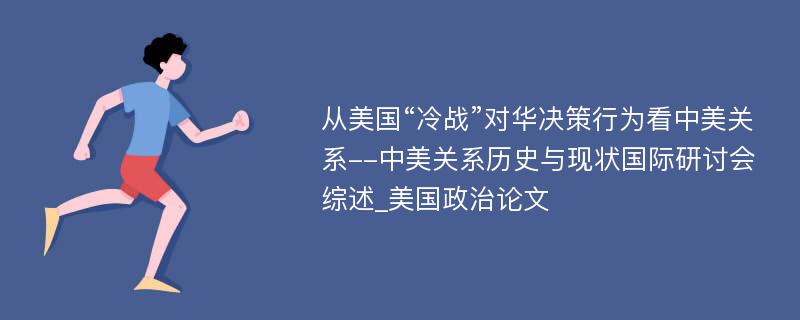
从美国“冷战”对华决策行为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美国论文,冷战论文,现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现行美国对华政策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冷战”思维与行为惯性影响,那么,华盛顿的“冷战”思维与行为规律究竟是什么?其到底在哪些方面影响着“中国政策”?两者间的“兼容”关系应如何通过实证方法加以描述?围绕着这些问题,30多名中国与旅美华裔学者在2001年1月9日至12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会上所宣读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历史分析法的核心是立足档案文献,以求作出“接近原来”的描述与判断。在过去的15年间,美国公布、解密了大量“冷战”时期关于中国的军事、外交、经济档案,特别是有关1945-1972年间的材料极为丰富。如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所存的包括国安会、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文件均已系统开放,其中“精华”已由国务院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分卷出版;尼克松时期的外交、军事部分虽还正在整理中,但美国国家档案文献局已通过“尼克松总统文献”项目将国安会文件提供给学者使用,其中包括最新、最具价值的洛德担任的“政策计划委员会”的文件卷。除了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献外,大量有关美对华政策的材料分别存于各个时期的总统档案馆,不少的个人文献则散存于国会图书馆、美国海军历史资料室、大学图书馆内。由旅美学者提交的论文,均不同程度地利用了这些档案,体现出“立论有据”。
毋庸置疑,单纯的历史方法有内在的局限性:决策行为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会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据此得出“普遍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则必须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假设”相结合。会议提交的论文将“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根据“对外决策论”的“动因(Driving Forces)”与“结果(Outcomes)”关联链,剖出十个政策分析面,并将单个的决策行为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检验”,以求得出接近“普遍意义”的推论。据此,论文得出以下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美对华战略考虑与安全政策。本人关于此题的论文提出:“冷战”时期的美对华战略决策存在着“结构”上的局限性与“主观”上的非合理性,因而在六个方面决定了政策结果的“非理性”:(1)在“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上出现严重混淆。在考虑中国时更多地以“威胁”定“利益”。结果,每当华盛顿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在朝“严重”方向延伸时,中国相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地位便随之“加重”;(2)美国相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认知威胁”的重要“坐标系”,这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中“人为夸大”利益或威胁的现象;(3)作为主导对华战略决策“话语”框架的美国式“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使得“理性选择”常常成为空谈与幻想,因为“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与思维阻碍了“现实政策”的择取;(4)军政关系“恶化”使得华盛顿的对华战略思考“误区”环生,特别是由于军方对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专利权”的极力维护,致使判断片面、政策失当;(5)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中的“个人烙印”甚大,参与各个环节决策者的教育程度、职业背景、政治可信度、行政能力与经验以及政治利益等诸因素,造成战略态势不连贯、具体政策相互矛盾,以致给对手传递出“偏差”、“错误”的信息而造成对手误判;(6)美国式的“战略文化”对华战略决策呈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认知、判断“威胁”的性质与程度,以及决定是否动用武力、动武的方式与烈度这两个战略关键层面上,常常“忽略”甚至“否认”中美双方由于“文化价值观”以及“历史意识”不同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这样形成的“文化偏执狭隘”观不同程度地使美国对中国在亚洲所谓的“战略扩张”、“穷兵黩武”的“动机”与“意图”的判断,不时出现严重偏差。
第二,美国对华的经济“外交”。为政治目的开展的所谓“经济外交”,是美国“冷战”期间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政策面。依据本人拙作《经济冷战》(斯坦福大学2000年英文版)形成的论文表明:华盛顿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武器”使用,呈现出从短暂的“正面运作”(如杜鲁门早期的经贸、经援“诱惑”政策)很快转向历时数十年的“负面实施”的轨迹。后者包括对“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对双边、多边贸易的封锁,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制裁,对任何形式的对华金融、物贸、技术援助的堵截。牵涉面之宽,持续时间之长均属罕见。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赋予这些“经济武器”众多的“政治目标”,诸如“惩罚中共的侵略”、“在中苏同盟间打入‘楔子’”、“威慑中国的区域扩张”、“促进中国的政治变动”等等,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华“经济武器”的实施中,美国决策层实际上已认识到“经济外交根本没有且不可能达到战略目标,反之对美国国内经济、美与盟国关系都带来严重后果”。然而,华盛顿甚至在主要盟国纷纷“对华解禁”后仍坚持其对华经济制裁与封锁。对此的研究结果表明:(1)美国将自身的经济科技力量作为其对外政治运作的重要“实力基础”与“战略资源”;(2)美国对外决策者明确地要求经济利益服从国家“安全”利益;(3)美国频繁使用“经济外交”是其“实力的傲慢”使然;(4)美国在考虑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时,实施“经济武器”常常是在既不能“动武”(风险成本过大)又无法“无所作为”(效益成本过小)的两难间作出的必然选择。
第三,美国对华文化战略。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现代化”制度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对外利益的政治武器?“理想主义”的答案是肯定的。对“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政治目的实施的对华“文化战略”,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副教授李洪山博士作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他的初步研究表明,华盛顿整个50年代对华“文化战略”的重点是堵截新中国取得西方“文化资源”,具体体现在通过“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以及部分“半官方”组织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劝说”、“威吓”、“感化”,为他们提供工作研究便利等,以阻挠数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与此同时,至60年代初,美国通过“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科技发展项目加强了对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教育、新闻传播界的“攻心战”,培植“现代化台湾人”的主体与意识。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美对华“文化武器”又翻新花样,把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的“有限交流”当作“胁迫”北京放弃与美对抗的“奖励诱饵”。此后,艺术、体育、卫生、新闻“交流关系”的先行发展,又成为“改善”中美冲突关系的“试探运作”。李洪山博士指出,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美国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有计划、有配合地“打文化牌”,是美“冷战”思维与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
第四,中美“冷战”时期的外交谈判。从1949年到1972年,中美在亚洲的对抗虽然“时间长”、“烈度强”、“危机四伏”,但两个“殊死相搏”的大国却维持着长期的“非正式”谈判。这种“谈判”机制为何存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谈判”对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起何作用?利用美国最新解密档案与中方材料,通过对“黄华—司徒雷登”、“板门店”、“日内瓦”、“华沙”、“巴黎”、“北京”、“纽约”中美谈判的分析,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兼博士得出四个结论:首先,此时期的中美“接触”并非实质性的外交谈判,由于出自“揣摩”对方意图的需要,双方看重的是“沟通”、“对话”、传达“信息”(美国务院所有关于“谈判”的文件,均使用“对话(Talks)”一词),而不是指望通过接触解决双边冲突;其次,此时期的中美“对话”并非对称性交往,中方受到北京最高决策者的直接指挥,而美方则隶属“部门”工作,很少得到总统乃至“国安会”的关注,即便是“负责部门”国务院内也未成立专门研究、指导班子,以致“情况报告”多、“政策建议”少;再次,此时期的中美“谈判”表现出“文化磨合”过程,特别是美国代表,由于对中国政治文化缺乏了解、加之“文化偏执”倾向严重,常常将中方的“严正立场”与“原则声明”不是认作“顽固不化”、“死要面子”,便是解读为“阴谋诡计”、“耍花腔”、“无诚意”,结果失去不少与北京“深入沟通”的机会;最后,此时期中美“交流”的最主要作用为“预设管道”,一旦政治机会成熟,便可由有限“对话”提升为“实质谈判”(起码基辛格对这一“预设管理”的存在感到欣慰)。中美间这种“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边打边谈”,反映了“冷战”遏制与接触的基本特征。
第五,美国对华情报分析。美国“冷战”期间的战略情报分析的出现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源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武装介入”误判的“痛定思痛”。美国澳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副教授李小兵博士通过对1949-l972年间的美国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NIE)”、“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以及“每周情报简报(WIB)”的比较分析,发现:(1)美国对华情报分析对最高决策层影响甚大,其分析、判断与建议常常被直接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案;(2)情报分析家们在判断中国“使用武力”可能时,往往从中国的军事能力(capability)去演绎中国的战略意愿(intention),否认“能力”并不一定会决定“意愿”;(3)美国对华情报分析的材料来源极为有限(相当一个时期,主要依赖设在香港的“大陆报刊分析点”与台湾“大陆情报网”),误识、误导现象严重,以致于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受贬;(4)美国对华情报分析“军政对立”现象明显,国务院、“中情局”、海陆空军各情报系统,常常“各持己见”,让高层决策无所适从;(5)情报分析人员的“中国训练”十分欠缺,基本不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变化,故表现出严重的“文化偏执”倾向。
第六,美国国务院内的“中国手”。一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受国务院内的所谓“中国通”影响,但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高铮博士基于国务院档案的研究却提出一个新概念:“中国手”。在他看来,由于40年代末麦卡锡主义对国务院内“中国通”(主要指那些对中国有研究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的清洗,该院内负责中国事务官员的背景、作用发生变化。通过对历届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中国科科长、“政策计划委员会(PPC)”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他们政策提案的研究,高铮的初步结论为:国务院中负责远东与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已从“专家型”变为“职业型”,其作用也从单纯提供“专业”咨询变为运作具体政策,从“通”变成了“手”。这一变化的政策意义十分鲜明:首先,这些“中国手”的中国知识贫乏,判断、提议源于“想当然”者甚多,因此误判不断;其次,由于对台湾“消息源”的依赖,他们更易受到台湾的蓄意操纵和影响(其中罗伯逊最为突出);再次,考虑到自身“仕途”,他们更关注“顶头上司”的意图,并刻意去迎合(如艾奇逊时期的腊斯克、基辛格时期的洛德与格林);最后,由于“国安会”是“核心”政策的决策机构,国务院的“中国手”们更侧重政策的操作与评估。
第七,美国盟国与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冷战”期间,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德、日)看似“跟着美国跑”,对此,美国奥本大学教授翟强博士却认为盟国对美国的“主动”影响不容忽视。他的结论有三:首先,美国的盟国将本身利益置于“同盟”利益之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集体”防务与经济重建需要美国长期大量的投入),英国从二战一结束便致力于“锁定”华盛顿的“欧洲为主、亚洲为次”的战略取向,伦敦的历届政府附和并参与了美国在亚洲的“危机处理”,但其“集体行动”始终以避免“美国陷入亚洲”为原则。日本也屡次向华盛顿施压,以求不使东京的“区域防务”负担过重、对外经济利益受损。其次,美国决策者十分看重欧洲主要盟国对其“中国政策”的反应。这一点在文官身上表现最为强烈。从艾奇逊、杜勒斯、腊斯克、邦迪、麦克拉马拉到基辛格,均不同程度地出于对盟国的“担忧”与“顾虑”,说服总统与军方不得对中国“冒险”,以“避免自由世界分崩离析”。再次,美国的“亚洲盟友”有明显的“搭车(Bandwagoning)”倾向。特别是南韩与台湾,由于深谙美国朝野十分在乎所谓“政治信誉”的价值,它们不断以此“要挟”、运作华盛顿“一步步走向亚洲泥潭”。
第八,美国国会政治与“中国政策”的制定。在考察美国对外关系时,国会的“干政”通常被忽略。美国依阿华威斯利洋学院副教授许光秋博士认为国会的作用甚大,在“冷战”中明显呈上升趋势。尽管基于理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利益应高于任何政党利益”的考虑,美国“冷战”期间确立了在对外政策上所谓“两党一致(BiPartisanshiP)”的原则,但白宫在对华战略思考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反映在国会中的政党之争(如共和党控制的第80届国会对杜鲁门所谓“同情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迫使民主党政府在朝鲜冒险)。在对华政策上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两党政治”,无疑影响了美国与对外与国防有关的“高级行政主管委任”、“机制设立(如构建新闻总署、“美国之音”、国防情报局等)”、“预算分配(对台军援拨款)”、“法案制定(“福摩萨决议案”、“台湾关系法”等)”及“军事行动允准”等国家行为。另一方面,许光秋博士发现,白宫也会有意利用国会为其对华政策服务。艾森豪威尔曾多次以国会为“筹码”抵制英国、日本、法国要求美国“克制”对华敌意的压力;肯尼迪、约翰逊甚至尼克松均曾试图建立“国会对话管道”,以此试探北京的对美意图。这种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的“互动”,起码是美国对华政策运作的一个不容轻视的决策层面。
第九,美国的智库与对华政策。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副教授王建伟博士对美国的所谓“智库”在“中国政策”制定中作用的研究别具一格。“智库”的出现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特别是随着60年代“区域研究”的加强与普及,“智库”与对外政策制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通过对“半官方”研究机构(如兰德、企业研究所、东西方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非赢利基金会(如传统、福特)”以及设在大学的“区域(Area Studies)”研究组织(如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比较,他发现有关中国的“智库”至少发挥了五方面的作用:(1)确定政策“议事日程”(Agenda-Setting):通过学者的专项研究报告(commissioned papers),提出“热点”问题,建议政策的中长期研究议题排序与计划安排;(2)“聚焦”舆论(Opinion-Forging):通过发表论文、演说、答记者问等形式引导媒体,炒作“热点”,如有关中国的所谓“蓝队”与“红队”的“争风吃醋”;(3)教育动能:主要通过为本科生提供“实习”机会、为研究生提供“论文奖学金”、为年轻学者提供研究资助以及组织研讨会等,传播观点;(4)为对华决策与实施培养人才:“智库”的显赫人物如怀丁(Allen Whiting)、路易斯(John Louis)、李洁明、奥克森伯格、李侃如等均属此类;(5)非正式外交角色(Informal Diplomacy):如担任“第二管道”的策划、组织、运作和参与等。
第十,美国的左翼运动与中美关系。现代国关理论仍将对外政策当作国内政治的延伸。“冷战”时期美国内政的一大特点是“左翼”政治、社会势力蓬勃发展,诸如劳工、“女权”、“民权”、和平、“反文化”、“新左派”、乃至“人权”等“左派激进”运动,均不同程度地成为美国对外行为的“动因”。这些“左翼”团体对“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有无影响?对此,美国印地安那宾州大学副教授王希博士的研究得出肯定的结论。他发现,这些势力的影响主要有“正负”两方面。正面影响是:基于其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立场,“左翼”势力对当政者“为了特殊集团的利益与中国为敌”的批判,形成了“公共压力”。几乎所有的“左翼”运动,尽管“政治理念”不同,但都表现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倾向——“少管外部闲事,集中解决好内部问题”。在“中国政策”上,更是认为“执意与亿万中国人对抗不符合美国人民利益”。这一观点对美国“公众论坛”中要求与中国“缓和”的声音影响甚大。负面作用是:中国与某些“左翼”势力(如美国共产党)的交往以及对“反政府”抗议行动、游行示威(如劳工、黑人、反越战团体等)的公开支持,往往被美国政府以及保守势力认作蓄意“干涉美国内政”、“渗透美国政治”、“颠覆美国政权”,从而加剧了决策者对中国的“疑惧”、“怨恨”、“防备”与“敌意”,结果降低了中美缓和的可能性。
上述这十方面的概括,充其量仅仅是对美国“冷战”时期“中国政策”行为轨迹的一个“扫描”图像。值得欣慰的是,这十篇论文将扩展成十本学术专著,并作为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胡礼忠教授与本人主编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决策机制研究”的丛书出版。研究成书后可望引起对这些专题更详实、更透彻、更深入的描述与剖析,以期对解读现时美国对华政策起到借鉴作用。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华盛顿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