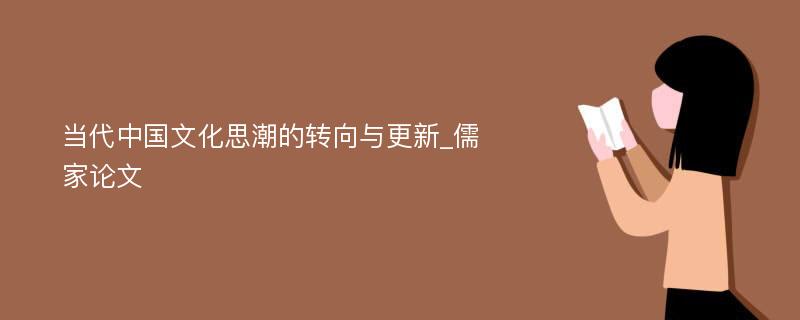
当代中国文化风潮的转向与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潮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5-0008-10 一、新启蒙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化风潮的转向 综观中国近世以来的文化启蒙历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续的一系列文化论战,启蒙的基本宗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演变,从向往“国强”、“民富”到伸张“民权”、“民主”,再到追求人性解放和文化更新。①由于这个深化过程是在国势渐颓、西风日盛的情况下推进的,因此自始至终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和片面化特点,尤其与中国当时的民族处境和政治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启蒙过程中,随着西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进步人士的鄙夷和抨击,在许多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儒家思想往往被视为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根基。虽然在抗战期间,出于救国保种的现实需要,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儒家曾一度复兴,但是到抗战结束之后很快又趋于式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国际两大阵营的对垒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中国内地理论界长期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共同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对“孔老二”和“救世主”的双向批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如同近世文化启蒙一样云谲波诡的激烈变化。从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到重铸民族信念的“寻根文学”,从《河觞》的“全盘西化”导向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反西方主义煽情,从“萨特热”、“尼采热”等西方哲学时尚到方兴未艾的“国学热”……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变革,可以归结为两个方向相反、旨趣相关的思想倾向,即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所以说二者旨趣相关,乃因为它们都是对前三十年(1949-1978)“革命大批判”的一种背离;而二者的方向之别,则如同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派”与“国粹派”的分歧一样,表现出了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 与此前“突出政治”的时代和此后“发展经济”的时代相比,1980年代堪称一个注重文化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于各种新鲜事物充满了兴趣。在失望与希望相交织、迷惘与反思相砥砺的精神背景下,文化问题就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聚集点。无论是理论界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学术界众人瞩目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文学界风靡一时的“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和“现代主义诗群”,艺术界标新立异的“第五代电影”、“85新潮美术”和港台流行歌曲,都表现了一种挣脱思想枷锁、追求人性解放的文化启蒙要求,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与“文革”时期“文化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导向以及1990年代以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主义导向不同,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文化问题本身看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他们像“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一样,把中国贫穷、落后、专制、闭塞的原因都归结到文化问题上,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启蒙运动。 1980年代,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看世界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社会的蒙昧落后与西方社会的开化发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鲜明对照很容易在文化心态上产生一种短暂的晕眩感,即对阔别已久的西方文化的狂热崇拜和盲目模仿。受这种文化晕眩感的影响,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就如同“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一样,陷入了“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专制蒙昧/民主科学”等一系列对偶结构的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中,从而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传统(以及专制、蒙昧)相联系,而把西方文化与现代(以及民主、科学)相等同。对于这场运动的许多积极参与者来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要彻底摆脱传统,效法西方,实现脱胎换骨式的文化大变革。李泽厚在1986年的《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论述“启蒙”与“救亡”这两个“五四”时期相互促进的主题是如何由于民族危亡的现实困境,最终转变为“革命战争”挤压“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的吊诡结果,导致了封建传统以“革命”的名义在“文革”时期全面复活。该文的宗旨就是要重新高扬起被“救亡”和“革命”所斫丧的文化启蒙大旗,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成为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标志性文献,它激励青年知识分子以一种更加自觉的方式去重振“五四”启蒙精神和清算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同时也再次明确地把启蒙的思想源泉回溯到西方文化中。 这场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其间虽然不乏精辟的睿智和无畏的勇气,但是却更多地表现了一种情绪化的特点。尤其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往往缺乏深沉的理性反思,再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砸烂孔家店”的偏激姿态。例如,当时的青年思想精英甘阳就明确断言,中西文化之争的实质就是古今之争、旧新之争,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这位新启蒙运动的激进干将明确表示:“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因为要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的‘系统’,舍此别无它路可走……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②在1980年代的一些文化批判者眼里,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已经“解体了,退化了,变得丑陋不堪”,而“文明一旦死去,谁又能够起死回生,使它重现于世?复现的‘传统’甚至已不再能被称作文明,它只是历史的余响,病态的畸形儿”③。1988年,一部六集电视政论片《河觞》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播出,在知识分子和普遍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片毫不掩饰地表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全盘西化”主张,它宣称黄河和黄土地所孕育的古老文明“已经衰老了”,它那已逾更年期的机体已经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文明,也无法抵御蓝色海洋所滋润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劲挑战,而导致“黄色文明”衰落的罪魁祸首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④ 面对着由于儒家文化所造成的衰败命运,濒临绝境的黄河文明唯有使自己最终“汇入蔚蓝色的大海”,融入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大洪峰”中,才能“补充新的文明因子”,获得涅槃新生的希望。 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氛围中产生的一场文化更新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激情多于反思,批判多于建构,但是它却像6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热情和自由理想。在这场新启蒙运动中,各种思想观点竞相绽放、争妍斗艳,但其主流趋势无疑是“向西走”的主张,而极端表现就是以《河觞》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观点。但是到了1990年代,文化风向却骤然改变,一股强劲的传统回归和民族复兴的文化潮流汹涌而至。而且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迅猛崛起,这股与1980年代的“西化”导向背道而驰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显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演化成近年来乱花迷眼的“国学热”现象。 198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趋势从追求西化转向了回归传统。在学术界,海外新儒家反哺内地,使得深受西化潮流压抑的国学派扬眉吐气。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思潮、后殖民文化批判、“新左派”思潮等具有明显反西方情调的理论也竞相登场,对于以西方为标准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1980年代的“青年思想导师”李泽厚也在海外发表了“告别革命”的观点,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后果进行深刻反省和重新评价,得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温和结论。在文艺界,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心理涟漪,激起了人们对“黄土地”的无限眷恋。以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导演继1980年代崭露头角的《黄土地》、《红高粱》之后,在1990年代又连续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情调和乡土气息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和“秋菊”系列。美术音乐方面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特点、将原始情调与民间风格相结合的“寻根艺术”取代了深受西方人文主义影响的“85新潮美术”,苍凉遒劲的“西北风”和“信天游”压倒了缠绵悱恻的港台流行歌曲。凡此种种,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一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趋势,即民族精神的振兴和西方情趣的衰减。这种变化趋势也与日益凸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相契合——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怀古情调的“西北风”顺理成章地演化为奋发图强的“中国梦”。在这种新时代精神氛围下,从1996年开始,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字头的作品(如《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等等)纷纷问世,它们与《河觞》宣扬的“全盘西化”主张针锋相对,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和西方价值说“不”的民族主义立场,抒发了“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西方神话破灭,东方文明复兴”的文化理想。⑤同时也从文化上对倡导西化倾向的五四启蒙运动进行了清算,主张“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以‘飞龙在天’的雍容豪迈之气崛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明”⑥。 《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类的书籍在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畅销中美。与推崇普世价值、向往西方启蒙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针锋相对,“中国×××”系列的作者们呼吁国人重新挺立起民族的脊梁,拒绝在西方文化面前顶礼膜拜,豪气十足地宣称“要让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⑦。一百多年来,当大批洋货和文明新事物从西方涌入中国时,国人在器物、制度和精神等方面也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而今,当中国人开始把大批“中国制造”和孔子学院输向世界时,“中国模式”似乎大有希望取代“西方中心”而成为全球文明的引领者。 在这种文化大气候的影响下,一些早年积极倡导西化主张的激进学者,也纷纷改弦易辙,转投到文化保守主义麾下,成为复兴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崇者。例如曾经在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激烈批判儒家文化的甘阳,自海外游学归国之后转而对西方启蒙价值进行全面颠覆。他认为自从孔子以来,中国就已经奠定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启蒙传统,因此完全不必亦步亦趋地效法西方启蒙运动。“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导致了各种妄自菲薄的新迷信,而今中国新一轮的文化启蒙(可谓“新新启蒙”),就是要打破这种新迷信,摆脱“西方人的指引”,用自己的理智来思考,用自己的脚来走路。⑧对于主流社会所推崇的“和谐社会”理想,甘阳认为“和谐社会”概念本身就根植于儒家传统之中,而中国改革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位曾经厉声质问“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的批判者,现在却以卫道士的姿态宣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⑨ 无独有偶,另一位曾与甘阳同为1980年代西化派新锐的知识分子刘小枫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近二十多年来,刘小枫作为在中国青年学者中影响巨大的思想“风向标”,其在学术方向上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会在大批知识“粉丝”中引起巨大的“蝴蝶效应”。1980年代后期,正是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在中国青年学人中掀起了一股基督教神学研究的热潮;21世纪初,他开始从基督教神学转向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和施米特的政治法学,又在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政治哲学研究的新热点;再往后,他又从政治哲学转向了古典学,从众人瞩目的现代性批判骤然转到遥远冷僻的希腊学术和古典注疏,但是此举仍然得到了一批拥趸的积极响应,激起了一道西学经典诠释的涟漪。然而就在不久前,这位素来对中国当代政治问题讳莫如深的学者却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天宪政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演讲,不仅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新国父论”,而且还对儒家在构建“德政国家”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加褒扬。事实上,早在刘小枫把学术兴趣从基督教神学转向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的古典政治哲学和施米特的国家主义的政治法学时,他就已经在思想上开始从早年“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姿态向“依托乡土”的保守立场回归;而他倡导解读西方经典的一个隐秘目的,就是为了重新阐释古典中学、尤其是儒学经典。他不仅援用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来为抵制“普遍的技术理性和西化民主政治”、捍卫“自身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进行辩护,⑩而且也举起毛泽东确立的“民族自立”的政治原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相抗衡。(11)在最近发表的那篇公开演讲中,他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并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是民族的德性和人民的幸福,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儒家在国家政体中起决定作用的德政国家。他甚至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基本理念就是平等。 一位原本靠着宣扬基督教神学思想而起家的“西化”先锋,近年来竟一头钻进了儒家德政国家“传统大法”的“乡土”情结中。这种脱胎换骨的思想变化,固然有个人气质和学术旨趣方面的原因,(12)但是更多还须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所谓的“时务”,无疑就是中国崛起的现实背景,以及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盛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 二、当代儒家的文化理想 与狂热煽情的民族主义者和激流转舵的“新新启蒙家”不同,现代新儒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将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谐相融的途径,试图从先秦儒家经典和汉宋儒学思想中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建设提供文化根据。早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虽然“向西走”的呼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主流,但是主张深入发掘、反思和弘扬儒学传统者也大有人在。1987年10月,在以介绍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为主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辑刊上,刊载了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文。杜维明对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和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进行了系统探讨,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了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对“儒学”、“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等概念作出了学理上的辨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西方学者关于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结论,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文化前景。杜维明像牟宗三、唐君毅等老一辈新儒家一样,一方面承认儒家思想中确有一些致使近代中国凋敝落后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儒家传统是使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他坚信,儒家传统在经历了100多年的颓运磨难之后,已经显现出一阳来复的振兴征兆。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儒学要想继先秦两汉儒学和宋元明清儒学之后实现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必须充分吸取西方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摆脱保守主义、权威主义和因循苟且的心理,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使儒学获得创新和进一步发展。(13)而儒学第三期发展是否可能,则完全取决于新儒学能否对西方文化挑战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应战,能否有效回应“启蒙精神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技效应、个人主义等等。(14)正是这种扎根传统面向现代、立足儒学兼容西学的开放态度,使得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学创新”、“文化中国”等观点在中国大陆的儒学推崇者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老一辈新儒家坚持“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认为从儒家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但是到了21世纪的现实处境中,这种文化理想在当代儒家那里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当代儒家内部的文化分歧。 当代儒家的一种比较温和、理性的修正意见认为,近100多年来,西方文化构成了儒学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那些最初发萌于现代西方文化温床、而后逐渐被世界各文明地区所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如自由、民主、宪政、科学等),它们虽然并不能直接从儒学传统中被“开出”,却可以与儒家的道德心性相协调,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中绽开更加绚丽的现代花朵。上述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大多持有这种观点,这既与他们的西方处境和全球视野有关,也是他们对儒学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反省的结果。与海外新儒家过往甚密的一些国内新儒家代表人物也所见略同,例如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一方面满怀信心地展望21世纪儒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复兴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则强调西方文化对于儒学复兴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道:“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岁月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文化的更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5)针对主张把儒教确立为“国教”的原教旨主义观点,汤一介先生明确表示反对“政统的儒学”、慎对“道统的儒学”和提倡“学统的儒学”的基本态度。另一位国内新儒家代表郭齐勇教授也表达了对于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对话意愿,强调儒家传统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价值协调互补的必要性。他承认,儒学虽然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一样,“不能直接地开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它却可以通过自身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而充分吸纳和消化这些现代价值,使之在新的文化土壤上更加健康地成长。他提倡要以一种“开放的胸怀”来促进儒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新时代的诸子百家”之间的对话,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融通。(16)与这种温和、理性的开放态度相区别,当代儒家的另一种修正意见则表现了与西方文化势不两立的偏激立场,根本否定了老一辈新儒家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必要性。这些力主在当代中国社会全方位复兴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满足于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试图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全面贯彻到社会各领域,将儒教树立为“政教合一”的国教或者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当首推隐居贵州龙场阳明精舍、以今文经学和公羊学传统来为中国现代社会设计政治制度的蒋庆先生。这位“当代大儒”奋力疾呼,当今中华文明复兴的首要之义就是要全方位重建儒教文明,以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分庭抗礼。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蒋庆系统地设计了一套儒教重建方案,儒教复兴大业通过相辅相成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来实现。“上行路线”需要自上而下地由“圣王”来创制,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立国之本写入宪法,将儒教提升为“王官学”或国家意识形态,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宪政体制”;重建新的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形成一套礼乐教化的“礼制”和“文制”,对整个社会进行礼法规范和道德熏陶。“下行路线”则通过民间的“中国儒教会”来推进儒教的全面复兴,其内容包括重建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理想)、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乡村自治、社区文化等)、儒教的生命形态(对天神、地示、人鬼或“天地亲君师”的信仰)、儒教的教育形态(新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等十项事业。蒋庆强调,在儒教崩溃而亟待复兴的今天,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政治上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下行路线”则是应对时代变化而采取的“变通路线”。如果二者可以相辅互济,儒教的重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蒋庆重建儒教的构想可谓情真意笃、用心良苦,然而在王道政治、科举制度、宗法社会已经土崩瓦解的现实社会中,儒教的复兴将何以为据?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诚如著名海外新儒家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今天儒家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缺乏制度支撑的儒学只能成为依附于个人心性和大学讲堂的“游魂”。(17)至于要想重建儒教赖以栖身的那些基础性社会制度(如蒋庆在《政治儒学》一书中构想的“议会三院制”、“太学监国制”等),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则更是异想天开!蒋庆先生复兴儒教的满腔热忱固然令人敬佩,他本人长期固守阳明精舍践行儒学精义,更是显现出儒家知行合一的真性情,但是他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却未免流于空泛,成为现代社会的天方夜谭。 正是由于蒋庆重建儒教的实施方案过于虚幻,复古气息又过于浓郁,致使一些赞同儒教理想的学者纷纷提出了更加切合实际的修改方案。例如,与蒋庆试图在当今中国恢复古圣王之教以转化中国政治秩序的“上行路线”不同,陈明教授认为重建儒教必须从公民社会入手,使儒教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如同基督教之于美国社会一样),通过一条“下行路线”自下而上地来推进政治重建进程。(18)另一位当代著名学者张祥龙教授一方面明确表示赞同蒋庆“重建儒教”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政治经济大潮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当政者来使儒家进入政治权力核心、立儒教为国教的“上行路线”是不切实际的,而通过“中国儒教会”的教育、宗教功能来复兴儒教的“下行路线”同样也是前景暗淡。他从儒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精神特质出发,提出了“中行路线”的设想,即“专注于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质”,复兴和维护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的传统家庭和家族模式,以家庭关系和亲子源头为基础来重建儒教。具体做法就是建立“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文化特区,在经济上奉行环保的自然生活形态,在教育上推行儒家的礼乐教化,在政治上实行儒家导向的天人合一的家族社团民主。以这种生物保护区似的儒家文化特区为“根据地”,不断地向主流社会输出合格儒生、教育模式、政治体制、技术形态等,从而逐渐实现儒教重建的宏伟事业。(19) 近年来,在大学校园的一些儒家新秀中,出现了更为激进的儒学复兴主张,甚至走向了以“儒家普世价值”来对抗和否定“西方普世价值”的地步。在他们看来,以往的新儒家都试图从儒家价值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如牟宗三等人),或者用儒家价值来附和西方普世价值(如杜维明等人),但是他们却要强调儒家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意义,以此来取代西方普世价值。2011年11月,复旦大学召开了“儒家与普世价值”的研讨会,与会的儒家少壮派语出惊人地喊出了“拒斥西方,排斥异端”的口号,声称要把长期以来“鸠占鹊巢”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踹出去”,让真正的主人(儒家)住进来。他们主张用儒家的“人伦”来取代西方的“人权”作为普世价值的核心,用儒家的“优质的普世价值”来超越西方的“劣质的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右派(自由主义)和左派(马克思主义)都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他们甚至异想天开地要用儒释道等传统文化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共产党割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效法孙中山的做法,认祖归宗。这一百年来,我们一直认外来的东西为祖宗,其中最等而下之者,则是自由主义认贼作父的搞法。现在,我们应该回归自己五千年的大传统了。(20) 对于这些儒学复兴的激进派来说,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西方的“劣质普世价值”是不值得效法的,西方传入的基督教更是具有笼络人心、窥伺中华之嫌,必须联合儒释道等本土宗教,将其拒于国门之外。(21)这种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不仅使“儒家原教旨主义”与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鼓角相对,而且也与已经具有“全球化素质”的基督教势不两立,从而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宽容胸襟的偏激姿态。 与主流舆论潜移默化地把“中国特色”转变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做法相契合,当代儒家大张旗鼓地把传统儒家价值提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最初只不过是一个被迫变革的特例;然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它却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后来居上典范。儒家的那些价值理念,曾经被启蒙时代的知识精英当做封建糟粕而抛弃,今天却被传统文化的崇拜者奉为克服现代社会弊病、实现大同世界理想的法宝。在中西古今的对偶中,天平开始从西方倒向中国,今背离古也转变为古召唤今。亨廷顿在谈到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文化张力时曾精辟地指出: 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22) 三、“国学热”时尚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通过宗法家族的伦常规范、私塾书院的经典教育、科举考试的仕途进取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特权,儒家不仅使其基本价值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然而,自从20世纪初叶科举制度和封建帝制被废除之后,儒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又进一步清算了儒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颠覆了孔孟之道在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再往后,随着封闭的自然经济体系被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彻底打破,以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逐渐瓦解,儒学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也日益式微。而且由于儒家(或所谓“儒教”)又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宗教那样拥有独立而稳定的宗教场所和经济资源,所以一旦当它与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就很容易变成无处栖身的“游魂”,只能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存在于纯粹的学术领域中。这就是儒学在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即陷入一种无根(现实制度之根)的飘零状态。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之所以侧重于“心性儒学”,正是由于他们明智地认识到儒教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已经崩塌;余英时等海外新儒家则感叹道:“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23)甚至连主张重建儒教的当代儒家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是“儒家生存史上最惨痛衰微的一页”,所谓“新儒家”不过是西式大学中的一些“聊胜于无”和“无关大局”的个体研究者,而官方所搞的种种祭孔活动更是一些旅游项目或统战姿态而已。(24) 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现实状况,当代儒家理想的热忱鼓吹者们力倡让儒学走出狭隘的大学校园和学术团体,重新奠立为个人的生存之本和国家的制度之基。蒋庆极力鼓吹要把作为一个思想派别的“儒家”提升到作为“王官学”或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从学术象牙塔中的“心性儒学”全方位地走向“生命儒学”、“政治儒学”、“民间儒学”和“宗教儒学”。(25)另一些倡导“下行路线”的学者则主张让儒学走向广阔的民间社会,试图像王阳明那样开辟一条“觉民行道”的儒学复兴之路。然而,在时过境迁的全球化时代,当代儒家的各种重建儒教方案在现实社会中都显得志向远大而践履乏力,难以付诸实施。 虽然儒教重建的前景渺茫,儒学复兴的文化要求却与当代中国民族振兴的现实状况以及大国崛起的社会心理相适应,也迎合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某些商业需要,因此近年来儒学在表面上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虽然当代儒家重建“儒教”和“王官学”的政治儒学路线不会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但是通过弘扬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确立一个合适的文化身份,这却是符合中国当前的文化战略的。正是由于官方的支持和参与,近年来民间出现了许多场面盛大的振兴传统文化的活动,如祭奠黄帝、炎帝陵寝,举办孔子诞辰庆典和孔子文化节等等。在海外,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虽然其主要功能只是对外国人讲授汉语);在国内,各种级别和规模的儒学学会、国学院、国学培训班、国学大讲堂等也纷纷成立,不仅面向大学院墙内的青年学子,而且更注重对社会成功人士和权势阶层——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等——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当然昂贵的学费也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在大众传媒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等栏目中对中国历史和儒家经典的通俗化讲解,则在普通大众中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国学热”时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学术明星对于推动传统文化复兴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要比当代儒家重建儒教的高谈阔论更加广泛和持久。这种现象恰恰也说明了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的消费化和娱乐化特点,它对于当代儒家魂牵梦萦的儒教国教化的原教旨主义理想无疑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激起了广大民众对于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热情关注。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所谓“国学热”现象,无疑具有一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斑驳特点。无论是阳春白雪的大学讲坛,还是下里巴人的市井社会,各种死灰复燃的旧习俗和改头换面的新事物都纷纷打着“国学”的旗号以壮声威。中国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资源——从宗庙朝堂的典章制度到乡间坊里的风水八卦—无不囊括其中,其内容远比单纯的儒学或“儒教”要广泛、庞杂得多。这股包罗万象、纷纭芜杂的“国学”复兴热潮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复苏的大国理想相互砥砺,使得当今中国文化在精神面貌上呈现出一种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盘西化”倾向迥然而异的景象。事实上,这股强劲的“国学热”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它也与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文化保守主义遥相呼应,尤其是与“后冷战时代”的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东方宗教的复兴潮流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了21世纪国际文化舞台的主旋律。 所谓“国学”,无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通称,胡适先生曾以“科学的态度”对“国学”概念进行了定义:“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6)在“国学”中,儒学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主干和核心。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儒家思想和伦理规范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古代闭塞的文化环境中,在不存在“西学”威胁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无所谓“国学”。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以儒学为主、儒释道互补、兼及各种民间宗教和文化传统,形成了浑然一体、张弛有序的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范。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自成一统的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范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随着中华帝国紧闭的国门不断被西方列强轰开,“向西走”的文化呼声也逐渐高涨,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则危殆日深。在此紧迫形势下,张之洞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想在“固根柢”的中学和“补阙遗”的西学之间达成一种融通互济之势。然而,这种“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自提出之日起,就不断遭到来自激进和保守两个方面的质疑。批驳者们不仅在文化立场上不赞同“中体西用”的折中方案,而且从学理上也指出了这种主张的荒谬之处。(27)与“中体西用”的主张相对峙,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界又先后出现了“复古主义”、“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多种观点,相互争锋,各显身手。但是在此过程中,总的趋势是“西学”日盛、“国学”渐衰。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所谓“国学”曾一度被看作封建糟粕,横遭摧残,几近湮灭。 然而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和中国国力的迅猛增长,在“文明冲突”或文明对垒的新时代背景下,加强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伴随“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文化预期而来的,必定是汹涌澎湃的“国学”复兴潮流。近年来“国学热”现象的出现,固然与现代传媒的巨大影响和快餐文化的明星效应有关系,也与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相呼应,但是它同样也反映了儒学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学在20世纪的中国虽然历尽坎坷,但是它毕竟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成功地铸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儒家所提倡的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刚毅纯正的浩然之气、敦实宽厚的仁义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远鬼神尽人事的生活态度、黜玄想重实用的价值取向等精神内涵,仍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且完全具有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现实可能性。而近百年来儒学几度复兴的事实也表明,它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丰富的滋养,没有任何外来资源可以取而代之。因此,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复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毋宁说,当前的“国学热”正是中国现实政治经济状况在文化上的必然表现。 然而,所谓“国学热”能否超越喧闹浅薄的快餐消费,转化为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文化更新,这就要看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是否能够真正与全球化时代的普世价值和谐对接,从根本上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曾多次谈到文化传统的“创造的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他对这一概念解释道: “创造的转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里的健康、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改造,而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会而产生的。在这种有所根据的创造过程中,传统得以转化。(28)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其一,儒家或“儒教”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那样拥有独立于家庭和世俗政权(国家)之外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教会),它的根基一直附着于依靠血缘关系而维系的宗法社会。今天,传统的宗法社会已经土崩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伦理价值系统在现代社会中丧失了赖以维系的现实基础,这是儒学复兴所面临的最为纠结的难题。其二,在隋唐以降的传统社会中,儒学通过科举制度开辟了使“田舍郎”登上“天子堂”的通衢大道,将读书修德与及第入仕协调地统一起来。但是现代教育体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儒学格格不入。随着科学教育的普及化,儒生或者“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不复存在,儒学只能退而成为一种内在的心性之学,很难再从“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儒学是否应该像基督教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将其主要功能从建构制度内敛为安顿人心?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夏夷”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儒家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比自己落后、蒙昧的夷狄之族,而是更加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以夏变夷”模式已经难以奏效,而更新自身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价值理念或许才是儒学的复兴之路。对于由西方文明所发轫的那些普世价值和现代规范,儒家既不应采取闭目塞听的拒斥方式,也不应一厢情愿地指望从自身传统中独立地“开”出来,而应该虚心坦诚地直面相对,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以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应战。 ①赵林:《近世中国文化启蒙历程之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 ②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5-36页。 ③梁治平:《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读书》1989年第3期。 ④电视政论片《河觞》第六集“蔚蓝色”解说词。 ⑤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⑥摩罗:《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⑦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知识青年从军歌》中的歌词,转引自宋晓军、王小东等《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⑧甘阳:《启蒙与迷信》,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421.html。 ⑨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783-3.html。 ⑩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11)刘小枫:《毛泽东与中国的“国家理由”》,《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12)如同许多读着保尔·柯察金小说开启情智的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人一样,刘小枫骨子里也有着浓郁的“冬妮娅情结”。而且对于一个浪漫主义者来说,在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变节”似乎成为一种难以逃遁的宿命。海涅在谈到德国浪漫主义天才谢林的思想变化时诙谐地写道:“如果创始的工作完成了,创始者要么就死去,要么就变节……不是倒在死神的怀抱里,便是倒在他从前的敌人的怀抱里。”(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44-145页)此外,从学术旨趣的变化来看,当刘小枫开始把眼光从基督教神学转向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施米特的政治法学时,他已经在学术上为“依托乡土”的文化回归进行精神奠基了。 (13)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9页。 (14)杜维明:《儒教》,陈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0-141页。 (15)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130页。 (16)郭齐勇:《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3-94页。 (1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8页。 (18)参见陈明:《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8-123页。 (19)参见张祥龙:《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载任重、刘明主编《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77页。 (20)曾亦、郭晓东编著:《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21)“中国人讲宽容,绝不是要照单全收那些外来的东西,是要有所甄别的,尤其对于想要喧宾夺主的耶教,当然要拒之门外。更何况,目前许多中国人信仰耶教,对时局是个不安定因素,非常危险。“目前,耶教凭借其社会化的优势,笼络了越来越多的国人,形势真是堪忧。佛教应该振作起来,这不仅有益于政府,有益于民生,而且,还能在抵御耶教的渗透方面,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曾亦、郭晓东编著:《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40页。 (2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7-68页。 (23)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7页。 (24)参见张祥龙:《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载任重、刘明主编《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25)参见蒋庆:《儒学的时代价值》,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6页。 (26)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27)例如严复就曾对割裂体用关系的做法进行过深刻批判:“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参见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40年,第82-83页。 (2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388-389页。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可以说不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基督教论文; 普世价值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杜维明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