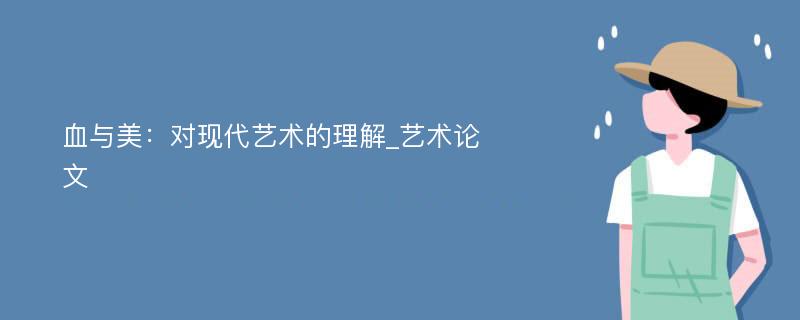
血与美:理解现代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美学协会的一次晨会上,一小群人在上午9点的时候挤进一间屋里,被论述“当代艺术中血的美学”时放映的幻灯和录像震惊得毫无睡意。我们看到了玛雅国王和澳大利亚土著青年在成人仪式上的血,看到了在马里喷洒在雕像上的血,以及在婆罗洲从祭祀的水牛身上喷溅出的血。有些离我们很近。有浸透了表演艺术家的成桶的血,还有从奥兰的嘴唇上渗出的血滴——她让外科医生为自己整形以模仿西方艺术中的美人。有些东西使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感到厌恶。
为什么这么多艺术中使用血?原因之一就是与绘画存在着有趣的类似之处。鲜血以耀眼的光泽而具有抢眼的色相,它黏附在表面,使你可以用它来作画或设计(在土著青年的皮肤上,其闪烁的交叠图形令人想起“蒙昧时代”)。血代表了人类的本质——德拉库拉(Dracula)就是因吸吮它而长生不老。血可以代表神圣或高贵,如殉道者或士兵的献祭之血;白布上的血点意味着失贞和成人。血还可以代表玷污和“危险”,如梅毒或艾滋病之血。显然,有大量的表现和象征意义可以与血联系起来。
血与仪式
然而,怪异的现代(都市、工业、第一世界)艺术中的血和“原始”仪式中的血意义一样吗?有人提出了一种艺术仪式理论:日常物品或行为借助融合到一种公共信仰系统中而获得象征意义。当玛雅国王在帕伦克当众刺穿自己的阴茎并用细芦苇三次穿过而流血的时候,他表现的是他连接永恒之地的萨满教力量。有些艺术家试图重新创造一种类似的艺术仪式感。蒂亚曼妲·嘉乐斯(Diamanda Galas)在其《大众瘟疫》中将歌剧魅力、灯光展示和光焰闪闪的血相混合,恐怕就是要祛除艾滋病时代的痛苦。“放浪形骸的神秘剧院”的维也纳创始人赫尔曼·尼采(Hermann Nitsch),通过音乐、绘画、轧汁和动物血与内脏的仪式性倾倒的结合来确保人们的精神发泄。你可以在他的网页WWW.nitsch.org上看到这一切。
并非所有这样的仪式都与欧洲传统有关:在其原初的犹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传统中,有大量关于血的描述。耶和华要求希伯来人为履行他们之间的契约而献祭,而阿伽门农和亚伯拉罕一样,则面对神旨牺牲自己的孩子。耶稣的血如此神圣,直到今天,那些虔诚的基督徒还在象征性地饮用它,以作为赎罪和心灵生活的保证。西方艺术一直表现这些神话和宗教故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通过献祭动物来赢得神的宠爱;而罗马的卢坎(Lucan)和塞尼加(Seneca)悲剧则堆积了比弗雷迪·克鲁格(Freddy (Krueger)的《艾尔姆大街上的梦魇》(Nightmare on Elm Street)更多的人体。文艺复兴的绘画表现的是殉教者之血和戴圣光的头;莎士比亚的悲剧都典型地以刀剑和刺伤而终场。
艺术仪式理论似乎是有理的,因为艺术可以在某种目标下产生聚合,通过仪式、姿势和手工制品的使用产生象征价值。许多世界性宗教的仪式都含有丰富的色彩、设计和壮观的行列。但仪式理论却没有考虑到现代艺术家有时奇怪而强烈的行为,如表演艺术家使用血的时候。对仪式的参与者来说,对目的的确定和认可是中心,仪式通过人人了解和明白的姿势来加强社团与神旨或自然的关系。但观看和对现代艺术家有反应的观众并不以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或以将显现出的先验知识参与其中。处于剧院、美术馆或音乐厅情境中的大多数现代艺术,都缺乏对规定了精神发泄、献祭或成人仪式含义的公众信仰的背景支援。他们并不是让观众来感受部分作品,有时只是让观众受到惊吓而抛弃了他们。明尼阿波利斯就曾出现过这种事情。当时,确诊为艾滋病的表演艺术家罗恩·阿塞(Ron Athey)在台上割同台演出者的肉,然后用巨大浸血的纸覆盖向观众以制造恐慌。假如艺术家只是想让中产阶级震惊,人们就很难将《艺术论坛》中报道的最新艺术与马里兰大厦的表演区分开来——那里的表演就包括在舞台上举行邪恶的动物祭祀仪式。
有人嘲讽说,当代艺术中的血并不造成意义联系,而是带来娱乐和利润。艺术界乃竞争之地,艺术家需要他们能够得到的所有优势,包括震惊的效用。1934年,约翰·杜威在《作为经验的艺术》中指出,艺术家必须努力寻找奇异性以应对市场:
工业已经商业化,而艺术家却不能机械地生产大众产品……艺术家发现已无法避免……使自己成为作品中“自我表现”的唯一手段。为了不致迎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他们常常感到有必要将其与众不同之处夸大到偏执的程度。
因为在1990年代展示封在有甲醛的玻璃展柜中的死鲨、切开的牛和羊羔而激起争议的“英国帮”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成功地利用了他的丑闻而在伦敦开设了自己有名的药物餐馆。很难想象赫斯特烤肉的场面(完全是异想天开)怎么能有助于他在食品生意中的形象——只不过是以神秘的方式完成了著名的作品。
近几十年来的一些最声名狼藉的作品开始因其对人体和体液的惊异表现而引起争论。在1999年布鲁克林美术博物馆的“知觉”展上,最受争议的作品(克里斯·区菲利的《圣母马利亚》)甚至使用了大象的粪便。在人体被穿刺和展示而使血、尿、精液成为艺术的新宠之后,1980年代末爆发了对美国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发放基金问题的争论。像安德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尿基督》(1987)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吉姆和汤姆,萨索里托》(1977)(作品表现了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嘴里撒尿)中的形象成为当代艺术批评家的攻击中心。
无一例外地这类作品都是关于宗教的,也涉及体液。当这些作为许多宗教之核心的表现痛苦和受罪的符号脱离其公众时,就可以造成震惊。假如它们和更世俗的符号相融合,其意义就会受到威胁。使用血或尿的艺术品,消除了通过美来表现易于理解的仪式意义或艺术赎罪的语境而进入公共领域。也许,现代艺术的批评家还怀念类似西斯廷教堂那样的优美和促进道德的艺术。在那里,至少对殉难圣徒的血腥场面或罪人痛苦的表现,在《最后的审判》里面都表现得极为精彩,具有明确的道德目的(就像古典悲剧中的恐怖用鼓舞人心的诗来表现一样)。同样,当代艺术的批评家认为,假如展示人的裸体,就应该像波提切利的《维纳斯》或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那样。这些批评家似乎在塞拉诺不名誉的图片《尿基督》中既不能发现美,也找不到道德性。参议员杰斯·赫尔姆斯总结道,“我不认识安德斯·塞拉诺先生,而且我希望永远不要见到他,因为他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怪人。”
当然,关于艺术与道德的争论并非什么新东西。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也曾谈到道德、艺术和趣味的难题,这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件要事。可能休谟不赞成亵渎、不道德、性或对体液的使用在艺术中是合适的。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支持启蒙运动的进步价值观和道德改革。休谟及其后继者康德(1724-1804)的文字构成了现代美学理论的基础,所以下面我就回过头来谈他们。
趣味与美
“美学”一词来自希腊语aisthesis,意思是感觉或知觉,是在德国美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1714-1762)把它作为研究艺术经验(或感受)的一个标签之后而知名。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不用此词而是说“趣味”,一种能从艺术品中获取高贵品质的提取能力。“趣味”可能完全是主观的——我们都知道这种说法:“人各有所好”。有人特别喜欢某种色彩和甜点,就像偏爱某种汽车或家具一样。艺术也恰恰如此吗?也许你偏爱狄更斯和法斯宾德,而我则喜欢斯蒂芬·金和《飘》,你怎么能证明趣味好于我?休谟和康德都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二人都相信,某些艺术品确实好于别的艺术品,而有些人则有良好的趣味。他们怎么解释这种差别?
两位哲学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休谟强调教育和经验:有些趣味敏感的人学到了某种能力,使人们认同哪些作者和艺术品最好。他认为,这些人最终将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他们就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趣味标准”。这些专家可以区分高质量的作品和一般的作品。休谟说,趣味敏感的人必须“保持没有偏见的自由之心”,认为一切人都不会赞赏艺术中不道德的态度或“邪恶的态度”(他举的例子,包括由于过度的热情而受到损害的穆斯林艺术和罗马天主教艺术)。怀疑论者现在批评这种观点的狭隘性,认为休谟的趣味仲裁者只是通过文化灌输而获得了它的价值。
康德也谈论“趣味”的判断,但他更关注对“美”的判断的解释。他意在展示,优秀的美学判断乃建基于艺术品本身的特性,而不只在于我们或我们的爱好。康德试图描述我们人类感知周围世界并给予分类的能力。包括知觉、想象和理智或判断在内的人的精神官能,有一种复杂的交互作用。康德主张,为了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以达到我们人类的目的,我们要为我们感知的许多事物命名,常常是以完全无意识的方式。例如,现代西方人从世界中认识了圆的平面物体,我们就把其中一些分类为餐盘,然后我们用它吃饭。同样,我们也接受了有些东西是食物,而另一些是潜在威胁或婚姻伴侣。
要说明我们是如何认定像红玫瑰这样的东西是美丽的,并非易事。玫瑰的美并非像圆和平面存在于盘子里那样天然地存在于世上。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趣味上的不一致。当然,说玫瑰是美丽的也有某种基础,毕竟有那么多人同意玫瑰是美丽的,而蟑螂是丑陋的。休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就说趣味判断是“互为主体的”:有趣味的人愿意彼此认可。康德相信,对美的判断是普遍共有的,而且基于现实世界,尽管它们实际上并非“客观的”。这怎么可能呢?
康德是现代科学心理学家的前驱,他们研究美的判断的方法,是观察婴儿喜欢什么样的面孔、如何追踪观看者的眼睛运动,或引诱艺术家做磁性共振形象(MRLs)。康德注意到,我们的典型做法,是把标签或概念用于世界以为合目的的感觉输入分类。例如,当我在洗碟机里发现我认为是盘子的圆而平的东西时,我就把它和其他盘子一起放到碗盘橱而不是勺子柜里。美的事物不是像盘子和勺子那样用于满足人们的日常目的的。美丽的玫瑰令我们愉悦,但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吃它,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把它摘下来做插花。康德的认识方式是说,美的事物乃“无功利的合目的性”。这个奇妙的术语需要进一步展开。
美与无利害性
当我知觉到红玫瑰之美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就把它放入我贴着“美”的标签的精神条目柜里——我也不会立即把讨厌的蟑螂扔进我的“丑”的条目的精神垃圾箱里。但对象的不同特性,却几乎是迫使我(“诱使我”)不由地为之贴上标签。玫瑰可能有自己的目的(产生新的玫瑰),但这不是它美丽的原因。其色彩和结构排列方面的状况激发了我的精神才智,使我认识到对象是“正确的”。这种正确性,就是康德在说美的对象是合目的时候所指的意思。我们称一件事物是美丽的,在于它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或“自由发挥”了我们的精神才智;我们称某事物是“美丽的”,是因为它带来了这种愉悦。当你称某物美丽的时候,你由此而断言人人都该这样看。尽管这个标签受主观意识或愉悦情感的刺激,但恐怕对世界产生了客观作用。
康德警告说,美的愉悦和其他类型的快乐有别。假如我花园中成熟的草莓有红宝石般的色彩、质地,而且味道如此地诱人,以至于我一下就送进了嘴里,那么审美判断就被玷污了。为了欣赏这个草莓的美,康德认为我们的反应必须是无利害的——独立于其目的和它带给我们的愉悦感。假如有观者对波提切利的《维纳斯》产生色情欲望,好像她是供欣赏的艳女,他实际上就不是在欣赏她的美。假如有人喜欢看高更的塔希提绘画而幻想着到那里去度假,那么他就不再与它的美有审美关系。
康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并不认为上帝在艺术和审美理论中担当解释的角色。人类需要天才来制造美的艺术,他们由于具备了这种支配事物的特殊能力而创造了官能之间的和谐,把观者潜在的快乐调动出来(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考察一个实例,勒努勒的凡尔赛花园)。总之,对康德来说,审美是在具有美感的事物刺激我们的情感、才智和想象之后才有的。这些官能是被以“自由展现”而非任何更用心和勤奋的方式激活的。美的事物吸引我们的感官,但却是以冷静、超然的方式。美的事物的形式和外观是最重要的特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关键。我们对事物外观的正确性做出反应,它满足了我们的想象和理智,尽管我们没有对事物的目的做出评价。
康德的遗产
康德发展了对美及我们的反应方式的论述,但这并不是他的艺术理论的全部,也不是说他坚持艺术必须是美的。不过,他对美的论述已成为后来强调审美反应观念理论的中心。许多思想家坚持认为,艺术应该激发一种对距离和中立性的特殊而无利害的反应。康德对美的看法形成20世纪的众多分支,如批评家强调促使观者以审美的态度欣赏像塞尚、毕加索和波洛克那样新型而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家。像克莱夫·贝尔(1881-1964)、爱德华·布鲁赫(1880-1934)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1909-1994)这样的艺术写作者,接受各种观点并为不同的观众写作,但他们对待康德美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如,贝尔1914年的文章就强调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有意味的形式”特别强调了激发我们审美情感的线条与色彩的结合。批评家可以帮助别人看到艺术中的形式,并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独特而高尚的:贝尔把艺术说成是形式曲高和寡,并坚持认为艺术与生活和政治无关。
剑桥大学文学教授布鲁赫1912年写了一篇著名文章,把“心理距离”描绘成体验艺术的先决条件,这是对康德的美是“想象的自由展现”的观念的改进。布鲁赫的观点是,性或政治主题往往阻碍审美意识:
……直接涉及官能之爱、身体的物质存在、尤其是性事物,通常都不能达到限制距离的要求,只有特别谨慎地借助艺术才能达到。
显然,梅普尔索普和塞拉诺的作品作为“艺术”的代表,距离布鲁赫心目中的要求最远。
而波洛克的主要鼓吹者格林伯格,称赞形式是绘画或雕塑得以取得高品质的手段和创造条件。观看作品的关键不是看它表现了什么或“说”什么,敏锐的观众(有“趣味”)要看的恰恰是作品的平面性及其把颜料作为颜料的处理方式。
在把艺术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说法上有许多重要的竞争者,我将考虑某些后起之秀。但像康德和休谟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观点,仍然在今天关于品性、道德性、美和形式的讨论中回响。艺术专家为在展示有梅普尔索普作品的辛辛那提美术馆进行的淫秽实验作证说,他的图片之被算作艺术,在于其精到的形式特性,如讲究的用光、古典的构图和优雅的雕塑形象。换句话说,梅普尔索普的作品满足了对真正艺术“美”的期待——即使有着硕大阴茎的人体也应不动声色地被看做是米开朗基罗《大卫》的同宗。
那些支持者是如何为塞拉诺的《尿基督》辩护的?这幅照片极大地冒犯了许多人。塞拉诺还制作了其他一些引起争议的照片:针对着可怕的死尸的《太平间》系列;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形象《天堂与地狱》,表现的是一个穿着红衣服打扮成红衣主教的自鸣得意的男人(其实是艺术家列昂·格鲁伯),旁边是一个上吊的女人体和鲜血淋漓的躯干;《卡贝扎·德·瓦卡》的特点是用一个被斩首的牛头,似乎令人不安地窥视着观众。批评家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迎着挑战来解释这些作品,在1990年4月的《美国艺术》上撰写了一篇评论塞拉诺的文章。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评论,看看艺术评论家是如何谈论引起争议的当代艺术的。由于她强调艺术的内容和塞拉诺情感与政治评价,利帕德提出了一个与康德20世纪后继者的审美形式主义不同的传统。
为塞拉诺辩护
利帕德给塞拉诺的辩护采用的是三相分析法:她审查了1.作品的形式和材料特性;2.内容(作品表现的思想或含义);3.语境,或其在西方艺术传统中的位置。每一步都很重要,可以让我们更详细地评价它们。
首先,利帕德描述了如何观看像《尿基督》这样的一幅作品及其创作过程。许多人非常厌恶作品的题目,以至不忍观看;其他人只能看到很小的黑白复制品。我的学生认为它表现的是厕所中或尿罐中的基督受刑图——二者都不对。实际的图片看上去与杂志或书里的小样不同——就像狂热的崇拜者会说,复制品无法传递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本身的品行一样。《尿基督》是一幅巨幅彩色照片:60x40英寸,色彩泛黄,丰富而发光。这是一种很难控制的材料,因为底片光滑的表面粘上指印或哪怕一点点尘埃都容易报废。
尽管这幅图片是用(艺术家自己的)尿做成,而且题目中也有“尿”字,但尿不可这样理解。基督受难图看上去大而神秘,沐浴在金黄色的液体之中。利帕德写道:
《尿基督》——挑剔、发怒的对象——是一个具有忧郁美的照片形象。……这个小型的木与石膏做成的受难基督,由于在显示着既不详又荣耀的深深的金黄与玫瑰流中飘荡而使图像放大,最终产生了纪念碑的感觉。气泡漂过表面暗示着星云。而作品的题目——这对整个计划至关重要——只是改变观看情境就把这种易于理解的文化圣像转化为一种反叛符号或一个令人厌恶的对象。
塞拉诺的题目是刺激人的(这无疑是故意的),好像我们注定被那些神秘的、抑或甚至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撕成两半——要么为之震惊,要么为之冥思。
考虑到艺术品的“材料”性能,利帕德解释说,塞拉诺并不认为体液是羞耻的而是自然的。也许他的态度来自其文化背景:塞拉诺是美国一个少数族群成员(其血统一半是洪都拉斯,一半是非裔古巴人)。利帕德指出,在天主教教义中,身体受难和体液,千年来一直被描述为宗教权力和力量的来源,教会的小瓶里装着的是纪念圣人和圣迹的织品、一点血、骨头甚至颅骨。人们并不认为这些圣物给人以痛苦或恐怖,而是受到人们的敬畏。也许伴随着塞拉诺成长和回忆的是他与肉身神灵的生命交会,而不是他在他周围文化中所看到的。艺术家试图谴责的是,文化只是口头为宗教服务而不是真正认同其价值。
形式和材料的讨论很难不逐渐进入内容的讨论。我们在考虑艺术家想要表达的含义时,已经开始进入利帕德的第二相分析。塞拉诺告诉利帕德他的宗教关怀说:
我创作宗教画已有两三年的时间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创作了大量的宗教绘画!我沉迷于此竟一点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拉丁美洲人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欧洲人的事情,而不是美国人的事情。
塞拉诺声称,他创作的作品不是要谴责宗教,而是谴责其制度——展现我们当代文化是如何日益商业化并贬低了基督教及其圣像的。利帕德通过提示支持了这一说法:艺术家1988年制作了一组类似作品,把西方文化中的其他圣像,从教皇到撒旦,都漂在尿中展示。对其他如《天堂与地狱》这样令人不安的作品的内容或含义的分析,需要进一步讨论利帕德的“语境”。
利帕德为塞拉诺所作三项辩护中的第三点,随后脱离了对其作品之形式特性或主题的讨论,而谈论其灵感来源和艺术经历。塞拉诺曾提到他与“西班牙艺术传统的紧密联系,其中可能既有暴力的一面也有优美的一面”,特别提及画家戈雅和制片人路易·布努艾尔(Luis Bu?uel)。这种艺术史的语境是有趣和重要的,但又是复杂的。我将只瞄准其中的第一位,并非常详尽地考察戈雅的作品,以评估利帕德将塞拉诺有争议的当代艺术与这位著名而受人尊敬的西班牙先驱联系在一起是否应用了合理的策略。
戈雅——先驱者?
佛朗西斯科·戈雅(1746-1828)是休谟和康德的同时代人,当代民主价值的拥护者。他的一生横跨美国和法国革命,经历了法—西伊比利亚半岛之战的恐怖。按照西方艺术的标准,他作为天才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1799年成为西班牙国王的钦命画家时,戈雅以披裹镶金制服的贵族和身着华丽绸缎的淑女肖像而闻名。他画人们熟悉的西班牙风俗场景,如斗牛,但性和政治却从未远离他的艺术,他迷人而引起争议的《裸体的玛哈》他引起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注意。
戈雅目睹了拿破仑军队入侵西班牙时喧闹的政治事件,画了许多战争、骚乱、暗杀的场面,如著名的《1808年5月3日的枪杀》,无辜的市民被一队无情而没有姓名的拿破仑士兵枪毙了。画面中央站着一个人,在子弹击中的一瞬间极为恐慌地张开双臂;另一些人则倒毙于血泊之中;神甫们掩面于大屠杀的恐惧之中。有人会说这种死亡的场面在西方艺术中并非鲜见,艺术家利用殉教圣徒的宗教形象来描绘新的政治殉难者。
戈雅的艺术使人们正视极端危难之际人类天性中可怕的一面。在《加普里乔斯》系列中,戈雅创造了道德沦丧的兽行形象,场面画成妓院和漫画的样子——人画成鸡,医生画成驴。画家为其目的辩护道(以第三人称自述):
谴责人类的过失和罪过——尽管这好像是修辞和诗歌的禁地——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绘画对象。他从每一个市民社会常犯的各种愚蠢行为和错误中选择适合其作品的主题,还从被作为习俗、无知或自私而宽恕的常有的昏噩和谎言中选择主题,他认为这些是最适合于讽刺的素材,同时还适合于展开作者的想象。
可能有人会说,戈雅的道德主张使他不同于像塞拉诺这样的艺术家,因为(有人认为)塞拉诺寻求轰动效应,或者说像《尿基督》和《天堂与地狱》这样的作品中,形象的含义过于模棱两可,而戈雅的地位似乎是清晰而可辨的。但这种比较不那么容易做出。因为戈雅支持法国大革命,人们把他设想为启蒙运动的忠实信徒,和休谟与康德这样的人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但戈雅目睹了入侵西班牙期间可怕的暴行,一面是暴力,一面是反击。他在令人不安的系列作品《战争的恐怖》(1810-1814)中一而再地召唤这样的情景,清楚地表明,在这场战争中没有道德赢家:有一位法国士兵闲荡就有一位农民被绞死,然后农民又砍死一位衣冠楚楚的无助者。戈雅的素描似乎是以表现砍头、私刑、刺杀、钉死等没完没了的可怕场景来反对启蒙运动关于实现进步、改革人类、达到纯粹道德的愿望。
不仅对政治失望,在一场可怕的疾病导致他失聪之后,艺术家似乎陷入了惨淡无望之中。他画在自家墙上的《黑色绘画》成为整个艺术史上最令人不安的作品之一:《农神噬子》描绘了一个吃人肉的杀婴犯肢解人体的血淋淋场面。其他形象尽管没有那么血腥和残暴,但甚至更加令人不安。他的《巨人》安坐如泰山,威吓大地,庞然如独眼巨怪;《沙冢之狗》是一个在狂暴的自然力中不知所措的可怜动物,孤独而绝望。用审美距离说就无法评价戈雅的这些晚期作品。它们是病态心理、病态想象或健全心态一时失足的产物吗?由于这些作品表现了痛苦或其道德立场模糊,戈雅已不再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否认这一点就是完全教条的表现。
这段艺术史的迂回简述,使我们可以对塞拉诺把戈雅看做是形象联结起美与暴力的先驱者的声言,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回想一下,这种比较是利帕德为塞拉诺常常引起麻烦的形象所做辩护的一部分。当然,诋毁者可能会说戈雅与塞拉诺不同,因为他有更大的艺术才能,因为他描绘暴力而没有赋之以美感或使人震惊,而恰恰是为了谴责它。每一种观点都有问题,人们将很难将任何一位20世纪艺术家与像戈雅这样的老“大师”相比较。我们无法了解历史的最后审判,而且不是戈雅并不意味着就完全缺乏艺术才能。利帕德合乎情理地论辩道,塞拉诺的作品展现出他的技巧、训练、思想和精心准备。
其次,很有可能戈雅所有的作品并不是在宣称一种道德提升,而是相反,说人类的天性是可怕的。可以说,哀悼是艺术中合理的意思,即使呈现出使我们无法保持审美距离的震撼内容时也是如此。也许塞拉诺是想侮辱现有宗教,但这可能来自一种道德动机。当他为死尸拍照时,可能并非沉迷于其衰败,而是为人类偶尔出现的同情提供匿名对象。这样的目标将确定他与其出类拔萃的前辈艺术家戈雅之间的连续性。
结论
近年来的艺术品结合进大量的恐怖:摄影家展示死尸或极为可怖的动物头;雕塑家陈列生蛆的烤肉;而表演艺术家则倾倒整桶整桶的血。我还会提到其他使用类似题材的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佛朗西斯·培根绘画中扭曲的人体,或安塞姆·基弗大型黑画布中对纳粹炼尸炉的再现。
至此,我已对两种艺术理论提出了质疑。作为集体仪式的艺术理论没有考虑到许多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和影响。走进宽敞、明亮、有空调的美术馆或现代音乐厅的感觉,可能会有某种仪式感,但与那些像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有着超验价值观的严肃参与者那种仪式感完全不同,如玛雅或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聚会。因为我们不是试图与上帝和更高的现实沟通,或抚慰我们先辈的灵魂。
但是,当下艺术用康德或休谟那种基于美、良好的趣味、有意味的形式、超然的审美情感或“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理论都无法做出辩护。确实,有许多批评家称赞了梅普尔索普照片的优美构图和赫斯特里面悬着动物的发光展柜的优雅风格,但即使他们发现了作品的美,其触目惊心的内容也需要思考。也许无利害性对于我们要费劲地观看和理解那些好像非常矛盾的东西才能接近的生涩艺术已没什么作用了,但作品的内容仍非常重要,我认为赫斯特的题目就是这样——他使观众直接面对难题,如有鲨鱼的作品题目是《在某些活人心目中物理死亡的不可能性》。
通过对往昔的重要艺术家戈雅作品的回顾,我提出,按照西欧的标准,像塞拉诺那样丑陋或令人震惊的当代艺术有明晰的前驱来源。艺术不仅包括有“趣味”的人欣赏的形式美作品,或表现美与道德提升的作品,还包括表现破坏性反道德内容的丑陋而令人不安的作品。如何解释这样的内容还有待作进一步讨论。
(译自辛西娅·弗里兰《这是艺术吗?》一书第一章,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题目有所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