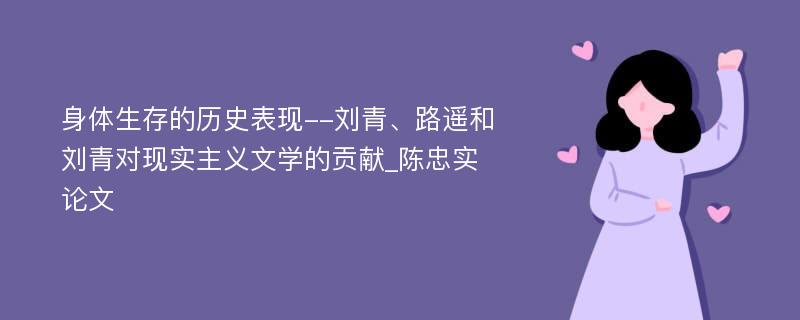
肉身生存的历史展示——柳青、路遥、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肉身论文,现实主义论文,贡献论文,路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柳青、路遥和陈忠实都是“农裔城籍作家”,有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都把笔触伸向乡村、伸向底层生存者。柳青从40年代的《种谷记》到60年代的《创业史》,一直把中国农民的命运作为自己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为了写好农民,他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多年,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推进社会发展,体验农村新生活的苦与乐。路遥自觉以柳青为师,公开倡言:“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因为在大地上生存的亿万农民,既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及未来走向①。陈忠实也是在学习柳青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他在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后记中说,“农民在当代中国依然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我是从这个世界里滚过来的”。“这样的生活阅历铸就了我的创作必然归属于农村题材。我自觉至今仍然从属于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②。他们三人为中国当代文坛奉献了一部又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这些作品不但以其特有的形式感染了几代文学大众,也为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当代中国农民肉身生存的历史展示。
一
作为农民的儿子,三位陕西作家深知在中国广大农村这一乡土社会,自古至今,农民一直是肉身化生存者。在乡土社会中生存,就意味着人的肉身能在乡土社会中活动,并占据着乡土社会的一方空间。在乡土社会中能够继续生存,其标志就是自己生了儿子,育了孙子。乡土社会用“肉身”作为“自我”的代名词,这里用“自身”称谓“自我”,用“身世”称谓个人经历与遭遇,用“立身”称谓获得做人资格,用“终身”概括整个人生历程,用“身前身后”表述生前死后。因此,乡土社会是一个肉身化的社会。
对这种独特的生存景观,我们的祖先为乡土社会的精英创立了一套“修身”哲学,其中孔子的《论语·宪问》最引人注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有病诸?’”在孔子心目中,“修身”不但是任何一个君子立身做人的根基,而且是让广大百姓安心的重要条件,其最高境界连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未能完全达到。为使人的自然肉身转化为人化的肉身,他提出用射、御、书、术来锻炼人,用习礼习乐的方式来培养人,使人的视容、听容、手容、足容充分人化。孟子更把“修身”与治天下联系在一起,提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之后,儒家经典《大学》更进一步提出修、齐、治、平的做人程序与方向。在儒圣看来,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中心是人的肉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肉身正则天地正,肉身斜则社会歪。
与儒学的精英们相对,下层百姓的人生志向则在“养身”,其实质在于使出全副看家本领“养活”双亲之身,“养活”老婆、娃娃之身,“养活”一己之身。在农耕文明中,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商品经济的落后,一个男子汉要“养活”一家老小的身体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能够“养活”父母之身的就是“孝子”,能够“养活”儿女之身的就是“慈父”,若能在此基础上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把自己养的精精壮壮,就是受人羡慕称誉的角色了。反之,自身饿得面黄肌瘦,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男人,则是被人瞧不起的缺乏养家糊口本领的“笨熊”。挣扎在“养家糊口”生存线下的肉身生存者,都有一副空虚匮乏、亟需填充的身架,时时处处想用“吃”来填充自身,并由此为自己创造了一套最具乡土特色的“吃”文化。文化是人为了生存创造的生活方式,肉身生存者表示健康生存的话语是“我还能吃能喝”;与人套近乎的方式是“问吃问喝”,“请吃请喝”;敬神祭祖的方式是“献吃献喝”;他们最感恩戴德的统治者是“使天下皆有所养的万岁爷”;最尊敬的地方官是“让一方百姓人人都有饭吃的父母官”。所以,荀子说:“以财货为宝,以养身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这话在特定的意义,并非专指下层百姓,或者小看劳动人民;用它来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肉身生存者,则是再恰当不过的至理名言。
在古代,社会精英们考虑到“民以食为天”,在设计政治蓝图时非常重视养民之身。孔子首倡“先富后教”的思想,孟子则把先使“黎民不饥不寒”而后实行礼仪教化作为明君实行“仁政”的标志。荀子顺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政治观点。认为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国家的仓库里,“府库实而百姓贫”是亡国的征兆。汉儒董仲舒也提出了居上者只有对肉身生存者进行先富后教的治身之术,才能使下层人民感激其宽厚仁慈,服从其统治。
在乡土社会,不论上智们所“修”的“身”,还是下愚们所“养”的“身”,都不是拖累人的臭皮囊,更不是僵硬无趣的外部躯壳,而是活生生的、能感觉痛痒体验冷暖的“生灵”,它总是带着特定的情绪,以特定的姿态,穿着特定的文化服饰,向世界传达特定的生命信息,与其他生灵进行对话交流。乡土社会称呼肉身生存者为“生灵”,将各种肉身生存活动总称为“生活”。对此,柳青、路遥和陈忠实都有切身感受和深入认识,他们都把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体验作为自己文学创作和诗意思维的主要维度,着力表现当代中国不同时期广大农民肉身生存的悲喜命运。他们的作品都关注肉身生存的核心——饥饿、情爱和性欲问题,都把最切身的肉身体验——痛苦、挫折和悲伤作为描写对象,为读者塑造出了各具时代特性的肉身生存典型,让读者充分感受那个时代的生存气息。
柳青写作《创业史》的年代是一个政治热情高涨的时期,全国人民一心想着超英赶美,直奔共产主义。那个时代的关键词是“政治挂帅”,解决几亿肉身生存者的吃饭问题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每一个肉身都以是否处于“饥饿”状态来进行政治划界。饥饿者如梁生宝、高增福是贫下中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动力;温饱者如姚士杰、郭世富是地富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梁生宝们勒紧裤腰带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是要解决几亿处于饥饿状态的肉身生存者的温饱问题,他们置自身的“饥饿”于不顾,最大的快乐在于“吃苦”而不是享受。至于情爱和性欲,那是次要的,甚至有腐化堕落之嫌,与革命者的远大志向相互抵触。以当时的社会风尚,如果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就应该把自身的人生历程当作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把共产主义思想从里到外融化为自然本性,并不断过滤自身欲望的过程。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员,柳青自觉地用文学作品捍卫新生的政权,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笔下的人物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烙印的肉身化的“政治人”,他歌颂以梁生宝、高增福为代表的饥饿的肉身生存者,歌颂他们身上迸发出的社会主义创业热情,歌颂他们不顾自身安乐的共产主义精神;同时,鞭笞以姚士杰、郭世富为代表的追求个人发家致富的肉身生存者,鞭笞他们身上的个人主义享乐思想。
路遥创作《人生》等作品的时候,正值中国社会又一次转型期,政府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城乡差别”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关键词。这在听了几十年“以粮为纲”的宣传,饿着肚子,却为“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而自豪的乡里人看来,如同头上突然浇了一盆冷水。乡民们打个激灵之后猛然醒悟,自己一向瞧不起的小市民原来活得要比自己滋润,于是闷起头狠劲侍候自己那几亩庄稼地,让自己发起来也过几天滋润的日子。然而,靠种庄稼发家又谈何容易,于是老一代的庄稼人叹一口气,安慰自己说:“土地是个宝谁也离不了。”他们不想折腾,再说也没有折腾的本钱,只好安心守护自家的几亩地。青年人则不一样,他们思谋着,城乡差别不就是人的肉身位置的差别吗?城市在中心,乡下是边缘,置身城市就意味着置身于社会中心,不但能够白馍果腹,制服遮体,还能够迎来周围艳羡的目光,享受做人的光荣与尊严。置身乡村就意味着置身边缘,只能黑馍果腹,粗布遮体,它让人活得没声没息、没人搭理。既然中心和边缘,光荣与黯淡,只是身体位置的问题,年轻人为何不让自己的身体挪动一下呢?树挪死,人挪活,使出浑身解数向城市挪动吧。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城市自身对于外来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想进入城市必须得到一张城市户口。虽然乡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都是户口,但是这两种户口之间却有着不可逾越的疆界。从城市到农村是从高往低,很容易,但是很少有人做这种傻事。从乡下到城市是从低往高,非常之难,那时即使拼命考上大学的人,到了分配时也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所以,一个想变成城里人的乡下人,进城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那些渴望从乡土抽身,向城市进身的边缘生存者,默念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想方设法要跳出农门,跨越城乡的疆界,思谋着:城市里也没写着就该准来安身,我进城安身没什么不对!事实上,乡下人想进城和城市用力把乡下人推回乡下,是当时令人无奈的一种现实,从主观愿望来说,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当时的城乡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阻止人们随意越界。《人生》中的高加林是越界者,他没有穿墙术,只有越界的豪情壮志,然而“墙”是无情的,它不认豪情壮志,越界者一定要以头撞“墙”,显示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进身决心。路遥所塑造的就是这样一些越界者的形象。
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念头起于80年代中后期,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城乡差别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缩小,社会的民主进程也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快速推进,旧的社会问题没完全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出现了。于是,一些人想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痼疾,另一些人则想从民族文化中寻找整治当下问题的良药,中国大地卷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文化心理”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思想界把目光转向新儒学及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经济界则关注台湾、新加坡、韩国这一儒学文化圈的现代化特征;文学界则出现了《古船》这样具有广泛影响的寻根作品。受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陈忠实决心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者身上挖掘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源。“文化是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③,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精神活动,都有特殊的创造和表现本民族精神活动的途径和方式。中华民族从文化创始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始,就用心关注、调节、运转、安顿我们的生命。“中国人首先重德,德性这个观念首先出现,首出庶物”④。德性是通过具体生存者的行动来践行的。在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者那里,被具体化为生命的生生不息,绵延无穷。《白鹿原》描写的就是乡土社会中那些肉身生存者为了追求自身及家族生命的生生不息,有意识地把自身装扮成狼或鹿,在原上演出的一幕幕鹿狼争霸的悲剧,以及灾难深重的人们对白鹿精灵的深情呼唤。小说开头描写白嘉轩为避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悲剧娶了七房女人,并对此极尽铺排;对于一向光明磊落的白嘉轩,竟为了得子得福而实行换地阴谋,也进行着力地渲染,都反映了乡土社会肉身生存者的一种生命文化观。陈忠实极力挖掘每一个乡土社会肉身生存者身上的这种文化蕴涵,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作为肉身生存者都是活生生的,具有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或者毒素,都对解密我们民族文化的内蕴具有一定的作用。
二
文学自古以来在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者眼中就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为脚踩大地眼望蓝天的肉身生存者探索生活的尺度,树立生存的楷模,衡量肉身生存者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肉身生存者是向死而生的生灵,从来都把自己的生存当成追寻生存意义、创造生命价值的艰难历程。当我们走遍三秦大地,仔细观察所有为肉身生存而奋斗的边缘生存者时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活得响当当、鲜亮亮,没有一个愿意自身活得没声没息,因此每个肉身生灵降生到这个世界一个月的时候,家人都会尽己所能为他举行一次满月宴会,让他的肉身在街坊邻里、远近亲戚面前鲜亮一下;每个肉身告别这块大地的时候,后代都会叫来一帮响家子(乐人),弹唱一番,用乐声告诉世人一个鲜亮的人响当当地走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在肉身生存者眼中就是鲜亮亮、响当当的人生,那么,人怎样才能凭自己的本领把自身活得响亮呢?这既是一个切身的生存问题,又是一个费人思量的哲学问题。作为农民的儿子,柳青、路遥和陈忠实对此非常清楚,他们知道面对广大的乡土社会写作,就是要为肉身生存者探寻和塑造活生生的做人榜样,让他们感到只有这样做人才有顶天立地的模样。作为陕西作家,他们在陕北看过乡民们头上用白羊肚手巾打的“英雄结”,在关中听过乡民们挣破喉咙吼出的“秦腔”,亲身体会什么叫做三秦大地的血性男儿,也更理解这些肉身生存者的愿望。
柳青是从乡土中挣扎出来的革命文学家,他带着双重使命探索生存的尺度、塑造人生的榜样。一方面,他的探索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要符合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种探索还要满足几万万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挺直腰杆做人的愿望。为此,他提出作家必须进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去学习,把他们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认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⑤。进前两个学校是要求作家以一个切合社会政治的身份介入生活,不仅了解生活,还要明辨生活中的是非。进“艺术的学校”要求作家在生活中保留读书和写作的空间,把握以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勾画生活的权力。一个只知道追随政治潮流,或只是被政治潮流推动着走的人,虽然能感受到生活底层蕴藏的巨大力量,却无法采取艺术的眼光和手段,去发掘和表现其中存在着的生动的形象;而一个只站在生活边上把玩艺术,不愿意关注时代和社会的人,则只能看到纷纭变幻的生活表象,无法真正感受和传达生活中动人心魄的力量。柳青认为,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具有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精神,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在三个学校里勤勤恳恳学习一辈子,既不偏废也不见异思迁。柳青把自己的学习成果结晶为梁生宝这样的创业英雄形象,这个英雄作为乡土社会众多肉身生存者的一员,他懂得群众迫切要求发家致富、过上滋润的日子的愿望,所以只身赴郭县买稻种,以提高粮食产量;他相信只要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就能创社会主义大业,所以积极组织精壮劳力进终南山割竹子,壮大了互助组的基业,增强了互助组的凝聚力。柳青笔下,创业英雄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存者,他也要吃、喝、拉、撒,也有爱的欲求。只是“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这热火使他“把人民的事包揽在自己身上,为集体的事业操心,伤脑筋,以至于完全没有时间和心情思念家庭和私事”⑥。梁生宝是那个重视理想和“大我”的时代,肯于为理想和“大我”献身的新中国农民典型。对此,《创业史》并不回避写人物的肉身感觉,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加以表现,把时代背景、肉身欲望和作家对于人性的理想融合为一体。当朋友知道他喜欢改霞,劝他主动拥抱、亲吻改霞时,他骂人家说的是“烂脏话”,这样的细节描写并不表示梁生宝不是一个肉身存在,而表现他面对个人的欲望,却羞于为自身着想,为那个时代的乡土大众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并因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每一种生存探索都是在特定境遇中的探索,每一个人生楷模都是特定人群的楷模。作家是在特定境遇中写作的人,同时又是为特定境遇的读者写作的人。创作与阅读是一种共谋的关系,作者和读者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彼此寻找,相互影响,作者选择世界的某一种面貌,探索人生的某一方向,也就选中了某一特定类型的读者。当生存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读者的人生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时,作者对生存的探索,以及塑造的人生楷模也就需要调整,或者暂时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探索及其人生楷模就将鲜亮地登上历史舞台。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生活由过去的以政治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为中心,人们由关心“大我”转变为关心“小我”,目光由遥望未来转变为紧盯当下。柳青的探索和梁生宝的榜样作用黯淡了。路遥及时站出来,为社会转型期迷茫的肉身生存者塑造了高加林这样的一个榜样。
高加林是出生于黄土地、却幻想着出人头地的农村青年。他想把自己从黄土中拔出来,跳出农村,选择一种与父辈们不同的活法。“他想离开土地,不是厌恶劳动和艰苦,而是不能忍受闭塞、愚昧和屈辱,不能忍受明知贫困而又安于贫困的一潭死水。他向往城市,也不是向往舒适和奢华,而是向往文明、开放和尊严,向往那种时刻给人提供机遇的动态人生环境和允许选择、竞争、让青春和生命得以释放的积极人生观念”⑦。既然人是自由的,没有所谓先天决定论;既然整个社会在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那么,一个出生于黄土地的农家子弟探索一条离开土地的活法,不是正好符合时代的精神吗?没有人反对一个有志青年的探索,但是探索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最终要求探索者为自己的探索“买单”。在当时,城市对于农村人来说,就像卡夫卡笔下约瑟夫·K眼中的城堡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中间没有通道只有界墙,等待越界者的似乎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碰壁。高加林明知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一堵不可穿越的墙,却义无反顾地以头撞墙,即使碰得满脸是伤,也要证明自己争取自由生存的勇气。作家为人生探寻行动的尺度,为肉身生存者塑造人生的榜样。如果他是真诚的,这尺度就必然出于他对人生的认识,也适合测量自己;这榜样就必须来自他的人生体验,适合模铸他自身。路遥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写道:“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现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⑧ 路遥笔下的那些受难的越界英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生命的追求与写照。
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文化寻根和反思思潮兴起的年代。大家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满怀激情和希望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更多的不满?为什么人们在蛋白质摄入量明显增加,做人自由度显著提高的时候还要满腹牢骚?为什么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为什么中华民族历经灾难仍然能够生生不息?寻根有两个目的,一是继承五四传统,寻出民族的劣根性,进行新一轮的疗救;一是返回历史,倾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呼声。陈忠实所做的就是第二种反思活动。他认为文学是神圣的,“文学艺术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各种肤色和语系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以致不惜生命而进行创造活动的全部理由”⑨。文学的魅力主要来自对生命的呵护。文学是人学,是专门调节、运转、安顿人的生命,为生命寻找测量的尺度,让人生充满诗意的栖居地。一个具有生存尺度的人,才会成为自我的真正的主体,倾听生命的呼唤,控制、改变和净化生命中不纯不粹、影响人生响亮度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最能增加人生响亮度的就是德行,中国文化强调德行优先原则。“人所最关心的是他的德行,自己的人品,因为行动更有笼罩性与综纲性。行动包摄知识于其中而为其自身一附属品。他首先意识到他的行动之实用上的得当不得当,马上跟着亦意识到道德上的得当不得当。处事成务,若举措得不得当,则达不到目的,因此他难过。待人接物,若周旋得不得当,他觉得羞耻。羞耻是德行上的事。这是最尖锐,最凸出,而最易为人所意识者。知识不及,技艺不及,是能力问题。德行不及是道德问题。前者固亦可耻,但不必是罪恶;而德行不及之愧耻于心则是罪恶之感。”⑩ 德行优先原则,要求每一个肉身生存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道德,否则就是没有走上做人之道。陈忠实于是走进早已被当代人遗忘的白鹿原,寻找当年曾经拯救了人的白鹿精灵的踪迹,塑造当年为乡土社会树立榜样的朱先生的形象。朱先生是德行文化的化身,他的言行都以“仁义”为根本、以民生为核心。当白、鹿两个家族为争地混战一团时,他用诗化解矛盾,使他们把自己的居所变成“仁义白鹿村”。他只身徒步到乾州义退清兵,使西安民众免遭大难。主持放粮救济灾民,高风亮节净化白鹿原。白发从戎赴国难,暮年壮志冲霄汉。历尽艰辛修县志,秉笔直书正气凛然。他一生不做官,不图利,践仁践义,是一个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文化英雄。他用德行关怀百姓,也用德行呵护自己。
陕西当代三位现实主义作家,严格履行了自己作为当代社会“书记官”的职责,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了当代中国人不同阶段的生存肖像,描绘了当代楷模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走过的每一步路,可以感受到不同时期肉身生存者的希望和梦想,挫折和感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立下了一座座里程碑。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经济效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幸福”成为人生活中最大的、甚至唯一的追求,“崇高”在人心中越来越淡漠。于是在编写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时候,我们总觉得陕西这三位作家史诗情结太浓,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太高大、太理想。我们批评那些高尚的人是一种忘记个人幸福的单向度生存者,觉得他们为高尚而牺牲幸福很不值得。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也许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为幸福而忘了高尚的存在,拿出卖高尚而换取幸福是否就很值得。文学是人学,人永远都走在学习做人的路上,文学永远都行进在探索人类尺度的路上,因此,回视以往的人、以往的文学,我们应带着一种温情和理解,决不能吹毛求疵,正因为它是片面的、有缺陷的,所以它也和我们一样——有人气、有生命,因而有着存在的权利。
注释:
① 路遥:《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② 陈忠实:《四妹子》,中原农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③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④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⑤ 柳青:《柳青文集》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⑥ 柳青:《柳青史集》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⑦ 马一夫、后夫:《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⑧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⑨ 陈忠实:《凭什么活着》,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⑩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