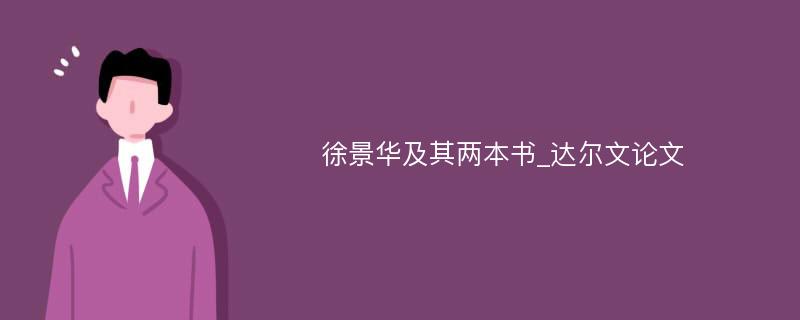
关于许靖华和他的两本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本书论文,许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七期“文事近录”栏摘录了台湾《远见》杂志上许靖华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质疑,因我刚读完许靖华的《大灭绝》,读到这则摘录,仿佛感到了一种回应,欣喜之余,引起许多关于许靖华的联想,尤其是他对达尔文主义的质疑和批评。
许靖华,一九二九年诞生于南京。十五岁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十九岁获理学士学位,以优等生资格获奖学金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深造,得硕士学位。二十五岁成为理学博士。他在美国生活、求学和工作近二十年,于一九六七年移居瑞士,任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教授至今。
许靖华在地质学、海洋学和环境科学等许多科学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九○年间,他共参加或组织了十多次大型国际科学合作研究项目并担任重要职务。他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九八五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他还致力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沟通和融合,以通俗的文笔介绍地学领域的重大成果,使能影响人类思想的地学新发现新观念为社会大众所认识。
一九九三年秋,我在南京中科院古生物所短期工作,十月十二日,与几位友人参加了南京大学授予许靖华博士荣誉教授授职仪式。那天逸夫楼学术大厅里座无虚席。许先生接受聘书后的答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的忧患意识,是一位智者经历多年艰辛的科学活动所得到的顿悟,尤其是他对自身以及科学本质的反省,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科学发展到今天,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一方面,社会上的大众对科学和科学家怀有一种尊敬和羡慕;另一方面,社会上对科学家又有着一种鄙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是科学政策,而更主要的是科学界内部的一些人搞坏的,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崽”。许靖华把那些不是真正献身科学的人称为“科学崽”。科学崽败坏了科学的形象,从而使得科学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在国外,某些搞技术、物理的,只顾向大公司出卖自己,去挣钱,而不管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将来。在国内也存在这种现象,一些科学家为了某种目的甚至于说假话,更是违背了科学家应遵循的科学道德。
对目前科学界存在的问题,他讲了一个“呆子找钥匙”的故事:晚上很晚了,警察看到一个人低着头在广场上走来走去找东西。警察忍不住过去问他在干什么,这人讲,我正在找钥匙。警察便帮着他找,又细致地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警察便问,你在哪里丢的钥匙?这人指着广场边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说,我在那里丢的。警察感到疑惑:那你怎么在这里找呢?这人答道:因为这里有亮光!许靖华感叹现在有许多科学崽就像这个呆子找钥匙一样,只在容易出成果的领域从事研究,只是去证明着,而不是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许靖华于八十年代中期曾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工作了三年,在二十名成员中只有他是地质学家。在讨论一项提交联合国大会批准的议案时,他与其他十九位成员产生了分歧。议案是有些物理学家建议将核废料倾倒入大洋洋底。在论及核废料是否会对人类和环境带来危害时,有的物理学家讲,原子能给人类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危害,医学家也持这种观点。讨论了三天,主席最后宣布,虽有一些危害,但全体一致通过同意在大洋底倾倒核废料。许靖华注意到这一点,发表声明:“这是除我之外的‘全体一致’”。就因许靖华的反对,这项方案没能通过。“在我所从事的科学活动中,我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没有这次反对的意义重大”。许靖华如此说。他最为关注的是全球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生存,“我并不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一定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前景,火箭、原子能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也许将是毁灭,人类的自我毁灭将比恐龙的灭绝更为悲惨。”许靖华入世的态度是积极的,“科学家应具有社会参与精神,当代社会,科学家已不可能封闭在纯粹的科学王国中。”
使我震动的是许靖华最后的发言,他自以为近年来所从事的另一件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活动就是对达尔文的质疑尤其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在谈到达尔文主义时,他用了“邪恶”一词。直到读完他的《大灭绝》,我才理解了他何以用“邪恶”一词。
我对许靖华的“认识”缘于他的《地学革命风云录》。
一九八五年夏天,当时的深海钻探计划(DSDP)主席来青岛访问,在他做的有关深海钻探的报告中,配以数量颇多的照片,其中就有关于许靖华的“特写”,他介绍说“许上船前是一个固定论者,下船时成了板块学说的拥护者。””他还介绍了许靖华写的一本记述深海钻探的书。后来我得知,这就是《地学革命风云录》。我五年以后才读到这本书。
这本书叙述的故事,都是围绕一艘船、一场革命以及在船上从事这一革命实践的人物的。这艘船,就是“格洛玛·挑战者”号;这场革命,就是起始于六十年代末的地学革命。许靖华以“格洛玛·挑战者”号考察船的大洋钻探活动为主线,通过他的亲自经历,介绍了深海钻探计划(DSDP)的全过程,反映了六十年代末开始的“地学革命”及板块构造理论的发生和发展,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生动的书。
“格洛玛·挑战者”号自一九六八年夏天启航,开始了深海钻探计划,至一九八四年结束。如果不是数以千计,至少也是数以百计的人参加了它的航行。各航次的报告加起来超过八十卷,每卷厚达千页以上。许靖华描写了一批在地学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包括他的老师、朋友、同事和学生,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传记性的。尤其是他强调了他在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失误。
他在中译版的“寄中国读者”中写道:在科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解。有人认为科学“真理”是绝对的,而科学实践只不过是观察、测试和数据处理的总合。我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实践。科学研究是一个思考过程。科学行动则是推行某种思考过程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检验这些思考过程的有效性,进而修正和改善这些思考过程,以期达到更高的认识。像一切科学实践一样,科学的判断力取决于个人的经验、信仰和情绪。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或者说我们全体,在我们的专业经历中,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科学工作者应当有虚怀若谷的精神,敢于摒弃先入之见,敢于摆脱对错误思想的感情上的依附。
当然本书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了给人类思维以深刻影响的地学革命。在地球科学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即十八世纪末叶地质学的奠基时期和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地学革命。在地质学奠基以前,人们对地球历史的解释充满着《圣经》的神秘色彩。《圣经》上的洪水成了一切疑难的最终答案。十八世纪末,詹姆士·哈顿的地质学是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均变论强调物理规律的不变性,宣布了与以《圣经》为最后依据的传统观念的决裂。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加上莱伊尔的均变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均变论所向披靡。哈顿的理论本来是根据地质旅行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却逐渐滋生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前半期,地质学家们用自然状态(或条件)的永恒性替代了物理定律的不变性,从而引伸出“海陆永恒”的统治性科学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固定论”。
在地学革命以前,地质学争论的焦点是大陆漂移说。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认为:陆地曾经连接过,但不是通过后来沉没的陆桥,而是大陆间的直接连合,永存的不是个别的海盆和陆块,而是整个海陆的面积。魏格纳在他的《海陆起源》中,从大西洋两岸的地质的吻合性出发,复原了地质历史时期的海陆分布,说明大陆向西和离极漂移的两种趋向。如果没有“格洛玛·挑战者”号,如果没有深海钻探,那么这一学说不会得到验证,地学革命也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
许靖华曾是传统固定论的信徒。在一九六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登上了“格洛玛·挑战者”号,得以置身于随船科学家的行列。正是经过这次航行的实践。他接受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完成了“从梭罗到保罗”的转变。由于这一观念的转变,他被一些同事指责为传统固定论的叛徒,甚至有人把他说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科学的良心促使他面对事实,接受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大踏步向新的目标走去。
这并不是一本海洋地质学教科书,而是记叙了人类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并催生了认识自然的新思想。正是由于许靖华参加了这次带来地学革命的实践,在大量事实和发现中,尤其是关于恐龙灭绝原因的新发现,使他产生了对达尔文主义的怀疑。在书的最后,他写下了一段富有哲理性和预见性的结语:
格洛玛·挑战者号的成就,证明了海底扩张,促成了板块构造学说的诞生,结束了一场地学革命。那么,我们是否正在目睹生物科学的一场新的革命呢?达尔文在总结他的进化论时,受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那弱肉强食的年代,他目击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然而,如果恐龙灭绝的天外原因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演化的速度和方式。加拿大渥太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戴尔·鲁塞尔告诉我,恐龙的灭绝是在它的极盛时期。如果不是由于地球与一个天体的偶然相撞引起了突然的出乎意料的环境变化,它们本来是可以继续发展,赢得这场生存竞争的胜利的。今年(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访问了鲁塞尔,他给我看了一个假想的塑料头盖骨,那是由他的助手制作的。如果恐龙不是由于白垩纪末期灾变而为哺乳动物所取代的话,这个头盖骨也许能成为一种具有当代人类智慧的动物的头盖骨呢。
在《大灭绝》一书中,许靖华用通俗活泼的文字介绍了生物演化的科学事实。他描写了自十八世纪末恐龙化石出土以来,直到深海钻探计划,一切有关古生物演变及环境变化的研究历程,揭示出因深海钻探计划的成功,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生命史过程的了解。
纵观地球上的生命史,就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地球上现存的物种虽然数以百万计,但是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物种却几乎都灭绝了。因为在五亿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某一时代的物种总数变化不大,但物种的平均寿命是短暂的。现在还活着的种,大约只占地球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生物的百分之一。
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任何一种生物演化理论,不仅要解释物种的新生,而且必须解释物种的灭亡。对达尔文来说,生物灭绝的机制与生命产生的机制毫无二致。每种生物个体都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其他生物,而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在如此难以胜数的生物个体中,自然界进行着独具创意的选择,只有那些机能的特征最能适应其生活方式的种属,才能幸存下来并不断繁衍,将优秀的品质传给后代。反之,不适应者只有灭亡一途,其弱点亦将从种群中消失。当某种变化中的种群因为某种原因与主体的演化趋势隔绝,而无缘发生混种时,就会变成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种。尔后遇到有亲缘关系的种属时,其中的一种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无情地扑灭竞争对手。达尔文如此解释他的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
我想,生物界将无可避免的遵循这一规律:在时间的长河中,新的物种通过天择应运而生;而另一物种则日趋减少,乃至灭绝。起源相近的生命形成,同一种群的各种变体,同一属或相关属的物种,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结构、素质和习性,通常会陷入最激烈的竞争之中。结果造成每一个变种在演化进程中,势必对最接近的宗族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求置之于死地。
现代生物科学已证实了达尔文在百余年前提出的生命皆有共同祖先的预言。在达尔文的时代,人类对基因或DNA还一无所知,所以他的思想十分不同凡响,并引起激烈的争论。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沃森和克里克破解了DNA分子结构的共同语言,重新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孟德尔关于基因的研究之后,达尔文的预言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也昭示了达尔文的远见卓识。
许靖华质疑的其实是达尔文的“天择说”。即从生物灭绝现象出发来对其提出反证。对许多学者来说,达尔文天择理论的核心缺乏根据。生物演化的动力可能是自然选择,但是选择者并非竞争对手,新种的诞生也绝不是对老物种的死亡宣布。许靖华对达尔文质疑的根据主要是恐龙和其它古生物的突然灭绝。按照达尔文的学说,这些横行在六千五百万年以前的怪兽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失去了生存竞争的能力。动物生存竞争的竞技场是自然界,达尔文把它比作一个“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的弹性面,受着连续不断的敲击。有时敲到这个,有时打着那个。”每一个楔子好比一个生物种或变种,而每一次敲击就是天择的驱动力。由于每一个楔子可以往里挤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打进去一个就非挤出一个不可。因此,一个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想必会排斥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
许靖华在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有关恐龙灭绝的探根究源,如同副标题所示“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他以一个个独立而又连续的故事,揭示了探寻恐龙灭绝秘密的过程。在地质历史中的白垩纪末期,即距今六千五百万年前地球曾受到陨星(彗星或小行星)的撞击。正是这次撞击,导致地球上生物种属大规模的灭绝,其中最主要的是恐龙。制造这种灭顶之灾的“杀手”是来自宇宙中的“天外来客”。“天外来客”撞击地球何以具有这样大的杀伤力?当陨星撞击地球时,造成漫长与黑暗的“核冬天”降临,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引起生物链的瓦解;另外,巨大的撞击甚至可以诱发火山爆发、大陆分裂等,使全球气候与环境产生巨大灾变,从而引起大规模的生物灭绝。当然,地球还遭遇过多次陨星的撞击,而以这次为最。(一九九四年夏发生的“彗木”相撞,无疑给此说提供了新的“证据”——笔者。)
通过这种“对一个消失年代的寻找”,达尔文提出的生物演化的规律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许靖华指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失去了意义,因为大多数物种的灭绝是由灾变引起的,那么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将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正是这种大自然的灾变促成了生物演化的巨变。
这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充满激情和对人类处境的忧患意识,他的某些观点和语言也许是偏激的,但这源于他的科学良知。在中文版序言中,他写道:
……我们如今愈深究生命历史的记录资料,适者生存并非自然规律的事实就愈明显,它只是英帝国的邪恶政治哲学。愈钻研史料,就愈发现达
尔文主义主张的自然选择并非科学,而是宗教信仰。……
适者生存理论被奉为自然规律,顺应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正是为了对这种“宗教信仰”的质疑和批判,许靖华才写了这部《大灭绝》。他指出地球生命历史过程并非残酷的争斗,而应是共演,花无蜂不能传种,珊瑚无共生藻类不能存活,人类最后消灭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也会灭亡。在十亿年的自然过程中,互助共存是通则,互斗而亡才是特例。地球的生命史上根本没有生存竞争这回事,更没有保存优秀种族的自然选择。这就是近二十年来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得出的新解释。
造成达尔文思想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固然他受制于当时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水平,但更重要的是他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得到的“灵感”。达尔文的种数空间有限论,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空间有限论,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一八三八年十月,就是在我开始进行自己有系统的问题调查以后十五个月,我为了消遣,偶而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物和植物的生活方式的观察,就已经胸有成竹,能够去正确估计这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生存斗争的意义,马上在我头脑中出现一个想法,就是:在这些自然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应该有被保存的趋势,而无利的变异则应该有被消灭的趋势。这样的结果,应该会引起新种的形成。因此,最后,我终于获得了一个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达尔文回忆录》,78页,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版)
这样我也就理解了许靖华何以把达尔文主义归入邪恶的政治哲学。“发明达尔文主义的不是达尔文。他只是给了它望似可敬的科学烟幕,促成霸权主义如野火燎原席卷世界”。这部书最主要的就是告诉读者:达尔文主义并非科学,其实是以传统英国社会哲学为基础的错误的科学解释。
许靖华的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他否定了物竞天择,用与达尔文迥然不同的观点观察生命。在本书结尾,他写到:“根据我们从地球生命史中学到的更古老的格言,我相信人类必须真诚相处,不要假装明瞭谁是适者,谁又不是适者。相反,我们倒应当对各种生命形式和滋育生命的各种方式采取兼容的态度。回顾长达数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我感慨万千。这就是我对道家生存哲学的认识。”我记起在我那次难忘的海上考察中,我带上船的书中还有一本《老子》,在如摇篮般的舱室里,我曾躺在床上,听着涌浪撞打舷窗的声音,读着这本薄薄的小书,“道可道,非常道”,我记住了这句话,但我不知道是否理解了老子。对许靖华,我是否又真正理解了呢?
此文完稿后不久,我收到西安西北大学友人寄来的该书的另一中文译本《祸从天降——恐龙灭绝之谜》,信中讲此书多堆集在书库中,征订数极少。我发现此译本的序言与台湾版的有较大的差异。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于青岛汇泉湾畔
(《地学革命风云录》,何起祥译,地质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版;《大灭绝: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任克译,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四月版;《祸从天降——恐龙灭绝之谜》,翦万筹、王媛译,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