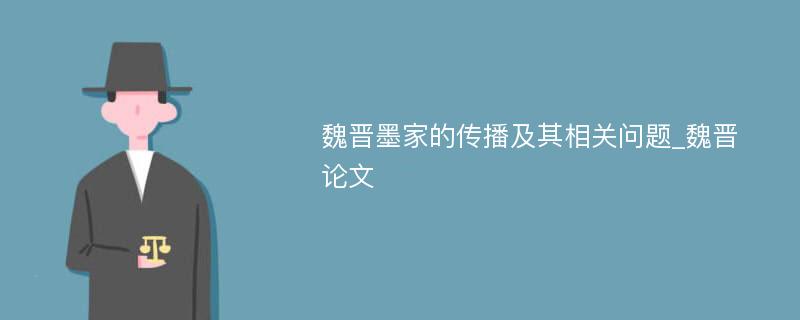
魏晋墨学之流传及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子部著录墨家书三种十七卷,又注出《田俅子》一卷至梁以来方始亡佚①。《二十五史补编》收录的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对此无所增补,丁国钧等人的《补晋书艺文(经籍)志》增晋有鲁胜《墨辩注》一种。据此,魏晋所存墨家书今可知者共五种,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录墨家书六种八十六篇相比,亡失的有《尹佚》二篇和《我子》一篇,尚存的是《田俅子》、《随巢子》、《胡非子》和《墨子》四种共十八卷,而汉晋间新撰墨家书仅有西晋鲁胜《墨辩注》一种。
魏晋以来传世墨家书较之《汉志》所录不增反减,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不少研究者都因史籍未见汉人撰有墨学著作,遂以为秦末汉初墨学已微,汉武以来竟成绝学②;进又认为鲁胜的《墨辩注》作为迅速亡佚的绝后孤响,不足以为墨学至魏晋仍在流行和发展的依据③。不过清人如俞樾、孙诒让④、近代以来如梁启超、方授楚等先生,均曾注意到汉代墨学之况及其流变⑤,贺昌群先生更梳理了魏晋以来墨学流行的不少史实⑥。可以认为,过于强调汉代墨学衰微,认其至魏晋已成绝学的看法,在观察和分析相关问题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纰漏⑦,并不符合墨学在汉晋间传播、发展和得到人们尊重的大量史实。以下试从四个方面加以申说,以明其要。
一 墨学与魏晋名理学之关联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述其上疏论事,谓“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云云。贺昌群先生上引文即以为此处“刑名”即“形名”,指名理之学,认为名、法两家夙有关联,三国初年法家学说的兴盛,也推进了名理学的发展⑧。汤用彤先生则详析《人物志》等魏晋间所撰名家新著之学理,指出“汉魏名家即形名家,其所谈论者为名理”,着力勾勒了魏晋名理学与清谈的关系,及其贯注于当时儒、法、道、玄各家学说之态⑨。从这些讨论中不难体会,在魏晋时期清谈盛行、玄学勃兴、思想活跃和学术发展的潮流中,名理学洵为其基本方法论,乃是当时学术、思想界共所关注的显学。⑩
鲁胜注《墨辩》,正须在此背景下来理解。《晋书》卷九四《隐逸鲁胜传》载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
据此,鲁胜之所以要注《墨辩》,直接原因在于时人公认辩名析理对明确同、异、是、非及道义、政化都十分重要,但早期名学著作存世很少(11),而《墨子》书中的名辩理论则自成系统,保存相当完整,遂注释整理之“以俟君子”。栾调甫先生说汉末以来,“子学流行,《墨子》固赖以保存;清谈所被,墨辩亦籍以显闻”(12)。亦正有鉴于此而指出了墨学预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情状,因为辨名析理在魏晋既已蔚成学界风气,为方法论之大宗,而周秦以来墨学与名学又渊源特深,学缘甚密(13),也就理所当然地与名家著作一起受到了重视。因而鲁胜在注《墨辩》四篇的同时,又“采诸众杂集”而撰《刑(形)名》二篇,足以说明墨学与名学已成相连传播和发展之势,都在魏晋学术、思想的主潮中活跃了起来。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关注名学固已蔚成风气,留意墨学的也绝非只有鲁胜。如夏侯湛作《抵疑》,述当时贵游、缙绅、天下之彦,“讽诂训,传《诗》、《书》,讲儒、墨,说玄虚,仆皆不如也”。魏晋间“讲儒、墨”与“说玄虚”同为时人所尚,就是因为其中往往都贯注了名理学。晋武帝时石统因忤扶风王司马骏而得罪,其弟石崇上表有曰:“所愧不能承奉戚属,自陷于此,不媚于灶,实愧王孙。《随巢子》称:‘明君之德,察情为上,察事次之。’所怀具经圣听,伏待罪黜,无所多言。”(14)《随巢子》为墨子后学的作品,石崇引其“察情”、“察事”之理为据,一方面说明此书所含辨名析理的内容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墨学地位不低足可引据。《抱朴子外篇·蔽喻》讲到葛洪曾与“同门鲁生”讨论王充《论衡》“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的问题。“属词比义”正为当时名理学所关注(15),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则表明其讨论及于墨学,且非兼通儒、墨者不能有此看法。这里的“同门鲁生”是否就是注《墨辩》的隐逸鲁胜可以存疑,但葛洪及其师门确是经常与人讨论到墨子和墨学的,《抱朴子内篇》和《外篇》中相关议论比比皆是(16)。这些事例不仅说明鲁胜注《墨辩》有其深厚背景、广泛基础而绝非绝学孤响,也直接反映了墨学在魏晋名理学盛行的潮流中颇为活跃、甚受重视的状态。
二 汉晋间对墨学的晓谙和关注
魏晋时期墨学的活跃固然与名理学盛行相关,更与长期以来墨学流衍传播的脉络相续,名理学盛行只是墨学受人关注的放大器而非前提条件,因为汉魏以来学人晓谙和关注墨学本不限于名理学,其例比比皆是。
如东汉光、明帝间冯衍宦不得志,自论有曰:“杨子号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丝。知渐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17)其“泣乎白丝”取诸《墨子·所染》篇(18)。和帝时期的宰相胡广曾作《百官箴序》,其中讲到“墨子著书,称《夏箴》之辞”(19),说明胡广必研究过《墨子·明鬼》篇(20)。卒于灵帝末年的赵咨遗书薄葬,称“墨子勉以古道”,又述“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于速变”(21)。甚崇墨学的节葬观念。同一时期,何休与其师羊弼撰写了《公羊墨守》一书(22)。其坚持《公羊》家法而称“墨守”,取鉴的是《墨子·备城门》诸篇所支持的墨子守城牢不可破之例。正是这类事例,说明《淮南子》所部分代表的“山东墨者”的影响(23),并未随汉武以来独尊儒术的过程而迅速衰竭,也把汉代与魏晋时期墨学的流播串联到了一起。
《宋书》卷二一《乐志三》载曹操作《天地间》歌词有《度关山》一首,其中有句:
侈恶之大,俭为恭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田畴传》载畴违令吊祭袁尚,曹操不问其罪。裴注引《魏略》载其时曹操下教为畴开脱有曰:
使天下悉如畴志,即墨翟兼爱、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结绳之道也。
曹操屡屡称述墨家的兼爱、尚同、节用等旨,既说明其晓谙墨学,也令人联想其节葬观念和骤然推行的相关措施,同样受到了墨学的深刻影响,这就继承和发扬了东汉以来墨学流播的势头。由此可知,魏初邯郸淳作《受命述》,歌颂曹氏“屡省万机,访谋老成;治咏儒、墨,纳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务在谐万国,叙彝伦”(24)。只能是确有所指的治道概括,说明的是当时统治者对墨学要义的关注。
另如曹植《玄畅赋》序,述“或有轻爵禄而重荣声者,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异旨,杨、墨殊义”(25)。可以看出其深谙墨家殉道之义及其与杨朱学说的对立。阮籍《咏怀诗》感慨“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26);张华《轻薄篇》有句“墨翟且停车,展季犹咨嗟”(27)。皆表明时人熟知墨学典故与要义。刘徽注《九章算术·衰分》篇“列置爵数,各自为衰”曰:“《墨子·号令》篇以爵级赐,然则战国之初有此名也。”(28)是其必甚熟《墨子》各篇。《晋书》卷九四《隐逸郭瑀传》载其为敦煌人,“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其《春秋墨说》书名似亦有鉴于何休的《公羊墨守》。又《抱朴子外篇·省烦》抨击西晋礼事繁琐,“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至于墨子之论,不能非也。但其张刑网,开塗径,浃人事,备王道,不能曲述耳;至于讥葬厚,刺礼烦,未可弃也。自建安之后,魏之武、文,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其所引墨子语,出于《墨子·非儒下》,“张刑网”云云,则出《墨子·号令》、《尚贤》、《节用》、《节葬》等篇。其《勖学》篇又述:“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仲舒命世,不窥园门。”所谓“载文盈车”,本于《墨子·贵义》篇“墨子南游使卫”而载书甚多之事。
从这些事例可以断定,墨学要义和相关典故仍是魏晋学人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仍在其学术讨论和思想表述中起着重要作用。并非庙堂之士的刘徽、葛洪精读《墨子》各篇而引据其文,更足表明汉代以来《墨子》一书绝不会是深藏中秘的“海内孤本”,而必存在着相当广泛的传承扩散脉络。(29)
三 “儒、墨连称”之例与墨学的影响
魏晋人往往以“儒、墨”连称,这类事例绝大部分都不是泛泛袭用《庄子·天下》篇等处的儒、墨连称故事(30),而是汉代以来人们公认儒、墨学说渊源极深和相互渗透的证明,也是时人习知和甚重墨学的反映,至少也是孟子式尊儒抑墨主张在很长时期内并不得势的体现。
儒、墨或孔、墨连称的习惯,根基是由于两家学说渊源有自、异中有同,其差异被凸显放大而泾渭分明,则为时甚晚(31),故汉魏以来儒生虽有抨击墨学者(32),但世人在习惯上仍常视儒、墨为一体。如汉武帝时赵人徐乐上书论政,其中谈到秦末土崩瓦解之事,述陈胜“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33)。这是以孔、墨并为大贤。《盐铁论·毁学第十八》大夫曰:“儒、墨外贪内矜,往来游说,栖栖然,未为得也。”这是以儒、墨为同类而语含讥刺(34)。班固《答宾戏》讲到“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35)。其虽用“栖栖”之典,却是以孔、墨并为圣哲。《隶续》卷一《司徒掾梁休碑》则赞休“素精孔、墨”。这些例子表明汉人连称儒、墨,乃基于战国以来儒、墨并为当世显学的背景,也基于时人对两家学说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和把握,决非人云亦云泛泛而言。魏晋时期儒、墨连称的大量语例正承此而来,具体则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况:
一是体现了人们对儒、墨两家学说要义的深刻理解。如魏晋间刘寔作《崇让论》有曰:“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36)汉代以来人们经常感慨孔、墨当年不遭世运,刘寔所述亦然。《抱朴子内篇·明本》:“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疾疫起而巫医贵矣,道德丧而儒、墨重矣。”这是以儒、墨同为入世进取之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抱朴子内篇·论仙》:
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况乎仙人居高处远,清浊异流,登遐遂往,不返于世,非得道者,安能见闻?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训,故终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
世人皆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葛洪这里则说主张“明鬼”的墨家于神鬼也“终不言其有”,再次表明其必精读《墨子》深晓其义,方能有此概括。(37)
二是说明当时学人往往以儒、墨同为入世进取之学。《弘明集》卷一牟融《理惑论》:
观三代之遗风,览乎儒、墨之道术,诵诗书,修礼节,崇仁义,视清洁,乡人传业,名誉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
这里不仅指出了儒、墨在诗书礼义上的相通处,而且把“览乎儒、墨之道术”概括为汉末以来“中士”的习惯。前面引到西晋夏侯湛《抵疑》,说时风“讲儒、墨,说玄虚”,正可与之相证。又《晋书》卷四九《向秀传》载其注《庄子》,至“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38)。点出了儒、墨在此前后的影响和声势。张敏的《头责子羽文》自嘲有曰:“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39)。所谓“中不效儒、墨”,也说明了儒、墨入世进取之道为当时一般学人所效法的状态。(40)
三是反映当时墨学与儒学地位相近而甚受重视。如《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载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等四人联名上疏举荐管宁,誉其“娱心黄老,游志六艺……韬韫儒、墨,潜化傍流”云云。所述“韬韫儒、墨”意在说明举荐管宁的依据,自非泛泛称述而已。西晋张协作《洛禊赋》述时人洛滨修禊而“主希孔、墨,宾慕颜、柳”(41)。则典型地体现了孔、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其时孔子尚未尊至极致,墨子亦非如后世之绝难比肩孔子。《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传文立、柳隐以下二十人事迹,其末譔曰(42):
若斯诸子,或挺珪璋之质,或苞瑚琏之器,或躭儒、墨之业,或韬王佐之略。潜则泥蟠,跃则龙飞,挥翮扬芳,流光遐纪,实西土之珍彦,圣晋之多士也。
这里“或躭儒、墨之业”,义与上举《理惑论》述儒、墨之道“中士所施行”,《头责子羽文》“中不效儒、墨”等例相通,然其语气极尽褒奖,足证墨学地位仍与儒相近。
儒、墨连称既是一种用语习惯,自必有其社会认识和思考背景。如果孤立地看其字面辞义,就会轻易放过这一习惯背后的种种社会内容。而若联系前面所说魏晋墨学流行和影响颇大的史实,这种用语习惯的流行,显然还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学人仍视儒、墨为同类的风气,也确凿无疑地包含着墨学地位仍与儒学相近的学术和思想背景。
四 墨子的多重形象及其为道教所托附
魏晋时期,墨子仍以多重形象为世所称,又越益为道教所关注和附会,这类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墨子事迹和墨学主张对于世人的巨大感染力,其显然不能视为墨家的“墮落”,而是墨子和墨学影响及于社会基层的体现。
方授楚先生曾论墨学对于各家学说之影响:“其直接影响而发为行动者,有许行及任侠一派;而其尚同重功利,见取于法家;节用平等,见取于道家;儒家受其影响则尤深。(43)”学术、思想层面的这种影响反映到社会上,便是墨子一身而兼具多重形象。从上面举到的例证中,可以看出墨子在魏晋仍以大贤著称,甚至与孔子并举,这可以说是墨学与儒学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当时脍炙人口的墨子行迹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大侠和大匠两种形象。
如《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载其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以书干东海王越曰:
秘之不天,值此衰运,窃慕墨翟、申包之诚,跋涉荆棘,重茧而至,栉风沐雨,来承祸难。(44)
《晋书》卷九四《隐逸郭瑀传》载张天锡遣使备礼徵瑀,其徵书有曰:
昔傅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
《抱朴子外篇·博喻》:
出处有冰炭之殊,躁静有飞沈之异。是以墨翟以重茧怡颜,箕叟以遗世得意。
这些议论中的墨子,都是急难好义,舍身救人的侠之大者,这当然也是墨家在周秦之际屡屡践行其义、悲壮殉道而感动世人的结果,足见墨子事迹的传诵与墨学要义的传播本难截然分开。至于墨子的大匠形象,见于魏晋人议论的,如《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杜夔传》裴注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有曰:
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
《抱朴子外篇·名实》:
嗟乎!彍棘矢而望高手于渠、广,策疲驽而求继轨于周穆,放斧斤而欲双巧于班、墨,忽良才而欲彝伦之攸叙,不亦难乎?
又《抱朴子外篇·应嘲》:
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
墨子的巧思精构和擅于制作,其事广见于《韩非子》、《列子》、《淮南子》、《论衡》诸书,而墨家学派本具手工业者背景,墨子之道深思而尤重践履,力行而讲求工具,墨家弟子必亦以诸巧思精构而拒强敌,益民生,践道义,这既是墨子形象熠熠生辉的又一背景,也是墨学在社会下层易得呼应流衍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这多重形象的流传于世和深入人心,汉魏以来墨子又越益与神仙家及道教关联,并开始以仙道身份著书立说、现其神迹、拯救世人而进入道教神仙谱系(45)。如《抱朴子内篇·遐览》述道书有《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又记其师郑君之语:
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
其《金丹》篇又载有“墨子丹法”:
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火熬之,以铁匕挠之十日,还为丹,服之一刀圭,万病去身,长服不死。(46)
葛洪又撰有《神仙传》,其书卷四有《墨子传》,述其从赤松子游,入山逢神人而成仙,“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五卷”。同卷《刘政传》、《孙博传》则载二人俱治墨子术而获神通。这些都说明墨子与道教的关联,到魏晋已骤然强烈起来了。
墨子被道教所托附的这类现象,曾被学者认为是墨学“变质”而趋微的标志;但从传播学角度来观察,在世间流传其多重形象的前提下,墨子与墨学趋近于民间巫鬼之道而出现变种别体,只能说明其影响甚大和活跃于世,方得流衍分枝于俗间而成相关传说的“箭垛”。若再联系墨学传播的种种史实,其又明显与当时社会上层研习和熟悉墨学之况脱不了干系,并且与之一起构成了汉魏以来墨学传播和发展变迁态势中的重要一环。至于其流传和影响于民间的分枝终于压倒其本干,《墨子》及其他周秦墨学文本也更为寥落而真成绝学,那恐怕是较晚的事情,而非魏晋时期的状态。
五 小结和余论
综上所述,结论有四:
其一,魏晋时期的墨学固然不如儒学、玄学之盛,却仍预于学术、思想界主流而流传甚广,影响甚大。
其二,魏晋时期墨学流传之况乃直承汉代而来,鲁胜注《墨辩》也绝不是墨学的绝后孤响,而自有其久远学脉、深厚背景和广泛基础。
其三,魏晋时期墨学的影响并不限于学人书斋,而是兼及于庙堂之上的现实政治和社会下层的生活空间,故其流衍变化自应存在多个分支。
其四,周秦墨家著作在魏晋时期的部分亡佚,不足以证墨学的衰微;旧式学派的不存和新撰书籍的稀少,与其学说演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绝不可贸然定其衰亡殆绝。
应当指出,魏晋墨学流播之况,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当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非儒家类子学的状态,从而提示了当时子学仍颇发达的场景,提示了清谈盛行和玄学兴起的很大一部分学术、思想背景,也提示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学与子学继续流播之间的某种共生关系。
事实上,魏晋以后墨学仍颇受关注而未迅速消沉。如《高僧传》卷八《义解五·齐上定林寺释僧远传》载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准沙门觐见之礼有曰:“臣闻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岂止敬恭?将欲昭张四维,缔制八字。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流,至于崇亲严上,厥繇靡爽。唯浮图为教,逷自龙裔……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皆当尽虔礼敬之容;则朝徽有序,乘方兼远矣。”此处有司奏谓“儒、法枝派,名、墨条流”,表明时人仍惯以诸子为说,且深知名家与墨家的密切关系。此书同卷《梁剡法华台释昙斐传》述其会稽剡人,出家受业于慧基法师,“方等深经,皆所综达,《老》、《庄》、儒、墨,颇亦披览”。是为沙门读《墨》之证。又陶渊明诗文往往涉及墨学,论者以为其有“墨派倾向”(47)。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说蕃》述“周公旦则读书一百篇,夕则见士七十人也”。此其所据为《墨子·贵义》篇(48),是人必亦熟读《墨子》。《陈书》卷三四《文学陆琰传》附《陆瑜传》载太建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作书悼之,誉其“博综子、史,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一褒一贬,一激一扬,语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尝不闻者心伏,听者解颐”。《魏书》卷八四《儒林刘献之传》述其“曾受业于勃海程玄,后遂博览众籍。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其小也!’”是其颇知“名法”与“杨墨”之内在关联,其所读群籍中必有名、墨之书。《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载其北齐时与魏收论《齐书》起元之事,其论有曰:“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是其亦读《墨子》而用于行事。至于《史》、《汉》、范书唐以前各家注文所引《墨子》之文,更是不胜枚举。
与之相应,各种非儒家类子学也还在活跃流播并影响于世,《文心雕龙·诸子》篇述《七略》著录诸子百八十余家,“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即可视为对此前子论蜂起而子学甚盛之况的概括。唐代马总《意林》(《丛书集成初编》本)前附贞元二十年抚州刺史戴叔伦所撰之《序》,谓汉代以来,“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劲案:原缺一字),盖数百千家,皆发挥隐微,忌翼风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纵横立权,变通其要”。说的就是萧梁庾仲容编《诸子抄》以前的子学流行之况。至于唐太宗命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五十卷,其中二十卷摘抄周秦和汉魏以来子书达四十七种,认为其亦有助于治道,“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则又鲜明地表达了标榜王道的贞观君臣对于子学的态度(49)。由此联系相关的种种史实,不能不引人深思魏晋以降子学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而去更为深入地考虑其存在的生态、发展的方式及其著述和著录形式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反省那种把汉魏以来的儒学与子学对立起来,又把玄学从子学中割离出来的研究框架,从而把子学重新纳入到当时学术、思想界发展演变的全景画卷中来加以认识。
注释:
①《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盖蓂荚为难蒔也,故旷世而不睹”,李善注曰:“《田俅子》曰:尧为天子,蓂荚生于庭,为帝成历。”是唐初《田俅子》一书仍以某种形式存世。
②如汪中《述学·墨子序》(收入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墨子旧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谓墨学“至楚、汉之际而微,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栾调甫《墨学研究论文集·墨子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文则认为《墨子》一书自汉代收入秘府后,已是“人间孤本”。
③如陈柱《墨学十论·历代墨学述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述鲁胜注《墨辩》,“独能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日,怀兴灭继绝之志……而其书亦已不传。岂非以世儒学重浮华,崇文而弃质故?故晋人所注之《老》、《庄》至今完好,而《墨辩》之注阙焉”。
④孙诒让《墨子间诂》俞序述孔墨本为显学,“至汉世犹以孔、墨并称”。《墨子间诂》之《墨子后语下·墨子绪闻第四》摭“秦汉旧籍所纪墨子言论行事”,《墨学通论第五》又辑战国至汉“诸子之言涉墨氏者……至后世文士众讲学家之论,则不复甄录”。观此二篇则汉代墨学未绝之况可以概知。
⑤如梁启超《墨子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八章《结论》即论及了汉人有关墨家的论说,其中特别分析了王充《论衡》对墨学的批评。方授楚《墨学源流》(北京,中华书局,1940年再版)上卷第九章《墨学之衰微》则指出了“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非顿”;认为“西汉武帝时,墨学之师承家法,犹未绝也”。
⑥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收入《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二卷上篇《汉魏间学术思想之流变》二《诸子之学重光》。
⑦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八篇《别墨》第六章《墨学结论》说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学早已消灭,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然本篇第一章《墨辩与别墨》提到了鲁胜的《墨辩注》,又说汉代学者如刘向、班固等所称的“名家”,“当日都是墨家的别派”。其间即存在着矛盾。又如栾调甫《墨学研究论文集·墨子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认为“张衡、马钧,机巧若神,然亦徒凭妙悟,不闻墨子之术。盖自汉初,墨家已绝”。然《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载其作《应闲》,内有“弦高以牛饩退敌,墨翟以萦带全城”之句。是张衡熟知《墨子·公输》篇“解带为城……守圉有余”之事。
⑧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也指出:“《文心雕龙·论说》篇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⑨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及其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⑩参田文棠《魏晋三大思潮论稿》第三章《魏晋三大思潮的方法体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所述周秦名家著作时已“亡绝”。这当然不符《汉志》和《隋志》著录的名家书之况,而只能理解为鲁胜自承兴灭继绝之任的个人看法。清代以来整理《墨子》者往往夸大其书传世的孤绝之态,不少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12)见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所收《旁行释惑·〈墨子〉书传本源流》一文。
(13)谭戒甫《墨辩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一编《别墨衡异第四》、《名墨参同第五》及其《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学徵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皆区别名家与形名家,认为两者截然不同又易混目。其论盖就战国时期而言,而《汉志》既将名家与形名家之书一概归入了诸子略的名家类,足证当时两者已经合流。另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八篇《别墨》、郭沫若《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七《墨家辩者》,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14)分见《晋书》卷五五《夏侯湛传》、卷三三《石苞传》附《石崇传》。
(15)其载葛洪之语有曰:“夫发口为言,著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艺文类聚》卷一九《人部三·言语》引晋欧阳建《言尽意论》有曰:“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两者言名理关系如出一辙。
(16)如《抱朴子内篇·金丹》述“世人饱食终日,复未必能勤儒、墨之业,治进德之务,但共逍遥遨游,以尽年月。”此以儒、墨入世与老、庄为对,亦深谙墨学之语。《抱朴子外篇·吴失》载葛洪师郑君,而郑君之师左先生有曰:“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轲、扬雄,亦居困否;有德无时,有自来耳。”这又是葛洪师门论及墨学的例证。参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第三编《语言哲学、本体论和政治哲学》第一章《识别“所以”:〈老子〉和〈论语〉的语言·曹魏时期关于语言与圣人之意的讨论》,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17)《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下》。
(18)《墨子·所染》篇载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不可不慎也”。此篇内容又被秦国墨者撰入了《吕氏春秋·当染》篇,亦为墨学的重要文献。
(19)《太平御览》卷五八八《文部四·箴》引。
(20)《墨子·明鬼下》引“《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而《逸周书·文传解》引“《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胡广意谓《墨子》引《周书》文出于《夏箴》,故曰墨子“称《夏箴》之辞”。
(21)《后汉书》卷三九《赵咨传》,李贤注:“墨夷谓为墨子之学者名夷之,欲见孟子,孟子曰:‘吾闻墨之治丧,以薄为其道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见《孟子》。”
(22)《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何休传》。
(23)《盐铁论·晁错第八》大夫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
(24)《艺文类聚》卷一○《符命部·符命》引。
(25)《艺文类聚》卷二六《人部十·言志》引。
(26)《阮步兵集·咏怀八十二首》之二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2册,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版,1990年。“杨朱泣歧路”即《荀子·王霸》篇述“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墨子悲染丝”出《墨子·所染》篇。又《晋书》卷八三《袁瑰传》附《袁乔传》载其与褚裒书有“染丝之变,墨翟致怀,歧路之感,杨朱兴叹”之句,亦用此典。
(27)《乐府诗集》卷六七《杂曲歌辞七》张华《轻薄篇》。“墨翟停车”典出《淮南子·说山训》“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汉书》卷五一《邹阳传》载其狱中上书有“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之句,师古即以《说山训》此语注之。可见“墨子停车”之典,是与汉淮南、衡山王幕下“山东墨者”发挥的“非乐”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28)刘徽、李淳风注释之《九章算术》卷三《衰分》,收入郭书春等点校《算经十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9)如王充《论衡》多处谈及《墨子》与墨学,《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载其曾“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乃来自洛阳市肆所卖书,其中应当也包括了墨家书。葛洪亦熟知墨学,其《抱朴子外篇·自叙》述其知识来源:“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洪既“贫乏无以远寻师友”,是其所读“近万卷”包括《墨子》等书,当为句容一带地方所流传者。
(30)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一文特别强调:“魏晋时虽然常常儒、墨并称……似乎墨学又与儒、道鼎立,实则此时儒墨一词仅是沿袭《庄子》中与道家相对的联称。”其实当时经学与诸子并称之例甚多,儒、墨连称现象即从属于此,许多都不是与道家相对而言;但即便是那些与道家相对而连称“儒、墨”之例,仍然可以反映墨学与儒学颇有共性,且其当时地位并不甚低的事实。
(31)《宋书》卷一一《志序》:“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是儒、墨两家著述被视为泾渭分明而“异部”著录,《七略》是一个标志。《史记》卷二三《礼书》论礼有曰:“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其论有取于《荀子·礼论》,这自然是对儒、墨之分的深刻认识,却并不是当时的普遍看法。如《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弘为举首。”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人们尚视之为“以广儒、墨”。
(32)如扬雄自比孟子,其《法言·吾子》篇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闢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同书《五百》篇则述:“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载其作《傅子》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当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
(33)《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传》。《汉书》卷六四《徐乐传》述之为“孔、曾、墨子之贤”。其语盖袭贾谊《过秦论》而来。
(34)《盐铁论·论诽第二十四》文学抨击秦政“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
(35)收入《文选》卷四五《设论》。又《后汉书》卷三○上《苏竟传》载其建武初与刘歆兄子龚书,晓以大义,内有“仲尼栖栖,墨子遑遑”之句,亦用此典。
(36)《晋书》卷四一《刘寔传》。《抱朴子外篇·审举》述汉来选举紊浊,“于是曾、闵获商臣之谤,孔、墨蒙盗跖之垢”。亦然。这类言论实承自汉人,如《史记》卷八三《邹阳传》载其狱中上书有曰:“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刘向《新序·杂事第三》亦述邹阳此书,而语作“夫以孔、墨之辩而不能自免,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可见这类话题汉代甚众。
(37)核之今存《墨子·明鬼下》篇结语云:“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这里“若鬼神之有”与孔子的“祭如在”不异,可见《论仙》的概括准确无误。
(38)《抱朴子内篇·金丹》述“世人饱食终日,复未必能勤儒、墨之业,治进德之务,但共逍遥遨游,以尽年月”。也是对西晋末年老庄盛而儒、墨鄙的写照。
(39)《艺文类聚》卷一七《人部一·头》引。
(40)《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范宁传》载东晋简文帝前后,“时以虚浮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或曰黄唐緬邈,至道沦翳,濠濮辍咏,风流靡托,争夺兆于仁义,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怀超绝,辅嗣妙思通微……’”所述“是非成于儒、墨”亦表明了两家学说在魏晋时期的影响。
(41)《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中·三月三日》引。
(4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一《后贤志》校“譔”字元丰、《函海》本作“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3)方授楚:《墨学源流》上卷第九章《墨学之衰微》。关于墨学对儒学的影响,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重编版《经学抉原》)认为汉以来儒家重明堂、重《孝经》及《礼运》大同之义,实皆本于墨学而申说之。
(44)此“重茧”指《战国策·宋策》等处述墨子救宋,“百舍重茧”,自鲁赴楚见公输般之事;《淮南子·修务训》亦述墨子是时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其后文又曰:“宋墨、楚申,以载驰存国;干木、胡明,以无为折冲。”
(45)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所收《旁行释惑·〈墨子〉书传本源流》一文指出:“李少君乃假《墨子》致物之术,淮南亦钞《墨子变化》为枕中鸿宝。迨后道流方士,造作并出,由变化而服食,墨子遂列《神仙传》而入于道家。”由此推论墨子与神仙家或方士的因缘,似亦隐隐与淮南、衡山王治下的“山东墨者”相关。
(46)《隋志》子部医方类著录有《墨子枕内五行纪要》一卷,原注云:“梁有《神枕方》一卷,疑此即是。”
(47)景蜀慧:《读〈山海经〉十三首与陶渊明思想中的墨派倾向》,《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48)《墨子·贵义》篇:“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劲案:七也)十士。”此典时所常引,故《艺文类聚》卷五五《杂文部一·读书》首列“《墨子》云:周公朝读百篇,夕见七十士”。
(49)魏征等奉敕撰《群书治要序》,收录于国学基本丛书本《群书治要》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